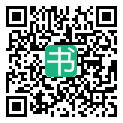第六章 深夜狗肉香
建宁县果然被大水淹得彻底,阿茕目之所及处皆苍茫,她缓缓吁出一口浊气,寻了个人少的地方下水。
阿茕不懂玄学周易,故而并不知晓,羊胡子老者究竟在算些什么,即便头脑清醒,听了他们的对话仍无法作弊,轮到她的时候,只能如实报上自己真实的生辰八字,以免时运不济因瞎报而错过什么。
阿茕本以做好了全面去应对的准备,岂知那少年下一刻竟道:“既然如此,那你走吧。”那少年话锋着实转得太快,以至于阿茕一时间都未能反应过来。
少年面上笑意不减,若不仔细去探寻,定然会教人觉着他心情不错,他道:“你猜。”
阿茕搁下碗筷,一摇头,道:“吃饱了。”
被夺了碗的阿茕非但不气,反倒松了一口气,倒是二丫的眼睛明显湿润了。
阿茕伸手戳了戳她脑门,笑着打趣:“自然是和我一同走回来的呀,你呀你,八成是被肉香给熏昏了头吧,竟然连这都回想不起来。”
他这般寸寸逼紧,阿茕着实应付的吃力。
遭受过上一次的惊吓,阿茕死都不会忘记这个声音!
阿茕既已豁出去,又哪会这般轻易地妥协,纵然被人扫地出门,仍紧咬牙关,像条死狗似的趴在门外,只要少年一出门,她便像块牛皮糖似的黏在其身后,少年去哪儿,她跟着去哪儿,惹得那少年几度生出想杀人的冲动。
她顺着香味一路前进,最终又停在当日看到铁锅的那片空地上。
陆九卿神色不变,倒是白为霜见着阿茕这样一副打扮神色颇有些古怪,他三言两语打发走了陆九卿,拧着眉头对阿茕道:“你怎穿成这样?”
阿茕心脏几乎都要跳出来,她力气不大,着实没办法抱着一个十岁大小的女孩子逃命,无奈之下只能拖着二丫躲进草丛里。
阿茕险些踏进他的圈套,不过迟疑了一下,便想到了这层关系。
阿茕如今正躲在草丛里,并不清楚那边所发生的事。
考验阿茕演技的时刻到了,她一副遭人诬陷的悲愤模样,毫不畏惧地回视少年的眼睛,气势汹汹道:“你这什么语气?我既没做贼,又无梦游的恶习,究竟睡没睡你难道还能比我更清楚?”
阿茕若是承认自己躲起来了,他又能抛出一堆问题,将她逼得现行。
才欲躺下睡觉的阿茕突闻一阵异香,细细分辨便能发觉,这股子异香与当日所闻到的狗肉味无异,她不禁神色大变,腾地自草垫上爬起,跨过众人熟睡的身体,蹑手蹑脚闻香而去。
阿茕这货倒是机灵得很,每瞧少年脸色不对她便主动消失一会儿,待到人气消了,她又阴魂不散地出现,继续纠缠。
闻起来有几丝辛辣味,且不似寻常蘑菇那般鲜香,阿茕也不知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却莫名其妙联想起数日前,那只被人拔光毛的歪脖子鸡,那时候白为霜似乎与她说过,那歪脖子鸡之所以受人操控,正是因为被喂食了一种致幻的毒蘑菇。
阿茕连忙笑着走了过去,不胜感激地与那人道:“有劳了。”
这事恰好与陆九卿回的那句“城中乞儿有古怪”,相对应,此外陆九卿又恰恰好在此处,着实让阿茕心生怀疑,怀疑这个决定究竟是白为霜做的,还是陆九卿做的,可若是陆九卿做的决定,白为霜又为何要照做呢?
看着夜鸦的身体渐渐远去融入夜色里,阿茕的那颗心始终悬在嗓子眼,怎么也沉不下去。
这一下几乎要将阿茕吓得魂飞魄散,她不明白自己怎就被这少年给发现了,她穿男装和女主区别分明那么大,甚至连江景吾都无法一眼分辨出,那少年又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
阿茕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走了过去,边走还边用眼角余光来观看四周,除却那个打狗肉的糙汉子,这片空地上只有阿茕及一群虎视眈眈盯住狗肉的灾民,那个多番出现的古怪少年并不在此。
她抵达世子府已是一盏茶时间以后,纵然世子府管家与阿茕已混熟,见到穿女装的她仍是一愣,半晌方才反应过来,闹明白这竟是陆大人。
不过片刻,便有一人缓缓走了过来,恰好停在她前方,她紧张到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手指已经下意识搭在右手手臂上,那里藏了支袖箭,实在不行,她掰动手扣,一箭射死那人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如此一来,她想要混入乞儿窝将会变得越发不容易。
瓢泼般的大雨仍在继续下个不停,阿茕不知自己究竟呛了多少口水,亦不知自己究竟抱着这根圆木喊了多久,只知天将黯下之际,终于有人伸出一根竹竿,将她拉到岸上去。
这顿朝食阿茕可谓是吃得心惊胆战。
阿茕毕恭毕敬朝白为霜行了个礼,方才笑吟吟地望向陆九卿。
在她即将抵达拐角处之时,身后陡然传来一阵音律古怪的笛音,而那原本乖巧听话的二丫却像突然中邪一样睁开阿茕的手掌,转身往回走。
阿茕莫名其妙成了个异类,才走一半的路,又听到了那个嗓音,与此同时,她能明显地感受到一道森冷的目光在她身后游走,像是背后蛰伏了一条毒蛇。
近段时间阿茕都与这伙人混在一起,白日一起领粥喝,夜里一同睡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
不知身后少年究竟有何用意的阿茕身子陡然一僵,身体比脑子先一步做出反应,顷刻间便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假装自己被笛声所操控,学着前方人那般不慌不忙往马车上爬。
只是今日怕是就此为止了,先不说凭借她一己之力可能找到那所谓的圣地,即便真让她找到了,怕是连有没有命下这阴山都不得而知,思及此,阿茕直接舍弃了再寻圣地的念头,随意寻了个碑文已模糊到完全看不清其上文字,且爬满杂草,明显就无人来祭拜的墓,“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嘶www.hetushu.com.com声哭喊着:“娘,女儿来看你了!”
突逢此变故的阿茕又是一愣,几乎就要露馅的她脑袋飞快运转,脑中突有灵光一闪,回想起当日的场景,那时候二丫已然被笛声所操控,她非要拖着二丫走,于是二丫整个人都暴躁了,发疯似的挣扎着。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事发五日后的一个深夜,叫她再度撞上。
二丫被阿茕看得不自在,忙问道:“阿桐哥哥,你在看什么呢?”
阿茕冻得直打哆嗦,手臂紧紧地抱住一根漂浮在水面的圆木,直喊救命。
虽无确凿的证据证实眼前这碗狗肉汤中的蘑菇可致幻,阿茕却再也无法淡定了。
自从被那少年骚扰后,阿茕在阴山之上走得越发小心翼翼。
这来历不明的神秘狗肉一时间成了北街灾民棚中最时兴的话题,既有谈“笛声”与“狗肉”二字色变者,又有经不住香肉的诱惑,想暗夜食狗肉者。
直至笛声完全飘远消散,阿茕方才挪了挪身体,目光下意识地往某处一瞥。
她反正也不是什么要脸之人,索性一掐自己大腿,“哇”的一声哭出声:“求求你不要赶我走……”
食下狗肉的灾民们仿佛被这笛声给勾去了心神,一个个乖顺听话地排队跟在吹笛人身后走,以阿茕来听,只觉笛声诡谲古怪,也不知落入那些食了毒蘑菇的人耳中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
前两个问题不过是少年对阿茕的试探,说是可有可无也不为过,第三个问题方才与阿茕动了真格,他道:“那天晚上你为何要躲起来?”
今夜明明有些微凉,阿茕却出了一身的冷汗,夜风扫过,那些肌肤即便被衣服所遮盖,仍是起了一身细密的鸡皮疙瘩。
阿茕又岂看不透他的心思,并未直接作答,而是装作一脸迷茫地问道:“你是说哪个晚上?”
而今尚未入夏,冰冷的河水漫过胸口,寒意瞬间钻入骨头缝里。
阿茕既已豁出去,又哪会这般轻易地妥协,纵然被人扫地出门,仍紧咬牙关,像条死狗似的趴在门外,只要少年一出门,她便像块牛皮糖似的黏在其身后。
阿茕犹自天人交战,那人却不曾展开任何行动,一直静静站在这里,又隔半晌,方才低低笑了一声。
阿茕悬起的心终于微微落了地。
除此以外,阿茕莫说再遇到那少年,即便是那诡异的笛声与诱人的狗肉都再未出现过。
只不过阿茕时常能从别的灾民口中听到有关那狗肉与笛声的传闻。
那声音算不上大,恰恰好清晰地传入她一个人耳中:“果然是你!大哥哥,我们可真有缘啊。”
将她摇醒之人名唤二丫,正是那名救她的粗汉子的女儿,今年刚满十岁,很是喜欢黏着阿茕。
“挺好的呀。”二丫一派天真,复又回想起什么似的,不开心地嘟嘴抱怨着,“不过从醒来到现在都脖子疼,明明都没有枕头呀,怎就落枕了呢?”
“第二个问题,你究竟是何方人士?当日明明在阴山扫坟,现在又怎成了建宁县的灾民?”
阿茕心跳几乎都要漏了一拍,少年却又在这时候轻笑出声:“你脸色变得好生奇怪呢,我不过是说着玩玩罢了。”
这只夜鸦恰是她与陆九卿的传讯工具,既然它来了,也正说明陆九卿回了她先前传出去的信。
短短七个字写得没头没尾,阿茕根本不知究竟是在回复她先前寄出的那封信,还是陆九卿下达的另一个指令。
少年仍不为所动,阿茕急了,索性豁出去,厚着脸皮抱住少年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着,噼里啪啦说上一通,诸如她小时候如何如何苦,先是没了娘,后又没了爹,总之怎么惨就怎么说。
这少年倒是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一听便道:“我想,你也确实聪明不到哪里去。”
少年听罢摊摊手,笑得一派和煦:“这就得由我来问你,为何会出现在狗肉摊前了。”
阿茕倒是真这么想啊,可眼前这架势,又岂有她说是的余地。
当日入夜。
她屏息凝神躲在草丛里。
阿茕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才欲转身离开,又被白为霜喊住,转身停了下来。
阿茕仍不曾收回目光,斟酌着问了句:“你昨夜睡得可好?”
阿茕又急又气,索性豁出去了,两眼发直望着桌上的粥和包子,一派天真无辜地道:“我饿得都没力气说话了。”
她不动声色将周遭打量一番,确认四周无人后,方才解下绑在那夜鸦腿上的竹筒,取出一张寸许大的条子,上面只简略写了一句话:“城中乞儿有古怪。”
这少年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性情古怪,脾气也是阴晴不定的,上一刻还笑眯眯,下一瞬瞧见阿茕摇头不肯走,就已危险地眯起了眼睛,沉着一张脸问阿茕:“你莫不是想一直赖在我这里?”
阿茕一愣,又顺势夹起那干蘑菇放置鼻端闻了闻。
此时此刻,阿茕的睡意已然完全被冲散,已然清醒的她本生出了退却之意,下一瞬便被二丫领着拐了个弯,弯道后是一块长满青草的平地,平地上摆了一口大铁锅,锅中大块大块的狗肉与沸汤一同翻滚,那诱人的香就像长了翅膀的钩子,不停钩着人往前移。
猜你个大头鬼!
少年从头至尾都不曾说话,就这么居高临下地默默看着她,直至阿茕再也挤不出一滴眼泪,开始扯着嗓子干号时,少年终于没法忍了,冷酷且无情地拎着阿茕衣领,丢垃圾似的将其一把丢出门外。
阿茕计划被打乱也不气馁,安安静静地坐在车内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阿茕下意识坐直了身体,不多时便听少年道:“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名字。”
阿茕听罢不禁莞尔一笑,又道了句:“有劳了。”
她茫然回首,却听白为霜道:“潜入乞儿时
https://m.hetushu•com•com,你莫要再穿女装了。”二
实际上她正在竭力思索对策。
阿茕回到天水府的时候已至黄昏,她才欲往世子府赶,便径直飞来一只两掌大小的夜鸦。
当天夜里阿茕便写了一封信,绑在夜鸦腿上,连夜传给陆九卿。
阿茕拍拍二丫的脸颊,才欲说几句话来安抚她,便又听那炖狗肉的汉子道:“那个没吃到狗肉的过来,俺再给你盛一碗。”
随着那道声音的落下,原本就显古怪的笛音愈显诡谲,而那一直站在阿茕身前的人也终于迈步离开。
她拧着眉头,眼珠微微往上翻,一副陷入回忆中的模样。
她这理由着实找得莫名其妙,少年非但不戳穿,反倒笑得越发灿烂,道:“既然如此,你先过来吃,吃饱了再与我细细解说。”
楚地向来潮湿多雨,临近的建宁县已然闹了洪涝,近日已陆陆续续有灾民逃至天水府,再过几日怕是会来得更多。
如此一来阿茕越发放心了,她排队站在最后,领了狗肉便假装大口大口吃起来,暗地里用眼角余光观察在场所有人,细细分辨那些食下狗肉者的每一个表情和反应。
阿茕不知,上了马车究竟会被带往何地,不禁有些心急,在她即将跟在众人身后爬上马车之际,身后突然传来个熟悉的声音。
这话也不知究竟是说给阿茕听的,还是说给那汉子听的,阿茕犹自内伤,下一瞬便被人抱了起来,至于抱她之人究竟是少年还是粗汉子,她也不得而知,她只知道自己后来又被人抱上了一辆马车,再然后……她竟莫名其妙便睡着了。
以及,她若是否认了,少年却是实打实地看到了她,她又该如何圆回这个谎。
救阿茕的是个年近三十的粗汉子,嗓门大心却细,瞧阿茕面色苍白脚步虚浮,连忙将其背至一间临时搭建的草棚中。
包括阿茕与二丫在内,这锅狗肉共引来了近二十名灾民,每一个都饱受水患之苦,莫说是吃肉,连粥都喝不饱,而今再嗅到这诱人的狗肉香,哈喇子早已流了一地。
即便那少年已走远,阿茕仍未起身,心有余悸地捂着胸口,生怕他突然又杀了回来,抓她个措手不及。
她茫然睁开眼,挣扎了好一会儿,方才看清楚眼前之人,于是,颇有几分不解地问:“怎么了?”
阿茕的目的便是混进灾民群中从而潜入乞儿窝,连夜赶路什么的虽令人痛苦了些,她却对此无任何异议。
她话音才落,那羊胡子老者便开始用她的生辰八字进行演算,待到得出结果后便与身边人道了句;“带走。”
天将欲黑的时候,带着阿茕在街上乱晃了一整日的少年方才回到自己的院落。
已然打定主意要下山的阿茕又号了几声,方才给那座无名氏的坟上了一炷香,又不着痕迹偷偷观看一番,方才挽着竹篮,三步一回头地往山下走。
锅前依旧站着个声音粗粝的糙汉子,而他身前则是一群被肉香搅乱心神的灾民,犹自排着队打狗肉。
阿茕最后一个上车,三辆马车倒是恰恰好坐下了十八人,阿茕本想在车内暗中记下路线,岂料一推开车门便见车中还坐了个彪形大汉,显然是用来做监视的。
阿茕面有戚戚然,摇头如拨浪鼓,死活不肯走。
这个问题更好答,阿茕甚至都不需要太过刻意地去组织语言,直接将阿桐的身世说与少年听,便已糊弄过去。
随着她这么一跪,紧随其身后的脚步声陡然就停了下来。
一
此处草木葱郁,夜色又黑,即便那伙人追了过来,怕也得费上一番工夫将她与二丫找出。
少年的目光始终聚集在她身上,他虽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却没来由给阿茕一种,豺狼虎豹在盯梢猎物一般的错觉。
建宁县的的确确有阿桐此人,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女,既无亲朋好友也无相熟的邻居,独自一人居在深山里,堪称与世隔绝,除此以外,这个阿桐的母亲又恰恰好是天水府人士,一切都是白为霜替阿茕安排的,即便这少年有心去调查,也查不出任何纰漏。
瞧二丫的反应倒还依旧正常,只是不知昨日的事她还记得多少。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阿茕也算是稍微摸清了这少年的脾气,她在他面前不是不能耍赖,只是得有底线,只要不超过这个底线任凭她如何闹腾,那少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可一旦超过这个底线,阿茕毫不怀疑,自己定会落着个极为凄惨的下场,万一将其惹怒,被一刀子给捅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这种话当然只能在心中默默吐槽,阿茕亦朝他粲然一笑,道:“我笨,猜不出。”
他那眼神着实看得人心中发毛,阿茕不敢与他对视,又不想继续纠缠下去,索性假装踩到了石子,“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闭上眼睛装晕。
这一笑几乎让阿茕身上所有的毛发都炸了起来,阿茕分不出心神去抚平自己手臂上的汗毛,左手食指已然开始施力,就要按下去……
阿茕登时急得想要挖个坑钻进去,却仍是一派淡然地端着狗肉汤,牵着二丫离开。
阿茕有样学样,手中破碗“哐当”一声落地,两眼发直望向前方。
她甚至不敢去想,倘若她真承认了,而那少年又压根没看到她,将会发生怎样的事。
阿茕不敢松懈,边吃边思索对策。
白为霜说是与阿茕商讨此事,却全程都皱着眉头,一副十分不愿让阿茕去办此事的模样。
更令阿意外的是,陆九卿今日竟也在世子府。
她一只脚才踩上踏板,身后却陡然传来一股巨力,那少年竟一把拽住了她胳膊。
一旦入夜城中便会设宵禁,这伙人时间倒是掐得和图书准,天才刚刚亮,一伙人便已赶至城楼下。
会说这话的,除却那古怪的少年,还有谁?
阿茕几乎一整夜未眠,直至天之欲亮,方才困得睁不开眼,昏昏沉沉睡了去。
阿茕又不是白为霜肚子里的蛔虫,自不晓得白为霜究竟在嫌弃什么,也懒得去纠结他到底是在嫌弃什么,才欲与其说自己今日所闻,他便正了正神色,道:“你来得正好,本王恰有事要与你商讨。”
这样的日子一连过了三日,直至第三日入夜,那双暗中观察的眼睛方才按捺不住,终于撒网开展行动……
许是二丫也意识到自己的眼神太过赤|裸裸,当即便羞赧地低下了头,小声询问阿茕:“阿桐哥哥,你怎不吃呀?”
雨下至半夜便停了,蜷缩在茅草棚中睡得正酣畅的阿茕突然被人摇醒,原来这伙人打算趁着雨停了,连夜赶往天水府。
才从地上爬起的阿茕只觉眼前这小鬼将皮笑肉不笑发挥到了极致,先是被他脸上的笑吓得整个人都僵了一僵,随后方才开口询问那少年,自己而今身在何处。
“原来会这样啊……”二丫拖长了尾音来感叹,眼睛仍是黏在阿茕手中的破碗上。
就在她沉默的空当,那少年又说话了,他直勾勾地望着阿茕的眼睛,道:“你怎不说了?是因为心虚还是怕说多了露馅?”
她不明白,脑袋里犹自一片混乱,正思量着该不该一箭射死他。
阿茕不比这些来自建宁县的平头百姓,打她头一次开始领粥喝,便发觉人群中有双暗中监视他们这伙人的眼睛。
这纸条上自是写了阿茕昨夜所遇之事,顺便还提了下那个古怪的少年,也不知她将这纸条传出,多久才能等到回复。
一盏茶工夫后,桌上粥碗碟盘已然见底,阿茕再也找不到理由继续拖延时间,那少年的声音适时响起,他就像个体贴的小弟弟般询问阿茕:“吃饱了没有,可要再添一碗?”若能忽略掉他眼中的调侃之意,怕是真会阿茕误以为他在关心自己。
他这话语里满满都是嫌弃,也不知他究竟是在嫌弃阿茕穿女装,还是在嫌弃阿茕这一身太过邋遢。
她强行压制住不断翻涌而上的恐惧,步伐越发稳重,握住二丫的手掌却在不停地冒汗。
少年不曾搭话,阿茕哭得越发凄惨,简直闻者伤心见者落泪:“我已无家可归,若是连你也不肯收留我,我便只能再次流落街头了……”
阿茕记性向来好,她又岂会不记得,这把嗓音正是当日在阴山上一路跟踪她的少年的声音。
约莫又过了近半个时辰,阿茕方才松懈,揉了揉已然开始发麻的小腿,卖力地抱着二丫往回走。
她才这般想,二丫便又上前一步脆生生地喊了声“阿桐哥哥”。
若不曾发生过什么刻骨铭心之事,一个心中无鬼的人怕是很难在第一时间回想起,自己五日前的晚上做了什么事,又身在何方。
天水府内的灾民几乎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减少,有些人失踪了还会再度出现,乍一看与从前无异,当有人问起他们去了哪儿时,便笑得一脸神秘,只道:“一个有趣的地方,莫急,你们也会有机会去,只需吃上一碗狗肉……”
而那些失踪了的人则是彻底得消失,仿佛突然之间便蒸发在人间。
用过午膳后,阿茕便马不停蹄地连日赶至建宁县。
接下来几日,阿茕一直混在灾民群中。
所以,她方才就这么大剌剌地穿着女装在白为霜与陆九卿二人面前瞎晃!
二丫神秘兮兮地拽着阿茕的胳膊,压低了声音道:“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可大伙儿都悄悄往那儿钻,我便想叫你一起去看看。”
二丫的目光早已被那白花花的粥所吸引,压根不曾去注意,也无从注意,阿茕方才塞给了那施粥人一张纸条。
阿茕眼睛盯着前方的布粥之人,顺着杆往上爬,道:“大抵是的吧,都怪哥哥又起晚了,也不知现在的粥还稠不稠。”
阿茕向来就有早睡的习惯,一贯睡得早的她又早早陷入了黑甜乡香,犹自睡得昏沉之时,又有个人在拼命将她摇醒。
她提着纸钱香烛等物又围着山顶找了足足一整圈,仍是未能找到所谓的圣地。
白为霜这话说得没头没脑,却叫阿茕如遭当头棒喝,她竟一直都没反应过来,自己而今穿的是女装!
越是跟着二丫往前走,越觉前方肉香扑鼻,阿茕不禁吸了吸鼻子,不足片刻便已分辨出此乃狗肉香。
那双眼睛究竟出自何方势力,她也不得而知,只是暗自庆幸打一开始便选对了路。
阿茕不敢将他逼得太急,并未尾随跟着一同进去,像个二傻子似的杵在门外呆呆望着。
阿茕试图将二丫拖回,她却又哭又喊,手脚并用地挣扎,动静着实太大,害怕将身后吹笛之人引来的阿茕只得狠下心将她劈晕。
十六七岁的少年已比阿茕高出半个头,力气自也比阿茕大上不少,他游刃有余地化解着阿茕的攻击,嘴角挂着一抹淡笑,眼睛里却始终冰凉一片。
他这问题问得不清不楚,看似简单,实则处处是陷阱。
最最主要的还是,她又岂能这般轻易地走,好不容易才摸到这里,若是走了,岂不前功尽弃?
少年也不与阿茕卖关子,直言道:“五天前的那个晚上。”
阿茕才欲出口的话,又一下子被咽回了肚子里。
下车后,呈现在阿茕眼前的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空地,空地上摆了一张方桌,桌前坐着一名手持毛笔的羊胡子老者。
阿茕莫名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简直恨不得将自己掐死来泄愤。
她心中尚有困惑,不明白大晚上的会有谁跑来外面炖狗肉,二丫已然止不住地咽口水,加快速度领着她走,边走边道:“快到了,我方才就是看到铁柱他们从这儿拐弯的。”
所以,白和*图*书为霜到底知不知道陆九卿已然知晓她的身份,而陆九卿又可知晓白为霜已揭破她身份之事?
少年目光寒如冷月,脸上却带着盈盈笑意,他道:“小姐姐,你我怎这般有缘?”而后又是一笑,“不对,你今日穿的该是男装吧,我现在得喊你小哥哥才是。”
这一幕让阿茕恍然觉着回到了上一次,只不过这一次她身边并未带二丫,即便有危险,她应对起来也方便。
今日粥棚前明显少了很多人。
她跪在坟前,一边组织着语言絮絮叨叨与这座完全不知葬着何人的坟茔说话,一边斜着眼,用眼角余光观察身后之人的动向。
眼看就要消耗掉大半个月的时间,阿茕不禁有些心急,近日来四处与人打探何处会再度出现那口盛满狗肉的大锅。
马车行驶近半盏茶工夫,突然停了下来,那些食了狗肉的灾民纷纷在笛声的操控下走下马车,阿茕亦如此。
草棚中燃着火堆,火堆旁围了近十人,有老有少,皆是受难的建宁人。
她微微皱起眉,一点点回想起昨夜之事,全然不曾发觉那个少年正坐在不远处淡然喝粥吃包子,她将昨日之事全部从脑子里过了一遍,方才慢吞吞从地上爬起。
听阿茕这么一说,二丫越发疑惑,不过这小姑娘性子单纯,亦不是个认死理会钻牛角尖的主,既然她阿桐哥哥都这般说了,那么她也不必再去想什么,于是便朝阿茕甜甜一笑,亲昵地牵着她的手,一同前往粥棚。
低头享用朝食的少年明显发觉阿茕已然清醒,微微侧着脑袋,笑眯眯地望向她。
阿茕暂时辨不清尾随自己者是敌是友,也无从确认可还是那少年,心中着急,面上也依旧装出副急切的样子。
她本欲打翻二丫的碗,叫她别吃,一撇头竟发觉二丫的碗已然空了,正眼巴巴地望着她手中那碗满满的狗肉。
有了先前被人跟踪的经历,这次她比之前要走得更谨慎,边走边用眼角余光去感受,可有人在继续跟踪自己,果不其然,未过多时她便发觉有人尾随在自己身后,那人一路跟得紧,总之,不论阿茕走得快还是走得慢,他都能悠然跟在其身后,也不知其究竟有何目的。
一整日就这样过去。
临近辰时三刻,阿茕方才被准备拎着碗去讨粥喝的二丫推醒。
待到再一次醒来,她便发觉自己正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房间里,背后是坚硬而冰凉的地板,头顶是一片黛色青瓦。
不仅仅是阿茕觉着奇怪,就连二丫都感到困惑,睁大了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问阿茕:“阿桐哥哥,是不是我们今日来得太晚了呀,怎只有这点人?”
阿茕只得苦笑,道:“我吃不了狗肉,一吃就出热疹。”
阿茕就这样两眼发直地跟在一行人身后走,七绕八绕地拐了个弯后,前方的人便停了下来,三辆毫无任何特色的马车缓缓行来,停在吹笛人身前。
天底下不会存在掉馅饼的事,这些人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却早已在这锅狗肉面前丧失了理智,眼见而今的局势就要演变成灾民哄抢狗肉,那一直低头炖狗肉的汉子终于抬起了头来,他朝大伙露齿一笑,慢条斯理地道:“别急,别急,都有,排队来领,一人一碗不多也不少。”
那夜天色太黑,她并不能完全确认少年究竟是真看到了她,还是在虚张声势。
少年依旧皮笑肉不笑盯着阿茕,懒懒道了两个字:“是吗?”
容不得阿茕多想,眼看最后一个人都排队跟在了那吹笛人身后,阿茕连忙跑过去,跟在最后,跟在最后一个倒是方便她做事,若是出了什么意外,悄悄跑走也不容易被发现。
阿茕拧着眉头思索片刻,便随手将这张条子给毁了,直往世子府所在的方向走。
白为霜要与阿茕商讨的便是,叫她混迹在灾民中,想法子打入天水府内乞儿窝内部。
阿茕听得几乎都要翻白眼了,又听他道:“你如今正在我的住处。”
那人一拐一拐地从暗处走出,不曾停歇地吹着骨笛引诱着世人。
约莫半盏茶工夫后,食下狗肉者眼神开始涣散,一个个犹如木头人似的杵在原地。
阿茕嘴角含笑应了声,二丫又突然神秘秘地凑了过来,特意压低了声音道:“其实我觉着昨夜很奇怪哎,我只记得昨夜带着你一同去吃狗肉了,却怎么也想不起究竟是如何回来的,阿桐哥哥,你还记得吗?”
这一眼几乎要叫将阿茕吓得魂飞魄散!她身侧竟站了个人,那人即便逆着月光,她都能根据他面部的轮廓判断出,他便是那名少年。
少年面不改色,毫不留情地拒绝:“我连一碗面的钱都付不起,哪还养得起你?”
今夜所发生之事非同寻常,她定然要传讯告之陆九卿,至于白为霜那边,她自也会想办法去与他传讯。
她既不知那人的目的,自然就无法轻举妄动,她声嘶力竭地在坟前号了老半天,身后之人都无任何动静,一直都不曾进行下一步。
这声带走可谓是让阿茕心惊胆战到无以复加,一行十八人中仅有一人被留下,其余十七人则再度被引回马车上。
这个问题好答的很,阿茕不假思索道:“阿桐。”
阿茕若是直接否认自己躲起来了,他便能见缝插针,从而逼问阿茕又岂知道他问的是那天晚上。
白为霜只是让阿茕混入灾民中,并未叫她这般做,她却觉着,既然都已经开始做戏了,便要将整场戏做全,她这般做来所耗时间虽多,甚至极度危险,却给自己制造了充足的证据,这样的天灾之中,建宁县所有户籍定然都被大水冲走,即便有人怀疑她身份作假,也拿不出任何证据,她反倒能将今日所见的所有人都变作她的证据。
最后一个字才溢出口,远处便传来一个不甚陌生的嗓音,懒散中带着一丝倨傲。
少年盯着阿茕https://www•hetushu•com•com的眼睛,将“阿桐”两个字细细嚼了一遍,方才开始问第二个问题。
有了这话,原本蠢蠢欲动的灾民顿时安静了,竟真的老老实实排起了队。
少年的目光从未离开阿茕,他眼神如刀,一寸一寸在阿茕身上扫,半晌方才道:“剁碎,喂狗。”
阿茕更觉无奈,不明白自己怎么又招惹这位大爷了。
而那群食下狗肉者则在笛音的操控下乖巧地站在老者身前排队,她虽看不到老者究竟在做什么,却能清楚地听到其声音,她在与食下狗肉者询问其生辰八字,再用那些人的生辰八字加以推算。
如此一来,阿茕倒也有了初步判断,首先排除掉那人是劫匪,想半路打劫抢人钱财的可能性;其次,又排除那人想取她性命的可能。最终,阿茕将那人与昨夜的挖坟人捆绑在一起,乃至今日所遇到的那个少年,她也隐隐觉着其定然与那两个挖坟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指不定他们还就是一伙人,只不过阿茕暂时缺乏证据来证明这个推测。
她本欲开口解释,微微张着嘴,欲言又止地望了白为霜都能解释出个所以然来,只得作罢,更遑论白为霜也一副不想与她多说的模样,二人眼神才撞上,他便回以她一个白眼。
近些日子已陆陆续续从建宁赶来好几批灾民,镇守城门的将领非但没将这伙人赶出去,反倒告知他们,楚世子在哪些地方开仓施粥,叫他们快些赶去打粥喝。
阿茕一时间想不通,紧接着又听白为霜解释了一句。原来他上次埋下的眼线也已经摸到乞儿窝与吸血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嘿,既然你小子吃不了,倒不如让俺来替你分担分担!”一道粗粝的嗓音突然从身后传来,阿茕甚至都未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便冲出个陌生男子,一把夺走她手中盛狗肉的破碗,开始大快朵颐。
她演技着实不错,说倒就倒,摔得毫无含糊,以至于镇守在马车外的汉子看着她摔便觉肉疼,又隔了片刻,方才躬身询问那少年该如何处置已然“晕倒”的阿茕。
笛声并未停止,伴随着一阵清晰可闻的脚步声越离越近。
甫一睁开眼便瞧见二丫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阿茕眼睛里出现了一瞬间的迷茫,片刻以后方才全然清醒,第一反应竟是瞪大了眼睛将二丫从头到脚打量一遍。
她的疑虑太多,围绕在她眼前的迷雾散不尽,又该如何入睡?
她这般做虽有些,却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
阿茕连忙又道:“我不用你养的,只需留一处干净的地给我睡便好,至于吃的,我可以去街上领呀,我很能干的,既可替你洗衣做饭,又能劈柴挑水。”
阿茕这番话倒是说得颇有几分气势,以至于少年还真垂下眼眸去沉思了一番。
锅中狗肉尚剩一半,那些吃完狗肉的灾民仍杵在原地,眼巴巴望着。
如此一来,阿茕越发怀疑这狗肉中是否藏着什么秘密,否则那炖狗肉之人又岂会观察得这般仔细,甚至还要给没吃到的人补上一碗,怎么看怎么都觉诡异。
阿茕向来不喜吃味道太重的肉类,纵然被二丫逼着领了一碗狗肉,仍无法下咽,更何况,她总觉得整件事都透露着古怪。
她用筷子在装狗肉的碗里不停地搅,这本是个无意之举,却不想真让她在碗里搅出一朵不甚完整的干蘑菇。
阿茕寻白为霜心切,管家又是个能藏得住情绪之人,以至于见到白为霜那一刻,阿茕都未能反应过来自己仍穿的是女装。
那少年却又换了副神色,笑意寸寸蔓延,他眼睛里满满都是恶意的挑衅:“今日就此为止,咱们后会有期……慢慢玩。”
几乎就在阿茕出现“异常”的下一瞬,那旋律古怪的笛声便从暗黑中响起,宛如一条吞吐着猩红信子的毒蛇一点点自黑暗中滑行而出,不多时,阿茕便见到了那吹笛人的真容,那是个形容异常瘦小的异族人,完全符合阿茕曾在书籍中看邻国常年盘踞在深山里驱蛇人的描写,且大周三面沿海,又处北边,即便是位于南部的楚地人都个个体型修长,一眼望去见不到几个矮个子,长这么矮且穿这么奇怪的人,阿茕还是头一次见,当下便判断出,他绝非大周人士,指不定真是从邻国来的。
阿茕丝毫不敢怠慢,挣扎得一点也不含糊,对那少年又踢又甩。
而今正值深夜,二丫的父母皆睡得香甜,阿茕虽很不愿去与二丫折腾,又耐不住她撒娇,只得摇摇脑袋,起身跟着二丫走。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近五日。
“走起!”一道粗粝的嗓音仿似惊雷一般在黑暗中炸开。
阿茕着实想回个无比冷漠的“哦”字,面上却露出了一派纯良天真的表情:“那我又怎么会在你的住处?真是好生奇怪啊。”
与这第三个问题相比较,前面两个问题倒更像是用来麻痹阿茕的。
这话看似没什么不寻常之处,实际上,却是阿茕与白为霜约定好的暗语。
少年目光锐利如刀,盯得她全身冒冷汗,脸上却从始至终都挂着一抹笑。
暗号对上了。
阿茕顿时沉默了,只觉与这小鬼说话着实危险。
那少年却又换了副神色,笑意寸寸蔓延,他眼睛里满满都是恶意的挑衅:“今日就此为止,咱们后会有期……慢慢玩。”
她话音才落,那正忙着给人舀粥的男子不禁抬起了头来,笑吟吟回应着阿茕:“稠,咱们可是奉世子之命来施粥的,粥怎会不稠?”
这些问题想得她脑仁一阵阵发疼,偏生那少年又正虎视眈眈盯着她,她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耗费太多的时间,无奈之下,她索性豁出去了,道:“五日前的那个晚上我和往常一样,早早喝完粥就躺下睡了,所以你为何说我在躲?”
少年等得便是这一句,他道:“既然如此,你可得想好了该如何回答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