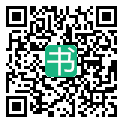第五章 城郊乞丐窝
寒意顺着脚底一路蹿至头皮。
他这一笑叫本该悠闲看热闹的阿茕心中一悸。
她条理清晰、言简意赅,边说边偷偷打量白为霜的神色,却见他从始至终都板着那张阎罗王似的勾魂索命脸。
短短一瞬之间,她已心思百转,终究还是下了决心,决定不与陆九卿禀明此事。
白为霜给出的时间着实太短,短到她已分不出心去搭理旁的事,短到她已无暇去关心自己的生死。
阿茕吃过一次亏,虽依旧对这少年感到好奇,却再未那般赤|裸裸地盯着他看。在阿茕的眼角余光里,少年悄无声息地挪开椅子站了起来,正蹑手蹑脚往门外溜。
约莫一个半时辰后,那两名男子方才刨出坟中棺木,继而以工具撬开棺木,将棺中尸体撞入麻布袋中。
樵夫摇摇头:“俺也不晓得,反正年年都有人失踪,还都是夜里失踪的,所以,年轻人啊,眼下都快要入夜了,你可千万莫往山上跑。”
有足够强大的家世做背景,她在苍家行事一贯嚣张跋扈,自她进门起,芸娘与尚且年幼的苍琼便未过过一天好日子。
白为霜还在静待下文。
阴山位于天水府的最东边,云阳山则位于天水府的最西边,恰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
而他笑起来的时候,整张脸都舒展开,先前的阴郁之气一扫而空,眉眼弯弯,无忧也无虑,竟有种不谙世事的童真感,甚至嘴角还陷出了两个甜糯的梨窝,哪还能教人联想到他先前那副模样。
两个时辰后,她已恢复意识,本该转醒,却在即将睁眼的一瞬间察觉到一股森冷的目光将自己锁定。
二人虽懒散,动作倒是利索,未过多久便又将那棺木给阖上,开始堆土复原那坟包。
白为霜却觉她这笑刺眼,逃也似的转身离开。
仍凭她如何去想都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索性开口去与白为霜探讨。
阴山虽不高,却也十分陡峭,不过半个时辰,阿茕便已走得脚痛,索性一屁股坐在山石之上歇息。
少年穿了一身粗麻缝制的短打,低头坐在那里吃面,阿茕不过是随意扫了他一眼,他便警觉地抬起头来,目光阴鸷地望着阿茕。
少年不为所动,反倒一脸无辜:“我可没跟踪你,不过正好顺路,便一路看着你鬼鬼祟祟围着山头乱转。”
他与阿茕相识十余载,同房七八年,到头来,她又将他视作什么来看待?
阿茕顿时就变了脸色,目光不善地望着那一脸天真的少年:“你跟踪我究竟有何目的?”
大半夜的突然冒出个人影,还是一袭白衣满身煞气的那种,换谁看到都得先被吓上一跳。
她聚在面上的笑意寸寸瓦解,颇有几分惆怅地杵在原地,犹自纠结着,要不要与陆九卿禀报她身份败露之事。
以玄学的角度来看,东方属阳西方属阴,而佛学中又常说西方极乐净土,事已至今,她甚至怀疑她那生生父亲与那黑袍裹身的凶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许是意识到自己方才的话说得重了些,白为霜面色终于缓了几分,声音却仍是那般干巴巴的,他道:“你这般乱来只会徒送性命!根本取不回你母亲的遗体。”
那一幕着实太过骇人,何氏足足愣了好几瞬,方才反应过来。
至于那两名衣衫褴褛的男子究竟是干什么的,也能从他们丢掷在一旁的锄头与铁揪猜测出个大概。
阿茕并无搭理那少年的打算,颇有几分冷淡地点了点头,又将脸埋回面碗里。
阿茕这如意算盘倒是打得响,却不曾料到,她才走至山脚便遇到了白为霜。
直至阿茕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枯枝的缝隙里,那茅草屋内方才又走出一人,那人与樵夫一样穿着粗布缝制的短打,目光阴郁地望向阿茕消失的方向。
这一眼扫来,几乎教阿茕浑身头皮发麻,仿佛有无数根细如牛毛的冰针往她毛孔里扎。
阿茕心中一震,没想到自己竟进了这小鬼的圈套,当下再也无要与其交谈下去的意思,佯装生气地狠狠瞪了他一眼,道了句“懒得搭理你这小鬼”,提着纸钱香烛便走。
这里果然有古怪。
阿茕方才实属无意之举,无奈之下只得朝那少年抱歉一笑,无声表达自己的歉意。
就在这时,被白为霜派去跟踪偷尸贼的影卫传来消息。
阿茕听罢,下意识将自己右手往衣袖里缩。纵然白为霜只道了两个字,她仍旧能凭此猜测出,泄密之人究竟是谁。
那座坟包,显然是座才堆不久的新坟,阿茕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正是因为那座坟包不似周遭的坟那般长满野草,甚至连泥土的颜色都与其他坟不一样,加之坟前还有尚未燃尽的蜡烛,而今尚未至清明,鲜有人会这么早来扫墓,故而阿茕才会猜测这定是一座新坟。
香料的作用无非是熏香除臭,其间却掺杂着花椒味……
阿茕尚未想好要与那少年说什么,那少年便又笑着凑近了几分,道:“这位姐姐一直在山上转悠,可是迷路了?”
m.hetushu.com.com芸娘的死因太过骇人,即便何氏目睹了全程,也不敢站出来为她说一句话。
那名被她一骨头砸晕的副将正两眼呆滞地望向前方,阿茕深知自己当日所用力度有多大,不禁有些心虚,暗自思忖:这人怎成了这副模样,该不是被她一骨头砸傻了吧?
不待白为霜再度开口说话,阿茕便已快速做出决策,她道:“我去阴山看看。”
众所皆知花椒味辛,即可防虫又可防腐,除此倒是鲜有人知,它还能用以除尸臭味,历代帝王的棺木中都会混入花椒与龙脑等香料。
阿茕的直觉告诉她,眼前这少年绝对不简单,在尚未摸清其底细之前,她并不愿暴露身份,只得解释道:“我是在找娘亲的坟茔。”
她不知白为霜今日究竟是怎的了,试图掌控话语,毫无隐瞒地将自己今日所见都与白为霜说了一遍。
既然察觉到此处有异,她便更不会轻易离开。她下山找人借笔墨纸砚给陆九卿传了一封书,又买了些瓜果及香烛纸钱,只等天完全黑下来,再上山去探寻。
那一刻,她的心脏几乎就要蹦出胸腔,身体先一步做出反应,连忙蹲下身去,躲在窗后的花丛里,紧紧咬住手指,不让自己发出一丁点声音。
白为霜嘴角紧抿,不曾作答。
片刻后,便有个衣着邋遢的男人打树林后钻出,一脸谄媚地瞅着这少年,很是殷勤地道:“这小娘们行踪可疑得紧,可要属下去一探虚实?”
那条线正是阿茕当日用枯骨砸晕的副将,一直被白为霜关在密室里,至于当日那只被人用鱼线钩住的鸡,白为霜也差人一并在尸坑附近找了出来,正如阿茕所预料,那只鸡被人喂了能致幻的毒蘑菇干,故而才会这般轻易地被一根鱼线所操纵。
少年听罢,一副全然不信的神色,道:“笑死人了,普天之下竟有连自己母亲坟茔都找不到的人。”
终于在走了近三分之一路程的时候,阿茕终于冷静下来,决定放弃。
那少年却突然弯唇,朝她一笑,道:“多谢小姐姐。”
樵夫没说的是,阴山山脚下住的本就人不多,又总是发生这种事,渐渐大家全都搬走了,只剩他与另外几户人家。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她已很久都未梦到芸娘,本以为这件陈年往事就将化作尘烟散去,却不想十五年后,那个裹着黑斗篷的男人又来到了苍家。
店伙计还真是个不知死活的,即便收了阿茕的钱,仍对那少年无任何好脸色。
阿茕不知白为霜究竟有何打算,只见他在何氏到来后径直走向其面前,面色如常地盯着何氏看了半瞬,不带任何感情地朝她挥出一拳。
白为霜走了,阿茕并未即刻跟着离开。
樵夫道:“原来这里本是一座专埋死人的坟山,即便是燥热的夏夜上山都能感到冷飕飕的阴气,从前倒还好端端的,没出过任何事,约莫是十五年前,这座山突然就变得十分古怪,像是会吞人似的。”
阿茕话音才落,白为霜便垂下了眼帘,阴恻恻地扫她一眼。
樵夫瞥了他一眼,继而摇头,道:“那小子的穿着和周身气度,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八成是个出来游山玩水的富贵人家公子,吓跑就好,不要招惹是非。”
白为霜的观点倒是出乎她的意料。他竟将那放鸡引诱阿茕之人,与七年前放暗箭杀死古怪男子之人联系在一起。
从未想过背后还隐藏着这样一件事的阿茕面色凝重,倒是白为霜从头至尾都未变过神色。
阿茕幽幽叹了口气,询问白为霜下一步有何打算。
阿茕听罢点点头,璀璨一笑:“陆某晓得了,多谢老板。”说完这话,她便将茶碗还给了樵夫,起身与其告辞。
前者一箭射死半夜悬绳入尸坑的古怪男子,救阿茕与白为霜性命。后者看似在恶作剧,实则从头至尾都在给阿茕与白为霜提供线索。
阿茕这次之所以选在下午来,不过是出于安全考虑。
她这次特意乔装打扮了一番,从前扮男装的时候总需用螺黛将眉加粗,画出几分英气,而今她已恢复了女装,眉毛自然画得又细又长,宛如两道笼在烟雾中的远山。
阴山与风景秀美的云阳山不同,山如其名,是座彻头彻尾的阴气飕飕的荒山。
她顺着昨日的路,一路往山上走,却是怎么都找不到那两个男子口中的圣地。
从那以后,整个梅城县的人都知苍家主母疯了。
阿茕明显在给那少年找台阶下,少年又岂会不知道,却偏生不愿好好顺着杆下,饶有兴致地挑眉瞥阿茕一眼,颇有几分轻佻地道:“小姐姐你人可真好。”
阿茕猛地一抬头,这才发觉自己竟被白为霜领到一间密室里。
说完这席话,何氏已泣不成声。
芸娘房里的窗尚未完全阖上,她能透过窗上的缝隙将屋内之景尽收眼底。
最后几个字甚至都还在她舌根打着转,她便一阵风似的冲了出去,白为霜即便想去阻止都来https://m.hetushu.com.com不及。
是了,她早就怀疑白为霜已然知道,只是依旧保有侥幸心,在自欺欺人罢了。
这孩子分明是在笑,却莫名给她一种危险至极的感觉,就像一条龇着獠牙,即将出击捕猎的阴冷毒蛇。
白为霜冰冷的视线已然定格在她脸上,她竖起的汗毛久久不曾软下,甚至连头皮都在阵阵发麻。
原本还在嘿嘿直笑的何氏顿时绷直了身子,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僵在了原地,仿佛被这一下给吓傻。
阿茕将这几个字来来回回细细嚼了几遍,忽而眼睛一亮,才欲与白为霜道,她曾在苍家家主书房内见过一幅血莲图。
阿茕反倒因他这句无意之话而紧绷起身体,面色僵了近两瞬,方才再度舒展开:“你都知道了。”是陈述句而非疑问句。
是了,一个人即便心智不全,在面对突然袭来的拳也会下意识去避开,而不是像失了明似的愣在原地。
待到确认那少年已然离开,阿茕方才搁下面碗,连忙结账,提着香烛纸钱往阴山上赶。
阿茕确确实实是才从外地回来,也从未听过阴山闹鬼之事,不禁点了点头,道:“愿闻其详。”
依他所见,二者就是同一人。
“去他大爷的!大晚上的又被拽起干活,还让不让人睡啊!”
说起来,那少年倒也是奇怪,都闹成这样了,还能死皮赖脸待在面馆里不走,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阿茕看。
阿茕并非无脑之人,就她那三脚猫的功夫,不消片刻就能教人发现,届时莫说找到娘亲的尸首,能否有命回都不一定,率性跑来阴山本就已够冲动,而今既已摸清方向,倒不如先收手,明日再找个借口将白为霜引来此处。
阿茕听罢,又拐弯抹角地问那樵夫那些人的具体失踪世间。
面馆的生意简直清冷得可怕,放眼望去,除却阿茕,便只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这话看上去像是没有任何问题,只是这臭小鬼的语气着实令人不喜。
许是瞧出阿茕并无搭理自己的打算,少年又笑着看了阿茕几眼,方才起身离去。
樵夫神色不明,欲言又止道:“这山啊……有些古怪。”
“做什么?”白为霜冷笑着将那三个字给复述了一遍,“这个问题该由本王质问陆大人才对吧!”
芸娘的死就此成了一桩悬案,被当时的梅城县令给压了下去,而苍家则对外声称芸娘乃是死于恶疾。
她犹自垂着眼睫回忆昨夜的路线,身前却突然笼来一道黑影,她猛地抬起头来,却见面馆里的那个少年正笑吟吟地望着她。
那樵夫的话定然掺了假,她在天水府待了这么多年也从未听过这等奇事,更遑论院外还弥漫着那股子若有似无的香味。
可他白为霜呢?楚国世子,将来必承楚国公之位的人上人。
少年仍笑嘻嘻地站在她身后追问:“小姐姐,你莫不是恼羞成怒了,否则,跑什么呀?”
阿茕抵达阴山山脚下的街道时,已至午时。
店小二不回头去骂倒好,一骂整个人都炸成了炮仗,也不管自家店的死对头是否正杵在门外看热闹,连拉带扯地将那一只脚已迈出门槛的少年拽了进来,朝他劈头盖脸一通骂:“狗娘养的小杂种,还想在老子的店吃霸王餐不成?”
换作平常,阿茕定不会花时间来管这等闲事,怪只怪她比那双手叉腰、呈圆规状的店伙计更懂识人。
而这时候,本想继续装下去的何氏却已绷不住。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面上露出悲戚的表情:“还请世子大人开恩,民妇也是逼不得已啊……”
一个半时辰后,何氏已然抵达世子府,仍是那副疯癫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手舞足蹈,像个心智不全的孩童。
不过须臾,那甚是简陋的茅草屋内便走出一拿着斧子的樵夫,瞧见阿茕站在门外,立马将斧子收了起来,很是热情地询问阿茕是来讨水喝的还是来歇脚的。
阿茕听得膛目结舌,她倒是从未往这方面去想,本还想再问仔细些,一直领着她往前走的白为霜却突然停下了脚步,道:“我们到了。”
那件事即便过了那么久,仍在何氏心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阴影,即便后来的很多天里一直风平浪静,她仍时不时梦到那一幕,梦见芸娘扶着自个不停流血的脖颈神色凄楚地质问她:“你为何不救我?你为何不将真相说出口?我恨你!恨你!”
次日上午。
她一路风尘仆仆,赶到阴山山脚时,早已饥肠辘辘,而今距离清明尚有段时日,山脚下并无多少过往行人,她顺着萧条的青石街,一路漫无目的地走着,终于在某个拐角处寻到一家还算周整的面馆。
她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对他甩脸色?就凭借从前的那点点交情?
全然捋清思路的阿茕,终于决定收手下山,却在转身之际听到不远处传来一个粗声粗气的嗓音:
直至阿茕的背影完全消失在那少年的视线里,少年面上方才恢复正经,一点点敛和-图-书去浮在脸上的笑意,目光阴沉望向阿茕所消失的地方,也不知究竟有何用意。
阿茕又岂会回他的话,越发加快了步伐。
阿茕嘴甜又活络,不足片刻便已和那樵夫聊了起来。
农舍外弥漫着一股子若有似无的香味,阿茕吸吸鼻子,闭上眼睛细细分辨一番,她能闻出那是花椒与劣质檀香相混杂的味道,她即刻翻身下马,站在农舍半人高的篱笆外张望着,隔了半晌方才喊道:“可有人在家?”
无边无际的恐惧犹如黑夜般笼罩着她,她甚至听到了那人寸寸逼近的脚步声,五米……四米……三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终于停在了她床畔。
他笑起来的模样与不笑的时候俨然两个人,不笑的时候总给人一种暴戾乖张之感,就像整个人都笼在一片黑雾之中,仿佛随时都有暴起取人性命的可能。
床上叠着两道人影,芸娘被一个裹着黑色斗篷的陌生男人压在身下,向来细声细语的她不停地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声,血腥味透过窗棂一点一点地漫出,朝站在窗外的何氏疯狂涌来……
这,便是整件事的始末。
阿茕莞尔一笑,自言自语似的道:“不然你那时候又为何这般突然地唤了声苍琼。”
从前她也不是没见过白为霜发怒的模样,却无一次似如今这般令人生畏。
一直躲在暗中观看的阿茕,甚至都能以此联想到十五年前,她娘亲尸骨被盗的画面,整个过程她都咬牙切齿,竭力压制住自己的怒火,心中却在不停嘶吼,不停咒骂这群畜生。
大抵是十五年前,那时的苍家主母还是芸娘,而她则凭借优越的家世,一来便是苍家的平妻。
那两名偷尸贼的路线已经被摸清,他们却是兵分两路,去了两座不同的山,分别是阴山与云阳山。
她气势汹汹迈步而来,却在即将推开芸娘房门之际停了下来。
她与芸娘看似平起平坐,实则谁人不知真正掌主母之权的乃是她。
被运去云阳山的乃是苍家家主的尸体,被运去阴山的则是苍家大少的尸体,阿茕虽不能分辨其中究竟有何区别,心中却隐隐有个猜测。
阿茕把要说的话都给说完了,他老人家仍如磐石似的杵在这里,既不说话也不动,以实际行动告诉阿茕,而今的他很是不爽快。
明知芸娘对她而言无任何威胁,仍是被她视作了肉中刺眼中钉,她日常的消遣便是想着法子来折腾那娘俩。
“两个月。”白为霜声音冰冷彻骨,如从寒冰地狱传来,“本王只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她那紧闭的房门被人猛地从外推开,二儿子与一众家奴顿时涌入房来,她方才悠悠“转醒”。
思及此,阿茕便屏气凝神,坐在此处窥视。
阿茕神色一凛,又临时改变了主意。
这一问,不仅仅是何氏,就连阿茕都有些呆愣,一时间竟有些反应不过来。
听闻此声的阿茕连忙吹灭纸灯中的蜡烛,小心翼翼将头伸出去偷看。
白为霜面色不变,只言简意赅地道了两个字:“手腕。”
看似简单随意一句话,所囊括的信息量却相当之大。
至于那少年,阿茕本就对其无任何好感,自打面上了桌,便再未拿正眼瞧过他。
她一语罢,撇头望了眼神色不明的少年,笑意盈盈道:“你瞧我说得可对?”
所幸阿茕也是个脸皮厚的,倒不会因这种事而动怒,神色淡然地回了句:“应该的。”又坐回先前的位置上,召唤店伙计给她端面。
她不知自己究竟在花丛里躲了多久,直至屋内再无任何声息,直至天之欲亮,终于有奴仆回到紫云苑、发现芸娘冰冷的尸体时,她方才挪了挪已然僵硬的身体,跌跌撞撞地逃出紫云苑。
周遭并无奴仆,她既不敢大喊大叫亦不敢继续待在原地继续看下去,本欲悄悄逃离,那裹着黑色斗篷的男子却在她即将离开的那一刹猛地一回头!
十五年前芸娘惨死的画面陡然跃上心头,她的眼睛因恐惧而越睁越大,某一瞬间她只觉两眼一发黑,便直接栽倒在地,再无任何意识。
乔装打扮后的阿茕气质瞬变,即便再撞上先前那个樵夫,也不一定能将她认出。
他不说,阿茕又何以知晓?
那个吸血杀人的黑袍男子尚未离去!
终究还是因阿茕这般不顾性命地乱来。
周身遍布的戾气连她看了都觉心生畏惧,那店伙计却迟钝如斯,犹自叉着腰,不停地骂。
她不由得前进一步,伸手在那副将眼前晃了晃,那副将犹自两眼发直,阿茕又换了种方式,拔下头上的木簪作势要去刺那副将的眼睛,木簪即将逼近副将眼睛的时候,他终于有了反应,连忙侧身躲开,且神叨叨地念着什么。
“哎……你这年轻人啊……”为了劝住阿茕这非要往山上闯的年轻人,樵夫终于说出了实话,“你是打外地来的,或许还不知这阴山闹鬼的事吧。”
那少年虽被他拽着领子一通骂,周身气势却不输那喋喋不休、一直在不停和*图*书骂人的店伙计,非但无一丝羞赧之意,反倒嘴角一勾,露出个意味不明的笑。
二
约莫二十米开外的一座坟前坐了两个衣衫褴褛的男子,由于此时的光线太过微弱,阿茕只能依稀看到他们的衣着,并无法看清他们的容貌。
阿茕纠结着该点什么面吃之时,那少年已然吃完整碗面,才准备招手唤小二来买单,面色又是一变。
她这辈子很少主动求人,而今只求白为霜能给她找出娘亲尸骨的时间,此后任凭他如何处置,她都无怨无悔。
只有苍家之人才会记得那件事,而苍家人中最有可能记住此事的,不是当事人便是当时在场之人。
白为霜身上寒气却越来越盛。
阿茕换了身粗布衣衫,假扮成来阴山上坟的民女。
他因何而气?
何氏被白为霜差人带去画师那儿口述黑袍男子的容貌。
阿茕着实不想与这小鬼继续纠缠下去,又道了句:“爹爹临终前只与我说过,娘亲的坟茔在阴山上,除此再未说其他,我找不到不也正常?”
也不知究竟是阿茕笑得太过诚恳,还是那少年本性如此,见阿茕朝自己笑,便也回以一笑。
白为霜吩咐旁人:“去苍家把何氏请来。”
阿茕被这小鬼盯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要竖起了,实在没法忍的她不禁抬起了头,望了那少年一眼。
从始至终,她都只是陆九卿的一颗棋子,她纵然再不愿去承认,也是无法反驳的事实。
眼下天已全黑,阿茕提着一盏纸灯,孤身上阴山,越往山上走越觉夜色寒,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森冷阴气顺着脖颈直往衣服里钻,冻得她直打寒噤,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许是因这孩子的反差太大,以至于阿茕半晌都未能缓过神来,店伙计终于在她身边站得不耐烦了,若不是瞧她生得好看,怕是早就破口大骂了。
那日苍家所有奴仆都在外院忙活,紫云苑中只余芸娘一人。
结果不言而喻,她藏了这么多年的秘密竟因这么小的一件事而暴露。
阿茕不动声色扫了那农夫一眼,粲然一笑,道:“既要喝水又要歇脚,谢过老伯了。”
这个声音于阿茕而言并不陌生,正是她下午所遇的那个热情樵夫。
孰可忍孰不可忍,阿茕终于被白为霜这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举动给惹烦了,再也不想去顾忌他的身份,一把将其胳膊甩开,语气不善地道了句:“世子大人这是要做什么?”
她昏迷的时间并不长,两个时辰而已。
本以为这样便能打发那少年。
阿茕缓缓垂下了眼睫,大概那间茅草屋内藏了不少尸体,否则又岂会花费这么大的手笔。
连他自己都不知自己究竟因何而怒,又到底为何而怨,只莫名觉着心中不痛快,一股无明业火腾地在胸口燃烧开。
梦魇折磨得她夜夜无好眠,她甚至将怨恨与恐惧转移到年仅五岁的苍琼身上……
“古怪?”阿茕挑了挑眉,旋即朗声一笑,“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这山还能吃了陆某不成?”
她本以为是自己眼花,结果,翌日便发觉自己相公死在书房,不到一个时辰,向来被她视作心头肉的长子亦惨死房中,死状与当年的芸娘一般无二,她声嘶力竭地抱着儿子尚未凉透的尸体放声痛哭,却以眼角余光瞥到一截藏在屏风后的黑色衣袍。
她猜,她那与苍家大少一样死于吸血的娘亲,定然也被带去了东方阴山。
阿茕却毫无征兆地跪下,朝他磕了个响头。
白为霜的拳在她眼前一寸处停下,薄凉的唇勾出一抹寒意彻骨的冷笑:“你究竟还要装到何时?”
然而,连一口气都未能完整地吁出,白为霜这厮竟二话不说便拽着她往山下走。
阿茕不禁开始怀念当年那个被她耍得团团转的白为霜,不禁触景生情,悠悠叹了口气:“哎……”
一
她夹在嘴角的笑意越扩越大,几乎可以称之为璀璨,只可惜眼中并无丁点笑意,生生暴露了她的情绪,她一字一顿,璀璨笑意转换成痞气:“我无从解释。”稍作停顿,复又道,“只想知道,你究竟从何得知我的身份。”
阿茕险些溢出喉间的话又被生生压了回去。
又过半个时辰,那两名男子方才堆好坟包,抬着装尸麻袋径直往山上走。
少年周身的戾气已越聚越浓郁,凝在嘴角的笑意亦越发森冷,阿茕看得提心吊胆,生怕他下一刻就会暴起杀人。
阿茕看了眼二人所去的方向,并未尾行,直至再也听不到那二人的脚步声,她方才起身,往山下走。
阿茕再也不能以一种看热闹的心情继续围观下去,连忙起身拍拍那店伙计的肩,掏出两枚铜板,朝他粲然一笑:“这孩子生得这般机灵,又岂会做出这等事,我瞧呀,他八成是忘了要付钱的事。”
简直得意忘形!
少年不曾言语,只是微微颔首,那男人便会意,像条灵活
www.hetushu.com•com的蛇似的,“嗖”的一声钻入树林里。
正如那樵夫所说,阴山乃是一座坟山,隔三岔五便能钻出一座坟来。
阿茕一路策马飞奔,终于在山脚下找到一户农舍。
连他自己都不知自己究竟因何而怒,又到底为何而怨,只莫名觉着心中不痛快,一股无明业火腾地在胸口燃烧开。
阿茕又岂会听不懂,这一下倒是彻底拉回了她的理智,从前在杏花天的时候倒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大家都是同窗,并无贵贱之分,而今却不同,她不过是陆九卿的棋子,一个芝麻绿豆大的七品县令。
这样的孩子阿茕还是头一次见。
此时此刻,即便她想走,怕是也无任何办法能保证她走的时候不发出任何声音,况且此时的她还不能点灯,须得摸黑离开,既然如此,她倒不如守在此处暗中观察,看他们口中的圣地究竟在何处。
她就这般神色悲戚地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回忆起当年之事。
直至如今,她都还能清清楚楚回忆起那一夜所发生之事。
惧从喜中来的阿茕连忙咧开嘴,上前一步道:“原来是世子大人,可吓死下官了。”
那一刹,她的心脏仿佛被人狠狠捏在了手中,喉咙亦像是被铅块堵住,巨大的恐惧使她浑身发颤,不敢动弹。
这少年天生一副讨喜的娃娃脸,笑起来的时候嘴角还会陷出两个甜甜的梨窝,若不是阿茕见识过他先前那副模样,十有八九要被他的笑容所迷惑。
本面如死灰,不报任何希望的阿茕瞬间喜笑颜开,忙不迭道谢。
何氏依旧是那副痴痴呆呆的模样,阿茕在脑子里将白为霜方才所作所为反反复复过一遍,方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究竟是在做什么。
倒是阿茕掉以轻心了,少年听罢,又是一笑,只是这次笑意明显未达至眼底,他话语里隐隐带着几分调侃之意:“这位姐姐你倒是不见外,无缘无故便与我这陌生人解释这么多,又是为哪般?”
屋外吆喝之人恰好是这家面馆的死对头,小二登时便回过头去冲那人骂道:“干你这没腚眼子的臭王八屁事!”
直至那浑身煞气浓郁到像入了魔似的的白为霜步步逼近,阿茕方才恍然发觉,眼前那尊凶神竟是老熟人白为霜。
约莫戌时三刻,天就要完全暗下来的之时,她终于抵达芸娘所居的紫云苑。
少年既然知道她一直在山上转悠,又这般恰恰好地与她相遇,除了一直都在跟踪她,她再也找不出别的理由。
那夜恰逢苍家家主纳妾之夜,宅中宾客络绎不绝,她则又欲将一腔怒火发泄在芸娘身上。
白为霜大抵是从她先前逗弄副将时得到的提示,是了,一个人即便心智不全,在面对突然袭来的拳也会下意识地去避开,而不是像失了明似的愣在原地。
而阿茕之所以替那少年买单,不过是怕店伙计惹祸上身,结果那伙计还是这般不识好歹,阿茕也懒得去管,心中暗骂一声“蠢”,便开始埋头吃面。
他的重音完全压在“本王”与“陆大人”五字上,摆明了就是在提醒阿茕,莫要忘了他们而今的身份。
说到此处,樵夫停下,意味不明地瞥了阿茕一眼,方才继续道:“那是临近清明的一个雨夜,当天夜里有三个来自外地的青年男子特地赶来上坟,由于在路上耽误了些时辰,他们赶来之时已至深夜,结果啊,那三个青年男子上山后,嘿,就全都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像是被这阴山给吞了似的。总之,从那以后,这阴山一带总有人突然失踪,全都是上去就没了。”
他声音有些含混不清,又断断续续,只能依稀听到“血莲现世,神祇降罪,大周将灭”几个关键字。
今日并非全然无收获,起码她已得知这山上有古怪,以及那茅草屋内的樵夫绝非普通人,既然如此,她又何必一时冲动,在不能确定能否全身而退的时候贸然行动。
待到阿茕将话头转至阴山之上时,樵夫那两道杂草似的眉全然皱成了一团,颇有些忌讳莫深地与阿茕道:“俺劝你还是莫要再往山上走了。”
阿茕听完白为霜的叙述,佩服幕后人手段高明的同时,又不禁开始思索那人究竟是敌是友。
阿茕一听便来了兴致,问道:“为什么?”
她心中一喜,连忙提着纸钱香烛等物走了进去,准备垫饱肚子再上阴山。
这阴山之所以被唤作阴山也不是没有道理。
另一名男子很是随意地抄起坟前一枚鲜果往嘴里塞,边吃边含混不清地道:“少抱怨,先垫垫肚子,待会儿赶紧挖,定要在天亮前把里面那玩意儿给挖出来,送去圣地。”
他一切都做得十分稳妥,怪只怪那时候店外突然有人朝小二吼了一嗓子,道:“哟,你家今儿个终于接了两单生意咯!”
与此同时,已然走出樵夫视线范围的阿茕勒马停了下来,回头望了那全然被枯枝遮蔽的茅草屋。
屋外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娘亲”,那道森林的目光方才从她身上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