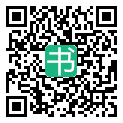第二十四章 荷叶杂衣香
我笑出来,一手撑起身子坐直,纤纤食指在他颈间轻轻划过一道,佯怒道:“你与堂堂湘东王妃有私,若是王爷知道了,只恐留你不得!”
要了解一个人的过程,必定会经历很多痛苦。可是,我已经经历了太多痛苦了,我太伤心了,所以我没办法继续下去了。我将满腔热情和一颗真诚的心捧给了那个人,可是他不在乎。任何毫无回报的付出都是一种徒劳的痴愚,而我却竟然花了这么漫长的时光才真正看透。
贺徽笑笑,对于我信口指定的题目也未多作评论,垂首静思了片刻。我在他身旁“一、二、三、四”地数数,数到七时,他睁开眼睛,对我笑道:“有了,这回你可罚不到我了。”
“……娘娘且莫动怒。王爷只怕是一时鬼迷心窍……”浅儿踌躇半天,见我又不说话了,才壮着胆子相劝道。
贺徽倒是不曾来迟。事实上,他从不曾来迟过一次。每回当我到了约定地点,总见他已先行一步来到,找个地方坐了,手里拿一卷书,安静读着。他的眼帘微垂,格外秀致的长睫在眼下形成一圈暗影。他的面容宁谧,无论周围是安静或喧嚣,他永远那样静定,注视著书上字句的眼神格外专注。看到要紧处时,他的双唇会微微抿起,下颌的线条也微微绷紧,却并不显得严厉,只透出某种在红尘的繁华与浮躁喧嚣里遗世独立的文士况味。
我开始任意妄为。恶佛理而嗜饮酒,终日半醉半醒,半睡半梦。我放浪形骸,随性纵情。与我幽会的俊美男子,从贺徽、到府中小吏暨季江,早已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
而王菡蕊……她进入王府固然是萧绎青睐,自己却也有不能不来的原因。无非要将自己全家从贫穷困苦中解救出来,老父年老体弱仍在军中当差,兄长王琳虽满腹抱负却报国无门,只能屈就在军中做个风餐露宿、廪赐微薄的小小兵丁;母亲操劳一世、体弱多病却无钱医治,一家人苦了几十年也没有更好的生计……
偶尔浅儿也会来报告一些她打听来的萧绎的近况。他又收纳了何方俊才至自己麾下,他又接见了何人,朝中传言他又做了何事,他又去了何处;他又遇见了谁,打算纳她为妾……
这一切千回百转,方等都浑然不知。他只靠在我怀中,嘻嘻笑着和我掰手腕,每次当我的手被他的小手发力压倒,他就咯咯大笑,显得很快活的样子。
她慌忙又低垂了脸,声音细不可闻。“十……十六。”
我忽然停住,又想气、又想笑,觉得这一切都是如此荒谬,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我看着他无知但快活的小脸,不禁又是宽慰,又是酸楚。
寺院的一处隐秘净室里,我倚在白角枕上,懒洋洋地望着贺徽坐在床畔的背影,看着他将方才弄凌乱的头发重新理顺结束,不经意地开口道:“欸,大才子,我给你出个诗题,限你在七步之内做成一首诗,如何呀?”
“也许我应该感激,感激他虽然不爱我,却给了我方等。有了和*图*书方等,我便可以有个人将我的一颗心都托付……”
她们头垂得更低,唬得几乎连声音也发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拼命点头。
兰裳依旧不解世事般地娇憨而笑,跟随姊姊对我福了一福。而菡蕊虽然行礼如仪,听到我的话后,却明显地一震,神色里就涌上了某种悲哀的黯然。
“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裳……”
只是呵,那个人不是他。我的一颗心,即使捧在手中,从滚烫直至完全冷却,他也不肯接收。
贺徽面容上笑意一凝,沉肃地盯视着我,半晌突然不甚正经地勾唇一笑,拉拢自己中衣的前襟,玩笑似的说道:“那有何惧?王妃也不必急着将微臣灭口呀。”
“懦夫……自己逃避也就罢了,还硬塞给我一个你的儿子,让我忽然觉着得了多大的指望,又笨得开始以为可以得到你了……结果却是这样!混蛋……你的儿子虽然可爱,可是我想爱的是你,不是你的儿子呵……”
我心下一震,先前多少有些半真半假借机试探的意味,现下却不料他说这样的话,正色道:“我是说真的。王爷可以自己三妻四妾,可他未必容得下我在外任意妄为。万一东窗事发,你要如何应对?难道你就不怕因我而获罪么?”
“你是姊姊菡蕊?今年多大了?”我不动声色地问着左边那女子。
菡蕊的俏脸微白,脸上的表情仍是沉静而恭谨,缓声道:“回娘娘,此句乃是出于王爷《采莲赋》之中。”
我再追问他,他却怎么也不肯说了。我微恼,薄嗔道:“你这个人怎么如此优柔寡断,吞吞吐吐!也罢,《芳树》为题,七步之内,你要做出一首诗来送我,否则我一定追问到底!”
我在一旁看着,虽然“长门殿”那几字颇觉刺眼,但词句的工丽华美还是令我不禁赞叹,静看他继续写道:“啼鸟弄花疏,游蜂饮香遍。叹息春风起,飘零君不见。”
“光说的不行,你写在这上面才作数!”
贺徽叹了口气,温声道:“那娘娘又是指定《芳树》为题,还又要七步成诗,难道……就和七王爷没有一点关系么?”
她们姊妹两个不晓得我的用意,这会子反而被唬得跪在地上,头垂得低低的,生怕我一个不高兴,迁怒到她们身上去。
“谁不怕死呢?那是假话。我都不知道为何要继续下去,你也不曾给我半点好处,譬如荣华富贵、官升数级……”他长长叹息了,手滑到我颈间、我肩上。
我看着兰裳那个天真烂漫的笑容,心里却没来由地忽然一阵黯然。想当年,我也拥有过这样澄澈纯然的笑靥,但曾几何时,我已凋零残败,雍容高贵的躯壳掩盖之下,内里已化为一片荒芜的废墟!而那个人,剥夺了我的自由、我的期待、我的爱与快乐的那个人,却仍可以若无其事地在其它人身上去寻找我已无存的烂漫温柔,而将我遗弃在往事里凋谢枯萎,零落成泥——
菡蕊年纪较长https://www.hetushu.com.com,通晓人事,一张俏脸已然变得苍白。兰裳年龄尚幼,听不出什么弦外之音,犹自天真烂漫地笑着,乖顺地听我训诲。
我深吸一口气,把到了眼角的泪意硬生生逼了回去。
我读着纸上的字,沉吟片刻,冷冷一笑。
我看她这副如履薄冰的样子,倒是当真失笑了出来,一仰首饮尽杯中甘醇的桂花酿。
然而从今往后,我再没了别的念想,也只能,好好地爱你的儿子一人了。
我笑了,向后坐回椅中,怡然道:“兰裳,这一句里可巧嵌着你的名字哩,还不好好记熟?若不是王爷见着了你们,只怕也做不出这一篇《采莲赋》哩!看看,他还不是整日心心念念着要‘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么?如今你们进了湘东王府,也正遂了王爷的心愿——”
看他这般云淡风轻,我的怒意更甚。“又是‘长门殿’、又是‘飘零君不见’,字字扎眼刺心,教我又能作何是想?”
“娘娘……”浅儿嗫嚅,一径地恭顺垂首,不敢再引起我的话头。
我轻似无声地叹了一口气。揽紧了怀中的方等,我对门前的菡蕊、兰裳姊妹冷然道:“唯愿你们走这一遭,能在这王府里,求取你们想的,得到你们要的。”
这样背景,就连李桃儿都比她强过百倍,至少李桃儿早已是登记在册的宫人,虽然宫禁森严,总能吃饱穿暖,如今得宠,更能披绸着缎。可王菡蕊却不得不用自己和妹妹来换取一家饱暖富贵,纵是那妖童青梅竹马情深意重,也要忍痛割舍,来与我这堂堂信武将军爱女争宠。
我见她们这样,也就缓下容颜,一边和方等顽笑,一边冲她们摆了摆手,示意她们退下。
看到最后一句,我的瞳孔猛然紧缩,突如其来的怒意涌上眉间。“贺徽!你……是在藉诗讥讽于我吗?”
妖童媛女,荡舟心许……也许,他们宁可当日不曾歌采莲于江渚,或者没有遇见高高在上的荆州刺史、湘东王爷罢?
他忽然停下话头,我急着追问:“那又如何?”
贺徽看了看我显得略微急切的面容,忽然摇了摇头,轻描淡写道:“……也没什么,不过就是一些妄自推测而已,不值一提的。”
方等。我只有方等。这世上,如今我只余方等一人,可以让我敞开心怀去爱、却不担心会被伤害,可以让我毫无保留地拥有。
我惊讶,他竟然能做得这样快?生怕他信口开河诌个几句来搪塞我,我跳下床,在桌案上找到笔墨,捧到榻上来。左右看看却没有纸张,我灵机一动,将白角枕往他面前一放。
“我当真不睬他了。从今往后,什么李氏宫人、或者王家媛女,都统统随他去罢。这《芳树》一调,我亦终身……再不复闻!”
“可是,你要我现在放手?很奇怪呵,我也竟然想都没想过……”他凝神片刻,忽然道:“其实,昭佩,据我揣测,王爷未必全然蒙在鼓里。表面上看,王爷素来宅心仁厚,又怎会轻易降罪于你这结发https://www.hetushu•com.com妻?再深一层想——”
我眉间一凛,随即微笑道:“不错。菡蕊……这一句,倒也配你。”
“……很好。”我忽而笑了一笑,怒意自我的眉间消失。虽然方才脸上气愤的红晕尚未退却,我却已经冷静了下来。我甚至还可以绽出一个带点刻意的、微微挑逗的笑容,倾身向前,向贺徽的后颈间呵了一口气,语调陡然一转,带着些微的娇嗔。
“那又如何?我这一辈子都已经被他绑住了,被‘湘东王妃’这个冠冕堂皇的头衔绑住了!我争取过,我失望过,我等待过,我也伤心过……你说我如何能不生活在他的阴影笼罩之下?从八岁起,他就是我的夫君,我世界里的唯一……你现在要我完全不去在意他,你要我在一夜间改变十几年来的习惯,如何做到?怎么可能?!我已经很努力去摆脱他了,我已经尽力了,我只是还没有完全成功而已,难道你就都看不到吗?……”
贺徽没有立刻回答,静静地凝视着我,直到我被他那灼灼的眼神看得心慌意乱,躲开他的视线。他的眼中浮现了一抹悲哀,轻声说道:“昭佩,你心底……仍是在意他的吧?我相信你的确不是有意而为之,只是他带给你的影响太深重,已经嵌入你血脉骨髓;所以你不自觉地要提起关于他的事,让你的生活里仍旧充满他的阴影笼罩……可是昭佩,他已经放弃你了!即使他曾经爱过你,他现在的枕边人也已不再是你了!——”
“你听说过……‘落英逐风聚,轻香带蕊翻’这句诗么?”
“王爷好闲情逸致啊。这回是个采莲女?还做了一篇《采莲赋》给她?瞧瞧这都是些什么字眼!‘……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鹢首徐回,兼传羽杯……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故以水溅兰桡,芦侵罗袸。菊泽未反,梧台迥见,荇湿沾衫,菱长绕钏。泛柏舟而容与,歌采莲于江渚——’”
我骤然紧紧抱住方等,在他的小脸上亲了又亲。方等或许以为我在和他玩耍,因此咯咯笑起来,有样学样地也在我脸上胡乱地亲了一气。
“方等,好孩子……”我蓦地哽咽了。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在乎,但心底那种被羞辱、被冷落、被无视的委屈,止不住地涌上来。
从此,萧绎不再踏入我的房门。而我,也一日日逐渐堕落下去。岁月的流逝于我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彻底放弃了挽回我的夫君的努力,也彻底放弃了挽救我自己。
他提笔在那枕上写道:“何地早芳菲,宛在长门殿。夭桃色若绶,秾李光如练……”
“娘娘误会了。”
贺徽闻言讶异地转过身来看着我,脸上流露出一个温柔而带点宠溺的笑意,戏谑道:“昭佩,你难道要仿照那魏文帝为难陈思王,也要我做《七步诗》?我做错了什么,惹你生气,一定要藉此除掉我?”
她仿佛有丝踌躇,沉默了一瞬方恭谨回道:“……此句出自于王爷《芳树》一诗www.hetushu•com•com。”
“他的枕边人不是我,又有何妨?我现下的枕边人,也不是他呀。如果他以为将我弃如敝履,我还能乖乖为他守身如玉,痴痴盼他回心转意,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贺徽放下笔看向我,神情倒是很从容。
一颗眼泪,悄无声息地钻出我的眼角,坠落在方等的幼小肩头上。
“你住口!”我震怒而晕眩,血冲上了我的头顶,我的脸涨得通红,皮肤里的灼烫感直要烧熔我的意识。
与他们在一起时,我的心仍是空虚的。仿佛斜倚在榻上,与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谈笑戏谑的,只是我的一具躯壳;而我的精神和意识早已脱离了肉体,飘飘荡荡浮在半空,居高临下地冷眼旁观着这一场场所谓的幽会,无止境的嘻笑打闹,打情骂俏。
我一愣,方才意识到萧绎的确排行第七,小字七符,所以贺徽刻意称呼他“七王爷”;却又偏偏和曹植的七步成诗暗合,难怪贺徽从一开始便想歪了。但我也是性子烈的人,冷哼一声说道:“那又如何?不过是一些荒谬的巧合罢了,也值得你这样反应激烈,讽刺于我?”
她沉默无语。我略略往前倾了倾身子,又问兰裳:“我也来考一考你。‘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故以水溅兰桡,芦侵罗袸’,却是出自于哪里?”
“去通报贺大人一声,明儿在普贤尼寺礼佛、赏花的约,可别忘了。来迟了,可要受罚的。”
“萧世诚……你为何要拿这些人来羞辱我?”我喃喃自言自语,有些出神了。
我吃吃笑着,纤手在他衣襟之下慢慢滑动,眼波流转。
我仍然微笑着,眼光又横向一旁沉默着的菡蕊。“瞧瞧,这可怜孩子!想是在家还不晓得这一段哩!你这做姊姊的,就替妹妹解解围罢。”
他不爱我,我好不容易才学会了不再苛求。而现在,从穆凤栖、李桃儿到王菡蕊、王兰裳姊妹,纵使我们在出身背景上有若云泥之别,但在他面前却是一样的:我们争夺他的心,争夺他的温柔,然而在那些出身贫贱的对手面前,我高贵的身份没有给我增添半点胜算。
“真是绝妙好诗。能与君白角枕上以诗唱和,何乐融融!”我笑着,纤指抚过贺徽的后颈,滑下他的肩头,直至他半敞的前襟之内。
然而我不在乎。我全都不在乎了。
“奴婢王菡蕊、王兰裳,给王妃娘娘请安。”
贺徽的笑容也消失了,他静静注视我许久,忽然伸手来抚摸我的面颊,以指勾勒我脸侧的线条。
我不禁笑出声来。“很好啊!可不正合了那句‘叶嫩花初’吗?”
“十四!”她倒是没有一丝畏惧的样儿,扬着头,天真地说道。
在这种不见血光、却仍然惨烈的争斗中,反而是我,堂堂圣旨亲册的湘东王妃,出身豪族世家,却最一败涂地,输给那些原本一无所有的女人!穆凤栖获得皇上的欢心,李桃儿和王家姊妹则拥有湘东王本人的青睐,而我,我又有什么?
待她们行礼退出之际,我又唤
和图书住了菡蕊。浅儿唯唯诺诺,不敢多言。想来是关于我最近“脾性骄奢、喜怒无常”的传言愈演愈烈,连带着她也不由得有三分信了。何况以我从前的性子,遇上了这种事情定然是当场发作;而今日我不但没有发火,反而还面色淡定、与她说笑如常,多少也吓着她了罢?
贺徽有些吃惊地看看那白角枕,又看看我,忽然抚额失笑起来,拿起毛笔。“好好,昭佩,你说什么都好。”
兰裳尚幼,只怕在家时也不曾如姊姊一般识文断字,此刻愣在原地张大了嘴,却是回答不出。
我收了笑,对她们正色道:“你们不必如此紧张。既然王爷属意于你们,你们就是王爷跟前的得宠人儿了,只怕我这当王妃的,也不如你们这般讨王爷的喜欢呢!我也不去管王爷的好恶,今后只要你们守府里的规矩,尽心尽力服侍,王爷自然喜欢,就是我,也不与你们去争这个了!只一点:规矩既是人定下的,自然也有人幻想着可以由人随意更改,要变着法子绕过规矩这两个字去;我从前对这个计较得厉害,现下年纪长了,也没了当年那股子锐气;只盼你们别忘了本分二字怎么写,我便不与你们为难。若是有人自个儿一时没想明白,犯了胡涂,我少不得也得秉公行事,更顾不上看谁的情分、谁的体面,知道了么?”
我凝神注视着她,不防怀中的方等已等得不耐烦起来,此刻忽然抓住我的一只手,扳起我的手指,径自与我玩起了掰手腕的游戏。我被他的小手这样一拉扯,却猛然醒觉,示意她们姊妹可以退下。
望着王菡蕊细瘦的背影,我突然对自己方才的结语感到好笑。求自己想的、得自己要的?那不过是嘴上功夫,说得动听罢了。我在这王府里呆了十几年,也求了十几年,又何曾得到过自己想要的?这轻飘飘的一句话,要实现,却是绝难呵!
我沉吟,不着痕迹地细意端详那两个女子。果然是江南人家,纤腰束素,娇怯可怜,别有一般动人心处。左边那个女子眉眼楚楚动人,格外秀致,温婉沉静;右边那个五官略略显小,神态天真娇憨,却也另有引人之处。
我把那张抄有《采莲赋》的纸往桌上一丢,拿起手边的酒杯,以杯就唇,冷笑一声。“我却又跟他动哪门子怒去?哪个皇子不是三妻四妾、左拥右抱的?我倒是想跟他一个一个计较呢,可我要是当真这么做了,忙得过来嘛?”
我又问着右边的兰裳。“你呢?”
“哈!叶嫩花初?这么个娇娇嫩嫩的可人儿!单看这一篇赋里的形容,就连我也要倾倒不已哩,又何况是咱家王爷?”我越想越好笑,指着纸上一段话,对一旁面有忧色的浅儿笑道:“人家媛女都有个‘妖童’荡舟心许了,王爷反而硬要从中作梗,横插一杠子,坏人姻缘?这不是忒也胡涂么?”
贺徽闻言,吃惊地转过头来盯着我,仿佛不敢相信我居然说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昭佩!你……当真……”
我怀里揽着方等,懒懒地睨着堂下跪着的一对姊妹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