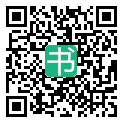下卷
第三章
忽然,不远处传来男子的唱声,今夕何夕兮……
之前为什么想不通呢?
司马衷下诏,搜捕司马颖。
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屋外夜色如染,寒风呼啸,刘曜点了柴火,屋中才暖和一些。
他吃着,我也吃着,只怕都饿了,不再言语。
“我在金墉城找过公子,为什么公子不在金墉城?”
“臣妾饿了,陛下也饿了吧,先进膳吧。”
一时之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尖锐的问题,心头转过数念,却没有一个说服力强的借口。
军务要紧,他分身乏术,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我只能等,耐心地等。
“你听我说……”
那人身着一袭黑衣,一步步走上来,抬脸盯着我,目光如豹,狠悍冷冽,锁住了猎物。
“好,好吧。”他扭扭捏捏地坐下来,瘪着嘴。
直至黄昏,他才送我回去。
我问表哥,他支支吾吾地说道:“正月,成都王奔向长安,听闻河间王正与东海王求和,就没有进长安,此后再无踪迹。”
近几年的折腾,他御驾亲征,来往于洛阳与长安之间,风餐露宿,吃了不少苦头;被亲人挟持,几度命在旦夕,身临险境,担惊受怕;他比之前更瘦了,可以说瘦得皮包骨头,可见他在长安过得并不好。
其实,我可以让司马衷不再册立碧涵,可是我不想这么做,因为,他是否册立她,要看他对她的喜欢,到底有多深。
我不语,相信他会明白,要让我再次相信他,除非他不强迫我。
“公子。”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很亲切,亲切得就像兄长,像孙皓那样,也许是因为他会唱《越人歌》,也许是因为他的清醒与智慧给我的指示。
没想到的是,他的唇很快下滑,攫住我的唇。
看着他受伤、无辜的表情,我心中抽痛,可是,他看得到我心中的伤吗?
不,我已经复立为皇后,一言一行太过惹眼,还是再等等表哥那边的消息。
“陈永说,碧浅不喜欢他。”刘曜忽然提起这件事,好像别有深意,“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临别前,刘曜抬起我的脸,在我眉心轻轻地吻。
“想不到陈永是痴情种。”我轻笑,有点僵硬。
是啊,他这么说是可行的,百姓饱受兵祸之苦,做梦都想着战火连绵的日子立即结束、天下太平的那一日快快到来,成都王秉承先帝遗诏,即皇帝位,名正言顺,不该有人非议、讨伐。
我缓缓道:“我是嫂嫂,成都王是小叔子,仅此而已。假若非要说我和他有什么,那就是他想利用我这个废后,为他争取一点裨益。先前我觉得他颇有才干,手握强兵,忠君爱国,能够辅佐陛下佑护大晋江山,再者他姿容俊美、风度翩翩,我对他略有好感。可是这次他据守洛阳,多次向我表明心迹,竟然是利用我。”
我淡然道:“翾儿还在我手里,怕什么?”
司马颖握着我双臂,掩不住激动的神情,“容儿,你会帮我的,是不是?”
这夜,碧浅和表哥陪着我来到华林园。
其实,与其说他的呆傻误了朝纲、家国、天下,不如说是先帝、他的父皇误了这天下苍生。
“皇后不必太担心,王爷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避过这一劫。”碧浅总是宽慰我不要胡思乱想。
每日,表哥将得来的消息告诉我。
他走过来,从身后抱着我,悲伤含情的嗓音令人动容,“就算我利用你,对你多有欺瞒,可是,我对你的爱,日月可鉴。你嫁给皇兄,朝不保夕,废立数次,就连小小的洛阳令、一介武夫都可以下废后令,几度濒临生死,你可知道我多么担心、心疼?我爱你,皇兄无法给你的安稳、荣华,我想给你,而只有我取代皇兄登位九五,才是最圆满的,这样我才能更好地保护你,我们才有可能厮守终生。”
司马颖得不到我的支持,没有再强逼我,怅然离去。
“你这种粗暴的人,我很难再相信你;再者,你一次又一次地食言,不守信诺,我如何相信你?”我心灰意冷地说道。
我啃完烙饼,他递给我水囊,我举起来就喝,想不到水囊中装的不是水,而是烈酒。我被烈酒辣到了,剧烈地咳起来,他拍着我的背,满目疼惜。
我应该帮他吗?应该为他多年的筹谋与艰辛献出一份力吗?应该终结这场持续多年的天阙内乱吗?只要我出面,也许司马颖就能顺利登基,就能力挽狂澜,结束内乱,整顿朝纲,让动荡的山河不再动荡,让流离失所的万民回归家园。
这样的静默,气氛越来越压抑,刘曜忽然起身,拽着我来到简陋的木板床上,我骇然一跳,立即推拒着,他轻而易举地推倒我,压下来,制住我双手。
八月,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录尚书事,执掌朝政,成为新一任权势滔天的权臣。
我笑了笑,他竟然为我剪除了宫中唯一的敌人,可是,他怎么会有这么绝妙的处置法子?
当年的繁华锦绣、风流韶华不复存在。
“陛下不先进膳,臣妾就永远不说了。”我含笑威胁道。
先前是谎话连篇哄骗我,现在是利用我,这教我情何以堪?
今年,我二十五岁,司马衷四十八岁,接近半百,我嫁给他,已经六个年头了。
刘曜的声音越来越大,像是雷霆震怒,怒火直喷我的脸,几乎将我焚烧殆尽。
想不到他发怒的和_图_书时候这般可怕,一如猛虎出笼,张开嘴就能把人一口吞掉。
因为,东海王麾下大将攻克河桥,畅通无阻地进逼洛阳,大军压境,司马颖没有胜算,只能先行离去,放弃洛阳,直奔长安。
唱毕,青衣转过身,望着我,却好像没有看见我,好像我只是一缕无形的风。
可是,再怎么艰难,我也要反抗到底!
“虽然你是废后,但你出身高门、家世清贵,你所说的有很大的说服力。再者,你是皇兄的妻子,没道理胳膊肘往外拐,是不是?你向臣民出示先帝遗诏,说明你忠于先帝的遗愿与旨意。”
久违的男子歌喉,熟悉,浑厚,哀伤,苍凉……心头猛震,我循着歌声传来的方向,奔至瑶华宫,碧浅和孙皓也一路跟着我。
刘聪曾经说过,司马颖有几次机会带我离开洛阳,可是,他放弃了,为了权势、为了帝位,放弃了一次次良机。
我走向床榻,但听他悲声道:“容儿,诸多兄弟中,我自认为才智谋略远远超过其他兄弟,可惜父皇把帝位传给了痴傻无能的皇兄。这么多年,我苦心孤诣地经营,算计筹谋,就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继承大统,让大晋在我的治理下永享太平、国泰民安。可是,内斗多年,希望越来越渺茫,现在河间王和东海王的决战胜负将分,正是我夺位的好时机。有先帝遗诏,只要你助我一臂之力,我就能顺利地登基。”
“那又如何?”刘曜注目于我,反问道。
他说的对,离开洛阳去找司马颖,始终太过草率。
我拼命地扭动,却无济于事,无法撼动他分毫;他啃咬着我的乳蕾,那股尖锐的痛意击中了我,我弓起身子,惧意涨满了心间。
“你没有和家人一起过年吗?”
他略有慌张,“我不是故意的,容儿,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过了半晌,他重重叹气,嗓音里微含歉意,“刚才是我冲动,我向你赔不是,以后再也不会了。”
他拍拍我的手背,“别担心,眼下河间王和东海王这次决战胜负已分,大局已定。东海王不会让成都王一直据守洛阳,也不会让这场决战再拖下去。”
他问:“好点了吗?”
“想去就去,无须犹豫,率性而为,有何不好?”青衣温和道,眉宇间似有怅然,“不过,我想提醒姑娘,倘若你去了,找到那人,自然是好,可是万一找不到呢?再者,找不到那人倒也没什么,假若你身处险境,那就无法做出弥补了。”
忍回眼中的热泪,才发现碧浅不在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在了。
我惊惶地叫了两声,她没有回应,我觉得奇怪,正想往下走,却有人登上来,脚步声略重。
“以后再也不会了……我不会再动粗了……”刘曜真的急了,“容儿,相信我。”
天地之大,他身在何处,我从哪里找起?就算孙皓陪着我去找,可是前路茫茫,去哪里找?还不如等孙皓有了他的踪迹,再去找他也不迟。
正中他的下身,刘曜闷哼一声,捂着下面,我趁此良机、迅速地爬起身,往外面奔去。
青衣凝视我的双眸纯澈、漆黑,“偶尔来,如若姑娘想见我,可在瑶华宫前这株树上绑一方粉红丝绢,我就会在此等候姑娘。”
半个时辰后,碧浅为我卸下钗钿,问道:“刚才,皇后为什么不让奴婢说?”
我摇头。
“你一再利用我,多次放弃我,多日前,你对我说了那么多甜言蜜语,现在却要我帮你夺位,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我怒道,泪水夺眶而出。
对,我应该帮他!我必须尽快回去,对司马颖说,我愿意帮他!
殿中只有碧浅在,我吩咐道:“碧浅,服侍陛下坐下进膳。”
“我落在你的手里,反抗不了,也逃不了,被你囚着,任凭你为所欲为,你捏死我就像捏死一只蝼蚁,我还能怎么样?”我漠然以对,“不如你现在就一掌打死我,一了百了。”
“我做错了很多事,我想弥补,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希望他能为我解惑,或是给我一点启发。
想通了之后,我问:“公子时常来这里吗?”
半个月后,司马衷大赦天下,改元光熙。
“现在我担心的是他还会来烦我,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做出一副苦恼、不胜烦扰的样子。
换言之,司马颖还没有死,一直在逃,我应该去找他吗?
我悲愤道:“够了!原来我爱的男子竟然是一个满口谎言的无耻之徒!”
不知怎么回事,额头磕在床头木板上,剧烈的痛陡然袭来,我好像闻到了血腥味,头很晕,黑暗如潮水般涌来,淹没了我……
走进瑶华宫,昔日的一幕幕从眼前晃过;走上二楼,屋中空旷,只有一张木案,孤零零的。
他半信半疑地问:“他利用你?利用你什么?”
给他夹菜,司马衷欢天喜地地吃着,不顾形象,好像一整年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膳食了。
如果不是身处绝境,司马颖不会再次利用我,不会想着以先帝遗诏的法子即位,他这么做,虽然是为了自己,圆自己的皇帝梦,可也是为大晋着想。
我朝他走去,碧浅和孙皓留在当地,没有跟来。
他转过脸,嗓音沉沉,“明日我就带你走。”
看来,他没有告诉我实情的打算。虽然我有很多疑问,诸如他离开金墉城后https://m.hetushu.com.com去了哪里,在哪里栖身,为什么在华林园,等等。华林园不是闲杂人等可以出入的,但我知道他有着看透世情的大智慧,不同于凡夫俗子,不问也罢。
我慌张地解释道:“你听我说,我和成都王没有私情。”
“河间王、东海王和文武百官不会觉得我与你合谋吗?”
“陈永说你发生了一点事,我就赶来瞧瞧。”刘曜拿了一个烙饼递给我,“还热着,吃吧。”
只要我出面,向大晋臣民说我发现了先帝的遗诏,说先帝属意成都王司马颖即皇帝位,也许很多人会相信。
不是不信你,而是我已经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你和何乔的密谋,是你权欲熏心。就算你再如何信誓旦旦,再如何情真意切,我也不会被你蒙蔽双眼。
我瞪向她,她不情不愿地收口,没再说下去。
他会像刘聪一样残暴吗?他会不会丧失了冷静与自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只是,宗室诸王当中,已经死了很多人,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他是无辜的吗?
寒风袭身,可我并不觉得冷,因为他不是拥着我,就是握着我的手,与我如胶似漆,俨然恩爱情深的夫妻。每每我想着司马颖、心神不宁的时候,他就会问我怎么了,我都以额头痛这个借口来打消他的怀疑。
我笑言:“我来这里散散心。”
“你来了。”青衣的声音无波无澜,没有再见到我的喜悦。
碧浅道:“陛下若想为皇后出气,就赐死前贵人,前贵人……”
我知道,她担心司马颖在司马衷面前说她在洛阳的所作所为,担心被司马衷遗弃,就赶紧回到他身边服侍,哄他开心。只要把他哄住了,她就不会死,也不会被遗弃,说不定还能恢复贵人的名分、地位。
再过一日,表哥匆匆赶来,说司马颖来不及赶来金墉城与我告别,已经匆匆离开洛阳。
司马颖,你究竟在哪里?
而司马颖呢?
这句话好像大有深意,我觉得,他的笑和以前不一样,别有一种冷酷的意味。
“容儿,怎么了?”他略有着急,发现了我的异样,“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到底怎么了?”
“你——”司马颖惊了,面色剧变,不知所措。
我激烈地挣扎,以各种法子掀翻他、推开他,因为,我不想再重蹈覆撤,不想再委身任何可恶的男人,我羊献容只属于自己!
可是,我看不透。
如今看来,司马颖真的是这样的人,真的会为了皇帝梦放弃我。而今日,他为了坐上太极殿那至高无上的龙座,摆明了利用我这个废后、庶人。
是啊,这是一个死局,周而复始;假若司马衷一直在位,势必有宗室变成权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此一来,这权臣就变成诸王讨伐的对象。
刘曜的语声里含着款款情意,“你额头上的伤口不太深,我给你敷过伤药,包扎过了,应该没事了。时辰不早了,早点歇着吧。”
“容儿……”他双臂用力,想将我拥进怀中。
洛阳落在东海王司马越的手中,全城戒严,风声鹤唳。
“陛下吃饱了吗?”我笑问。
“那是怎样?”他的神情变得很邪恶,心中仿佛藏着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猛兽,露出白森森的尖牙,“司马颖为什么救你?为什么三番四次来金墉城看你?为什么多次留宿?为什么……”
那年,我刁难他,拒绝跟他回邺城,他被我伤了心,伤得很重,就做出那些僭礼无德、无视国君之事,大失人心,才会招惹其他王爷的合兵讨伐,才会从人生的最巅峰跌落,走向另一个转折,才会一步步丧失了他曾经握在手中的一切。
“匈奴男子都是痴情种。”他云淡风轻地说道,“为了得到喜欢的女子,匈奴男子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目龇欲裂,黝黑的脸膛像是泼了血水,风起云涌;他用力一扯,衣袍撕裂,我身上没有了遮蔽的衣物。寒意袭来,可我感觉不到冷,只觉得害怕,从心中扩散的惧意,流窜在四肢百骸。
他关上门,拉着我回屋,我坐在简陋的床上,心中惴惴,“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这是司马越的主意。司马颖曾经是手握重兵的皇太弟,在邺城颇有声望,如果他潜逃在外,始终是司马越执政的心腹大患。因此,司马越不会放过他。
他瞪着我,嗓音里似乎压抑着怒火,“就算你不愿意,我也要带你走。”
这番话,多么动听,多么感人,假若是以前,我会感动得无以复加,会欣喜若狂。可是,此情此景,我无法投入太多的感动,疑心和芥蒂让我无法再完全相信他。
我转身向床榻走去,却被司马颖拽住,“容儿,你真的不愿意帮我?”
陡然间,刘曜攫住我的唇,蹂躏地吻,疯狂地咬……我极力闪避,却始终躲不开他的追逐。
他开心地笑起来,拉着我的手臂,“容姐姐,再次见到你,朕太高兴了。”
我预感不祥,问:“陈永不会做出伤害碧浅的事吧。”
也许是因为刚刚确认了他与何乔的密谋,太过惊痛,才会觉得自己被他利用了吧。
我不知道,只是越来越觉得,他可怜可悲可叹,我起了恻隐之心,怜悯他。
他淡淡一礼,唱着那曲《越人歌》,缓步离去,犹如一个仙风道骨的道士。
心跳加剧,我喘着粗气,一眨不眨地瞪他
和*图*书。
“我怎么做,你才会相信我?”
这些年,洛阳被士兵劫掠过,激战过,被大火焚烧过,被浓烟熏过,被尸首堆积过,早已破落不堪,满目疮痍。华林园也被那些烧杀抢掠的士兵糟蹋过,树木零落,花圃变成一片贫瘠之地,亭台楼阁破败得令人痛惜,断井颓垣,到处是火烧烟熏的痕迹。
表哥说,碧涵也离开了洛阳,只带了几个宫人前往长安。
青衣没有死!青衣还活着!
“你知道我为什么匆匆赶到洛阳吗?”
可是,近来很担心司马颖,想着他究竟是生是死,在哪里落脚,心事沉重,烦郁无法排解。
假如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密谋,我真的会帮你,可我知道了,我无法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按你的意思祝你一臂之力。我想知道,先前你所说的那些话,隐居避世,过一种宁静、开心的日子,是真心的,还是哄我的?是为了赢得我的欢心与信任,让我对你死心塌地,才说的花言巧语?
紧接着,他派人来金墉城接我回宫,复立我为皇后。
我没有回答,没有表态,我不能激怒他,必须想个法子让他改变主意。
是我害了他,一切都是因为我。如此,我更应该帮他夺位,让他以先帝遗诏登上帝位。只要有先帝遗诏,他就有可能赢得民心、赢得文武官员的拥护,就有可能以他的睿智、谋略威慑宗室诸王和朝廷,重新创立天子、朝廷的威严与神圣。
他扯开自己的衣袍,身子稍稍抬起,我趁机抬起膝盖,往他的要害处顶去。
怎么办?
河间王司马颙杀了张方,以张方的人头向东海王司马越求和,可是,东海王拒绝了。
“我也不知道他想怎么利用我,但我发觉了,今日他说要复立我为皇后,向东海王投诚。我训斥他几句,就吵了起来,后来他气色不太好,或许是因为被我骂了,觉得颜面无存,就走了。”我拣一些无关紧要的瞎编乱造。
他的话一字字从齿缝间挤出来,“如果你们没有私情,为什么他三番四次留宿在你的寝殿?”
回到宫城的那一日,晚膳时分,宫人奉上粗食,我正要吃,司马衷就来了。
河间王败逃后,东海王大将率领鲜卑骑兵进入长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杀了二万人,日光四散,赤红如血,哀嚎遍野。
“哦,原来如此。”他看着我,目光犀利无比,“陈永对我说,他认定碧浅是好女子,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妻子,他不会放弃,一定会设法打动她、得到她。”
次日午时,表哥赶来金墉城,说已经传话给司马颖了,不过司马颖忙于军务,一时走不开。
在深宫内苑等待、期盼、煎熬的日子,一日犹如一年,漫长得好像没有尽头,焦虑得似有文火焚心。可是,我什么事也做不了,只能等候孙皓带来好消息。
“当真只是如此?”他仍然心存疑虑。
刘曜嗤之以鼻,“晋廷宗室已经死了那么多王爷,被毒死,被火烧死,手足、亲人惨死没多久,这二王的下场可以预见。”
醒来时,我躺在床上,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
“若想弥补,就去弥补,无须犹豫。”
“刘曜,如果你再次强迫我,这辈子,我不会原谅你!”我森寒道,“我羊献容说到做到!”
“没有为什么。”刘曜的眼中跳跃着火焰,却是冰冷的火焰。
“王爷当真有过与我隐居避世的念头?不是哄我开心才说那番话?”我终究忍不住,问出心中的疑团。
细想起来,司马颖丧失了兵马、落魄至此,其实还是因为我。
屋中没有人,只有一盏灯烛,我静下来想了想,不是刘曜就是刘聪,我必须趁他不在赶紧走。
我微微屈身,“谢谢公子。”
刘曜付之一笑,“不好说,我无法保证。”
司马颖看着我,脸上的慌色渐渐消散,冷静下来。
我发狠道:“你可以强迫我,但我告诉你,就算你得到我,我死也不嫁你!我死了也会恨你!”
司马衷被河间王、官员遗弃在长安,六月初一,他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洛阳,坐在熟悉的太极殿龙座上,俯瞰那些熟悉的文武官员,君臣相顾,哀感流涕。
前几日我的拒绝,终究让他失去了登位九五的良机,我再次害了他。
“八年前你已伤害我一次,八年后你还想摧毁我吗?”我幽冷道。
“为什么不帮我?”顷刻间,他变成一个任性的孩子,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大吵大闹,“太极殿那龙座,我只有一步之遥,为什么你不帮我?你到底爱不爱我?”
我道:“倘若陛下有心册立她,我又能怎么样?”
五内隐隐作痛,我只能在冰冷而破败的金墉城枯守着,暗无日月,天地俱黑。
屋中寂静,柴火哔啵做响,呜呜的风声充塞于天地间,犹如鬼哭狼嚎,怪吓人的。
这日,他和我在农屋的附近骑马、游逛,乡野一片静穆,萧条荒芜,翠绿的山野已经变成杀戮的战场,到处都有无人收敛的尸骨。
温柔与霸道兼而有之,深情与粗野仿若双生,我一动不动,任凭他汲取。
可是,他武艺高强,反应神速,手臂那么长,一个转身,他就拽住我的手腕,将我往回扯。
刘曜道:“陈永飞鸽传书给我,说你受人迫害,差点儿被杀,成都王突然出现,救了你。”
随驾的宫人将三碟菜肴放在案上,接着纷纷退下www.hetushu.com.com,只剩下我与他二人。
我拼死不从,就在这样的拉扯中,刘曜手上加大力道,我被他拽得跌回去,摔在地上。
此时此刻,我确定,他故意这么说的。他说陈永与碧浅之间的事,其实是在说他与我之间的事,他要让我知道,假若我有意中人,他得不到我,大有可能做出伤害我的事。
他的眸中跳跃着诡异的火光,很熟悉,与刘聪一模一样,那是一种足以摧毁神智、撕裂所有、令人崩溃的火。他盯着我,眸色如染,越来越暗沉,沉得仿如深潭潭底的暗无天日。
我知道,陈永会将我发生的事一一向他禀报,可是,我没料到陈永会瞧出我与成都王有私情,瞧出端倪。
就这样,他抱着我,我一动不动,许久许久……
醒来后,震惊地发现,我不在寝殿,而是在一户农家。
忽然之间,我惶惶不安起来,“你的意思是,东海王大军很快就会攻到洛阳?”
“昨日就到洛阳了。”他的声音很冷,有点怪怪的。
“我问过碧浅,她……已有意中人。”
可是,为什么心那么疼?
不!司马颖不能死!我怎么能让他死?他绝不能死!
如我所愿,过了几日,司马衷仍然没有册立碧涵为贵人,也不再宠幸她,给了她一份不闲也不重的差事,有内侍看着她。
“我是金墉城的活死人,陛下大赦天下,我就离开了金墉城。”
“哦,原来如此。”一想又不对,我又问,“那你怎么在这里?”
“当然不是。”他面色微变,“刚到洛阳,我真的厌倦了一切,想和你离开洛阳,找一出清静之地,和你厮守一生。后来何乔告诉我遗诏一事,我不想辜负父皇的心意,这才动了心思,想为大晋出一份力。”
他没有看我,清寒的目光落在火光上,却好像落在我身上,让人觉得那么刺。
接下来两三个月,司马越大军突破了司马颙所设的几道兵马防线,步步紧逼,逼近长安。
“表哥,我在想,东海王司马越掌权后,会不会有其他王爷讨伐他?”我问。
他慌乱地解释:“当然是真的,我怎么会骗你?”
“姑娘心事重重,是否有什么烦忧?”青衣总能一眼看透我。
“那陛下回去沐浴更衣,今晚好好睡一觉,明日臣妾再陪陛下玩。”
“这个不好说。”他寻思道,“如果东海王掌政后大失人心,必定有人不满。”
这一夜,我们只是相拥而眠。
我夹菜递给他,他一喜,笑着接过,又笑嘻嘻的了。
手中握着他送给我的玉刀,由于握得太久,这玉刀很烫很烫。
可是,我没有等到司马颖,却等到了他弃城而走的消息。
“你别跟我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们什么都没做。”
我慌了神,“那东海王不会放过他们吧。”
从相识的那一刻开始,他没有问过我的身份,好像对我的身份并不好奇。他只是唱歌给我听,我有什么疑难杂症,他会开导我,给我指出一条明路。他就是这么一个气若幽兰、心如止水、言行清淡的高人。
永兴三年(公元306年)二月初六,司马越遣几名大将奉迎皇帝大驾。
泪水如倾,心痛如绞,这个时刻,我很想转身背对他,宁愿看不透他。
今夕何夕兮……
可是,正要开门,屋门就被推开,刘曜矗立在门外,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
孙皓一直为我打探他的消息,可是,他总说没有他的踪迹。
可是,天下万民只会怨怪他,怨怪他的呆傻误了天下。
可是,他为什么在华林园?他不是金墉城的活死人吗?难道他从金墉城出来了?
额头的伤处的确还疼着,只是可以忍受罢了;我拂开他的手,别开脸,冰冷道:“假如这伤口再深一些,或是伤在要害处,我就死在你手里了,你开心了?”
忧心的是,司马颖究竟在哪里,是否安然无恙?
“吃饱了。”他接过碧浅递过去的绸巾,胡乱地擦嘴。
心那么痛,我放不下自己的惊痛与烦乱去助他一臂之力,因为我的任性,让他失去了这次千载难逢的夺位良机。
“爱?”他竟然这样质问我,竟然对我说出这样的话!心头落满了雪,我冷了脸、冰着眼,“王爷,这些年,你利用我多一些,还是放弃我多一些?”
心魂一震,我呆呆的,不知如何回答。
虽然很担心他再次兽|性大发,可是他信守承诺,没有再逼迫我。
“碧涵姐姐?”司马衷狐疑地皱眉,好像在想一件很重要的事,“她怎么欺负容姐姐了?容姐姐快告诉朕,她怎么欺负你的?”
脸颊好像有火在烧,也许是因为咳,也许是因为烈酒。
“只要你真心待我,不是糊弄我,我就相信你。”刘曜揽过我的肩,侧搂着我。
我静静地看他,想看清楚眼前这个男子的真面目,想看清楚他的心究竟是怎样的。
倘若我太过抗拒,会惹他怀疑,我只能随他的意。
我应该帮他,不应该总是觉得他利用我,更不应该被那虚妄的痛楚蒙蔽了双眼;既然爱他,就应该付出所有,不遗余力地帮他,助他一臂之力。
他离开后,我难抑心中悲痛,哭倒在床……昏昏地睡过去。
不!不行!我一定要阻止他!
“好耶,容姐姐,就这么说定了哦。”司马衷拍手叫好,接着蹦蹦跳跳地回去了。
“我怎么会和小叔子有私情?和-图-书虽然成都王比陛下俊美年轻,但他只是利用我,我怎么会……刘曜,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肯相信?”我不耐烦地叹气。
一日,我到华林园散心,碧浅陪着我。
他不肯松手,死死地抓着我的手腕,“容姐姐,容姐姐跟朕说说,你一人留在洛阳,有没有人欺负你?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朕,朕治他死罪。”
我轻咬着唇,思忖着他为什么突然来洛阳,为什么突然有这个决定,他是否发现了什么。
“不嘛,容姐姐先告诉朕……”他摇晃着我的手臂,半是恳求半是耍赖。
“姑娘怎么也来这里了?”青衣徐徐笑问。
他站在瑶华宫前,孑然一身,形销骨立,衣袂飘飘,熏黑的断墙让他给人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好像他已经不是俗世中人。那袭素朴的青衣那么熟悉,那张青铜面具锁住了他的面容,他站在天地之间,断井颓垣之中,仰望天宇,唱着一首苍凉的《越人歌》。
可是,刘曜说,黄昏时分再送我回金墉城,要我陪他一日。
四目相对,我目光冰寒,他眸色沉鸷。
他如何潜入我的寝殿,如何带我出宫,我一无所知,他可真是神出鬼没。
我惊震道:“你想怎么样?”
司马颖更急了,“容儿,你不信我?遗诏一事,的确是何乔告诉我的……”
刘曜疯了似地咬我、吻我,就像一只饿了三日三夜的猛虎,咬得我全身疼痛,在我身上留下一个个可怖的血口;我只觉得全身都散架了,双腿酸软,双臂疼痛,他庞然大物似的身子压得我喘不过气。
虽然他呆傻、失智,但也并非完全傻掉了,他也知道被人挟持、软禁的痛苦与无奈,也知道这天下已经大乱,自己的手足、亲人正在骨肉相残,也知道这大晋江山变成生灵涂炭、流血千里,是他的错。因此,他怎么可能过得舒心、自在?
五月,司马颙弃城而逃,单骑向西南狂奔,逃进太白山。
“是,我和成都王有点交情,但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急急地辩解。
这个瞬间,心隐隐作痛,“我是废后,是庶人,他们会相信我所说的吗?”
他点点头,语气十分笃定,“河间王和成都王必败无疑。”
他坐在火堆前,火光映亮了他的脸孔,那冷峻无温的神色分外瘆人,“容儿,我决定了,三年之期太过无稽,我不想等。”
我仍然不说话,微抬下颌,不看他一眼,整出一副冷傲的模样。
先帝不该立他为太子,不该传位给一个连自己都无法保护的傻子。
我躺下来,他也跟着躺下来,搂着我。
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身心很放松,没有任何负担,也能得到不少启发。
“一有王爷的下落,我一定立即告诉你。”孙皓信誓旦旦。
难道他和刘聪一样暴戾?
五脏六腑似有火烧,那么痛……
回金墉城当夜,我就派人让孙皓来一趟,因为,我想让他传话给司马颖,我想见司马颖。
“河间王会这么想,但只要大晋臣民相信这份遗诏是真的,我就赢得了民心;废掉皇兄,我即位为帝,就是民心所向,是不是?”司马颖说的头头是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不要碰我!”我愤怒地推开他,“遗诏一事究竟是真是假,我还有分辨之力。”
“为什么?”我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冷静。
本以为就此告别,却听他以冷沉的声音警告道:“容儿,最好不要骗我,如若我发现你与司马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私情,我不会放过他!过阵子我再来看你,你一人在洛阳千万小心。还有,三年之期,我会遵守,我希望你也会守诺,如若不是,我会做出什么事,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我想弥补的那人,不知所踪,也不知道生死,公子,我应该亲自去找他吗?”
“陈永还说,你与成都王似有私情,我不相信,特意赶来洛阳瞧个究竟。昨夜我抵达洛阳,今日我乔装成侍卫,守在你的寝殿前。”他一字字地说道,语声充满了力度,“我亲眼目睹,司马颖进入你的寝殿,很久以后才出来。”
我点点头,慢慢地不咳了,一笑,“我没什么事,你别担心。前贵人想害我,不过已经没事了。”
我动了动,惊醒了趴在床边的刘曜。他惊喜地握着我的臂膀,问:“容儿,你醒了,头还疼吗?”
她忧心忡忡地说道:“万一陛下再次册立碧涵为贵人呢?”
破败的园子虽然修缮过,但国库空虚,年年征战,朝廷与民间的财宝早已被洗劫一空,园子只是简单地清理打扫过,不可同往日而语。
他的狠辣与粗暴,比刘聪有过之而无不及。
“和容姐姐分开这么久,朕想死容姐姐了。”他终于吃饱了,搁下碗箸,打着饱嗝。
又过了须臾,刘曜沉声道:“好,三年之期,我会等;但我希望你不要骗我,你与司马颖之间的私情,我会查清楚。假若你还和他纠缠不清,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
他的唇是刀锋,割下一片片的血肉;他的舌是冰锥,扎出一个个血窟窿;唇很痛,我似乎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头晕目眩。我抵挡不住他高歌猛进的攻势,步步后退,片片沦陷。
他再三地追问我是否愿意帮他,我凄然一笑,“今日身子不适,我要想想,明日再议吧,我先去歇着了。”
物不是,人已非,司马颖,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