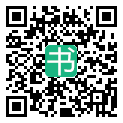第四十四章 伤离魂,金闺梦里人
司徒凌黑眸盯紧我,看不出是火还是水的混乱情绪在其中翻涌。
他凝视着我,忽然笑了,“若我说有十分真心,你会信吗?”
转身要走,司徒凌忽然道:“阿永死后有端木华曦相伴地下,不知我死后,又有谁来相陪?”
抬起头,阳光早已不见,四处铅云密布,冷风飕飕。枯黄的野草和矮矮的坟茔在风中呻|吟着,号啕着,却不见半滴雨水。
这是她第一次依着司徒永的称呼唤我。
他哑声道:“我是看到了那些鲜血,可我一样希望你信我,希望阿永信我。子牙山艺成归来,母亲看我长成,才敢跟我提起这事他跟我说了多少次,秦家是仇人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可我听到一个”秦“字,便只能想到你,想到想到你像一注清泉一样,亮晶晶地笑着,终日跟在我的身侧,我从小便把你当做未来的妻子看待,认定了会执手一生还有阿永我不耐烦他看着你的眼神,但我始终把他当做亲弟弟般看待……”
朝中多人建议派出秦家军主将秦晚前往北疆坐镇,并遣出目前镇守在京畿以北的秦哲所部近两万秦家军。司徒凌留中不发,却从南方调派兵马,开往北疆支援秦家军。
然后,他无奈地走上前来,为我们披上自己的衣袍,用他结实的臂弯拥住我们,有些不甘地说道:“为什么你们俩一起玩时,常把我撇在一边?”
它空着鞍辔,茫然地跟着司徒凌,待见到我,才长嘶一声,嘚嘚地跑过来,用它湿湿的大嘴磨蹭着我的脖颈。
芮帝司徒永登基才半年多,因连番遭遇太妃。太后薨逝,伤恸而病,并于送太后灵柩入地宫后不治而亡。因其少年无子,朝臣拥立其堂兄司徒凌为帝,改无弘睿。新帝司徒凌为堂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上其庙号为孝烈。
十日,足以让我来回狸山一次。
他们用白玉做成一个箱子,外面饰以明珠,让箱子内部始终保持着苍白却毫无变化的颜色,再让他们寄予厚望的女子同时服下了令其四肢麻木的药和令其神志异常清醒的药,然后关入箱子,埋入地底,只留一个小孔透气。
我身体一倾,将司徒永护于身下。
司徒永自以为帮到了大师兄,也帮到了小师姐,曾经很是开心。但小师姐常常头晕目眩,噩梦频生,又让他有些发愁,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会好转,那一年,父皇因久无子嗣,终于召他回京。他成了晋王,依然无意在朝政上用心,甚至常常不回宫,只寄居在司徒凌府上。
柔然闻得芮国动荡,趁机发兵攻芮。秦家军抵敌不住,撤军到燕然山以北,与柔然军队僵持。
后肩骤痛,箭镞深入骨髓,几乎将我钉穿。
他终于讲完了,手指缓缓地抚着我掌中的梅花锦袋,低低地问着我。他的额际渗着密密的汗珠,虚浮雪白的面庞上,有散落的一缕乌黑发丝飘过。
我向前方那个唯一聪明人笑了笑,“凌师兄,今日好威风!”
我穿的是女装,伴我前去沈小枫闲来没事,每日变了法子为我绾着灵蛇髻、惊鹤髻,望仙髻或百合髻,然后敷了胭脂,佩上承影剑。虽然还是瘦得不像样,到底有了几分原来的飒爽英姿。
我疲惫答道:“对,即便我领情,我也跨不过那么多亲人的鲜血。你能吗?”
“我只需十日。”
但始终一无所获。
他拉了个满弓,对准我。
身后,传来司徒霠惨痛至极的呼号,惊天裂地,如同被逼到困境无路可走的猛兽。
这里的美酒是用鲜血酝酿而成,这里的百花是用鲜血浇灌而成。绚丽多姿的霓裳,步步生莲的身姿,温柔如水的笑容,一点一滴,都是他人和亲人的血肉编成。
许久,他眼底的湿润和眉宇间的狂躁慢慢地褪了下去。
他的目光无悲无喜,便那么沉寂地看着我。
而我和他共同的师弟已在我的怀抱中冷了,再不知是去了天堂,还是地狱。
不论原来他是什么打算,但我到底能看出,至少,他现在其实并不希望我死去。
隔了一两年,他到底不甘心,借口出去游历,独自奔到南梁四处行走,想着小师姐的性情,一定不甘心总在一个地方参禅的,他也常到江南繁华地四处行走。
不过,他真的这样说过吗?
司徒永见秦惊涛和司徒凌都放弃了追查小师姐的下落,大失所望,又怕自己在司徒凌身边被人识破身份,遂回了子牙山。但往日热热闹闹的三人行只剩了他一个,心里的凄凉自是不必多说。
穿过前方正打斗着或者说正屠杀着我们部属的大队人马,司徒凌一身玄衣,骑了他的乌云踏雪马缓缓而来。
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明白,帝宫九重,九重帝宫,无非是九重华丽的陷阱。
第二天,我亲自到武英殿求见司徒凌,要他追封端木华曦为皇后,与司徒永合葬。
但他终究没有踹下来,只是眸光沉暗地望向我,许久,才凄恻一笑,低声道:“别坐地上了,越高的地方,凉气越重。你没瞧见,坐到这个位置的人,血都开始冷了——若司徒https://m.hetushu.com.com永多当两年皇帝,暗算起我这个师兄来,只怕比秦家当年对付我父王更要狠毒十倍。”
卫玄答道:“秦惊涛有旧疾在身,活不了多久,他的儿子非病即残,也不中用,只有个女儿好,便是把农业挣得再大,也不过为小侯爷奔忙而已!”
有人过来把我和司徒永从箭丛中抱出。
身后,传来嘈杂的马蹄声,然后是呼喝声,打斗声,惨叫声。
有水滴落下来,落在他的脸颊。
我向他磕了个头,然后扶着龙案,强撑着站起身来,拖着隐隐作痛的伤腿,踉跄着走出大殿。
他便道:“既然你不会信,我又为何要向你坦白?你把十分真心留给了他人,我又为何要留给你十分真心?”
他肯定地说着,句尾的疑问中却带了星子般微微闪亮的希冀。
何况,他是同谋者。
我沉默片刻,答道:“我和永师弟一样,愿赌服输。我们从不是聪明人,当然不可能比定王殿下聪明。”
没有人觉得那是怎样了不得的苦楚惩罚。只是所有人都如坐针毡。
他身体一僵,“什么意思?”
我盯着他,往日一家团团圆圆围桌而坐的欢笑情形,在一个个年轻生命陨落的血光四溅中一晃而过。
他是为了权势,为了秦家军,才打算娶小师妹的吗?
他甚至只是生擒了沈小枫,待我回北都后依然把她送到了我身边侍奉我,只是我身边更多的则是他的亲信侍卫,竟把未央宫封得严严实实,再不容我踏出皇宫半步。
每天要歇下的地方,也早有快马提前过去预备好了,饮食医药料理得极妥当。我尽量多吃食物让自己恢复体力,反而是沈小枫吃不下什么东西,脸色蜡黄蜡黄。
于是,他设法接近端木华曦,并搬回宫中,以温雅有礼的姿态频频出现在端木皇后的跟前。
他看着我,沙哑着嗓子道:“安县八万精兵,都已到了距离北都不到三十里的地方驻扎。与神策营首尾呼应,御林军很快会得到皇帝驾崩的消息,将会成为一盘散沙。北都尚有你兄长,和一万八千多秦家军。你是聪明人,不想他们悦皇帝殡葬吧?”
那时他也才十五六岁,身手相当高明,可到底在山野间长大,未曾经历风雨,眉眼间一团稚气,看着比“盈盈”还小出一截,淳于望倒也不曾留意他,竟让他一路寻着踪迹跟到狸山,并查到了他们在狸山的住处。
下雨了吗?
卫玄笑道:“王妃英明!”
他的脸色苍白,黑发凌乱地散落在汗涔涔的面颊,像刚从地狱中爬出。
我只是着实心疼这个无辜卷入纷乱争斗中的师弟。
司徒永用他的手指从我的眼旁擦过,指间便一片水渍。低声道:“我知道我错了,错得离谱。卷入这权势之争,一切身不由己。连我都开始学着猜忌,甚至猜忌你为什么我要把你带回来?我再也没见到你快活的笑容。我该让你自由自在生活在南梁,我自己也该带着华曦远远离开那所谓的九重帝宫晚晚,那里不属于我们……”
她便粲然一笑,艳若桃花,“谢谢师姐。”
我早该离了这里。
一步一步挪向台阶,我又看了一眼高台之上那座万人仰望的大殿。
天色已暮,但我跟他相处时,竟没有一个宫人敢入内掌灯。
他听话地应了一声,也如小时候被人欺负得无路可走的小男孩那样乖巧着。
她道:“其实我们并不属于这里。”
被熏得暖洋洋的空气里飘着凝滞的血腥味,这种气味对于落胎两次的我已经不陌生。
结局都已是一样。
他柔声叹道:“晚晚,即便我们这样相拥着死去,也再无师兄过来为我们披上一件衣袍吧?”
中了那个什么见鬼的移魂术后,我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
我推开他,却用力太大了,浮软的身子便受不住,自己一跤摔在冰冷的金砖地面上,嘶哑地笑了起来,“于是,你对我用了移魂术,让我要么疯掉,要么命不长久?于是,你亲手将阿永射死,一箭不够,再添上一箭?”
清脆的一声,司徒凌手中的茶盏碎了。
她便望向我,“听说,他去时,你在他身边?”
他抬起袖子,按着自己的额,笑得居然也是那般凄凉,“谢谢你还能说一句不信。可如果我告诉你,跟素素只是酒后冲动,一时把她当做了你,你大约也不会信吧?”
夏王妃一笑,问道:“听说那丫头目前挺好的。”
司徒永微笑,向我摇了摇头。
“大约多久会死?”
我总算不负端木华曦的那声“师姐”。
孤零零的身影,高傲倔强,一意孤行,果然是我或司徒永怎么也无法企及的帝王风度。
也许有过吧?
我想去看一看。
“不知道。”我答道,“总之不会是我。髀肉复生,僵卧床榻而死,于秦家人才是死不瞑目。臣愿为皇上效忠,马革裹尸而不悔。”
她凭什么相信他,而不去相信现在正和她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大师兄?
雪白的尾羽在眼前颤抖,司徒永也仿佛颤了一颤,身hetushu.com.com体便在我怀里越发沉了下去。
我心里一跳,却半丝惧意都无。他留我性命,只怕用意也便在此。
当时他并不知道该拿这个不认识自己并嫁给他人的小师姐怎么办,犹豫了许久,终于回了大芮,把前因后果告诉了司徒凌。
事实再明显不过,那个美丽的小尼姑在深夜遭遇地震和山洪,根本没来得及脱逃。那么大的天灾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再正常不过。而凡人就是把武功炼得再好,也难敌这样的天劫之威。
于我,亦如是。
但如果我愿意,我还是可以去看看别的妃嫔。
“这个就看王妃和小侯爷的意思了。安魂药不是毒药,没有人会疑心。何况秦家和那丫头信任小侯爷,分量重或轻,火候完全可以把握住。”
我低头问司徒永:“永师弟,你怕不怕?”
我拥紧司徒永,倚着坡地向前方凝望。
我微笑道:“我当然知道。不然,你以为我带你去南梁做什么?”
而我过去看时,的确看到了很多侍奉她的宫女太监,却没有一个是原来侍奉她的。
我点头,“是啊,他如果挣扎着活下来,只怕比死还艰难。便是永,也一定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这份活罪。”
司徒凌当即调来一批缟手,又带了司徒永一起前去南梁,把万佛山搜了一遍又一遍,秦惊涛不便自己前去,也派了相当多的人手前往南梁搜寻。
只是她已依在一个俊逸公子的怀里,注意力全在奶娘手中那个刚生的小娃娃身上,懵懂地与他对面走过,恍若不识。他故意在她跟前走过好几次,终于能确定,她是真的不认识他了。
渡江之时,她静静地坐在船头,对着北都的方向。
我淡淡望着他,并不接口。
是他查出了小师姐的下落,是他一手把小师姐从她的夫婿爱女身边拉开,推到了大师兄的怀抱中——也推到了死神的怀抱中。
我在万佛山失踪后,师傅无量师太苦觅不得,随即通知了秦家,当然也瞒不过当时刚回北都不久的司徒凌和尚在子牙山的司徒永。
司徒凌当时的脸色很怪,分不出是悲是喜,是怒是惊。他和夏王妃商议后,即刻通知了尚在北彊军中的秦惊涛,自己则带了司徒永、卫玄和一批精干部属,先行前往狸山。
她一怔,才领会出我是什么意思,急道:“大小姐,二公子还在北都呢!”
这时,夏王妃病重,司徒凌尚在边疆未及回来,他便常常过去侍奉,算是为自己的师兄尽点孝心。卫玄也已赶回北都,为夏表王妃治病。
她问:“晚晚师姐,你说,如果我死了,可以和阿永葬在一起吗?”
我便安慰了许多,抱住他低低道:“不错,有小师姐在,什么都不用怕。”
又是弓弦声响,回头看时,司徒凌竟又搭箭于弦,疾射而来。
“晚晚,你恨我吗?”
我问她:“是谁做的?”
若知道司徒凌对秦家原来有那么深的恨意,推断出这些来并不难。
所谓妻随夫贵,定王妃秦氏依例册为皇后,又有一秦氏姬妾,封为昭仪。秦皇后病重,册封之日都不曾出来受礼,但秦皇后的胞兄秦晚曾带病出现在朝堂,领一班文武官员向新帝朝拜。
若不是浸透地面的鲜血,或许我会认为这只是一场梦。
他做梦也没想到,虽然沉默寡言但待他们那等温厚的大师兄,竟会这样居心叵测。
“不,我愿意相信。”我慢慢走上前,轻轻抓过他的手,将他发冷的手指一一伸展,与他双掌相对,低低道:“可是皇上,你看到我们之间有多少鲜血了吗?透过那么多的鲜血,我信,或者不信,又有什么重要的?”
我蹒跚地立起身,回头再看那处箭丛,分明用森冷的羽箭刻出了两个相拥的阴影。
“离开定王府后才发现的,因此,素素完全不知情。”我不确定地看着他,“我甚至猜测过,你污辱素素,会不会也是报复秦家的一种手段。可我总不信,你会这么卑劣。我不信。”
卫玄在其完全崩溃时施法,再三暗示她,她是因为和那个叫浪于望的男子在一起才会经受这场折磨,她不能再想起他,否则这场苦楚可能会再次来临那时她的心智完全混沌,像一张白纸般随人折叠涂抹。终于有些知觉时,她对那个密闭的白色空间的恐惧,远甚于任何内敛的折磨。为了躲开再度袭来噩梦,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愿意忘记不久后,曾经的盈盈重新做回了秦晚,身体状况却急转直下,整整病了两个月。她在病中重新和司徒凌、司徒永相处,像原先在子牙山那样和师兄撒着娇,或者欺负自己的师弟。根本不知道自己生命已被人生生地剜去了三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三年。
我回头看她。
他居然一息尚存,满是鲜血的手探出。摸索到了我身后深深扎入的羽箭。
她凄然一笑:“谁做的并不重要,重要是的,大多人不想他生下来。即便生下来,他也未必活得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娶了她还嫌对秦家军控制得不够牢靠,和图书务必要置她于死地?
夏王妃叹道:“至少,得等那丫头掌了秦家兵权,然后再带着那支铁骑嫁到我们家吧?”
我们周围的地面和短坡上,如刺猬般插着密密麻麻的羽箭,在风中巍巍颤动。
所有关于那个小姑娘的消息,都停顿在前一晚做完晚课后回房休息的那一刻。
他还是那样讨厌朝中尔虞我诈的争斗,但他必须拥有足以保护小师姐并牵制司徒凌的力量。
“永……”
我笑了起来,“永师弟也这么说。”
我很庆幸当时没有给她任何名分。如果她是秦彻的妻子甚至小妾,如今我就没那么容易将她带出大芮。
司徒永听得手足冰冷,连气都喘不过来,悄悄回到自己住处,只觉得浑身冒冷汗,脑中空白一片。
我静默片刻,向他说道:“我想出宫十日,十日后,我会回来,让皇上的心腹大患彻底消失。”
司徒凌也正冷冷地看着我,幽沉的眼睛泛着莹光,有恨、有怒、有伤、有悲,还有着隐隐的脆弱和乞求我还没看懂他眼底更多的意味,他的箭镞忽然微偏。嗖地离弦而出,径直奔向司徒永的前胸!
“十八年前,夏王临登基前被一名姓吉的内侍所杀,人都说是夏王御下太过暴虐招来的祸事,只将那吉内侍凌迟处死了事。但不久后,厉州有一户姓吉的人家全家暴死,据查便是这内侍未入宫前的私生子。他们中的,是来自燕然山的毒瘴。这毒瘴即便不是秦家人所下,也必与秦家有关。后来淳于望把这种毒瘴交给了端木皇后,端木皇后甘愿用这种毒瘴自尽,一是想让司徒永疑心秦家,不致让华曦失宠,二是给淳于望机会,让他说明秦家和定王有着血海深仇,以阻止我和你继续在一起。后来我小产出血,差点死去,淳于望并没敢把这事说出来,偏偏我阴差阳错地又发现了当年的那桩血案。”
我慢慢道:“好好对素素。秦家纵有欠你的,家破人亡再加四条人命,也该还得够了。”
他们于这个被人刻意抹掉过去的“盈盈”完全是陌生人,但她似乎对司徒永还残留着往日熟稔和信任,司徒永听从师兄的吩咐将她引了出来, 让卫玄施术,试图唤起她对于过去的记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她是因忘忧草而失忆,卫玄的巫医之术一样可以唤出部分潜藏的记忆。
他的身旁。是我留给沈小枫骑的紫骊马。
即便现在有人告诉我,是司徒凌亲口喂了我毒药,我都不会觉得惊讶了。
我坦然看向司徒凌,“夏王暴戾专横,不念私情,若是称帝,秦家那支虎狼之师早晚是他的眼中之钉。我相信,应该是我祖父或父亲在权衡之下选择了收买内侍暗杀夏王,扶立性情瘟懦的锦王为帝。他们自以为做得干净,你们母子并不知情,看着你对我好,对秦家长辈也恭敬,因此将你容了下来,还当做女婿般看待。但事实上你早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隐忍多年,依然不忘为父亲复仇。是你派人向端木皇后告发了祈阳王下属闯宫送信之事,让德妃姑姑百口莫辩,也让秦家与端木氏、司徒永的裂痕越来越深,是你出卖了司徒永,让他因与南梁私下交往而被囚,成为端木氏的弃子,让秦家完全失去保护,也是你让伏在俞竞明身边的亲信出了这个主意,借刀杀人。”
司徒永死了,我败了。
狸山离大芮边境很近,如果淳于望听我的话离开了大芮,他很可能会去那里。
她已病得形销骨立,弱不胜衣,待见到我时,大而无神的眼睛里慢慢滚落泪珠,顺着高耸的颧骨滑下。
可被他逼到无路可走的人,分明是我和司徒永。
这时司徒焕正为端木氏的坐大而头疼,因司徒凌对他素来谦恭谨慎,并无夏王的锋芒毕露,又是自己的亲侄儿,遂开始重用司徒凌,逐渐让他在朝中立稳脚跟。
更没有我秦晚所冀望的幸福。
看着即刻有秉笔太监前去拟旨,我也松了口气。
司徒永想不出生性活跃的小师姐该怎样孤独而恐惧地待在那个密闭的空间,不能说,不能动,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连睡眠的权利都被剥夺两天后,司徒凌从地下抱出来的那个女子,果然已经彻底崩溃,傻了似的谁也不认识,并且不会说,不会动,不会笑,连眼神都是呆滞的,手指伸到她的眼睛上都不晓得眨一下。
他的神色很不好看,“你的意思,这么阴毒的主意,是我出的?”
他便笑道:“你既认为我圣明,我倒要做几桩圣明之事给你瞧瞧。目前我有个心腹大患未除,想来你知道是什么吧?”
就算什么都想不起来,我还是想看一看,仔细想一想,然后认真地告诉自己,原来我也曾那般快活过。
我抱紧他,轻声道:“傻子,我怎会恨你?有你这么个倾心相待的师弟,是我秦晚前世修来的福分。”
它不解,亦不动,站在一边打着响鼻呆呆地看向我。
我懒懒道:“他已经死了。”
沉吟片刻,我答道:“要除去这个心腹大患却不伤大芮元气,大约只有臣能做到了www•hetushu.com.com!”
喂了她吃点清粥,我转身离去,她忽然唤住我,“晚晚师姐。”
这种术法也是巫医的一种,施展的法子有些霸道,但能令她忘记一切于淳于望相关的事。连无尘、无量都不甘心自己辛苦教出的弟子就这样被世俗情爱毁了,所有人一致同意了冒险用这个法子。
即便他没去,那里也有着他和相思生活过的痕迹,甚至有当年盈盈生活过的痕迹。
他抬脚,似很想一脚把我踹翻在地。
他便笑了笑,说道:“可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你。还有对不起华曦。其实,我一直对她很冷淡我觉得你是我的责任,却总看不清,其实她也是我的责任。我把她留在宫里,她便猜到了可能会有事发生。临走时,她抱着我,告诉我,她和宝宝在等着我回去。她还说还说,她真的很喜欢我,很喜欢我。晚晚,你说我笨不笨?我木头一样抱了她很久,居然忘了告诉她,忘了告诉她其实我也喜欢她。喜欢很久了……”
我便很真诚地抬脸看向他,说道:“是真的,凌,你比任何人都适合坐这个位置,这个——孤家寡人的位置。”
她心生惶惑时,司徒凌等人将她引出,并焚毁她一家人隐居的木屋,将她带出南梁,先回子牙山寻求师门的帮助,并让卫玄每日以巫医之法治疗,终于让她慢慢回忆起往事。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她拒绝回北都继承家业,也拒绝承认和司徒凌的亲事,她跪在赶回的秦惊涛跟前,苦苦哀求着,要回狸山伴着她的夫婿和女儿。
我低吟一声,将司徒永抱得更紧。
顿了一顿,我笑道:“也许,很快要改口,称你为陛下了吧?”
弓弦紧绷的声音嘎嘎响在耳边,冷冷的箭镞正对着我。
他慢慢将碎了的茶盏丢在地上,静静地看向我,“你知道多久了?”
有时候,人活着比死去更艰难。相信司徒永地下有知,也不会怪我为什么不尽力把端木华曦留在人世间。
“是阿永自己突然离开我,投向了端木氏,然后处处和我作对”他无力望着殿外楼阁连垣,飞宇承霓,低低地喊道:“至于你,卫玄是母亲的人,我当年对你用移魂术时,根本不知道会害惨你。等我明白时,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只能重用卫玄为你治病。若真的有心害你你体内的毒素早就足以要了你的命了!”
有或者没有,其实也不打紧。
我道:“不要紧,我带你回宫,你可以亲口告诉她,告诉她很多很多遍,你喜欢她,你喜欢端木华曦,喜欢很久了……”
“你难道不知道什么意思?”
卫玄道:“王妃放心,她挣扎不了多久。这天底下哪有什么神仙道法,可以彻底抹杀一个人的记忆?早晚会断断续续浮出水面。可她要想起时,先要突破移魂术那个关口。那段地狱般的经历,加上前后所发生的那么多事,足以把她刺|激得再度崩溃,成为一个神志不清的疯妇。若要永远想不起来,除非一直服用安魂定神的药物,那药物虽无大毒,但日积月累,体质绝对会衰弱下去。”
“用亲人来威胁人犯招供,这一招,对真正心肠狠毒的人来说并不奏效。俞竞明好歹读过几本圣贤书,闵侍郎有头无脑,必然想不出这样阴毒的主意。”
他黑沉沉的眼睛盯了我许久,答道:“准了。”
“不错,他已经死了,所以他对我再狠毒,在你的心里,还是他对,我错,因为我的推波助澜,秦家的人着实死了不少。你不明白我母亲从天堂跌入地狱的惨烈,却承受了失去自己亲人的悲痛,我的复仇在你看来当然也是不可原谅的。因此,我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对你好,你都不会再领情了,对不对?”
我轻叹道:“皇上,其实我也想问你一句话。当日我想纵身柔然军营的火海之中一死以求解脱时,你说愿意和我共同承受一切屈辱到底有几分真心?是为了秦家的兵权,还是因为知道我命不长久而心怀愧疚?”
我微微笑道:“不谢。”
许久,他坦诚答道:“不能,即便为了你,我都不肯放过秦家,因此,我大约也不能。”
他想,他必须做点什么了。
这座皇宫,繁华富丽,却步步杀机。于她已是人间炼狱。
我拿手掌撑着地面想站起来,却觉肩上的伤疼得厉害,遂倚了龙案坐着,轻喘着说道:“永师弟临死时告诉我,他最初是因为听说你用移魂术害我才决定涉足朝堂,也好保护我,阻止你——你说他是不是太幼稚了?高处不胜寒。这个地方,起进来不容易,出去,更难。”
我拍拍它的脑袋。笑道:“辛苦了!你跟着我辛苦一辈子,该歇歇了!马儿,马儿,你去吧!”
不知算不算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真的找到了他的小师姐。
他不答,拨转了马头,策马奔了出去。
他的黑眸宁谧,宛若少时那般澄澈明净。
便算没有白来这世上一遭。
可那又能如何呢?他改变不了她接受移魂术后的身体状况,这消息只会让她更加惊恐。
沈小枫并不十分明了我和司徒凌之间到底有了多深m.hetushu.com.com的裂痕,但她也早已看出目前在前帝的压力下,秦家的举步维艰。想着秦彻倔强骄傲的脾性,她便也沉默了。
司徒凌能调动的力量并不多,却不在如何重振家门上用心,即便回到北都,依然将不少人遣到南梁继续打探消息。他的颓丧终于激怒了母亲,关起门来将独子好一顿训斥。
梦里,还是少年的司徒凌和我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把我们吓个半死,却毫发无伤。
他盯着我,眼圈仿佛红了,“晚晚,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的眼你和永师弟。要么一起哄我欢喜,让我看着你们两玩耍,便觉得满怀喜悦,要么一起和我离心离德,凭我想尽法子,也没法拉回分毫。”
我失声惨呼。
他很少来看我——即便偶尔过来,经历了那么多的变故,我跟他也已无话可说。
好一会儿,他答道:“我只给十日。”
她的眼眶通红干涩,好像早已把泪水哭得干了,但这一刻居然又滚出了水珠。
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无力。虽是皇子,他没有一点自己的力量,无法阻止司徒凌夺权,无法帮助小师姐和她的秦家军,甚至没有能力为小师姐延请到最好的大夫治病。
这时我正被困在未央宫中,几乎每天都给灌上比我膳食更多的药汁。
司徒凌踩在我们身上,以他一贯舒徐有力,一步步登上他梦寐以求的宝座。
与实力最强的端木氏联姻,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
这里有寻常人梦寐以求的富贵荣华,却永远不可能有寻常人的平安喜乐。
我这个人有点傻,身边最好的朋友也傻,没想到连养匹马都这样傻傻的。
有一日,他在无意间听到了夏王妃和卫玄的对话。
却再无一根射到我或司徒永的衣角。
秦惊涛大发雷霆,连司徒永也是万般不甘心,想不通自己的小师姐怎么会糊里糊涂被一个南梁人迷得神魂颠倒。这时,始终沉默的司徒凌提出让卫玄对她施用移魂术。
没有人知道夏王妃都骂了他什么。司徒永只看到司徒凌回卧房后把自己整整关了两天两夜,连他去敲门都敲不开。等他瘦了一大圈自己走出屋子时,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把遣往南梁的人撤回北都,第二年事则是去拜见秦惊涛,依然执婿礼。恭谨备至。秦惊涛见他为女儿憔悴至斯,也很感动,遂也屡加提携。
嘶号声终于停下时,司徒凌摸着空了的箭囊,无力地垂下长弓。
“对,他说,他有句话要告诉你,可临别时,只顾木木地抱着你,却忘了和你说。”
他的身影很快淹没在寂寂的黑夜之中。
回到大芮后,司徒凌比以往沉默许多,却依然不屈不挠地查着未婚妻的消息。司徒永虽是皇子,却是最无依无靠的一个。当时芮帝司徒焕尚未宣他回京,他也不敢公然回去,悄悄扮作司徒凌的小厮留在他的府第——那时,司徒凌也才十八九岁,连南安侯的封号都没有,他的母亲虽然保有“夏王妃”的封号 ,可为了打消芮帝的疑虑,她早就把“夏王府”的匾摘下,同时深居简出,只让下人称其为“夫人”。
“永”他笑得惨淡。却依然有一丝冰冷的锐气,“我顾念往日兄弟之情,如非迫不得已,从来不想伤你们可我已经做下的事,我绝不后悔!这大芮的天下本就该是我父王的!虽说有了这天下,我也未必留得住你,可如果没有这天下,我更留不住你。你像祈阳王守不住你姑姑,就像我父王留下了母亲孤寡半生……”
他眉目不动,端了茶盏静静地喝着茶。
不想让自己太狼狈,我没有骑马,而是乘着一辆华丽极舒适的马车前去,一路可以稍事休息。
快出芮境时,她才悄悄地告诉我,:“大小姐,我有孕了!”
他忽然间拍开我的手,一把将我拥到怀中,他激烈的心跳响彻耳边。
司徒凌缓缓抽出羽箭,搭到弦上,缓缓说道:“我一直遵守承诺,不会先向他动手,但昨日是他想伏击我,他想我死。晚晚,放下他,否则……”
“他说,他其实也喜欢你,喜欢很久了。他说他很想带着你远远离开这里,过消遥山水的日子。就像当年也曾有个人带我离开这里,偷偷地过了三年消遥快活的日子。”
司徒永很想立刻奔到北疆,奔到小师姐身边,告诉她这一切。
我想了想,答道:“大概,能吧。”
也许,是我醒悟得太晚,也许,是我奢求得太多。
“什么话?”
暮色里,如刻的剪影,依然巍峨,尊贵,高高在上,庄严得不容亵渎。
比如,孝烈帝的贤妃端木华曦,司徒永离世后,端木华曦哀痛而病,新帝将其迁居别宫,延医细细调理,甚是礼遇害。
我点头,“皇上圣明!”
那持续许久的痛苦嘶号声中,弓弦声频频响起,无数羽箭凄厉地划破长空,自耳边呼啸而过。
这天夜晚,端木贤妃薨逝。
夏王妃道:“我病成这样,看来是无法亲眼看到秦家覆灭了!”
我柔声道:“你担心什么?担心我会抛下他?放心,只要你和他未来的孩子平安,我怎么着都会哄着他过来和你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