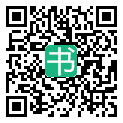第二十四章 行路难,离人心上秋
秦彻呆住,忽执了我的手问道:“你是不是不舒服,一时想不起往事来?要不,我让大夫过来给你好好诊治诊治?”
他的性情坚忍却骄傲。如果行动顺利,绝不致如此暴怒。
我失声惊呼,仿佛自己也被人一剑贯穿,踉踉跄跄地疾奔过去。
他胡乱把流血的手缠了,静默片刻,才道:“我虽想利用淳于望阻你婚事,但并无害他之心。听说上午秦府有辆马车载着个小女孩儿离去,我猜他也在车上吧?可我也由他去了。”
那边林木茂盛,是附近最可能藏身之处。
沈小枫担忧地看我一眼,默然退了出去。
叫沈小枫带了相思去看还有什么她喜欢的东西要带走时,淳于望正从茶壶中重新倒了茶,坐在桌边慢慢地喝着。
“这……妥当吗?此刻城门应该已经关闭了。”
我也像犯病了,一阵阵地喘不过气,连头都开始疼了起来。
相思开始还没怎么当回事儿,待和我挥手告别时,却呜呜咽咽地哭起来,搂着我脖子磨蹭了好久,泪水把衣襟湿了一大片。
我嘲讽道:“殿下已位及人臣,读上一肚子书,难道还打算考状元不成?”
看着恬淡尔雅云淡风轻的模样,分明一肚子的奸诈狡猾,居然也能欺世盗名,博个风雅闲王的清名!
我点头,说道:“明早的药,我会让人帮你煎好。路上的药我也会为你备上。用完早膳便请你带相思走。”
我不曾留他们午膳,只令人为相思预备了她爱吃的几样菜式,装在提盒里送上马车,让她在路上吃。
我本已盘算好,若他当着相思拆穿我的谎言,即刻便想法把他和相思一起弄晕送走,此时忽见他改变主意帮着我劝慰相思,大是讶异。
“是呀,晚晚,你怎么了?”
屋中便又静寂,有清风吹在窗纱上轻细的扑扑声。
如今,那飒飒飘动的大蝴蝶后,分明有一枚小蝴蝶正灵巧地舞动着,像谁家小女孩正牵着母亲的衣襟往前奔跑,一路撒下娇憨无邪地清脆笑声……
他和司徒凌,一个温雅,一个冷峻,可他们的行事,竟同样让我有深不可测之感。
我抬头看看天色。
烦乱之际,沈小枫悄悄进来回道:“午间我去南安侯府取点东西,侯爷没在府上,听说出城了。”
我心中如有一把火把烧灼得难受,匆匆把缰绳扔给沈小枫,借着林梢透下的些微亮光分开草丛往前摸索。
他向外看了看,说道:“可惜我的药都留在原来的住处了。听说陆老太医开的方子里有些药甚是少见,不知这会儿还来不来得及出去配齐。”
待喝得差不多,看相思在地上玩耍片刻,我唤了她过来,说道:“相思,舅舅家还有些事,娘亲一时走不开,呆会你和父王先动身回狸山,隔两天娘亲就赶过去伴着你,可好?”
司徒永脸色顷刻变了,紧紧盯了我片刻,才道:“五年前你和他有过纠缠?我怎么不知道?”
里面是一幅裱好的画,正是当日在狸山梅林时,淳于望在相思的涂鸦之作上改绘而成的那幅梅下母女图。
判断着淳于望可能走的路,我带了沈小枫转向另一条路,慢慢往回行去。
“什么?”
淳于望问道:“怎么了?不爱喝?”
相思便诧异望向我,“娘亲,你还在怪父王接我们接得太迟了?”
正在想着如何辩驳时,紧盯着那泥人的淳于望忽轻轻一笑,取过相思手中的那个泥人,细心地包了起来,说道:“嗯,相思跟着娘亲果然有进益,画的颜色真漂亮!这可是相思给父王最好的礼物呢,父王可得好好收藏着!”
淳于望端着茶盏,目光不动声色地从我面庞滑过。
我扫了一眼,也是怔忡。
他口中的第一个他,自然是指司徒凌了。
“淳于望……淳于望就能阻止两家联姻吗?”
随侍众人领命而去,只剩了沈小枫略带紧张地跟在我身边,许久才问我:“我们现在怎么办?”
他烧了马车……
耳边一阵一阵,只回响着司徒永拦我时说的几个字。
母亲散逸不羁,女儿稚拙可爱,背后暗香疏影,红梅盛绽,落瓣起伏,清泠泠的意境和暖融融的人物揉作一处,看着悠然出尘,却潇洒流丽。
“对,他只是一个敌国亲王。可你为什么会认为,一个敌国亲王能动摇我心志,甚至让推迟亲事?”
我若无其事道:“还好。就是烫了些。”
他紧随我身后向前,叹道:“你是不是太高估我了?你瞧我伤病未痊,又孤身入你秦府,你秦晚一声令下,立时身陷囹圄,刀铖加身。——你满心不就盼着把我千刀万剐,以报我当日辱你伤你之仇?”
我若无其事地品着相思帮助泡的茶,果然和平时喝的茶水味道大相径庭,怎么尝味道怎么怪异。
司徒凌认定是司徒永在嫁祸给他,他也指责司徒凌嫁祸他……
“你不想留下峰回路转的机会吗?”
那堆马车的灰烬已经冷了,犹有金玉碎片混杂其中,依稀辨得是淳于望或相思之物。
淳于望神色萎顿,勉强在地上支起身,低喘着说道:“近来一直服着药,本已好多了。只是今儿太过劳碌,又断了药,便有些透不过气来。这会儿胸肺间疼得厉害。”
我一犹疑,便将茶盏放下,不再去喝。
苍穹如墨,玉钩摇挂,星河明淡。
“我自是不敢清高到不屑一顾。但秦家的根在大芮。”
我忙喝道:“住手!”
秦彻点头,正要以主家身份去说时,原正和相思说笑的淳于望忽然变了脸色,掩着胸口栽下了椅子。
苍白的月光,居然也能把那殷红映得如此触目惊心……
不过如卫玄等医术极高明的名医,又为我治过那么几年病,不会毫不知情吧?
淳于望却出乎意料地沉默,直接马车临行前一刻,才让人递出一只锦盒,便从和_图_书我手中抱走相思,令人驾车而去。
我给逼问得狼狈,想来脸色已涨得通红。
即便……即便证实了我真的忘记了与他有关的部分记忆,即便我真的是盈盈,又能改变什么?
他不答,向前唤道:“相思,走慢些儿,等等父王!”
“我也想知道。伴着你和相思一路回北都时,我还以为我还是。”
沈小枫见我脸色不对,早将卫玄开来的药方煎了一剂,送来给我服了,却纳闷道:“不是说昨晚服过两丸了?连煎药也天天吃。怎么还不舒服?难道真的服用太多,已经没什么效用了?”
司徒永也不再拦阻,径带嫦曦离去。
我和淳于望,本不该有任何的交集。
可那总是洁净得纤尘不染的衣衫,此刻已被大片血渍染透……
相思见淳于望不责怪她,便眉开眼笑,将手中用丝帕攒住的什么东西放到淳于望手中,说道:“可我画画很好啊,父王看我这颜色涂得多好啊!”
他道:“我没想到会被他将计就计污赖到我身上;但他大约也没想到淳于望那等机警,将计就计来了个金蝉脱壳,竟避到了你府上。”
我拍拍她的小脑袋,说道:“女孩儿家的,又不考状元,读许多书做什么?认得几个字,不给人欺负便罢。”
可淳于望偏偏说道:“晚晚,我从不会胡说八道。若你心里有我和相思,请你,推迟和司徒凌的婚期。”
司徒永苍白俊秀的面庞弯过虚弱的笑弧,“晚晚,父皇病重,时局多变,我不会让你嫁给司徒凌。”
秦彻问我:“亲事怎么办?”
“峰回路转?”
他黯然笑道:“我和你从小一起长大,我自认能看穿你心思……或许是我太相信自己感觉了?可有这样想法的人,似乎并不只我一个……”
这只纸鸢看着也像无意缠在树梢上的纸鸢,可它的式样实在太眼熟了。
淳于望不答,默默喝着那味道怪异的茶,许久才道:“我只是亲王,还是南梁的亲王,的确不足以让你们秦家另眼相待。”
他的目光总是那样清寂而炙烈,让人心烦意乱。
“他自然有他的事。”我心不在焉,回头吩咐道:“去找合适的材料来,重给相思做个弹弓吧!”
从屋内到院中,从花园到廊榭,无处不是空落落的,空落得让人惶惑甚至害怕。
“记得父亲曾亲去探望过我几次。”
“凭什么?”
那日我陪相思放纸鸢,因收线时掉了后面缀着小蝴蝶,相思哭闹不休,第二日我到底令人到市集上找到一模一样的纸鸢,重新买了一只回来。
“凭我们是一家人。”
再问相思时,果然又到书房去和她父亲做伴了。
“和你有关便够了。”
我怒道:“你当我不敢么?”
我冷笑,“你将计就计,手段何等高明!你手下那些人又岂会白白送死,自然有人李代桃僵,乔装成你遇害的模样。如今你何止安全,一出这秦府,只怕还有一堆心腹死士牢牢守护着吧?”
但能让如此多的人为他舍生赴死,越发让人觉得他不简单。
我低头喝着茶,若无其事地道:“太子,你便是想杀他,或者想杀司徒凌,我都不会意外。”
沈小枫赶忙走过来,却和秦谨一左一右急急扶了他离去;相思慌得泪汪汪的,亦步亦趋跟在后面。
带了十余名随侍,我顺着淳于望离去的方向追去。
“把他扶回书房去休息,找出那方子,快给他煎药去吧!”
“一起走。”
他也不装病了,正披了衣倚在枕上看书。
相思惊诧,“啊,师傅只捏了身子,脸不是娘亲捏的吗?难道我睡觉时娘亲又去找那师傅了?可那师傅也没看到过父王模样啊?他怎会捏出父王的模样来!”
连她也认出来了!
“我好生奇怪,我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我十五岁生日前后的事?我……也不记得父亲曾陪过我两个月。”
虽已入夏,可北方晚上还是有些凉,说不准还会刮大风,不晓得淳于望记不记得给她加件衣裳。
她身边的人若依着她往日的性子,必不晓得时时留心给她盖被子。我竟忘了多嘱咐几句了。
相思见我不喝,便有失望之色,闻言将她喝过的茶送到我跟前,说道:“娘亲喝我的茶!已经凉了好一会儿,一点也不烫了!”
“你相信你就是盈盈,只是认定我们已回不了头?”
只闻“咯嚓”一声脆响,抬头看时,却是司徒永手中的茶盏被捏得碎了。
“听着你好像并没有把我和相思放在心上。”
寻到淳于望的马车时,已经接近三更。
“我……”
夕阳西下,霞光满天,映住叠岩成嶂,陡坡如削。
他神色愈加不好,神情间的激动却消褪了下去。
好在他只是紧盯着我,清寂的目光中如有荒野间缈杳的幽焰跳动,却没有和我争执。
许久,我方道:“东西按原样摆放着,就和……她在府里时一样。她的东西,什么不许丢了,不许……”
听得越多,疑惑越多,只怕我真的要疯了。
等煎了一剂给他服下,他便似缓过来些,只是精神萎蘼地卧在榻上,阖着眼睛仿佛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冷笑了。
我脸上顿时窜烧,忙喝道:“别胡说,明明也是那师傅捏的。”
他笑得真挚,看着却如此可恶。
我紧紧捏着缰绳,四处一打量,策马冲向前方一处山坡。
淳于望见我模样,温默地笑了笑。
司徒永居然轻轻笑了。
“是!相思唤我为父,唤你为母,我们怎会不是一家人?”
便是有满腹怨怒,也无法在她跟前发作。
我轻笑道:“你父王事儿也多,带着你走不快,只怕会误事。相思最听话,一定不会误你父王的事儿,对不对?我一个人骑马飞快,就是晚走两天,也和图书能很快就赶上你们。”
我转身走出去,正要掩上门时,忽听他冷笑。
同样让人触目惊心的,没于那片殷红中的一柄长剑,已深深将他前后贯穿,只露剑柄……
少了会说会笑会哭会闹的相思,怀中顿时空落起来,长长的锦盒冷硬地硌在手间。
我一惊,忙过去查看时,他盯紧我,竟是用力一推,将我推出老远,恨恨道:“我便知道你会这样说!你信司徒凌,信淳于望,却总不愿意信我!”
我很是疑心淳于望故意装出这等模样来,可见他满头冷汗,本就清减的面庞愈加苍白,连唇边都失了色,也不觉慌乱,扬手便唤人进来。
我挣开他,冷冷道:“你挑了这时候才赶过来,不但想解释是我误会了你,更是想告诉我,淳于望父女可能已经死在司徒凌手中?”
两国敌对,我和司徒凌的婚姻也因两家利益攸关早已牢不可破,他怎敢还抱着那样的幻想?
陆太医给淳于望开的方子都有拿给我过目,有些难配的药材也是府里集齐了送过去的,因此药还算现成。
淳于望身份特殊,地位尊贵,他的随身之物说不准有些对大芮很有价值的东西;他若掳了相思,如果不想为她多费心,自然也会留着她素日所用之物。
风过耳边,月光惨淡,忽然便有了女子细碎惊慌的哭泣声。
相思闻言,更是得意洋洋,缠着淳于望撒着娇儿,倒也不再计较泥人是谁捏的问题了。
“和我也无关。”
提起茶盏品尝时,淳于望笑道:“相思在你这里,倒是健壮活泼了许多。不但帮摘花叶,还亲手洗了,说要泡给娘亲喝。”
沈小枫见我勒下马,正在奇怪,顺着我的目光只一瞧,便失声叫了起来:“那……那不是……”
我当然更没法和司徒凌张口。难道要我告诉他,我因那个凌|辱过我的男子而心乱如麻,所以不想成亲了?
我厌烦道:“你闹够了没?如果闹够了,尽快带了相思走吧!”
也许这辈子,我都不会再看一眼这画了;可也许这辈子,那个小小的女孩儿,都走不出我心头了。
相思很是为难,看看我,又看看淳于望,估料着满心不愿意,又怕给说成不听话的孩子,不肯说出来,却委屈地把小嘴儿撅了起来。
他也不去收拾身上的茶渍,低垂的眼睫微微颤动,好一会儿才道:“我的确想控制住淳于望,因而那日令人拿着玉瓶为信物,想把他引到城外囚禁起来。但路上有人杀了我的信使,劫走了玉瓶。柳子晖不知信使被杀,奉我命令预备劫走淳于望,偏眼线发现淳于望一行人去向不对,赶忙跟过去时,他们已被引入陷阱杀害。他知道不对,急忙想退回城中商议时,被你和司徒凌碰上了。”
一大早起床,阳光透过窗棂投到屋中,刺得扎眼,头疼得更厉害,连身体都绵软无力。
我淡淡道:“即便你是南梁皇帝,也和秦家无关。”
淳于望微愕,便有些哭笑不得的神情。
我捏着弹弓,无力地摆了摆手,示意她们出去。
至于淳于望……
我叹气,耐心劝道:“淳于望,回你的南梁去,丢下你三年的春秋大梦,再给相思寻个好母亲吧!这里不是你该留的地方,别为了那些回不了头的往事害人害己,说不准还会害了相思。”
我的心立时沉了下去。
淳于望心思不在这上面,闻言也不好计较,放下那页纸说道:“还好……以后再多多用功吧!”
“不许?”
淳于望或许会对我用什么诡计,却绝不舍得伤着相思一根汗毛。
那是一条从官道延伸过去的小道。
茶水淋漓间,有一缕殷红自他指间蜿蜒而下。
“淳于望!”
回南梁。
我脱口道:“为什么?因为……我在五年前和他有过纠缠吗?”
忽然发现我和淳于望对峙的形势完全逆转。
我迎上前去时,司徒永的脸色很是阴沉。
我嗓间干涩,艰难地笑了笑。
竟像给人砍了几刀般绞痛,一阵阵地酸意上来,竟要涌出泪来。
我一怔,只得说道:“没有。”
我应了,看一眼抢先窜到前面引路的相思,低低向淳于望道:“我这里不便留你。用了晚膳,便请带相思离去吧!”
如果淳于望所言非虚,我莫名其妙失踪了三年,和我同门学艺的司徒凌和司徒永,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是哦,南梁才是她的国,南梁才有她的家。
淳于望如今睡的,正是我的卧铺。
我默然在路口立了许久,待那马车完全不见了踪影,才无精打采地回了府,打开那只锦盒。
“为什么?”
画面骤转。
算行程,现在他们应该奔出去至少五六十里路了吧?
相思便笑起来,倚在父亲怀里扭着小身子,娇娇地说道:“我才不生气呢!我就是想和娘亲在一起嘛!”
他握紧拳,咬牙道:“只看在相思份上吗?可我怎么觉得,这世上能让你改变主意的,就只有他!”
秦彻纳闷道:“你怎会问这个问题?你十八岁时才因为生病被接下山来调养,之前十年可不是一直呆在无量师太那里,何曾回过北都?”
可难道就这么回去吗?
我浑身发冷,却逼着自己冷静。
即便知道来不及,我也无法安坐于秦府等待噩耗的到来。
就如,之前他让手下故意步入陷阱,却确保了他自己安然无恙脱身离去。
淳于望打开丝帕,托住里面的东西,只看一眼,便已呆住。
“天下之大,容貌相类的人多得很,你怎会听一个敌国亲王的胡说八道?”
他笑了笑,“哦?你安置我在书房住着,我还当你盼着我多多拜读你的高论呢!”
他便冷着脸不再说话。
听他话里有话,我只微笑道:“殿下是南梁的亲王,想在南梁办的事,大约https://m.hetushu.com.com都能办到。”
普普通通,市集上随处可以买到的纸鸢。
相思惊讶,澄净的大眼睛睁得圆圆的。
傍晚又有贵客来访,竟是太子司徒永和嫦曦公主。
我看着他依然流着血的手,再不知心里是何等滋味,只叹道:“永,你忘了当年在子牙山,我们三人何等亲密无间,一体同心?”
淳于望那样聪明的人,话说到这份上,若还固执己见,还真的不可救药了。
如果淳于望没有遇害,他多半带着相思从别的路出了城;这马车留着,只是用以诱开敌人的虚晃一枪。
字字如刀斧斫下,斩钉截铁。
淳于望也不计较,走到桌边提过茶壶倒了盏茶,微笑道:“刚看着这院里奇花异草不少,挑了几种健胃补气的摘了花叶过来和绿茶一起泡,味道还不错,你尝尝看。”
我的心跳有瞬间的停顿。
这么个祸害兼祸水,明天无论如何得把他弄走。
淳于望将她抱起,手指拨了拨她撅起的小嘴儿,笑道:“这是怎么了?生娘亲气了?”
秦彻摇头,叹道:“这话我没法和南安侯张口。但如果你自己去说,我没意见。”
他从不是关于掩饰的人,说得虽然肯定,脸色却不对。
只是此刻已是初夏时分,灌木草丛间蚊蚁毒虫不少,相思那身雪白娇嫩的皮肤,又怎么受得了?
好容易哄她睡了,我走去书房,去看淳于望。
沈小枫特特跑来告诉我司徒凌出城,我心烦意乱,竟从不曾想到这上面来。
我道:“不用看了。谁不知轸王殿下文武双全,能诗善画?”
秦彻、秦谨略知一二,将其送出时脸上俱有忧色。
“诊治?”
我洗了把脸,依旧一身浆洗得笔直的武者衣袍,缓缓踱过去查看。
但他没道理连淳于望和相思的行囊一起烧了。
待她走了,我才陡地觉出,这偌大的秦府,竟森冷安静得可怕。
只是言谈之间,不觉略冷淡些。
沈小枫在后低低提醒:“将军,小心脚下!”
“为什么要我们先回去?我们等着你办完事一起回去不行吗?”
往前又行了半个时辰,离那马车焚毁之处越来越远,离北都城倒是越来越近了。
我魂不守舍般在往日相思玩耍过的地方徘徊半日,又到相思的卧房看时,两名洒扫的侍女正在收拾屋子,把她乱涂乱画的纸片捡作一处,又拿包袱出来,欲将用不着的卧具陈设收起来。
于是热热闹闹围着桌子用膳的,怎么看都像别后重聚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让司徒凌怎么想?
饭毕,秦彻悄问我:“下面怎么安排?”
“对,为兄腿脚不便,小谨自幼体弱,因此父亲都是亲自去探望你。记得你十五岁时,因到了及笄之年,父亲特地赶过去看你,陪你过了生日才回来,足足在子牙山呆了两个月呢!”
奔不多远,疯长的野草越发将路堵得不见,马儿便难以前行。
竟是上回捏的三个小泥人。上了色,一家三口和谐安详的模样。
我点头,“在一起混了那么多年,我这府上旁人看着门禁森严,和你们亲近的人该大有人在吧?早知瞒不过你们去。”
至少她会抱一线希望,少了许多伤心。
她路上玩耍时,只怕又要为失了准头不高兴了。
不过她也晓得自己最近根本没用心练字,写得实在不怎么样,无论如何是达不到她父亲要求的了。
“是……是么?”
身陷狸山时,相思是我的挡箭牌,也是我的挡箭牌;如今,成了淳于望的了。
我怅然良久,依旧卷起来令沈小枫收好。
相思听得表扬,笑得眉眼俱开,说道:“娘亲也夸我聪明啊,我的弹弓打得可准了……”
秦家和秦家军始终是芮人,一直以来的敌手虽是柔然人,但对边境屡起争端的南梁也没什么好感。
我忽然间也有些失控,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叫道,“他囚我辱我,我只看在相思份上才留他性命,你又凭什么认为,他能阻止我们的亲事?”
满天的星斗仿佛落入了睡梦中,我一夜不曾睡好。
“你凭什么不许?你阻止得了吗?”
我还是大芮的昭武将军,我还是不能辜负司徒凌待我的情意,我还是得为了保住秦家的地位和南安侯联姻……
看来只是我喝不惯这类茶,一时多心了。
司徒永仿佛给人打了一拳,忽然跳起来说道:“胡说!那时我和你一起在子牙山上呆着,怎么从不知道你曾失踪三年?”
“一般大夫恐怕诊不出来。不过……”
往日有相思伴着,时常给闹得慌,连练剑都练不安心。
慢着,司徒永知道了,那么司徒凌……
远远听得相思无忧无虑的笑声,我心神顿时舒朗,偏很快想起她将随着淳于望离我而去,从此天南海北,也许再也不能见上一面,心绪立刻沉了下去。
淳于望唇边的笑便冷冽下去。
难得他有这兴致,居然画着我穿男装的模样,看着俊朗英气,倒还不俗。
我看着几人离去,才发现自己吩咐了些什么,怔怔地站在当场。
我疑惑,“可去抓淳于望的人,不就是你们派的吗?”
确切的说,只是马车被焚过的车架。
我叹道:“殿下,你身体未复,劝你先调理着身体要紧罢!”
我慌乱转眸,没看到一个人影,却发现了山石上静静伏着的一个人影。
我因司徒永暗算淳于望并试图嫁祸司徒凌之事很是不快,但于他而言,这二人都是敌非友,故而我也不提起,如以往那般延他入厅,看茶款待。
我和秦彻、秦谨自是一肚心事,极不自在,可当着相思的面也不好露出。
我紧逼着问道:“我在子牙山学艺时,是不是曾经失踪过三年?为什么有些事,我好像想不起来了?”
他道:“晚晚,我不会让你和司徒凌成亲!”
他在和相思说m.hetushu.com.com话,目光却看着我,口吻坚决得不容置疑。
我们之间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甚至更久远的年代可能发生过的那些事,都只能当作大梦一场了。
见我变色,司徒永竟似看出了我心思,轻叹道:“司徒凌出城追击淳于望去了。你该明白了吧?真正想把他千刀万剐的人是司徒凌。”
“相信……什么?”
相思惊叫,差点没被带得跌倒,忙扑上去扶她父亲,连声唤道:“父王,父王怎么了?”
他不答。
这样说着时,已由不得被她拉了,却是我的一幅画像。
“你相信了?”
但相思的手又软又小,捉在手中说不出的可怜可爱,我再不舍得将她甩开。
我想起历年来医药不断,苦笑着摆了摆手。
她白天爱胡闹,晚上便睡不踏实,不但蹬被子,而且有几次还滚落到床下。
今日一别,也许永不能相见;可如果我成了南安侯夫人,也许永不相见的结局更好。
为何我从不曾听他们提过只字片语?
我一颗心砰砰乱跳,几乎要跳出腔子来,面上却只维持着平稳的声调,淡淡地吩咐:“两人为一组,在方圆十里内细细搜查,寻找相思小姐,以及……跟在她身边的男子。如果发现行踪,不许惊动,立刻通知我;如果……没有消息,天亮后各自回府,尽量别落人眼目。”
淳于望到底还有几分理智,终于也没有固执着一定要我随他回狸山,听从我的安排,悄悄地乔作普通商旅上了马车,径自出城。
淳于望笑道:“我不会捏泥人儿,倒还会画几笔,只是终究不如你捏的泥人神似。”
他瞳仁收缩,再收缩,然后转作微寒的笑。
淳于望那些南梁随侍的尸体不见很好解释。
他闻言坐起,将手中书册向我一扬,轻笑道:“看这书,考不了状元,但说不准能当上大将军。”
我心头烦乱,再看一眼拍手欢笑的相思,说道:“让他带着相思,走吧!”
相思特特地抓过那个淳于望的小泥人,高高举到他面前,说道:“看,我娘亲是多么聪明啊!她只看捏泥人的师傅捏了两个,便能捏出父王的模样来!”
“啊!”
我深吸一口气,提了宝剑便要往外奔去时,司徒永拉住我臂腕,“来不及了!”
常有村野人家的牧童买了,或自己做了,趁了天晴风大的时节放上去,不小心给树枝缠上,再取不下来,从此便高高悬在树梢上。
他瞥我一眼,见我漠然,唇边恍惚一抹黯然的笑,慢慢道:“纵我能许给秦家比大芮更尊贵无俦的地位,你大约也会不屑一顾吧?”
这时淳于望说道:“相思,你娘亲瞪我呢!”
“我是不是做梦,日后再看。可我不许你和司徒凌成亲。”
我想要否认,却又想起那许多推断我就是盈盈的证据,顿时烦躁,“我不想听你胡说八道。”
慢吞吞走到书房中,已见淳于望和相思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正站在窗口看着什么。他们还是保持着原来的衣着习惯,均是素白衣裳,手间也捧着一模一样的茶盏。
我也知许多花草可以泡茶,但素日不在这上面留心,倒不晓得我院里这些花木还可以用来泡茶。
我举目看时,却是我闲来写的一篇策论,劈手将其夺过,怒道:“你既是客,也该有点客人的礼数。谁许你乱翻主人家的东西了?”
后院把守得虽紧,马车离开时总会有些形迹露出,司徒永、司徒凌猜出淳于望自秦府离去也不奇怪。
我摇头。
我见他这般激动,倒也意外,复退回自己座位上坐稳了,叹道:“好吧,是我太过愚蠢,分不清是非。那么,就请你来告诉我,到底该信谁,不该信谁吧!”
这对尊贵之极的兄妹,居然穿着内侍的衣裳,拿着东宫的名贴令阍者通传。
这样的夜晚,别说我只带了区区十余人,便是千军万马,想找出藏于夜色中的两个人,也是大海捞针。
忽然眼前一亮,深密的树林已然到了尽头,前面坡上山石裸|露,只几株不高的松柏静静在石缝间立着。
我轻笑道:“我这院里还有什么你喜欢泡茶的花花草草,你令人都采了带走也不妨。这味儿忒古怪,我却不爱喝。”
我迟疑片刻,低声道:“我们……从别的路回城。”
晨间他们还在我身边散漫地品着茶,赏着画。一个眉目含笑,温雅脱俗,一个稚拙可爱,活泼灵动。
淳于望身在异国,又带着相思,便是有几个随侍相护,又怎么敌得过司徒凌身边的高手如云!
“你呢?”
那边传来沈小枫的叩门声:“将军,二公子请您领着贵客过去用膳。”
见我过去,相思放下茶盏便来拉我,笑嘻嘻地说道:“娘亲,来看父亲刚画的画儿!”
朝中尔虞我诈,正万般混乱,一不小心,便会有把柄落入敌人眼目。他不想此事被太多人知道,自然要悄悄处理。
我低声道:“咱们总有机会……捎点东西给她吧?”
刚服的药丸,竟似失效了。
相思着急,拉扯着我袖子道:“娘亲,娘亲,快给父王抓药……”
月光倾下,山石的颜色有些苍白。我在眼前突然的空旷中无端地紧张起来,这种心慌气短不确定的感觉陌生却又似曾相识。
给她新做的弹弓她嚷着不合手,这两日竟没想到给她重做一个。
黯淡的月光下,激烈的搏杀痕迹清晰可见,沆洼的地面和凌乱的青草间有大片的血迹,却看连半具尸体也看不到。
雪色长衫,素锦质地,正是淳于望晨间离去时所穿衣裳。
“不然还能怎样?你认为……你可能跑到南梁去和一个敌国亲王结为夫妻,还生儿育女吗?”
我愤愤道:“府外必定守着他的人,他不愁没地方去。何况他外表忠厚,内藏奸诈,还怕给人算计了去?”
“这不一样。我不hetushu.com•com想杀他,也不想利用他和南梁谈条件。我只希望……控制住他,能逼你推了十天后的亲事。”
但灰烬中并无骸骨,连拉车的马都不见踪影。
因婚期临近,近日一直告假在家,不必去衙中应卯。
不论他有没有耍诡计,他留宿于秦府都已成定局。
说也奇怪,夜间做着醒后什么也记不起的梦,浑浑沌沌睡了一夜,却越睡越困;醒来服了药,勉强逼着自己去练了半个时辰剑,出了一身汗,精神反倒恢复了好些。
但我想到的,司徒凌一定也想得到。我搜寻的地方,司徒凌一定也早已搜寻过。
他却焦急地看着我,黑眸亮得灼烈,模样是我熟悉的诚挚认真。
清寂内敛的父亲,天真可爱的女儿,和谐如春日里最美好的一幅图画。
沈小枫愕然,“相思小姐已经回南梁了!”
我不想细看,转身走了开去,淡淡道:“殿下过谦了!”
有一声半声若有若无的叹息在草木山石间飘过,同样似真似幻。
说着,另一只小手已自然而然地抓住我的手,高高兴兴向前走着。
他若不肯,说不得一拳打昏,派辆马车把他远远扔出大芮。
“不可能。淳于望,相思的确需要一位温慈的母亲,但那人不会是我。你别做梦了。”
沈小枫走到我跟前,低声问道:“怎么办?看样子,他们已经被抓走了,或者……”
秦彻推着轮椅行到我身侧,皱眉道:“晚晚,你留下他?万一司徒凌知道,你让他怎么想?”
我问秦彻:“二哥,我十五岁到十八岁这段时间,是不是一直在子牙山学艺?最近常常头疼,那时候的事,好像已经记不大清了!”
我忽然间说不出的心寒,惨然笑道:“永,你那个还是侠义爽朗宽厚热忱总以一颗赤子之心待人的司徒永吗?”
我头疼欲裂,无力和他争辩,一字字道:“我即将嫁给司徒凌,我和他,以及将来我们的孩子,才是一家人。”
这内院的书房是我呆得最多的地方,有时午间倦了,便憩于此处,因此一向备有卧具。
相思因重回父亲怀抱,很是兴奋,见淳于望不舒服,也不敢很闹他,却缠着我叽叽呱呱地说话,竟在算计着什么时候一起回狸山了。
司徒凌晓得我对相思另眼相看,他不想和我反目,应该会留些余地。即便杀了淳于望,也不至于取了相思的小命。
淳于望淡淡一笑,说道:“相思,你放心,你娘亲跑不了!她终究会和我们在一起!”
“不是!”
许久,他轻轻一笑,懒懒地阖上眼,慢悠悠道:“你只相信你记得起来的……好,我会让你记起那一切的。”
我动了动唇,掌心尽是冷汗,竟不敢再问下去,只抓过袖中一条巾帕,递到他手边。
他冷笑,“我没忘,却已不敢想。如今的他,早已不是我们当年的凌师兄了!他远比你想象的手段厉害,并且可怕。我不想我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也不想你成为他的帮凶。晚晚,我只想用淳于望来阻止你们两家的联姻。”
司徒永极敏锐,坐下寒暄没两句,便道:“晚晚,我并未派人去杀淳于望。”
不过几个时辰的工夫,就来不及了吗?
他是南梁轸王,北方的大芮,又岂是他能呼风唤雨的地方!
灵猿仙鹤缩在山石边无精打采,厨下的鸡鸭也静静地等着宰杀。
两个侍女忙见礼时,我过去翻翻她涂鸦的字纸,看看墨汁尚未干涸的砚台,还有被她拉坏了的弹弓,少了一只小蝴蝶的纸鸢,养得枯黄的小花……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淳于望泡的茶……未必安全。
我心知已不可能打探到消息,正待吩咐沈小枫快马加鞭回城时,偶抬眼一瞥,已是顿住呼吸。
淳于望眸光一闪,低叹道:“丫头,想把我往死路上逼么?你难道不知目前正有人全城搜捕着我?”
淳于望脸色发白,却一字一字道:“我一定会阻止!”
前方一株老榆树的树梢上,挂着一只纸鸢。
南梁二字,我咬得特别重,却在暗示他看清楚他目前在什么国家,他面对的又是什么人。
我头疼得站不住,扶了额坐到一旁的椅子上,说道:“对不起,我不相信。我只相信我记得起来的事。还有,我相信,不论我是不是盈盈,我和你,都不可能在一起。”
相思本在前面小步奔跑着,闻言忙又奔回来,牵住淳于望的手,说道:“我陪父王走。”
“是么?真的……只是如此?”
相思与父亲分别已近两月,今日团聚,自是开心,从头到晚叽叽喳喳,撒娇儿撒个没完没了,淳于望也是谈笑晏晏。
又将司徒凌置于何地?
我竟真的有两次险些被脚上的藤萝绊倒,心中焦急,遂拔出承影剑一路砍斫,奔往前方。
我郁闷之极。
远近村廓山林,层层迭于夜色之中,苍黑一片。
“你想引开并劫走淳于望?”
我勉强道:“何必大惊小怪?哪里就能病死人了?”
我越发疑心,追问道:“你可知道淳于望娶过一个妻子,长着和我一样的样貌?”
昨天上午我和司徒凌在城外的时节,相思就在侍女的陪伴下放着这只“母女相依”的蝴蝶纸鸢,然后遇到了有心前去找到的淳于望,顺理成章地带他进了府……
嫦曦瞥他一眼,掩着唇轻笑道:“我不过正好在二哥那里,顺道过来看看姐姐。刚坐车上正坐得腰酸,且四处走走散心,你们慢慢说话儿罢!”
还有……
“可你的根并不在大芮。”
我苦笑道:“我可以再推迟些日子吗?”
淳于望带着年幼的相思,必定加倍谨慎地掩藏踪迹,我又怎么找得到他们?
我见她目光殷殷,颇有冀盼之意,遂笑着接过喝了,却是一样的怪异味道。
晚膳尚算精致。
胸口骤跳,仿佛被他一寸寸斫于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