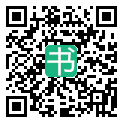第十六章 深宫变,天意高难问
很艰难地挤出一丝笑,我低低道:“我哪有不舒服?我向来……只会让旁人不舒服。”
我微笑,将她抱得紧紧的。
片刻后,他拨转马头,走到近前向我说道:“晚晚,神策营那边出了点事,我先过去瞧瞧,晚点再去府里看你。”
我皱眉道:“她是我认下的干女儿,长得像那是缘份。”
她刚刚洗浴过,头发尚湿漉漉的,面庞也是湿漉漉的,却爬了一脸的泪。
如果战斗力极强的秦家军没有控制在我的手上,如果司徒凌没有日渐威凛并逐步成为手掌军政大权的南安侯,我们这桩从小订下的亲事有没有这般牢不可破?
身后有少年略嫌稚嫩的嗓音,满是愤郁。
“司徒凌不是小心眼的人。”
我忙再次叩首谢了,才在站起身,垂手侍立。
秦家和端木皇后并无仇隙,姑姑久居深宫,自然也深谙自保之道,无故给卷了进来,只也是因为秦家和司徒凌走得太近的缘故。
“不开心的事……”
永远消失。
我什么也看不清。
淳于望……
司徒凌稳稳坐于他那匹被称“乌云踏雪”的白足黑马上,正略俯着身听马下一人禀报着什么资。
秦彻怔了怔,“这是……”
那厢秦谨听到动静,赶过来做鬼脸扮猫狗要哄她欢喜时,她却哭得更凶,涨得满脸通红,只拉着我不肯放。
我接过侍女的巾帕,一边为她擦着泪,一边柔声哄道:“娘亲出去办点儿事,呆会就回来,你乖乖的,娘亲给你买好吃的糕点。”
这位大芮皇帝虽然优柔寡断了些,但也不至于黑白不分,那么多的破绽又怎会看不出来?
秦彻振足精神,沉吟道:“这一招声东击西之计,当然比兴师动众暗中调兵强。只是秦哲那里,有高监军日夜督守,想要瞒天过海避开他的耳目,恐怕不容易。”
“这……看他什么时候把事办完。”
见我回来,她才抹着眼睛“哇”地一声哭出来,委屈万分地扑在我怀里。
或许,他也在等着我前去觐见。
我穿着方便路上行走的褐衣缚裤,随意绾着男子发髻,坦然步入府中。
他的面庞苍白憔悴,他的眼神绝望痛楚,他像是悲泣,又像在发誓,用尽最后的力气向我说:“望……一生一世只守望一个人……晚晚,若能从头再来一回,我……绝不再等你!”
我本待想问明那闯宫的男子送来的到底是什么信,才让一向宽仁的司徒焕这样大发雷霆,但见姑姑这般模样,也不好提起,接过侍女手中的药碗,坐到床沿亲自喂她喝。
我踌躇,但这样的多事之秋,我万万不敢将她带到皇宫去。
“我想暗中把北疆的兵马调动一部分过来,万一有人想毁我秦家,也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
旁人不晓得秦家三公子秦晚是个女儿身,却晓得昭武将军秦晚和南安侯司徒凌情谊甚笃,也晓得司徒凌久久不曾娶妻,是因为早已聘下了秦晚的双胞胎妹妹为妻。秦家和南安候早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我不敢惊动,悄悄退了出去,只唤来她的贴身侍女细问。
“是!”
他拍了拍我的臂膀,说道:“放心,老将军临终将你托付给朕,朕也便把你当女儿般看待着,绝不让你委屈着。”
秦彻脸色发白,急问道:“有没有旁人听到?”
眼前不由闪出司徒永和华曦的身影。
走至瑶华宫宫门前,便有监守的太监犹犹豫豫地想伸出手拦我。
如果他还活着,他必定记挂着相思,说不准真会跑大芮来接回相思。
“出了点意外,又让二哥操心了!”
我把她抱紧了,哄了许久,才见她止了泪,抽抽噎噎地说道:“我以为娘亲再也不要我了呢!父王也不来接我,好像也不想要我了!可我明明很乖,我明明没有惹他生气!”
“什么准备?”
他支着额,苦涩地说道:“若不是为了镇守大芮边疆,我们秦家何至如此人丁单薄,不得不把你一个姑娘家推到了前面冲锋陷阵……唉,误了你的终身,还给人这般疑忌。”
可惜自从我被选作秦家的承继者,我便已注定了不可能过寻常女子的生活。
我忙道:“万万不可!”
我摇摇头,咬牙吞咽下嗓间的气团,脖颈却似生生地给拉直了般地痛楚着。
“让他们手脚利落些,没有柔然军也需得给我找出一队柔然军来,没有大战也需得操演出一场大战来,务必做得天衣无缝!”
他皱眉道:“晚晚,你手边的事儿本来就多,这样下去可不行。”
沈小枫不敢再说话。
我摇头,“我一无所知,只是……姑姑如今病着,竟会在病中呼唤祈阳王的名字,着实……令人生疑。”
“晚晚你这话错了,怎么就不可以长相厮守了?有战乱时可以夫妻齐上阵,无战乱时携手花下共享天伦,同患难,共富贵,不是该比寻常夫妻更加情深义重?”
“谢太子关心!”
“从出了那事后,娘娘一直……一直不对劲。对了,昨晚发烧烧得厉害了,还说梦话。”
忽然间又有心灰意冷的感觉。
我强笑道:“没事,小孩子都这样,初到陌生地方不习惯,哭两天就好了。”
我恭谨应了,又道:“听说德妃娘娘病了,不见外客,晚晚打算先去探了病再回去。”
司徒永点头,却轻叹道:“德妃娘娘待孤素来不薄,孤也盼她尽快好起来。”
“姑姑呢?她有没有和皇上辩解什么?”
我轻笑道:“些微小伤小痛,何足挂齿!想我秦氏五代忠烈,马革裹尸或伤病而亡的已有一十人。秦氏一门深沐皇恩,如今臣的长兄早逝,二兄瘫痪,幼弟孱弱,蒙皇上不弃,委臣于重任,臣自当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秦彻吸了口气,身后有侍女因吃惊而呛咳,发出隐忍的低低咳嗽。
管事低头应了,并不敢多问一个字。
前面引路的管事闻言,惊骇地望向她。
而眼前,白茫茫的一片,似被大雾遮住了所有的去路。
相思却还是郁闷,愤愤道:“www.hetushu.com.com怎么着也不能把猎狗宰了呀!假如有没捉干净的野兔呢?假如别的山里又跑来了野兔呢?”
秦彻摇头,神情已凝重起来,“晚晚,想来想去,只怕是咱们秦家树大招风,便有人想趁着你不在北都时对我们动手吧?姑姑再怎么糊涂,也不至于公然在自己的宫内和祈阳王的使者相见。”
一回头,却是小弟秦瑾从门外踏入,脸上犹带怒色。
“承平帝……与我更不相干。”
她的长发披散,瘦削憔悴,眼角已有细细的皱纹,却娴雅端丽,依稀见得年轻时的天姿国色。
侍女在旁禀道:“娘娘病了好几天了,守卫不让传太医,咱们的人也进不来。南安侯找人问明了病况,让大夫斟酌着开了药悄悄送进来,可一直不见效……上午太子回宫,不知怎么就知道了,亲自跑过来吩咐了,这才传了太医。可娘娘她……”
但我知道我一定要走下去,一步步地在看不见的大雾中走出一条路来。
可惜,从皇子,到太子,然后到皇帝……
司徒焕神情间便闪过愠怒恼恨之色,但到底没有说秦德妃是给他禁了足才不能见客。
他闷闷地道:“晚晚,你是不是太多疑了?我瞧着司徒凌待你实在算得上情真意切了。”
沈小枫再不看他们一眼,冷冷地哼了一声,按紧腰间的宝剑跟我走入宫中。
锦衣华服,玉带金冠,举手投足稳健有,雍容尊贵,完全是大芮太子不容亵渎的合宜风范,丝毫不见一路相随间的谈笑不羁。
“若是成了亲,多放些心思在家中。”
二人俱是紫色锦袍,一个高挑俊美,一个纤纤袅袅,慢慢地融到渐深的暮色里,看着像一幅和谐的剪影。
“什么时候来?”
左仆射杨晋是杨太妃的亲弟,也算是朝中很有份量的人物,不想居然舍得把孙女嫁给司徒凌为侧室。
我的喉嗓发直,胸口闷得阵阵酸疼,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潮湿了。
廊阁轩昂,台榭高筑,飞馆生风,重楼起雾。宏伟峻丽的正堂高悬着列代帝王钦赐的忠烈牌匾,府中下人屏息静气迎接我,无一不是华衣丽服,举止端庄,进退有度,并不比淳于望的轸王府差。
一回北都,他再不像在外面那般随性。
我冷笑,“那高监军是端木氏派过去的吧?养得那样白白胖胖,在敌军入侵时跑不快死于乱刀之下,并不是什么奇事。”
太监们面面相觑,声气便低了下来:“这个……大人,咱们不过是奉命行事,不关咱们的事呀!”
“朕瞧着那孩子也是个实心眼的,前儿左仆射托了杨太妃来说,想把他孙女指给凌儿做侧夫人。可朕跟他提时,他却请朕为你们主婚。”
我垂头道谢,“既然太子已遣御医诊治,想来应该不妨事。”
“父王会来吗?”
“我在江南认下的女儿,叫相思。”
秦彻目光微悸,沉郁地望向我,“晚晚,你听说了什么?”
我忽然很想落泪,忙低了头,几乎是逃走般抱了相思回自己的屋子。
若他已死去,那温暖的躯体只怕早已冷冰冰掩于黄土之中,清雅柔和的笑容和寒梅暗香般的体息也将随之无声无息地湮灭消失于黑暗之中……
我沉吟着,向秦谨说道:“小谨,约束我们家的人,还有秦家在北都的族人,令他们最近需得谨言慎行,无事不要出门,更不许惹事生非,以免落人口舌。”
他自幼体弱,一直请了名医调养,这几年才养得好些,到底不如同龄人健壮,看着甚是单薄,但腰间一般地佩着宝剑,攥着剑柄的白皙右手隐见青筋跳动。
记忆里的他,始终更像个潇洒自若的少年侠客。
我问:“谁在闹事?”
司徒永点头,便携了华曦走向宫外。
“应该只有她的侍女听到,她们素来忠心,想来不至于乱说。但关健不是她们说不说,而是姑姑和那祈阳王,到底是不是有所牵扯……皇上不会无缘无故就因为一封书信就信了旁人攀扯,如此冷落姑姑。”
对着相思,我又怎能那样轻易地把她父亲抛诸脑后?
司徒焕微微动容,叹道:“你一个女孩儿家,也算是……难得了。”
“胡……胡说!娘亲满心里疼你还来不及,怎么会不要你?你父王……你父王事儿多,所以才耽搁了?”
我深知他能有今日,全仗了端木皇后支持,也不好与他争执,只叹道:“秦家树大招风,早有人看不顺眼了?可怜我姑姑,无子又无宠,孤孤单单在这深宫里呆了半辈子,又得罪谁了呢?”
“明白了。我去安排。”
秦彻叹道:“可把人当傻子了。明眼人应该一眼看得出,这是平安侯在暗中捣鬼了!”
未至德妃姑姑卧房前,便听见她压抑住的低低咳嗽,让我心里一阵发紧。
我道:“皇上仁德,举朝称颂,万民景仰,臣又怎会委屈?”
相思居然也能看得出来,气喘吁吁地跟在我身后,说道:“娘亲,这就是舅舅家吗?好大的地方,好像比我们家还要大些呢!”
“是,奴婢遵命!”
无一不在昭示着秦氏这将门世家的不世功勋,和福泽后代的百年富贵。
待出了大门,坐上车轿,我又唤来心腹侍从吩咐道:“即刻多派人手前去南梁,设法到狸山和雍都打听南梁轸王的消息。”
我也知自己性情执拗古怪,特别经了阿靖之死和柔然军营之辱后,对男女之事更是抗拒,只叹道:“二哥,我知道是我亏欠了司徒凌。我欠他的,我不能给他的,我会通过别的方式回报他。如果他愿意……他应该很快就能有自己的孩子。”
“后来呢?什么时候下的旨意,要把我姑姑禁足?”
只听她们呜咽道:“将军,你可回来了!咱们娘娘可给人冤死了!”
这侍从名唤沈小枫,却也是个女儿身,从小在秦家长大,开始侍奉秦彻,后来随了我。
那么,你一定会来找我,把相思要回和*图*书去……
忽又想起淳于望曾和我说过的话。
“那日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是指你两次送给他的八个美人?”
他负手站着,向我微微颔首,眼底却有着熟悉的明亮笑意。
“皇上就因为瑶华宫内出现了一个自称祈阳王使者的男子,就疑心上了姑姑?”
我走近德妃姑姑,轻唤道:“姑姑!姑姑!”
司徒焕并没有让我久等。
“可他那边说要成亲,你却一再推托,为了拖延亲事还自请送公主和亲,不清不白失陷于芮国这么久,还带了个女儿回来……晚晚,你真有为他想过吗?真的喜欢小孩,何不尽快成亲,生几个名正言顺的儿女?”
“对,以后,你就跟娘亲住这里,直到……你父王来接你,好不好?”
“娘娘好像受惊得厉害,后来一整天都失魂落魄的。到晚上皇上过来,却是关了门和娘娘说什么,不知怎的就大怒起来,我们进去时,便见皇上发怒,要把娘娘关冷宫去。一群人跪了一地求了好久,皇上才怒冲冲离去,却下令封闭瑶华宫,不许任何人进出了……”
他的语气颇为不善,我只作未听见,告退出来,向守在奉先殿门口的大太监说道:“李公公,你方才听到了,是皇上让我去瑶华宫拜见德妃娘娘的。”
子衍……
这么多日子都没有消息,也许他真能侥幸存活下来。
我走过去,将他推到桌边坐了,向相思道:“相思,过来见过二舅。”
我疲惫地叹道,“我只是想知道……只是想知道那轸王是死是活而已……”
我明知现在的大芮正有人想方设法对付我们,忙道:“你快去吧,姑姑那边,我自有主张。”
他叹道:“若是喜欢,找个乳娘过来帮照看着就行,没必要这样亲力亲为。何况……你到底还没成亲,莫名其妙弄出个女儿来,即便旁人不敢说,你叫司徒凌怎么想?”
振臂一呼,从者云集,连司徒焕也不得不忌惮三分……
我已经回到了大芮,回到了北都,回到了我原来的生活中,再度和司徒凌携手,配合默契如鱼得水地应对朝堂中的明枪暗剑,保全我自己,也保全秦家威名不堕,保全司徒凌稳稳立足于朝堂之上。
我实在不晓得当日淳于望要上朝或办事时是怎么摆脱她的。
她必是突然到了陌生地方,又瞧不见熟悉的亲友侍仆陪伴,心中害怕了。
“梦话?什么梦话?”
我站定身子,冷冷一瞥,叱道:“皇上令我过来探望德妃娘娘,你们也敢拦?开门!”
一贯温和的秦彻忽然提高了嗓音,眉宇间有怒其不争的悲哀。
再和谐,也摆脱不了他们二人联姻的实质,只是两个家族各取所需的利益联合。
我叹道:“可狗毕竟是狗,不是自己的家人。活着浪费粮食,还得担心误咬到自己家里人,不如宰了清净,还可一快朵颐。”
相思好奇地打量着他的轮椅,倚在我腿上小声地唤了声“二舅”,总算没开口说出甚不合时宜的话来。
统率神武营的神武将军,名义上虽隶属镇国大将军治下,实则是平安侯端木青成安插过去的心腹,此番闹出事来,多半又是针对司徒凌了。
她的目光直楞楞的,不复往日的神采,我连唤了几声,她才像有点知觉,眼神恍恍惚惚地在我脸上飘过,轻飘飘地应了一声,低低道:“晚晚,你回来了?”
但也可能早已死去,只是死于狸山,梁国朝堂没那么快得到消息,当然也没那么快宣布这消息……
秦家部下兵马素来骁勇善战,尤其在应对北方柔然入侵方面经验极丰,若是边关告急,以司徒焕的谨慎,断不肯让秦家军的主将在这时候遭受无妄之灾。
“晚晚,你终于回来了!”
我应着,伸手一摸,只觉她额上滚烫,身上赤烧,分明正在高烧之中。
我忙走过去瞧时,相思正被侍奉我的侍女小心地牵在手中哄着,见我过去,立时奔了上来,抱住我的腿叫道: “娘亲,父王怎么还不来接我?乳娘、温香她们也都不跟着我……娘亲你要去哪里,怎么不带着我?”
她的手哆哆嗦嗦地接过我手中的药碗,捧起便喝。
秦谨也回过神来,拍手道:“不错。若是北方边关告急,别说皇上,就是端木皇后再打什么主意,想动我们秦家,也得掂量掂量这其中的厉害了!”
“嗯,的确情真意切。只是……”
她似很厌烦,摇了头又要推开时,我柔声道:“姑姑,快先喝药。便是有多少不开心的事,也需等养好了身子再作计较。”
“姑姑,我回来了。”
“那人的确是祈阳王当年的侍卫,宫中不少老人都已认出了他。并且他手中所持书信,经过与当年祈阳王笔迹的对比,的确……乃是祈阳王亲笔。”
“仿佛是神武营有个参将在城南置了一块地,却把神策营一位队正家的田屋都给占了。那队正前去理论,反被那参将毒打了一顿。神策营的右卫将军向来护短,闻讯便沉不住气,竟让人把那参将府第一把火给烧了。若率起这参将也不过六品小官儿,手中实权也有限得很,居然能纠集上千的神武营官兵,跑到神策营那边堵了营门鼓噪闹事。”
他便沉默片刻,抬手道:“罢了,你一路劳碌,想来也累得很,早些回府歇着!”
司徒焕咳了一声,沙哑着嗓子道:“罢了,朕这一向病着,可心里还不糊涂。事发突然,换了谁都是措手不及。嫦曦和永儿都已经向朕回禀过,你已经尽力了,也吃了不少苦头,朕又怎会再怪罪你?”
“二哥,你放心。”
秦彻连连点头,又与我商议了些细节,方才找了心腹之人过来安排。
她生得眉眼英气,武艺不俗,便也换了男子装扮随我东征西伐,纵横沙场。
司徒凌少年成名,俊伟不凡,的确是很多京中闺阁小姐仰慕心仪的英雄人物。
秦彻、秦谨和几名侍女连番哄着,连大哥的遗腹女秦素素都过来想方设法逗她,都没www.hetushu.com.com法哄她展颜一笑。
“亲笔!”我骇然,“难道那个祈阳王真的没死?他……他又找姑姑做什么?”
我心里一跳,忙道:“这事不许和一个人提起。记住,你们两个小心看护着,她清醒前别让其他宫人靠近!”
也许我连司徒永都不如。至少司徒永伴着我们走过的那一路,相思没这么闹腾过。
秦彻的脸色愈发苍白凝重,低垂的浓黑眼睫在面颊投下暗色的阴影。
这次去南梁,本说是件闲差,又因二嫂有孕,怕秦彻顾不过来,便留了她在北都照顾他们夫妇,再不想遇到南梁宫变,一同前去南梁的随从或遇害,或被囚,反是她留在北都逃过一劫。
秦彻又在问我:“晚晚,依你之见,我们家要不要预先作些准备?”
相思问我:“娘亲,什么是狡兔死、走狗烹?”
“俗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凌儿是夏王独子,年纪也不小了,虽有几个侍妾,却至今都不曾育有一儿半女。如今北疆还算安定,你可以把那边的事交给温将军、高监军他们,先顾着自己的终身大事要紧。”
“不知道。听说皇上就是看了那封信方才龙颜大怒,当即下令收去姑姑德妃册宝,打入冷宫。姑姑身边的宫女太监再三辩解德妃并不知情,这才没再坚持废她尊位,只令人守住了瑶华宫,不许任何人进出,——其实那些宫女太监在皇上面前哪里说得上话?多半是皇上自己头脑冷静了些,不想和秦家翻脸,这才给姑姑留了点脸面。”
我摸着相思柔软的黑发,心里想着,也许是因为她吧?
“秦氏一门煊赫,深得皇上宠信……”
“信上什么内容?”
我哼一声,扬手推开站在门前的太监,一掌拍开宫门,快步走了进去。
他略带不耐皱了眉道:“好,你去看望看望也好。朕倒也想知道,她到底……是哪里生了病!”
他的脸色比以往更加憔悴,眉宇间却有如释重负般的欣喜和欣慰,“我本待遣人到南梁去助你脱身,南安侯都不同意,说有太子去就够了,人多了反而误事。如今看来,竟又让他料准了!”
如今我既回来,当然不会由着别人把秦家当作棋子拨弄。
我不想和他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唤了两名细心的侍女带相思去沐浴更衣,看她一步三回头地恋恋离开了,便屏去众人,转头问向秦彻:“宫里到底出了什么事?那个与祈阳王有关的男子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僵坐在桌边,只觉脑壳疼痛得厉害,别过脸说道:“不错,我自认从来不是好女人,也不是好妻子。即便成了亲,嫁过去的也只是名义上的秦家大小姐,依然会有个秦三公子留在秦家,领着秦家军纵横沙场……哪可能如寻常夫妻般亲亲我我,尽享闺房之乐?”
她得我吩咐,一边差人出去,一边奇道:“将军,为何要打听这轸王的消息?南梁朝廷也不安稳,咱们是不是该多多留意那个刚当上皇帝的承平帝?”
一时喝完,她的臂膀软软地搭下床沿,手腕一歪,空了的药碗便顺着床边滴溜溜地滚到我脚下。
我上前见礼,“太子殿下!”
“让人这么欺负?”
平安侯端木青成是端木皇后的二哥,也是太子妃端木华曦名义上的岳父。
我啜着茶,一边思量着,一边向秦彻说道:“二哥,秘密传令去边关,让秦哲、温良绍留心柔然人动静。想来柔然安份了一年多,也该缓过气来,这会儿应该又在打青州、幽州的主意了!”
我无奈地叹息,“只要秦家还在,只要秦家军还在,我根本不必用寻常女子的手段来争夺夫婿宠爱。”
相思哪里懂得我满心的忐忑,见我待她温存,便咯咯笑着,直往我怀里钻,那样甜腻腻地撒着娇唤我:“娘亲,娘亲……”
我掀开帘子,便见前方城池巍峨,如山矗立,悄无声息的挡住了城内繁华热闹的千街百衢和气势恢宏的楼阁殿宇。
司徒焕满意地点点头,又道:“永儿说你伤病屡屡发作,平时也需得多多调理。”
秦彻一怔,皱眉道:“为何不可?我们若要行动,自是会小心掩蔽踪迹,不让朝廷发现。”
待我好,不是因为我是秦晚,不是因为我是盈盈,而仅仅是因为我这个人。
他奔上前和我见礼,犹自耐不住心中忧惧,憋红了脸向向我,“阿姐,难道咱们就这样束手待毙?”
但这世间,又有多少人可以随心所欲呢?
我给她哭得心都揪了起来,再也坐不住,把她抱了起来,在厅中来回走动着安抚她,喃喃道:“虽然时间长了点儿,可他一定会来罢?他怎会舍得你呢?他明知我从不会照顾小孩,不懂得怎么哄小孩欢喜……”
华曦秀眉轻蹙,含愁说道:“可不是呢。大约也吃了不少苦,只是蔫蔫的,话都不想说。我待要细劝,又记挂着你还在等着,便先出来了。明日你忙你的,我一个人进宫来陪她说说话!”
“晚晚,别的女人巴不得把夫婿拉在身边寸步不离,最好永远不看别的女人一眼,哪有像你这样千方百计把美人往自己夫婿怀里塞的?这样的蠢事你能不能别再做了?”
我心中一凛,却答道:“谢皇上关心,臣一定谨遵皇上旨意,尽快把北疆之事安排妥当。”
他的眸光一暗,待要说什么时,身后已有女子柔声唤道:“太子!”
李公公目光一闪,干干地笑了笑,说道:“秦将军请!”
而她再不看一眼,阖了眼睛像是倦极而睡,眼角却还是湿湿的。
我叹了口气。
我瞥他一眼,淡淡地吩咐道:“这是我在别处认下的干女儿,从此之后,她就是秦府的小姐。即刻去预备她的吃穿应用之物,一样不许马虎。”
“听说德妃病了,孤顺道过来问问她的病情。”
司徒凌应了,领了人策马转道,奔往城南方向,却是身手矫健,身姿挺拔,丝毫不比淳于望逊色。
近年司徒凌威名益盛,颇有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之势。司徒焕登基十余年,早https://m•hetushu.com•com有一班忠心拥护的大臣,根基自是稳固;可司徒焕御体欠佳已久,万一有个什么,太子司徒永年纪轻轻,只怕制不住司徒焕这等矫龙猛虎般的人物。故而近年端木皇后等人明里暗里屡屡进谏,想劝芮帝削去南安侯兵权;司徒焕虽也担心司徒凌恃功而骄,只是性情优柔,朝中又有不少文臣武将支持司徒凌,始终未能有所举措。
他始终身不由己。
“知道,日后我再和他细说。”
沈小枫跟在我身后,却顿下身向那几个太监说道:“看什么看?如果不信,去问问皇上身边的李公公去。我们将军不在家,便敢这么着欺负我们德妃娘娘?摸摸自己脖子上,到底长了几颗脑袋!”
我听得也是纳闷。却不晓得那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才让素来宽仁的司徒焕如此一改常态大发雷霆。
秦彻、秦谨都是一惊。秦谨问道:“阿姐难道是听说了什么消息?”
“啊,好啊,最好父王明天就过来,我们住在一起……”
其实路上那个和相思玩骑大马过家家玩得不亦乐乎的司徒永,才是真性情的司徒永?
“她……似乎在叫一个人的名字。她迷迷糊糊地在喊,子衍,子衍……叫了好几遍,我们把她唤醒了,这才没再叫……可烧得却更厉害了!”
抬眼看时,有女子肤凝新荔,腰流纨素,娉婷如水,袅娜而来。正是太子妃端木华曦。
秦彻叹道:“后来连我和小瑾都找了去再三讯问,竟是疑心我们秦家与祈阳王早有瓜葛。皇上也不想想,若是秦家有意相助祈阳王,又怎会把姑姑嫁给他?祈阳王又怎会冒那么大的险把书信往宫里送?便是想给姑姑写信,让秦家转交不是更方便?”
秦彻却眸光一闪,若惊若喜地望向我,“只怕他们行动没这么迅速。”
我恭谨答道:“承蒙太子和太子妃不弃,从不把我当外人,秦晚感激不尽!只是国有国法,宫有宫规,礼仪不可废。”
我便含笑举步,径自奔往瑶华宫。
好容易哄相思吃了点儿东西,把她安顿得睡下,我疲惫地回到怀德堂时,发现二哥秦彻还在等着我。
我微微地笑,“就先让他们得意着吧!姑姑那里,我呆会入宫一次,看看皇上态度再说吧!”
我笑了笑,“如果秦哲他们说柔然人行动迅速,那么柔然人行动一定迅速;如果秦哲他们说柔然人已经攻下了幽州几座城池,那么柔然人一定已经攻下了幽州几座城池。”
姑姑纵声笑了起来,却更是凄厉,喃喃地说着。
这些人挑着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下手,显然对我也有几分忌惮。司徒凌明知我遇险仍然坚守大梁,果然明智之极。若我二人都不在大梁,或许连南安侯府和我们这秦府都都该换主人了。
相思摇头道:“我不要糕点。我要娘亲,我要父王!娘亲你去哪里?你带着我行不行?”
我不敢细想下去,转头问秦彻:“二哥,姑姑嫁入锦王府前我尚年幼,你可还记得那时的事?姑姑她……成亲前是不是认识祈阳王?”
我捏着一把冷汗,匆匆出了瑶华宫,还未及定下心神,一眼便见到司徒永正站在宫门前向看守的太监低低询问着什么。
如果他死了,相思天天和我要父王,我到哪里找一个父王给她?
华曦浅浅一笑,剪水双瞳脉脉流转,看向司徒永。
相思吓了一跳,叫道:“为什么要宰来吃?自己家里养的狗,不是自己的家人一样吗?怎么会舍得宰来吃了?”
对寻常女子来说,这样的蠢事的确愚不可及。
行至北都东门,马车忽然顿了顿。
我心里也忐忑起来,皱眉道:“她……还有没有别的异常?”
她身畔的两名侍女却是跟了她许多年的,转头见我来了,忙放下药碗行礼,眼圈却已红了。
“无非是看如今边境太平,用不着咱们家了呗!”
“还要一阵子?”
我坐于车厢中,仰起头,将一块雪白丝帕掩住脸庞,让帕子把沁出的泪水吸干,让未及沁出的泪水顺着眼眶流回体内,吞入肚中。
我叹道:“二哥,既然有人要对付秦家,自会密切注意秦家动向。我们再小心,上万的兵马奔波几百里赶过来,又怎能做到完全掩人耳目?”
她又大哭起来,“他去办什么事要那么长时间?以前他都带着我,现在为什么这么久不找我?他是不是不要我了?”
司徒焕慢慢地说着,原来浑浊的眼睛闪过些微的锋芒。
淳于望,你一定不放心相思吧?你虽然让我照顾她,可一定并不放心吧?
她呜呜地哭着,鼻涕眼泪把我衣角蹭湿了一大片。
我给她哭得心都揉碎了一样,一路胸口发堵。
“哦,哦!”秦彻苦笑,“这个……这事南安侯知道吗?”
“会来。”
忙进去看时,姑姑正无力地倚坐在软枕上,推开侍女奉上的药碗。
如果他已经死了……
二门外已备好了车轿,我正要过去时,却听得相思呜呜咽咽的哭声传来。
沈小枫慌了,期期艾艾道:“将……将军,你……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他一气喝了,才安静了些,低了头答道:“神武营的人正在和神策营过不去,我悄悄带了些人过去查探,想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刚刚见凌大哥已经赶了过去,我去相见时,他说阿姐已经回来了,让我回府听阿姐示下。”
很快回到秦府。
司徒凌缓缓将锦帘放下,低低噫叹:“这两年,我们也太招摇了些。若再落人口舌,只怕也逃不过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
“可他什么时候把事办完啊?”
相思哇哇大哭的稚嫩嗓音还在耳边回旋,冷不丁又似听到淳于望惨淡地在说道:“晚晚,好好照顾相思。她……没了父亲,不能再没有母亲……”
看看天色已经不早,我狠了心肠将她抱到秦谨怀里掉头而去时,她更是哭喊得惊天动地。
听闻这华曦性情极好,温柔体贴,与太子司徒永情感甚笃,想着他们的婚事不过是两方势力在利益驱使下的结合,还能如此和顺,算来
m.hetushu.com.com也是司徒永的福分了。
奉先殿内,三跪九叩完毕,他已咳嗽着从软榻上支着身体,说道:“秦将军免礼!”
他的举止神色丝毫未变,可不知怎的,就在那一瞬间,他那身流光溢彩的华美蟒袍似在散发着浓浓的悲伤和无奈气息。
正想着时,司徒永忽回过头来,向我瞧我了眼,复转过头去,依然向前走着。
我呆了呆,劝道:“怎会没有值得开心的事?你看,二嫂已有六个月身孕了,眼看着秦家又要添丁;何况今年我又在家,等孩子生下来,大家一定要好好庆祝庆祝。素素今年及笄,正预备物色人家,最好入赘到我们家,以后大嫂也有个依靠,大哥也不至于断了香火。小瑾这两年来没怎么发病,长得越来越壮实,前儿看他武艺,也大有进益。族里也有好几个后起之秀,这两年也越来越出息,应该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了。咱们秦氏一门煊赫,深得皇上宠信,如今又后继有人,难得不值得开心?”
我黯然道:“只怕另有些人,满心盼她再也好不了。”
刚刚我和司徒焕说德妃生病,原是过来探她的托辞,不想真的病得不轻。
其中神机营目前由太子司徒永直接执掌,神策营、神武营分别由神策将军和神武将军执掌。现在的神策将军正是司徒凌的心腹亲信;而司徒凌自前年奉旨前去平定晁天王之乱,一直兼着镇国大将军一职,若是在京城内出事,说不准便给扣上个治下不严的罪名。
秦彻打量着她,“她……和你长得很像。”
我答道:“就是说,山里的野兔都给捉完了,帮捉兔子的猎狗没用处了,可以宰了猎狗煮汤喝了。”
秦彻微愕,眼底也微微黯然,说不出是伤感还是怜惜。
回到秦府时,相思还在闹脾气不肯吃饭。
秦谨低声应了,却是不忿,说道:“难道我们就这么让人欺负着不成?眼看着姑姑还在宫里关着,又有端木皇后暗中使坏,那起跟红顶白的奴婢不知会让她受怎样的委屈。”
到了怀德堂,已见下人推了二哥秦彻迎了上来。
司徒焕虚弱地抬起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忽挥手示意随侍宫人退下,微俯了身子,问道:“晚晚,凌儿已经和朕说了几次,打算近来便把你们婚事办了。你意下如何?”
“一阵子是多少天?”
“娘娘跪在地上,煞白着脸,什么都没说……后来人都走了,我们扶她起来,她还是整天都不说话,只是常看着窗外不住地掉泪……这些日子泪水都没干过的。”
“秦氏一门煊赫……”
忽然间心乱如麻。
相思便笑了起来,“我是娘亲生的,当然像娘亲了!”
“相思……”
“神策营那边出了什么事?”
我心里一抽,却又麻木般觉不出什么酸痛,低头答道:“若得边境绥靖,家中平安,早些将婚事办了也不妨。”
我见天色不早,也不敢耽搁,急急回房中换了一身衣裳,紫衣玉带,金冠巍峨,却是从一品的武官服色,衬着俊美却冷峻的面孔,端地一身优雅贵气,却冷冽逼人。
太监畏怯地缩回了手,踌躇地向外张望着,一时不敢应我,却也不敢拦我。
司徒焕点头,“算算你们两个,也老大不小了,便是为国事烦心,也不能这样耽误下去。”
此地到北都,一路俱是宽阔的官道,马车向前行去,越行越快,前面锦帘上一对精绣的白虎晃动着,抬足欲奔的姿势看着好生踌躇,不知是打算奋勇进击,还是打算掉头逃去。
“他不是小心眼的人,可他也不是圣人。当年你出了那么大的事,他半句抱怨都没有,反过来百般待你好;你是他没过门的妻子,却心心念念记挂着那个死去的阿靖,他也由着你,要多体贴有多体贴。”
我微愕。
功高震主,备受猜忌,原是意料中事。怎样释去君王疑心,又得费一番思量。
司徒永的眸光自我面庞划过,落在华曦身上,唇边已弯起笑意,问道:“华曦,已经看过皇妹了?”
我忙见礼时,她已站在司徒永身侧,微笑道:“秦将军不必多礼,你与太子多少年的好友,何必如此见外?”
果然,司徒凌答道:“神策营的右卫将军和神策营的人闹上了,只怕又是有心人在挑唆。这时候还是不要横生枝节得好,我去看下,先将他们安抚下来。”
我心里一动,拍了拍她的脑袋,笑道:“没错,我瞧着这猎狗呀,还着实烹不得!”
他治军素严,京城这边又在天子脚下,更是谨慎,安排的部属无一不是谨慎机警之人,断不会在秦家出事之际无故闹出什么动静来。
姑姑怔怔地重复着我的话,忽凄然笑了起来,“难道这世间还有甚么值得开心的事?”
“回三公子,奴婢们也不是很清楚。那日早晨,娘娘正在院里折梅花,那个男子突然便出现了,我们过去时,娘娘惊得脸色都变了,正从那男子手中接过那封信……好像娘娘就看信的那么片刻工夫,便闯进来一堆人,说宫中有刺客,又有人说刺客是当年祈阳王的亲信,竟把那信也抢走了!”
这镇守京城的兵马,除了大芮皇帝直接控制的五千御林军,另设有神策营、神机营、和神武营,分别驻于西南大营、城北大营和东南大营,各有三千人马,俱是千挑万选身家清白的精兵强将。
我见他额上尚有汗珠,示意他坐了,抬手给他倒了杯茶,淡淡道:“不用着急,先喝口水润润。这是去了哪里,跑出一头的汗。”
我伏地,沉声道:“臣保护公主不力,令公主异国蒙尘,请皇上赐罪!”
低垂的眼睫下,有泪水一滴滴迅速滑落,滴在深褐的药汁里,然后被她大口大口地饮尽。
司徒永皱眉,向我走近了些,看了一眼自觉退到稍远处的太监,低低道:“晚晚,此事可能与皇后无关。”
按我素常的性气,他那般凌迫欺辱我,我将他一剑刺死并不为过。可为何,时日过得越久,越是没有他的消息,心里越是空落落般悬得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