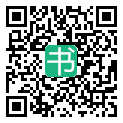第三卷 鸳鸯谱
第三十六章 相逢敛恨念旧缘
阿原叹道:“只怕你猜对了!”
左言希听得他来,已快步迎出,皱眉道:“北湮,你怎么来了?”
萧潇记挂阿原,只得先丢开左言希,大踏步奔了出去。
“……”
刚踏出门槛,便听得墙头有人惊喜叫道:“王爷,可找到你了!我就晓得小坏也在找你,跟着它果然找到了!”
约摸半个时辰后,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左言希才从丁家步出。
阿原微笑,“原大小姐闹出什么事都不稀奇,正如小贺王爷闹出什么事旁人都不会意外。我是不是厉害,你是不是无能,只怕没人关注。”
此刻,与郢王、韩勍都有联系的姜探竟出现在乔府……
小坏乌溜溜的眼睛瞪她,茫然不解。
阿原提过桌上油腻腻的茶壶,给自己倒了盏茶,若无其事地笑道:“没病没灾的,难不成一直窝在家绣花?不如来瞧瞧你案子查得怎样了……”
他端起那药碗,仰脖饮尽。
哪怕她怎样努力地告诉自己,记不得往事的她,只是阿原,并不是什么风眠晚……
天黑如墨,弦月如钩。
阿原道:“但有可能是朝中要员的外室,或手下的什么人。”
嗯,女为悦己者容,正是天大的事。
跟着老贺王身经百战的侍卫果然与众不同,惟恐晚了片刻便误了阿原的大事,话音落下,人已飞奔而去,堪称疾如闪电。
他们这里有动静时,早有伙计飞奔入内禀报。
他故意将左言希的来历和来意说得极清楚,意图惊走这个好看却不知好歹的年轻人。
阿原叹道:“他想查的,无非就是那些事儿。应该不难找。”
慕北湮失声道:“乔府?她怎会去乔府?”
于是,他曾将慕北湮挂在茅厕熏了一整夜,慕北湮可以报复回来,将他也挂在茅厕里熏上一夜?
于是,慕北湮对景辞的大度嗤之以鼻,再不曾当真。
小坏扑了扑翅膀,看他一眼,似有些得意的模样,却再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正如慕北湮完全不晓得它想表达什么。
这是小坏从胆大如虎忽然变得胆小如鼠的唯一解释。
“你是指……姜探和韩勍有来往?”
“怎么说?”
左言希但抿着唇沉默好久,才轻声道:“我对不起义父。”
有人打着灯笼,引出一抬青布小轿,正是先前姜探所乘。
那对灯笼上各有一个“丁”字,显然是主人的姓氏。
慕北湮呼吸有些粗浊,“总不会是死人吧?”
阿原连忙带了小坏和两名侍从匆忙奔离原地,惟恐小坏忽然间的失态引来乔府守卫察看。
侍从道:“那位姜姑娘在言希公子离开不久便又出门,我们跟了一路,跟到了乔府。”
可惜小坏和黑衣人的实力委实相差太过悬殊。
“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在这边见的人,都不简单。”慕北湮的脸色有些阴沉,转头看到阿原专注认真的目光,又笑了起来,“既然来了,咱们就一起过去瞧瞧,韩勍偷偷摸摸见的这位,到底是什么人……”
侍从骇然,“原大小姐想夜探乔府?”
她当然也算是有志气的。
慕北湮相信养兄的医者父母心,但也不得不承认左言希身为影卫,也不是吃素的。他对阿原都起过杀心,更别说其他人了。
若是看得顺眼,果然时时处处都顺眼。连过其门而不见,都能代为揣摩出一堆的善意来。
慕北湮道:“自然不是。”
他正懊恼之际,左言希已跟姜探说了两句什么,竟随之步入那院中。
因韩勍是梁帝心腹,在确定韩勍就是杀小印子的人后,阿原等便几乎能确定,小印子和瑟瑟必是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才被梁帝密令灭口。
慕北湮道:“我父亲虽是武将,但更倾向于待人宽仁的博王,而且……有点瞧不上郢王,觉得他急功近利,见识短浅。这些话我曾听他跟杨大将军提过,估计也跟皇上提过。若是二王争夺储位,父亲无疑会相助博王。还有,升宁长公主也偏爱博王,说博王和均王是皇上诸子中最厚道的。而郢王好武,长公主便很不喜欢,说他行事狠毒,和他母亲一样,满脸的刻薄相……”
阿原于鬼神之说不过付诸一笑,抚着破尘剑沉吟道:“其实若只是儿女情长,倒还好说。”
但阿原并未唤琉璃梳妆打扮,抬手随意绾了个髻,换了身剪裁利落的衫子,便带上小鹿、小坏,英姿飒爽地出了门。
伙计便笑起来,“哦,论起他家门楣倒也不算高,只是这会儿去求亲,只怕难。”
隐在暗处的慕北湮稍稍松了口气,嘀咕道:“有本事你留宿在丁家,我就服了你!”
而她究竟是怎样在他莫测的目光下沉沦的,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慕北湮喝骂得虽狠毒,一双桃花眼却幽光闪过,紧紧盯着左言希,分明在等左言希的解释。
阿原留心细看时,正见那边小巷里一抬青布围幔的简朴小轿行出,看着并不招眼。她低头一想,便明白过来,问道:“韩勍在这里有房子?”
轿中行出之人,果然就是姜探。那府前已有人候着,一见她便飞快地迎了进去。
慕北湮已赶到她身后,看着那白衣男子,差点把桃花眼瞪成杏仁眼,“言希?”
阿原紧跟着姜探所乘的那抬小轿,转过两道巷子,便见小轿在一座气势不凡的府第前停了下来。
阿原沉吟许久,向其中一名贺王府
和-图-书侍从道:“小贺王待会儿必定会回丁家察看,你去候着,待他回去便告诉他,我要进乔府探上一探。”
萧潇也有些诧异,松开按剑的手,上前行了一礼,“贺王爷!”
慕北湮青衣布袍,正翘着腿坐在窗边,跟两名同样乔作寻常百姓的侍从说笑。见阿原进来,他不由直了眼,“你不在家休养,跑这里来做什么?”
但小坏无论如何都不该忽然出现在他身边。
阿原道:“好是好。只怕等他到时,我想找的人也跑了!”
阿原眺向黑夜笼罩下的深宅大院,缓缓道:“如果我没猜错,杀害升宁长公主的凶手,和当日出现在说书人屋子里的黑衣人,应该是同一位。他是薛照意的同伙。他们背后的主子,就是杀害老贺王的主使者。如今那个黑衣人应该就在乔府。机会难得,我一定要进去看看那人的真面目!”
萧潇倒了盏茶,倚在门边,一手抱肩,一手持着茶盏慢慢喝着,算是在为众人守望,却能将众人神情尽收眼底。
她的眼睛里蒙着雾气,却格外的清亮晶莹,显然对眼下情形十分欣慰。
原夫人很是满意,感慨道:“我的女儿,果然比我有志气!”
阿原喝两口茶润了润嗓子,抬眸向他一笑,“当日的清离劫杀案算是水落石出,可老贺王案中犹有疑点。我可以放下清离案,你却不可能放下贺王案。你想查明你父亲遇害的背后真相。”
那白衣男子眉眼间有些愠恼,但容貌俊秀出众,举止温雅舒徐,——正是老贺王的养子、慕北湮的养兄左言希。
阿原亦大笑,说道:“对,旁人越不想我们快乐,我们越该快快乐乐地过着,才是对那些居心险恶之人最大的报复!”
他与左言希的行事风格南辕北辙,性格迥异,但自幼便如亲兄弟般相处,彼此了解甚深。贺王遇害后,即便有人刻意挑拨嫁祸,两人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并维护对方。
隔日,她便将预备好的嫁妆单子拿给阿原看,竟比贺王府的聘礼单子还要长上很多。
如深泉寒水,看不出半点风浪漩涡,但绝不是冷冰冰三字所能轻易形容。
慕北湮看到他这样的眼神便忍不住地嫌恶。
但这一刻,慕北湮已禁不住彷徨起来。
虽然连她自己都说不清,这么着离经叛道过了半辈子,到底是对还是错。
左言希虽有武艺在身,居然不躲不闪,生生受了他大怒之际的一脚,立时被踹得飞了出去,沿着墙边滑落,口角竟已渗出血来。
两位妃嫔的心腹宫人都被灭口,可见他们知道的那些秘密实在不宜为外人所知晓,故而连原夫人都不便去跟梁帝求证。
阿原瞪大了眼睛,“这鹰成精了!不然就是小鹿附体?”
报仇诚要紧,小命价更高。
侍从听阿原提到老贺王的案子,也不敢拦阻,踌躇片刻,说道:“大小姐既如此说,不如越性等上片刻,等属下找回王爷,商议了再一起行动可好?”
左言希面庞泛红,尴尬之余便也有了几分羞恼,“北湮,你跟踪我?”
萧潇眼见闹得大了,慕北湮还欲冲上去揍人,景辞冷冷看着,竟没有插手之意,忙要放下茶盏去阻拦时,忽听身后风起,尚未及回首,已见小坏扑进屋来,翅羽扫过他手边,恰将他的茶盏打翻在地。
她对朝中大员并不熟悉,但姓乔的恰好知道一位,正与她前阵子留意过的宫人落水案有关。
慕北湮怔了怔,“你认识他?”
不仅慕北湮,连她自己长得都太招摇了些……
它这一生最惊险的遭遇,当属薛照意被杀那晚,为相助主人险些被黑衣人开膛破肚之事。后来它九死一生找回县衙,倒也没见它怕过,还色厉内荏地攻击过萧潇。倒是数日前长公主遇害,它孤身追凶,虽只断了几根羽毛,回到阿原身边时却似受了很大惊吓。
小鹿坐在马车上想了一路,总算想明白了,“对!小姐就该这般打扮!小贺王爷不抵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公子哥儿,什么样花枝招展的美人儿没见过?小姐素面朝天,方才见得天生丽质,不同凡响!这就叫出奇制胜,对不对?”
也许真的只与风眠晚有关?
小鹿肯定道:“或许,也在忙着预备你们的婚事?小姐这边有夫人照应安排,他那里得事事亲力亲为吧?再则,小姐这几天精神不大好,他不来惊扰,也可见得他对小姐真不是一般的温柔体贴呀!”
慕北湮的脸色已十分不好看,“如果韩勍是郢王的人,那么……我父亲的死,可能真和郢王有关。还有升宁长公主遇害,也能说得通了!”
阿原斟酌片刻,站起身去取破尘剑,“走,咱们去贺王府瞧瞧!”
慕北湮也不觉叹道:“若你推断正确,那朱蚀受往事所累,一世白身,自然不愿郢王继位。他对皇上的影响力远不如我父亲,但成事难,败事易,亲友间挑唆几句,郢王想当太子,阻力更大。那么……朱蚀遇害,可能也和郢王相关?”
但慕北湮等再不曾想到,姜探竟已来到京城,还跟左言希暗中有所联系。
小鹿懵了,“小贺王爷没在府里?他……会去哪里?”
她拍了拍兀自不安拍着翅膀的小坏,“怕成这样就别在这里碍事!去,帮找北湮去!”
也为他的可恶,升宁长公主遇害后,他特地唤出https://www.hetushu.com.com慕北湮,问他为何执著要娶阿原时,慕北湮很恶意地说只是想报复他。
阿原抚额道:“你跑得再快又有什么用?难道慕北湮会在丁家门口等你?”
伙计向后一指,“他是老贺王的义子,皇上身边的人,如今正陪着皇上跟前最得宠的端侯住在我们家医馆,和我家老爷子一起为端侯诊治呢!”
阿原啼笑皆非,由她胡说八道一番,方道:“待会儿小贺王爷如果没在府里,你便留在王府玩耍,到傍晚时再乘这辆马车回府,不用等我,知道吗?”
他答毕,便知阿原在提醒他,姜探背后可能牵涉甚多,不可打草惊蛇。
眼前这情形,正与它那日被断羽后的模样差不多……
阿原沉吟之际,小坏已飞入乔府,在乔府上空盘旋片刻,忽唳叫一声,飞快折身而回,一气冲下来歇到阿原肩上,蓬着翅膀哆嗦不已,一对黑眼睛东顾西盼,竟似惊恐之极。
以慕北湮性情,此去必起争执。但阿原经历过贺王案,深知二人兄弟情分颇深,想来还不至于闹翻,倒也不怎么担忧。可慕北湮能从左言希口中问出多少真相,就很难说了。
萧潇知这扁毛畜生莫名地恨他入骨,偏又是阿原的心肝宝贝,伤它不得,忙退出数步,留意防范时,小坏已越过他,一径飞向慕北湮,歇到他肩上,傲娇地睥睨众人,倒也没有找萧潇报仇的意思。。
“那家主人叫丁昭浦,在郢王府里做事,听说最得郢王宠信。谁不晓得郢王是当今皇上最年长的亲生儿子?回头郢王继位,他身边的人自然跟着一飞冲天。这丁家的姑娘生得好看,人又聪明,听说还懂医术,所以提亲的还真不少,但听说都回绝了。大伙儿都猜着,这丁昭浦是不是打算日后当了大官,把姑娘嫁给哪家的王侯公子,或者根本就是打算将她直接送入皇宫当娘娘……”
侍从跳下墙来,奔上前急急禀道:“原大小姐让小人转告王爷,谋害升宁长公主的凶手,就是当日出现在说书人屋里的那个黑衣高手。现在那人就在乔立府上,她要进乔府探探,看清那人真面目。”
慕北湮当时听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慕北湮愕然,胸口恶怒登时翻涌而出,连骂都骂不出,抬起腿来,狠狠一脚踹在左言希胸腹间。
慕北湮一凛,顾不得再揍左言希,忙问道:“小坏,你怎么没跟阿原回去?阿原呢?”
慕北湮看到快步走出查看的英秀少年,终于相信景辞的确在这里,“萧潇?”
阿原散漫而笑,说道:“不论你娶我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同情,我既入了贺王府,从此跟你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出点什么事儿谁也逃不了。所以,你的事儿,没一桩跟我无关。”
萧潇忙抬眼,已辨出那个攀在墙头向院内张望的人正是自己的侍从,忙问道:“你怎么来了?阿原呢?”
他向阿原道:“既然有了头绪,不怕理不出真相。我现在去找言希谈谈,你先回去,把我两名侍从留在这边监视着丁家的动静就行。一路小心,别把自己累着!”
伙计受惊不轻,吃吃道:“左……左公子吗?”
但慕北湮旋即想起,他若敢这样做,梁帝指不定会剥了他的皮把他丢茅坑里活活淹死。
小轿终于停在了某处民宅前。
小坏已被阿原教过,居然也机警地不肯暴露形迹,待阿原等走出好长一段路,才振翅跟了上去。
阿原盯着那小轿,低声道:“你猜,那轿里的人是谁?”
阿原走到近前,举目看向门楣上的金漆大字,“乔府?”
阿原摇头,“我不是说这个。听闻当年吕氏怀着郢王,入京投奔皇上之际,皇上正征战在外。途经沁河时,吕氏病困潦倒,曾向朱蚀求助,朱蚀因她是个营妓,置之不理,后来还是慈心庵的住持妙枫收留了她,并容她生下郢王。朱蚀是皇帝堂弟,皇上登基后却没捞着一官半职,指不定就跟这个相关?而且,朱蚀虽未入朝为官,到底是朱家的人,跟宫里的太妃、宫外的宗亲多有联系。听闻诸位皇子路经沁河时,也多会前去拜望,更见得他在朝中并非全无影响力。但前去拜望的皇子里,只怕不包括郢王吧?他跟郢王这仇怨结得可不浅!”
小坏听得“姑爷”二字,立时昂起头来,一扑翅膀便飞了出去,端端正正飞往慕北湮离开的方向。
阿原叹道:“找北湮,慕北湮!慕北湮!就是小贺王爷,你家姑爷!”
“那小轿里的人是……”
慕北湮真的惊住了,不由松开了那伙计。
在查贺王案时,隐约的线索指向姜探曾参与其中,阿原便在结案后挖开了姜探的坟墓,证实姜探未死,并曾在墓地出现,陪伴过因她而疯癫的朱继飞。
一时原夫人离去,阿原沉吟片刻,问向小鹿,“贺王这几日都没过来?”
阿原失笑。
原府侍奉阿原的侍儿众多,小鹿常常插不上手,虽然地位不清闲得很。小坏凶猛,却只认得小鹿,于是小鹿便时常跟小坏说话儿,提到慕北湮时,一口一个“你家姑爷”,再不料小坏别的听不懂,却已晓得慕北湮就是它家姑爷……
左言希被戳中软肋,无可辩驳,想想的确己身不正,遂只好由着慕北湮胡闹,自己常https://m•hetushu•com.com在皇宫或端侯府住着,眼不见为净。
而姜探依然一派恬恬淡淡的娇柔模样,一路眉眼温柔,与左言希轻言细语,再不晓得都在说些什么。
慕北湮虽担忧阿原,却一万个看不惯景辞这气势凌人的模样,怒道:“我拉她一起查案怎么了?我们夫妻一体,不论富贵忧患,同进共退,天经地义!我的父亲,她的公公,一世英雄,岂能死得如此不明不白?我再不成器,也不会是左言希!我会不惜代价查到最后!”
慕北湮不答,步入房中看时,景辞坐在临窗的竹榻上看书。他的手边有碗药,已经没有半分热气,大约早就凉了,却一口都没动过。
乔贵嫔之父,大理寺卿乔立。
阿原、慕北湮终究分开行动,各自带了一名随从,一前一后盯着那小轿,一路小心谨慎,到底没被轿中之人发现。
景辞听他说起夫妻一体云云,竟似被人当胸射了一箭般连退数步,正退到案边,俯首看向案上那碗凉了的药。
小坏的姑爷已被萧潇引入药铺的后院。
左言希皱眉道:“经营这药铺的吕大夫与我亦师亦友,对端侯所患的这类病症颇有心得,所以带端侯过来住几日,方便就近诊治。”
只是左言希居然还跟卷入他父亲案子的姜探不清不楚,不由让他倍感沮丧。
阿原再不料母亲竟已想得如此深远,心头五味翻涌之际,不由握了母亲的手,强抑住喉嗓间的哽咽,微笑道:“妆奁再丰厚,也抵不上母亲心意万一。可阿原从不曾好好孝顺过母亲,何德何能受母亲如此疼爱?”
他淡淡瞥了眼左言希,并未起身,闲闲地继续翻着书。他的面容清瘦,气色也不大好,但眉眼清凉而坚毅,并未因病痛显出孱弱来。
慕北湮静默了片刻,叹道:“阿原,这事儿跟你无关。”
慕北湮看左言希去扶姜探,不禁捏紧了拳,正待步出阻止时,阿原忙拉住他,低问道:“你做什么?弄清姜探和韩勍的关系了吗?这处房屋虽是寻常民居,看着挺大的,应该不是姜探一个人住着吧?”
阿原吸了口气,立时改变主意,向侍从一招手,紧随那小轿蹑踪而去。
慕北湮不由问向那伙计:“端侯是吃错药吃坏了脑子,还是病得快死了?好端端的皇宫和端侯府不住,跑这里来做什么?”
小鹿道:“来过两次呀!或早上,或晚上,不过好像有急事,来去都挺匆忙的,也没进内院,就喊我出去问问你的情况,然后就走了。”
慕北湮反问:“你又怎会在这里?”
嗯,左言希如果不是被女鬼迷了心窍,多半是被景辞传染了疯病……
阿原一拍他的肩,“放心好了,我不是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娇贵小姐,有宝剑在手,又有小坏伴着,怕什么?你忙你的去,我待会儿就回去。”
和朱继飞一样对这泥足深陷的,是左言希。
于是,那次关于阿原终身的交谈,两人不欢而散。
但见多识广的原夫人对女儿的这桩婚事很看好,对新换的女婿也十分满意。
他一把揪了伙计前襟,问道:“方才进来的年轻公子呢?”
显然是京内有年头的老药铺,并有相当出名的老大夫坐诊。
他还待要说什么,忽瞥到窗外,忙一拉阿原,藏了身形只从侧面观察外面动静。
他迟疑了下,又道:“那凶手应该武艺极高,小坏发现后立刻躲了回来,根本不敢照面。小人虽劝原大小姐等找回王爷商议后再行动,但原大小姐怕错失机会,不一定愿意等。”
阿原跟那黑衣人正面交过手,吃过亏。可当时夜色深沉,黑衣人蒙面持剑,除了武艺极高外,阿原并未对他其他特征留下印象。但小坏视觉敏锐,并不需要依靠人的五官来辨认。它必定认得将它重伤的黑衣人,并且印象深刻。升宁长公主遇害时,它正是因发现了它天字第一号的大仇人,才顾不得通知主人,奋勇追凶而去。
阿原沉吟着,看天色不早,便吩咐贺王府的两名随从继续监视,正要带小坏先回府时,却听那边“吱呀”声响,竟是丁家大门打开。
景辞言语间虽未示弱,但已说得很明白。他在为上次之事道歉,并愿意接受慕北湮的报复。
当日他戏弄阿原一回,景辞设计擒他,将他吊在臭不可闻的茅厕中时,便是这样清凉可恶的眼神。
待左言希、姜探等人进去,慕北湮忍不住叉腰低骂:“这个糊涂虫,被美色迷晕了头,打算一错到底吗?这都是什么事儿!他真想把自己给搭进去?”
估计它在被削断半截翅羽后,才后觉后觉地惊恐起来,意识到对方刀剑凌厉,想取它小命易如反掌,于是慌不择路高飞逃开,从此对此人的惧意根深蒂固,乃至刚刚见到那人后,立时吓得敛翅而还,再顾不得报仇雪恨了。
慕北湮怒道:“你天天跟在大贵人身后摇头摆尾,我得多犯贱才有那心跟踪你?我盯的是韩勍,发现有人鬼鬼祟祟跟他来往,顺便跟着那人小轿走了一回,不想盯到郢王心腹丁绍浦家,正见姜探下轿,然后和你牵着手进屋……”
阿原正了正衣冠,笑道:“走吧!你这副打扮,是不是乔作我的随从更方便?”
左言希对阿原没什么好感,当然对慕北湮自己做主定下的这门亲事并不赞成,甚至十分头疼。只是慕https://m.hetushu.com.com北湮向来我行我素,连老贺王在世时都管束不住,何况他这养兄?
“祸水!标准的红颜祸水!而且,他知道她住处,必定晓得她来历,那么,那么……”
慕北湮惊异,“朱蚀案?嗯,朱蚀好歹是皇亲,他的继室夫人敢联合姜探谋害他,多半还是因为姜探背后有郢王撑腰的缘故。”
勤姑在来到原府后,曾特地告诉阿原,小印子可能是被灭口。她更曾提过,小印子告诉过她,乔立是靠郢王之助才当上京官,随后更因为乔贵嫔的缘故做到大理寺卿这样的高官。乔贵嫔与郢王来往得很密切,似乎很不寻常。
慕北湮便有些笑不出,“你知道我在查案?谁多嘴多舌又跟你提这个?”
她拉着慕北湮悄悄退开,到附近寻了一家胭脂铺走进去,先挑了盒胭脂买下,才向里面的伙计打听:“东面那户人家是不是姓丁?昨天我哥哥经过那里,无意见到他家的姑娘,说生得真好,喜欢得紧。若是门当户对,便打算和父母商议,托人前去求亲了!”
继续监视丁家时,两人都有些心事重重。
见面谈起此事时,左言希再三说起阿原与景辞纠葛极深,慕北湮不宜卷入其中;而慕北湮则认定景辞和阿原婚约已解,又有皇上发话,凭谁也不该阻拦他的亲事。且左言希因维护姜探受了个把月的牢狱之苦,慕北湮当然也会反问左言希,到底和姜探是什么关系,怎能为一个身份不明的女子迷失本性,甚至助纣为虐……
姜探弱不胜衣,却苍白清秀之极,瞧着的确不似活人。
他恨恨地盯着左言希,“你在丁家等候,足见得你早就知道,姜探还有一重身份,是丁绍浦的女儿,是郢王的人……那么,在姜探一再出现在先前那些案子里时,你就该知道她,或者说郢王,与父亲被害有关?你还帮她?一而再地帮她?甚至回京后还在跟她暗通款曲?”
原夫人道:“你不是那等小家子气的矫情女子,凡事能想得明白,又有自己的主见,我也放心得很。嗯,我这辈子得不到的,我的女儿必定可以得到,必定可以一世快快乐乐的。”
景辞的眼睛只往上瞧吗?
慕北湮的确生得太好一些,青衣布袍难掩一身贵气,桃花眼宜喜宜嗔总是含情,如何装作随从?
慕北湮点头,“有个情人住在这边,他隔个三五日便来一次。但我不觉得他过来不仅仅是为了会情人。”
“不管是什么事儿,先弄清这姜探的底细吧!”阿原看向大门两侧悬着的灯笼,沉吟道:“嗯,这家人姓丁。”
景辞也住在这里?
阿原失笑,却不由地点头,“对!长乐公主曾说,皇上派她上山,原是接升宁长公主回宫。皇上近来抱恙在身,调养了这几个月也不曾完全好转,必会考虑储位问题。叫长公主回宫,很可能会跟她商议此事。对了,还有朱蚀案,如今看着可能也不是那么简单了!”
“确切地说,应该是丁昭浦,或者说是郢王……跟韩勍有来往。”
就是病得快死了,也该请大夫上门诊治才是,哪有跑寻常医馆里住着的道理?梁帝恩威并施之下,再有名的大夫也不敢不出诊吧?
若因此被对手察觉,也是万般无奈之事。
慕北湮叹道:“我是不是该请些高僧回去做场法事?言希一向是聪明人,怎会忽然如此糊涂?八成是被女鬼迷了心窍吧?”
景辞眸光闪了闪,终于看向左言希。
阿原藏到墙角窥望,尚未及看到轿中之人的模样,先看到了立于宅院前默然等候的那名白衣男子,忙揉了揉眼睛。
左言希面色已由红转白,“你……还在查韩勍?查义父遇害的案子?”
阿原翻看着,苦笑道:“母亲,这也太多了吧?打算将半个原府给我做陪嫁吗?”
她是小姐的贴心小棉袄,最识大体,当然不能因争宠误了小姐的大事。
说话间已经到了贺王府,那边阍者认出是原府小姐的马车,连忙打开门,一径将马车引了进去。
说不出那是怎样的目光。
相助姜探假死脱困,在姜探刺死傅蔓卿后代为引开追兵,都是确凿无疑之事;阿原更曾猜测,当日追杀沁河衙役丁曹、并放毒蛇试图灭口的人,也是左言希,而不是病弱的姜探。
慕北湮猜他是不是进去抓药,遂在门口等了片刻,始终不见他出来,遂踏步进去察看时,哪里还有左言希踪影。
“可如果我没记错,郢王和韩勍素来不睦,给外人的感觉势如水火……”
看左言希的神色,似乎颇有些不悦,但他隐忍着并未多说。从姜探踏出轿门的那一刻,他的目光便没有从她身上移开过。
阿原嘀咕,“有急事?”
左言希已紧跟着走进来,追问道:“北湮,你怎会知道这里,追到这里来找我?”
慕北湮冷笑,“就近诊治?是就近跟你的心上人姜探姑娘相见吧?”
不论景辞对阿原究竟是怎样的感情,至少他是真的不想其他男人碰她。只为慕北湮向阿原下了药,都不曾做什么,便能那样对他,那如果慕北湮娶了她呢?还是借着皇命光明正大地娶了她,爱怎么碰她便怎么碰她呢?
景辞、萧潇都不由凝神看向左言希。
左言希迎向小轿时,轿帘已被轻轻挑开,里面盈盈步出一少女,长发如墨,肌肤似雪,极美丽,极娇弱,——正是当日在朱蚀案中“和图书死去”的朱继飞心上人姜探。
显然,左言希也不曾说起过此事。
但阿原想来想去,只记得他居高临下垂眸看向自己的目光。
小坏虽驯服未久,跟着阿原也历过些风雨,从未有过这般退缩恐惧的时刻。
“可如果所谓的势如水火,只是他们有心营造的错觉呢?”阿原眸光闪动,如夕阳下的潾潾秋波,明光绚目,似要扫尽眼前的晦暗不明,“查贺王遇害案时,说书人曾遗落郢王府令牌,又故意让李瑾青知道小玉有这么块令牌,还暗示姜探与小玉、薛照意有联系。他这是千方百计想把我们查案的目光引向郢王府。但正因为他做得太刻意,反而让我们觉得他居心叵测,故意混淆视听,移祸江东。可如果说书人说的是真的呢?如果郢王和韩勍,早已暗通款曲呢?”
慕北湮恨恨地说着,却越想越心惊,立在夏日的夜风里,竟觉那风冷嗖嗖地穿胸而过。他打了个寒颤,嗓子都低哑了,“若姜探曾受命参与谋害我父亲,他还敢跟她交往?那他……他又成了什么人?”
想来景辞还是吃错药吃坏脑子的可能性更大。
慕北湮原以为景辞羞怒之下必会大发雷霆,谁知景辞安静了许久,才低低答他一句:“若你因那次之事怀恨在心,我向你道歉。我怎样报复你,你也可以怎样报复我,我承受便是。但请你善待阿原。否则,我不饶你!”
原夫人不以为然,“给上半个原府又如何?我一世谨小慎微,挣下偌大家当,不留给你们,难道留给原家旁枝儿的侄子侄孙?清离这么着一走,离得那般远,便是想着多多给她嫁妆,也有限得很。若不是贺王丧父未久,不宜招摇,我必定预备得更多。不过也不妨,婚后我一般地可以给你添补东西,绝不叫你和我的小外孙委屈,也不叫北湮委屈。你们母子俩,日后哪怕只靠你的嫁妆,也能丰足一世,不必看人脸色,也不必觉得占了贺王府便宜,心里不自在。”
侍从忙道:“我会速去速回!”
慕北湮叹道:“不论我娶你是何居心,你既入了我贺王府,平平安安做贺王府的女主人就好。这么着舞刀弄剑的,岂不是显得我太无能?”
而不是官方结论里那个简单而窝囊的结果。
景辞终于站起身来,盯着慕北湮,“难道你拉着阿原一起在查你父亲的案子?”
慕北湮叹道:“我倒也愿意乔作你随从,可叹我这颠倒众生的模样,想装也装不像吧?”
阿原思量着回京后断续听到的一些传闻,却是越想越心惊,“老贺王……不喜欢郢王?”
半个时辰后,阿原便在一家小面馆找到了慕北湮。
原夫人也不禁盈了泪,亲昵地揽着她肩,柔声笑道:“傻孩子,天底下哪会有母亲因为希图儿女的回报而爱惜孩子?无非出于母女天性而已!何况我生了你却未能庇护你,让你流落别处,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好容易母女团聚,自然该好好补偿你。”
她道:“北湮是个有心人,虽然匆促,聘礼倒也预备得丰厚。所谓投桃报李,咱们家去的妆奁也不能少。我按他的单子,双倍陪嫁过去。另外还有两处最肥沃的大田庄,也会作为奁田随嫁。至于那些四季衣物,珠宝首饰,原先便有预备,近来还在陆续赶着添补,绝不会比别家的公侯小姐差半分。”
连禽兽都掂得出二者的轻重缓急。
阿原想着姜探淡若轻云的身姿,苦笑道:“因为朱蚀在皇家的那点影响力便决定杀他,似乎有些小题大作。或许只是姜探想报仇,郢王顺水推舟?北湮,你那兄长喜欢上的,究竟是个怎样的女子?”
慕北湮苦笑道:“你也该看得出来,皇上对郢王并不满意,不然早就该立作太子了!”
慕北湮斥道:“别和我提什么义父!你不配!再怎么谦恭孝顺受人称赞,你都不配!你唯一的那重身份,就是那个参与害我父亲的小贱人的情人!还义父……你别他妈恶心我了!父亲瞎了眼才收养了你这么个畜生!我瞎了眼才把你当兄弟!什么狗东西!”
慕北湮抬头见小坏歇于一处檐角,褐色身形几乎与暗夜融为一体,并不惹人注目;阿原穿得也简素,夜间看着并不出奇,便也放了心,转身追向左言希。
但以阿原今时今日在贺王府的地位,想问出慕北湮的行踪也是轻而易举。
他退开一步,仔细将药堂又看了看,才发现这药堂收拾得虽然齐整亮堂,但药柜什么的都有了年头,木把手被汗渍浸得油光发亮。
如阿原所料,慕北湮真的没在王府。
小鹿欢呼雀跃,“小姐要去见姑爷?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小夫妻俩正该如此!正该如此!我去唤琉璃姐姐来给小姐梳妆,她的手比我巧多了!”
阿原对朝中之事不甚了了,却很快猜到这些事的关键所在,“与……储君之位有关?”
慕北湮打量着有些陈旧的屋宇,说道:“看这情形,应该只是有点闲钱的寻常人家,不会是朝中要员。”
慕北湮白她一眼,“你就逞能吧!”
慕北湮跟着左言希转过巷角,看着行人稀少,正待追上前时,却见左言希一转身步入旁边的药铺。
阿原笑道:“我没觉得受苦。如今更有母亲和北湮真心待我好,我开怀得很。那些让我不痛快的事,让我不痛快的人,自然该远远甩到脑后,绝不自寻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