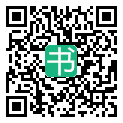第二卷 帐中香
第十七章 金屋有怨不成眠
阿原拍手道:“好主意!只是我本就声名狼藉,这名声再坏又能坏到哪里去?不过从此皇上和谢岩都会知晓,公主是怎样欺负羞辱伤病失忆的原家小姐……不知会不会觉得公主气势如虹,威风八面,大大长了皇家颜面?”
景辞正待推门时,阿原抬脚,奋力一踹,已将反闩着的门生生踹开。
“我养的鹰……”
阿原道:“你家竹筒长得美人蛇似的,有点弯,一次倒不干净,只能多来几次。若再倒不出来,爷只好剥了蛇皮慢慢捋出来了!”
傅蔓卿将手猛向窗外某个方向一指,嘶声道:“他……”
一名细腰修腿的女子支着额卧于榻上,长眉秀目,乌发如云。她披着一袭金凤纹银红大袖衫,是寻常女子很难压住的的华丽色调,偏生被她穿出迥异他人的慵懒和雍贵,令她整个人明艳得令人不敢逼视。
“……”
阿原摸摸头,只得用水勺一次次将芳香扑鼻的热水舀入木桶,然后一桶桶拎出去倒掉,最后才能和人将沉重的浴桶抬出。
阿原不答,转身去厨房重新预备热水,然后意外地见到景辞正坐在灶下。
左言希文采风流,精擅琴棋,又以医术闻名,才名远胜慕北湮,加上性情又好,在阿原看来,除了不会武艺,这人已近乎完美,所以才屡屡将他和景辞认作一对,再不想他剑术之高,竟也能与萧潇抗衡一时。
柳薇已在旁催道:“原姑娘,赶紧烧水要紧。公主等得久了,只怕又会不悦。”
她拔出破尘剑,正要去相助萧潇,擒下左言希时,左言希已一剑将萧潇刺来的剑挡住,然后轻轻一松手,宝剑已弃于地间。
还是个遇事头一缩不肯担责的男人,真真晦气。
她道:“这位差爷,白天不是已经查过了吗?我们家蔓卿实在人,跟竹筒倒豆子似的把该说的都说了,还想问什么?”
谢岩道:“不会是北湮。”
谢岩显然对长乐公主避之惟恐不及,但刚也说了,君臣尊卑有别。别说阿原如今只是沁河县不入流的小捕快,即便是京中的原大小姐,她没母亲的能耐,便不可能无视公主的吩咐。
长乐公主见她安之若素,越发纳罕,随即道:“该沐浴了。还需麻烦原姑娘去瞧瞧,那水温还合适不合适。”
看他们眉眼含情的模样,哪里像去查案,分明就是打算出去看看星星,看看月亮,顺便看看今夜能不能凑成双。
阿原看看她腰际的宝剑,虽无惧意,却也头疼不已,说道:“嗯,她不悦,只怕会令我更不悦。”
慕北湮的桃花眼终于眯起,却有些不可置信,“嫁祸?”
阿原问:“这里脏脏的,你跑来做什么?”
刀剑交迸时的声响和光芒,立时将黑衣人快要消失的身影暴露无疑。
李斐抬袖擦着额上的汗,下定决心以后做一个安静的追随者就好,绝对不再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即便对阿原从此也得多留个心眼,不能随意呼来喝去了。长乐公主住在京城皇宫里,也不是寻常人想得罪就得罪得了的。
“长乐公主?”阿原懵住,“那是谁?”
那厢小鹿已叫道:“就是被咱们夫人赶出去的那位公主呀!她虽厉害,可不是一样怕我们夫人?”
紧绷的身体一软,她无力跌落地间,纤白好看的手兀自伸着食指,也已重重垂落。她的眉眼间依然满是楚楚韵致,甚至眼睛都还保持着生前的美好形状,却已没了呼吸。
“长乐公主……”
景辞睨她,“你倒想得开!”
“去吧!”
他将傅蔓卿的那方绢帕塞入怀中,摔门而去。
“那是喜欢你的公主。”景辞转身向外走去,“我便不信她愿意让‘情敌’看到她满脸疹子的模样。当然,应该更不愿意你看到她那副模样。嗯,你这一路辛劳,身累心更累,正好赶紧睡个好觉去……”
阿原的面颊被灶膛内的火映得红扑扑的,笑意明朗舒展,“可我敢肯定,此事必定和花月楼脱不开干系。”
“她也忒倒霉!”慕北湮脱口而出,随即苦笑,“没事,原夫人虽然不在,这不是还有端侯吗?呵!这小小的沁河,几时变得这么热闹?”
阿原道:“看着慕北湮嫌疑更大,但细看下来左言希更可疑。”
她再不似先前那般矜贵娇婉,却如春日海棠般明媚动人,同样地摇曳人心。
他接过,看着上面那个“傅”字,已疑惑道:“这是傅蔓卿的手绢,怎会在你这里?”
谢岩苦笑,“于是,阿原不为难,我为难了……你可真是……”
长乐公主轻笑,“嗯,的确急。不过再急也得等本公主洗去风尘,略事休息。”
景辞道:“不会是言希。”
正思量时,那边小道上传来阿原的笑声,忙举目看时,景辞正携了阿原的手,不紧不慢地向县衙外走去。
左言希摇头,“我倒不担心这个。我只想着凶手看着嫁祸失败,也许还会有所行动,可惜这两日一直留心观察,并未发现谁有异常。”
长乐公主身边的确有个佩着剑的女侍者,应该是个贴身保护公主的剑道高手。但细致活儿做不来,鸠占雀巢后短短一两个时辰便让这屋子大变样,又是谁做的?
一个素衣浅淡,一个锦衣华贵,都是爱洁之人,却偏坐在油腻腻的桌边说着话儿hetushu•com•com。
阿原连忙奔过去时,已听得有年轻男子清朗的责问:“左言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谢岩道:“哦,好像尿急,换裤子去了……”
柳薇欠了欠身,“多谢公子和原姑娘提醒,我会让公主留意,别让热水碰到出疹子的部位。”
简直就是废话。
“没请到左公子。下人说他身体不支,可能在哪里打盹,但黑灯瞎火的一时也找不出来。”
谢岩扫她一眼,凤眸里闪过一丝怅然,但很快恢复微冷的清明,“你最怕的那个。”
长乐公主抬头看了眼着实没法装饰的陈旧屋顶,叹道:“这个我倒相信。若换了以往,我打死也不信原大小姐会住这鬼地方。”
这时候,难道她不该故态复萌,拿出她逗引男人的手段来,抿唇垂泪,做出种种令人怜惜的委屈情状,令那些自承正直的男子拍案而起,指责公主仗势欺人、气量狭窄?
阿原回到沁河县衙时,并没有立刻看到李斐,倒是谢岩迎了出来,还抬头看了看天色,“嗯,半个时辰,也差不多吧!”
左言希道:“你应该看得出来,李知县那点能耐,哪敢查我们王府的案子?无非是因为有景典史在。我跟他也算是知己,若我认定你是被嫁祸,他必定会选择相信我。”
阿原咳了一声,笑道:“大约已经凉了。没事,我重给公主预备热水去。”
左言希道:“县衙里的人明面上似乎都回去迎接使臣了,但原捕快应该还留在府里某处暗察。刚刚有人赶过来,救火似的四处在找,估计很快会把原捕快给请回去。”
阿原看她出了浴桶,忙去拿她衣衫时,长乐公主道:“柳薇会服侍我更衣。你去把水倒了吧!”
长乐公主抓了抓手臂上那些小红疹,怒道:“这热水怎么越洗越痒?不洗了!来替我更衣!”
阿原实在想不出自己怕谁,一时不可思议。
傅蔓卿也是个聪明人,应该在最后关头想到了自己遭人毒手的缘由,可惜身中要害,竟来不及说出那个关键人物是谁。
若诊治无效时,他便不得不去请他的好表弟手下留情了。
简朴得一眼可看到底的房间,已被松花色的帐幔层层分割开来,地上铺了织锦毯子,桌上也铺了锦罩,摆了一套青瓷茶具和一只青釉花瓶,质地光润明净,比阿原原先用的不知珍贵多少。
不久之后,沐桶便已装满热水。
“不……不知……”
谢岩何等聪明,猜到他必定做了手脚,苦笑道:“辞弟,那是公主……”
阿原道:“我怨她做什么?她做得越多,越无法讨心仪的人欢心,也怪可怜的。何况她绞尽脑汁想着怎样让我不开心,偏偏我还开心得很,于是她只会更不开心。”
阿原做了个鬼脸,“对,我现在就是个好姑娘!只求公主也能尽快看出,谢公子你不领她的心意,绝对不是因为我呀!”
话未毕,那边已传出齐刷刷的两个声音。
左言希笑了笑,“他会信我。”
长乐公主懒懒地答了一句,抬臂看胳膊上刚起的红疹子,叹道:“这屋子,再怎么收拾也干净不了。得多脏的人,才能在这里长长久久地住着?”
尿急也不至于换裤子,除非真的吓得尿身上了……
长乐公主显然不习惯跟人斗嘴,懒懒地转过头去,吩咐道:“带她去拿我的晚膳。记得,先让她洗一下手和脸。”
而她长乐公主是恶人,自然只能继续恶下去。
看着他已不是近乎完美,而是真的很完美。只是这么完美的人居然是杀人凶手,这种“完美”未免幻灭得太快。
谢岩紧走几步追出去,正见景辞披上知夏姑姑递来的外衣,悠闲地踱了开去。
屋内窗户洞开,帐幔飘摇,傅蔓卿倒于地上,胸口血流如注;一名黑衣人正掷下手中染血的利匕,飞快跃向窗外。
但阿原的确是因为发现疑点,才尽职尽责地赶来花月楼查案。
左言希自幼发奋,读书有成,年纪稍长离家拜名师学习兵法,意外对医道大感兴趣,研习没几年,居然成了远近闻名的医道高手;慕北湮天资虽高,却洒脱不羁,习武读书在他看来都是追求心仪美人时应该具备的风流才艺,所以才肯稍稍用功。
谢岩欲待相唤,想起他这些年的坎坷,苦笑着闭了嘴,举步走到阿原的卧房前,看着窗口透出的明亮灯光。
阿原道:“这里哪来的太医?不如我去请谢大人过来?”
长乐公主诧异,细看阿原时,却见她满额乱发,满面尘灰,精巧的鼻翼还渗出细密的汗珠,看着很是狼狈。但她举止爽利从容,双眸清亮带笑,明洁如玉的双颊在奔忙中泛起浅浅红晕,虽是男装打扮,不施脂粉,也有一种水底明珠般的夺目光彩。
左言希已继续道:“贺王是养育我成人的义父,实与生父无异。我比谁都想尽快查出谁是真凶。我也是对傅蔓卿有所疑心,才暗中赶过来打算问她一些事,可惜我来晚了!”
阿原向他们笑了笑,“但二者必居其一!”
而拦住他正跟他交手的那年轻男子,则是来自京城的剑客萧潇。
景辞急问:“是谁?”
屋子里静默片刻,然后传来铜镜砸下的声音,“你给我出去!出去!传太医https://m.hetushu.com.com!传太医!”
他低头看傅蔓卿,见她胸口尚在微微起伏,抬手将她抱起,沉声问道:“傅蔓卿,是谁在害你?”
谢岩想起景辞曾在沸水前晃荡过,蓦地有种不妙的感觉,“你做什么了?”
阿原在内纳闷道:“不应该呀,刚这洗脚的水是清水,怎么还起疹子?莫非公主这体质,闻不了窗外的花香?还是公主带来的被褥太久没晒过?咦,脸上也开始泛出疹子了,是不是很痒?”
谢岩轻叹,“若我去劝了,她今晚恐怕睡不着了!”
眉眼清淡,意态安闲,谢岩看起来与上回离去时并无二致,只是他眼底的确似有什么在灼烧,却生生地压住,令他的脸色看着确实很不好看。
女侍应了,将她领入厨房,看她洗了手,便抱着剑监督她将一碗清粥、三四碟小菜端进去。
阿原走入自己住了四个月的屋子,有种走错门的错觉。
阿原走过去见礼,“小人沁河县捕快阿原,拜见公主!”
还没来得及追问,这两日在衙门里躲懒的小鹿已飞奔过来,叫道:“小姐,你可回来了!长乐……长乐公主把咱们房间给占了!”
左言希苦笑着看向阿原,“你也这样认为?”
傅蔓卿一息尚存,挣扎着喘息道:“不……不是小贺王爷……”
谢岩听着她直白之极的回答,却也不生气,凝视她的眼底竟微微漾开了笑意。
景辞看着并不感兴趣,令小鹿给自己倒了茶来,慢悠悠地啜着,说道:“我已去过花月楼,那位傅姑娘证明,慕北湮整夜都和她在一处,并未离开过。”
阿原已走过去烧水,笑嘻嘻道:“谢公子放心,我是忍辱负重、心地善良的好姑娘,不为难!正好你们都在,索性再把李大人请过来,我们分析分析案情吧!”
“我……怕?”
指不定就是得了阿原在沁河的消息,疑心谢岩是过来与她相会的,才执意跟过来。
因原夫人的缘故,后来谢岩与原清离的来往尚算平静。但长乐公主究竟嫉恨成什么样,便只有天知道了……
阿原已渐渐习惯他的口是心非,一边折着柴枝,一边笑道:“叫知夏姑姑给你预备个暖炉就好……不过这时候还用暖炉,只怕有些夸张。”
她一推谢岩,悄声笑道:“要不,你去劝劝?”
“来的使臣,就是谢岩。”左言希答着,却无半分欣慰之色,“但长乐公主也跟着来了……”
慕北湮问道:“你为何不担心我被官府疑心?”
阿原再次给长乐公主预备好热水时,心情更是愉悦无比。
他和阿原都已来过一两次,对这花月楼已是熟门熟路,如今既有疑心,不用老鸨引路,径冲向傅蔓卿卧房。
慕北湮愤然道:“他倒是提了些,你却只字未提!”
如梁帝、谢岩这等聪明人,岂会不知原清离浪.荡无.耻?
左言希道:“那夜好些人亲眼看到傅蔓卿将那绢帕丢给了你,这绢帕却出现在义父遇害现场。这样的话,你当晚不曾回来,怎么看都像刻意制造不在场证据,欲盖弥彰。”
景辞笑了笑,“我也觉得有些夸张,所以就过来火边坐一会儿。长乐公主为难你了?”
阿原叹道:“禀公主,我数月前遭遇匪人,头部受伤,先前的事一件也记不得了,大约口味也会有些变化。”
跟在阿原后面的女侍看得明明白白,阿原不曾偷懒,烧水提水舀水事必躬亲,并不假手于人,虽把自己闹得满脸尘灰,满桶的水却清澈洁净,只得向长乐公主示意,着实无隙可寻。
长乐公主笑盈盈地站起,扶了阿原的手步入崭新的浴桶。
她转身往她被占了的卧房走时,谢岩紧跟在她身后,突然问道:“喜欢景典史?”
阿原白他一眼,“当然。不喜欢他还能喜欢谁?难不成继续犯蠢跟公主抢男人?”
阿原指住自己,“你当我眼瞎?还有景典史是跟我一起过来的,他总不至于陷害你吧?”
除非傅蔓卿因某些原因不想接客。
阿原道:“对啊,我居然觉得这里住着轻松自在,可见我和从前那个原清离,真的已经完全不同了!嗯,喜欢的人也不一样了,公主切莫再将我与当日的原清离相提并论!”
左言希叹道:“好像谢岩跟皇上提起人选时,长乐公主正好来了,然后便跟皇上说,谁都不合适,不如她和谢岩来。于是……”
傻子都看得出长乐公主是有心要折腾死她。可惜阿原虽疲乏,但她星眸清亮,顾盼生辉,完全不像会被累垮的模样。倒是跟在她身后监视的那个叫柳薇的女侍者,已是满脸无奈。
景辞走到窗口,看向傅蔓卿所指方向。
“小坏?”
谢岩退后一步,叹道:“可惜……这里并不是京城。她虽忌惮原夫人,原夫人却鞭长莫及,帮不了你。”
老鸨虽不敢无礼,但发现景辞又来了,着实不快。
原本温度正合适的水,放上半个时辰,能合适才有鬼……
阿原很头疼,也开始怀疑当年的自己究竟是怎样的眼光。
谢岩道:“嗯,的确不是因为你。”
景辞眸光一沉,忽推开老鸨逢迎过来的身躯,快步奔上楼去。
但黑衣人的身手显然在她之上,转头看了她一眼,略略踌躇了下,忽折转方向,向另一www.hetushu.com.com边房屋低矮、巷道错综处奔去。
预备洗澡水而已。
谢岩静了片刻,方道:“她是公主,做臣子的不能不顾着君臣尊卑。”
所指之处分明就是街道。街道上尚有行人来往,观其行色,多是青楼或酒馆的常客,并无任何异样。街道的另一边,对面的茶楼和布庄已打烊,屋宇漆黑一片。
连谢岩都这么说,阿原深感压力。
谢岩摇了摇头,转身走了开去,挥手传自己的随侍,“立刻去找大夫,把沁河最好的大夫都找过来!”
谢岩诧异,“你不怨她?”
长乐公主的脸黑了黑,侧头看向女侍,低喝道:“谁预备的这香?”
长乐公主立时叫道:“不用!算了,给我去请大夫,赶紧的!”
阿原道:“公主何出此言?我从不敢拿它和人比,公主为何去和它比?”
谢岩深深看她,“我相信,你没得罪……”
正打量她时,阿原已笑问:“要不要我侍奉公主沐浴更衣?”
景辞跟她冲出两步,然后盯着前面那个飞快消逝于黑夜中的身影,顿住了脚。
阿原噎住,忽然间很想冲上去拍他两巴掌,拍掉他那自信好看的笑容。
阿原听得倒真的诧异了。
随侍应了,说道:“沁河最好的大夫,应该是左知言左公子。不过他如今正有孝在身。”
谢岩凝视着她,眸光闪了又闪,轻笑道:“你是个好姑娘。”
长乐公主很满意这样的效果,向女侍使个眼色,女侍便将一个黑漆托盘送到阿原跟前,上面排了六只玉碗,盛了各色花瓣和香料。
慕北湮道:“你担心什么?担心你的端侯斗不过长乐公主?呸,也是活该!”
阿原眼珠一转,“公主想用晚膳?那我不得不先跟公主回禀一声,我虽会煮饭,但煮出来的东西好不好吃,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目前似乎只有我家小坏没嫌弃我给的东西不好吃。”
小鹿道:“长乐公主过来没说几句话,景典史便顾自走了。李大人说,景典史是查案累着了,旧疾发作,站不住。但我瞧着景典史就是懒得听才拔脚跑了,李大人在帮圆场而已!”
旁边景辞懒懒道:“其实也方便。若你陪她睡,她必定能睡着,而且再不会为难阿原。”
阿原惊得一个趔趄,差点没摔倒在地。
此时她真的万分庆幸她不是那个只会弹琴绣花的原大小姐,不然这会儿只能蹲在墙角抱着瘦瘦小小的自己哭了……
萧潇的剑,便在下一刻架到了左言希脖颈上。
长乐公主道:“那就麻烦原姑娘替我预备沐浴的热水吧!”
这般想着时,她已坦然地笑了笑,“好!公主说怎么着,便怎么着吧!”
长乐公主噎住。
谢岩踌躇片刻,只能叹道:“罢了,先叫那两大夫去给公主诊治吧!”
哭完还得继续给长乐公主预备洗脚水,因为长乐公主说洗得不舒服,想用热水泡泡脚。
可她已奔到近前,便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个黑衣人眉眼清俊,温雅蕴藉,正是贺王养子左言希。
慕北湮家世高贵,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风流公子;谢岩倒像是纨绔子弟中的一道清流,可公主因他为难他的往昔情人,他还真打算置身事外?
阿原持了破尘剑在手,正奋力地追着那个黑衣人。
对原清离这种揉合了天仙与恶魔双重特征的女子来说,名声二字的确太虚无。
贺王赫赫威名在外,他这小贺王爷却是风流名声在外。敢害死贺王之人绝对不简单,若真刻意对付他,他身在明处,必定十分被动。左言希藏起嫁祸之物,却难保对方不会采取下一步行动。如果素日交好的谢岩来了,于他当然十分有利。
放在汴京城,也许傅蔓卿算不得什么。但在沁河县,傅蔓卿绝对青楼第一红人,夜间居然不曾接客,着实是怪事一桩。
阿原一时闹不清他弃剑缘由,谨慎地打量着他,说道:“我不想这样认为。但我们查贺王案刚查到傅蔓卿,就遇到你前来灭口,却不知你想让我们怎样想?”
以她近日下厨煮红豆汤的经验来看,便是让她奔灶下烧水,似乎都没什么问题。
慕北湮那日在花月楼喝了不少酒,但神智还清醒,倒还记得这绢帕。
可惜就是他真能狠下心不理长乐公主,他也找不回那个愿意跟他看星星、看月亮的原大小姐了……
阿原再不晓得她先前和长乐公主闹过怎样的矛盾,但她生性豁达,倒也不在意,老老实实侍立一旁,看长乐公主优雅地用完晚膳,奉上温水让她漱了口。
谢岩沉吟着,“你这是疑心北湮,还是言希?”
景辞道:“对,长花了!”
阿原不知是骇是笑,问道:“到底谁要见我这么个小捕快?我天天在这小地方抓抓小贼而已,不至于得罪什么大人物吧?”
阿原拍拍脑袋,“好吧,她是公主,我是草民,我先去拜见公主吧!小鹿,你去告诉景典史,我回来了,不用担心。”
景辞道:“没做什么,你看刚阿原和那个柳薇都碰了那水,不都好端端的?”
阿原垂着看看自己那身打扮,又看向香气氤氲中的尊贵美人儿,笑问:“公主,要不要唤谢岩进来侍奉?”
长乐公主虽尊贵,也得顾忌原夫人没事在梁帝耳畔吹点枕边风,害她被父皇训斥还是小事和图书,乱点鸳鸯误她终身便是大事了。
那场莫名的伤病后,她忘了太多原先的技能,没法当个琴棋书画样样精妙的风流小姐,但抓贼驯鹰乃至烧火煮饭这样的粗活倒像天生就会。
左言希道:“你跟他并没什么交集,提不提原也不打紧。你只记着别再去招惹阿原就行了。那个小女人,他应该打算留着自己捏死。”
才到门口,却听得里面一声女子惨叫,二人不由大惊。
阿原记挂着景辞有足疾,忙道:“你看下傅蔓卿,我去追凶手。”
左言希看着他的背影,已是无语。
这态度好得凭谁都指摘不出半分错处来。
阿原大是头疼,继续笑道:“公主匆忙找我回来,是不是急着想知道贺王的案子?抑或已经有了眉目,有事吩咐小人去做?”
慕北湮忍不住弯下腰来,又想呕吐。
可偏偏和那些只看脸的世俗男子一般,对她另眼相待,百般爱怜……
萧潇有些讶异,手中的剑依然持得稳当笔直。他问:“你果然背叛皇上,害死了贺王?”
慕北湮咕哝道:“阴魂不散!”
阿原干笑道:“应该,应该……”
言外之意,往日的恩怨,可以别记在她头上了。
景辞淡淡瞥了阿原一眼,已伸手揭开了锅盖,说道:“水开了,你该为公主端洗脚水了!”
小鹿见谢岩有袖手旁观之意,已忍不住问道:“咱们夫人帮不了忙,难道谢公子也不打算帮忙?”
谢岩点头,“若那侍卫所言是真,至少那绢帕是从傅蔓卿的卧房带出去的,的确得设法查清。只是你怎知公主会消停?”
小鹿的卧榻卧具早不知被扔到了哪里,阿原的卧榻还在,已被金紫眩目的帐帷衾被掩得出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景辞盯着灶膛里跳跃的柴火,淡淡道:“有点冷,过来烧点柴火取暖。”
阿原道:“才没有。我倒觉得她怪可怜的,明明又不算胖,晚膳还吃得那么素,那么少,跟个行脚僧似的,何苦呢?再一想阿辞的鸡汤,便觉再怎样千金万金的公主,也顶不上我半分快活!”
长乐公主愠怒,一甩手拍得水花四溅,“你敢坏我名声?以为我是你这样的贱人吗?”
一时阿原和柳薇提了水离开,景辞向谢岩道:“兄长,待会儿公主应该可以消停了,我跟阿原再去一次花月楼。”
左言希轻叹,“你还做梦呢!这方傅蔓卿给你的手绢,在义父遇害时被人丢在义父房中。”
可奇怪的是,左言希偏偏一看到凶案现场的绢帕便断定弟弟是被嫁祸,慕北湮也认为哥哥藏起绢帕暗护自己理所当然,彼此连个因由都没问。
长乐公主睨她,“莫非觉得委屈了你?可我来得匆忙,只带了个粗使的女侍,玩刀弄枪还可以,这些细致活儿全然做不来。若是觉得委屈,也只得请原姑娘委屈一下了!”
他凑上前,在她那又开始蒙上黑灰的面庞亲了一亲。
长乐公主慢慢放下她的茶盅,轻笑道:“等了这么久,本公主饿得很,倒不急着沐浴了。”
见黑衣人跑得越来越远,渐渐与她拉距离,阿原正焦灼时,前方蓦地有剑光闪过,然后是锋刃交击之声。
细腰长腿,乌发如墨,将肌肤映得更是腻白如脂。
阿原又道:“何况公主用茉莉花泡澡,应该知晓茉莉遇热后散发的香气,能刺|激男女欲望吧?再则,公主所用的香料里配了这么重的栴檀……栴檀不仅润泽肌肤,更可使人愉悦。公主与谢岩同来,又用这样的香,不知想我如何理解?”
阿原一边拎起一桶清水倒入铁锅里,一边笑道:“当然想得开!你看,公主皮肤娇嫩,也不知触碰了什么,已经开始起疹子了,可她为了折腾我,偏去泡什么热水澡,却不知热水只会让疹子越来越痒。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嘛!还亏得我聪明,故意从她沐浴所用的香料上挑刺儿,让她早早洗完。不然,夜里疹子越冒越多,又得怪我那屋子不干净了!”
左言希道:“我跟他相识时,他只是我的病人,并不是什么端侯。后来我护送他去汴京后便回了沁河,倒也不晓得他是几时封的侯。关于他的根底,你和谢岩走得近,他应该提醒过你。”
果然不想见阿原,也不想见谢岩了。
左言希熬了两三天没睡,如今趁着公差离开、使臣未到之际抓紧时间养养精神也在情理之中。
所谓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这时夜色黑暗,难以看清贼人样貌,贼人想遁逃也方便。如今若往哪个角落一钻,阿原孤身一人,往哪里找去?
提起景辞,慕北湮又想起那一夜所受的屈辱,简直气不打一处来,冷笑道:“你自然早已知晓,他就是端侯。”
待李斐赶至,她便将发现小馒头那根珠钗,以及靳大德带人进去寻找傅蔓卿绢帕的事一一说了。
老鸨脸色变了几变,迅速从满脸松懈的褶子里拧出一个大大的笑脸,媚声道:“咱们家姑娘的确太娇气,我也瞧着得多捋捋。差爷肯帮捋几下,也是咱们家姑娘的荣幸!正好今晚咱们傅姑娘闲,屋里也干净,就别去衙门了,直接去傅姑娘屋里坐坐可好?整夜捋都行!怎么着都让她把豆子给倒得干干净净!”
长乐公主下颔微抬,冷冷一笑。虽未发一语,那神色分明
m.hetushu•com•com已在道:“小贱人,你莫把我当成白痴!”便如阿原虽是原家大小姐,论起君臣尊卑,也万万无法与长乐公主抗衡。原夫人既是公侯夫人,又与梁帝关系暧昧,才敢在长乐公主到原府堵人时将她逐走。
“……”
阿原问:“我们大人呢?”
长乐公主怪异地盯她一眼,“你拿吃生肉的扁毛畜生跟我比?”
阿原只得将那花瓣、香料一样样地洒入水中,那热气中立时蒸腾出馥郁的芳香,令人闻之欲醉。
阿原笑道:“不妨。她赶了一天路,又折腾这许久,也该累了。待她睡下就好了。”
阿原愣了下,指向自己的鼻子,“我?”
谢岩更无奈,叹道:“原姑娘,真是委屈你了!”
见阿原提着个洗脚的木盆进来,景辞依然眉眼清淡,向谢岩笑了笑,说道:“这还没完了?”
论起这差使,就该精致洁净的小侍儿来做,或者换作者夫妻爱侣间的情趣,也会颇有气氛。
阿原笑道:“我脸上长花了?”
可公主让她委屈下,她当然只能委屈下。
青布素服、满头灰尘的阿原,顿时黯淡失色。
而近来,除了贺王府这事,还有什么能把她扰乱到连表面的若其事都做不到,直接拒绝接客?
女侍慌了,忙答道:“都是挑的公主素日所爱的花儿和香料各带了些过来,委实没细研究过都是什么材料所制……”
景辞道:“嗯,不是小贺王爷,是谁?”
景辞摸了摸自己的脸,“其实皮肤动不动就起疹子,也是一种病症。我小时候不慎碰了柴草,或嗅了某些花香,就会浑身起疹子。后来药吃得多,这症候不知什么时候就没了。”
长乐公主妙眸微微一闪,将她上上下下仔细扫了一眼,才轻轻一笑,“原清离,你跟我装什么小捕快呢?是不是这县衙里有什么特别的男子勾了你的心,特地跑来寻个新鲜?刚一个个看了,好像也没见几个人模狗样的呀!你这口味倒是越发独特了!”
阿原笑道:“公主,如今我是男装打扮,却侍奉公主沐浴,公主倒不怕坏了名声?”
沸腾的水汽扬起,迅速将厨房弥漫得雾气氤氲。景辞似也被水汽模糊了视线,将手在水汽上方扬了几扬,才将锅盖提到一边,向那边一直警惕站着的柳薇说道:“你看清楚了,原姑娘送过去的水很洁净,回头公主的疹子若是变严重,可不能冤了原姑娘。”
不久,便听得里面传来长乐公主的惊叫,然后是怒喝:“原清离,你这屋子以前养跳蚤的吗?看看我这满身的疹子!”
萧潇收回了剑,盯着他道:“那个傅蔓卿刚遇害了?你想说,杀害傅蔓卿的另有其人,你只是赶来的时间不巧?”
她的破尘剑“笃”地磕在老鸨面前的凳子上,问道:“你说,让她自己倒好,还是我们带回衙门里慢慢捋好?谁叫她是贺王世子那晚上不在场的唯一证人呢?按本朝律令,凶手未能确认,相干证人都可囚入狱中,以防诬告或伪证。妈妈准备好送牢饭没有?”
有这样的义子比照着,贺王当然对慕北湮诸多不满,慕北湮自然也对把自己比下去的义兄诸多不满,每每出言挤兑,兄弟二人算不得和睦。
嗯,总算还是有个靠谱的。
“什么意思?”慕北湮问了一句,随即想起阿原于他其实真的只是个陌生人,倒是他和贺王府目前已陷入难测危局。他不由灰了心气,转过话头问道:“你既和谢岩通过书信,应该知道来的使臣是谁吧?谢岩是跟着一起来的?”
长乐公主看着她眼底欣喜跳动的火花,不得不怀疑她当日是不是真的把脑子给摔坏了。
长乐公主“噗”地一笑,“我怕什么?到时当众扒了你衣服,就说你是女人,到时是谁坏了名声?”
按旧例,父母新丧,孝子贤孙应该日夜跪侍于灵前,绝不可躲懒回房休息。只是连着几个日夜不睡,凭他铁打的人也受不住,所以困乏之极时,多有倚墙坐着打盹的,也有悄悄在僻静无人处打个地铺卧上一两个时辰的。
阿原瞧着小鹿神色,才猛然悟出,这位长乐公主便是不时纠缠谢岩,还跑到原府堵人的那位“情敌”。好好的不在宫里当她金枝玉叶的公主,也跑来这小小的沁河县,显然来者不善。
谢岩道:“不妨,去把他也请过来吧!就说是我相请,他会来的。”
阿原第三次走到厨房烧水时,不仅景辞在,连谢岩也在了。
景辞便转头看她,眼底映着火光,璀璨得近乎绚丽。
左言希沉默片刻,答道:“还是不要热闹的好。”
傅蔓卿的面颊滚过大串泪珠,依然漂亮的眼珠绝望而迷惑地转动着,蓦地似想起什么,猛然闪亮起来。她挺身几乎要坐起,直着嗓子叫道:“是他,是他……”
慕北湮双手按于桌面,呼吸急促,“那个试图嫁祸给我的人,自然就是杀害父亲之人。你怕我被人疑心,所以藏起了绢帕?”
半个时辰后,附近的两个大夫已赶到,去请左言希的随侍也回来了,却是空手而返。
阿原笑道:“对,你看我多安分,肯定没得罪过那些大人物。”
可惜谢岩下一句道:“但人家认为你得罪了,你就是得罪了!”
阿原又问小鹿:“景典史呢?”
左言希轻叹道:“我没有杀傅蔓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