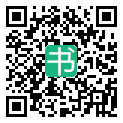第二卷 帐中香
第十六章 飞花留梦轻踏浪
阿原正要问左言希的事,见状便清了清嗓子,斯斯文文地唤道:“那位姑娘,请过来说话,在下有事相询。”
阿原却已有恼意,“你这是明欺我们无法入宫找皇上对质吗?”
井乙摆手道:“不清楚,谢大人身边那位贵小姐,将我们扫了一眼就问那位姓原的捕快哪里去了,李大人说还在查案,那贵小姐便说,竟敢不来迎接,立刻去找来!半个时辰内见不到人,先把李大人打个三十杖……”
这话自然不假。小玉容色出众,天天侍奉左言希,甚得宠爱,但被人奸杀前尚是处|子,足见左言希绝非好色之人。
李斐忙整理衣冠,急问道:“知不知道来的是哪位大人?”
夜间无人服侍,那么左言希后来有没有出去过,等于没有了人证。
阿原左手背在身后,右手手指有力地叩着那些卷宗,说道:“证词应该不假,但慕北湮睡下后难道不能趁着夜深人静再悄悄回来?他有武艺在身,对地形又熟悉,瞒过众人耳目悄悄回来,应该没什么难度吧?左言希虽文弱了些,但住得更近,去而复返向贺王下手,估计也不难。”
若是为了死去的贺王,得罪这位显然深得皇上看重的贵公子,那才是背到家了。
井乙大喜,喘着气冲上来道:“原兄弟,可找着你了!走,赶紧回去!”
也曾怀疑过二人之死有所关联,但贺王近来才到别院静养,小玉又住在左言希的医馆内,相隔甚远。从近侍们的证词来看,小玉心思玲珑,聪明俊秀,颇得靳大德、薛照意等人怜爱,但并未与高高在上的贺王有所交集。若非小玉遇害,只怕贺王根本不晓得府里有这么个叫小玉的侍儿。
他皱眉回忆着,继续道:“夫人和侍儿们当时似乎都吓坏了,应该都没留意那帕子。我想来想去,都觉得是言希公子收起来了。但他并未跟人提起,我也不敢乱说。”
靳大德道:“王爷毕竟只有小王爷这么一点血脉,言希公子素来贤德,必定不想小王爷牵扯进去。”
薛照意失声道:“大人怀疑,是贺王府的内贼所为?”
李斐张了张嘴,没敢说话。
阿原忙注目看时,却见小坏正在前方盘旋不已。
阿原忙问:“出了什么事?”
阿原拈过一颗香丸,细细闻时,便能辨出其中有沉香、藿香、丁香等名贵香料,沉香行气止痛,藿香和胃化湿,丁香舒缓心境,算来都对贺王的伤病有些益处,大约是特地为贺王所制的香料。
阿原问:“你是不是也说过,以后不会再对我说这些刻薄话儿?”
阿原道:“查案当然越快越好……但如果大人有疑虑的话,等个两三天应该也没事吧?”
若左言希在跟前,即便不曾喝茶,茶中异味飘出,也很可能被他察觉。
死的是当朝猛将,位列王侯,正得梁帝器重。杀人的疑犯必在府中,若能分开拷打审问,应该不难找出真凶。
阿原忙跟过去,“你觉得呢?”
他的嗓子哑了,再抹一把眼泪,拉着那侍卫又悄悄退了出去。
那衙差便笑起来,“是……前儿刚回去的谢大人!”
阿原踌躇了许久,说道:“如今贺王府没被盘查、又能让贺王全无防备之心的,只有两个人了。”
李斐终于把景辞、阿原都叫到了一边。
寻常女子提起这刀都吃力,更别说用它将贺王钉在地上;健壮男子倒是能做到,但贺王当时还未睡,再怎么伤病在身,都有武者的警觉在,身手差不到哪里去,怎么可能毫无挣扎便被人刺倒在地?
贺王府上下,包括左言希在内,都认定小玉是因为母亲重病回老家了……
阿原吸了口气。
小馒头道:“公子性情好,王爷向来疼爱得很。可前儿小玉姐姐的事,公子擅自放官差进来查案,王爷那天早上知道,不知怎么就恼了,罚他跪在那里反省,直到王爷从衙门带回靳总管,这才让他回去。晚上则是因为小王爷的事儿,又被罚……后来我们把他扶回来看时,两边膝盖都青了一大片。”
李斐咳了几声,说道:“这个……都难说,难说……我先去喝盅茶。”
这算是……证词?
何况,靳大德完全靠着贺王威势才能作威作福。
左言希抚着他肩,安慰道:“若是有人刻意算计,那夜不下手,早晚也会下手。打起精神,等谢岩来了,再跟他好好商议,如何找出真凶。”
阿原指向他腰间宝剑,说道:“我认得这剑,还有这剑穗。同样的宝剑,同样花纹的剑穗,难道还会有错?”
可贺王与小玉虽无交集,他们中间连结着一个左言希。
她觑着景辞的俊雅面容,忙笑道:“嗯,我以后改,一定会……像一个好好的姑娘家!”
“难道是你该去的地方?”
眼见又遇需下决断的为难之事,他当机立断地踱了开去。
一颗是小玉嘴里含着的,一颗是小馒头珠钗上的。
李斐等日夜辛苦,足足盘查比对了两日,却惊异地发现,似乎别院所有可能杀害贺王的人都排除了嫌疑。
景辞不由转过身站定,阿原红着脸闷头走,差点撞到他怀里。
傅蔓卿……
“一样的?”
阿原道:“你想多了,他没你高,生得也没你好。”
半晌,靳大德急急地低问道:“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萧潇一笑,“我自然留下来听从公子吩咐!”
阿原道:“左言希好像很爱惜小玉,才让我们在贺王府查案,后来被贺王责骂,也是因为小玉的事。这事闹到贺王跟前的当天夜里,贺王便遇害。”
阿原尴尬地揉着鼻子笑道:“我这个原家大小姐,咳……的确算不得好好的姑娘家。我以后不吃红豆了,还成不?”
当然,这话万万不能告诉景www.hetushu.com.com辞。她虽不记得以前是怎么诱得那些俊秀男子神魂颠倒,至少猜得到哪些话景辞更爱听。如今她既然打算收景辞的心,自然得挑景辞喜欢的说给他听。
靳大德叹道:“或许言希公子觉得小王爷情有可原,希望能保全小王爷吧?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那日王爷病中脾气暴躁,前儿更把他们两个都责罚了……”
平时左言希赏众侍儿的钱帛其实并不少,但他不在女色上心,极少会赏这些女孩儿用的饰物,故而小玉和她对各自的珠钗都很珍爱。
景辞翻着案上越来越厚的证词,缓缓道:“也不必盘查,这些侍卫和下人不经意间的证词,基本能证实这两位主子那晚的行踪。慕北湮当晚住于花月楼,整夜未归;左言希跪得双膝红肿,回到医馆后便敷药睡下。”
那段时间,因贺王大怒赶逐,随侍们都有些忐忑,除了部分值守的,其他人聚在一起议论好久才散去,大多可以找到证人,且彼此分开询问时,连讨论小王爷最爱的是哪家的小娘子之类的证言都能对得上。
左言希道:“追查此事,和被视作凶手追查,完全是两回事。”
阿原看时,却是左言希那个叫小馒头的侍儿正提着个食盒走向那边正屋。
倒是小坏已将萧潇视为仇敌,见他离开,撵在后面盘旋唳叫,只是慑于他剑锋之威,到底不敢攻击。
她凝视着景辞俊秀得不似真人的面庞,细细思忖一番,终于恍然大悟,“莫非皇上喜好男风?他……他对不住你?哎,那什么,谁过去没点算不清的烂帐?算了,别放心上,咱们好好过以后的日子便成了……”
阿原已从她发髻间拈出一支小小的珠钗,问道:“这支珠钗哪里来的?漂亮得很。”
阿原被他这么一叫,差点真的扭到腿,连忙站稳身,背着手笑道:“没什么,刚左言希的一个侍儿走去,走得好生怪异,我学着走两步,看看是啥感觉。”
“皇上跟我没关系,早已桥归桥,路归路。只是他自觉欠我罢了……”
阿原爽朗地笑,“没什么,没什么……即便你从前喜好男风也没啥,反正我从前也荒唐……”
景辞很满意,又叮嘱道:“特别要记住,以后万万别再说那些糙老爷们说的脏话。跟没刷过的马桶似的,臭不可闻,难道你自己说着不恶心?”
萧潇向阿原点一点头,阿原还未及问他这般神出鬼没所为何事,萧潇眸光一转,已掠过她看向景辞,向上一礼,“见过公子!”
待井乙带着小馒头到书吏那边复述一遍,看书吏记录下来,让她按了手印,小馒头才觉得似乎哪里不对。
这一回,连阿原都忍不住冷笑了,“不是内贼,难道还真能有刺客飞檐走壁,不惊动一名守卫,便能夺走贺王兵器,刺死贺王?若贺王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我倒还相信。”
阿原各处看了一圈,便潜入贺王的卧房中,再一次仔细察看现场,希望能找到一星半点与小玉或左言希有关的线索。
景辞眸光黯沉下来,“我父母早逝,是舅父将我养育成人。”
靳大德沉吟,“那时都谁去了?”
她明明只是照实说了公子那夜的作息,顺便提起公子送了她一支小珠钗,为何还特地让她按个手印?
慕北湮抬眼,“什么意思?我爹遇害,我肯定得追查到底,什么叫我们卷进去脱了不身?此事我们本就不可能置身事外。”
可惜小玉的珠钗还好好的,她那支珠钗上缀的小珠子却掉了。亏得她手巧,那日捡了颗鎏金银珠,挂上去后浑然一体,再看不出换过珠子的痕迹。
阿原怔了怔,细想当日原大小姐颠倒众生,必定气度高贵,优雅不凡,的确不可能像她这样动不动拔剑拍桌子。
正觉得隐隐有什么快要浮出水面时,却听得外面忽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衙差匆匆奔入,气喘吁吁回禀道:“大人,大人……京中使臣到了!”
想想也是,如景辞这般人物,旁边站着个言行举止比男人还粗俗的女子,的确不般配,太不般配……
景辞一口气上不来,差点噎死,指着她怒道:“你……你才喜好男风!什么乌七八糟的,哪里想出来的?”
她的笑容温柔,好看的眼睛里清清莹莹地倒映着小馒头看痴了的脸。
小馒头忙道:“是我和小钿姐姐侍奉的。”
她愕然抬头时,景辞正无奈地瞅着她,“我说你现在举止跟个男人似的,言语也动不动粗俗不堪……你没觉得哪里不对吗?”
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将一切能预备的都预备好,等使臣过来,能准确无误地陈明案情,再让景辞能赶到前方替他挡掉些风雨,他便无功无过地把这事交给使臣。
因贺王之死,小玉之案不得不暂且靠后,这两日主要在查贺王遇害当晚,府中那些平日让贺王信重的随侍有无可疑迹象。
“装作也回去?”李斐疑惑看她,“你不打算一起去迎接谢大人?”
又或者,根本就是冲着她来的?
阿原却暗自纳闷,待无人在跟前时,便悄声问景辞:“喂,你跟皇上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为何封你为端侯,还特地跑郊外去看你?”
她嗅了几嗅,走到了床榻边,便觉香气更深了些。
靳大德喝道:“心惊胆战也得继续憋着!回头使臣再来排查讯问,你一定要当这事没发生过,听到没有?等回头有机会,我会再细问言希公子是怎么回事。”
景辞道:“他又不能预知贺王之死,来沁河自然有别的事,我留他下来做什么?给你欣赏他高挑身段、俊秀脸蛋?”
他当然没有滚,返身离去的背影清健挺拔得像和-图-书株小白杨,令阿原不觉又多看了几眼。
阿原看那金鸭香炉中的香料,早已燃尽凉透,隔了这么几日,不可能还这般芳香。
景辞还未回答,萧潇已问向她:“哪晚?”
侍卫低叫道:“可小王爷……小王爷很可能是凶手呀!言希公子也不理吗?”
景辞的笑便有些发苦,低低道:“我并不需要他看重。不过……还是赶紧查案吧!”
李斐哆嗦了下,看了眼阿原,问道:“景典史是不是去花月楼了?我绕个弯儿,喊他一起回去迎接谢大人吧!”
阿原吸了口气,“好威风的贵小姐!这是哪尊大佛呀?谢大人也不管?”
李斐道:“这个好办,我们就请小贺王爷和左公子配合下,最近封闭别院门户,不许任何人进出。能得贺王信任的侍卫也先一一筛查,不管有无疑点,都派人昼夜守着,不让四处走动就是了。”
抬眼看时,却见帐中以银链悬着一枚银制石榴纹镂空银球,下方还用珍珠、琥珀做了小小的流苏坠子,做工十分精湛。
阿原瞧他面色很不好看,似乎有些羞怒;再听他说什么桥归桥路归路,倒似有一刀两断的意思。
小馒头呆了呆,慌忙奔了过来,满脸堆笑问道:“二位爷有何吩咐?”
李斐惊疑不已,“小玉临死时把这珠子含在口中,到底是什么意思?想告诉我们此事与左言希有关,还是想告诉左言希什么事?”
阿原灵光一闪,“假如他有所顾忌,不想让人知道小玉被杀呢?”
如今瞧着知县带着公差们尽数撤出,一方面暂时松了口气,另一方面不由对朝中使臣的到来捏着把冷汗。
景辞抬手抚额,“好像见过两面。”
井乙怪异看了眼阿原,高喝道:“兀那小娘们,官府办案,大爷有事要问,还不滚过来?”
这样护短护得不分青红皂白的好主子,他就是打着灯笼也没地儿找去,又怎会相害?
左言希伸手搭住他脉门,眼底焦灼,声音却甚是柔和:“我知道你为义父之死难过,但慕家就你一根独苗,你还是得保重自己,才能承继慕家香火,也才能配合使臣,查出真凶!”
萧潇便笑了笑,“那必定不是我。原姑娘,你认错人了!”
阿原忙道:“你腿脚不方便,还是我去吧!”
阿原再一想,左言希与景辞如此亲近,不好女色不假,不好色则未必……
可如果是贺王信重之人,岂会是平平之辈?若是背后有人,更是伸伸手指头便能将他这小知县碾个死无全尸。
他摸着脖子,差点没哭出来。
景辞沉默,然后道:“若是拖得久了,凶犯更有机会销毁罪证,掩饰罪行,甚至可能潜逃他处。”
阿原虽藏身得快,但也吃不准有没有被左言希发现,又听出是井乙等人正在寻她,只得先奔过去,问道:“什么事?”
左言希已从怀中取出一方绢帕递了过去,问道:“你还认得这个吗?”
小馒头偷眼觑她,正见她模样俊美,似比自家公子还要秀丽几分,不觉脸颊通红,虽缩了缩脖子,竟不曾躲闪,连看她握剑的姿态也觉得格外气势昂扬,再不觉得害怕。
总之就是拖也要拖到使臣到来。
侍卫惶恐地看向靳大德,“可言希公子为什么不将这事说出来?”
待说完他才想起,阿原其实也是个小娘们,这两日还和景辞走得亲近,知县大人似乎颇有撮合之意……
萧潇点头,“正是!”
然后,在小玉之死被揭穿的第二天,贺王死于非命……
于是,少了县衙公差四处巡睃的目光,很多人抓住了这短暂的空白时段,卸下紧绷的面具,找素日交好的同僚或友人吐一吐这些日子想说却不敢说、不便说的话,或做些想做却不敢做、不便做的事。
“哦!”阿原看着珠钗下方缀的镂空鸳鸯鎏金小银珠,笑容更是温和,“借我把玩几日可好?”
景辞漫不经心道:“这事跟你前来沁河的目的有关?”
想来这香囊也是那位薛夫人所制,虽悬在帐中,但贺王心情不好,自然没那心情赏香,也便没人去点燃这香了。
靳大德跺脚道:“叫我怎么管?如今那帕子根本找不到,口说无凭,到时说你诬陷主人,以杀人罪反坐,掉脑袋的就成了我们了!何况这事也说不准。或许并不是小王爷做的,或许小王爷只是一时糊涂,言希公子又明摆着在包庇小王爷,便是最终能查到证据,难道将王爷亲子义子一起断送,日后连个清明上坟的后人都没有?”
嗯,必须是景辞这样高冷好看偏偏有着好厨艺好武艺的男人!
李斐仔细听着他们交谈,闻言已不由屏住呼吸,悄悄向后退了一步。
李斐想起贺王从衙门带人时的威霸蛮狠,摸头道:“那也不对呀!贺王想弄死一个自家的小侍儿,不比捏死蚂蚁麻烦吧?犯得着这样大动干戈杀人抛尸?”
“萧潇!”
阿原完全不晓得萧潇所传达的梁帝口中的“她”是谁,但梁帝所探望的那位公子是谁,连李斐都猜到了。
萧潇笑了笑,声音更低了些,“那晚我随侍皇上去探望一位公子,但那公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京了。皇上便在那公子的卧房坐了一夜,我等便在廊下站了一夜,听了一夜雨。那公子府上的人都可做证。皇上离开前,还跟侍奉那公子的姑姑说,‘她没说错,他果然去沁河了。赶紧找他去吧!’那姑姑如今应该已到沁河,也可为我作证。”
唯一的解释,杀贺王之人乃是他所信任的熟人,他在毫无防备之下,遭受致命一击,当场死亡。
她抬手,慢慢搭上小馒头黑鸦鸦的发髻,在其上摩挲着。
阿原道:“我又去小玉卧房看过了,并未发现一模一样的小珠钗和*图*书。小玉的那支,应该是在遇害时遗失了。”
除了尸体被移走,卧室基本保持着原状。血腥味已淡了许多,却依然丝丝缕缕的清香在屋中萦缠。
阿原想起谢岩清风朗月般的气度,颇有些心向往之,随即想起景辞来,忙道:“好。大人这便召集大家一起去迎接谢大人吧!我便装作也回去了吧!”
好在,那证据尚与第三人有关。
景辞道:“不用了,你滚远点就好。越远越好。”
贺王已装入棺椁,慕北湮、左言希除了配合查案,每日都在灵堂守着。只是案子未破,使臣未至,暂未通知京中亲友,如今只有他们和数名姬妾守着,并请了两名高僧念颂经文。
景辞便问:“我查案,那你呢?”
景辞怔了怔,淡漠地转过脸,说道:“我去花月楼,查证下慕北湮那夜行踪。”
“嗯,公子一起买的,给了我们一人一支。”
须知近来梁帝身体也不大好,有什么事大可把人叫进宫去吩咐,岂有纾尊降贵自己跑去看望的道理?端侯府又不在汴京城内,沿途有些地段还颇是荒凉,才有原家大小姐遭遇劫杀之事。
他拍开她的手,快步走了开去。
更耐人寻味的是,景辞不在,梁帝也不生气,安安静静地待在他的卧房,一待就是一整夜……
井乙笑道:“这些小娘们有什么好学的?”
阿原愈加纳闷,挠头道:“怎样的来头连谢岩都退避三舍?”
“那皇上……”
“如今怎么办?先填好尸格,将贺王入棺,然后咱们一边慢慢调查,一边等着朝廷使臣到来,可好?此事不比先前朱蚀的案子,顶多两三天,京中使臣必定赶到。”
阿原蓦地猜到来人是谁,正要奔出去时,却见小坏鸣叫着已经飞了过来,几乎同时,另一道玄黑人影已逾墙而入,其迅捷居然不下于空中的小坏。
阿原掰了掰手指,“应该是十三吧!那日下了一整夜的雨。”
萧潇点头,“兹事体大,未必是私仇。为皇上计,希望公子能协助沁河知县尽快破案,不要等待朝中使臣,以免贻误时机。”
尤其谢岩已知晓她是原家小姐,他身边那位贵小姐多半也已知晓她身份,居然没把她放在眼里?
景辞有些意外,将他细一打量,才认了出来,“是你?你就是萧潇?”
话未了,慕北湮已弯下腰来,痛苦呕吐。
“嗯?他有病,平白封你为侯?”阿原挠头,“你到底是怎样的身世?往日必定告诉过我吧?可惜如今我全忘了,连你父母是谁,哪里人氏都不晓得……”
小馒头见她双眼发亮,有些讶异,又有些得意,说道:“是我们公子给我的。”
正沉吟时,忽听得屋外有细微的脚步声,阿原忙收好香囊,纵身跃起,握住大床上方顶盖支架,藏于帐帷顶部,悄悄向下观望。
左言希道:“谢岩资历不够,但很得皇上器重,若能从中斡旋,至少可以安排与贺王府、谢家亲近的大臣前来。我就怕来的是不相干的人,你我卷进去后便脱不了身,才特地给谢岩寄了书信,请他尽量帮忙。”
“小玉姐姐也有一支。”
景辞心神不属,开始没留意她说什么,待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劲,才留意看向她时,她正很男子气地一手叉着腰,一手拍着他的肩以示安抚……
若是簪在发际,尸体泡在水中被冲刷了那么久,自然是找不到了。
正说着时,忽听头顶传来鹰唳之声,急促而尖厉,分明有警戒之意。
李斐哈着腰道:“好!好!”
有一日她和小玉随她家公子路过集市,公子不知为何忽然想着拐到旁边铺子里买了一对珠钗,也不晓得打算送给哪位贵家小姐。她和小玉不过多往这小珠钗看了两眼,公子便令将这小珠钗也包了两支,赏给她们。
“当时是什么时辰?左公子入睡又是什么时辰?”
慕北湮看向他,“你怎么知道来的是谢岩?他回京尚有别的事,何况资历尚浅,皇上怎会让他来?”
“那他入睡后有没有人在他屋内听候使唤?”
根据死亡时间推测,贺王应该在左言希、靳大德等离开不久便已遇害。
慕北湮不解,“被视作凶手……我?还是你?”
阿原沉吟之际,目光扫过小馒头低垂的头,不觉定住。
景辞却已肯定地答他道:“贺王昨夜遇害,死于他自己的刀下,目测应该是熟人所为。”
景辞道:“我觉得你背着手一点不像好好的姑娘家。”
阅人无数,青出于蓝,红豆都快凑成百了,她自然算不得好好的姑娘家。不过她原来怎样的,景辞应该一清二楚吧?当日婚约,分明是两厢情愿的。
阿原甩着被他拍疼的手,鼓起腮瞪他的背影,“弄错了?好吧,错就错吧……不过我怎会喜好男风呢?我只喜欢男人!”
小知县不敢拿贺王府这些人怎样,使臣奉皇命而来,一切说不准了。稍有疑心,好不好先打上几十杖,丢入狱中百般刑讯,能不能活着出来就难说了。
那侍卫摇头,“我不会瞧错。服侍更衣的侍女是最先发现王爷遇刺的,惊得奔出来时第一个便遇上我。我一边让她们通知言希公子和总管,一边进来看时,就看到一块绢帕飘在门槛内,当时还特地弯腰瞧了瞧,上面分明绣着一样的百合花,还有个‘傅’字。我想着言希公子或你老人家过来必会处置,所以也不敢乱动,谁知后来就不见了!”
小馒头不由应道:“好!”
萧潇声音低了一低,“当时我正随侍皇上身侧,皇上便可证明!”
“可这是弑父!弑父呀!”侍卫几乎要哭出来,“这事憋在我心里几天,我看着那些个典史捕快的就心惊胆战……”
景辞神情阴郁下来,大约自觉已经解www.hetushu.com.com释得够细致,转身便要走开。
二人紧张地四下寻找着什么,却又顾忌着被人察觉,并不敢胡乱翻动。
他忽然一拍书案,“莫非小玉之死与贺王有关?贺王不是急着想带走靳大德,而是不想我们查小玉的案子?”
萧潇也不在意,问阿原道:“是不是贺王出事了?”
阿原不由瞪向景辞,“你怎跟他说这个?你可知他很可能就是那晚在涵秋坡想杀我的那名杀手?”
小馒头犹豫,“这……”
见他走得不见人影,阿原方问:“你怎不留他下来帮忙?”
李斐摸向帽子的手顿了顿,“谢大人?谢岩?”
小小的沁河县衙,从知县到捕役,对威名赫赫的贺王府本该毫无威慑力。但基于贺王被认定是内贼所杀,府中之人各自忐忑,看旁人固然疑心重重,也担忧自己被人疑心,这两日无不谨小慎微,对着衙里的小公差们也不敢有所失礼。
偏也就这么巧,灵鹤髓一案告破没几天,知夏姑姑就跑沁河找他来了。
阿原笑道:“刚才你所说的,连同这个珠钗的事,那边的书吏都会记录下来,你去按个指印,若到时我不还你,你让你家公子拿着那证词找我算帐好了!他跟我们典史大人熟着呢!”
景辞便问阿原,“你觉得呢?”
左言希的医术,旁人不知,景辞却是最清楚不过。
他们都看向了景辞。
谢岩年轻尚轻,只在吏部挂着闲职,但到底是梁帝心腹,查朱蚀那类闲散宗亲的案子资历算是够了,但如今遇害的是贺王,威名赫赫、手握兵权的贺王……
景辞有些头疼。他看着左、慕等人,轻叹道:“那么,这府里素日得贺王信重的健壮男子,大约都难逃嫌疑。”
阿原短短的数月记忆里,并未见过这样的银球,却晓得这银球实际上是个银质香囊。这种香囊被称作帐中香炉,乃是在镂空银球内安置两个同心机环,环内置一小小圆钵,用以盛放香料。因其设置机巧,不论在帐中如何转动,哪怕跌落在衾被间滚动,圆钵都会保持着水平,球内燃着的香料便不会洒到衾褥间。
贺王死得憋屈,死后又没人供他打骂砍杀,想更不痛快。即便这经文无法超度亡魂,让他平心静气、少些怒意也是好的。
很不高兴……
景辞果然释怀不少,眉眼也舒展开来。他看向李斐,轻笑道:“大人,我们还是继续查案吧!”
阿原怔了怔,“什么样的年轻人?”
萧潇明显有些震惊,但唇角很快弯过柔和笑弧,“可那不会是我。我当时还在京城,不可能分身出现在涵秋坡。”
小馒头看着她手中的破尘剑,战战兢兢道:“大约过了亥初才回来的吧!我等听说左公子又被罚了,都不放心,已经去看了几次,大致时间应该没错。公子回来后应该很累,敷完药就睡了。”
贺王活得粗疏,贺王府两名公子却活得各有个性。慕北湮喜欢精致的美人儿,而左言希自己便活得很精致,小馒头另外为他预备饮食便不希奇。
李斐等临时用来处理案情的那间屋子里,阿原正盯着眼前的两颗珠子。
“可……如果真是小王爷杀了王爷,靳总管你也不管吗?”
门被小心推开,却是靳大德带着贺王的一名侍卫悄悄蹩了进来。
那些受贺王信重的随从大多跟随贺王出生入死过,平时没有一个是好相与的,李斐亲见他们在县衙打人伤人跟打稻谷劈柴火般寻常,原没那个胆子去细查,但如今他一躬腰,顶着这事的成了景辞,便没有太大顾忌了。
阿原警惕地看向他,“你问这个做什么?”
慕北湮,贺王世子;左言希,贺王义子,且是景辞好友。
景辞的面色不大好看,眼底也微微地泛红。半晌,他轻轻撇开话题,“你为贺王之死而来?”
李斐也由不得沉吟道:“贺王虽霸道,但那日一早亲自冲到县衙强行把靳大德带走,本官一直觉得蹊跷……靳大德再怎么受器重,到底是贺王府的下人,犯得着这么着急?随后为这事儿大动肝火,罚了干儿子又打亲儿子,怎么看都像小题大作……”
陈设奢华的卧房里,慕北湮踉跄走入,扑到桌上抓过茶壶,仰头便灌。
阿原叹道:“他不想我们查下去,罚了干的打亲的,难道小玉之死跟他有关?”
慕北湮神思恍惚,似没怎么注意,左言希却转头看了一眼,才继续向前走。
阿原跃身跳下,站在那时一时懵住。
若是使臣主导破案之事,不管真凶是谁都怨不到他李斐头上,他就能平安无事继续当他的县太爷了……
阿原已惊住,“你们认识?”
井乙见她犹疑,已一把扯过她便飞奔出去,叫道:“小祖宗,半个时辰快到了,赶紧回衙吧!再晚一刻,便是三十杖没打下来,李大人都该吓出病了!”
萧潇清秀的面庞顿时窘得泛红,却依然清朗答道:“是,公子!”
阿原默默思量着自己从前在原府时该是怎样的言行,顺便扭着腰向前走了几步,忽听得身后井乙叫道:“原兄弟,你腿怎么了?扭伤了吗?”
正踌躇着要不要奔去看时,外面已阍者奔来,仓皇说道:“
和图书外面有个年轻人,求见原捕快。”侍卫道:“先是薛夫人、赵夫人带着侍儿进去哭叫,再就是言希公子过来,将我们都赶出屋,又命赶紧报官。再后来你老人家也到了,都不曾有机会进来。我出门时,那绢帕好像就不见了。”
贺王很可能是慕北湮所害?左言希有证据在手,却暗中维护?
李斐飞快权衡着其中利害关系,满脸赘肉已堆得跟怒放的花儿一般,急急答道:“成,成!为皇上做事,本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好能赶在使臣来到前破案,皇上必对公子更加看重。”
她弯腰捡起地上那柄五十八斤重的陌刀,挥舞了两下,也觉有些吃力。
阿原打开银香囊,果见里面有雪亮的银钵,中间盛着满满的香丸,虽未点燃,兀自香气馥郁,正和屋中所飘的淡淡清香气味一致。
阿原虽愤愤,但景辞显然没打算跟她讨论此事,转身便坐了肩舆离开别院。
一模一样的镂空银珠,连鸳鸯相对的姿势都全无二致。
阿原闪身从窗外跃出,依然关好门窗,正要潜出别院,赶到花月楼找傅蔓卿查证,忽见左言希拉着慕北湮正从灵堂出来,正想着要不要跟上去看看时,忽听不远处一叠声有人在高唤道:“原捕快!原捕快!快出来,有急事,急事!”
事发当天,慕北湮与贺王激烈争吵,甚至动上了手;左言希无辜受累,同样被打骂罚跪。虽是父子,可算来都有矛盾。
他慢慢抬手抚了抚额,问道:“你刚……在说什么?”
目测其方位,其目标应该在别院正门附近。
靳大德叹道:“这么看着,多半是他收起来了。据你所说,那天不只你们两人,言希公子也在花月楼,亲眼看到小王爷从傅蔓卿手里拿走了这方帕子。你都认出来了,言希公子那么细致的人,怎会认不出?”
萧潇微笑,“三面。”
景辞道:“不用,那地儿不是你该去的地方。你留在这里,去找言希的侍儿谈谈吧!”
左言希紧跟着走进来,伸手便抢茶壶,急急说道:“别喝!这两天咱们都没回房,也不知这茶水放了多少天了……”
阿原问:“谁能证明?”
景辞显然不愿意多提此事,只淡淡道:“没什么关系。”
景辞懒懒看他一眼,并不答话。
贺王意外遇害,左言希明显支持官府查案,世子慕北湮惊痛父亲之死,尚未回过神来,何况已知晓景辞身份非同寻常,遂也不曾对小小沁河知县敢在贺王府兴师动众排查凶手提出异议。贺王府声势再暄赫,此时那些武将没了凭恃,倒也敛了气焰,乖乖配合一次次的调查盘问,赶紧先洗清自己嫌疑要紧。
“他就给过你一个人?”
萧潇有些犹疑,“我不确定。其实皇上一心盼公子好生养病,应该不愿公子卷入这些事。但我着实放心不下,怕误了皇上的事,才希望公子帮忙。”
他愧悔交加,这两日守着父亲棺椁,几乎不吃不喝。刚左言希再三相劝,才浑浑噩噩随他回房更衣。
“我没事……”慕北湮甩开他的手,蹲在地上,掩着这几日蓦地清瘦下来的面庞,哽咽道:“都怪我,怪我……如果不是我激怒他,他不至于那样大发雷霆,把侍从姬妾都赶走,给了凶手可趁之机!”
景辞皱眉瞥阿原一眼,也转身走向门外。
但衙差肯定地答道:“是谢大人!在咱们衙门里住了好几日,我怎会认错?这回还带着女眷呢,看着也是个贵家小姐,长得可好看了!不过谢大人的脸色不大好,看起来很不高兴。”
阿原疑惑,“什么叫又被罚了?左言希不是挺得贺王欢心嘛,怎么老被罚?”
小馒头仿佛飘来一眼,也不知是没听清,还是装作没听清,沿着回廓径自往前走着。
他忽然间万分庆幸,昨天被贺王羞辱后,没能有机会在景辞身上找补。
小馒头连忙摇头,“我们公子向来洁身自爱,夜间并不要侍婢入内服侍。”
阿原微微一笑,“我想看看衙门里的人都撤走后,这贺王府的人都会是什么反应。”
井乙摇头,“不知是什么人……谢大人脸色很不好,低声跟我们说,还不去找?我们就赶紧骑马奔过来了……”
阿原自然明白李斐心思。但她对朝中之事一无所知,印象里端侯似乎也是个不管事的,虽不知为何封了候爵,却不晓得够不够能耐担下贺王这档子事。
李斐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只是萧潇性情安静却明澈,言语温和又不失爽利,何况又有种少年人萧肃磊落的气度在,怎么看都比清冷孤傲的景辞顺眼,无怪当日的原清离迷得七荤八素,差点女霸王硬上弓。
幸亏没得罪他,幸亏还一起看秘戏图的好同僚,幸亏他们阿原生得俊俏,便是有慢待之处,到时将阿原往他怀里一推,再没解决不了的事儿……
阍者慌忙地比划着,“二十上下的年轻人,这么高,瘦瘦的,长得倒还好看,但拿着剑,很凶。我只说了句今日府中有事,他就把剑搁我脖子上了……”
因前日之事,李斐对靳大德颇有成见,但贺王爱姬薛照意因贺王大怒,在离开后即与靳大德商议,想在第二日设法将贺王世子劝回来,免得贺王气坏了身子。以薛照意和她的侍女兰冰的证词,靳大德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阿原也深感她办案时着实不便进入她原家大小姐的角色,一抬右脚重重踏在旁边青砖砌成的花坛上,手中破尘剑戳着砖面,方笑问道:“贺王遇害那晚,是你侍奉左公子洗漱睡觉的?”
他咳一声,忙向前一指,“是不是那个侍儿?”
思忖之际,猛看到手边的食盒,想着耽搁这么久,饭菜都快凉了,公子也该饿着了,忙丢开那些疑虑,飞奔着去送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