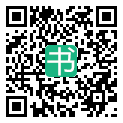第七章 意外
宁小宇赶忙挥了挥筷子,制止说:“在吃饭,在吃饭。”
“好吧,谢谢老师。”他说。
通过时有时无的观察,我发现周围每个人身上都萦绕着一种奇妙的孤独。这种孤独很可爱,充满了狡黠,是一种于角落处种小蘑菇般的没落。
又是盛夏酷暑。热浪阵阵,林木繁森,蜀都实验阳光炽烈。初三一同学试图自杀。
“可怕?”
“我做人失败?”章子腾不屑地笑了笑,指向旁边的芋头,“他呢?他怎么不自杀?”
学校举行了哀悼仪式。
机器的轰鸣声平空响起,整个教室都好像一个巨大的造粪车间。
但,在枯燥的学习生活中,浪漫小插曲的结尾往往是这样——“鲁美嘉来了,鲁美嘉来了!”小胖一溜烟跑进来,沉浸在想象里的同学们一哄而散,章子腾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了座位上,不一会儿,开始执笔做题,表情专注而虔诚。动作之连贯,姿势之娴熟,神态之老到,让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人才不做团支书,还有谁能堪此任!飘扬的团旗映着他俊朗的脸庞,那炯炯的目光似乎在向所有人宣告,优秀的精神之光将在团员中间代代相承。
故事大致是这样的——“我”少不更事,一个人只身前往东京开始新的生活。内心强烈的矛盾感、无奈感似乎在相遇沉静雅美的直子与活泼动人的绿子两位女生后得到了某种安置。在因为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结识到的贵公子永泽、同寝室学地理的“敢死队”之间,生活铺展开来,交错环绕,迷茫不断,也模模糊糊地追求不断。这情况一直延续,直至于后来直子精神难以控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身与周遭的世界种种复杂的关系,心中悲凉不已。
全班晕堂。
“私奔,私奔啊……!”
“我们的教学楼是坚固的!”返校集会上,姬大校长郑重承诺,“专家们都很赞叹,希望你们放心,安全可以保证。”
他总是低头算题的姿势,凝固为一尊雕塑。除了学习,什么都进入不了他的视野,什么都得不到他的回应。看起来,他仿佛要把人心不息的力量化作永恒。
翻开书,是温润如珠的诗歌般的语言,清新飘逸的梦呓般的叙述,孤独得可以穿透夜空的声音,洗尽铅华的如水一般的青春情感……
“不能以捐款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爱心。”我表明我的观点,是辩驳,更像是希望。
“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他们非常年轻。坐在开往重庆的火车上,把行李箱顿在脚边,手放在膝上,目光空洞地看着窗外流动的黄昏。雾霭和夜色笼罩着山野,远处山麓下点缀着零星的房屋。
宁小宇淡淡地看了我一眼,不为我的话语所动。她不急不慢地从包里掏出一包湿纸巾,取出一张,撩开刘海儿,轻轻擦拭额前的汗水。
我不希望宁小宇被开除。虽然我知道,即使被开除了,她爸想方设法也会使她前途光明,但我不愿失去这么一个朋友。像世界温暖的楔口。
“废话。所有阳光都落在他身上,我们就一团漆黑了。”
纯粹的是我们的感伤,杂糅的是捐款的种种。
“你有窥探别人隐私的癖好。”
她关注的东西总是偏的。大约这就是她只能当生活老师的原因。
“李松?没什么好说的。”芋头的回答更加直接。
“不管什么原因,他们的确是私奔了。”艾利亚压低了声音,环视了一周,重重地说出了“私奔”两个字。原先叽叽喳喳犹若雾里看花的众人仿佛一下纠住了整件事情的灵魂,先是一阵寒冷的欷歔,少顷,爆发出撼天动地的欢呼。
学校依然举行了期中考试。
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我最近在看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本《百年孤独》。书里,村民染上了一种叫“失眠症”的孤独病,患病者了无睡意,记忆衰退,每个人都睁大了惊恐的眼,独自面对一个个漫漫长夜。
“你非要问我家是怎样的?我妈就是个家庭妇女,我爸就是个生意人。”芋头无奈地说,“只懂得生意。生意以外的事一概不知。对我,他只知道成绩。他相信鲁老,相信商机,相信钱有力量。”
他们这样解释:“反正都地震了。”
正说着,宿舍门嘎吱一声,她石化在那里——结果进来的是宁小宇。
偏偏宁小宇就喜欢这样的回答。她把艾利亚当作知己,当作唯一理解她的人。
“你家到底是做什么的?”我问。
我考到了全班第六名。总算是进步了。苏明理是第十名。李松第一。芋头稳坐最后一把交椅。
这两天,不见宁小宇,也不见柯冉,对我而言,某一方和_图_书坍塌了。
我想了想,计算这个月必要的开支,捐了两百。
芋头回过头去,又转过头来,意味深长地补充道:“也有可以说的。比如,我现在知道的东西,李松可能永远不会懂。”
“惨了,惨了,我和柯冉被我爸抓到了!”
“我知道了。”鲁老点了点头,对她的坦白表示肯定,“还有吗?你们再没联系过吗?”
“行,你坐下吧。终归来说,这是孩子气的行为。”
“浅薄?你到底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那你怎么说?说起人生目标就要挨骂?”
熬夜读完此书,心中冲荡着一股巨大的感情激流。既不悲哀弥漫,也不愉悦非常。只是深深沉潜于那绘梦之文,又被书中浓烈的时代气息所感染。书中那种仿佛英雄末路般的不屈与悲凉超越了我所有的时间观。一种可能性在膨胀。——即使在这个生之维艰的世界上,人仍然可以拥有一片精神森林。
洗漱,铺床,熄灯。一切有序而又无聊地进行。
这让我想起一部革命著作,标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转念又想,何不来个画蛇添足,狗尾续貂,改之为:《钢铁是怎样炼成废铁的》。
“小型造粪机……”艾利亚喃喃。
“都快气疯了,”宁小宇说,“但他没有进来。”
我一低头,看到雪白地毯上华贵的金色花纹。这种炫目的美丽卷集成了一个旋涡,快要将我吞噬。
实际上,这本书所叙述的故事从头到尾都与我朝夕相处且熟悉非凡的一切毫不相关。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在中国,时间也是很久以前。再而言之,我的生活与其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奔流涌动在我内心的情感又是什么?——我想了很久,终于才明白,这本书真正撼动我的,与我的心产生了强烈的共振的,很遥远却又很巨大的,是一种名为“孤独”的旋律。
私奔的事,换来了记过处分。已然万幸。但她和柯冉仍旧我行我素,好像这是为感情必须付出的代价。
“好了,”说完,生物老师将粉笔潇洒地丢入了盒子里,拍了拍手,“剩下的时间,你们就自生自灭吧。”
我还是那句话,没事,没事。我很想说点什么有道理的,但思前想后,也只有这么一句。
艾利亚瞪大了眼睛,瞳人黑亮黑亮的。
“什么发现?”
我们读着宣传栏里摘抄的只言片语,苏明理说:“嘿,这同学还挺有文采。”
“空虚。无尽的空虚……整个世界忽然变得细微,我的心缓慢,平静,然而却悲哀。城市的声音轻轻流过……”
“不清楚……”生活老师心不在焉,一下又很激动,指着一边,“哎!苏明理,你的柜子又变乱了!”
“谁的妈妈?”
接近期末,又逢上地理生物会考。我们学习太累了,走到哪里都能闻到一股因为用脑过度而产生的焦煳味儿。
“我对你的遭遇表示深深的同情,”我说,“不过我理解你爸妈。”
他一时非常发窘,就像在情绪激昂时被人挠了痒痒一样。于是,他回过头去,看了看黑板上的讲题——生物界的物质循环。灵感呼啦一下掠过他的心上。他清了清嗓子,庄严地训斥道:
“是挺恶心。但仔细想来,居然觉得言之有理!”艾利亚一个激灵,睁大了黑黑的眼。
下课后,苏明理转过来,一脸沉痛地对我说:“我现在越来越无法和我妈他们交流了。”
余震时不时地发生,起初还有些心惊,次数太频繁,大家也觉得无所谓了。
“算了。”章子腾不想争了,一下又很困惑似的,“搞什么搞?全世界集体自杀?”
章子腾听到消息则连连叹息。
“压力太大了。不是老师,也不是父母,我只是厌恶于自己的渺小,不论如何努力,也进不了年级前十……”她修书一封,吞下母亲为失眠而买下的安眠药,躺在床上,想一了百了。
“没准会被开除。他俩都会。”艾利亚说,“私奔啊,情节太严重了。”听起来倒不像是担心。
“去!我只是对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感兴趣罢了。跟我说说你家吧。”
“什么?空虚?”我诧异地看着章子腾,怀疑自己的耳朵。
事实上那天我并没有看到他俩。我也是听说的。他们一回来就进了老师办公室。宁小宇的爸爸来了,柯冉的爸爸也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并不是坐火车去的,他们也没有怀揣这样的心情。他们包了一辆出租,一路上谈天说地。一天在公园里晃,一天在游乐场玩,直到索然无味。
柯冉果然大方,两千元钱眼睛都不眨。芋头的一千五,放进捐款箱就走了。和-图-书章子腾的一千则捐得百转千回,让人想起慢处理的镜头。他生来就是为了表演的。
我几乎惊叫起来,想他们一直视校规校纪为一纸空文,视陈腐说教为一滩烂泥,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敢在一起洗澡。
这个时期,迈克鲁斯的英语课每况愈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对英语越来越缺乏热情。迈克鲁斯手舞足蹈,引不起我们一点学习兴趣。他在讲台上焦躁地来回踱步,寻思是不是地震给了我们太大刺|激的缘故,差点儿要给我们做心理辅导。
“也不仅仅是这样。他们可能早就想好了,毕竟,学校和家长都不会认可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想以这种方式表示反抗。”
苏明理搜肠刮肚,冒着日日吃榨菜的风险,捐了一百。交钱的时候,她不无悲戚地说:“我爸知道了会把我吃了……厂里捐款,他只捐了五十。”
宁小宇继续说:“那时躺在浴缸里,看着天花板上复古的雕花,一条细纹若隐若现。那么多天,我一直很恐惧,但那一刻忽然觉得,即使它突然塌下来也无所谓了,只要柯冉在我身边。我问他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他说,那样会死得很漂亮。耳边是哗哗的流水,整个世界静谧得好像只有这水声。那瞬间,地震成了很遥远的东西,什么学校啊,同学啊,老师啊,都变得很远很远……我们还想唱歌来着。谁知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我爸的声音,他大喊,‘宁小宇,你在跟谁说话!’听到这个,我们都傻了,天知道我爸怎么突然回家了,他本来是要去公司安排工作的。”
艾利亚面露惊奇,带着虚假的羡慕。
“光是因为这个还很正常,关键是,他们说着说着我的成绩,就说起我的人生目标来了。”
宁小宇抬了抬眼,没有说话。她径直走向里间,看样子特别烦躁。我们只好作罢。
其中亦庄亦谐的幽默笔调,冷静自制的抒情风格,时不时隐入意识深处的深刻哲理,让人耳目一新的行文,无一不给我留下了清晰得不可思议的感觉。阅读起来,轻松恬淡,但又不失一种足以震撼人的,悲哀的底蕴。它敲开了我心中本来打算彻底紧闭的一扇门。每一个字都在说:喂!开门看看,我为什么在这儿,好好寻思一下,你到底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
“昨天,在我家。”宁小宇先前跑得太急,现在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我们一起洗澡,被抓到了。”
“我们班有些孩子,就是不成熟。那点破事儿,做给谁看呢?”她冷笑着,明显就是针对宁小宇和柯冉的。
“说白了,他们是为了逃避惩罚。上次,德育主任那事还没说清。”
白丽嗔怪了一声。
“简直是王者气象,好像所有的阳光都落在他身上。”苏明理说。
她是如此会说话,芋头的爸爸真以为她心思缜密为学生担忧了。
文章写完了,思绪却没有停下来。
艾利亚似乎很不喜欢这样的场面,仿佛在无形之中背上了同谋者的黑锅。她磨磨蹭蹭地站了起来,说:
吃过晚饭,回到教室,柯冉和宁小宇回来了。
“真是爆点!柯冉那小子可真有胆乱来啊。”章子腾大声感叹,连连摇头,每当有什么事发生,这种场合总有他的身影。
临睡前,她终于叹了口气,自言自语:
“那当然,你爸是男的。”艾利亚说完,又低下头看杂志了。她对所有事都是这样。姿态是进入的,内心是旁观的。什么都与她无干,她不过爱欣赏别人的混乱。
——“我”相逢永泽,两人孤独相投,但在价值观上却走向了陌路;初美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女子,但仍然不能介入永泽的内心世界,“我”理解初美却无能为力;直子与绿子更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孤独的象征,直子是默默,忧伤,淡雅的。绿子是活泼,开朗,然而悲哀的;“敢死队”是平平凡凡地活在这世界上的孤独者……
有时人们之所以爱凭自己的想象叙述,完全是因为这与现实大相径庭。
苏明理很无奈,有吐不完的苦水:“岂止是挨骂呀。当时都12点了,我很想睡觉,第二天一大早还要去戴氏补英语。我很不耐烦,心里很火,所以说,我觉得自己以后随便考个大学就行了,毕业后回到厂里工作,生活过得去就行。谁知这么一说,我妈彻底愤怒了,她冲我大叫,‘苏明理,人活着总要有点奔头吧?’如此种种,语气那叫一个悲愤。”
“能读这所学校,各位同学家境都不会太困难。”老师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希望大家踊跃捐款。我们老师约好了,都捐出自和*图*书己一个月的工资。”
“不要恶心了。你毁了这句话。”芋头突然出现,“不过,最近挺流行这种说法的。盲目追风倒是很能证明你的浅薄。”
被他这么一说,教室里霎时间似乎弥漫了熏天的恶臭。大家嗷嗷地叫着,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疑心自己是否真的有这个特殊的功能。
“又不是第一次。”艾利亚不以为然,哗哗地翻着一本时尚杂志,“多久的事?”
我寻思不是什么好事,苏明理也这样觉得。
“他们真的很年轻。面对陌生的地方,内心张皇不安。他们小心翼翼地打量周遭的一切,旅客们脸上满是倦容,靠在椅背上,似睡非睡。花花绿绿的行李塞满了他们头上的搁物架,似乎稍一颠簸便会哗哗坠地。一个消瘦的少年带着心事重重的寂寞看着不知是哪的地方。火车穿过风的声音。喁喁低语的声音。温热得有些闷的空气里混合着淡淡的皮肤的味道,婴儿奶粉的味道,形形色|色的行李上携带着的尘埃的味道。极其疲惫,可又难以入眠。恍恍惚惚里,情感的温热积压在心里,他们颠三倒四地做着不知是什么的梦。”
他们的对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凑了过去,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鲁老照常进了教室。今天她穿着一件淡绿的连衣裙,套着白色针织外套,样式呆板。登上讲台后,她像往常一样威严地环视了教室一周,目光在宁小宇和柯冉的空位上停留了一会儿,不露声色地移开了。她并不急于开口,皱着眉像在思忖着什么,骇人的沉默里,她忽然抿嘴一笑,而且似乎是故意笑出了声,那尖细的声音听起来极像讽刺,或者说,本来就是讽刺。
——考试啊考试。
“昨天,宁小宇给我发了短信……说是要和柯冉去重庆来着……”
“我觉得没什么。”她坦然地说。
“我看就是小型造粪机……”生物老师冷笑着,继续恶心着我们,“你们对促进生态系统的循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你们既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
“但是我知道,你们是不会学他们的。看不清现状,只顾头脑发热,这样的人终究是会吃苦的。作出这种事,不用老师和家长惩罚他们,他们自己就会尝到苦果。如果他们一直不改变自己的性格,未来生活的苦果,很苦,很苦。”鲁老的语气像是预言一般阴冷。
女生捐得温柔。白丽一千,宁小宇八百,艾利亚九百。
他俩同时白了我一眼。
“找他的妈妈。”
她在日记里写:“孤独啊,窗外那株树,落下的雨点,雨中嬉戏的孩子,无一不让我感到一种一望见底的孤独。”
“我作业还没写完。”苏明理开始翻找她的《轻松一练》。
“不过,有谁知道宁小宇的去向?”
门一关,苏明理又将衣服揉作一团,往柜子里一塞,嘭地关上百叶门。怒怒低吼:“老娘才不把柜子收拾得像太平间!”
“李松家不是很富裕。”良久,我说。
教室里一片静默。有几个人转过头,意味深长地看了看艾利亚。
苏明理转了回去。
“柯冉。”
此事震惊了校方。于是,德育处层层设防,挨班进行心理辅导,原先门庭冷落的心理咨询室一下成为了圣光笼罩之地,叫人忍不住想抱住它的门框大赞“生命之源”。
“我不会自杀,怎么都不会。”宁小宇说,“活着,才有爱。但没有爱了,还是可以活。”
也许,他就像黑洞,默默观察周遭发生的一切,思绪万千却又不动声色。
“去重庆干什么?”
“理解?我也理解呀。但是他们能不能理解一下我呢?”苏明理眼睛往下一垂,有些愤愤的伤感。
最后,我想说的是,《挪威的森林》是我所读的第一本小说。我十岁的时候第一次翻开了它,而今,我已经十四岁了。这四年里,我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可它对我的影响是经久不变而难可言喻的。它的语言氛围,抒情格调,思想气息,在我每一次执笔时,始终陪我独坐在无言的静谧之中。我一直相信,一个人面对文字之际而产生的情感,乃所谓生命一种永恒的乡愁。也许,百年后,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会很高兴地再读它一次。
我和苏明理相视无言。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古怪的感觉。
说到这里,鲁老过来了。我以为我们说闲话被她发觉了,硬着头皮准备挨批。但她只是叫走了芋头一人,而且言语温和。
“昨天就没来。”
“他?上来就打呀,我妈在一旁煽风点火,就差哭天抹泪了。我爸一边打,一边咆哮,‘你就和-图-书这样,以后长大能干成什么?我们为你付出了那么多心血,花了那么多钱……’”
我无语,埋下头写起了讲稿。
苏明理很无语,自叹倒霉,爬下床来,开始整理柜子,拉出一大堆衣服,似要翻天覆地地改革一番。生活老师见状,在本子上扣了分,走了。
艾利亚点了点头:“只有一条短信,今早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已经关机了。”
“你们……”
“因为我过的不叫生活,叫寂寞。”他说。
李松也这样想过吗?
“虚伪的家伙”,有几个女生笑骂。
“算了,不说他了,说说李松吧。”我插话道。
“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翻腾着手上几乎装订成册的复习题单,大家痛苦地呻|吟着,“全要背吗?”
感叹自己的处境之余,我们把目光投向了班里的阔少们。
“哇,你们真是太有个性了!”她夸赞道。
艾利亚偏头想了想,问:“你爸冲进来了?”
我正想开口,芋头干脆地抢过话来:“说白了就是暴发户。从小,他就不允许我把西瓜吃到白皮,总要我留一层厚厚的红瓤,好像那样就挺有尊严。”
星期日晚上,宁小宇没有返校。看着空空的床位,我感慨万千,以为她是生病了或者罢课抗争了。
我无所事事起来,四下张望,最后,注意力落在了李松身上。
我的心里猛然一扯,觉得不寒而栗。
鲁老说服了芋头他爸,让芋头转学,“寻求更适合发展的环境”。
“残酷意识流的书读多了。”旁边一个女生对同伴说,“她就是我们班的,每次考不好,就说‘谁谁谁吊死在某某某的睫毛上’”。
我觉得不可置信,芋头他爸怎么这么容易就上了鲁老的圈套。
“私奔尽头,空无一人。”
接下来几天,学校稍作整顿。进行了几场逃生演练,基本恢复了教学秩序。
其实不是这样。很多事都不是他想的那样。可是,他对人对事每每带着无可救药的慈悲,让我们充满了近乎同情的愧疚。
“有这么一句话,”芋头直视着章子腾的眼睛,“纵使置身釜底,也希望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看来她是来真的了……昨天宁小宇给我发了短信,我以为是开玩笑,结果她真的这样做了。她只给她爸留了一封信,就和柯冉走了。”
当时,门一开,宁小宇的爸爸就扬手给了柯冉一巴掌。他转过来想打自己女儿,手悬在半空中,又放下了。
周一早晨,一进教室,就听到有人问:“宁小宇还没来吗?”
“生命是美好的,是值得热爱的,我不应该一时鲁莽,要对得起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是阳光的少年,生活在美好的时代,有学校与老师的关怀……”
——明天的阅读课轮到我向大家推荐书目。
天长日久地待在学校里,我们没有生活。既然生活教育不了我们,那就只有书本能教育我们。生活单一的年代,感受贫乏的年代,我们靠拼命阅读来填补空白。这其实是另一种空白。
这天晚自习,苏明理说,自己一直很纳闷,为什么王励励光芒万丈而她不论如何学习都借不得他的一点光辉。
听到这里,我觉得我们真是站在阳光下了。这一面阳光普照,大地焕发生机,那一面却已经冷了。那些边远学校的领导,也许是太苦了,但终究是太狠了——个别腐败分子贪污修建教学楼的公款,那么多学生的命。
我依然是一头雾水,只想向知情人探寻事情的原委。结果看了一圈后,我发现大家都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已。“私奔”这个遥远的词汇,激起了他们心底最幽而秘又最大胆的联想,那种热烈的狂野,那种不羁的傲气,搅和在一起,此刻正无可救药地荡涤着他们的心神。
再往下看,是那女生后来写的心路历程。
这种认真也许肤浅。但如此的坦白固执,有时还真让人有些感动。
我对他们并没有依赖,也不存在期望。只是他俩与周围的一切自成一个精致的体系,任何一点缺失,都有损于这个体系的美。
当即给柯冉家打电话。
“哦。”我觉得自己是被排挤了。
日记发下来后,我去翻看苏明理的日记,刹那间我觉得,孤独症确乎已经在班上蔓延开来了。
生物老师停下了手中的粉笔,缓缓转过来,问:“怎么,你们有怨言吗?会考分数是要算入中考成绩的!”由于说话时太过激动,他那庞大的身躯有节奏地颤动着,惹笑了不少同学。
他走到座位上,用手托着脸,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我不久就要和你们拜拜了。”
“你很想知道?”
如果说“私奔和*图*书”是为了追求自由,情有可原,那么,下面这件事就更上一层楼了,它不仅不以活得更好为目的,干脆来个自绝于人世。
章子腾在其中最为雀跃,嘴里咿咿呀呀地怪叫,还有人为了塑造气氛,强装雄厚的嗓音,唱起了《上海滩》,原因是,前两句听起来极像“裸奔……裸奔……”。
又是一节生物课。
可是安眠药早过期了。不到一小时,她就被她爸发现了。迅速送往医院,痛苦洗胃。康复之后,一顿暴打。
大半节课后,芋头回来了。
我们全都震惊了。
“如果你自杀了大家都会高兴。”艾利亚说,“你做人太失败了。”
越是不按规则出牌的人,越有顽强的生命力。这是我观察宁小宇和芋头得出的结论。
“又怎么了?不会是因为期中成绩吧?”
“算是吧。”
世界尽头的那片森林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与这本书的邂逅对我来说犹如在朦胧梦境般的小路上携带着真正的自己走向不知是哪儿的远方。
最后,轮到李松和王励励。都是五十元。
我们一连四人,恶狼扑食一般冲过去,询问事情的起因经过,尽是好奇而贪婪的嘴脸。
“你爸呢?没说什么?”
浮躁叛逆的时代,我们也有和谐。
“唉……时运不济。”芋头深邃地说,“来日苦多。”
“不要管了,这些不是你管的。”艾利亚关了手机,嘟囔着,翻过身,睡了。
“我看,人没有追求了,就像你们这样。你们一个个打扮得光鲜亮丽,说白了,其实不过是一台台小型造粪机!”
前面说得有理,但后面看来,简直就是检讨。检讨又极不到位,有的地方让我都想寻块豆腐碰死。
“你也配说寂寞?”
一大群人围在她身边,神神秘秘地议论着宁小宇,话语间有掩藏不住的兴奋。
“没有这么可怕。”芋头回过头来,鼻尖有一颗青春痘。
“不只是那个女生,有时我都觉得自己过得很空虚。”
“他是个特别的孩子,”鲁老说,“只是不适应这个学校的教学模式。这样耗着,与其两相耽误,不如趁早让他换个环境。这对孩子的发展很关键。老师虽然有不忍,但毕竟要为学生着想。”
“多半是为情所困。”苏明理幽幽自语。
“王励励……”苏明理说,“我无法欺骗我自己!他家再怎么样总比我家好吧!”
广播里播放着《感恩的心》。我们学习手语,站在操场上默默地合着音乐。我头一次见到如此安静的画面,每个人都低着头,没有调侃,没有矫作,忘却了矛盾,忘却了繁杂,而这种安静居然发生在日日聒噪的校园。
别来打扰,我不会为任何人改变。——因为,既然人无论怎样都备感孤独,与人交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能缩短任何距离,那不如任其自然,孤独即是!倒不如像本书译者所说的那样,“把玩孤独,把玩无奈。”宁可无人理解地留在这森林里,也不出去与世俗、庸众为伍。
她是如此理性的人。常让我们收敛慌乱到措手不及的情绪。这也是我们不喜欢她的原因。可是我们又倚赖着她。
也许很多年以后,当我回想起这件事,我想我会用这样一种笔调来叙述:
孤独。因而我们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与“我”所真正渴望的世界,相差太远了。这时,作者就在众生熙熙攘攘的地方中央,在喧嚣密集的世界的尽头,塑造了一片森林。于是,走进去,想想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谁也别来打扰。我们仿佛可以感觉那片森林本身就在说:
当然,内心即使遥居森林,“我”也并非消极遁世者。在这本书里,作者达到了现实与内心极高的平衡——“我”徜徉于生活本身的乐趣,喝酒,交友,看书,打工……却又时不时跳出来观察自己,观察人生,喟叹不已。然而这正是现在很多人一直困惑,且难以做到的。从某一方面来说,它点化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给我们展示了一种诗性的、富于哲理的生活方法。让我们内在的情感得以表现,得以释放,同时也不侵犯现实丝毫的权力。这也是为什么此书多年以来畅销不衰,为全世界大多数读者所热烈追捧的原因。
整个晚自习,他们都没有回来。回到宿舍,我旁敲侧击,想从生活老师口中套出关于宁小宇的信息。
又一周过后,鲁老说:“我们不能总沉浸在情绪里。未来是向前的,大家要调整自己,转入正常的学习生活。”
“我有一个新发现。”芋头总想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于是,双方的家长在最短的时间坐在了一起,不停自责,不停检讨,共商教育挽救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