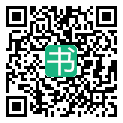第十二章 梦中的天使
但黎落落是个家境优越的女孩,没有人需要她挣钱养家糊口,甚至我估计在她结婚后,她的父母还要为她负担穿衣吃饭的费用。所以她自己那点钱,基本上挣了就随手花掉,毫无要赚钱去做点什么的观念。
我跳将起来,一把掀开黎落落盖在身上的被子:你这个厚脸皮的小妖精,你是想将全世界的男人都据为己有,然后看哪个女人可怜再出租给她吧?我倒要看看你这性感皮囊下装的是香水还是大粪,要不然怎么一会香气袭人,一会又臭气熏天?!
锦,你无法明白我和黎落落这样暴雨冰雹似的发泄,其实只是因为,我们爱对方太深,所以需要用这样自相残杀似的厮打,来将心内积聚的那些与爱一样深不可测的恨,统统地甩掉,驱开,赶走,击碎!
锦,我有一种可怖的感觉,总有一天,费云川会扔掉相机,当着黎落落的面,强行捉住我的脑袋,直视我的眼睛,并告诉我,他心内所有的爱恨纠缠。
黎落落依然很干脆地让司机开到她的住处。车到达她住的小区门口的时候,我习惯性地将包递给她,她却将我的包拉起就走。我拿着她的包,隔窗喊她:落落,你把包拿错了!黎落落头也不回:那你下来跟我换啊!
等她的眼泪干了,我才一边为她理顺着散乱了整个枕上的头发,一边拿出要开卧谈会的语气,挑开了话题:落落,你想和我聊什么呢?
我干脆踢掉了鞋子,脱|光了衣服,像条光滑的泥鳅,嗖一下便钻进了黎落落的被窝,又不由分说地将她抱住。黎落落挣扎了片刻,终于还是慢慢地无声地安静下来。
他很轻很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近乎呓语似的低低地说着:小白,我爱你,我爱你,我不能这样粗暴地对你,可是我又忍不住想要将你拥在怀里。就让我多抱你一会儿,什么都别说。我就是想要让你知道,我在上海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爱上了你,哦,不是,是很多年前,那个常常去逛书店却一脸忧伤的女孩,就已经将我的心偷走了。这么多年,我一路寻找,原来就是为了将你找到……
我坐在一边,安静地听他们笑闹,并不打断,但心里却因了费云川这样看似玩笑的话,而觉得有浓浓的温情。锦,我知道费云川对我的欣赏里,带着喜欢。我并不确定这样的喜欢,是裸|露在日光下脆弱的青苔,还是深藏在密林中长流不息的溪水。但我确定的是,费云川与我在一起,比与黎落落更能够深入地谈及某个话题。尽管这样的话题,俗世中一对快乐生活的男女,未必需要。
锦,我以为费云川早就忘记了我们,或者他从来就没有将我们收入到他温暖的记忆之中。他是那样儒雅又满怀了柔情的男人。38年的岁月里一定有不少的女人曾经对他动心,并主动地追求过他,可他竟然能够对两个小他十几岁的丫头,记得这样地清晰。
是上个周末的事情。费云川拉了我和黎落落去位于黄埔江口的森林公园。他说春天来了,那里有很多漂亮的待嫁的新娘,正在拍摄婚纱照。他要让我和黎落落去找找感觉,尽早将自己嫁出去。如果我们愿意,他还会破费租上一套婚纱,让我们更真实地体验嫁人的感觉,不过,新郎可是要让他来扮演,怎么说,赔出去了出租费,他好歹也要占一点小便宜。
黎落落懒到也不洗漱,将一只鞋子踢到窗台上去,另一只则孤零零地丢在地板上。我叹口气,将两只可怜的鞋子重新规整到一起,放到床底的鞋架上。黎落落背对着我,一头蓬勃的大|波浪卷发像是野生的大丽花,恣意绚烂地绽放在枕上。我看她一眼,又怜爱地帮她盖一下被角,便准备去洗手间洗漱。黎落落却在我起身之时,一下子转过身来,恶狠狠道:龙小白,你不准走,我要你上床陪我说话,立刻!马上!说完了便腾地欠起身来,将我粗鲁地拽倒在她的身边。
黎落落是个很容易就开心起来的丫头,她在我的挑逗里,也发了骚,主动地在我的镜头前对费云川又搂又抱,有一次,还趁我摆弄相机的时候,啪一下亲了费云川一口。这个镜头竟然被我的相机给抓拍到了,而且,效果出奇地好。黎落落看到这张照片,简直是乐坏了,很夸张地赏我一个额头之吻。
可是那些挣来的钱都去了哪儿呢,我却是糊里糊涂,始终记不清楚。总有人朝我要钱,同学,父母,弟弟,姐姐,这样那样的男人。当然,锦,还有你。只不过,给别人的钱,我会觉得心疼,给你,我却是心甘情愿。确切地说,不是你朝我要钱,而是我强迫你接受,又强迫你不能还我。
黎落落很快消失在一条小路的拐角。我和费云川坐在水边的木椅上,看着她走远了,突然就觉得有些尴尬,想要说些什么,又似乎说什么都是多余。两个人这样坐了有两分钟,我却感觉有两年那么漫长。
锦,在这个无法入眠的晚上,我想,如果没有你,我会不会爱上费云川?会不会大胆地从黎落落那里,将费云川争抢过来?而我和黎落落,会不会因此分道扬镳,再不相见?我庆幸一切只是如果,因为这所有的假设,听上去如此的残酷无情。我不想错过你,尽管我与你,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定会分离。我也不想失去黎落落,她是我生命中赖以为继的精神鸦片。我的成长,与她丝丝相连,环环相扣。而费云川,他在我的心里,不过是一个与你相像的男人,我遇到了他,犹如重温了你,如果一定要让我和他生出这样那样的摩擦,那么就全当这是上天让我在旧梦里,安静地多睡一会儿吧。
黎落落已经迫不及待地穿上了薄薄的黑色网格丝|袜,和众多的上海美女们在街头拼抢着男人垂涎的视线。我有点怕冷,但还是被黎落落“胁迫”着,每到周末就换上一身春意融融的行头,跟她和费云川“鬼混”。
锦,一切都和-图-书来得很突然,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费云川几乎有些粗鲁地将我慌乱不安的手拉过来。我整个的身体,一下子倒在他的怀里。我有些喘不过气来,觉得要窒息了。我要挣脱掉他,可是他的双臂,却将我结实地抱住,愈来愈紧,紧到我想要说话,都觉得艰难。
事实上,我也无法让自己的表情,在费云川的大胆的注视之下,保持一贯柔和的笑容。我会觉得脸上有火辣辣的光线照着,炙烤着,逡巡着。我不知道该如何放置调整那抹佯装出来的微笑。我还想将它们藏匿起来,可是最后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它们总能被费云川准确地捕捉到,并拍摄到相机里,永久地保存下来。
黎落落像一只生气的小狗,哼哼一声:可是你却比我提前入了他的梦中去。
我在黎落落去洗手间的空当里,很快地走到费云川的身边,看他一眼,轻声说:借我相机用一会儿好么?我不想……不想让落落不开心。费云川欲言又止,只低低地唤了一下我的名字,小白,便在不远处黎落落懒懒走过来的身影里,说:好。
黎落落惊愕地欠起身来:龙小白,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这个男人,就是费云川。
我只有试探着开了口。我说:落落,不管你怎么恨我,我都想告诉你,我不爱费云川。他只是少女时代的一个情人的影子,经过这么多年,早已模糊不清。现在重新相遇,那不多的一点回忆,也已经支离破碎,无法缝合。
我努力憋着,没有笑,但脸上的表情却是缓和下来。黎落落大了胆,继续讨饶:小白,以后如果你寂寞了烦了想找个男人揍了,我随时将费云川出租给你用,租金是一个小时一份“鼎泰丰”的蟹粉小笼包,好不好?
黎落落没了话,“哼”一声就上了楼。我则在后面喋喋不休,说她就知道臭美,连外套都不知道穿,又说她房间里肯定乱成了狗窝,所以才假意惺惺地让我住,不过是为了帮她收拾乱糟糟的屋子。但我说了那么多,却只字未提与费云川有关的一切。
我和黎落落都将费云川当成大款来傍,尽管我们都知道他的钱是自己一分一分地积攒出来的,但谁让这个男人喜欢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呢?而且他做饭超级好吃,就不能怨我和黎落落非要厚着脸皮住在他的房子里,跟生了根似的,拔都拔不掉。
我说过他跟你神似,但近来我又发现,在很多时候,他又与你有着很远的距离。这样的距离,除了我,没有人能够读懂,就连每日和他“厮混”的黎落落也不能够。
可是费云川却不同于你。当他说要给我和黎落落拍照时,我几乎就逃不掉他的视线。他会让相机代替自己的眼睛,聚焦在任何他想看到的地方,我的头发,我的眼睛,我的鼻翼,我的双手,甚至我的乳|房,我的鞋子。我知道他常常借故寻找合适拍摄的位置,在我的脸上长时间地游走。黎落落每次都在旁边叫嚣:云川,你快拍啊,我的表情憋不住要淌出来啦。
费云川不跟她计较,看她吃得满头大汗,还会体贴地将干净的毛巾拿过来,为她拭掉额头的汗水。黎落落毫不避讳,当着我的面,就将红艳艳的嘴唇伸过去,让费云川为他擦掉上面的油渍。我知道妖媚情|色的黎落落是想让费云川用唇为她吮去上面的残渣的,但又怕我吃醋嫉妒,所以还是有所收敛,只伸出满是油水的两只手,撒娇地让费云川用毛巾给她拭掉。
鬼混这个词是黎落落说的。她最爱用这类夸张堕落的词汇来形容我们的生活,她喜欢这样有些下贱的词语,觉得可以让单调枯燥的生活充满低级趣味和放肆动荡的快|感。她还常常把生活比喻成做|爱,说要么自|慰寂寞到底,要么就一路高潮,尖叫迭起。那些温开水一样混沌死寂、总也抵达不到高潮的日子,还是让它们统统地滚蛋吧。
如果接下来费云川睡着了,我和黎落落或许会悄无声息地回到隔着客厅的另一个卧室里,像少女时那样,鞋子也不脱,便头抵着头不知晨昏地睡了过去。可是偏偏看似睡着了的费云川,突然翻转了一下身,面对着黎落落,含混不清地说:小白,我喜欢你,很喜欢。
我摇头:落落,你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不爱费云川,真的不爱。他是你的,你尽管拿去蹂躏拿去享用,我连一丝的嫉妒也没有。
黎落落是唯一一个支持我做SOHO的朋友。她常常教训我说,挣那么多钱干吗呢?挣得多就被你们家人索取得多,挣得少你们家人也索取得少,所以干脆少挣一点,够自己花就是了;况且做SOHO多好啊,不用天天看老板的脸色,不想做哪个混蛋的广告设计了,就一脚将他们踢得远远的。
我笑着将黎落落的肩头扭转过来:那又怎样?铁马冰河入梦来,入得再深,也只是铁马和冰冷的河,哪有你这一腔热血的小妖精入得痛快?费云川再怎么傻,也不会放着个火辣辣的性感尤|物不亲不爱,天天朝那冷冰冰的铁马上碰吧?
但这样进一步的举动,因为我,而现出犹豫与疑虑。黎落落总是说,小白鼠,快快打扮好,见我们的情人去啦。是的,黎落落像少女时代那样,将费云川当成我们共同的情人,而且她愿意与我分享费云川的一切,他的呵护,他的温柔,他的宽厚,他的勇猛,他的结实的臂膀。黎落落说,谁让我和她是最好的闺蜜呢,所以她寻找了这么多年的费云川,一旦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依然愿意继续少女时代的梦想。
黎落落被拍照弄得兴奋至极,讨好说要好好慰劳慰劳费云川这个模特和我这个摄影师,自告奋勇要去不怎么近的地方买水给我们喝。费云川并没有阻止,掏出钱包给她,说:那快去快回,不准路上游逛让我们久等。
一切似乎都风平浪www.hetushu.com.com静,我和黎落落矢口不提费云川醉酒后的晚上发生的一切。费云川也一定不记得自己说过的醉话了吧?他照例带着我和黎落落在无事可做的周末,四处兜风。他对上海的各个角落都非常熟悉,我很惊讶他对那些充满了老旧故事的街道的发掘能力。三个人常常穿上一身休闲的行头,在那些曲折的弄堂小巷里一逛就是一天。费云川带领着我和黎落落,从中山公园,走到有数不清住家的愚园路,再穿越江苏路、华山路、徐家汇、淮海路。
黎落落总是第一个喊累,她臭美,明明说好了逛街,还是穿着半高跟的小皮靴,咔哒咔哒地像在给我们的散步做音乐伴奏。有时候费云川搞坏,故意地在前面跑。我怀疑他读书时是有名的运动健将,否则不会走起路来健步如飞,跑起步来更是虎虎生风。
后来我们终于厮打累了,在满床狼藉中,喘着粗气躺倒下来。锦,我突然觉得有些委屈,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让黎落落明白,费云川之于我,不过是一个温柔体贴敢于承担责任的好男人,世上像他这样的好男人很多很多,可是我没有精力全都去爱,也没有足够广阔的胸怀,承受他们爱情的重量。
可是,我还是在一阵鸟的鸣叫声里,醒转过来,并用力地挣脱着费云川的臂膀。费云川却是依然用力地拥抱着我,不肯放手。我终于急了,在他的肩头,狠狠地咬下一口。费云川痛叫一声,便松开了臂膀。
我不知道黎落落是否注意到了我因为微微的嫉妒,而现出的感伤。这个丫头总是粗心大意,马马虎虎,除了她自己几米内的视域,很少会关心外界的广阔世界。但这样的小迷糊,恰是她最讨人喜欢的一面,因为你永远都不舍得对一个一脸无辜表情的丫头动怒、发火、记仇。你总是会在她妖媚又天真的神情里,将那些明明是她做错了的事,一笑忘记。
那个笨重的专业相机,在我的手里,的确是不听使唤。我很费力地捣弄着它,还装出一副开心的模样,逗引着黎落落。我摆出专业摄影师的语气冲他们大喊:嗨,亲密一点啦,女孩子放开点不要这么羞涩好不好?对,这位男士把你的手环在女孩子的腰上,Wonderful!
别给我装傻,你知道我想要和你聊什么!黎落落这样一针见血地回复我,让我犹如被她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在这初春的夜晚,瑟瑟发抖地现出一脸躲不掉的窘相。
那么是费云川主动要求的么?他不止一次地在我和黎落落面前开玩笑说过,喜欢三个人在一起的感觉,让他像是回到了大清时代,可以做那个风流倜傥且有三宫六院的乾隆皇帝,这几乎是每个男人的梦想呢。他甚至还刮一下黎落落的鼻尖,说:跟你一个人混有点乏味呢,人家龙小白可比你有才华得多,跟她谈起诗书琴画来,有棋逢对手的感觉,哪象你,硬把徐志摩的诗按到戴望舒的头上,指着齐白石的虾硬说是徐悲鸿画的。
锦,我恐惧这样的一天。
黎落落在那天返程的路上,凑在我的耳边,说了许多遍“谢谢你,小白鼠”。一路上她还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用她特有的方式,来将内心急剧膨胀的兴奋传递给我。费云川说他累了,没有留我们吃饭和住宿,他还赶走了找了许多理由想要留下来陪他的黎落落。费云川脸上的疲惫和失落,我不知道黎落落有没有看出来,我想她肯定是太过开心了,以至于连费云川对她叽叽咕咕、喋喋不休地问东问西时,眼中一闪而过的鲜明的烦乱都没有看出来。
黎落落先挣开了我的手,恨恨地道:干吗这么厚脸皮跟我来睡,返回费云川的房子里好了!我扭扭她有些婴儿肥的脸,道:是哪个厚脸皮的家伙不好意思说让我陪她睡,非要将人家的书包抢过去就走的?
锦,我每次这样看着他们,就会微微地嫉妒黎落落。这个与我一路走来的丫头,她总是那样幸运地被命运垂青,作为家里的独生女,从小便享尽了父母亲朋的宠爱;读书的时候,每天都有情书等着拆阅,更会有男生们送的玩不尽的新鲜小东西;连后来高考的时候,成绩不怎么好的她,还因为意外猜中了几道题目,而超常发挥,读了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本科。等到后来工作,别人都在为此四处奔波,偏偏她,玩似的东炒一家,西炒一家,搞到后来,大家都叫她“炒女”。爱情上她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如日中天的明星一样,几乎没有出现过感情空档期。
黎落落嘴上不饶人,她常常边大快朵颐地吃着费云川做的雪菜四鳃鲈鱼汤和静安水晶虾仁,边损他说之所以费云川将饭能做得这么好吃,实在是因为他舍不得花钱请我们去东方明珠的旋转餐厅,又怕我们两个贪吃鬼将他吃得破了产。
黎落落显然在我的话里有些激动,顺手操起头顶的一个趴趴熊,朝我扔过来,恰好砸在我的嘴上。我的牙齿即刻袭过一阵火辣辣的疼。我等那钻心的疼痛过去之后,才扒开趴趴熊,怒气冲冲地瞪视着黎落落,冲她喊:黎落落,你这个小婊子,你以为你是谁?妲己还是蛇妖?天天往费云川的书店里跑不给他一点自由也就罢了,凭什么连费云川的梦话都要无赖地霸占着?!
锦,这封信给你断断续续写了很久,因为这段时间每有一点空闲,便被黎落落给霸占去了。我有些不明白为何黎落落总喜欢让我这个第三者插在她和费云川之间,是想要炫耀她现在的爱情么?她从小就是个爱张扬的丫头,得到的一切,总不忘给人拿出显摆一番,也只有我,才能宽容她这样的骄傲。但我觉得她未必是想让我看到她与费云川亲热的种种。她这个疯狂的丫头,更喜欢关起门来,和费云川肆无忌惮地在地毯上亲吻、做|爱、尖叫、滚打。当着我的面,她再怎么炫耀,终归还是像她说和_图_书的那样,有自|慰达不到高潮的气恼与失落。
我微笑:不,落落,他不是过去时,我不会让他成为过去,我要让他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他夺都夺不去。
我推开了黎落落,和她隔开半个手臂的距离,而后摆正她低垂的脑袋,道:黎落落,你是不是想要问我,我究竟是怎样勾引的费云川?怎样让他在梦里都说喜欢我?怎样背着你偷偷地跟他约会、亲吻、抚摸,甚至是做|爱?
我当然没有她这样的条件,不想辛苦地挣钱,却被一个始终甩不掉的家庭的责任拖累着,无法轻易地放手。所以我做起SOHO,总是会焦虑不安,每日熬夜,做接不完的活,就像一个养着自己男人的妓|女,不要命地躺在床上流血接着源源不断的嫖客。
锦,我要睡了。我不想醒来,我愿意环拥着这样的梦,到我老去的那一天。
我和黎落落将斜躺在沙发上的费云川吃力地扶到他的卧室里去。费云川沉沉地仰头躺倒在床上的时候,我和黎落落也因为疲惫被惯性拉倒在床上。费云川在醉意之中,突然伸出手来,很轻很轻地,帮我抚去额头的一缕碎发。这样一个细微的动作,在我还没有羞红了脸之前,便被黎落落窥去了。黎落落很霸道地将费云川的左臂伸展到自己的脖颈下,那一刻的黎落落,像一只任性的小猫,躺在费云川的臂膀上,又微闭了眼睛,似乎睡着了,但我知道她只是假装。她长长的密密的睫毛似一只黑色的蝴蝶,不停地扇动着轻盈的翼翅,似乎想要飞走,却又带着一抹委屈留了下来。
亲爱的锦:
但每一次费云川像一个称职的教练一样高声喊了停,我在黎落落冲费云川撒娇耍赖让他借肩膀一用的时候,便立刻从那迷雾里清醒过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下意识地躲着费云川,在停下歇息的时候,坐在几米远的地方,微笑着看黎落落冲过去吊着费云川的胳膊,哎呦哎呦地喊累,娇嗔地骂费云川坏蛋,又让他这个自封的医师给她揉故意崴了的脚踝。锦,我觉得费云川和黎落落真是般配,一个成熟稳重,一个风骚妖冶;一个温柔体贴,一个娇媚风情。
已经接近凌晨的一点,马路上的出租车早已稀少,偶尔一辆,则在春天夜晚的凉风里疾驶着不肯停留片刻。我和黎落落站在清冷的街头,瑟缩着等了十几分钟,才终于拦下了一辆。上车后我才发现黎落落将外套忘在了费云川的住处。她的嘴唇已经有些青紫,无意中碰到的手,也是冰凉。若在以前,我们两个一定笑闹着将手伸到彼此的脖子里取暖,可是这次却像马路上的水迹,冻住了。
黎落落像只凶猛的狼,一下子扑上来,无所顾忌地用手中的趴趴熊忿忿不休地砸着我。锦,你若是在现场,一定会被这样两个赤|裸着身体打闹的女人给震住的。你也会想不明白,两个素日好到常被男人们误认为同性恋的女子,怎么打起架来,像两只急红了眼的恶兽,恶语相向,毫不相让?而且还将被子踢到床下去,把大大小小的玩具也全都拿来当了武器,毫不留情地砸向对方这个始终不肯服输的靶子。怕是两个男人之间,也没有这样凶猛的打斗吧?
裸身的黎落落啊啊尖叫着与我争抢着被子。这让我想起有一年我们两个人在海上划船,黎落落大胆地脱|光了衣服,风浪袭来,有想见义勇为的男人高喊着朝我们划过来时,她同样嘶声尖叫着护住自己饱满骄傲的乳|房和惹火诱人的下身。
黎落落不服气,说:哼哼,可龙小白不仅分不清“克丽缇娜”、“欧珀莱”、“VOV”、“兰芝”、“高丝”、“DHC”、“ZA”等国际品牌的化妆品,还张冠李戴,将人家美国的“丝塔芙”当成法国产的!
我不知道费云川在温柔地为黎落落擦掉唇边菜渍的时候,因为我的注视,有没有一丝的尴尬。我倒是看得出黎落落很享受这样亲密暧昧的服务,而且她还想要进一步大胆的举动,比如吊在费云川的脖子上耍赖,或者跳到沙发上躺在他的腿上挠他的痒,再或夜晚睡不着觉的时候,溜到费云川的房间里去,赖在他的怀里假装醉酒的猫狗。
不管是他们中的谁,更希望这个三人的组合长久延续,最终的结果,都是我挤出接收设计订单以外的时间,跟他们不知天长地久地厮混下去。
上海的春天终于在丝丝缕缕的雾气里飘来,北京的春天也早就在蓬勃的大风里开始了吧?
锦,这一点费云川跟你真像,当我在后面一路跟着费云川奔跑的时候,我似乎又听见了你均匀有力的喘息声。我常常觉得恍惚,好像依然在跟着你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我所行过的那些巷子,全都变幻成京味浓郁的胡同,有鸽子在风里带着清脆的哨音越过湛蓝的天空。一切看上去都像我画的油画,静谧,稳妥,慵懒,闲散,空气里弥漫着午后煮沸的咖啡的浅香。
锦,我依然没有给自己找一份工作的打算,整日还是做着要么撑死要么饿死的SOHO一族。当然我从来没有被撑死过,总是在小康生活的下面晃荡。一不小心,那悬挂着我的蛛丝就有断掉的危险,将我直接坠入贫困的深渊。
我侧过身,面对着黎落落:那又有什么用呢?你知道我爱的是谁,过去,现在,将来,从来都不会变。
锦,我总以为这样我就可以将你留住,或者是将我留在你的心里。可是最后我发现,小镇不会因为我将自己的身体和金钱全都给了它,就因此可以容我。而你,也是如此。
黎落落的脚步声一点点地近了,我慌忙地起身离开木椅,拿起相机,假装拍摄眼前这片寂静无声的溪水。一阵风吹过,我看到镜头里的水面像被人拿棍子用力搅过,哗啦哗啦地,动荡不安。
锦,你不是那个和我一样只付出自己而不问回报的傻瓜。你一直都怀有理智,不会为任何人疯狂,并因此弃掉那些可有和_图_书可无但又事关身份的荣耀。
锦,你说话的时候,视线总是飘忽不定,你似乎很怕我的眼睛,怕我眼睛里的热情的火焰会将你融化,或者怕自己陷入我的爱中,无法拔出,所以你总是将视线聚焦到我的眼睛以外的地方,譬如人群,譬如服务生,譬如店铺。每当我想要对你表白什么,你更是会拿可有可无的话题岔开来。这让我们相爱的五年里,我除了写信或者纸条给你,再或做|爱的时候借助高潮来临前的激|情,几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让你读懂我的爱。
我很快地冷冷地打断了费云川:我不是因为落落,你不懂我的过去,你也不会参予进我的未来。你要珍惜落落,她那么爱你。
费云川并没有进一步的举止,他只是这样紧紧地拥抱着我,像拥抱着一块即将丢失的玉石,或者快要飞走的云朵。似乎也只有这样的姿势,才能让他不会亵渎了这块他不忍放弃的美玉。
锦,那晚我和黎落落相拥着睡去的时候,我又做了一个与几个月前相似的梦。依然是一片无边的汪洋,像我年少时总想要横越过去的大海,我在上面孤单地飘着,找不到将舟停泊的海岸。我不知道划了有多久,似乎有很多年,又似乎只是一个夜晚。我竟然隐约地看到一片光亮,或者是一片绿洲,一个岛屿。不管那是什么,锦,我能够确定的是,那是一个趋向美好的梦,只是被梦里依然不休不止要来打我的黎落落,一个拳头过来,打断在一片天光中。
锦,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像在你的怀抱之中,重新听到那些你很少对我说起的爱恋与想念,所以我才会微闭上眼睛,静静地,静静地享受着这片刻的温存,并在费云川温柔的爱抚中,内心涌起一股又一股细细的波浪。它们彼此纠缠着涌上来,又退去,又厮缠着重新涌上来。
黎落落想必真的是被一对又一对的甜蜜情侣们给感染了,特爱单独臭美拍照的她,这次竟是强烈要求让费云川将相机给我,而后由我给他们拍摄合影。费云川看上去有些为难,他找出了很多理由来拒绝黎落落,一会儿说我技术太差,肯定会将她拍成一个红眼兔子,一会儿又说这里背景杂乱不堪,不适合拍照。黎落落起初还撒娇抗议两声,后来就噤了声,闷闷不乐地甩着一个细长的柳条,又不断地对着费云川的镜头飞着白眼。我看出黎落落其实是生了气,只是一向坏脾气的她,在费云川面前像是被关了阀门,始终发不了火。一个人噘嘴生气,已经是她能表达的最强烈的抗议。
但我却窥见了费云川脸上与我同样的感伤。有那么几次,他的视线,越过中间的黎落落,落在我的脸上。我感觉自己像是碰到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炽烈的灼痛感倏地一下袭遍了全身。我想要躲开,却发现每一次都是徒劳,费云川总有办法,让我的慌乱,暴露在他的注视之下。他会走过来,假装帮我提东西,让我不得不面对他的眼睛。他还会直接地喊我的名字,他很大声地叫我:小白,过来我帮你和落落拍两张照片。
黎落落憋着一股子没有发泄完的气打断我:过去是过去,过去费云川根本没有喜欢过我们,可是现在他却爱上了你!
我也很快地收拾了自己的书包,换上鞋子,并赶在黎落落开门之前,站在了门口的楼梯上等她。我与黎落落谁也没有说要留下来,但也没有说究竟是去她那里还是各自回各自的住处。楼道里有些黑,是声控灯,以前在黎落落哒哒哒的高跟鞋声音里,总会准时亮起的廊灯,这次却不知为何,从六楼到一楼,都没有亮。我拿出手机,用上面微弱的光亮照明,小心地一阶一阶地下着。
黎落落说这话的时候,还会配合做上一个用高跟鞋恶狠狠踢开什么的动作。其实如果黎落落也有点艺术天分,可以写写小说,画画动漫,搞搞网页。她应该是最适合做SOHO的女子。本科毕业不过是三年的时间,她却炒了四五个老板的鱿鱼,炒到最后用她的话说,像女人习惯性流产,早就对疼痛麻痹不觉了。
我记不清是谁先开启了这个与费云川有关的话题。我只记得那天我和黎落落都很自觉地没有留在费云川的房子里过夜。费云川给我们做了丰盛的饭菜,因为那天是他38岁的生日。
黎落落的房间果然乱得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在她这里,我俨然成了一个能将房间收拾得有条不紊的优秀家庭主妇,不过是几分钟,我便将她堆满各类毛绒玩具的床,收拾出了可以容纳我们两个睡觉的地方。
这样过了有多久呢,黎落落起身将被子抱了过来,给费云川盖好,而后沉默不语地走进客厅,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黎落落先后碰倒了一个杯子和一把椅子,还有我们吃剩的一盘龙虾。她的脸隐在一团昏暗的光里,看不清晰,可是她冷寂的后背,却是让我看清了她心里积聚的无法融化的坚冰。这样的坚冰,冷硬,冰凉,并让我惧怕。
我第一次借助着相机的镜头,仔细地看着这个在黎落落的拥抱里有些挣扎的男人。锦,他有与你很像的硬朗的轮廓,只是他的眼睛比你更温暖,注视着你的时候,不会游走开去。他也和你一样,有我需要仰视才能抵达的高度。他的臂膀很宽,像一堵可以历经风吹雨打的石墙,你尽可以放心地倚靠着它。他还有黑硬的头发,一根根地直竖着,犹如一片茂密的森林。我有时候会无意中拍到费云川的胸膛,那里开阔平坦,犹如一望无际的平原,你尽可以在上面奔跑呼喊,跳跃欢叫。
我以为再也找不到一个如你一样的男人,可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世间竟然还有另外一个傻瓜,跟我在半路相逢。
但这个租婚纱的建议最终流了产,我估计是黎落落考虑到我的感受,没有租。不过也或许,她对费云川要轮流给我们当新郎的提议,生了气。黎落落应该是想让费云川,https://www•hetushu•com•com做她唯一的新郎吧,尽管她知道这只不过是费云川一贯的玩笑话。
费云川第一次在我和黎落落面前喝醉了,喝醉了的费云川话很多。他说能够在上海遇到我们两个丫头,真是他一生的幸事。他其实在我们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就想让我们留下各自的联系方式,可是那一年他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丢了妻子,丢了颜面,丢了钱财,也寻不到自己的出路,所以奔波之中,便将我们忘记。他也曾经在梦里回到过那个海边的小镇,想起常来书店蹭书读的两个女孩,想起我眼睛里挥之不去的忧郁,还有黎落落每次离开时可爱俏皮的挥手。他还能记起一次在街头与黎落落偶遇时,黎落落羞红着脸给过他的一个遥遥的飞吻,还有在书店里整理书时不过是偶尔碰到了我的手,便让我啊一声尖叫。
最后是费云川先打破了寂静,他说:小白。我慌乱地侧过头来,看他一眼,“嗯”了一声。费云川停顿了片刻,又叫我:小白。我将放在木椅上的手移到双腿上去,又将白色的棉裙一角在手里不断地揉搓着。
黎落落依然是气愤:苏锦安已经成了过去时,而且是永远的过去,再不可能回来!
我感觉到黎落落的眼泪,一滴滴地落在我的右臂上,但我却假装不知,没有去为她擦拭眼泪。这个从来不肯在我面前落泪示弱的丫头,我知道她最不需要的,便是别人的怜悯。她宁肯将不知羞耻有些下贱的大笑展示给路人,也不要有人走过来,冷漠地将她脸上的面具揭下,说,你不要假装满不在乎。
费云川终于没有再靠近我,他只是在听到远远的黎落落的歌声响起时,低声说:小白,这次,不是梦话,也不是醉话,你不要因为黎落落,就避讳或者拒绝……
我为黎落落和费云川拍下了许多“经典之作”,黎落落一直嚷叫着要将它们洗出来,放大了贴在墙上做明星画。费云川说:这可是你自封的,我可不是什么明星,不过是一个闯荡上海滩不红不紫的老男人。黎落落上前温柔地扭住他的耳朵,娇嗔道: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老男人。费云川很快地挣脱了她,又说口渴了,要去买点水喝。
我没有再多说废话,直接付钱给司机,而后提了黎落落的包就乖乖地跟在她的身后,啪嗒啪嗒地走。走到楼门口,有些黑,黎落落摸索着去开灯的时候,差一点跌倒,我上前一把将她拉住。灯突然地打开,我和黎落落在刺眼的光里看着彼此的眼睛。她的眼睛有微微的红,好像哭过的痕迹。
黎落落正要替费云川擦拭唇角饭渍的手,就这样停住了。那一刻房间里很静,静到我和黎落落可以听到彼此有些窒息的呼吸声。黎落落从淘宝网上淘来的一只卡哇伊的小熊抱钟表,也在费云川的书桌上啪嗒啪嗒地走着,那样永远都停不下来的声音,在静寂里听了,让人愈加地焦躁不安。
我很想走过去抱一抱黎落落,像读书时我们因为一句话而生了误会,另一个总会突然地就拦住对方,并紧紧地将其拥抱住且不肯放手。可是这一次我却怕了,我怕黎落落会疯狂地甩开我的手臂,让我的难堪无处可藏。如果那样,我不如保持沉默,假装那不过是费云川一句无心的醉话。
锦,有件事,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你说。这几天我的心里有些烦乱,前天夜里甚至还失眠了。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还有与黎落落不能言说的秘密。我们之间,一向是共享一切,毫无隐藏的,可是现在,除了你,我找不到人来倾诉。
锦,我真的希望,这一刻能够天长地久地持续下去。这样我就不会将你忘记,不会重新失去你,不会回到冰冷的现实中来,也不会觉得有无助的恐慌。
黎落落终于被我逗笑,一边骂着我“坏蛋”、“黄色妖姬”、“女流氓”,一边扑过来,热烈地捶打着我。我则假装冷淡地抱胸,丝毫不动地等她发泄。她看见我这副脸色,噘了嘴,犹豫着停下,试探着凑过来,摇着我的胳膊,哼哼唧唧道:小白,好小白,亲亲小白,每个男人都想爱想吻想摸的龙小白,黎落落有眼不识小白的好,还请小白高抬贵脚,放我这只小蚂蚁一条生路哦。
可是我知道这样的梦,会有结束的一天。我和黎落落总会因为那么一个男人,分开单独行走。不会有哪个男人,真的会做我们一生的情人,除非,我们谁都不想嫁给他。但现在黎落落寻回了丢失的初恋,她迫不及待地加倍地爱着费云川,当然也想要独占他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体。
春天的确让人蠢蠢欲动,女人们迫不及待地,都来到森林公园里拍摄婚纱照。费云川一路上一直走在我们前面,给我和黎落落抓拍生动瞬间。黎落落兴奋难耐,看到一对情侣在木桥上牵手深情对视,而后做出拥吻的动作,她即刻在旁边吹起流氓哨,惹得摄影师都分了神,回头笑笑地看她。黎落落还不满足,又丢给摄影师一个飞吻,大有贿赂人家转身给她拍摄婚纱照的意思。
锦,我这样拿你与他作比,你一定不开心,是吗?可是,费云川的确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与你相似的男人。我一直在寻找的,也是这样可以引领着我,翻过一座座山,穿过一丛丛浪,走过一条条崎岖道路的男人。我握住这个男人有力的大手,便犹如握住了整个漂浮不定的世界。
费云川在上海有个两室一厅的房子,这样的房子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简直是豪宅别墅。至少在我和黎落落看来,它的确提供了别墅的作用。每到周末,我和她可以借没钱打车又怕遭男人骚扰为由,在混到很晚的时候,赖在费云川的房子里过夜。
我很快地整理着自己被费云川弄皱了的衣服,一声不响,可是我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我努力地克制着自己,告诉自己说,小白,你不要哭,你不能哭,你不能让落落伤心,不能告诉她这个秘密。你要将它烂在肚子里,直到你死去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