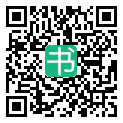第九部
第三章
白天,他拉着她的手,在院中小小的苗圃旁散步。看哪朵花耷拉下头了,便用竹枝扎个架子,支起花来;要不端上一杯水,一大口,噗地向花上喷去,再噙上一大口,噗地向另一株花喷。她懊丧地看着,他觉察到了,又拉起她的手,要她到书房欣赏他的古玉去。她赌气地一扭身子,看那些破石头有什么意思。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流淌着。
奚家是靠卖“猪仔”发达的。远在辛亥革命前,奚伯荪的祖父奚增轩正年轻的时候,汕头“契约华工”的招雇,是由美商元兴洋行统办的。这家洋行公开在大街通衢张贴“长红”,开列招雇华工的人数、待遇、条件、工作地区、年限及报名地点之类的条款,由该行派出人员诱骗当地破产农民、失业工人、手工业者上钩。同时与当地黑社会势力勾结,利诱胁迫无业游民充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英、法、荷等殖民主义者需要廉价劳动力日多,洋行逐渐把这项“业务”委托潮州当地的一些旅店、客栈接洽代办。奚增轩开办大通旅店本来不很景气,但叼上了这口肥肉,几年间便发达起来,并设了分店。
这一带的女人,只要当了嫂子辈,许是给伢儿把奶时落下的习气,大襟衫子总有三四颗布扣不扣的,到天热时,甚至有的与男人一样赤着上身,松瘪的乳|房如两个小白口袋般垂挂在胸前。奚伯荪出门难免碰到这般景象,每逢这时,他便低下头来,用衣袖遮脸,匆匆而过。但晚上他在家中沐浴宽衣,焚香夜读时,又每每摇头晃脑地吟诵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要换衣服接纳的定是贵客呀!叶雨兰悄和-图-书悄想着,不由躲在正房的廊柱后,想看看来的是个什么人。
整整一年,家庭风波才过去。风平浪静时,奚伯荪除了所珍爱的古玉外,家中的浮财已被扫荡空了。夜深人静,他搂着叶雨兰,眼望着天棚发呆。当他干枯的手抚着她的长发,从胸腔中嘘出一口长气时,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家中的“小妈妈”,只觉得他是自己的老爸爸。
院落的主人叫奚伯荪,五十岁出头。打年轻的时候,他就生成一副“相公胎子”,上了岁数后依然如兹。但见他脸面白净,那脸上该凸起的,该凹下的,都让人顺眼顺心。他终年穿一件蓝布长衫,说话细声细气,走路步步不冒失,尤其对不相识的女人格外回避。
女仆阿香走到门旁,把门开了一条缝,和门外的人说了一阵什么,又把大门关上,回来向站在院中的奚伯荪禀报:“老爷,门外有位先生要见您。这位先生我从没见过,他听说老爷要翻修大通旅店,想往里放点钱,和您搭股。”叶雨兰从来听不懂生意上的事,这时却惊异地发现,她男人灰白的脸上涌上了少有的红晕。只见他胸口剧烈地起伏了几下,对阿香说:“请那位先生稍等,我去换衣服。”说完提着袍子噔噔地回屋去了。
那天清晨,奚伯荪又拉着叶雨兰的手来到庭院中。花正开,正茂,蜜蜂嗡嗡地俯翔其间,蝴蝶飞到一朵朵花上后,便温顺合上了翅膀。这一派生机却唤不起他们的什么,在老夫少妻之间,所有别出心裁的消磨方式,似乎都已厌倦地走到了终点。
近些年来,汕头的旅业在过往华侨的刺|激下,一年强似一年和*图*书,旅业间的竞争很是厉害。奚伯荪很清楚,要想挤垮同人,站稳脚跟,靠黑道上的法子固然可逞一时之威,但不长久。靠得住的还是翻整老店,扩大客房,更新设施,以招徕旅客。但这需要一大笔钱,上世留下的钱,他大部分置了古玉,手头一时凑不出来。他生不出什么别的法子,也就只好闲闲地呆着,或关门读读书,或悉心把玩他精心收藏的古玉,实在无聊了,就去逗逗他的小女人。
奚增轩死后,其子奚荣春接过了这一摊。他本来就是潮州府的一个小官痞,有了这个背景,更不把清政府的官样文章放在眼中。汕头当局规定:任何旅业要有两家商店联保,不得拐带妇孺和贩卖人口,如有违反者则没收牌照并交官法办。对此,奚荣春嗤之以鼻,有恃无恐地干自己的。香港招工馆委托大通旅店代招收契约华工数百,每名身价近十两白银,总计几千两白银。他则以每名“猪仔”五两白银的身价包给大猪仔头,至于大猪仔头以什么价转包给小猪仔头他就不管了,只是这么一笔他就能干赚两三千两。
奚伯荪少年时跟着奚荣春贩运过“猪仔”。那时,不知国外来接“猪仔”的轮船什么时候来,运来的“猪仔”就先悄悄屯储在抽头官商码头附近的大木船里。船满了之后先驶到韩江口外汕头湾的海心里下锚,并派人严密看管,以防“猪仔”逃逸。奚伯荪随着大通旅店的人工船去送过臭咸鱼和糙米干饭,只见“猪仔”像罐头沙丁鱼一样挤在湫隘的舱中,衣衫褴褛,面目愁惨,无异囚徒。等到外国轮船来后,奚荣春即将全部“猪仔”变讫,塞入外轮的底舱,随即向洋商hetushu.com.com报账。至于这些“猪仔”是去南北美洲还是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西亚及印度洋中的毛里求斯,是去矿场还是垦殖场,已不必过问了,反正奚家已赚足了钱。
有人在拍击大门上的铁环,声音响遍了整个院落。
这女人叫叶雨兰,与奚伯荪的小女儿同庚,比他的年纪小了近三十年。她底子很潮,原是一家老举寨的歌妓,广东人称之为“琵琶仔”。干这行的,通常是云鬓花颜,自抱琵琶或秦琴,由一客嫂伴着到饮厅,坐好位置,展开乐器,娇声宣明所唱曲目,即自弹自唱,说是唱“南词”,其实全是撩人謇意的时兴小调。唱罢,挽着客嫂离开,又到别厅或另一酒家卖唱去了。“琵琶仔”只卖唱,不卖身,是老鸨悉心培植的“义女”。汕头的大旅店为招徕旅客,一般代招老举,住客若有孤枕独眠的惆怅,店方或招徕老举陪宿,或招“南词”以度清宵。当然,这种服务索价很高。事后,店方、老举寨、巡夜查册的警察三家分成。叶雨兰常到大通旅店卖唱,几次让来此巡视的奚伯荪撞上。每次碰见,奚伯荪都面无表情地转入下一个房间,实则心中一阵瘙痒,几次相逢后,春心难耐,径直找到叶雨兰的鸨母,谈了一天,扔下张四千元的庄票给叶雨兰赎了身,随即明媒正娶。
奚伯荪有一男二女。儿子自小看不上旅店业,大了后读了几年讲武堂,然后到北方当官去了,女儿们自幼看不上汕头这小地方,大了后一前一后嫁到广州去了。他老婆前二年过世了,他寂寞难耐,不久后便续了弦。
奚荣春在辛亥革命前不久就死了,给奚伯荪留下了一笔产业。但卖“猪仔和图书”这行也到头了,外国人不买了,中国人也不卖了,而主要吃这一行的奚家正常经营旅业并不十分在行,生出些黑道上的法子,也都是别的旅店用滥了的。在奚伯荪手上,大通旅店也就是平平,始终没有像上两代人经营时那样狠狠地冒几下。
奚家的一男二女回来大闹了几场。穿着黄色军服的儿子是带着荷枪实弹的马弁回来的。在她对这个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小军官投以钦羡的一眼时,他却大步走过来,大手拧住了小尖下巴,狞笑道:“我的小妈原来就是这么个小婊子。”说着掏出尺把长的手枪点点她的脑门说:“三天之内滚出去!”她当时吓得尿了裤子。没到三天,他倒先走了,走时带走了两万多元。两个女儿回来是一样的招式:捶胸顿足揪头发,又哭又喊:“我们不要老举当妈!奚家的门风全败啦:你把她撵出去!”后来,她们不哭不喊不捶胸不顿足也不揪自己头发了,兴高采烈地走了,带走了家中的全部金银细软。
叶雨兰心上凄惨。南国热,她每晚睡下却感到身上发冷,她在男人的臂弯里热烘烘地入睡,哪怕年长自己几十岁,但他是自己的男人,她要在他的爱抚下一觉睡到天亮。她睡得很轻,捕捉着的她床边走来的极细极细的脚步声,但迷迷糊糊睡又迷迷糊糊醒来,身边仍是空着的,只有泪水打湿的枕。脚步声过来了,她醒了,急急揩净脸上的泪渍,一动不动地。一只男人的软绵绵的巴掌抚到了她的额上、脸上、肩上,手又替她放下蚊帐,摸起扇子一阵横扇竖扇,赶尽了蚊子,合了帐罩,脚步声又渐渐离去。她咬住被头,仍禁不住抽啜出声。离去的人听到了,
m.hetushu.com.com在房门口叹息一声:“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可人儿!乌黑乌黑的长发用银簪子别着;乌黑乌黑的眸子被睫毛遮着;红通通的小嘴巴撅着,细溜溜的水蛇腰扭着,待头饰一拿,通身衣裳脱去,在奚伯荪枕边呢喃燕语,低吟浅笑,乖乖巧巧,妖妖娆娆,这位通晓唐诗宋词的老新郎通体全酥了……叶雨兰漂亮,漂亮女人难耐寂寞。两年后,奚伯荪的虎狼精神全无,纵然是鹿茸加虎骨酒也支撑不住时,叶雨兰寂寞了,她毕竟是“琵琶仔”的来路。
这种古怪的格局竟固定了下来。他与她分开睡了。她仍睡在卧室里,他则让用人在书房旁的一间屋里支了张床,每晚念罢书后,独自睡在那里,和他的古玉为邻。
汕头市南边,与名胜岩石隔海相望之处,住了不少富贵人家,其中有一座院落格外气派,里面的房子都是屋脊两头翘的。屋前屋后长满又高又粗的苦楝子,屋脊上、枝丫上时不时地飞来鹭鸶,这种长腿长脖子一身白的水鸟,在海滩上吃鱼啄虾,吃得嗉子像一条鼓囊囊的捎袋,就飞到沿海人家屋前屋后的树上歇息。它们一停下来便一动也不动,阳光下像一朵一朵白色的花。即便是水鸟,也知道挑地方,起码挑个人不会招惹它们的地方。它们总在这个院落落脚,就是因为这里很幽、很静。
仅此一眼,叶雨兰默默地想着,他就把她心灵底蕴的清寂和寥落全部看去了。
阿香开了大门,一个衣着挺括的男子大步走了进来。他自负而挥洒地随阿香向正房走去,要进门时,目光向侧面一扫,看到了站在廊柱后露出半张脸的女人,眼睛眯了眯,惆怅地盯了她片刻,随即一正脸,大步迈进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