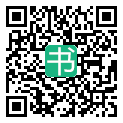第二章 夏夜篝火
我说:“周映,你怎么贴了这么张丑了吧唧的人皮?”
火光把我们都映得通红,所有人都仿佛烧了起来。夏天夜晚,我汗流浃背,对现状表示相当不满,却因为“寄人篱下”不敢开口反抗。
我怀疑他的衣柜里有二十件同样款式的黑色T恤,还有二十条不同花色的大裤衩。
我翻了个白眼,抬手捂住了耳朵。
他手里还是拿着那个蝴蝶风筝,依旧用那副要死不活的表情看着我。
一闭眼,凌野那吊儿郎当要死不活的鬼样子就出现在了我眼前,他叼着根没点燃的烟,在弹我脑瓜崩。
我在楼下一边逗猫一边想着策略,没想出来,反倒是困了。
“你还真别小瞧他。”周映说,“那家伙有点东西的。”
不能杀人灭口,于是,我崩溃了。
我就不应该搭理他。
我拍拍屁股走人,然后听见身后凌野喊:“张三!捕蝴蝶吗?”
但很显然,我脆弱的神经不允许我继续在那里逗留,下一秒我就演技拙劣地侧了一下身,躲开了他的触碰。
我不至于因为接个吻就要他负责,更何况,就算他愿意,我还不要呢。
说真的,不是我故意没事找事,也不是故意跟人家套近乎,我是真想学一门手艺,等回去之后,炫个技。现在不都喜欢立人设吗,我也想立个“什么都会”的人设。
而我所谓的“接吻”,事实上也并不是吻。凌野只是将手指贴在了我的嘴唇上,他的嘴唇在我的耳边。照片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正在亲他的手指,一脸的餍足。
我扭头看向凌野,突然发现,他可能也没我想象的那么文盲。
这群“岛民”,个个儿喝得豪迈,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跟酒神似的千杯不醉。
我是有点意外的,心说这是有人擅自跟我调班?还是说那可笑的“值日”根本就是他们耍我的?
当然,我知道这事不能怪他,是我个人戏太多,毕竟世界上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喜欢纳博科夫,也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对“纳博科夫的蝴蝶”耿耿于怀。
我揣着心思下了楼,一眼就看见了院子里的桌上摆着的饭菜。
我甚至想好了,往这个人物的身上添加一些凌野的样貌特征。
因为这个,我又给他贴了“渣男”的标签。
“啊,”周映了然,“今晚这顿是程哥做的,他醒酒后说你今天刚来,休息休息,他替你。”
我觉得他就是有毛病。
“啧。”我说,“又犯什么病?”
很显然,凌野在这个日记本里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如果日记也有主角的话,那么他一定是重要配角。
我感激地看向了程老板。
更何况,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多少有点与众不同,也可以说有些神神道道的,除了周映,我觉得我没法跟其他任何一个人好好说上三句话。
如果这件事我发在网络上,想必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替我网暴这个人欠嘴贱的臭男人。
“是呗。”周映坐在楼梯上扒拉她的吉他,她曾经是一个挺火的摇滚乐队的吉他手,跟主唱谈恋爱,结果主唱莫名其妙跑了,乐队也解散了,她非要追个答案,结果追到了这里来。
一个男人在门外背对着我们抽烟,周映蹲在门口逗猫,程老板回头看了我一眼问:“不好意思,你哪位?”
我突然怔住,惊讶于他竟然抢了我的台词。
怎么想的?夏天在院子里烧篝火。
因为我听见他对我说:“怎么着?对哪个产生兴趣了?”
突然,有人敲门。
凌野扭头看看我,我拉过椅子琢磨了半天自己该坐哪儿。
好几秒之后,我疯狂翻书,意识到这句话正是出自我此时此刻正在看的这本,而且,凌野还叽里咕噜地说出了那个我听不懂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胡诌的单词。
当我的视线再扫描到另一个人的时候,那个叫凌野的正一摊烂泥一样懒洋洋地坐在桌边的椅子上,还跷着该死的二郎腿。
他说:“纳什么?”
“他是不是对风筝有执念啊?”我问周映,“怎么见天儿在那儿放那个破风筝。”
连着十好几张照片,都是我钩着凌野不让人走,手脚并用,像只非让人宰掉自己的猪。
第一,初印象糟糕。我刚来时他那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实在有些惹人烦。
当然,这句台词不是我写的,是纳博科夫写给自己妻子薇拉的。
我看见凌野半张脸都被火光映得通红,我的脸也跟着烧起来似的。
既然道歉了,态度也还凑合,我大人有大量,准备就此原谅他。
我问周映:“程哥有清https://m•hetushu.com•com醒的时候吗?”
“不吃。”
当时,我坐在周映跟李崇中间,凌野在我斜对面。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我咕嘟咕嘟,没事儿一口,没事儿一口,愣是把自己喝得头重脚轻,一趟一趟地跑厕所。
不过后来,过了很久之后,当我已经不在这个岛上,因为过于思念这里的一切而重新翻看它时,我才意识到,这本日记也可以称为《陈醒打脸手册》。
这三天,凌野像个外卖员,每顿饭都准时送到我门口。
我快步往自己的房间走,决心离精神病远点。
那天轮到凌野值日。
这个日记本是我来到苏溪海岛之后开始用的,专门记录在这里的一切经历,自然也包括在这里遇见的人。
“……不好意思,没兴趣。”我翻着白眼,回去了。
我看过去,凌野在院子里傻子似的扯他的风筝呢。
我挑拨离间:“他看你的眼神好像在看傻子。”
他指了指自己飞不高的风筝说:“我跟这家伙聊天呢。”
我晕晕乎乎地躺在那里时,看见李崇那个天才诗人竟然搂着他向来看不惯的天才修车工徐和。
他还书给我时,还非常做作地说了一句话:“在巴斯克语言中,蝴蝶是misericoletea。”
我僵在那里,有那么一瞬间动不了。
这话说得我就挺不高兴的,但当时周映拍了照片。
周映像往常一样扒拉着她的吉他弦,问我:“你是说你诱惑凌野的照片?”
他换了一件黑色的T恤,还换了一条花裤衩。
她笑了:“那不然呢?快点!”
那个叫邵苑文的,自从我住进来就没见过这个人,他值日那天是程老板替他做的饭。
我问给我透露八卦的周映:“他把这儿当自己家了吧?”
“……”在这一刻,我的母语从汉语变成了无语。
程老板从柜子里拿了瓶酒,过来笑着问我说:“来一杯?”
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着不舒服,他丢过来的每一个眼神我都觉得是染了剧毒的暗箭。
我就不懂了,他竟然还好意思这么说我?但那会儿我喝酒喝得舌头都麻了,跟他吵架毫无气势,甚至还有点大舌头,分分钟就败下了阵来。
我听着他的声音,又盯着他看了好半天。
我突然想起“醉生梦死”——《东邪西毒》里的那壶酒。
他这说的是什么话?我究竟为什么生气,他是真不明白吗?
周映说:“你对野哥挺感兴趣啊?”
我猜测,当时的我应该是羞愤至极的,脸滚烫滚烫的,赶紧拿回内裤,塞进了裤子的口袋里。
那个蝴蝶形状的风筝从我头顶飞过去,呼啦啦的,我跟被传染了精神病一样,竟然恍惚间觉得那是一只真的大蝴蝶,正扑扇着翅膀从我眼前飞过。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什么时候诱惑他了?明明是他强吻了我。”
当然,他从不搭理我。
总之,那时候我觉得凌野是个讨人厌的文盲。
“……姐姐,我一直当你是个耳聪目明的修仙人,没想到,修仙修得脑子不清醒了啊!”
挺潇洒的姑娘,这些人里我最喜欢她。
凌野喝了多少我不知道,但他那时候可能也不太清醒了。
我说:“你教我弹吉他呗。”
他笑着说:“抱歉。”
他这个老板,虽然看起来整天迷迷瞪瞪的,但人应该还不错。
连凌野都能挑逗起我的春心了?
凌野在外面说:“你挂在窗边的内裤掉到楼下了。”
我对凌野是有偏见的,归根结底有两个原因。
“你才是张三!”我回头骂他,“你就一法外狂徒,迟早丢精神病院去!”
但我不能理解,我怎么反应大到了这种程度?
写稿这件事,讲究个缘分,偶尔我跟故事没缘分的时候,就开了窗,趴在窗边进行人类观察。
做好事不留名。
“……”我看向窗户,果然,我的皮卡丘内裤不见了。
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五雷轰顶。
酒鬼的生日,场面会如何失控,可想而知。
最新版的《说吧,记忆》,这是纳博科夫的自传,封面上就印着一个正在翻看蝴蝶标本画册的男孩,扉页上写着“献给薇拉”——也就是他的妻子。
身后,程老板又喊:“陈真!喝酒吗?”
但是生活永远不会让我预判它未来的发展,或许是因为,“生活”这家伙跟我一样好面子,觉得被我预判了会很丢人。
我对凌野是充满偏见的,在我住进“岛”的第一个星期里,我把这个人当作一个讨人厌的https://m•hetushu•com.com浑不懔。
凌野看着我笑,笑得春光灿烂的,特讨人厌。
他手劲儿很大,说真的,按那么几下,按得我挺爽。
我故意拿这本书,里面写了纳博科夫是如何对蝴蝶产生了兴趣又如何痴迷于此的,我试图以此来暗示凌野少蹭热度。
我反锁了门,把自己丢在了床上。
我很少会跟人这么近距离接触,觉得很奇怪,也很奇妙。我嗓子发紧,脑袋发烫,心脏怦怦跳。
“啧,真硬。”他说,“建议你适当多做运动。”
凌野这人说的话,他说十分,有两分是真的就不错了。
我说:“太热了。”
我转身就往回走,凌野说:“不谢谢我吗?”
我听见他说:“未经允许就摸我脸,这是性骚扰吧?”
我呆住了,而凌野丢下这句话之后就继续在院子里放他的破风筝。
中午那顿饭估计大家吃得都不开心,而我恰恰擅长自动过滤不开心的事,所以就过滤掉了今天晚上我还要继续给他们做饭的这件事。
我在某本书里曾经用过这个隐喻。引用纳博科夫在《洛丽塔》里的那句话——如果说洛丽塔是亨伯特的生命之光,那么蝴蝶研究就是纳博科夫的生命之光。
我酒量一般,不过,这个所谓的“一般”得看跟谁比。
周映就笑,一边扒拉她的吉他弦,一边大笑。
有时候我会劝他:“兄弟,记得每年体检。”
照片一张张翻过去,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我诱惑凌野的证据。
我在“岛”的第二个星期,我以为就这么凑合过着,大概等到一个月结束,我会因为交不上稿子,被编辑鞭打而死。
好家伙,真是喝断片了。
紧接着,他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哦!欧阳娜娜!知道!鹿小葵站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一切。
还有那个天才诗人李崇,食材沦落到他手里,可以说很让人心生怜惜,这家伙的厨艺还不如我,纯粹糟蹋食材,做出来的东西实在难以下咽。
周映笑了:“都做好了!你下楼就行了。”
当然,我也没写稿,整天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我就不该来。
比如他脸上的痣。
周映说:“他那是看你呢。”
我冲出去捡内裤时,发现它就挂在凌野的风筝上。
凌野倒是不会对异性或者同性进行什么恶心人的骚扰,但那张嘴也是够欠够贱,我不爱听他说话。
他说:“你怎么那么欠呢?”
至于其他人做的饭,马马虎虎,能吃。
凌野竟然不生气,叼着没点燃的烟,继续放他那破风筝。
正经八百的饭菜,不是我中午糊弄的那种方便面。
“它自己掉出来的,又不是我偷出来的。”凌野在我身后笑,“不过,还怪可爱的。”
狗东西,想赖账。
正说着,凌野拿着他那破风筝又从我面前晃悠过去了。
这小子挺行。
我这个人有时候是很小肚鸡肠的,因为觉得他冒犯到了我的文学偶像,第二天就拿着纳博科夫的书去院子里显摆了,并试图以此嘲讽他一番。
“我想杀了你。”
我说凌野:“你故意的吧?”
却没料到,当我转身要走时,他又说:“你可以骚扰回来。”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我说:“你直接对瓶吹?”
看吧,我这人就是这么肤浅,就是这么虚荣,就是这么诡计多端。
周映就笑:“我修个屁的仙!”
不过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这顿饭是凌野做的,那句“休息休息,我替他”也是他说的。
他还是那身打扮。
我突然又抬起另一只手,干了一件我一直想干但清醒的时候没敢干的事。
照片里,穿着黑色T恤的凌野双手插在他的花裤衩口袋里,他站得笔直,我歪歪扭扭像摊烂泥黏在他胸前。放大照片可以看见,凌野正小人得志地笑呢。
我说:“我有熟悉的按摩师傅,一小时两百块,专业的,不用你操心。”
那天,大家都喝酒喝到不知今夕何夕。
我晃悠着想起来,可是命中注定要丢人——我栽倒在了凌野的怀里。
当我拿着书走开时,听见他大声说:“你就是那无数的小小的箭矢——每支箭都射中了我。”
“几乎没有。”周映说,“不过这不重要,你看他过得多开心。”
不对,肯定不是,看程老板就知道了,我来这么久,就没见他酒醒过。
我们俩几乎鼻尖贴上了鼻尖,他靠得也太近了,近到我觉得他的鼻息都打在了我的脸上。
神经病。
“他?”我说,“他弹m•hetushu.com.com棉花吧!”
我拿着书起身要走,觉得可能这辈子都不要指望着跟凌野交流。
我说:“你读纳博科夫?”
我去找周映,问她:“你还拍到别的照片没?”
可是第二天凌野说他没吻我,都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
我叫陈醒!
“……你干吗?”我被他吓了一跳。
我的手被抓住,那家伙抓得特用力。
凌野拿着风筝,倚在一棵树下。
我跟周映喝了一口,发现人家是真厉害,一口喝进去半瓶,说她一句女中豪杰真的不夸张。
吃撑了的我琢磨着应该怎么去把这件事调查个清楚,我可不想不清不楚地欠他的人情。
我把这句话写在了当天的日记里。
他说:“你有点脖子前倾了。”
总之,第二个星期的周四晚上发生了一件让我,也让凌野都为之感到震惊不已的事情。
别人喝酒碰杯,我们喝酒碰瓶。
火光通天,把凌野照得也好像一团火。
她手里拿着啤酒,一整瓶的啤酒。
说完,我紧贴着走廊的另一侧,躲鬼似的快步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推门进去时,我听见凌野的笑声,然后才发现,我刚刚同手同脚了。
“不了,谢谢。”
皮卡丘内裤的坠落,可以算是我跟凌野关系发生转折的重要导火索。
我说:“你刚才说什么?”
不知道怎么的,我的斗志总是燃烧在这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我说:“常跷二郎腿会得血栓塞。”
我看到照片里大家化身群魔,在院子的各处乱舞,我也不知道大家都折腾什么呢,反正没一个人干好事。
不过,我觉得他肯定是个天才。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因为一般来说,我看不懂一本书,不是书不行,是它太厉害,肤浅的我读不懂罢了。
现在,我觉得自己被凌野的行为冒犯了。
第二,日常手欠嘴欠。我平时生活中虽然是个喜欢呼朋唤友出去玩乐的人,但在交朋友方面是很挑剔的,话要投机,也不能太低级趣味。偏巧,凌野就是跟我话不投机还沉迷于低级趣味的人。
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次跟凌野“亲密接触”,不过他身体的触感我是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后来搂着我脖子,像拖拽一只笨猪一样把我拖到了旁边的躺椅上。
周映跟他说我就是陈醒,今天新来的住客。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如果可以,我希望雷峰塔倒下来的时候直接砸死我,免得我活在这世上丢人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旁边的周映变成了凌野,我看见那张脸那双眼睛的时候还恍惚了一下,迷迷瞪瞪地伸手就往人家脸上呼。
我看着凌野,强压着呕吐感对他说:“你过来点。”
因为对这人没什么好印象,也就不愿意搭理他,大部分时间我就躲在房间里。
在凌野突然靠近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它掉在了地上。
可有些事,它由不得我啊。
这件事的严重性对于我来说,无异于网恋十年奔现时发现网恋对象是仇人。
“人家那不叫放风筝。”周映说,“他说这叫‘捕蝴蝶’,是一种行为艺术。”
凌野往这边瞥了一眼,像看傻子似的看周映。
被他手指碰到的那一瞬间,我浑身毛孔都张开了。
他敲门:“吃饭。”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要弄清楚那天晚上的吻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明明一点都不重要的。可是一想到凌野吻了我他还不承认,我心里就躁郁。
我准备上楼睡觉,却恰好看见倚在走廊窗边叼着烟的凌野。
我问周映:“值日那事儿到底真的假的?”
我这个人向来爱面子,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之外,再没人知道我云淡风轻的天才作家表面下,有一颗收藏卡通内裤的心。这是不能被别人知道的秘密,一旦被知道,要么我杀人灭口,要么我精神崩溃。
他双手手肘搭在窗框上,面朝里,漫不经心地瞥向我。
走廊的窗开着,带着海味的风缓慢地吹进来,把他发质还不错但有点长了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
我说完才十分迟钝地意识到,坐在我旁边拿着酒瓶子往自己嘴里灌酒的是凌野。
蝴蝶样式的风筝,才刚飞起来,就挂在了歪脖子树上。
她说:“走一个。”
“真的啊。”周映说。
阳光打在他的侧脸上,我当时想的是:很快他就会被晒成阴阳脸。
因为唯一的主角,是我。
但我还是听见了凌野的笑声,大白天,让人觉得瘆得慌!
我非常清晰地记得,我就软趴趴地瘫在躺椅上,是他先俯身过来,我们非常近
和图书距离地对视,在我觉得自己快斗鸡眼时,我闭上了眼睛,他吻了我。
人是永远逃脱不了个人特征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本性难移”。那些深烙在个人身上的习惯已经成了抹不掉的印记,就像一个作者的文字风格、遣词造句的习惯,如果不是刻意变化,其实很容易被一眼识别出来。
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凌野这人不像是会读书的,他怕是连纳博科夫是谁都不知道。
我算是发现了,这地方真就没有正常人。
凌野说:“以为你睡着了。”
她直接把相机丢给了我,对我说:“看完不许删,记得要完璧归赵。”
挂了电话,我满腹狐疑,想着如果被我发现他们耍我,我肯定是要理论一下的。
我扭头说:“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对我造成了性骚扰?”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了,毕竟喝得真有点多。但是那个夜晚,我确实干了一件让我恨不得去死的蠢事——我跟凌野接吻了!
我所谓的低级趣味,包含很多层面。
不想挨着他,也不想看着他。
据我观察,住在“岛”里的人都爱自称岛民,而且这几个家伙在这里住的时间最短的是那个叫李崇的,自称是个流浪诗人。
回去的路上还撞见了又叼着没点燃的烟在瞎晃悠的凌野,我看见他就狠狠瞪他,他在我身后跟周映说:“怎么我没亲这家伙,对这人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吗?”
“找凌野教你去,他也会。”周映说。
“唉,不好意思,我刚刚一直在工作,忘了下去做饭。”虽然并不是这么回事,但借口还是要找的,而且还得冠冕堂皇一点。
但我不要是一回事,他不承认又是另一回事了。
“是吗?”凌野说,“我以为就只是影响精|子形成呢。”
我用手肘怼旁边的人说:“哎!你看那两人合计什么呢?”
那一天,我顶着酒后疼到炸裂的头,化身名侦探陈·柯南·醒,打开了周映相机内存卡的文件夹。她在那个晚上拍了好几百张照片,绝大部分都失焦了,由此可见,她也喝得挺醉的。
“琢磨什么呢?”周映问我。
这地方究竟有没有正常人啊!
没料到,他这人,戏弄别人很有一套。
凌野弯腰把书捡起来,重新递给我。
因为我很喜欢的作家纳博科夫是个酷爱研究蝴蝶的人,我曾经珍藏在手机里的一张照片就是他拿着个捕蝶网愉悦地在草丛中捕蝴蝶。
我跟周映说:“你看着吧,不出半年,这人准疯。”
不过,有时候遇到一些跟自己气场不合的人,偏偏就可以激发一些平时不会有的灵感,于是我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决心等初稿完成后,在整个故事线里加入一个角色——一个阴损狡诈甚至还带了点变态色彩的反面角色。
我擅自给程老板编了个刻骨铭心的故事,写出来的话,怕是又会有人在网上骂我矫情。
不过,我曾经在看他的书信集时非常刻意地把这句话给记了下来,还发了条微博说:以后我跟心上人告白时,就要说这句。
说起来,我长这么大真的很少因为什么事觉得困扰,也真的很少记仇,唯一牢牢记得的就是网上那些说我写的是厕所读物的家伙,我记恨他们。
凌野说我:“你有毛病吧?”
当我得知凌野已经在“岛”住了三年的时候,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想熬死整天酗酒的程老板,然后顺理成章地继承这间青旅。
我坐在凌野平时坐的那个躺椅上,鸠占鹊巢,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
我对诗人没有偏见,但李崇的诗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
所以那顿饭吃得我特别心虚,心虚到一口气吃了三碗饭。
我用手指,使劲儿抠了他脸上的痣。然后,我就被凌野弹了脑瓜崩。
但因为我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凌野值日的时候,所以没吃过他做的菜,于是我就真的听信了周映的话,以为那天替我值日代我下厨的是程老板。
他的对面,更不坐。
那天程老板生日。
那之后,因为觉得丢人,我三天没从房间里出去。
我跟凌野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是在第二个星期。
这事儿对我来说不重要,毕竟我又不是来交朋友的。
但是等他走了,我还是会偷偷把饭菜端进来,吃完之后把空的餐具放回门口去。
凌野手劲儿挺大的,我当时就蒙了。
“毛病!”我说我自己。
另一个叫徐和,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站在青旅院子外面背对着门口抽烟,我保守估计,他一天得抽一盒,搞不好苏溪海岛上仅有的那几个小超市的所有香烟都被他一个https://m•hetushu.com•com人买去了。
“饿死你算了。”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那颗不起眼的痣让他看起来又笨又丑,但过了没多久,我竟然觉得那颗痣变得尤为性感。
“那今天晚上……”
那天晚上,程老板非要在院子里搞篝火晚会——所有人围着篝火喝啤酒。
凌野凑近了我。
所以,那天我很快就发现了猫腻。
后来周映给我描述:你们俩一块儿站起来的,凌野没碰你,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一根手指头都没碰你,是你主动往人怀里贴的。
而且,周映教我弹吉他,肯定不能收费,我出了这个岛,上哪儿能找到这么厉害还免费的老师去!
人家一口喝半瓶,那我肯定也不能输啊!
我现在充分理解了为什么懒猫爱晒太阳睡大觉,我现在就是一只大懒猫。
我知道,我的行为十分可耻,但我就是这么个烂人,谁能怎么着我呢?
凌野的厨艺是有特点的,我形容不好跟其他人的区别,但只要吃过我就能感觉出来。
至于来得时间最长的,除了程老板,就是凌野了。
我对凌野的排斥原因又加了一条——我讨厌他用“捕蝴蝶”这个意象。
我觉得我跟周映也没法做朋友了,她根本就和凌野是一伙的。
他突然凑过来,手指落在我的脖子上,用力地按上我的某一个关节。
事后想想,我恨不得拉着凌野同归于尽。
周映他们都过来了,五个人一起吃晚饭。
他叼着烟笑了一下,笑得眼睛微微眯起来,看着就不怀好意。
后来我琢磨了一下,那程老板都醉成狗了,你把猫粮递给他,他都能直接扔锅里炸,怎么可能好好地做出那么一桌子饭菜来。
“再说吧。”我拿过她的相机,迫不及待要打开寻找证据。在这短暂的几秒钟里,我甚至想好了如何嘲讽凌野。
我来这儿一个多星期,除了邵苑文,跟每个人都见过,但并不是和谁都熟悉。
毕竟,我这人虽然厨艺不行,但嘴巴刁得很。
另外,我记得很清楚,我伸舌头了,然后整个人都麻了。
凌野吻上来的时候,我整个人晕得不行,我觉得他的嘴唇都是烫的,而且有点干,很想建议他每晚睡前涂点润唇膏,我可以给他推荐好用的牌子。
不是因为书没劲,只是因为阳光太舒服,很难不睡觉。
我走过去,想着先不理他,却没料到,当我经过他面前时,他突然伸出长腿挡住了我的去路。
但很快,周映拿出了我诱惑凌野的证据。
离谱的是,这位姐的相机没电了,我抠出内存卡,小跑着回了房间。
程老板搬出两箱冰镇啤酒来,每个人手边都放了三瓶,我真的很担心他什么时候会酒精中毒。
我翻了个白眼,又给这人贴上了“低俗”的标签。
我不是什么纯情小天使,十几岁的时候就因为看了部电影太痴迷男主的身材,半夜想着人家流了一枕头的口水。但我也没想过要在这种地方跟一个我很讨厌的人接吻,这对我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让我觉得人生无望死了算了。
说着,我立刻站得笔直,让他知道什么叫体态大师。
我瞪他:“你才脖子前倾!”
我觉得肚子特胀,脑袋特晕,思维特缓慢,很担心一张嘴就吐出来。
但我无心管别人做了什么丢人的事情,一心想要找到凌野和我接吻的证据。
众所周知,现在是法治社会,即便苏溪海岛是个地图上都难找的地方,当地也还是有派出所的,凌野叫我几回“张三”,我不至于真的去当法外狂徒。
我知道,是我轻浮了。
我愤怒地往楼上走,又听见他说:“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望之火!”
我确实差点就睡着了。
还行为艺术?
来“岛”一个星期,大家的厨艺我基本上都领教过了,程老板厉害,可以说是岛民中的厨神级人物,当然,前提是他在给我们做菜时是清醒的。
我自然不信他没碰过我,那种接吻的实感太强了。
海那边吹来的风直接透过毛孔灌进我的身体里,把我的血液都给惊得翻腾起来。
不过说起这个邵苑文,我发现院子的黑板上他的名字已经被擦除,想必是已经走了。
走廊很窄,平时两人通过刚好,他一抬腿我就无路可走了。
这时候,菜已经都端上来了,电饭煲就在旁边放着。
他的旁边,不坐。
行吧,或许我真的诬陷他了,但他也骂回来了,我们还是互不相欠的。
我手里第二瓶啤酒已经见了底,这是我酒量的巅峰,一般来说,我喝完一瓶就倒了——这在我朋友圈里,酒量叫一般,不叫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