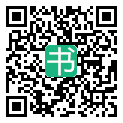第九章 钦赐世子妃
你这样的人呀,哪家姑娘会不喜欢呢?
阿茕站在人群里,望着那个身影怔怔发呆,不曾感受到人群中已有一道毒蛇般的目光将其牢牢锁定,直至镇西大将军人头落地,那道目光方才从她身上撤离,如同一尾潜入水的鲤,消失在茫茫人海里。
阿茕这一番话教白为霜感慨良久,一时无语的他,只定定道了句:“你倒是用心良苦……”接着竟二话不说,便将阿茕打横抱起往床上丢,戏谑道,“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咱们现在就成亲如何?”
阿茕所不知的是,敲门者正是多日未与她相见的陆九卿,他此番前来,不是为别的,而是求白为霜让他再见景先生最后一面。
“哈哈哈……”反客为主的阿茕却在这时一把抱住了白为霜,“我是说真的呀,你长得这么好看,哪怕真是个姑娘家我都会喜欢的呀,可我一无显赫家世,二又身负血海深仇,又岂敢肖想你这等天之骄子,既然如此,倒不如调戏调戏你,多多占些便宜。”
阿茕这番话说得决绝,小豆芽无从插话。
他将重音都压在“成亲”二字上,又是贴着阿茕耳朵说这话,听得阿茕老脸一红,才想着该如何扳回一局,屋外便传来了敲门声。
余音消弭在一声“噌”的拔剑声中,长剑插入血肉中的闷响顿时传入阿茕耳中,她猛地一回头,却见小豆芽面色苍白如纸地趴在景先生身上,他嘴唇在不停地张合,只是重复着那两个字:“快走!”
见状,景先生也只是笑意盈盈地瞥了小豆芽一眼,说出的话却不似他眼神那般无害,直叫人心头发颤:“不过是养的一条狗罢了,还真以为我舍不得杀你?”
一
景先生对自己犯下的事供认不讳,却无任何悔改之意,只嘲讽一笑道:“我并不是输给你们这两个黄毛小儿,而是输给了他。”
凭这道圣旨来判断,能够猜测出,白为霜将所有的功都堆在了阿茕身上。
醒来时首先映入阿茕眼帘的是一树青翠欲滴的绿叶,再然后,便是小豆芽那张阴鸷的脸。
阿茕都不知究竟是该点头还是摇头,她又岂听不懂这样的话?只是真相太过残酷,她宁愿真听不懂……
阿茕越发不知该如何作答,只是止不住地流泪啜泣。
而那辆本该前往梅城苍家的马车,却走向另一个方向。
他一反常态,格外聒噪,一会儿问阿茕饿不饿,一会儿又问阿茕渴不渴,见阿茕从头至尾都无任何反应,他甚至还以手指头戳了戳阿茕的肩,阿茕不甚烦闷地抬起眼帘瞥了他一眼,却见他以食指沾茶水在桌面写了个“陆”字。
苍家的夜宴设在次日戌时。
景先生虽未确切地说明那个“他”究竟是谁,阿茕却已猜到大抵是指陆九卿。
陷入往事中的阿茕泣不成声,直至哭得再也流不出一滴泪,方才嘶哑着喉咙恳求白为霜再留给她一点时间,待到她埋葬好芸娘,便任凭其发落。
看着阿茕脸上错综复杂的表情,小豆芽心中顿生报复的快|感,他笑得嘴角几乎都要咧到耳根。
阿茕如今尚在他手上,故而他底气足,知道白为霜不会不顾阿茕的性命与他相缠斗。
“……”
不过他倒也没给阿茕任何说话的余地,忽而璀璨一笑,道:“不过你也无任何拒绝的余地,圣上都已赐婚了,不论如何,你都将是我的世子妃。”
“有趣,有趣!”景先生听罢不禁仰头大笑,“小霜霜你可真是一如既往地有趣呢,我都舍不得杀你了。”
突遭此变故,景先生倒是从容淡定,眼中波澜不惊,甚至连眼皮子都不曾动上一动。
而此时小豆芽的表情根本就不知该用悲来形容,还是该用喜来形容,他先是垂着眼帘喃喃自语:“你怎么就往回走了呢?果然还是在乎我的罢……”再然后又有一抹悲戚自眼底划过,“你为什么不走?明明都叫你走了呀,还留下来做什么?”
她才走进闹市,便看到一堆人疯狂往北街菜场跑,不明所以的她随手拉了个人询问一番,方才知晓,原来是当今圣上要斩杀镇西大将军。
白为霜自然一脸茫然地摇摇脑袋。
事已至此,她对胖童子是陆九卿的人有了七八分的把握,也只有他是陆九卿的人才能解释得通那一系列古怪事。
景先生却一如从前,甫一见到阿茕便道:“多年不见,小阿茕竟出落成了这般水灵的大姑娘。”
白为霜面上无悲无喜,只道了个“好”字。
“要不要我再告诉你一件更残酷的事情呢?”
阿茕不知他究竟有何意,率
和*图*书先跳入那尸坑里。
小豆芽话音才落,便又笑了起来,这一笑几乎叫阿茕全身汗毛都立了起来,因为她正看到小豆芽笑容诡谲地拿着铁锤和一根铁锥做捶钉的动作。
阿茕脸还被他捏着呢,怕是一说话就得流口水吧。
好不容易才稳住心神的她颤声道:“我这是要嫁给谁?”
阿茕缓缓吁出一口浊气,本欲与白为霜告辞,却忽地脚下一软,整个人往前一栽,便再无任何意识,最后的最后,只隐隐约听到一声又一声急切的呼唤:“阿茕!阿茕!阿茕……”
他这么一说,倒成了阿茕自作多情了。
之后的日子阿茕都在云阳山上度过,与明月山一样,云阳山上亦有景先生的别苑,阿茕的日常起居皆由从前杏花天上那胖童子来照料,与其说是照料,倒不如说是监视。
白为霜丝毫不给阿茕置喙的余地,倒是说了个不容辩驳的理由,他道:“本王是这楚地的君,自要妥善处置这些不幸丧生的子民。”
小豆芽死了,最终还是因阿茕而死。
景先生这一剑刺破了小豆芽的肺叶与心脏,此时的他呼吸已有些困难,却仍笑得像个孩子一样,他道:“如果说,你第一次救我,只是为了使苦肉计,那么第二次,明知我定然会报仇,又为什么唯独放了我,留下我的性命?所以……你先前说的那些话都是骗我的对不对?”
瞧见阿茕惊慌失措地从地上爬起来,小豆芽骤然放下手中活计,忽地朝她露齿一笑:“多日不见,阿琼姐姐倒是越发美艳动人了。”他已知道她是苍家长女苍琼。
阿茕虽对那镇西大将军有所耳闻,却从未见过其本尊,又想着,这等情况下,白为霜定不在世子府,便勒着马往刑场赶。
她的母亲并非完整之躯。
他话音才落,周身气质瞬变,浑身散发出一股冰冷的气息,仿佛换了个人。
然而阿茕此刻却无要与他“狼狈为奸”嬉笑成一团的打算,脑子里混乱得很,一下子在想楚国公那些意味不明的话,一下子又在想,自己当初的猜测果然没错,镇西大将军既勾结外党成立了这个丐帮,企图为害朝纲,那么也就解释了为何不论是那吹骨笛的驱蛇人还是致幻蘑菇都来自南诏国。
此言一出,白为霜面色瞬变,他才欲张嘴说话,却被阿茕抢了先机。
阿茕顿觉不对,一把拽住他的手,才欲说话,便见他神色凝重地摇了摇头,复又指向自己。
待到阿茕醒来已是翌日清晨。
眼看坑中只剩最后几具尸骨的时候,阿茕突然僵住不动了,她两眼湿润地望着其中一具尸骨,喃喃道:“找到了。”
阿茕也不知她今日怎就这么,一点也不似往日那般威风,竟声音颤抖着问白为霜:“站着!别动!你要做什么?”
白为霜理都不想理他,白眼几乎就要翻破天际。
小豆芽仍握着铁锤,一下又一下地敲打着那根铁锥,然后,他阴冷如毒蛇攀爬的声音缓缓淌出,他道:“他本不用这么早丧命,怪只怪,我抢先登上了总舵主之位。”
此言一出,景先生不禁怔了怔,倒是十分坦然地取掉了红莲面具,饶有兴致地问白为霜:“你究竟是如何猜到的?”
景先生依旧保持着微笑,轻轻将软瘫在自己身上的小豆芽推往阿茕身上,以实际行动来回复阿茕。
阿茕虽不忍小豆芽丧命,却也并不代表她就能全然信任这个孩子,她脸上露出警惕的神色,连身上的灰都顾不上拍走,只冷冷问了句:“你是哪里?而你又要做什么?”
那件事发生在十五年前,那日何氏不知因何事而心生不悦,只不过这一次她并未将气撒在芸娘身上,而是借机发挥,说阿茕偷了老爷送给她的首饰。
两名婢子行了个礼齐声道了句:“拜见世子。”相互对视一眼,便捂着嘴溜走了,只余门前僵着身子的阿茕与疾步走来的白为霜。
“别哭,我很喜欢很喜欢你呢,还有,那晚的红烧肉也美味极了……”
阿茕此时不但穿着拖沓的礼服,身上的药力也尚未完全散去,几乎用一步三晃来形容都不为过。
江景吾仰头狂笑三声,拍了拍阿茕的肩,亦随之追上去,徒留阿茕一脸蒙逼地站在原地,轻声嘟囔着:“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阿茕不曾出声,只用一双已然麻木的眼睛望着他。
今日的景先生风流依旧,只是身上所穿的那件绣满血色红莲的黑袍着实灼伤了阿茕的眼。
尸坑中的尸骨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多,阿茕、白为霜以及那列穿着铠甲的士兵不停不歇地统共挖了三个时辰,直至破晓天明,那
hetushu.com.com个仿似无底洞的尸坑方才见了底。
“不知道你个大头鬼!”堂堂楚世子竟被阿茕一句不知道气得爆了粗口,也是相当得不容易。
这些天,阿茕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又拽着那人询问了一番,方才知晓,原来这镇西大将军勾结外党,意图扰乱朝纲,故而斩立决。
阿茕与公鸭嗓交代了几声,便提着裙摆踏上马车。甫一推开车门,便有个熟悉的身影跃入眼帘,她瞪大了眼睛,本欲惊叫出声,那人却用尽蛮力将她往车内一拉。
阿茕自是想不到白为霜会主动跳下尸坑来帮自己挖骨,稍稍一愣,便道:“不必了,我自己可以的。”
纵然如此,白为霜仍是一见面便认出了他,直言道:“才多久不见,景先生竟变得无法以真容见人了?”
随着她声音的落下,白为霜连忙朝她所说的方向望去,一眼并看不出任何异常之处,阿茕却红着眼圈抱住那具狰狞可怖且沾满泥土的白骨,不停地重复那句话:“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最后一个字尚未落在,他便拽着阿茕往前一拖,大声吼道:“还愣着做什么!快走!”
白为霜动作温柔地替她盖上被子,拍了拍她脸蛋,仍不忘调戏:“这次就勉为其难地放过你。”
那时,阿茕不过是个五岁大的孩子,既不曾做过这样的事,自然是被吓得不停地哭泣。时隔太久,即便是当事人阿茕都已记不清多少细节,只记得那时何氏死咬住她不松口,非要将她送去受家法,芸娘跪在她脚下磕破了头都未能换来她一句饶恕,后来还是芸娘以自己的双手换来阿茕的安稳。
她挣扎着跑开,小豆芽已然奋不顾身地抱住景先生。
正如阿茕与白为霜所猜测,陆九卿与景先生乃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只不过景先生的母亲乃是南诏国当今的女皇,他所做之事在大周子民看来天理不容,可从在他的角度来看,不过是替自己母亲扫清障碍,他母亲野心勃勃,妄图效仿前朝,以邪教为害大周朝纲,景先生不过是一颗实现南诏女皇野心的棋子罢了。
白为霜嘴角一扬,生生扯出个轻蔑的笑,他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本王便是那黄雀。”
“很简单。”白为霜的声音里依旧不含任何感情,“可我为何要告诉你?”
阿茕不必再回答先前的问题,小豆芽便已回答:“铁锥钉头,瞬间毙命。”
白为霜眼中的柔情随着她这话的落下,顿时转为鄙夷,很是嫌弃地瞥了她一眼,颇有几分无赖地道:“你觉得呢?”
既然阿茕都已这么说,白为霜也再无与她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结的必要。只见他右手一挥,便有一群同样穿着铠甲的士兵蓄势待发,从暗处走出。
这个问题才从阿茕嘴中溢出,守在门外的两个婢子便不禁相视一笑,那个与阿茕更熟一点的笑盈盈道:“苍姑娘刚醒来,不知道也是正常的,这次您又立了大功,圣上龙颜大悦,又觉赏您金银财宝太过俗气,索性下了道圣旨,给您赐了个婚。”
阿茕睚眦欲裂,一个猛冲便又跑了回来。
也不知究竟是被阿茕这无所谓的态度所恼怒,还是真被阿茕戳中了什么心事。他瞬间敛去依旧挂在面上的笑容,咬牙道:“你倒是什么都不在乎!”
阿茕再次醒来已经是翌日午时,令人感到惊恐的是,她竟发觉自己躺在一间红得刺眼的婚房里,被褥是红,帷幔是红,甚至连墙上都贴了大张大张艳红的壁花,结合先前的记忆,她只觉一股寒意顺着尾椎骨直往脑子里蹿,一个荒诞又离奇的念头无端占据了她所有的思绪,她……该不会是死了,有人在替她做冥婚吧?
阿茕听闻只是冷冷一笑,心想苍家消息倒是灵通得很,她自不会拒绝苍家的盛情邀请,此番不但要去,还需盛装而去。
阿茕失望至极,转而将请柬交由胖童子,由他代替陆九卿参加自己的婚宴。
此时的阿茕只觉太阳穴那儿突突跳得疼。
小豆芽像是在竭力克制着什么,停了半晌方才又道:“所以,对我也是这样,从未用过真心可对?”
这样的日子也不知究竟过了多久,终于在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白为霜寻到了此处。
这个问题一出,原本嚣张不可一世的阿茕瞬间便愣住了,她足足沉默了一瞬,方才笑容可掬地道:“既然你都知道,又何须多此一问?还有,麻烦你不要将背叛这等高帽盖在我头上,我对你从来都只有利用,既然只是利用,便无所谓的背叛之说。”
这婢子倒是不面生,阿茕记得是白为霜府上的,从前只要和图书她住世子府,便是由这个婢子来打理生活起居。阿茕与这婢子倒也算有几分熟悉,耐人寻味的是,从前这婢子虽也算手脚麻利却从未这般“贴心”过,始终与她隔着些什么,也就是说,一直都将她当外人来看的,正因从前如此,她才越发觉着这婢子今日有些热情过头了。
说不感动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从一开始她就误会了白为霜。
阿茕一时间闹不明白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仍是跟在胖童子身后走,再然后便看到这样一幅画面。
阿茕很是无辜地摇了摇头:“不知道。”
凭良心来说,白为霜这次的眼神着实温柔,一点也不冻人,饶是如此,阿茕仍是止不住地打了个哆嗦。
五日后,又有一道圣旨自帝都传来。
至此,这件横跨十五年的吸血案方才真正完结,到此告一段落。
“这里?”小豆芽一挑眉,“云阳山,埋葬你父亲的地方。”
阿茕此时住在有凤来仪客栈,但是自打她回来便再没见过陆九卿的身影,而今整个客栈都是交由那公鸭嗓来打理。
正如她所预料,白为霜而今果然身在此处,而刑场上跪着的镇西大将军也莫名令她觉着眼熟。她揉着隐隐发痛的太阳穴,仔细回想了一番,方才想起,她为何会觉镇西大将军看上去眼熟了,撇开脸不说,镇西大将军的身形简直与她当日在丐帮祭典上看到的帮主一模一样,再结合圣上给其安的罪名,她莫名地觉得浑身发凉,很多从前都解释不通的东西瞬间便无答而解了。
阿茕无从辩解,小豆芽笑得越发璀璨:“我就知道,你定然是在乎我的……”
胖童子这么一做,阿茕即刻便猜出,他定然是陆九卿的人。
她才欲转身踏入房门,身后便传来一阵咳嗽声。
她才推开门,便有两个婢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颇有几分慌张地道:“苍姑娘,您怎突然跑出来了呀,大夫说您这是个太过劳累,得多补补多歇歇才能养回元气,您呀,不管有什么事只管使唤奴婢便好,无需自己来的。”
阿茕本就虚弱着,一听这婢子的话,吓得两腿一软,几乎又要晕过去。
彼时的阿茕犹自沉浸在悲痛中,抽条版胖童子在景先生的命令下将其关入建在悬崖边上的那座高楼里。
景先生睚眦欲裂,满脸不可置信地瞪着那从始至终都一本正经板着一张脸的抽条版胖童子,他机关算尽,却是怎么都没料到自己亲手养大的另一条“狗”也会背叛自己。
只是她真不明白陆九卿与景先生究竟有怎样的纠葛,即便是问白为霜,白为霜也一无所知,与阿茕一样猜测他们大抵是同胞兄弟,到头来还是只能说陆九卿太过神秘。
对于阿茕这席话,景先生只笑笑不说话,而后他终于将目光落在了小豆芽身上,颇有几分责怪之意:“我一醒来便瞧见她不在了,还以为你将她偷偷放了。”
这种事不必由小豆芽再次复述,阿茕已然动了怒,紧紧捏着拳头。
芸娘容貌倾城又有一手冠绝楚地的琴技,何氏既动不得她的脸,便千万百计先要毁掉她的手。她倒要看看,一个指骨尽断的狐媚子究竟还能拿什么来勾引老爷!
阿茕说的倒是真心话,她是真喜欢过白为霜的,也知道自己与白为霜之间究竟隔着什么,她看似无赖,实则比谁都要傲气,既知不可能,倒不如直接断了自己的念想。
白为霜丝毫不为所动,他既然敢来,自是早有准备。不待他发出指令,便有一队手持弩弓的士兵自林中钻出,将景先生团团围住。
听到这里的时候,阿茕已然止不住地轻颤,她紧咬着牙关,骤然又放松,无比轻蔑地一笑:“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即便没有你提醒,我也比任何人都清楚。与其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说给我听,倒不如直说,你将我带来究竟有何目的。”
有了江景吾这和稀泥的货,阿茕心中仿佛被人抛下一块巨石,砸得她一时间回不过神来,更不知该说怎样的话来感激白为霜,怔怔地望着他,久久不能言语。
二人皆陷入一种古怪的沉默之中,周遭静得可怕,阿茕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碎裂声,细细去分辨下便能发觉,那是枯黄的落叶被人踩碎的声音,这个声音使得阿茕与小豆芽纷纷侧目,只是当阿茕转过头去的时候,整个人宛如遭到了雷劈似的僵在原地。
“自然是咱们世子大人呀。”说这话的时候,那婢子眼中的羡慕之意溢于言表,俨然一副恨不得代替阿茕去嫁的神情。
她之所以这般信誓旦旦说,只要看到,便一定能找出,并非和*图*书没有任何理由。
这种事无需提醒,阿茕自然是记得的。
整个动作太快,阿茕甚至都未能反应过来,便被人以迷|药浸湿的手帕捂住了口鼻。
彼时的阿茕又岂知晓,何氏用心歹毒,其一开始的目的便是要毁掉芸娘的手。
余下的日子,阿茕便在这样的疑惑中度过,直至今日,白为霜突然“来访”,胖童子方才笑着与阿茕道:“世子来了,姑娘请下楼。”
听到背后脚步声的阿茕连忙转过身来,却一下就对上了白为霜的眼。
躲在他身后的人只温柔一笑:“承认与不承认又有何关系?一切都已结束,我也该离开了。”
人群逐渐散开,白为霜冷着脸与楚国公一同走下高台,步步走向抱着必死决心的阿茕,依旧用那干巴巴,无任何感情的嗓子与楚国公道:“她便是苍琼,这次最大的功臣。”
这个念头才从脑袋里冒出,她便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连忙从床上蹦起,胡乱穿好衣便往屋外跑。
既如此,他便越发有恃无恐,气焰颇有几分嚣张地道:“小霜霜你这般乱来,莫非是想送小阿茕上西天不成?”
此人一副贱兮兮又油腔滑调的模样,不是江景吾又能是谁。
来者不是别的人,而是多年不曾正面相对的景先生。
阿茕仰了仰头,强行压下几欲冲出眼眶的泪水,换上一副淡漠神情与景先生道:“我逃不了,也不准备继续逃,这孩子心口受了您一剑,怕是也活不了了,只求您念在在咱们几年的师生情谊上,容我再与这孩子多说几句话。”
阿茕还记得,白为霜当日曾说过,他认为六年前一箭射穿悬绳人,与六年后用一只歪脖子鸡将她引向尸坑的乃是一伙人,那伙人的目的正是为了揭露景先生,只是无任何人将矛头对准景先生罢了。
阿茕犹自蒙着,没能缓过神来,楚国公已然笑着离开,又道了句他定当将一切禀明圣上,阿茕越发觉着摸不着头脑。
阿茕而今一心只想挖出自己母亲的遗骨,并未在意这等小事,况且即便是在意了,也无从反驳,便就这般默认了。
“别哭呀……”听到啜泣声的小豆芽声音听上去有几分担忧,“别哭,我很喜欢很喜欢你呢,还有,那天你烧的红烧肉也十分美味……”
……
小豆芽在景先生面前倒是乖顺,只觉垂着脑袋道歉:“属下有错,自当去领罚。”
即便阿茕都这么说了,白为霜仍是一脸紧张,生怕她下一句便会说出拒绝的话。阿茕却笑得像只坏心眼的小狐狸似的眯起了眼睛:“你可知我从前为何总爱调戏你?”
话音才落,景先生方才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就在他转身望向关押阿茕的屋子之际,胖童子已然领着阿茕从屋里走了出来,此时的阿茕与数日前小豆芽丧命时判若两人,她呈西子捧心状捂住胸口,且贱兮兮地浮夸地道:“哎呀,我好怕,要被杀了。”
如今,所有人都露出了马脚,唯独陆九卿依旧叫她看不透。
白为霜见之,亦随之跳下去。
景先生的身份昭然若揭,只是阿茕怎么都没想到,连景先生都是丐帮人……既然他是,那么,陆九卿呢?那个身份成谜又正邪莫辩的陆九卿呢?
对于小豆芽的这个问题,阿茕只觉好笑,反质问道:“莫非你带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说这个?”
这句话中所蕴含的信息可谓巨大,阿茕只觉仿佛有道惊雷自她脑子里炸开,两耳嗡嗡,几乎都要听不清小豆芽接下来的话。
半月后,阿茕身体已无恙,白为霜广发请帖宴请宾客前往他府邸喝喜酒。
圣旨上之乎者也地说了一大通,通俗点来说,就是讲阿茕女扮男装本犯了欺君之罪,却有一腔热血,纵然是个弱女子却有勇有谋,只身潜入乞儿窝,以一己之力破下这等悬案,圣上呢宅心仁厚,就不予追究这欺君之罪,只不过呢,阿茕这七品芝麻官也没得当了。
楚国公前脚才走,阿茕立即便将求助的目光投至白为霜身上,欲开口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料横冲直撞跑来一个气喘吁吁的人,此人满头大汗,头上那顶青玉冠都歪得几乎要垂落在地,甫一瞧见阿茕与白为霜便捶胸顿足道他竟错过了一场大戏,一语毕,又噼里啪啦接着说了一大堆诸如他早就看镇西大将军那货不顺眼了,到头来还真是个卖国贼此类马后炮的话。
他说这话的时候心情似乎很好,以至于掐着阿茕腮帮子的手也松了松,阿茕稍一用力便逃出魔爪,一边气鼓鼓地揉着脸蛋,一边叹气:“你这人好奇怪,怎就不问问我是否喜欢你?”
“喜欢你,勾引你呗!”
此言一出www•hetushu•com.com,阿茕整个人都不好了,几乎就要风中凌乱,足足愣了三瞬,方才推开那两名欲再扶着她的婢子,道:“你们走开,让我再躺躺,我一定是还没睡醒。”
而今再回想起来,阿茕怀疑那些事都是陆九卿授意胖童子去做的,只是她不明白,陆九卿为何要这么做,究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不方便出面,还是另有目的。
马车骨碌碌远去,胖童子盯着那封请柬若有所思,隔了半晌方才叹了口气,与身后人道:“明明好事都是您做的,为何偏偏就不肯承认呢?”
接下来几日,胖童子不曾给阿茕提供任何线索,阿茕被困高楼中也没闲着,一直都在想办法给白为霜与陆九卿传讯,只是那景先生精得很,偌大一座楼中,既无纸墨笔砚也无任何能染色的东西,她纵然有陆九卿送的那只夜鸦也无法传信。
白为霜很是无语地瞪了阿茕老半天,最后泄愤似的在她脸上捏了一把,眯着眼,一脸霸道地问:“你到底想不想嫁给我,嗯?”
那人也不嫌自己聒噪,才噼里啪啦说完一通话,又将不怀好意的目光投至阿茕身上,道:“啧,想不到你还真是个姑娘家,可真有能耐啊。”
小豆芽又怎会给她这样的机会,笑容几乎残忍:“你父亲险些成了总舵主,只不过被我抢先一步上位,事已至此,你该不会还不明白吧?”
再然后便是白为霜进一步,她退一步,不过多时,阿茕便被逼得无路可退。
阿茕面色忽白忽红,江景吾也没瞧出个所以然来,仍在滔滔不绝地道:“这下你可安心了,你能立下这等大功,又有我家小霜霜与小霜霜他爹替你美言,圣上定然不会怪罪你女扮男装之事的!”
早已做好心理准备的阿茕被白为霜这席话惊得合不拢嘴,才准备张嘴说些什么,便听楚国公笑着道:“阿霜已将所有事告知本王,苍姑娘有胆有谋,真真是不输任何男子的巾帼。”
这日,阿茕起了个大早,一整天什么都没做,光是衣服就换了不下三十套,或是太过隆重,或是不够镇压全场,换来换去,最终敲定一件绛紫色的广绣对襟襦裙。
他又笑着道:“听不懂这话是不是?”
前去会客的景先生依旧穿着那袭绣满红莲的黑袍,脸上戴着做祭典时的红莲面具。
奈何白为霜这货向来别扭不解风情,稍有几分尴尬地咳了一声,方才别开脑袋,躲避着阿茕的视线,口不对心道:“即便圣上能放过你,本王也不会轻易放过你。”接着竟红着耳朵,逃也似的疾步走远。
不过,阿茕而今倒是不想解决这些,只想知道她为何睡在了一张婚房似的屋子里。
他的声音缓缓流淌,无端令人联想到那些埋藏在地底的暗河中流淌过的水,他道:“想必你也知道,能用以祭祀的都须是阴年阴月阴日出生之人,而你母亲恰恰好便是这个时辰出生的女子,你以为你爹是真的想将一个娼妓娶回家做正房?别做梦了!他看中的不过是她的生辰八字,她是头一个被寻到的生祭者,故而死得十分痛苦,活生生被人撕开了喉咙,一点一点被吸干血而死的。”
阿茕笑容灿烂,眼睛里泛起涟漪:“你这样的人呀,哪家姑娘会不喜欢呢?”
阿茕几乎都要站不稳,她怔怔地望了景先生许久许久,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想不到您竟藏得这般深。”
时间倒回七日前,小豆芽被杀的那一日。
既无法自救,阿茕便只能将所有希望都集中在胖童子身上。
原来苍家亦得到了这消息,特此赶来请阿茕回去。
阿茕也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父亲与丐帮有关联,只是她从不敢往那方面想罢了。
二
阿茕穿惯了男装,后来虽也穿过一两次女装却都不是这种广袖的礼服,头一次穿上还真有几分不习惯,一番盛装打扮后,约莫又过半个时辰,苍家的马车方才抵达。
在世子府内闷了大半个月的阿茕想亲手将请柬交到陆九卿手上,马车才抵达有凤来仪门前,便听人道陆九卿已离开天水府,凤来仪现由胖童子接手打理。
阿茕心中感慨良多,屋外忽又传来一阵轻微的敲门声。
三日后,宜动土宜入葬,阿茕亲手修葺好芸娘的坟茔,待到芸娘入土为安,方才前往世子府负荆请罪。
这个回答让阿茕眉头皱得越发厉害,小豆芽那副模样分明就是有话尚未说完,阿茕也不急着说话,只冷冷注视着他,静待下文,果不其然,很快便又听他道:“你可还记得你父亲究竟是如何死的?”
总的来说,是个好消息,大大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