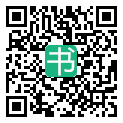第一部
白衣番外 立尽梧桐影,不见故人来
我问一旁随行的绯雪:“是不是城中已预先安排过,怎会有如此多的老百姓前来?”
呵,何止今生今世,来生来世,我亦是你皇甫栖情的人。
为了顺利逃离安氏掌握,她和她的母亲一样,开始无奈地对仇人微笑相迎。我甚至看到了她与安亦辰亲密拥抱,她说要让安亦辰爱上她,从此万劫不复。
那一刻,我心口疼得像刀割一样,而割我的刀上,分明又抹了蜜,让我痛,又让我甜。
再幸运点,或许,她还会注意到誓言下没头没尾的两个字:等我!
我喜欢这一切的美好,可我又清醒的知道,我不该拥有那一切。
我扬眉苦笑,自负孤高出尘,不惹尘埃,不料情丝缕缕,早如茧缚,欲脱无门。
萧采绎应该看出栖情与我之间的感情了,我偶尔去看栖情,都被他暗中遣人或明或暗地推开。他并不欢迎我,更不希望我和栖情在一起。
我救了很多的人,但我不知道,我所救的人加起来,够不够父亲和两个哥哥一场大战中的屠杀。
栖情,栖情并不知道我外出有事。她只看到那片烧成灰炭的草堂,看到我不告而去。
可是,栖情,你忍得我万劫不复么?
解救明州之围进行得很顺利。因为知道包围明州的是肃州萧氏,栖情的外祖家,所以我下令以破兵解围为度,不得穷追。
萧家如此恨我,那么栖情呢?
宇文颉则赶往沧南,利用我推断出的风向,连夜烧了安氏三分之二的船只。
栖情!栖情!
原来他要救的人,就是栖情。她满身是伤,落到了安亦辰手中。
萧采绎死了,栖情一定需要时间疗伤。
我无心理会什么姑娘,随口噢了一声,正准备踏入大门,又听几名侍卫也说道:“是啊,那姑娘好漂亮,比画上的仙子还美很多。小人们这辈子,就没见过这样美的姑娘!”
但不知为何,待要离去之时,我心中还是忐忑,总觉会发生什么事一般,心中一直细碎地闷疼。走到当日立誓的竹园中,誓言犹在。
绯雪格格笑道:“是宇文三公子名气大吧!人家都过来看看怎么个品貌风流,能不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呢!”
我冲过去紧紧抱着她,不敢放手,生怕轻轻一松臂,她便掉头而去,从此再不看我一眼。
一口殷红鲜血,终于吐出,巍巍颤于碎片之上。
我匆匆修了一封书信,交给李叔,让他若见到栖情来找时就交给她。信中,只说有至亲重病,不得不外出一次,少则十余日,多则一两个月,必然回来。
绯雪气跑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栖情,一身素袍,那样苍白孱弱而惶恐惊惧地倚在竹前。
“那么,我让你们给栖情的信呢?”我已止不住自己声音中的恐惧和颤抖。
“她走的时候,吹着个圆圆的东西,声音很好听,可真的好悲伤,听的人都忍不住要哭……”
在那茵茵的草地,我望着栖情如花的笑靥,告诉她,我要走了。
我很想彻底地拥有她,我也第一次有那样强烈的欲望,想在她身上印入我宇文清的印记,但她拒绝了。
父亲眯着眼看我,然后撑着道:“明州平定,为父打算就在越州登基了。清儿你真要走,须得等到为父顺利登基之后。——恐登基之时,有人趁机捣乱啊!”
栖情,栖情,你竟到越州来了?
我知道大哥的性情素来冷冽,不喜玩笑,不由惊出一声冷汗,只得跪于榻前,请求他收回成命。
其中,有不少人死于我所引发的瘟疫。
安氏终于不得不引兵而退,留下一地的尸骸,堆积如山。
但我竟又见到了栖情。
我的心告诉我,我已离不开她。这一发现,让我日日夜夜受着煎熬,常在子夜时痛楚惊醒,遍体冷汗。
我并没有安排人射箭,也无从猜度是谁下令放的箭,但我知道这事的后果必须由我承担,他是死于和我对阵之时!
我只想救人,不想杀人。我喜欢山林里洁净的空气,浓翠的碧色,飘缈的云霭。我愿逍遥避世于山水之间,扁舟弄长笛,心与白鸥盟,凭了医术自在地活着,如同草木,如同山石。世间太多的杀戮和污秽,我不想沾惹。
但意外还是发生。
我心头一阵又一阵的血气翻涌,李婶慌乱地啊啊出声,匆忙摸了随身携的药丸塞入我口中。
宇文府中,自然早备下了我的房间。
“十六七岁,一身白衣,感觉是在热孝里,可她穿着又很华贵……”
我写了封信,将我与栖情的事全说了,请求父亲成全,让我绝足军政与杀戮,以白衣之名与栖情偕隐山林,然后绯雪带这封信回去交差。
竹林悠悠,竹风漾漾,均可见证我们斯日的缠绵。
但他们的这个天下,我并不喜欢。我只要有一片小小的竹篁,与我的栖情相依相伴。
栖情在我肩上狠狠咬了一口,要我承认今生今世都是她皇甫栖情的人。
清心草堂烧了?而在栖情身上,又和图书发生了什么事?她有收到我留给她的信了么?
宇文氏大军的状况,比我想得还要糟许多。
总算,黑赫可汗钦利和她的异母姐姐钦利,待她们极好,衣食住行,都已给予了他们所能给予的最好的。
话犹未了,萧采绎已横刀劈了过来,怒吼道:“你想生生逼死栖情么?”
难道我看错了?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动手打人,还是打一个女人。
我鬼使神差般和她定了个三年之约。
“她说她是华阳山的未亡人……”
我抱了锦盒,徐徐站起,风吹过,胸口的闷疼愈不可忍。抬起眼,看到李婶含着泪又捧了药来,我黯然一笑,摇了摇头,扶住梧桐,忽然手一软,锦盒落地,埙片发出了忧伤的破裂声,碎得更厉害了。
或许,他是对的。宇文氏和皇甫氏那么深的纠缠,我和栖情苦苦痴缠,又能拥有什么样的结果?可我还离得开栖情么?
得与失,原只在一念之间。她以为的得,正是我认定的失;而她以为的失,我甘之如饴。
可我绝不想纠缠到那些红尘俗务中去了。我只想和栖情找个没有战乱的世外桃源,避世隐居。也许我该找机会回去和父亲谈一谈,请求他成全我。他该知道,以我的身体状态,本只适合隐居度日。
如今,我还是在等待,等待她来选择,恨,或者是更恨。
栖情,万劫不复的那个人,原来是我。
栖情那样如烈火般爱着恨着的女孩,冰火两重天,再不知这些日子正受着怎样的煎熬!
听着七嘴八舌的回答,我的心不断地浮着,沉着,寒着,烫着,翻翻涌涌,似要从嗓子口呕出来。
但栖影始终不曾来。
算是白衣的未亡人么?她心中,就当我已死了么?
信上说,父亲在沧南大败于安亦辰之手,身受重伤,希望能见我最后一面。
大红喜贴来自安氏所建的北晋王朝的秦王府。
这里是越州,不是肃州,栖情,离我太远了。但我一定要回肃州去,一定要告诉她,我没有打算抛下她!哪怕踏入萧府大门,被他们斩作肉蘼,我还是要说明白!
我知道,这一切,一定都是父亲和宇文弘的主意。他们一向知道,我缺少的,只是决心和勇气,却从不缺少才干。神鬼道人教我一年,当时就曾告诉父亲,论行兵用策,我是百年不一出的奇才,又曾叹息,如此才干,恐遭天妒,一身之病,只怕也是由此而来,所以不如藏拙的好。
我苦笑,紧按着胸口一步一步拾阶而上:“如果再见到她,立刻引过来见我。”
父亲尚在安氏包围之中,生死一线。我再无选择。
这是我欠她的,而我的一家,欠她的一家更多,甚至根本没有还清的可能。
是的,我只能选择忘却,选择退缩,选择放手。
我伏于她的颈间,无声落泪。
慌忙将酒坛推开,不想让她见我狼狈,却迅速被她若怨若愁的泪光俘虏,我便知这一生再也逃不开她。
我淡淡笑着不理会她的扯淡,只盼着尽快将眼前事宜结束,好去见我的栖情。
栖情果然到我隐居的清心草堂来找我了,犹如在遍地的森绿野草中,蓦然盛开一朵娇艳无比的怒放牡丹,让我心神俱荡。除了她,我再见不到别的。青山绿水,碧树幽篁,尽皆失了颜色。
那一刻,我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心中勉强筑起的堤防一溃千里,尽溶于两人的亲密相拥相偎中。
对月独酌,浇不尽,千古情愁。
浏王已称燕帝,安氏虽然新败,但江北势力依旧强大,安世远只怕也在准备登基事宜了。从明州回越州,一路甚是顺利,所过较大的城镇,四处都是张灯结彩,仿如在一夜之时回到了大燕全盛时的太平盛世了。
我惊痛得五脏六腑都纠缠到了一起。她到底听到了多少?
我揪紧那人衣襟,厉声道:“你们几个见过她的,立刻到府里给我叫人,不管叫多少人,把越州城挖地三尺,给我把她找出来!”
我感激神鬼道人加了后面这句,这些年来,父兄才不致太过凌迫我回到他们身边辅助成就所谓的天下大业。
谢谢你,栖情,从此你便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爱人,甚至比我自己的生命更加珍贵。
李叔连比带划,一点点将我的心扯入深渊。
我竦然惊起。
此时另一名守卫大了胆子又说了一句:“那姑娘说,她今天还来呢!”
苦涩而陌生的疼痛,开始无时无刻吞噬着我的心。
她那样虚软而无力地问我:“你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而我,显然是最不可能带给她幸福的那个。
看得出,萧采绎待她极好,或许,我该放心,并放手。
可我实在没有勇气告诉她,我是宇文清,我是那个你最憎恨的未婚夫婿。
在我这三年的爱情中,始终只是我在等待,等待她来选择,爱,还是不爱。
而我,又何尝不恐惧!我努力地想依从自己的理智离和_图_书开她,可我却无法迈开我的脚步。本想借送走安亦辰强迫自己离开,可这一打算在栖情那欲语还休的焦急神情中瞬时灰飞烟灭。
我看到她惊喜求救的眼神,心痛如绞,生生埋藏的感情,顿时被一道火种点起,让我的心都沸腾起来。
“三公子!三公子!”有部属唤我。我却已失去了气力,一头从马上栽下。
而是时,我发现我成了宇文氏的三军统帅。统兵虎符在我手中,谁也不肯收回:父亲重伤,无法视事;宇文弘也称伤不出;宇文颉忽然变成了才学着打仗的,每一步行动都会问我怎么办;其他众将领,不约而同向我请示着所有大小事宜;明州岌岌可危,告急的公文雪片般飞来。
明明处于劣势的萧氏军队,突然有一部冒死冲向我方阵脚。
随后的许多个日日夜夜,包括父亲登基之日,我都只在自己的院中等侯,等侯一个越来越缈茫的希望。
越州城中,更是人声鼎沸,我竟不知道我自己能那么受欢迎。一路过来,两侧街道,都是人群,如蚁般密麻麻簇拥着。
因为我随了栖情出城,本已性命垂危的萧后更是命悬一线。我尽力施救,却终于失败。看到受尽煎熬的萧后倒在自己跟前,以及栖情充满希冀望着我的脸,悲哀和挫败霎那让我沉痛到极点,连萧采绎打来的一拳都不曾觉出疼痛。
守卫一惊,忙道:“这个可不知道,她一路吹那个东西,一路走着,转过一道弯,就不见了。当时满街都看呆了呢,都说是仙子下凡来了。……公子认得她?”
我依旧四处游荡,行医为生。
“白衣!白衣……”
秦王安亦辰与大燕衔凤公主皇甫栖情喜结连理。
我蹙眉望着嘈杂的战场,一时头疼欲裂。肩头的鲜血越汪越多,已将座下的白马亦淋湿了大片。
李叔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摸出,完整无缺地交还给我,连封口都没拆过。
我本就一直猜测着清心草堂被烧,如果不与萧家有关,便与宇文府有关。
宇文氏手握大权,向来门庭若市,这些守卫们,什么样的绝色丽人没有见过,到底又要怎样的倾城倾国,才能惹得他们这样大惊小怪?
可是如今她即便收到,只怕也是不肯原谅我了。
我猛然冲了出去,冲出宇文府的大门,两侧张望,然后苦笑。
“白衣,告诉我,你只是一片白云,无羁无绊,洒脱无双。”她靠在我怀中,惊悸地颤抖。
他们都说,安亦辰曾在那日出现过,傍晚时换了传令兵的服色,带了一个形容娇小的人影顺利逃出了城。而安亦辰所投的客栈,后来证实了他身畔一直有个女子,就是那个倾倒了大街上无数行人的白衣仙子。
我承认了自己是宇文清,就是要逼死她么?
十余年未归家,我怎忍不去见他最后一面?何况身受重伤,未必就无救;但军中庸医,却未必能救。
宇文弘也受了伤,背部长矛被深深刺了个大洞,正在帐中包裹伤口,一见到我,就冷冷道:“人家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我宇文弘的三弟才识渊博,见解不凡,赶着回来帮我们收尸了。”
我徘徊在出世和入世之间,终于选择了入世。我找到了父亲派出寻找我的部下,告诉他,我会生擒安亦辰,但要先向他借兵。
栖情,我该如何和你解释这一切?你还肯不肯再原谅我?一如不顾国恨家仇,葫芦提地宽恕我的身世,再来宽容我一次?
父亲久有称帝之念,我无法阻拦,悲哀而无奈。但他总算松口让我离去了,我是不是该庆幸?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我按捺住自己的不安,尽量和缓地问着,可嗓音的尖锐,还是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是她的白衣,她是我的栖情。
而宇文弘即行升帐,宣布自己重伤,将领兵大权交予宇文三公子宇文清。
我按紧乱跳的心口,扶了汉白玉的栏杆,勉强平抑涌动的血气,问道:“她说今天还来么?”
灵前与萧采绎成亲……
三年,已足够让她时间长大,让她知道那个关于狗尾巴草的童年誓言,是多么的无稽。何况,那么长的时间,若她遇到了喜欢的男子,只怕已成亲了吧?
我随她和她的母亲去了黑赫,与其说是为她母亲治病,不如说是我想借机将她们平安送至黑赫。若他们能在黑赫安居,我也就放下心了。
从临山到平阳镇,我顺利地将安亦辰生擒,也顺利地将栖情和她的母亲交到了她的外祖家,交到了她常常念叨的萧采绎手中。
而她的炽热和大胆,更让我手足无措。她如此明皙地表达着她的爱意,用眼神,用语言,用生涩而温柔的亲吻。
我本便是你的,若你要来取我性命,也是使得。而且,你可知道,我真的很希望再见你一面。
萧采绎中箭了,不知何处飞至的暗箭,从萧采绎后心要害直直透入!
“既如此”,宇文弘踢走和-图-书为他裹伤的士卒,将一物掷到我的怀中,喝道:“就看三弟如何力挽狂澜!”
父亲身负重伤,被困于越州以南的玲珑镇,安亦渊、安亦辰兄弟联手,将玲珑镇围得水泄不通。宇文弘、蔡禀德在外围试图解围,屡屡失败。
“瓜子脸,眼睛又清又亮,可似乎一直在哭着……”
宇文弘冷冷看我,道:“你如不领命,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和你的皇甫栖情双宿双飞去了。再过得数日,宇文氏上下人等死得绝了,就没人知道你医者白衣是宇文氏的子孙了。”
脱却白衣,披上铠甲,我亲领两千兵马,烧了宇文氏粮草,并在烧粮草时加了些药材,足以让安氏军队星星的疫病,迅速发展成燎原之势。
我知道我该离去了,我不能在这些欲罢不能的沉沦中愈陷愈深,我也无法把一个刚刚十四岁的小女孩的狗尾巴誓言,当作一种真实的存在。
萧采绎身手极好,此时形同拼命,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我所遣的将领,竟然抵敌不下,而据称那萧采绎口口声声要见我,我虽是不想与他照面,竟也被他杀到了跟前。
晋州安氏素称以仁善以御天下,尤以二公子安亦辰最是爱惜声名,御下极严,从不许人欺男霸女之事。但安亦辰听说我不肯去治病时,竟派了人把我强抓过去。
白衣,栖情,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但见人潮涌动,挤挨作一片,再也找不到方才那张面孔了。
我默默摇头。
不仅是刺客,而且是死士,好在我和绯雪身手都不错,挡得一两招,早已侍卫一拥而上,打斗起来。
私心深处,我宁愿是萧家因萧采绎之事一怒烧了清心草堂,至少栖情和萧家可以稍泄怒火。可此时在宇文府见到了李叔李婶,我的心,忽然通透冰凉。
我唇边有些凉,轻轻一抚,却是唇边被咬得破了。
她直接唤了我的本名,显然已不再将我当成她心爱的白衣。
但不管听到多少,我都敢断定,那么多次的猜疑,足以让她猜出我的真实身份了。
我见他那么直白地向我提及了栖情,不由心神大乱。栖情可以接受白衣,却不可能接受宇文清。那层窗户纸,她不敢捅破,我同样不敢。
派将领迎战时,才知是萧采绎拼了命地打了过来。
栖情给了我她的荷包,荷包里装了一根狗尾巴草。
至于父亲登基大典,少了我,绝不会影响什么。
我接了宇文弘的信,前脚才走,宇文弘就派人烧了清心草堂,要二人前来越州。二人虽是我的侍仆,到底也算是宇文氏的人,何况清心草堂烧了,他们也只有回到宇文府,才有再见到我的可能。
栖情,若来了见不到我,一定要等我,好吗?
可如今,我还是避无可避,成了宇文氏大军的领袖之一。
那侍卫显然是逼了嗓子模仿着栖情的口吻。我似看到了栖情清冷而决绝的容颜。
我轻轻抚着栖情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然后刻了“等我”两个字。
解了明州之围,再等到父亲称帝,只恐又会拖个一两个月。栖情,你在等我么?你一定要等我!
终于回到了宇文府中,与先行回到府中的父亲和两位哥哥见了礼,但见他们的创伤早已平复,神采奕奕,看来已做好称帝准备了。
绯雪完全不能了解我的想法,在她看来,我放弃越州的权势富贵在这里清冷度日,是暴殄天物,是对于我才识的浪费。
我木然吞下,却再压不住心头的烈烈如焚。
猛然就想起栖情宜嗔宜喜招惹人的面庞,我心跳一顿,忙问道:“那女子长得什么模样?多大年纪?叫什么名字?”
而华阳山,他们居然回答我说,未找到清心草堂,更未见到我提及的李叔李婶。鹤翎峰的半山腰,有着大片竹林,而竹林前,尚有大片房屋烧焦的痕迹……
幸好是我。
这时我听到了前方有人欢呼,而萧氏军中有人惨叫。
“父亲!”我跪于父亲榻前,告诉他:“我会再去解明州之围。但解围之后,我便要回华阳山。有人在那里等我。”
我没有为难她,几乎在她微笑着请求我的那一刻,便答应了随她去救她母亲。
宇文弘扔给我的,竟是统兵虎符!
“是,我是一片白云,无羁无绊,洒脱无双。”我什么也不敢说,满心惊惶地抱住她,那种即将失去的恐惧,终于让我失控,我紧紧抱住她,将她拥倒在满是杏花落瓣的茵茵草地上,惊慌失措地吻着她,用尽力气地吻着她,用力扳着她娇小的骨架,几要将她揉到自己的骨血中。感觉她越来越热烈的回应,越来越沉迷的陶醉,我的心方才渐渐安定。
我知道萧采绎的性子有些孟浪,更知栖情和他感情极好,甚至远胜她那些皇室中同样流着她父亲血液的亲兄长,却不知他这么疯了般冲来,又是为了什么?
我没有理会他们的接风宴席,借口累了,自顾让下人领我去休息和-图-书。
我心乱如麻,几乎无法应战,三招之后,已被萧采绎劈上肩膀,差点掉落马下。众将一拥而上,护回了我,和萧采绎激战。
我几乎是毫不犹疑地请求:“请不要离开我,否则,我将万劫不复!”
美丽的珍珠大草原,细细吹拂的绿色的风,唳鸣而过的黑色飞鹰,还有那黑发随风飞扬的漂亮小女孩……
或许,她是对的,除了承诺,我几乎什么都没能给她。
从那一日起,我便知道,我开始沉醉,沉醉于她的笑靥如花,轻嗔薄怒,再不忍见她天真清澈的瞳仁,布上哀伤凄惨的阴霾;而当她泪眼迷蒙靠上我的肩,我更不想推拒。
“我该叫你宇文清,还是叫你白衣?”萧采绎指刀向我,形容凶狠,浓眉之下,一双怒目几要喷出火来。
我苦笑。
萧采绎死了,萧家隆重举丧。其中前大燕衔凤公主皇甫栖情以妻子之礼守丧哭灵。据说,栖情在萧采绎棺木前截发自誓,与萧采绎结作夫妻。
暄闹之中,我恍惚听到有人喊。那声音熟悉而凄怆,悲恨而忧伤,竟然像是……栖情?
我回过身,打算回府去牵马,却被门前守卫拦住,带笑禀道:“三公子,昨天这时候,有过一位姑娘来找过你。”
虽然满怀心事,心烦意乱,我还是决定等回到越州,待父亲登基大典完毕后再回去找栖情。
我默默在院中的梧桐树下徘徊,静悄悄地等待,等待那清冷而悲伤的身影出现,哪怕挥来的,仅是一柄利刃。
因为我不仅仅是医者白衣,我还是宇文清。
当梧桐叶最茂盛时,有人送来了一张喜贴和一只锦盒。
我不顾场中打斗正酣,急急奔到方才隐约看到栖情的位置,细细查看。
直到我伤势基本平复,肃州的暗探终于把消息传来。
我本想带了安亦辰回越州,从此离栖情远远的,或许,会对她更好。
“相信我,我会处理好一切,与你比翼天涯,双宿双飞。你什么都不要想,只须记得,我是白衣,皇甫栖情的白衣,好吗?”
有一种烙印,早已刻于心间。
我知道这对于这么个爱恨如火的女子有多么难,尤其对于宇文氏,那种恨差不多可以让她将宇文家任何一个人挫骨扬灰。但她居然答应了,她哽咽着吻我,呢喃着说:“好,我什么都不想。我只记得,你是我的白衣。”
而她找我,必定只会为萧采绎以及她自己丢了的那片心报仇,绝不会再温柔地唤声白衣,依依投入怀中。
当我第一次见到那个穿了淡碧水纹夹衫,披了天蓝披风的小女孩走入幽篁,我就知道,她是皇甫栖情。她脖颈间挂着的紫凤宝玉,已明白无误地昭示她的大燕王朝衔凤公主身份。
但她对于宇文氏的恨意,显然有增无减,望着她仇恨悲愤的眼,我忽然有了预感,预感我们这段感情,终究会以我的万劫不复告终。
而我在自己房间见到的人,却叫我大出意料。
君羽的死,正在意料之中;萧采绎想处死安亦辰,也在意料之中;而我意料之外的,是栖情居然会去救安亦辰。
狗尾巴草的誓言,被她用岁月磨成了真实的存在。
李婶端来的药热了又凉,凉了又热,我始终不曾吃。
我把我在华阳山的隐居地址留给了她,让她选择,找我,或者不找我。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她肯放下她心中的仇恨,不去穷究我的一切,只是单纯地喜欢我,接受我。
绯雪又来找我了,要我去越州帮父兄成就大业。我便知道,一回华阳山,父亲很快会派人找过来。
除了沉沦,我别无选择,哪怕就此堕入地狱,不得轮回。
当她为我洗衣落水,满脸欢喜地换上我的衣袍,温柔而霸道与我亲吻时,我想到了天长地久。她并不介意为我放下所有,哪怕我只是个布衣医者;而我有什么不能放下的?
我必须尽快和父亲说清楚,处理好一切,与她比翼天涯,双宿双飞。那将是我唯一给给予她的。
我用轻功从兵力单薄处的城墙越过,从伏于城外的宇文氏暗哨处取了马,紧跟着栖情而去。我担心那么远的路栖情会出事,也担心安亦辰会趁机抓走那个只顾自己同情心泛滥的傻丫头。但我却清晰地听到了栖情明白无误告诉安亦辰,她从十四岁那年就开始喜欢我,一直喜欢着;我也听到了安亦辰的警告,这个聪明人,已经料到了我背后必有着复杂的身世背景,其中最可能的,就是与宇文氏有联系。
我一向病着,如果不是父亲将我送入山寺疗养,千方百计找来名医医治,我不可能活到现在,更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那许多的名医,成就今日医者白衣的名声。
我很想辩白,那一切与我无关,我只是白衣,医者白衣而已。可我又如何去否定我的姓氏,我的血缘,以及父兄对我不绝如缕的亲情!
“她的头发特别短,可不知怎么弄的,看来特别顺眼,很漂亮……”
叫她该如何想?叫她该如何想?
我忙扭过头来寻找之际,似看到一张惨白的熟悉面容一闪而逝。还没来得及在人群中细找,已见十数道黑影迅速飘过,竟然是刺客!
打开锦盒,是眼熟的埙,经历了大火的煅烧,泛着清亮的釉光,却已破裂成许多瓣,如同被生生摔裂的心。
守卫多半听过我性子和顺的消息,所以开始和我说话并不拘礼,此时见我面色可怕,顿时吓得只敢连声应是。
我没有抵抗,因为很好奇这个真实的安二公子到底是怎样的人,又是怎样的病人迫得他居然违背一向的原则,连我都抓。
我知道,她爱我,一如我爱她那般深沉。
我早有过誓言,这一生一世,甚至来生来世,都是皇甫栖情的白衣,不离不弃。
为了私情,眼看着父兄家人惨死眼前?
我心下难过,轻叹道:“大哥,事情还没糟糕到那个地步。”
华阳山的未亡人?
栖情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和活泼,得空便邀我四处游玩。
绯雪的执拗让我由无奈渐渐转为烦恼,当她猜出我为栖情痴狂并辱骂栖情时,我打了她一个耳光。
栖情推醒我时,我才知自己竟醉了。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栖情,这将是我一生的誓言。我的一心人,只有你,唯有你……
立尽梧桐影,不见故人来。
大战初定,我在明州边疗伤边整顿军队,又暗中遣人前往肃州以及华阳山打听萧家及栖情消息。
只可怜了两旁的老百姓,立时兜头遇一场无妄之灾。
我忽然窒住。
笑容倏敛,她先是愕然,然后哭得像给抢了糖吃的小女孩,请求我,不要走。
竟是李叔和李婶!
“她……她现在在哪里?”我怔忡半天,抓住其中一个守卫的肩促问。
我看得出她对于宇文氏的仇恨,甚至看得出她对于我的仇恨。她憎恨着整个宇文氏,连带着憎恨从未见过的我。我相信,离开了宇文氏的掌握,她早把那纸婚约视同敝履了。她那样不羁而骄傲的个性,注定了她会勇敢地追求自己所需要的幸福。
何况,随之而来的萧采绎之死,她不可能不知道他是死在我手中!
父亲宇文昭,杀了她的父亲,占了她的母亲,将本来属于皇甫氏的王朝,变成了他的一统天下。而豆蔻年华的小姑娘,莫名其妙就成了我的未婚妻子。
安亦辰走了,我看到了栖情的害怕和无助;我相信她一转脸看到我时,也看到了我的害怕和无助。
她会离开我么?
但绯雪刚走,我又收到了大哥宇文弘的信。
我下定决心,若父亲同意,固然是好;若他不同意,我即刻带了栖情远走天涯,想来她同样地痴爱我,纵然舍不下外祖家,终究也会随我而去。
安亦辰显然于她有意,而她显然只钟情于我。事隔三年,我是否能确信,她的确已爱上了我?
守卫已经不敢乱说话了,细想了想,道:“对,我们本来问那姑娘要不要帮她通传了好在府里住下的,那姑娘说,‘不必了,我明天再来找宇文清’。”
可我还只是等待着,默默地等待着。
而我,也要给我自己一个希望,忘却的希望。有三年的时间,应该足以使我忘却曾有过这么个小女孩,让我痛,让我甜。
而我只有待父亲那边事了,才能再无牵挂地回到她的身边,任她处置,哪怕要杀要剐,要打要骂,或将我一世囚禁,我都由得她。
是的,栖情,我知道你已猜到了我是谁,可是,不要离开我,可以吗?我从不曾那么激动过,除了无法自制地亲吻,我丝毫不敢放手。
自从父亲上山告诉我,他已为我聘下大燕最美丽最尊贵的衔凤公主为妻,让我尽快随他回京打理军政之事后,我就悄悄下了山,一路掩饰行踪,只以行医为生,躲避着父亲和家人的耳目。
栖情!
窥伺那群刺客身手,颇有些像萧家的手段,只怕是给萧采绎报仇来的。
本来,她是天之骄女,该在父母翼护下洋溢她最美好的热情与纯真,而如今,她却在无数的算计和不尽的追杀中被迫长大,被迫褪去眸中最闪亮的童真和稚拙。
我想,以医者身份做这等丧尽天良之事,我必遭天谴。
但他们坚持要用安亦辰向安亦渊换回皇甫君羽。我一直觉得这个主意很愚蠢,但没有人听我的。栖情也不听,我却能从她的剪水双瞳中看到恐惧,害怕我一去不回的恐惧。
但总算,我救出了父亲,并成功将控制住他的伤势,救活了他。
我绝不敢让萧采绎出事,否则栖情一定不会饶我,又见萧况、萧采络前来营救,忍了痛忙让部属暗中安排,务必将他们父子三人放出去。
可我终究还是要回到华阳山,以白衣的身份,永远伴着她。
我虽是惊疑,却不得不道:“战场之上,我自然是宇文清。”
萧家还有流言传出,萧采绎生前虽未与栖情正式成亲,但早有了夫妻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