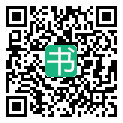第十八章 彻夜失眠
你的声音终于响起,果然是有些睡眼惺忪的慵懒语调。我听见你漫不经心地喂了三声,而后便沉默不语。但你并没有挂断,似乎,你预料到对面是个非同寻常的听者,或者你刚刚在迷糊中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你没有追问,也没有冷漠地挂掉,而是任手机开着,一直到我终于无法止住剧烈起伏的呼吸,颤抖着声音说出我们分离9个月零22天以来的第一句话:我是你的小白鼠。
你说:喂?
我知道那一刻的你,刚刚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醒来,你当然没有睡着。自从你的孩子离开,你说你再也没有过一次可以闭眼便进入梦乡的午休或者夜晚。你总是失眠,大段大段的时间都在混乱的胡思乱想中度过。没有什么药物可以让你获得彻底的安静和睡眠,除了我。你说我是你的安眠药,是你的大麻、罂粟、吗啡,明知用后会后患无穷,却让你欲罢不能,无法戒除,可你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听着窗外呼啸而过的车声,风声,还有始终热气一样升腾着的鼎沸人声,想起我的容颜,笑语,眼泪,疯狂,喊叫。
你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将房间收拾得犹如你刚来时一尘不染的样子。我的被你撕碎的衣服,都放进了行李袋中。你睁开眼睛,看着对面椅子上我收拾妥当的大大的旅行包,有一丝的困惑,而后才明白过来,说:明天我忙,不送你了,在上海好好照顾自己,找个爱你的男人。
我看见一个老人颤颤巍巍地急跑过来,可是老人还没有到达草坪,你的妻子便两步跨过去,抱起孩子,毫不留情地将巴掌啪啪地打在孩子的身上。我听见她一边无情地狠狠地打着,一边歇斯底里地喊叫着:再哭就打死你!你别想把我的宝贝小哲赶走!我不要你!我要我的小哲!!
我还记得9个月前的那场分离,那时你如此决绝,甚至近乎于残忍的分离,让我以为此生你都不会再跟我相见。而我也像个疯子,抱着一种毁灭般的无情,在人前那样蹂躏着你的尊严。
你明显地瘦下去了,就像艾琪说的,有了苍老的痕迹。你的头发蓬乱,表情茫然。蓝色格子的衬衫后面,不知是被人拥挤还是睡觉所压,有很多的褶皱。你的脚步,不再似从前那样矫健有力,而是有了犹豫和迟疑。
我还没有来得及从洗手间里转身出去,就被你一把从身后抱住。你重重地喘息着,像一只关在屋子里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的野狼。你忘记了自己曾经的警惕与疑虑,你被一条充满欲望的蛇越缠越紧,而我也被你的双臂,紧紧地抱着,几乎无法喘息。
我躲在一家精品店的玻璃门后,假装看一排琉璃的饰品,我的眼睛,犹如狙击手所持的枪,准确无误地瞄准着即将射杀的目标。一秒,两秒,三秒……你用了1分钟11秒的时间,从站牌下走至大楼的旋转门处。你在那里,被一个穿职业套装的中年女人叫住,你听她絮叨了50秒钟,而后挤出一丝职业性的微笑,点头,扭身要继续前行。
我用剧烈起伏的呻|吟,迎接着你的野性的欲望的冲撞,但我并没有在你密集砸下的吻里失去了理智。我第一次,在与你的激|情中保持了自我,并引领你一点点地向那绽满了洁白花朵的床上移动。
警察很快地过来,你只说了几句话,便被他们放走,你说:我不认识这个女孩,她或许是犯了间歇性的精神病,麻烦你们将她带走,我和我的同事还需要进行重要的采访任务。警察在你亮出的京城名报的记者证面前,果然相信了你,并在我的吼叫里,将我强行扭上警车。
我冷笑:我有那么可怖么?锦,只要你现在来见我一面,我立刻按照你说的,永远离开北京,再不扰乱你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不答应,我或许真的会如一条蛇,越来越紧地缠绕着你,直到你窒息为止。锦,你了解我的,我什么都不惧怕,只要我能得到。
哦,不,现在我不会凋零了。我又重新怀有了希望。或许不久之后,这个希望的小芽,就会长成一株参天的大树。它主导着我的天空,让我此后的人生,始终像有你陪伴一样,永不孤单。
按照原定计划,我在昨天下午两点一刻的时候,将一串倒背如流的手机号码,输入手机。我坐在床头,看着对面墙上曾经贴着我们照片的地方所留下的一块暗色的痕迹,紧张地等着一声接一声的“嘟嘟”响声过后,你的沉郁的一个“喂”字。
你并没有开口说话,而是将温热干燥的唇狂热地落在我的每一寸饥渴躁动的肌肤上。锦,那一刻,我多么渴望自己是一片花瓣,带着新鲜的欲望的芳香,被你揉碎在掌心里,并将自己的味道与温度,溶进你的身体。
墙上的倒计时牌,已经清晰无误地提示我,距离我的计划实施的时间,还有两天零三个小时。
我怔怔地看了你足足有五分钟,像看一个陌生的凶手或者罪犯。然后我便像一头凶猛的母狮,扑到你的身上,撕扯你的衣服,将所有的纽扣都拽落在地上。我恶狠狠地踢你咬你捶你,当着几米外你的那个吃惊地张大嘴巴的女同事。陆续地有人停下来,不远不近地朝我们看着。我听见一个女人指点说:看这个可怜的被小女人纠缠住的老男人!还有人吐一口痰,在你的身后,而后洋洋得意地离开。
锦,在你还有10分钟就出现在m.hetushu.com.com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将泡好的普洱茶,徐徐地倒入你的杯子。我准备了两只同样形状的玻璃杯子,一大一小。大的放在你的面前,小的放在我的面前。我还另外买了一只漂亮的碧绿色的杯子,我在里面放入几个茉莉花,而后冲入白水,花朵已经完全伸展开来,犹如水中漂浮的莲花,一瓣一瓣,那么纯净柔软,又婀娜芬芳。
问题的答案,是伊索拉告诉我的。你在警察将我带走之后,便跟同事告别,并请好了20天的长假,带妻子去海边疗养。你所选择的疗养所,位于岛城,而且,恰好在我们曾经住过的“时光之忆”宾馆的附近。你每天走十分钟的碎石子路,便会看到“时光之忆”那几个镶嵌在红木匾额上的大字。它们如同我与你一起走过的时光,站在不远处的小路上,注视着你,带着挥之不去的忧伤。
我走过去,一声不响地爬上你的双腿,坐在上面,温柔地环住你的脖子。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轻轻地咬住你的脖颈,感伤地轻触着柔软的双唇。锦,这一次,我没有像上次与你分别时那样,在你臂膀上,留下一排清晰的齿痕。你似乎在等着这样的啮咬,但我只是轻触而过。
说完了我没有等你说好,便啪一下挂断了电话。
我希望你的妻子,此刻是宁静安定的。
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带着你的小女儿出来接你。那个精灵古怪的小女儿,总是像我一样,挣脱开老人的手,飞奔着上来抱住你。你也会孩子一样奔跑过去,边喊着“宝宝”,边伸展开老鹰翼翅一样的手臂,将你的小女儿一把举起,并用粗硬的短发扎着她柔软的下巴。她在你的手中,快乐地扑腾着四肢,又咯咯地笑个不停。而旁边那个老人,则慈祥地看着你们,并走上前去,将孩子身上的灰尘,轻轻掸落。
你接着又喝下了那杯酒红色的普洱,这才停下来,将那口路上郁积着的气吐了出来。我微笑着将自己杯中的普洱茶喝掉,而后又倒入新的茶水。我将透明的玻璃茶壶放下,打开盖,续上新的热水。我还假装去洗手间,在里面用红色的唇膏重新将嘴唇涂抹一次。我看着镜子里那个一脸桃红的女子,得意地绽出一抹胜利的微笑。
但我没有想到,我依然像从未从你的身边离开过,像我不过是刚刚从你怀里离开了一刻,或者我们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我无法克制自己想你,主打地打电话与你求和。
锦,我要关了电脑,休息一会儿了。
你又是一声略带疑惑的“喂?”
火车已经离北京愈来愈远了。可我却听到你的呼吸,愈来愈清晰地在我身体的某个部位,响起。
我所熟悉的脚步声终于有节奏地在老旧的水泥楼梯上响起,它们一下一下,敲击着这个沉闷无聊的午后,将那水碱一样漂浮在空气上面的一层尘灰色的慵懒,一点点击碎,撞开。我的心快要撞碎身体冲出来了。我早已站在门口,等着你抬起右手,敲击那扇老旧的铁门。
你的手松开了一些,但我依然没法逃离你四肢围起的结实的牢笼。我看着你审讯犯人一样陌生的视线,突然地就恢复了理智与勇气。我让自己柔和下来,像玻璃杯里那朵优雅舒展开来的茉莉。
你狐疑地看我不再躲闪的眼睛,沉默许久,才说:那么,你确信你不会做什么疯狂的事情?
锦,我挨过很多次耳光,它们来自于父亲、母亲、唐麦加,不喜欢我的某个体育老师,或者年少时某个盛气凌人的男生或者女生的小头目。我从没有想过,你会打我,而且,是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锦,你怎么能够明白呢,我不想找工作,愿意这样一日日贫穷地浑浑噩噩下去,并不是因为我懒惰或者对生命了无希望,而是因为我怕我会被那样匆忙上班下班的俗世生活,给结实地捆缚住。我无法见你,无法在想要你的时候不顾一切地跑去找你。我的人生目标,锦,你知道的,与你有关,只同你有关。我愿意为了你,放弃一个正常女子应有的工作、家庭、孩子和世俗的幸福。
小女儿生了气,撒娇似的用小手拍打着母亲的胸脯,边拍打边叫喊:妈妈坏,妈妈不陪我玩,不是好妈妈。
我点头,哽咽地回了一个字:是。
在我还没有看清你的妻子有什么反应的时候,你的女儿已经被她用力地扯开且扔到了小路对面的草坪上。孩子立刻哇哇大哭起来,她的脸上,也像是被草坪上的蒺藜或者玻璃碎片划伤了,鲜血已经流淌出来。那一刻,这个被母亲抛开的孩子,像一片冷风中的树叶,剧烈地抖动着双肩,绝望地大哭。
尽管我知道你根本看不到躲在门后的我,可是那一刻我还是想要仓惶地逃掉。我的血液迅速地涌到发梢,如果有人现在用一把铅笔刀无意中碰到我的头皮,一定会有鲜血喷涌而出。我的双脚,挪不动半步,我的身体,犹如被人点了死穴,无法动弹。
锦,这样无心的一瞥,让我终于看清了你在我的心里,留下的深到几乎穿透五脏六腑的印痕。
你体内的潮水,终于缓慢地退去。你疲软如一只海底的生物,躺在潮湿的水草之上,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我像儿时那样,将双腿笔直地竖放在墙上,并斜侧着身体,看着你沉睡中的模样。你说,也只有在我这里,你才能安https://m•hetushu•com•com睡,而且常常是洁净轻盈到连梦都没有,犹如蝴蝶落在一朵清晨绽开的野花上。
先让我睡上一觉。锦,我太累了,快要被自己折磨疯了。
你终于开了口:那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我现在过去,但是如果你骗我,你知道我会怎样选择。
我说:锦,你想让我离开你,好,那么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原因我现在还不会告诉你,但我相信这个公开秘密的时日,并不会太远。我现在坐在哐当哐当的火车上,几乎闻到了那一天的芳香,它们沿着破旧的铁轨,伸向未知的远方,犹如无边的向日葵,朝着太阳的方向,一路伸展,光芒四射。
我是在上次与伊索拉的会面之后,才知道了你那时之所以如此冰冷绝情,原是因为你自己内心的挣扎已经抵达到可以承受的极限。
我紧张地等着你点头说好,你却不再向前,只在原地站着,那样复杂地看着我。也就有不到30秒的时间,你将我一下子推到后面的墙上,而后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你的右手用力地拽着我的头发,左手轻轻地抚着我的脸颊,一下一下,像抚摸一块即将破碎的玉石,或者一缕很快逝去的花香。你的眼睛里,写满了温柔,愤怒,疑问,渴望,暴力,挣扎,苦楚。它们混杂在一起,犹如纠缠盘亘厮扯着向上生长的藤蔓、杂草、荆棘和花树。
记忆里你从没有过这样勇猛,短短的4个小时里,你英勇无惧地发起了三次全部抵达至高点的冲锋。你的身体内似乎注入了某种会在瞬间繁衍肆虐无休无止的生物,它们刮起的旋风,携带着你,在我的战场上,无畏厮杀。
那时我所有毕业的研究生同学都找到了工作,我却依然晃荡在北京,不理会黎落落让我离京飞去上海陪她的劝告。你也几次让我找一份工作,并说如果我愿意,你会尽全力帮我寻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我为此跟你大吵,说你不理解我,不知道我究竟想要怎样的生活。你则骂我没有人生目标,活着像一株枯萎的植物。
锦,我真的看到了你!
我用手指,抚摸着你的肌肤,它们在我走后,开始像荆棘一样刺人粗糙。我的手,几次在爱抚中停留下来,将那些暴起的死亡的肌肤弄平。你的喘息,近在耳边,而我听来,却宛若天边大海的呓语。锦,我知道这海潮的喘息即将远逝,这一次之后,再也不会听到。我离开海边的小镇,踏上陆地的那一刻,我就知道,生命的水源快要枯了,除非我遇到一个所爱的男人,才能再次具有雀跃的脉搏。这个男人,锦,当然是你。
我本想在走完所有留下你我痕迹的地方,再写这封信给你,可是今天回来,我在窗前流淌的蜜色黄昏里坐下,看着对面那棵在暑气里躁动不安的椿树,呆愣了半个小时,终于还是忍不住,打开电脑文档,写信给你。
锦,你这最后的一句话,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子,插中了我的要害。我带着这把世界上没有任何医生可以拔掉的刀子,迅速收拾了行囊,离开北京南下上海。
锦,这一段时间,我已经坐公交5次路过你上班的地方。我还下车,在附近的商场和店铺里逡巡过几次。我佯装买东西,隔着一条车流不息的马路,用猎人一样锐利的视线,注视着对面那栋时常有人出入的大楼。
我笑:我在我们曾经住过的那个小房间里。我等你过来,我们谁都不要欺骗对方。
我说:锦,我只是路过北京,突然想来看你,难道,你连陪我喝一杯茶或者白水的时间都不肯给我么?你可以忘记我,可是,我办不到,我只想坐在你的身边,与你喝一杯水,聊聊我们的近况。
就在转身的那一刻,你朝我所在的精品店里看过来。锦,我想知道,这是你无意识的动作,还是你与我心有灵犀,冥冥中感觉到一双熟悉的眼睛在马路对面注视着你?我写给你的信,你一定没有看到,否则你的视线,不会如此了无光泽。或者你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那个信箱,不过没有关系,你总有一天会看到它们,这一封封的信,迟早会像疯狂的藤蔓一样,进驻你的身体,并缠绕住你的灵魂。
伊索拉只是一笔带过这一段过往,至于你和你的妻子,究竟有没有在岛城愈合伤口,她则并未提及。是到了艾琪这里,才有了一枚纽扣,将两段我所不知道的生活,连接起来。
今天我在1号线地铁里来回坐了两个多小时,看着各色男女上上下下,消失不见。我将视线穿越一张张苍老的单纯的风骚的滑稽的冷漠的嘻笑的色情的脸,试图将你从这些面孔中间,剔除出来。但我还是怕与你视线相撞的那一瞬间,我担心那会像巨石引爆,石块飞溅中,将我砸得遍体鳞伤。
我拉起你的手,我感觉到你的手有些僵硬,我回头温柔地笑笑:锦,走了这么久,你一定渴了,先坐下喝杯水我们再聊好么?
安。
锦,你永远都不会想到这个在我遇到你的那一刻,就开始萌芽的秘密。
艾琪在我见你的前一天,也就是两天前,用得到什么私密八卦似的小报记者的语气,打电话给我,说:嘿,龙小白,你知道么,刚刚听说苏锦安已经从高位上退下来了,好像是打算带他的妻子去海边长期疗养。因为他的妻子已经病得很严重了,据说有一次发作起来,差一点就将自己和她的女儿一和*图*书起摔下楼去呢。或许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辞职回老家,京城一支笔,自此就销声匿迹了。
我用假装的平静骗过了警察,让他们审讯了我几句,便将我放走。我走出警察局,便打电话给你,但你早已关了手机,并自此再没有接听过我的电话。
锦,你一定奇怪我这一次我为何会如此温情地对你,没有吼叫,没有威胁,没有逼迫,我只是替你穿好衣服,帮你一颗一颗系好衬衣的纽扣,又拿过梳子,整好你蓬乱的短发,就像一个妻子,为心爱的丈夫,整理出差前必需的行囊。
我屏住了呼吸,尽力不让自己制造出一丁点的声音来。我的周围,有一个中年女人在喋喋不休地给自己的男人打着电话,电视机里在播放80年代的某个絮絮叨叨的老电影,话吧的老板在指责着自己笨手笨脚的儿子,门外则是城市巨大的喧嚣声。
你突然无情冰冷起来,犹如一片骤然结冰的湖水:龙小白,我命令你现在就离开北京,随便你去哪个城市,你不要指望我会再去见你,永远都没有这个可能!如果你还存留幻想,以为我们会回到从前,以为我会继续容忍你的疯狂举止,那么你想错了。我已经不是从前的苏锦安,不是你爱的那个苏锦安,请你记住!如果你继续死缠烂打,那么我将立刻换掉手机号码,如有可能,我会报警,或者干脆连这份工作都不再要!
锦,如果那个老人,换成你的妻子,我想我的心里一定会升腾起浓郁的嫉妒,可是我却从未碰到过你的妻子。我曾经猜测她是懒得下楼,或者在家里忙着为你做饭,再或她更喜欢站在高楼上,深情地眺望你和孩子大踏步地向她走来。但我却从未想过,她会以那样衰颓的方式,出现在我的面前。
锦,不论你选择喝白水,还是普洱茶,都可以。只要你喝,我就会忘记你所有对我的淡漠无情。那一刻,我看见你喝下去,我想我的心底将只有闪亮如晨露般的欢悦。
疼痛从发根传导至我的每一个神经末梢,我想摇头,却发现无法动弹。我吃力地请求你:把我放开,我就告诉你。
我先看到的是一个女人,我不能准确判断她的年龄。她的面容憔悴苍白,像一个长年不见阳光的病人,或者一株长在背阴处又没有蝴蝶路过因而无法绽放的花朵。她的手指瘦削无力,仿若一截枯死的树枝,在阳光里孤寂地随意丢着。我从她的面前经过,她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眼睛空洞地看着不远处草地上的一小片阳光,没有悲喜,好像坐在那里的,不过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躯壳。她的魂魄,早已飘散到某个远离尘世的地方。
社区里的护士很快地过来,给她注射了一针镇定剂。我看看时间,猜测你很快就要下班回家,或许护士已经和你通过电话,你正在赶回家来的拥挤的地铁里。
你犹豫地问道:什么条件?龙小白,你不要再耍什么花招。
锦,一切都像我策划的那样完美无缺。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珍宝,尽管用了或许会被人认为不耻的方式,可是,我的目的达到了。那么手段的明与暗,高尚与卑劣,又有什么区别?我得不到你,也无法再得到你的爱,可是我却可以得到与这些一样重要的东西。
你的女儿一迭声地喊着“妈妈”,又爬上她的双腿,用胖胖的手臂环住她的脖子。你的女儿嗲声嗲气地不断恳求着:妈妈,你带我去草坪上玩,你帮我吹蒲公英好不好?可是你的妻子却是始终在茫然地看着什么东西,没有给女儿一句回复。
小哲是你去世的儿子的名字。锦,我以为这么多年你的妻子早已经从阴影里走出来,而今才知道,这个创伤在她心底留下的痕迹,原来如此之深。她青筋暴露的瘦瘦的脖颈,因为这样突然而至的暴怒,似乎要折断了。我在她将过来劝阻的老人也一下子推倒的时候,知道她已经很难再走出来了。她的灵魂落在原地,而躯壳却被时间撕扯着向前。时间走得愈远,那么她的身体衰老枯萎的速度也愈快。她注定要成为被创伤彻底击败逼疯的女人。
其实什么都不用问,没有了我,你只剩下了枯寂的枝干。没有了你,我也就此凋零。
我找了你很多天,翻天覆地地找,却都没有你的踪迹。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留言,你说:你走吧,我再也不会见你,不会跟你有任何的联系。我说到做到,我早就厌倦了你,也麻烦你,离开北京,并将我彻底地忘记。
所有可能遇到的意外我都早已想好。如果你说不过几句话,转头就走,那么我会哭着求你,直到你肯坐下来,为我多停留一分钟。我在这多停留的一分钟里,离我想要成功实施的计划,就又近了一步。如果你什么都不肯做,那么没有关系,你就陪我喝一杯茶吧,酒红色的普洱,在纯净的玻璃杯里,如此诱人地闪亮着,犹如密林里一闪而过的一匹锦缎。如果你不喜欢喝茶,那么一杯纯净水总可以吧,我们总不会到了连坐下喝一杯白水的恩情都不再有。
我绕过你哭泣的小女儿,或许是你母亲的老人,还有两个镇定自若注射针剂的护士,匆匆地离开。锦,我一路走着,一路难过,我为自己在你的痛苦面前无能为力而难过。我本以为我可以给你带来快乐,到现在才发觉,其实你一直孤单地走在生活尖锐的碎片之上,无人可以伸hetushu•com•com手相助,将你拯救出来。我,或者是你那一出生就注定是情感替代身份的女儿,所带来的都不过是短暂的欢愉。你的时刻会疯狂的妻子,会一次次将你从短暂的平静中拉进绝望的深渊。除了你自己,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帮你打败容颜惨烈的破碎生活。
锦,我想过千万次,我们在分离再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应该是什么。我想我或许会故作冷漠,来一声没有丝毫情感的“喂”,而后等你主动向我示好。或许我会固执地保持沉默,等待你的回答再做出相应的表情。或许我会歇斯底里地暴怒,指责你从来不给我回信,指责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男人,指责那些我在离开之后才发现的与你相关的种种秘密。或许我会嬉皮笑脸,假装已经将你忘记,不再在乎你的一切。我们云淡风轻地聊起彼此的现在,好似一直都是这样带着隔膜的亲近。
锦,你终于站在了我的面前。你穿着去年那件我买给你的米黄色的短袖纯棉衬衫,戴着我在你生日时送你的一条黑褐色的领带。你的皮鞋,着了灰尘,似乎有好多天没有擦过的样子。你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额头的皱纹又加深了,似乎在我走后,你就一直这样蹙眉工作与生活,再也没有过笑容。
锦,你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那只掉落在床头的安全套。你是一只旷野中吼叫的狼王,你只知道奔跑,冲杀,飞驰,怒吼。
你很快地将我抱上床去。你撕碎了我刚刚买的墨绿色的裙子,还有白色绣花的小吊带,而我的丝|袜则一条条地散落在床上,像水蛇身上蜕落的长长的网状肌肤。我刚刚染成栗色的长发,铺散在床单上,宛若狂野的大丽花。我躺在床单揉成一团的花朵上,任你的身体与灵魂,在我的体内,飞翔,冲锋,激荡,旋转,冲刺。我很清醒地看着你的脸。这张写满了岁月痕迹的脸,如此多情、温柔、犀利又疼痛。锦,这是我第一次,在做|爱的时候,细细看你的模样。你拍打着粗硬的翅膀,一下一下地俯冲进我的身体。我则在这样的冲击中,看着你的脸,一上一下,一上一下,犹如一艘大海中随波浪震荡的大船。我不敢闭上眼睛享受那涨潮时飞升的快乐,我怕睫毛落下再张开的时候,你便不见了踪影。我所设计的那个瑰丽多彩的梦,也真的只是一场漫漫长夜里的春梦,醒来的时候除了床单上湿漉漉的体液,再不会留下更多的印痕。
亲爱的锦:
我最终选择了更安全隐秘的方式:偷窥。我走下1号线末端地铁口的时候,在强烈的光线里有些晕眩。我看着那条熟悉的用视线抚摸过千万次的小路,竟是有些害怕,似乎踏上去,沿着草地一路而上,抵达的不是你的家,而是一个神秘莫测变幻万千的岛屿。
至始至终,我都没有问你,你在我走后,过得好不好。你也没有问我,究竟在上海有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找到一个可以一生倚靠的男人。
锦,在等你过来的那一个小时里,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我在想象,我打开门看到你后,我该怎么做,质问你为何从不给我回信,我到北京这么多天你都毫无反应?还是一下子扑上去,对你又撕又咬,像一条小狗见到出了远门的主人?或者拘谨客气毫无章法手足无措,并忘了自己要你来的初衷?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真想从窗户里跳下去,将整个北京城翻个遍,就为找到你,问一句“你真的厌倦我了吗?”
锦,请你告诉我,我究竟该去见你,将你诱进我隐秘的网,还是折回上海,就当此程没有来过?
锦,你一定以为我会被你佯装的冰冷吓住,或者真的就听信了你的威胁,离开北京,再不动任何与你见面的念头。可是锦你忘了,我不再是那个刚刚与你相识时的单纯幼稚的龙小白。我爱过你5年,在这5年里,我已经像一条蛇,蜿蜒至最高的一株野生的大树上,并因此看见了我所一直畏惧惶恐的未来的方向。
我在回程的火车上写这封信给你的时候,心里充溢了巨大的喜悦与满足。就在18个小时之前,我看这个世界,还是灰暗嘈杂混乱不堪的,可是现在,我已经坐在绿皮的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旁边一个庸俗男人不断地打着蒜味浓郁的饱嗝,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子大声地哭闹。过道里拥满了外出打工或者回家探亲的民工,一个穿着马虎的男人和貌似他的老婆的女人,正因为一点琐事,喋喋不休地争吵。就是这样拥挤吵嚷的环境,锦,我的心却是异常地安定、富足,犹如一株在旷野里为自己寂静绽放开第一朵花的扶桑。
我在之后一直失眠,我不知道还要不要执行我既定的计划。我不想那么自私,可是锦,你能不能告诉我,如果我不去见你,那么如何才能将你彻底地忘记,或者平静地度过没有你在的岁月?假若这次来京不去见你,不在原定的时间内实施我的隐秘行动,那么我便可以看清此后的人生,我将怎样残破地度过。
终于有一天,当我跟踪着你和一个即将去采访的女同事走出大楼的时候,你猛地回转身,看着跟在身后的我,一言不发。我走过去,仰头看你眼睛里马上就要喷薄而出的怒火,我想要问你,为什么躲着我,不接我电话,不和我吃饭,不与我做|爱?将我当成一个讨厌的商贩或者乞丐?可是还没有说出一个字,你便给了我和图书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终于害怕你在第三声“喂”之后,我会忍不住喊出你的名字。我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并哆嗦着手指,从钱包里取出一个一元的硬币。我没有等到话吧老板找我零钱,便神情恍惚地走出了话吧,并在一条陌生的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才想起伸手拦车,让司机送我去最近的地铁口。
所以锦,我在你的冷漠里,反而瞬间平静下来,不再哭泣似一个毫无出息又软弱无能的孩子。那个隐匿在心中许久的私密计划,又冷硬地探出头来,将我的心,一下子变得自私冰凉。那一刻,我的心里,只有我的计划。
你没有阻止我的歇斯底里,你只是不动声色地给你的同事发了一条短信,你在短信里说:请帮我拨打110,我需要援助。
锦,那时你妻子的抑郁症,时常地爆发;你在工作中,又处于被人排挤的动荡时期;你的父母还轮流地得病,需要你源源不断地寄钱。你加班加到常常在办公室的桌子上睡去,连我的电话都听不见。我则因为没有工作,被大段大段无人倾诉的寂寞时光逼迫着,一次次打扰你。你始终保持着沉默,在我的无理纠缠里不给予任何的解释,但事实上你被这样的生活逼疯了。
就在成功距离我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你突然地止住了。你重重地重新将我推到墙上去,而后将我的头发向后扯去。你冷冷地盯着我想要躲闪逃避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晰吐出见面后你的第一句话:龙小白,告诉我,你想要实施什么阴谋?
锦,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忽略的一个地方,是你的家。它在1号线地铁的最后一站。我曾经许多次想要走近一点看看,都忍住了。我只是在送你抵达站台的时候,站在出站口的台阶上,透过巨大的玻璃窗,看你穿过马路,走过上坡的草地,再一路直行,直至在倒数第二栋楼的拐角处消失不见。
我也想过许多种你所会有的反应。我猜测你可能会立刻呵斥我,让我回家,或者上海,只要是跟你不同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或者你脱掉衣服,无声无息地将我抱上床,并随手打开一只事先准备好的安全套。也有可能,你带来了警察,以某个不能成立的理由,威胁我,以此让我彻底地将你忘记。
如果不是一个小女孩跑过来,冲着她高喊“妈妈”,锦,我想我不会将她认作你的妻子。那个女孩,扭头过来,冲着我甜甜地绽出笑容。我从她唇边的一颗小痣,认出了这是你的女儿。我迅速地走开去,躲在一大株黄刺梅旁边的木椅上,假装打手机游戏。
锦,我在倒计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倒计时。我在不同的公共电话亭,让艾琪告诉我你最新的手机号码,打过5次电话,有4次响了一下,不等你接起,我便挂断了。只有一次,我紧张地等着铃声响过6下,而后电话那端终于传出我所熟悉的你的低沉的嗓音。
亲爱的锦:
然后我听到你用尽力压抑住的平静嗓音问我:小傻瓜,你在北京,是不是?
我知道你已经放松了对我的警惕,于是大胆地抬起右手,轻轻地抚摸着你眼角的皱纹,用迷幻般的嗓音对你说:锦,跟我来,喝一杯我为你冲好的白水。
我重复一句:我是你的小白鼠。锦,你没有看到我的已经流了满脸的泪水。我用了很大的气力,才克制自己,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出声来,让你跟我一样无助和伤心。
你停了大约有一分钟。我知道你在犹豫,我没有继续追问,看着床头那个还没有被扔掉的小小的闹钟,耐心地数着秒针一格一格滑过的啪嗒声。
锦,你终于还是收回视线,漠然地转身,走入大厅消失不见。而我,也在店主不满的一句提醒我买什么东西的问话里,清醒过来,随意选了一串绿色的玛瑙手链,离开了小店。
锦,我本应该在这次见面的时候,和你说说别后的琐碎生活,你也一定有许多的苦楚,无法对外人倾诉。可是短短的4个小时,我们却留给了彼此燃烧的身体。我甚至都忘了问你,究竟有没有看过我写给你的那么多信。我们像两个偷情的男女,一言不发,无休无止地做|爱,做到最后一滴残留的力气,化成汗水,流淌在那个我打算永远都不再使用的床单上。
锦,你的一瞥,控制了我的每一个神经细胞。除非你离开,不见踪影,否则我的穴道,永远无法解冻。
锦,我本应该心疼地将你立刻抱住,可我还是安静地笑笑,就像我们是一对素常的夫妻,你下班回家,我要给你拿一双拖鞋,再递给你一杯解渴的白水。
我在几个小时前,站在北京站喧哗的候车厅里,不停看着周围来往的人群。锦,我知道你不会来送我,事实上,你很少为我送行过。你说你不想看到我离去的背影,似乎我这样一走,便再不会回来。
你告诉伊索拉,选择岛城作为妻子的疗养之地,是因为这里也植满了我们的过往。你希望能够用淡然面对的方式,来将那些日日缠绕着你的回忆,一点点地忘记。你想治好妻子的病,亦想医好自己心头的伤。
你果然受了诱惑,放开了我,跟着我走进卧室,而后坐在书桌旁边的椅子上。你肯定是渴了,看见那杯飘有白色茉莉花的净水,想也没想,便端起来一饮而尽。喝完后你的身体便像打开了一扇封闭许久的窗户,一下子轻盈灵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