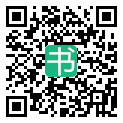第四部
第十章
人力车在秦淮河畔跑。车上坐着卞梦龙。他两膝间夹一包,包上用毛笔写着“海参”二字。
众人欢声叫好。猥琐在这时似乎被净化了。
“为什么要这么干?”冀金鼎极力挣扎。
冀金鼎环顾着房间。声音略略嘶哑,“漂泊了半辈子,我老冀要在这里安家了。”
不能归结于巧合,过去,他曾在盼盼苑苦等过冀金鼎,并一直追着他和小凤姐进了一家首饰店,这事又重演了。这日清晨,他从小黛玉房中出来,见此二人手挽手出去,他不由跟上去,出门往东竟又追入了那家首饰店。
四只脚走在泥泞中。沿河街到这里中断了,河面宽阔起来。他们已闻到了江水的气息,听到了远处的江涛声。
按说新郎得被簇拥到新娘那里去。天将擦黑时,他在聚友会馆穿上了崭新的深蓝长绸袍,戴上了红绸子扎成的花,正对着墙角上挂着的那面肮脏的小方镜拢头发时,猛地感到一个硬物狠狠地砸到头上。他听到了自己的一声惨叫,整个世界都扭歪了,都倾斜了,都黑暗了,只有一片片金星乱闪,接着一切都静了下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片黑暗、疼痛、炽热。他感到嘴里发酸发苦,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一阵眩晕,他又闭上了眼睛。后来他感到有人抓住了他的手和脚,把他抬起来。在那漫长模糊的梦境中,他看到了几张陌生而遥远的面孔,产生了一种清醒的无限宁静之感。他感到自己是被扔到一辆平板车上,被蒙上一层被子,晃晃荡荡地走了很久很久进了一个房间,又被什么捆绑起来。他浑身发冷,没有疼痛,昏昏沉沉间听到了嗡嗡的说话声。睁开眼,才发现自己手脚俱被捆住,眼前的两个人俱是过去吉顺手下的打手。是吉顺报复?这是他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不大像吉顺伤他,他还没有那份狗胆。是卞先生干的?他又何苦伤及手足呢?而一见到卞梦龙进来,他心里刷地凉了。
“没想到我一条六尺汉子会喂了鱼。”
老者拿出手镯,冀金鼎从他手上一把抢过,看都不看,转身套到小凤姐手腕上,又歪着头欣赏那套着手镯的白皙的手腕,老者不解地向小凤姐递眼色,那意思是问是否又要诓这个人作保。小凤姐无奈地摇摇头。
“今非昔比,上次承你告我这地方最来钱。后来,我没动本钱,这个赌场和妓院就归我所有了。我把这包海参扔到车上,不明着说,是诚心谢你的。”
他在包小凤姐房间时,冀金鼎曾来闹过房。而冀金鼎包小凤姐时,他也闯入过房间。
“听和_图_书说他俩快结婚了?”
小凤姐“嚓”地擦着根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她两个手指伸得直直的,用女人特有的那种不自然的姿势夹着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抵押就抵押吧,对不起祖宗我自己哭坟去。”她声音沙哑,像个男人似的,“只是我认准了一条,金鼎他没有携款外逃,没有,没有,没有!”烟卷叼在嘴唇间抖动着,她从腕上褪下翡翠镯子,在掌中搓揉着。“金鼎他已不在世上啦!”她猛地哭号了一声,伏在桌上号啕大哭起来。
卞梦龙一言不发,弯腰拿起“新郎”字样的红绸条看了看,淡然一笑。
“你非要带我来买什么首饰呀?”小凤姐问冀金鼎,他却神秘地笑而不回答,走到柜台前把一张庄票拍上,对老者说:“这是二百五十大洋,买这个翡翠手镯。”
只有烛光伴随着冀金鼎焦黄的脸。
厅内灯火通明,红烛高照,喜庆的音乐如水般奔流,盘旋。
三个人一同笑起来。
“都迎我进去,又都是香巢,我真不知该进哪家了。”他得意地说着,又扭头看看。车夫仍在街旁等着他。
“你太黑啦!”冀金鼎嘶喊起来。
就在那女人含羞地垂下头时,卞梦龙走出了门。
卞梦龙一指箱子,“聚友会馆这几个月的赢利全在这箱子里,会馆里已布置好了你盗窃后携款外逃的现场,什么时候逃呢?新婚之夜,趁众人不备,多合适呀。”
正在这时,两个人匆匆跑入,对卞梦龙说:“糟了,新郎官不见了!”
他笑着说:“我没什么可操心的,咱们来个省事的,聚友会馆这月的利和下月的利不用交给我了。两千块钱算我送给二位的贺礼。怎么样?不算少吧?”
满室愕然,又哄地炸了窝。
炮仗噼里啪啦响起来,像在驱逐污浊。
冀金鼎唾沫横飞,一副至尊模样,指手画脚地说:“斗蟀双方议定斗会后,向账台缴存,然后各提瓦盆到司掭人处将蟀蟋转放于高约一尺的硬纸制成的斗盆中。司掭人区分双方蟋蟀后,即用蟋蟀草或鼠须签掭于蟋蟀脖子下,使它振翅大鸣,两根须子直竖不动。这时就用硬纸片将胜败两虫隔开,使初败虫休息三五分钟起用,再掭败出上前复斗。如对三次头,败虫不咬而逃,就算输了。倘若败虫再咬,反败为胜,名为‘反闸’。”
过去,他曾整日想过冀金鼎在赌场上能搞来多少钱,又会给小凤姐多少。现在,这件事又占据了他的身心,如同由噩梦连成的光怪陆离的彩带在头脑里回旋。
老者惊异得咧了咧嘴,赔着www.hetushu.com.com干笑了两声。他脸上的笑纹又骤然消失了,神态庄重而严肃,双眸闪烁出充满灵感的光泽,向小凤姐伐伐眼。
吉顺抢上两步答道:“每月保人费五百。”
沿河街空荡荡的,雨沿街恣意驰骋,卷起灰茫茫的雨幕,把匆匆路过的行人吞噬得杳无踪影。走在前面的吉顺脚步忙乱,高卷的裤腿下露出苍白干瘦、青筋毕露的腿,完全是一种自惭形秽的人所特有的脚步。
冀金鼎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嘴蛀蚀斑驳的牙齿,“你用不着给小凤姐递眼神。这手镯不退,是我给她的定情物。”说着,微笑在他那潇洒得令人不敢接近的面孔上扩展开来,牵动了千百条明亮的笑纹,就像阳光在黑色的深水潭中闪耀一样。
“对。把你沉尸江底,再对外说你是携赌局的巨款外逃的。这么一来,妓院就得抵押给我。这主意不错吧?”
听着她的哭声,看着她的肩膀急剧地抽耸着,卞梦龙想起了徐州的唐代妓|女关盼盼。这个小凤姐,给妓院以盼盼之名。当年张尚书死后,关盼盼还落下个燕子楼。而冀金鼎这么一走,小凤姐抵押出盼盼苑后,将是一文不名了。更没有哪位傻蛋诗人会为她赋诗,因为她终究会被闷憋到这一步的,其中的机窍何在,她即便心里明白也无以向人启齿。想到此,他笑了,为自己的心智笑了。
“先生,结账吧。”车夫朝他喊。
坐在一侧的卞梦龙似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颇为同情地看看小凤姐。
青楼诸钗和聚友会馆的人会聚一室,这还是头一遭。
他大笑起来,“何止是来呀!老冀你是我的得力干员,小凤姐是保人,我得当主婚人!”
“忘不了。所以再请你帮我把妓院也搞到手。所不同的是,夺赌局时用的是你的赌技,而夺妓院时所要借用的是你的小命。得力干员嘛,你的小命用好了最得力!”
“车夫,”他问道,“这个地方哪里最红火?”
“小凤姐收到吗?”
冀金鼎尽力抬起脖子,“赌局你已经拿到手了。别忘了,是我帮你搞到手的。”
暗夜中,几个人把一个沉甸甸的麻袋抬上船。月黑风高,船往江心驶去,船到江心时,吉顺甚至在揣测舱中人此刻的感受。但又不肯多想,他们几个“扑通”一声把他扔入江中。
冀金鼎果真要在聚友会馆开斗蟀摊了。当卞梦龙不惹人注意地走入会馆时,他正给已沦为其门徒的吉顺等讲解这方面的大略。
冀金鼎最初引起他注意的便是其精湛的赌技。正是他初次来聚友会馆,听此间人说那个和_图_书“黑大个”捞走了几百,这才促使他去与他结识的。生活打了个滚儿,当他盘下了会馆并交冀金鼎经营后,头一件事便是到会馆,看看“黑大个”此番又有什么新的表演。
“正在操办。”
吉顺捧着一个箱子进来,放到他们面前便转身走了。
这位在侃侃而谈,真是拉起斗蟋摊了。卞梦龙掉头走了。但走归走,他仍离不开对冀金鼎的探防。
车夫停了,他放下包,走过去。
小凤姐已憔悴得不成样子。她疲倦地坐在椅子上。头微向后仰着,那双黑黑的,由于痛苦的折磨而显得特别大的眼睛里像飘着一缕缕蜡炬刚熄时的青烟,苍白的嘴唇上浮现着一丝令人恐惧的微笑。
吉顺进来,冷笑了一声,说:“冀好汉,恭喜恭喜。人生一大赌,你小子中了个头彩!”随即一棍子抡过去。
包里仍是干树枝子。
“用不着结了。”他过去说,“没看到车上那包海参吗?拉走顶账吧。”
吉顺推开门,卞梦龙一低头进了屋。只见两张冷漠无情、苍白忧郁的面孔在黑暗中忽隐忽现。他只感到有一只蜘蛛爬过脊梁,浑身打了个寒噤,耳朵嗡嗡作响。
他冲出了盼盼苑。秦淮河在雨夜中呈现出一片灰茫茫的色调。他两步又入了聚友会馆。
车夫边揩汗边说:“往前看,那里有两块匾,一前一后挨着。妓院跟赌场搭着肩膀,嫖客跟赌客来回串,这种地方生意没法不旺。”
“还不是不愿让卞先生跟着瞎操心。”小凤姐说。
潘大肚子背着手团团转。他边走边说:“小凤姐,不是我对不住你,你们三人签字画押的时候我在场,现在这个冀金鼎携款外逃了,契约不能不作数,你这盼盼苑就只好抵押给卞先生了。”
几个地方官员模样的人在看摊在桌上的契约。
“胜方由司掭人在纸条上盖一个‘上’字红戳后,就等条向账台领回双方原缴约款,同时付摊方十分之一抽头。如果‘反闸’胜的就要付七分之二。”冀金鼎答道。
小凤姐刷地摘下头盖,愣了愣,漆黑如炭的瞳仁闪了闪光,下颏颤动了几下,突然神经质地轻声哭起来,哭了两声,她一下昏死过去。卞梦龙喊道:“别慌!分头找去!”
吉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问道:“那胜方如何呢?”
门外传来吵闹声。他们无可奈何地相视一笑。吵闹声不曾止息,他们不情愿地分开。小凤姐去开门。
入冬时,由于仍不见冀金鼎踪迹,通缉令发了不少,都杳如黄鹤,在事主卞梦龙的要求下,只好承诺作保协议了。
“实话说,本想一年半载hetushu•com•com后再除掉你的,而你急着要和那个窑姐儿成婚。你想想,在你成家后再说你携巨款外逃谁会信哪,所以逼得我提前下手了。”
他走到卞梦龙前,向外一甩头,拔脚就走,卞梦龙也随后跟上,他们出了会馆后顺秦淮河往长江方向走。
门刚开,两个女人进来便快嘴快舌地说:“我们说小凤姐已不接客了,又说小凤姐和冀先生这会儿正热乎,怕进来不方便,可卞先生非要进来。”
冀金鼎呈大字形被绑在一张破床板上,浓眉下那双眼睛像是蒙上一层白翳,混浊无神,直瞪瞪地望着前方,如同一只被严寒困在荒野里的乌鸦。
“也不尽然。”卞梦龙挂着凶残的笑意,“我冒雨赶来就是为了给你托个底。让你死得明明白白。这是我卞某人唯一对得起你的地方。”说完站起出门。
这日,他在街上信步遛着,吉顺架着鸟笼紧随其后。
人们静下来,怀着神秘而深沉的喜悦看着老鸨转瞬成了新娘。
“只有让你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灭掉,再说你携巨款外逃不知去向才更牢靠。”
他在微微一笑间明白自己该做点什么了。
“噢?这我得下去看看。”卞梦龙说。
他们紧紧搂在一起,恨不能把对方融化掉。
卞梦龙已体会到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在事情已见分晓时,把自己的心计向业已无力反抗的受害者和盘托出。一经享受到这种乐趣,他会兴奋得难以自抑。他缓缓在他身边坐下来,背对着他,注视着烛光缓慢地说道:“从哪里说起呢?我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有一个车夫对我说,那个妓院和赌局挨着的地方生意旺着呢。所以我就盯上这个地方了。”
“看在小凤姐的面上饶小弟一命!”
卞梦龙满身是雨水,磕磕绊绊地走入,床前的两个人走开,他拿起桌上的蜡烛,来到床前。
“收了。有字据。”
卞梦龙实实在在地感到,生活是打着滚儿往前走的,前不久发生的事在日后会略有不同地重来一遍。他与冀金鼎打交道的过程就是这样。他以前做过的事到现在又都以另一种态势重演了。
他俩正式成亲是挑了个日子的,只是这日子天公不作美。秋雨不停地拍打着点戏花厅的窗户,玻璃打上了雨水后变得朦朦胧胧。
冀金鼎无力地闭上了眼睛。对于他来说,这个答复既在猜测之内,又在意料之外。
看着小凤姐坐下,卞梦龙对大家说:“等等新郎一来,大典就开始。盼盼苑和聚友会馆多年为邻,可又是各干各的,各挣各的钱。现在好了,聚友会馆主事的和盼盼苑的老板娘结为百年之好,中和*图*书间这堵墙拆了,两家快成一家了!”
两个人高兴地对视了一眼,几乎同声说:“结婚的时候你可得来呀,坐上席。”
车夫摇摇头,“再不干这傻事了。上次好像也是你,唬得我拉了就跑,以为真是什么珍稀土特产,结果回家打开一看,全是干树枝子。”
“小凤姐说得对,就是怕您跟着操心。”冀金鼎过来说。
卞梦龙笑呵呵地从两个女人间挤过来,双手搭拳道:“二位快结婚了,这么大的事都瞒着我。”
那几个官员在摊开的账本上指指点点,悄声议论着什么。潘大肚子凑过去听了一耳朵,一跺脚,鼓囊囊的左手背在肉嘟嘟的右手心上,拍了拍,愁眉苦脸地说:
车夫乐了,鞠了个躬,拉着车就跑。跑到个巷子里,他从车上取下包,美滋滋地撕开一看,愣住了。
卞梦龙喊道:“新娘到——”
“这里呢。”一个人应声出来。这是吉顺。
“这两个多月来,老冀月月都给那个保人小凤姐开支吗?”他问。
他们走过一条破船。吉顺停下,向前指了指,不远处的江边有一座孤独的小房。窗户透出幽暗的灯光。风吹过来一声狂喊,其声沮丧,抑郁深沉,犹如孤苦的呻|吟。
由于破败,屋内显得更加杂乱不堪,微微发红的烛光在咝咝叫着的江风中,带有几分狰狞地摇晃着。
“那好。把字据留好。”
室无一人,寂然无声。平日喧嚣的赌厅这会儿像个坟墓。卞梦龙摸着黑走来,轻声问道:“人呢?”
床上摆满了大小纸盒,床上摞着几套新做的被褥。
盼盼苑门口,小黛玉笑盈盈地迎上来。
这日,当冀金鼎入小凤姐屋不久,他又来到了门口。
“明白。”
“没办法,这是他娘没法子的事,老潘我想拉你一把都吃不上劲。账本上记着你按月收了保人费,每月五百大洋,还有你的收据。黑字白纸的事,不是红嘴白牙所能推的。保人费拿了,契约更得算数。总不能拿钱的时候是保人,事发了,该抵押的时候就不是保人了。”
小凤姐眼里闪着泪花,深沉地说:“从十五岁开始卖笑,二十年了,也要有自己的男人了。”
聚友会馆门口,吉顺诚惶诚恐地迎上前。
小凤姐盖着红头盖被两个老女人拥出来。
卞梦龙焕然一新,胸前别着“主婚人”的红绸条,四下张罗,八方应酬。命运多舛,严峻冷酷的人们这时都在笑。
冀金鼎一身新装,胸前还别着一朵大红花,花下是一个写着“新郎”字样的红绸条。看到卞梦龙过来,他使劲挣了挣,低沉沉地问道:“这是你让人干的?”
“你要干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