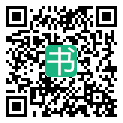第三章 梦游与往事
近处没有看见垃圾桶,她只好又把打湿的纸捏成团塞回衣服口袋。
过了好几秒,衡月才终于给了他一点反应。
是以,深夜不睡觉爬起来“念经”这事,他干了两天衡月都还没发现。
“有伞吗?”她问。
昨晚她胡乱蹬掉的鞋子整整齐齐摆在玄关处,随手扔在洗衣篓的脏衣服也洗干净挂在了晾晒间,看那一板一眼晾衣服的方式,并不是家政阿姨的手法。
少年呼吸稍滞,顿时僵成了块石头。
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林桁躺在床上,却感觉那一星半点的味道像是变浓了许多,似团化不开的雾气严密地将他包裹在其中。
衡月听他的语气,感觉他好像有点高兴。
衡月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手套,也不管合不合适,握着他的手松松垮垮给他套了上去。
况且手机里一搜出来的全是类似“可怕!一男子梦游时翻窗意外坠楼”和“十岁小孩梦游跑丢”之类的惊心标题,他实在不敢掉以轻心。
天光迅速消散在长空尽头,过了片刻,一个熟悉的身影快步从小区出来,折返到了林桁面前。
衡月愣住,回神后又帮他把手套戴了回去,低声道:“我不是来拿伞的,手套也不要。”
林桁一愣,看见衡月抬起手,用拇指与食指捏住了他薄软的耳垂。她手指一动,捻着那颗小痣很轻地揉了一下。
如衡月向村长承诺那般,她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林桁,至少在衣食住行上,林桁的生活质量全与她的比肩。
林桁看着她纤细的背影,眉头紧锁,久久没能回过神来。
他并没答话,半晌后,只沉默地摇了摇头,衡月并不理解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手已经被冻僵了,指尖生着细小的冻口,短暂接触的这几秒,衡月只觉挨着他的那片皮肤都冷得有些麻木。
因为母亲工作需要,衡月刚上初中就跟着母亲定居在了南河市,也就是林桁之前居住的城市。
他好像只是告诉衡月一声,说了这一句就没有后话了。
围巾上的细绒絮抚过他被风雪冻伤的脸颊,些微痒意袭来,小林桁眨了下眼睛,五指抓紧了伞柄,似乎是从来没戴过围巾,他不太适应地动了下脑袋。
林桁看起来比昨晚好多了,举了举手里的锅铲示意道:“等会儿就可以吃饭了。”
似是耐心告罄,这次不等他给出回应,衡月直接从书包侧面抽出伞,撑开了塞进他手里:“拿着。”
林桁在手机上查了梦游症,虽然衡月同他说这并不危险,但在他看来,衡月梦游时并没有自主意识,谨防意外,看着她点总是好的。
而衡月在家里从来不|穿鞋。
林桁知道她在拍自己,一般来说,这个年纪的学生正是自尊心、隐私感奇高的时候,很反感他人拍自己的照片,但林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甚至没问一句衡月拍照做什么。
衡月也转头看他,她坐在椅子上望着站着的林桁,这一眼对上去只觉得头仰得难受。
其中一部分是高定,一部分是直接从网上购来,盒身上的商标大多与摆在桌上的杂志封面上的商标相同。
随后和那夜一样,她站起身,独自慢慢回了房间,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小孩察觉到头顶的力度,抬起头,呆愣地看着衡月,神色有些惊讶,似乎没想到她会这么做,衡月自己也没想到。
盏盏明黄色小灯嵌在墙上,并不是一个适合看书的环境,林桁打开头顶的射灯,想了想,又把衡月手里的杂志拿起来,摆正了放回她手里。
衡月没有答话。
随后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包里好像没多少东西,瘪瘪地贴着瘦弱骨架,但背在他瘦小的身上,看起来依旧十分沉重。
林桁去完洗手间,出来后并没有回房睡觉,而是在衡月身边坐了下来。
衡月没理会他的小动作,只把耳罩也摘下来挂在了他的头上,耳罩内布满柔软的丝绒,还透着衡月身上的体温,似团温火包住了他两只冰冷红肿的耳朵。
阿姨和林桁说衡月吃不得辣、不喜欢酸口的时候,林桁也没觉得哪里不对。之前在老家做饭都是他来,到了这儿他也做好了包揽家务的打算,跟着家政阿姨把洗衣、做饭、扫地都学了个遍,甚至还给衡月冲了杯手磨咖啡。
林桁听见声,脚下一动,立马慌忙地站起了身,小腿抵着凳子猛地往后退开,凳子腿磨过地板,划开一串断续沉重的响声。
他没有拒绝衡月的好意,只呆站着任衡月摆弄,但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更像是m.hetushu.com.com在大雪里待久了,被冻得思绪迟缓,无法应对这粗暴又简明的善意。
翌日,衡月起床时依旧已经快到午时,和林桁一起用过饭,她抱着电脑窝在客厅的沙发里处理公司的事。
此地位于地段昂贵的别墅区,出入者非富即贵,一个看上去不到十岁的穷苦小孩无人看顾地坐在那儿,显然不太寻常。寒风凛冽的冬天,又是傍晚时间,四周安静得不见几个人,若有行人,来往也是行色匆匆,赶着早些回家取暖。
那时他穿着一身简朴宽大的灰色衣裳,脚上的板鞋已经磨毛了边,背上背着与他瘦小身形完全不符的大包,十分惹人瞩目。
林桁心中有鬼,白天不常待在房间里,总是坐在落地窗前的茶桌上看书刷题,甚至这些日的深夜,实在睡不着了,他也会来到客厅,开着一盏灯一个人低着头坐在那里温书。
入夜,皎皎月色似清透水光流入客厅,照见一道朦胧倩影。
他没说话,也没怎么动,就这么干坐着陪她,显然是打算等衡月安全回房后再回去睡觉。
两人在外吃了饭才回来,肚子还饱着。但林桁没有异议,衡月把牛奶插好吸管递给他,他就接过去喝着。
林桁对此毫无预料,身体僵住,不自在地眨了几下眼睛,半点没敢乱动。
这些是家政阿姨告诉林桁的,衡月没和家政阿姨说林桁是她弟弟,于是家政阿姨似乎是错把林桁当成了衡月的男朋友,一五一十把衡月的喜好都透露给了他。
衡月见此,几不可见地蹙了下眉。
收回手时,衡月捏住他柔软的耳垂,在那颗黑色小痣上轻轻揉了一下。
他身旁已经堆积了一捧蓬松的雪层,小小一个人像只小虾般蜷缩着,不似性格活泼的小孩坐在高处时跷着脚摇晃,他安静得出奇,仿佛一尊不会动的小铜像。
林桁咀嚼着口里的饭菜,撑得腮帮子微微鼓起来,像嘴里塞了坚果的仓鼠。他没再说话,只低下头,发扬了一贯优良的节俭作风,把桌上剩下的饭菜一口一口全扫进了肚子里。
衡月并没有停下来,她甚至站近了半步,用指腹在他的耳垂上轻轻摩擦起来,像是想看看那颗痣会不会因此而褪去浓烈的颜色。
衡月将杂志放在腿上,目光缓慢地顺着林桁结实的手臂挪到他宽阔的肩膀,而后又继续往上,停在了他的耳垂处。
但她突发的善心顶多只能延续到这个地步了,带一个可怜的小孩去警察局或是帮他找监护人这种麻烦事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
也就是林桁。
衡月缓慢地叹了口气,这副乖巧模样,也亏得这一带治安好,不然怕是要被人拐走,卖进深山给孤寡老头送终。
她身旁亮着盏小灯,看起来和白日里没什么区别,林桁以为她只是失眠,走近了问她:“你睡不着吗……”
天寒地冻,白雪纷扬,小林桁却衣衫单薄,头顶连伞都没撑一把,飘飘细雪落在他身上,又渐渐融化,将他的头发也打得湿润,仿佛要把他一点点埋进雪里。
他侧过身看向她,张了张嘴,迟疑着问道:“你还记得……昨天晚上的事吗?”
少年快速低声读背的声音回荡在客厅里,活像个为修心而深夜爬起来念佛经的小和尚。
遇见林桁的时候衡月正上高中,读高几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时正在放寒假,临近春节,南河罕见地下了场大雪,纷纷扬扬,几乎要淹没整座城市。
一句话没说完,少年突然止了声,因为他发现衡月手里的杂志拿倒了。
对林桁来说,错过一次的题不会再错,上过一次的当不会再上。可偏偏在衡月这里他学不了乖,吃不了教训,被人两次捻住耳朵,都不知道要怎么躲。
她的动作很慢,像是放慢速度的老式电影,且从始至终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许是见多了被学业压得弯腰驼背站不直的学生,医生开着玩笑:“以后可以去打篮球,再高点还能去试试跳高。”
明亮光线倾泻而下,瞬间涌入视网膜,林桁有所准备,却还是被晃得眨了下眼。但衡月却像是没反应似的,视线依旧看着前方,脚下半步未顿,继续朝他走来。
衡月畏寒,冬日出门必是全副武装,耳上挂着毛茸茸的白色耳罩,颈间围着一条羊绒围巾,头顶还戴着白羽绒服的帽子,双手揣在温暖的口袋里,整个人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了小半张脸。
好在这次衡月捏了一会儿就松开了他,她望着指尖,似在www•hetushu•com.com看有没有拓下他耳上的黑痣。
不知怎么,林桁的反应像被家长抓到夜里关了灯不睡觉而在床上疯玩的熊孩子一样,紧张得心跳都漏了一拍。
是刚才离开的衡月。
她站得离他很近,半步不到的距离,长发落下来,发尖轻轻扫过林桁的手臂,有点痒,他动了下手指,但并没有挪开。
林桁没想到她会回来,衡月在他面前蹲下时,他显然误会了什么,有些无措地把伞递还给了她,另一只手贴着衣服,还在试图将手上的粉色手套蹭下来,明显是想把手套也一并还给她。
林桁晚上去洗手间,看见衡月蜷缩着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低着头在读杂志。
衡月走到林桁身旁,却没有看他,而是低头看着桌上的书本。
她微皱着眉,看着被宽大伞面完全罩在下方的人,发现她离开的这段时间,他半步没挪过地方,从远处看上去,如同一只扎根在雪里的大菌菇。
客厅落地窗前的茶桌上摆着几本翻开的高中教科书,夏季浅金色的晨光照进来,一缕缕均匀地洒落在桌上。衡月瞥了一眼,《数学》《物理》,看得她头疼。
衡月在很久以前见过林桁,七八年前的事了,她本以为自己已经快忘了,然而昨晚忽然梦见,发现自己都还清清楚楚记在脑海深处。
她想起自己之前睡醒梦游到客卧歇下的事,端起桌上的咖啡战术性地喝了一口,思索着道:“我昨晚进你房间了吗?”
还没有哭,但看起来快了。
她拍了拍他的脑袋,从钱包里取出一叠红钞,也没点是多少,拉了拉他的衣服,随便翻出一只口袋塞了进去。
林桁转过身,看见衡月站在客厅昏黄的灯光下眨也不眨地望着他,她穿得清凉,细白的手臂落在微弱的光线里,裸|露在外的皮肤透出一股温润的暖色。
那香味很浅,若有若无地浸在他的被子里,并不浓厚。
她没叫他的名字,但林桁知道她是在同自己说话。
她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手绕过他的后颈,慢慢在他脖颈上缠了两圈,似是怕勒着他,伸手又把围巾扯松了些。
梦游吗?
此时正是半夜两点,落地窗外,城市斑斓的霓虹灯纷纷熄灭,只剩马路上数排亮黄色路灯和高楼上闪烁着的红色航空障碍灯尽职尽责地长亮着,零星几点灯光缀在城市边角,守护着这孤寂的长夜。
少年轻轻抓住衡月细白的手腕,衡月同时缓缓放下了手,随后如来时一样,悄声回了房间。
衡月蹙了下眉,伸手在他的耳垂上轻轻一抹,带走水珠又揩去残留的水痕。她从包里摸出纸巾,展开在他被雪淋湿的头发上胡乱擦了几下,一张纸打湿,又抽出一张,将他一头细软的头发揉得凌乱。
这话听起来并不太友善,他理解错衡月的意思,以为这处不能坐人,提了提肩上的背包带,局促地从花台往地上跳。
他左耳耳垂上有颗很小的黑痣,黑漆得像是墨汁浸透了皮肉,点在冻伤的耳垂上,明晃晃地印入了衡月眼底。
衡月不在意旁人的目光,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却还做不到视若无睹,她见他微垂着脑袋不说话,又问:“你爸爸妈妈呢?”
林桁意识到什么,屈膝在沙发边蹲下来,抬头看向她的眼睛,果不其然,发现衡月的目光和梦游那晚一样,视线涣散,没有焦距。
唯独林桁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那里,像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但衡月却敏锐地察觉了他的异样,她抬起眼,看林桁手里握着笔,低着头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发呆,开口道:“怎么了?”
衡月自认不是什么心地善良的好人,可冥冥之中,仿佛有条看不见的绳索在她脚下拦了一把,白靴陷入蓬松酥软的细雪,鬼使神差地,衡月就这么停在了他面前。
她“唔”了一声,提醒道:“你晚上睡觉记得锁好门。”
衡月见他一直看着自己,放下碗,不解地问:“怎么了?”
衡月颔首,只当他是个小哑巴。
她的生活十分规律,一周有几天会出门去名下商场门店巡视一圈,其余大多时间都待在家里。尤其林桁这段时间情况不稳定,她不放心把他一个人扔在家,因此连公司也很少去。
林桁看着她低垂的柔和眉眼,心中越发感到不安,又唤了一声。
衡月的卧室配有独浴,除了接水,晚上很少来客厅。林桁声音压得很低,并不用担心会打扰到她休息。
落在头顶的细雪凝成水珠,顺着他凌乱的黑色短
https://m.hetushu.com.com发滴下来,流经红透的耳郭,摇摇欲坠地挂在冻得红肿的耳垂上。
台砖上堆集着冰冷的厚雪,他连雪层都没来得及拂开,两只小手直接陷进雪里撑着台面,动作僵硬地落到行道上。
他低着头从口袋里掏出衡月塞给他的钱,抬手递给她,虽然不知道衡月给他的这半身冬装值多少,但实打实的钱他是能认出来的。
衡月从课外班下课,独自一人踩着雪慢悠悠走在回家的路上,在小区门口看见了一个低着头坐在花台上的小孩。
客厅地板上堆着几个购物袋和还没来得及拆开的纸盒,那是衡月给林桁买的衣服和鞋子,她一口气买了太多,出手阔绰得仿佛批发拿货,剩下许多林桁还没来得及整理。
没丢走,能找到家,不用报警。
衡月捻了捻指腹,莫名感觉手有点痒。
衡月看他喝得慢,以为他不喜欢,又叮嘱了一句“每天一瓶。”
他站直身时,还不及衡月胸口高,显然冻坏了,两条手臂一直在微微发抖,衡月低头看着他,发现他身上的衣服大了好几个码,像是捡了大孩子的衣服改小后套在了身上,灰白色衣服的袖口还留着整齐的黑线针脚,整个人看起来像只脏脏旧旧的小狗。
衡月听见这话怔了一下,第一反应便是自己的梦游症犯了。
衡月愣了一下:“缺什么?”
林桁这时才终于发现了些许不对劲。
和她平时看杂志时一样的折页方法。
林桁却没明白衡月为什么让他锁门,只是听话地点了下头:“嗯。”
逻辑还算清晰。
林桁含着吸管,听话地应下:“嗯。”
但她管不了那么多,她自认做到这份上已经仁至义尽,半辈子的善心都花光了。
“钙。”医生表情很认真,他说完扭头看了眼在衡月身旁笔直站着的林桁,也没多解释,只上下打量了一眼,欣慰道,“还能再长长。”
衡月看了眼有些局促的少年,应道:“好。”
她没打算瞒着林桁自己有梦游症的事,实话实说道:“我睡眠不是很好,患有梦游症,虽然不会做出危险的事,但会在屋子里乱走。”
现在已经是上午十一点,衡月从卧室出来,发现林桁并不在客厅,他的卧室门大开着,被褥整齐叠放在床上,里面也没人,倒是厨房抽油烟机呜呜作响,飘出了一股诱人的饭菜香。
他唇瓣微动,想开口让衡月停下,但又意识到此刻她根本听不懂自己说的话。
林桁匆匆避开视线。
听着手指敲在键盘上不断发出“啪嗒”声,林桁轻手轻脚地在衡月面前放下一杯咖啡,脸上又开始冒热气。
她没解释,行善行得如例行公事,脸上并无丝毫助人为乐的热情,直到一点点将他发丝上的雪水吸得半干后,才停下动作。
眼下,他坐在衡月对面扒着碗里的饭,偷偷观察着她筷子的走向。三菜一汤,好在衡月每一道都尝过几口,最后还喝了一小碗三鲜菌菇汤。
和总是站坐如松的林桁相比,衡月的坐姿并不端正,她蜷着两条细白的腿,没长骨头似的倚进柔软的沙发里,睡裙滑到大腿上了也不管。
衡月当时并不明白林桁一个小孩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后来听村长说,林桁奶奶病重的那年,他去城里找过他父亲。衡月这才恍然明白,他那时候应是一个人千里迢迢来找林青南。
这家医院是衡家产业下的私立医院,衡月带着他走了vip通道,大部分体检项目很快就做完了。
他说着,下意识抬起手在左耳上捏了一下,但他很快又放下了。
林桁怕衡月看不清,不小心撞到盒子,伸手将客厅灯全打开了。
宽大的伞面完完全全将小林桁与大雪隔绝开,做完这一切,衡月一句话也没说,把手塞回口袋,像在他面前停下那样突然,一言不发地越过他进了小区。
但视线却没有焦距。
他低着头,好像是在等人。
她被蚊子叮一下都难受,如果不小心磕着碰着了,怕是要皱眉疼上好几天。
她的嗓音天生柔和,叫人十分心安,但显然没怎么做过善事,关心人都不熟练。噼里啪啦一次性问了一大堆,也不管小孩听不听得懂。
她们在南河住了有近十年,也是在这期间,衡月的母亲认识了林桁的父亲。
他迎上她的视线,身上那层薄韧的肌肉都僵成了块,他张了张嘴,叫了她一声。
一边套一边想,冻成这样,或许会发烧也说不定。
本子上写得密密麻麻,高中生学业重,做笔记时的字迹连笔带画和图书,怕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写了些什么。
如同在一大杯澄澈无味的清水里滴入了一滴酸浓的柠檬汁,只一滴,却叫人无法忽视,足以叫少年嗅着被子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只要一闭上眼睛,他眼前就自动地浮现出衡月的影子。
细腻温暖的白色羊毛绒浸染着一股暖和的香,盖住了小孩大半张脸,只露出两只乌黑澄亮的大眼睛。
少年的睫毛微微颤了一下,似两片慌张扑动的翅羽,在眼下投落一片薄透的浅色灰影。他心如乱鼓,面上却不显,一只手搭在桌面,手指微微蜷紧了几分,安静地看着衡月迈开步子,慢慢朝他走过来。
他实在不怎么会撒谎,衡月看他这副模样,就知道自己肯定不只是“在客厅逛了一圈”这么简单,但她并没有追问。
街边,远处的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眨眼便照亮了被大雪摧残得不成样子的花台和一个撑着伞呆望着小区门口的瘦弱小孩。
客厅只开了一盏低亮度的暖色灯,衡月身穿一条浅色蚕丝吊带睡裙,柔软布料顺垂而下,行走间身上光影似水光浮动,隐约看得见衣服下窈窕纤细的腰肢。
清瘦的背影落在屏幕中央,“咔嚓”一声响,林桁转过头,看见衡月靠在厨房门口举着手机对着他。
她来回一趟,肩上、头顶已经覆了薄薄一层细雪,小孩显然也看见了,他没再把伞递给她,但脚下却小心地往她面前挪了一步,将伞慢慢罩在了她头顶。
她伸出手,细长的手指擦过他耳旁的短发,如那夜一样,捏住了他的耳垂。
大雪漫天,一望无际的云幕乌沉沉地朝地面压下,冬日余晖仿如倒放的影片开头从高楼大厦间退离,收成一线,聚在天地交接的边缘。
林桁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英语笔记本,他的手正搭在笔记本的中缝上。
他犹豫地抬起另一只手,在衡月眼前晃了晃,却见她毫无反应。
他也不躲,只呆看着她,但他终究只是个孩子,骤然体会到突如其来的善意,再藏不住遭受风雪的委屈,湿润水意迅速汇聚眼底,看得人心软。
果然无论怎么看都是只小狗。衡月想。
对他来说,这些钱太贵重了。
衡月没理会他脸上露出的茫然神色,也没解释什么,毕竟她自己都不明白今日富盛多余的善心是从哪里来。
他好像察觉不到冷,又或是耳朵已经冻僵了,雪水在他的耳朵上挂了好长时间都没发现。
衡月垂眼看着他,声音从捂得温暖的围巾里透出来:“你为什么坐在这儿?”
衡月从梦里醒来,有些恍惚地坐在床上,她忍不住想,如果那时哪怕她再多问一句,林桁这些年,会不会过得好一点?
医生在电脑上开着钙片的单子,提醒道:“买牛奶记得看看成分表,买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那种。那些配料表太杂的喝了没什么用,就是挂着牛奶名的饮料,少喝。”
衡月看着他,漫不经心地想,自己带回来一个大胃口的田螺姑娘。
衡月眉眼柔和,脸上却没什么表情,林桁不确定她是不是因为自己半夜不睡觉吵着她而生气。
阳光穿透窗帘的缝隙,聚成一束柔和金光照入房间,在地板上、床铺上落下一道细长的亮光。
林桁微垂着头看着锅里的菜,乌黑的后脑勺有点乱,后颈下方那颗脊骨明显地凸起,清瘦而坚硬。
衡月看着他,伸手在他头顶轻揉了一把,问道:“你是走丢了吗?找不找得到回家的路?要不要帮你报警?叫警察来帮你。”
不质疑不多问,这是林桁的好习惯之一。
小林桁还是闭着嘴不说话,但还好能听懂衡月说的话,他先摇头,又点头,后又摇头。
第二天,衡月带林桁去了趟医院,做常规性体检。医院人来人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衡月看了一眼,又给他塞了回去,淡淡道:“早点回去,别在外面乱逛。”
她想了想,掏出手机打算拍张林桁的照片发给村长,告诉他林桁如今一切安好。
林桁盛出烧好的红烧排骨,背对着衡月:“早上家政阿姨来过了。”
林桁出门时四手空空,回家时手里拎了两箱奶。
大雪渐渐模糊了她的身影,这次她没有再回来。
冬天日短夜长,从她离开又出现不过短短十几分钟,天色已经暗得像是快入夜。
“姐姐……”突然,闷不出声的男孩开了口,嗓音有点颤,一股小孩子的奶腔味。
等到林桁睡下,衡月才回房间。临睡前她吃了一片安眠药,第二天醒来,因药物作用头脑有些昏
https://m.hetushu.com.com沉,她坐起来,安静地靠在床头醒了会儿神,突然想起来她还没通知村长她已经把林桁带走了。林桁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老老实实摇了下头:“没有,只是在客厅逛了一圈。”
她仰起头,神色平静地看着林桁,双眸明净如水面,明亮的光线下,眼瞳中那抹浅淡的绿色如透亮的珠宝,清晰地映照出了他的模样。
指尖不小心蹭过她的手心,安静许久的人像是突然被人从睡梦中唤醒,衡月动了起来。
他在桌旁坐下,翻开练习册,心不在焉地刷了会儿题。昨晚的事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还没问衡月。
一大一小站在一块,无论从穿着还是年龄看,都犹如两块颜色割裂对比鲜明的色块,怎么也不像是姐弟俩,惹得过路人往两人身上好奇地打量了好几眼。
林桁的房间里有一股很浅淡的香,和衡月身上的味道很相似,其中还夹杂着一点不易察觉的沐浴液的味道,那是她之前睡在这房间时留下的。
似是担心惊扰了她,林桁的音量不高,很快便沉入寂静无声的黑夜里。
林桁渐渐皱紧眉心,乌黑两道长眉深拢,唇缝几乎绷紧,少见地露出一派严肃之色。
衡月从远处走近,看见他被衣领挡住小半的脸庞已经被冻得通红,而露在寒冷空气里的两只耳朵更是好不到哪里去。
林桁烧菜的技术意外得很不错,衡月平时都选择订餐配送,除了家政阿姨偶尔会来做做饭,她已经很久没吃过家常菜。
衡月“嗯”了一声,也没多问,但她看林桁面前翻开的食谱,觉得家政阿姨不只是来过这么简单。
他膝盖像冻僵了似的,脚下踉跄了半步,险些摔倒。
大片阴影兜头罩下,小林桁动作缓慢地抬起头看向她。他脸生得圆,婴儿肥未退,乌黑的眼珠子干净得仿若两片玻璃镜面,很是乖巧。只是眼眶泛红,好像是哭过。
英语、语文,随手一伸,捞到哪科看哪科,身上浸出一身薄汗了还端坐着不动,生生熬过升腾的热意,再回房间睡个囫囵觉。
林桁收拾完从厨房出来,一眼就看见了这一幕。
林桁见自己被发现,纤长的睫毛垂下去,不再看她,摇了摇头,低声道:“没事。”
衡月食量不大,但嘴却长得叼,不然以前也不会得胃病。不合口味的菜她只尝一口就不会再伸筷子,且每一餐,荤、素、汤都得有。
留少年一个人,捂着发热的耳朵在沙发上呆坐着,久久无法平静。
深冬傍晚,霞光睡不醒似的昏沉,严寒刺骨的冷风刀割般往脸上刮。
万籁俱寂的夜里,两人间的气氛静谧又安稳,林桁看着她眼前一缕垂落的头发,明明知道她没有在读杂志,还是伸出手小心替她挽在了耳后。
衡月并不是无缘无故叫林桁锁门,实在是因她之前有过太多次醒来后发现自己睡在客卧的情况。那也是她发现自己梦游的原因。
他看见衡月伸出手,纤细的五指抓住他的手腕,提起他搭在笔记上的手,放在一旁,而后在笔记的纸页上方折了个角,将其轻轻合上了。
诊室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指着报告对衡月说:“没什么问题,小伙子挺健康的,就是稍微有点缺钙。平时多喝纯牛奶,吃点钙片就行了。”
她路上想过林桁身体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但唯独没想过他会缺钙,这身高也不像是缺钙能长出来的。
比起昨晚,整个房间变得井井有条。
她早上起得晚,昨天睡前特意给家政阿姨发过消息,让她早上过来给林桁做顿饭,顺便教教林桁这一屋子家电怎么用,现在看来,阿姨许是尽心教了个精透。
衡月的拇指一顿,不小心点到屏幕,又听“咔擦”一声,照了张他略微模糊的正面照。她看了眼手机,因为林桁在动,所以脸部有点花,但耳朵上那颗黑色小痣不知怎么却很清晰。
衡月若有所思,脚下一转拐进厨房,看见林桁正系着家政阿姨的粉色围裙,立在灶台前做饭。他背对衡月,一手端锅一手执锅铲,站得肩背挺直,像棵朝天长的小柏杨。
衡月很关心林桁的身体状况,一回家就让他照着说明书吃了一片钙片、喝了一瓶奶。
这夜,林桁依旧进行着他的学习大计,他坐那儿翻了两页书,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轻缓的脚步声,声音有些闷,像是光脚踩在地板上发出来的。
她浅淡的目光虚落在林桁脸上好一会儿,突然,像被什么东西所吸引,那双眼珠微微一动,将目光投向了他的左耳。那地方长着颗动人的小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