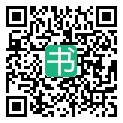Chapter 6 一步一步走过昨天我的孩子气
我筋疲力尽地瘫坐在地上,桌子上的玻璃杯或许也疲惫了,才会裸|露着粉碎的身体。我们相视,无言以对。
我起身,从卧室抱出被子盖在刘暄的身上,他翻了个身,仍旧呼呼大睡。
左凡柯本来在喝水,听到我这样说以后,他把水杯摔在桌子上,很用力地拉起我的胳膊,朝阳台处拖。我一直反抗,但他的力气很大,我挣脱不了。
我的手还没有触碰到刘暄的额头,他就一下栽进了我的怀里。
我斜眼看她:“我都没恋过,哪来的失恋啊?”
“伍月,上次你给我看你父亲的照片,听咱们会员说,在哈尔滨好像见过。”
刘暄抿了抿嘴,揉揉眼,看起来快要醒了,转头却又接着睡了。
连我自己都很难想象,不过两个月的时间,我竟然穿过了大半个中国。从春季微寒的东北到有些燥热的江南,我随着会员们一起,上山下海,我们路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小声嘟囔:“你表哥一个还不够,你是想把我置于死地啊!”
左凡柯的话语中全是责备和不耐烦。
他一定是为了耍帅,所以穿得太单薄了。
其实,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吧?如果刘暄可以看清我的内心,他还会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我义正词严道:“垃圾呀,要不然嘞?”
一罐接着一罐……他只是豪饮,却一句话也不说。
想起吴乐乐鼓励的话语,我发誓自己这次一定不能让她失望。
“好。”我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后,便挂了电话。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十年前做不到的事情放在十年后,我同样还是做不到。
“我当然介意!”
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却避而不答:“你还太小啦,不懂得大人的心事,等你长大就知道喽!”
我一点儿也不谦让他:“谁让你喜欢穿西装跑出来串门啊?我们两家只隔了一条路,你大可以穿睡衣来嘛!我不会介意的。你看,我都好心收留你在我家过夜了,还把我的被子全部分给你,我够意思了吧?”
左凡柯还是老样子,我根本无法从他的脸上观察到任何的情绪变化。唯一多余的,只有他手中待扔的垃圾袋。
我很害怕,害怕有一天父亲真的会在我的心里死去,害怕我们仅存的一点点记忆也会被残酷的生活腐化掉。
“哦,呵呵,我……”我一边笑,一边飞快地跑回去把沾满了油污的袋子捡回来,递给他,“抱歉啊,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你真的好善良啊!”
没错,这几年来我渐渐懂得了这个不算深刻的人生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好像已经无法记起父亲的脸庞了。不管他如今身在何处,但在我的心里,已经很少有他的痕迹了。
我的背弯得更加低了,一小步一小步地朝门外挪。
我心中一紧,来不及多想就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我很确定,他说这话时的口气不是疑问,而是肯定,是感叹。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是否认的,却不自觉红了脸。
他推了一下我沉重的脑袋:“这是给我买的。喏,这才是你的,笨蛋!”
他愣了愣,摇摇头:“还真没有。”
我和他并肩靠着沙发席地而坐,我不想吃泡面,他便很爽快地从外面买来了啤酒和小菜。
“我……”我有些不知所措,似乎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甚至在那一瞬间我忘记了刘暄的存在,整个人像是被抛进了深不见底的悬崖,除了下坠,就是下坠。
带着深深的疑惑和兴奋,我再次踏入了属于他的秘密领地。
我的双眼瞬间闪起了动人的泪珠,问:“这是真的吗?这不是我在做梦吗?”
他用被子紧紧包裹住自己的身体,望了我一眼,问:“你怎么没有感冒?”
如今,对我来说最大的现实是:交稿日期临近,我的文档却空空如也,一个字都不剩了。
我笑嘻嘻地接过他手中的垃圾,二话不说就跑到垃圾箱旁边,干脆利落地丢下。
左凡柯好像忘记了曾经发生的不快,他不仅客气地请我坐下,还给我倒了一杯凉白开。能喝上他亲手倒的白开水我已经很知足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是和解的前奏吧!
我瞪了他一眼,看到他瑟瑟发抖的身体后,还是有些心软,将自己脖子上的围巾摘下护住他的口鼻。
“好冷啊,伍月。”
夕阳西下时,我终于走到了距离住处不是很远的社区大楼。这一段仅仅只和_图_书有十五分钟的路程,我却走了整整一天。
我回头,看见刘暄已经坐起身来,正在冲着我诡笑。
不出意料,他果然是这样回答的。
在返程的火车上,我再次接到了会长的电话,他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寻亲活动。之前我总是刻意回避这种集体活动,可是那次我却破天荒地答应了。
我表现出有些感动,是我离开太久了,所以老奶奶想我了吗?
一切或许都是命中注定,从父亲和母亲离婚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在寻找亲情的路上,我只能是孤单的一个人。
我觉得心中酸酸的,一遍遍翻着手机通讯录,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给谁打电话。
他绕过我,走到刘暄身边,摸了摸他的额头,对我说:“他发烧了,你不知道吗?”
就在我疑惑之际,房租老奶奶敲开了我的房门,对我说:“姑娘,这段日子你去哪里了啊?”
电梯门打开后,刘暄一个箭步跃上去,我却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冲我咳嗽了一声:“伍月,你快上来啊!你不是答应送我回家的吗?”
我不知道自己前一天晚上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总之第二天清晨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和刘暄竟然挤在一张窄小的沙发上。他身上的被子几乎全部被我抢了过来,而我的头正好嵌在他的脖颈处。更加难堪的是,我的口水流了他一身。
我摊开手,摇摇头,耸耸肩,一副轻松的表情:“这我就没办法了。”
他有些得意地低头,却看到了自己衣服的胸口处有一片水渍。
眼下,他接连打了三十多个喷嚏。在他打喷嚏的这段时间里,我也没闲着,又给他冲了十包感冒灵颗粒。
再一次,我将我熟悉的城市、我的家乡抛在了身后,只为了一个目的和信仰:我要找到我的父亲,不管他身处何处,就算乘风破浪我也要把他找到,然后拥抱他,告诉他:“爸爸,我真的很爱你!”
他一边拉开被子慢条斯理地脱着衬衫,一边说:“你又把我想歪了不是?我是说,你把衣服脱了给我穿。”
下一刻,换我用同样的姿势和声音嘲笑他:“刘暄,那是……是我的口水!”
他灵活地闪开,对我做鬼脸。
我说:“会长先生,您如果不介意的话,还是叫我伍月吧!这次东北之行,我虽然没能找到我的父亲,但我好像明白了你们的心情。不,应该是……应该是我们共有的心情。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不是吗?就像刺猬一样,除了它的同类没有人愿意靠近它,没有人愿意给它温暖,它们只有抱成一团,才能生活,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抬起傲娇的脸:“当然,谁像你一样冷血,我可是很善良的。”
凭空的,家里面多了一个熟睡的男人,凭空的,心里好像涩涩的、痒痒的。
我没有去旅游,更加不是外出散心。母亲和父亲离婚后,我似乎就已经失去了放松和休闲的心情。父亲失踪已经十年有余了,在这十年里,他没有给我打过一通电话,也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我甚至连他的死活都不清楚。
他的手和左凡柯的完全不一样,左凡柯的手柔软而温暖,而刘暄的手却僵硬又冰冷。
他掸了掸西服上细微的灰尘:“这么脏了,你又不吃。”
我坐在花坛边,嘲笑自己的胆小和怯懦。
“是的,不过我们也不敢确定。你如果有时间的话,自己去确认一下吧!”
他的双眼怒放凶光,像是要把我吃了,怒骂道:“伍月,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这件衬衣有多贵?”
“奶奶,您走好,我不远送了。”
我能明显察觉出他神情的摆动和不安,但只是一瞬间。
他打电话过来时,我刚刚回到家。
我没好意思再捡起它来,反而是一双干净的手把它轻轻托起,然后毫不犹豫地扔进了走廊的垃圾箱里。
“喂。”
我睁开紧闭的双眼,侧过头去看到了他恼怒的眼神,还有额角暴起的青筋。
瞬间,我整个人犹如被扔在了深秋寒冷且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耳边只剩下树叶飘落的“哗哗”声。
但有时,沉默是比后悔更加恐怖的一件事情。就在五分钟之前,刘暄突然昏睡,他选择了沉默;我因为勇气不足,同样选择了沉默;左凡柯有过好奇,但最终也被沉默所代替。
吴乐乐激动起来:“尴尬就对了。尴尬恰恰说明他心和*图*书里有你,你心里也有他。你说呢?”
“你以为睡觉就能解决问题吗?伍月,”她坐到我的对面,郑重其事地说,“你现在要做的不是逃避,是面对。你随便找一个借口,比如说借一下菜刀啊之类的,把这件事和他说清楚不就好了?”
在别人看来,我们可能只是一拨再普通不过的游客。但他们不知道,每一个笑容的背后都暗藏着很多无奈和愁苦。我们似乎是为了活下去—更好地活下去,才刻意掩盖了自己的心事。
“能有多贵啊!大不了我稿费不要了,全赔给你可以吗?”
几分钟后,他松开了我,转身走向卧室,小声说了一句:“你走吧!我累了。”
刘暄耳朵尖,听到了我的话。
我嘻嘻笑着,把被我扯到地上的被子蒙在他的头上:“我只有一条厚被子,前半夜你盖,后半夜我盖,很公平嘛!”
他坐下来,打开一罐啤酒,仰着脖子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将它消灭干净,然后毫不犹豫地将空罐子捏扁,一动不动地问我:“伍月,你喜欢我表哥吧!”
左凡柯说罢,搀扶着刘暄,不顾我的阻拦走进了电梯间。
我快要急死了,并不是担心刘暄的病情,而是害怕自己的态度会影响我和左凡柯刚刚有了一些进展的关系。但电梯门已经关上,任凭我再用力,也打不开了。
都是西装惹的祸
那时候,我完全忘记了左凡柯、刘暄、吴乐乐等这些朋友。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反应,更加没有时间给他们发条短信,报个平安。等我想到这件事时,手机刚好没了电。
“切!你感冒我就要感冒啊?你的身子也太弱了,连我这个小女子都不如。”我实在佩服自己坚强的身子骨,但仔细想想后才发现,我好像只剩下这么一个拿得出手的优点了。
后来,我长大了,再后来,我写了书。直到那时我才慢慢理解工作人员的心情,他们或许是不愿看着我伤心难过吧!他们或许只是想帮帮十多年前尚且年幼的我吧!
他好奇地问我:“这是什么?水吗?”
“伍月,我应该谢谢你吗?”他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我趴在窗口向下看了看,几乎察觉不到楼下的一点动静。
时间仿佛凝固了:我的手臂在半空中停留,刘暄的身子靠在我的肩头,在他的身后站着左凡柯。他和我们一样,都被冻结在了温暖的春风里。
最开始的几年里,我很叛逆,任凭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听。在我看来,他们井井有条的工作程序只不过是一个冷冰冰的不会讲话的印章罢了,可我的父亲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残忍?
我说:“随你喜欢喽!我们是邻居,用不着这么客气。”
“哎,刘暄,你干吗呀,浪费粮食!”我想要制止他,却晚了一步。
“你……”
是时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你想要放下某件事,不再纠结,那你就必须狠下心来亲手去结束它。在以后的日子里,这道血淋淋的伤口可能会流脓,不过不要担心,日子久了,它就会慢慢结痂。到最后你会发现,忘记其实只是一瞬间的事。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翻了个身,蹑手蹑脚地从沙发上滚下来,无奈手一滑没有撑稳,屁股重重摔在了地上。
资本家果然就是资本家,冷血无情才是他们的本性啊!
“试问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煎熬的情绪是什么?不是爱情,是沉默,是无法坦诚相对。”
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抱着刘暄的西装时,心中想的却是左凡柯。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我想要去刘暄家还衣服,走着走着却莫名其妙地来到了左凡柯的家。
“说你胖你就喘。楼下就有。”
即使我一口气冲了五包感冒灵颗粒给刘暄,但还是挡不住他激烈的咳嗽声。
“你先表白又怎么了?”吴乐乐说,“被拒绝又怎样?又不是天崩地裂,更加不是世界末日。就算是天塌了,地陷了,也有高个子的人撑着,你怕什么?你这就叫‘庸人自扰’!”
“什么!”我惊恐地抱住身体。
我们的亲人,你在哪里?
只是没想到老人们说的话这么灵验。前一秒我还在嘲笑刘暄,结果下一秒,我的屁股还没坐上沙发,面包片还没有吃完,门铃就响了。
他对我的无视让我很是生气,我不悦地答道:“我知道,可和_图_书这和你没关系吧?”
吴乐乐点头如捣蒜:“伍月,自从你失恋后,整个人的境界都提高了!”
因为现实恰恰证明,我懦弱的坚持不是没有回报的。
“没关系,这西装口袋里有一个皮夹,里面有几千块钱,你拿去用吧!”
如果说脸红心跳就是爱情的话,那么此时此刻,望着圆圆的月亮,我十分肯定自己确实喜欢上了左凡柯。至于我为什么会喜欢他,我又喜欢他些什么,如今看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他摆出一副“吴乐乐式”的表情,盯着我看了好久,扭头又喝下了一罐啤酒。
换衣风波
我说:“我已经把我最厚的棉衣都给你穿上了,你还要怎样?”
只见刘暄从口袋里拿出一袋牛奶,我接过去时,还是温热的。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真的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心中想的是一回事,嘴上讲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从看到左凡柯的那一刻起,我诚心祈求过上天。我希望时间可以回到我们初次见面的那天,我希望我们不要认识彼此,不要踏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尴尬和难堪,不会有纠结和抱歉。
我开口了:“嗯,你……你”
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顺利,会长口中那个长相与父亲相似的老人,并不是我要寻找的父亲。即使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他了,但我知道,他不是我的父亲,他只是一个和我父亲一样可怜的老人。
社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经常来劝我:“你父亲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你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消息,说不定……其实,按工作流程来说,你完全可以报死亡处理了。”
为今之计,只有静悄悄地离开,当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才是一个最明智、最好的选择。
误会
火车准时到达终点站,我没有丝毫犹豫和停留,买了一张前往浙江杭州的火车票。
过去的两个月对我来说仿佛是一场梦,我为之努力过,却不得不回归到现实中来。
“怎么没关系,他是我表弟。你别管了,我带他回去。”
一如既往的玩笑口气,我竟听出了苦涩的味道。似乎长大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没人愿意长大,但总是被迫长大。
那一刻,我心底甚至有种轻松的感觉。天气不是很热,但我还是冒出了一身的冷汗。
我长出一口气,揉了揉屁股,拎起拖鞋朝门外走去。
他把脏兮兮的衬衣还有西服丢给我:“你洗干净了再给我送回去。”
“你有事吗?”我第一次用这种冷淡的口气和左凡柯讲话,一方面是难以解释,另一方面我也很想看一看他的反应。
为了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要马上结束它—亲手!
当我赶去火车站时,前往哈尔滨的最后一趟列车已经开走。我只能订了第二天一早出发的高铁票,然后一个人在候车室从凌晨坐到了天亮。
老奶奶无奈,将手中的袋子交还到我手里,说:“我说的是衣服,你又扯到哪里去了?我看这西服挺贵的,弄丢了就不好了。对了,这……是你男朋友的吧?”
这是刘暄第二次和我谈起左凡柯,对于我来说,则是第一次正面回答他的疑问:“我和你表哥最多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嗯……有几次他帮过我,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了。除此之外,我们真的真的真的毫无关系!”
“你”了好久,我按照吴乐乐的吩咐,随便找了一个借口:“你最近有没有见过刘暄?”
“嗯。”我点头时已经热泪盈眶。
希望来得那么快,却又消失得那么迅速。
我擦了下口水,想歇斯底里地把他叫醒,问问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转念一想,他昨晚喝得烂醉如泥,一定是我半夜被冻坏了才不知廉耻地爬到他身边的。
话还没说完,他就打了一个喷嚏,然后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不过我也因自己的自私而受到了惩罚。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我委屈地抱着双膝流泪。后悔,就是上天对我的最大的惩罚。
刘暄的大笑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挺直了身板,趾高气扬地将手中的拖鞋朝他扔去。
“谁?我爸爸吗?”我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一边哭一边问。
我仓皇地将房门关上,看着怀里的那套西服,不住叹气。
他看了看自己潮湿的衬衫,又看了看我身上穿的睡衣,最后做出了一个荒唐的决定:和图书“你把衣服脱了!”
她没有回应我,略坐了一会儿便离开了。
等到我终于到达预定目的地时,社区的工作人员早已经下班回家了。
对呀,如果我想要找刘暄,何必来找他呢?也可能,他才是我心中最惦记,最想见到的那个人吧!
“好点了吗?”
我一再补充定语,可是好像越解释越糟糕了。
我强辩道:“我……我是不吃,但我可以喂猫,喂狗吧?”
“你……你的那点稿费连一枚纽扣都买不了!你拿什么赔我?”他冲我大喊。
果不其然,他最后醉倒在了我的家里。任凭我如何喊他,他都昏睡不醒。
“什么?”
会长很意外:“伍小姐,这可是六年来你第一次答应参加活动啊!”
他走进了屋内,可房门还开着,这意思是要邀请我进去吗?
“衣服—他的衣服—他忘在我家的。”
老人们经常对我说:“背地里可不能说人哦!”可我偏不信。
每每看到这套衣服,我都能想起之前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你看,这是干洗店托我给你送来的,我找不到你,只好一直在我那儿放着。姑娘,不是我倚老卖老说些胡话,也是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出门从来不带脑子,下次可千万别忘了!”
手机的震动声让我有些厌烦,但我还是接起了电话。
三日后的清晨,我在熟悉的时间和地点醒来。
我感觉到深深的无力,把刘暄推到墙边,让他靠在那里。
坐在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时,我其实有点庆幸自己的懦弱。
“什么……可我没钱,你也看到了,我连空调都开不起了,你这种高档的衣服,肯定要花不少的干洗费吧!我可出不起,实在不行的话,我也可以手洗,只要你不介意。我是无所谓啦!”我有气无力地回应道。
“你去哪儿?”
喝到最后,他有些昏昏欲睡了。
我崇拜地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来表达我此时此刻激动的心情。
幸好,他终于停住了前进的步伐,站在我的身后,双手箍住我的肩膀。他剧烈地晃着我的身体,一遍遍重复道:“你看到了吗?刘暄的家在那里,你要去找他,何必来找我!”
虽然已经是深夜,我却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疑惑:我的父亲怎么去了遥远且寒冷的东北呢?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最怕冷的人了。
就在我步行前往社区的过程中,心中有过很大的怀疑。这看似轻松的一个举动对我来说是具有毁灭性意义的,在当下,可能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够懂得这种感受。
“这……好吗?”
加入“父母委员会”已经六年的时间了,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能够从会长那里得到一点点有关父亲的消息。
“好不好的,你试试不就知道了?你放心,你要是表白失败了,我一定来帮你搬家,让你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如何?”
“啊,原来我表哥又欺负你了?要不我去替你求求情,让他以后别再麻烦你了。”他一边说,一边就要朝楼下走。
刘暄披着被子朝洗手间走去:“当然!这是从你稿费里面扣的。你以后需要用钱可以找我来预支。”
他一边说,一边把衣服拉到鼻尖处闻了闻。
我再次傻眼。难道在我离家的这段时间有人偷偷潜入我家中,什么都不偷,仅仅是删除了我的文件吗?这个荒唐的理由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晚上,几巡敬酒后,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笑着笑着就哭了。这,或许才是我们最真实的状态。
夜晚来临,伴着室内浓重的酒精味道和轻轻的呼吸声,我本该睡一个好觉的,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可是上次那件事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彼此见了面也是尴尬,还不如不见。”
“还真没有!”我坚决地回复了刘暄提出的敏感问题。
我预料到我接下来的处境应该会很悲催。但出乎意料,左凡柯只是淡淡地问:“你找他有事?”
她忽闪着大大的眼睛盯着我,看得我头晕目眩,立刻想蒙头大睡一番。
我目瞪口呆,双手颤抖地握着那一沓子钞票,自言自语:“刘暄,我是该感谢你呢,还是……感谢你呢?”
我真的很想上前打他一拳,但想到他是我的出版商,也只能作罢。
我几次掉头返回小区的方向,走到半路又折回。一次次地折回,转眼就到了下午。
酗酒的上司
https://m.hetushu.com•com“那么我有幸请你这个善良的人吃顿饭吗?”
我想想,这个方法确实妥当,比她以前给我出的那些鬼点子靠谱多了。只是很奇怪,吴乐乐虽然和往常一样喜欢开我的玩笑,但是她的笑声好像不再纯粹,而是塞满了心事。
会长先生更加吃惊了:“伍……嗯,伍月,你说得很在理,回头我要把你的这番话告诉咱们的会员,让他们更加团结!我们要继续努力,相信终有一日会找寻到我们的亲人!”
“没想到,你还这么有爱心啊!”他贱兮兮地看着我,连语气都是贱贱的。
当我决定用吴乐乐的方法挽回自己和左凡柯的友情时,已经是两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我将他叫醒,说:“你要睡回家睡啊!我可不再收留你了。”
就在我们沉默的时间里,我几次开口想要同他解释这件事情的原委。但转念一想,我有向他解释的必要吗?或许他根本就不会在意,他可能只是好奇为什么自己的表弟会穿着我的睡衣出现在我的家门前吧?
在这期间,我去了遥远的东北,辗转又来到了和煦的江南。最后,才毫无收获地回到了家。
他不嫌脏,顺手接了过去。
我猛地颤抖一下,终于回过神来,看见他已经走出电梯,比我抖得还要厉害。
“是,是,”我赶紧说道,“我保证,下次出远门我一定带上脑子,不,在家里我也得时刻带着。”
此时的我和刘暄正站在电梯前,等待下楼。他百般央求我送他回家,我看在他是老板的分儿上,勉为其难答应了。
我快要哭了。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事,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要和我的胃过不去呢?刘暄和左凡柯不愧是表兄弟,他们一定是说好了来欺负我的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般怒气汹汹的左凡柯。他的样子确实把我吓到了,他该不会想要把我从楼上扔下去吧?
“我只怕有一天自己真正变为所谓的‘大人’时,你却走远了。”
他点点头。
刘暄虽然个子很高,但幸好身材比较瘦,所以勉强可以穿得下我的冬衣。但过分的是他不仅穿走了我唯一的睡衣,还罩上了我唯一的一件羽绒服。他给我留下的,只有一套待洗的西服和刚刚足够干洗的钞票。
他摇摇头:“当然不是垃圾,是我要捐给慈善组织的衣物。”
可那时的我想错了,因为不管我走到哪里,左凡柯都会找到我。我们同样会认识,会互相了解,也会像现在一样面对面站着,除了站着无事可做,也无话可说。
我吃惊地问道:“哪里有热牛奶,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刘暄一声不吭,我抬起手臂帮他测量额头温度。就在这时,电梯门再次打开了。
“什么?这是谁干的,谁把我的文件删除了?”我将嘴中的牛奶尽数喷到了笔记本电脑上,紧接着它便不争气地报销了。
不等他讲话,我就抢白道:“刘暄,作为朋友我真的很想提醒你一句,现在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但也不能穿得太少,春捂秋冻的道理没人告诉过你吗?”
我想了好久,答道:“我有东西要还给他。”
不!换句话说,我其实已经走了十年。
十二点,我回到宾馆,插上手机充电。未接来电中有吴乐乐打来的,也有刘暄打来的。除了左凡柯,所有的朋友都对我表示了合理程度的关心。
“既然来了,索性打个招呼再走吧!”我这样想着,刚刚打算按门铃,门突然间就被打开了。
我诧异道:“你是不是发烧了?”
他接着说:“伍月,这是你的家,你要去哪儿啊?”
我盯着那十罐啤酒,白眼道:“你确定你不是猴子搬来的救兵吗?我胃不好,你还买啤酒!”
我细想想,也是了。作为一个标准宅女,我很少外出,更加不喜欢光顾超市,那里面拥挤的人群、封闭的空间和压抑感通通让我感到害怕。
比我的遭遇还要悲惨的是那片面包。当我再次吃惊时,它又被狠狠摔在了地上。此刻,已经脏得不像样了。
我想要求饶,却紧张得张不开嘴。
这是吴乐乐从云南回来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想说的话很多,但最后聊着聊着还是避不开“左凡柯”这个话题。
吴乐乐很了解我,她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动心,所以她希望我可以越挫越勇。但我偏偏是一个扶不上墙的阿斗,在无法确定左凡柯的心意之前,难道要我先表白吗?如果被拒绝了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