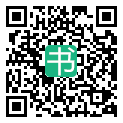第一卷 灵鹤髓
第八章 前缘旧恨伶仃人
他认定那只是恶梦。
景知晚眉峰微微扬起,扯了扯阿原的袖子。
比如,擦上一星半点在仿制的灵鹤髓上……
正要压下怜香惜玉的心思,将她押回衙门审问时,朱继飞已将她护在臂腕下,惊叫道:“不能抓她,不能……她,她重病在身,哪里经得起这折磨?”
李斐哼了一声,“你是想说,你跟朱蚀之死全无关联,只是恰好跟二公子要了些灵鹤血?”
姜探挣开朱继飞的手,又要往前冲时,李斐喝道:“再上前咆哮,给我掌嘴!”
阿原与井乙、丁曹等都相处融洽,知井乙家室所累,不敢出声,遂上前一步,懒懒笑道:“师太此言差矣!我佛悲悯,素来讲究众生平等,视王侯将相或贩夫走卒本无二致,师太何以如此计较贵贱之分?何况若有一百两黄金,我哪里住不得,跑这山野间喂虫子,也忒无聊。”
朱继飞兀自回顾车内,声音却已沙哑无奈,“探儿!”
靠墙的一面是个百宝架,放着若干装药材或药丸的瓶罐。阿原扫了一眼,已瞅见几个瓷瓶眼熟,正与当日装伪冒灵鹤髓的瓷瓶一模一样。
阿原一脚踩在车上,赶走车夫,拄着剑向他懒洋洋地笑,“那车里的姑娘是谁?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美人儿大家看嘛,何必藏着掖着?”
她居然把他和旁的女子扯在一起……
她一溜烟地跟着李斐跑开时,只闻身后景知晚闲闲道:“我只想告诉你,别毛手毛脚的,再被毒蛇咬几口!正经拔几株凤仙带身边,被咬了也不至于丢了小命!”
李斐对自己的得意部下极是满意,连连点头道:“对,对,就是因为棂幽之死,才让我们对朱绘飞起了疑心。算来,真是冤了他了!”
李斐也不急于逼他们即刻认罪。横竖证据确凿,回头堂上一审,杀威棒一打,不怕他们不招。
李斐很有气魄地一挥手,喝道:“搜!立刻把这人找出来!”
姜探淡粉的唇动了动,眉眼有些无奈。
竟一反方才的辩解,立时揽下所有罪名。
阿原问:“谢公子?哪位谢公子?”
井乙想去抓人的大手不由顿住,呆呆地看住少女,疑惑地问向阿原:“这……是凶手?”
一行人戒备着冲进去时,倒也未见毒蛇,甚至不曾见到半个人影。
朱继飞见姜探眉眼安静,竟也冷静下来,上前说道:“姜姑娘病得甚重,但父亲对灵鹤血管束得很紧。我听得大哥曾要灵鹤血过去给棂幽炼药,的确从棂幽那里要了一些,仅用于给姜姑娘配药而已。后来棂幽到底把其他灵鹤血给了谁配制假药,我等并不知晓。”
待阿原拉他,他才想起,如果朱夫人杀了皇帝的堂弟,犯的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皇帝绝不会饶她。
朱继飞紧捏着帘子,半挡住车内情形,说道:“原捕快说笑了!在下虽不才,还不至于做那诱骗良家妇女之事。”
姜探则盯紧暴露她的玫红色指甲,喃喃细语几不可闻,“不可能,不可能……”
一行人还未赶到县衙,那边已有衙役飞奔来报,说是京中使臣到了。
她举起其中一瓶,说道:“这个不是灵鹤髓,但这药里含有灵鹤血的成份!”
妙枫隐隐听得,问道:“还有何物证明此事与佛堂相关?不如拿出来让贫尼分辨分辨。”
景知晚终于转过脸,专心地看向跌跌撞撞冲过来的朱夫人,而眼前,还浮动着往昔那个娇俏的身影。
她尚有疑惑,李斐却已很满意,负手道:“二位,你们还有何话说?”
锦帘撩起,探出了朱继飞难掩仓皇的俊脸。
他的眼神幽黑,盯住她时宛如看不见底的一双深井,莫名令人心悸。
天很蓝,山很青,景知晚的鸡汤很好喝……
景知晚缓缓走过来,手中也多了一只小小玉瓶,“这里面,是玫红色的凤仙花加入明矾捣烂而成的花汁,可用来染指甲。染指甲时,需将花汁浓浓敷上,以树叶包住,第二日便会染作凤仙花的颜色。这期间若不留意,花汁便会沾到别处。”
可惜,那恶梦,竟永不能醒。
那马车在路上走得并不快,被赶到时更是欲行不行的模样。
阿原忙取过,拔了木塞一一试闻时,眼睛已经亮了。
以众人猜测,若是朱夫人涉入案中,多半是跟朱二公子暗有勾联,再没想竟一头抱住了姜探。
众人回头看时,却见两名健夫抬着一顶小轿如飞赶至,一个中|年|美|妇人正探出身焦急望来。
李斐顿住,“你……是说这些真灵鹤髓是你所炼?而毒害朱蚀的灵鹤髓……”
谢岩,慕北湮……
想想也是,山野里栽种招蛇的凤仙,着实不智。何况出家人又不能染指甲,再美艳的颜色对她们也无甚吸引力。
李斐问:“那什么姜姑娘有何来历?人呢?”
李斐原先担心朝廷追逼破案,影响政绩,着实对使臣的到来大是和-图-书头疼。如今凶手基本落网,偏生害人的和遇害的都不是寻常人,便开始盼望使臣尽快到来。如今忽听得使臣已到,却似想睡时有人塞了个枕头来,顿时大喜过望,笑道:“极好,极好!本官这便去迎接使臣!”
朱继飞一呆,脱口道:“不可能!不可能还有假灵鹤髓!”
其实也算不得玲珑细腻,只是她总在窥伺他的心意,不肯拂逆半分,和眼前针锋相对的阿原判若两人。
景知晚问:“怎样的贵客?”
若被乌鸦嘴说中,可真不是闹着玩的。
景知晚瞅她一眼,宛然在看白痴,“既然确定了与他们相关,距离真相大白已不远,何必多此一举?”
她凄惶环顾,低哑道:“没错,这些灵鹤髓,是我的。”
若对方有所察觉,难保不会提前将凤仙挖去,毁去证据。
见姜探不上当,阿原便继续道:“自然,你也没有杀人动机,也没必要将纤纤玉手染上血腥。你只是替朱二公子办事而已。那位王管事其实真是实诚人,一口道破二公子本性:貌似忠厚,暗藏奸滑!他害死父亲后,故意将假的灵鹤髓置于枕下,极易被发现,却也极易被人想到栽赃嫁祸,反而最易洗涮嫌疑。但你们所用的灵鹤血是从棂幽处得来,棂幽又很容易被怀疑,为了杜绝后患,你哄三脚猫本领的棂幽服下足以致命的金石药物,令他在回屋后暴毙。”
他只能在那恶梦里苦苦挣扎,努力从炼狱般的无尽痛苦里破开一条重生之路。
帘内竟是一个才十七八岁的少女,一身素衣,黑发如墨,容貌清秀之极,一双黑而大的眼睛盈满泪水,顾盼之际尽是小鹿般的惊惶无措,令人见之生怜,恨不得捧于掌心细加呵护。
“嗯,你没暗示,是我们大人神机妙算,向你作了点暗示。”阿原笑弯了眉,含糊地不提到底是知县大人还是典史大人的主意,“然后引蛇出洞,故意清查药铺,并告诉你找到了人证,只等那人从乡下回来便可去朱府指认。你惟恐露了马脚,反而提醒王管事他已被疑心,令他引开我们的注意力,趁机派书僮来通知姜探姑娘。书僮为避人眼目,故意从山间绕道而行,但丁曹早已暗中盯牢,一路跟踪发现了此处,并采摘了可以用作证据的凤仙离开。此时天色渐暮,他赶着下山,仗着健壮,便抄近道而回。但姜姑娘行事细致,察觉事情败露……”
阿原道:“你看,她生得又美,又会说话,又讨人喜欢,跟你简直是天生一对!你不是坏人,她自然也不是。”
景知晚却半点笑意俱无。
李斐愕然,“姜氏,你敢信口雌黄,戏耍本官?除非朱府上下都是死绝了,才能叫你一陌生人混进去换药!这病歪歪的,还能凭一己之力杀了棂幽和丁曹?”
姜探身形有些摇晃,纤弱得似能被一阵风刮跑。
棂幽死于金石药物,但炼丹服药者众多,有多少因此而死?何况他自己本身就是药师,虽然有点蒙人,也不至于全然不懂,明显是被比他高明太多的药师或医者所害;丁曹更是服药后神智不清摔死。他们的死,显然都是精通医药者相关。
见他竟不曾否认,阿原更笃定几分,转头冲井乙笑道:“井哥,如我等这样的粗人,拿着刀剑将朱二公子拖下来,是不是太不斯文?”
阿原无言以对,又将破尘剑用力地戳了下树干,垂头丧气地走向李斐。
妙枫接过,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沉吟道:“哦,若是此物,难怪会疑心我等。这佛珠清素小巧,雕工精湛,必定价格不菲,的确该是有些身份的礼佛之人才会佩带。话说庵中来往女眷虽多,如此别致的腰佩却也罕见。若贫尼曾见过,不会没有印象。看来只得劳烦知县大人到别处去找找了!”
那少女已提着裙裾,小心翼翼地下车,却还是踉跄了下。
景知晚已从袖中取出一物,淡淡道:“藏得挺严实,一般人也还找不出。”
连公主喜欢的男子也敢收入囊中,原清离这是多大的胆子!连公主都敢赶,原夫人又得是多大的权势!
“这都快结案了,怎能不管?”阿原提着破尘剑,用剑鞘一下一下地戳着旁边的老树,“就像做了一桌子的好菜,终于能入口了,咱们能舍下不吃就跑了吗?”
李斐很是羞恼最初不曾看出朱继飞的险恶,怒道:“你没有?姜探和朱府既无交集,怎会无缘无故仿制灵鹤髓?她的药又怎会跑到朱府,还跑到你父亲卧房?分明是你早有毒杀生父、嫁祸亲兄之心,令姜探炼药害人……”
小鹿的嘴角抽|动了几下,终于忍不住说道:“小姐,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你从没做过饭,做不出一桌子的好菜;便是做了,那也……没法入口啊!”
早上吃的鸡肉鸡汤还没消化完,阿原对他这一夜患和*图*书难与共好容易所积攒出的那点感情却已消化得差不多了。她压下气恼,笑嘻嘻道:“其实吧,我也觉得那姜姑娘不像坏人。”
阿原愕然,忙拉过她问:“什么事?”
言外之意,如有差池,这责任需县太爷担起。若日后影响县太爷的仕途,勿谓她老尼姑言之不预也……
阿原笑道:“贵干没有,公干有一桩。刚我们查案经过慈心庵,主持跟我们哭诉朱二公子拐跑了她们庵中一名女眷,我等只得前来看看,朱二公子车中是不是真藏了哪位美娇娘!”
正要令人将他们押入衙门时,忽身后有人惊呼道:“放开我儿!”
见她承认,李斐反有些不忍,叹道:“看着如此清灵的女子,竟能这般狠毒,真是红粉骷髅,红粉骷髅啊!”
又或者,朱晃心里清楚,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细究?
妙枫迟疑了下,说道:“那边精舍住的并不是庵里的弟子,而是留着招待贵客的。”
景知晚便道:“姑娘是想说,你触碰那些仿冒灵鹤髓时,并没有裹染指甲?”
朱继飞紧揽姜探,哆嗦着喃喃道:“我没有,没有……”
井乙已红了眼圈,狠狠地瞪了妙枫一眼。
小鹿叹道:“小姐必定更记不得,谢公子和小贺王爷和你最投契,你出事前那一晚,就是他们俩通宵达旦跟你玩乐着……”
少女点头,将众人扫过,便向李斐行下礼去:“小女子姜探,见过大人!”
妙枫脸色变了变,忙道:“贫尼之意,既然大人怀疑姜姑娘与此案有关,还是赶紧将她找回来问清楚吧!”
也许,本就已是两个人。
妙枫犹豫着还要上前说话时,李斐怒道:“师太,遇害者乃是当今皇上同气连枝的宗亲!为何慈心庵会和嫌凶扯上关系?若皇上追究起来,只怕贵庵清誉难保呀!”
阿原便取出那枚佛珠腰佩,问道:“你看下可曾有你庙中的小师父戴过?”
井乙待要再去揪出那女子时,帘子已被一只纤细的手轻轻拉开,白玉般的手指流转着一抹鲜艳的玫红,竟似有弯弯虹彩在人眼前晃过。
朱继飞忙奔上前,将她轻轻扶住,轻柔问道:“还撑得住吗?”
姜探忽道:“大人,我说的是,这些灵鹤髓是我的,但它们并非毒药,而是强身健体的补药,是我炼来自己服用的。”
他看向姜探。
景知晚道:“从厨下的药渣来看,此女应该染了风寒,或患有咳疾,且病势不轻,应该无力藏入山间。既然知道逃离此处,必定有人暗中通知,此刻……多半在同伙的接应下沿大道逃奔。赶紧追,也要留意沿路车马。”
歪理邪论,气死人不偿命,不只他景知晚会……
阿原点头,看向朱继飞,“你明知朱绘飞不通医药,只与棂幽有过交往,偏说兄长结识江湖术士,暗示朱绘飞有机会取得害死棂幽的药物,使他更难洗涮嫌疑。并且,我等从未说过棂幽因何而死,你又是如何得知,并作此暗示?”
但庵堂内外翻了个遍,竟连最寻常的凤仙都未曾见到一株,更别说那种叶片小而密的特殊凤仙了。
他定定神,强笑道:“原捕快,忽然拦我去路,不知有何贵干?”
他言语间全然不信,但眼见姜探娇娇弱弱的模样,再想象不出她谋人性命的狠毒,心下竟有几分将信将疑。
正满额汗滴滴时,阿原明知他棘手,走到他近前,轻声道:“大人,带回衙门细审吧!”
景知晚道:“那个姜探是挺倒霉的,被坑得一辈子疾病缠身,便是真的参与谋害朱蚀,也是情有可原。”
小鹿连连点头,“对,对,谢瞳谢大人的公子,谢岩。他往年时常随侍在皇上跟前,后来被长乐公主缠得没法,便不时告病离宫,跑来与小姐相会。小姐不记得么?长乐公主还曾到原府堵过他,被夫人赶走了……”
李斐忙问:“该往哪边搜?若是搜山,只怕得多调人手。”
景知晚点头,转眸看向阿原。
毒蛇或许能藏于室内,凤仙却只能种于室外。
景知晚眯眼瞧她,她便愈加笑得眉眼弯弯,毫不畏缩地跟他对视,甚至也带了些微的嘲讽……
她又想起那个剑上佩有双雀纹流苏穗子的黑衣杀手。
小坏正勾在树枝上打盹,见她手势,立时振作精神,张翅在众人头顶盘旋两圈,飞了开去。
姜探低眉垂目,声音轻柔:“回大人,小女子许州人氏,与朱家……并无关系。”
李斐半晌才咳了一声,拖着尾音问道:“你叫姜探?到底何方人氏,何时到的沁河?与朱家有何关系?”
朱继飞涨红了脸,“原捕快请自重!”
小鹿将她扯过一边,看离众人远了,才上气不接下气地低叫道:“小姐,来的那位使臣……使臣大人,是谢公子!”
眼前是一座独立于庵堂的小院,院中芭蕉舒展,绣球吐蕊https://m.hetushu.com.com,更觉幽静雅致,一时倒也未见凤仙。
李斐沮丧,悄声问向景知晚:“丁曹会不会是从别处摘来的凤仙?虽说寺庙就这一处,难保附近也有在家礼佛之人。咱也不能因为捡了枚佛珠便一口咬定是慈心庵的吧?”
如今,梦在延续……
“姜姑娘本该打算以毒蛇伤其性命,不料丁曹身手灵活,不但避开,还将蛇斩杀当场。姑娘无奈,只得暗施迷魂之药,丁曹不防,遂着了道。迷失神智前,他曾试图抓住姑娘,姑娘虽挣脱,但心慌意乱之际,将佛珠失落……”
李斐眼珠子差点掉下来,“女儿?”
她的手纤瘦白皙,病人的指甲也该苍白黯淡,但她以玫红色的凤仙花汁染过指甲,鲜亮的一抹色泽曳于指间,立时添了几分娇艳。
阿原叹道:“谋害生父、嫁祸亲兄,如今又携同谋潜逃……如此行径,朱二公子劝我自重?”
她转头看向李斐,“若大人执意搜查,贫尼自然不能阻拦。只是若惊吓了贵人,上面追究起来,贫尼也只好照实说。”
阿原思量片刻,终于换上了然的神情。
其他人看向妙枫等比丘尼的眼神,便也全然没有了最初的敬重。
朱继飞面色顿时惨白,紧紧握住姜探的手,一言不发。
李斐掐指算时,若朱夫人所说是真,那时朱蚀应该尚在汴京,依附当时尚是梁王的朱晃,再不知朱晃对堂弟这笔糊涂帐知道多少。
姜探泪光闪动,忽叫道:“此事与她无关,与二公子也无关……是我,都是我……我寻机混进朱府,替换了灵鹤髓,逃出后,也是我杀了棂幽和丁曹,一概与他人无关!”
“我喜欢的……”对着小鹿诡异的神情,阿原迷惑片刻,额下便滴落大大一颗汗珠,“是……和我相好的那个谢公子?”
或许,在她心里,只有死去的夫婿才是她的夫婿。
小鹿急得跺脚,挥着手连连比划,“小姐你真糊涂了,还有哪个谢公子?就是你喜欢的那个谢公子呀!”
她将双手拇指并拢,勾了两勾,比出个成双结对的手势,做着鬼脸大笑跑开。
朱夫人却急急又要扑过去,厉声叫道:“不要碰我女儿!”
朱继飞噤声。
可惜她四周都是手执刀枪的捕快和衙役,再大的风都没法带她逃离重重围困。
井乙等领命,立时冲上前,一脚踹开小门,冲了进去。
进退两难时,忽听翅翼破空,却是小坏越过墙头扑楞楞飞来,栖到阿原肩头,邀功似的将衔着的一抹绿意拂到阿原脸庞。
李斐便忍不住有丝怒意,“那你又怎会在朱二公子的马车上?你的住处为何搜出灵鹤血所制药丸?”
对着她婴儿般无辜的眼神,阿原不由嘲讽而笑,“姑娘必定没想到,你在炼制或装灌仿冒灵鹤髓时,在其中一枚上留下了凤仙花汁的印痕。我开始疑心朱夫人或朱家姬妾触碰过药丸,但仔细看过朱家女眷和侍女,并未发现有人染这种颜色的花汁;后来听闻棂幽是经傅蔓卿介绍进朱府,又疑心傅蔓卿。但留意过她的指甲和妆台上那些脂粉之物,同样未曾发现这种颜色。贺王府意外发现深玫红色的凤仙花后,贺王府那位名医便也难免有些嫌疑。可惜他刚来沁城未久,怎么都没有杀人动机。”
景知晚似信非信地睨她,“哦!”
这种荒谬感,在他被断去双足、于荒野间独面群狼苦苦支撑时也曾出现过。
待看清车驾中风都能吹跑的纤弱少女,一时也呆住了。
井乙早带人将车驾团团围住,道:“虽是粗人,尚晓得人伦天理,岂不比斯文人强太多?阿原,你下不了手,我来!”
朱继飞沉默,抿着唇盯住阿原一言不发,却执著地翼护住车中之人,毫无退却之意。
李斐点头,悄声道:“或许三人都有参与。嗯,最好等使臣到了再审……”
“……”
他站直身,咳了两声,方道:“你是说,你才是真凶?”
那厢李斐已笑了起来,“朱继飞,你为何只是一口断定搜不出假灵鹤髓?难道早已知晓,那里没有仿制的灵鹤髓,却有真正的灵鹤髓?”
阿原紧随着要跟李斐等一起回衙时,忽见小鹿从路的另一头飞奔而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冲向她。
若不是阿原走到近前扶着,李斐几乎想闪身避开。
阿原顿了半晌,无奈说道:“看来,我得向大人告假了……嗯,我昨晚被毒蛇咬了,的确该休息两日……”
妙枫眼底便隐隐有丝傲气,“贵客么,自然要尊贵些。若是平头百姓,便是一百两黄金拿来,贫尼也不会让他住进去!莫非知县大人觉得这样的贵家小姐,会半夜里跑去杀一个微贱的小衙役?”
阿原被毒蛇咬怕了,持了破尘剑在手,才一脚踹开精舍的门,向后提醒道:“大家小心毒蛇!”
原以为那位姓姜的女子狡滑狠毒,缉捕可https://www.hetushu.com.com能得颇费一番手脚。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刻钟后,他们便追到了她所乘的车驾。
从身形和身手来判断,绝不可能是朱继飞所为。
阿原怔了怔,倾下身时,却听景知晚低低而笑,“你推理得极有道理。但这回好像逞不了才,还闹了笑话!”
李斐一竖大拇指,说道:“我亲带他们追去!劳烦景典史带人以此处继续搜,若能将真假灵鹤髓找出来,那便是凶犯杀人的铁证!”
全然无法置信的荒谬感,甚至压过了断足和豺狼撕咬的痛苦。
姜探的唇动了动,便抿紧。
众人举目,却见寺院院墙边另有小门,乍看似乎只是进出庵堂的普通角门,细看才发现墙外绿树浓荫之下,也有屋檐隐隐,分明另有玄机。
她当然得多多珍惜自己的性命,才能继续喝汤吃肉,逍逍遥遥当她快乐的小捕快。
那妇人低眉顺眼,容貌端正,却他们都认识的,朱蚀之妻,朱绘飞、朱继飞的嫡母朱夫人。
而他当然不是一般人。于是,他找出了朱蚀那些被替换掉的真正的灵鹤髓。
朱蚀潜心炼丹之术,不好女色。朱夫人虽是朱府主母,却甚少管事,根本没什么存在感,乃至李斐、阿原等查案时,并未太留意她。
“我自幼重病在身,只知救人,不知害人。”姜探上前一步,衣带翩翩随风,愈觉风致楚楚,“至于那位大人搜出的灵鹤髓,是我托朱二公子觅来配方,找来灵鹤血,自己配制炼成,与害死朱老爷的毒物毫无关联,再不知大人怎会疑心是我所害?”
李斐自然不想担那断送仕途的风险,何况这老尼姑上面有人,看起来着实不好惹。待要撤时,景知晚忽道:“大约今日或明日朝廷所派使臣应该就会赶来督查此案了。若再不破案,皇上震怒,这责任……”
阿原一眼看出这是朱府的马车,更是笃定了几分,立刻带人冲上前拦住马头。
众人不由看向姜探的手。
她凑上前,贼兮兮地笑,“这是在怜惜姜探?咦,难得姜典史也懂得怜香惜玉!放心,你回头可以向李大人求情,只要她牵涉不深,李大人必会卖你面子。”
阿原见他安静,倒也稀奇,得空走过去问:“我既闹了笑话,景典史何不分析分析,那对母女,到底谁是主谋,谁是从犯?”
朱夫人恨恨道:“朱蚀那厮,不知听了哪个方士胡说八道,说我八字极好,正与他契合,能助他早日修成正果,觅得长生之道……他竟让人将我夫婿推入水中活活淹死,又送走我女儿,强行娶我为妻……可怜我的探儿那年才六岁,被扔在远亲那里饿了四五天,发高烧哭哑了嗓子都没人管……好容易托人救下来,已经落下病根……朱蚀害得我夫婿横死,独女重病,偏生跟他要几滴灵鹤血救人都不肯,要我眼睁睁看着我的探儿死去!这样的禽兽,他不该死,谁该死?”
景知晚不耐烦道:“怎不去问问九泉下的爹,死前经受过怎样的折磨?别急,这一路你还可以继续照应着。你以为这事你脱得了干系?”
算来他们搜查屋外也够了。
他在县衙待得久了,极有眼色,猜着这二公子人证物证俱全,再难翻身,也便没了顾忌,冲上前去抓着朱继飞衣襟只一拉,便已将他扯下车来,跌在地上。
阿原抱头,“我当然不记得……”
李斐一时哑然。
阿原回头。
朱夫人已奔上前来,一把推开走到姜探跟前的捕快,紧紧抱住姜探,冲李斐叫道:“大人,这不关探儿的事,不关她的事……”
李斐文人出身,走得未免慢些,此时方才赶到,气喘吁吁问道:“怎么不抓人?”
妙枫被阿原明嘲暗讽一番,不由面色微赤,说道:“这位施主当是新来的吧?如果久在沁河,该知晓这慈心庵与别处不同。旁的不说,庵中比丘尼多为功臣遗属,若是有所差池,并非贫尼说一句众生平等便能交待的。”
朱继飞胸口起伏,白着脸无力地辩驳道:“可我不曾谋害父亲,从来不曾……”
李斐惊异半晌,方问道:“朱夫人,姜探是你何人?她此案无关,难道你与此案有关?”
阿原再不知他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因何而发。
阿原低咒两声,随李斐等奔出院门,忽又转过身来,在墙角胡乱拔了几株凤仙塞入怀中,才匆匆追了出去。
李斐无奈,正待领人离去时,景知晚忽道:“请问师太,围墙那边的小院,是何人居住?”
姜探道:“兵者,诡道也。只需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完全可以斗智不斗力。他们哪个是死于蛮力?”
李斐顿时挺直腰杆,叫道:“下官不想惊吓贵人,但查案是职责所在,岂能有所疏漏?给我冲进去,不许跑了嫌犯!”
景知晚已将四周细细察看过,说道:“你们赶紧找到这女子要紧。从卧房陈设和衣物来看,应该是个未www.hetushu.com.com婚少女,爱穿浅蓝或淡紫的衣衫,衣饰并不是太华丽,但很有教养。”他看了眼百宝架最上面的空格,继续道,“她的身材纤瘦,个子不高,染着玫红色指甲,应该很好认。”
景知晚挖了个坑给她跳。不论她说染或没染,前提都是她曾碰过仿冒灵鹤髓。
她双目通红,眼底的恨毒之意不加掩饰,已叫人不得不信,她真能做出杀夫之事。
姜探叹道:“大人容禀,因小女子自幼多病,不得不四处游历求医,也因此学了些皮毛。经过沁河时,听闻朱家独有的灵鹤血极其难得,且益气补血,正对我病症,所以千方百计求了二公子,取了些灵鹤血回来炼药。”
“嗯,小姐既然不愿见他们,咱们就先避避……这案子就先别管了吧!”
待搜到东梢间,阿原才知那是药的涩香。
他腿脚不便,但舆夫却健壮,睡了一晚好觉,想着双倍的赏钱,跑得飞快,竟也赶到了。
联想着有关这座庵堂的某些传言,李斐顿起退缩之心,正待敷衍几句离开时,旁边井乙听得她言语间轻慢遇害的丁曹,所谓物伤其类,暗暗愤恼,悄悄扯了扯阿原袖子。
李斐这一回带来的衙役不少,路上听阿原说了凤仙和毒蛇之事,只暗暗吩咐手下留意有无未开花的凤仙植株,或新近翻动的泥土。
朱继飞紧握住姜探的手,咬牙道:“原捕快想得太多,我并未暗示什么。”
她看向那精舍,打了个手势,笑道:“我倒是真的好奇,这贵家女子住这里来做什么?”
姜探虽身姿纤弱,神色偶有彷徨,却比朱继飞要冷静不少。但她听到那声音,脸上蓦地浮上惊恐,猛地抬起头来。
无论如何,抢着认罪总比没人认罪好。真凶已浮出水面,他心头那块大石也可放下一半了。
阿原忙道:“我要保护李大人,就不陪景典史了!”
姜探垂着看着自己的指甲,低低道:“不……不可能!”
景知晚虽一路坐着肩舆,但明显精神不济,倚靠在肩舆一言不发。
阿原接过看时,已然大喜,高声叫道:“凤仙!就是这种凤仙!”
见此女柔弱多病,阿原本有几分怜意,忽听得她矢口否认,顿觉她奸猾且矫情,冷笑道:“姜姑娘这是看着未曾搜出仿制的灵鹤髓,我等并无实据,打算一口抵赖?可姑娘知不知道,姑娘的指甲便已留下了线索和证据?”
阿原碰了一鼻子灰,大没意思,正待拍拍灰远离他时,景知晚忽唤道:“阿原。”
肩舆落地,他依然懒懒地靠坐着,轻笑道:“如果我说,我在姜姑娘卧房中把真假灵鹤髓都搜了出来,你是不是还会说,是棂幽死而不僵,暗中嫁祸?”
朱继飞慌忙扶住姜探时,朱夫人已跪倒在地,泪痕满面地向李斐连连叩首,说道:“大人,民妇不敢隐瞒,朱蚀之死,与绘飞无关,也与继飞无关,全是民妇一手所为!”
他欲言又止,好看的手指踌躇般轻叩扶手,笃笃的微响愣把李斐听出了一头的汗水。
阿原打量着姜探弱不胜衣的模样,略有些犹豫,“又或者,不是你亲自出手,另有人暗中帮忙?”
阿原走过去,令朱继飞、姜探依然坐上他们的马车,又亲将朱夫人送入小轿,好好地护送他们前往县衙,然后暗中吩咐井乙等人留意,莫让三人串供。若想辨出真假,回头两边口供一对,自然一清二楚。
竟都跑沁河这小地方来了!
阿原忙上前将她压住,向朱继飞笑了笑,“二公子,这姑娘被咱们粗手笨脚地掌上几十个嘴巴子,必定再也说不了话吧?却不知还能不能站得起来……”
李斐沉吟间,那边忽传来景知晚的声音:“连我们都无法确定,那仿制的灵鹤髓到底是棂幽所炼,还是他给了其他什么人炼制,为何你就能一口咬定,是棂幽给了旁人配假药?”
一排四间精舍,格局玲珑,陈设典雅,清香扑鼻,却是檀香里裹着说不出的气味。
连她小鹿做的汤都没法吃,何况连厨房门都不曾踏入过的大小姐……
那边井乙已奔过来,急急回禀道:“大人,院中未见人影,后院另有一道门,似乎有小道可通往山间,也可折往庵前的大路!还有,后院墙根下植有凤仙花,很可能就是丁曹摘取凤仙茎叶之处!他必定查到了此处,又被人觉察了踪影,才匆匆逃入山林离开,不料……”
“这死乌鸦!死乌鸦嘴!”
究其源头,竟是这么个见不得人的破事儿,还攸关皇室体面,这是他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能管的吗?
这时,朱夫人忽将姜探猛地一推,险些将她推倒在地。她叫道:“探儿,你给我闭嘴!我做下的事,不需要你们为我顶罪!”
朱蚀虽是白身,却千真万确是皇帝的堂弟;朱夫人虽是续弦,也是他们这一支名正言顺的主母,皇室宗亲。他小小的七品知县,好像有点受不起这一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