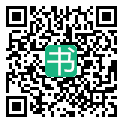第二部
第三十四章 几时归去伴卿醉
我怎会不饿?伸头望一望旁边摇篮里沉睡的小宝宝,我叫道:“夕姑姑,我饿……”
“公主,公主,你醒了么?”夕姑姑欢喜地跑来,笑道:“我还捂着鱼汤在那里呢,这就端来给你吃!”
“我的家国和梦想……”宇文清重复着我的话,原本如珠般闪着柔光的瞳仁渐渐失了神。他默默坐到我身畔,轻轻说道:“我呆在黑赫,是不是会给你带来困扰,让你不开心?”
奇怪的是,宇文清自那日去后一直没再出现,甚至连他的箫声都没再听到过。
一双黑瞳,洁净无尘。
我已复原得差不多,只是夕姑姑说产褥期不能见风,因此总不曾出帐篷走动。此时听说宇文清病了,顿时呆不下去,忙道:“夕姑姑,帮我备件厚厚的袍子吧,我去瞧瞧他。”
其他各部落的首领、内眷听说,也各各派人前来探望,赠送的礼品,同样堆得小山一样。黑赫民俗开放,又有昊则等人护着,我虽孤身回黑赫,夫家未明,倒也没有那么多的流言蜚语相侵。
宇文清一定也累得很了,走出去时一步一步很是缓慢。到得门口时,又冲我望了一眼,微笑了一下,也不知是不是因为灯光昏暗,还是我的视力没有完全恢复,我总觉得他的笑容有些虚浮,甚至和他的面色差不多的黯淡,模模糊糊看不分明。
我香甜地喝了两口汤,望着宇文清慢慢立起的身形,心酸中有一抹深切的欢喜:到底,他还是原来的白衣,肯这样的守护着我。纵然两人之间,依旧隔着山,隔着海,再不能在一处,可心底,到底还在彼此守望,彼此关切。
这极北塞外,能弄箫抚琴的,本就极少,而能将箫声吹得如此意韵深远的,除了宇文清,我再不作第二人之想。
不,姓宇文也没关系,只要你与我偕隐草原,远离是非与纷扰,我便知足。
“陪我……陪我一生吧。”
我沉默片刻,眼看已到了他的帐篷,遂钻了进去,方才说道:“可惜,我们终究还是回不到几年前了,是不是?”
那位胜出者,是昊则。估料着人家见他去参赛,也不敢和他较劲,因此他自己赢得毫不意外,倒是抱着无恨走马围场时更要开心一些,沿路眉开眼笑,十分得意。
满月那天很热闹,钦利可汗特地举办了一次赛马会,最终的胜出者抱了我的无恨在围场骑马跑了一圈,以示将胜者的勇气和力量与尊贵的小公子分享。
宇文清远来是客,他的帐篷在东面隔了好几处毡包的稍高地段。我沿了如银的月色,踏着敷了层轻霜的青草,在那如割的冰冷寒风中,向前冲去,却突然顿住。
夕姑姑忙搡着他,笑道:“王子,公主还在和-图-书月子里,不能烦心呢。还是过阵子再说吧!”
轻轻叹气,想着,他这么不打紧地病着,也好。不然,只怕已回南越做他的太子去了,还要和安亦辰拼个你死我活。
我才知当时他虽在安定着我,自己也捏着把汗。我的确是难产,再拖下去,可能真就小命不保了。
箫声中所传递的,分明是归隐的信念哦,他不想浮名虚利,不想虚苦劳神,只要伴云从月,诗酒相和!
平安,我想要知道的,也只这两字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帐篷几乎是从未有的热闹。
宇文清一声声唤着我的名字,用尽双臂的力道紧紧抱住我,渐渐炽热的吻似要燃烧起来。我的神智已被抽空,转成一片快乐的空白。
静静与我相对时,只看得到我自己的容颜,和着烛光,在他瞳仁内跳动着,浸润于一团如水的温柔之中。
宇文清拍了拍我的脸,微笑道:“吃鱼汤吧!你不饿么?”
“无恨,无恨……皇甫无恨……”
其后的许多日子,我再也不曾提过宇文清,也不曾再问过他的动向。他的走,或者留,对我已毫无意义,我不想为此再去多一分烦恼。母亲一直盼我有个可栖情处,可惜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无处栖情!
我微笑地唤着孩子的名字,滚下一滴晶莹的泪珠,落在他粉红的面颊。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
你肯么?
我听她说得有理,一时未便就去,只是心里着实忐忑,再不知他目前病到了何种地步。
如此又过了七八日,我依旧在我的帐篷中休养着,终日只凝望着无恨肥嘟嘟的小脸,也觉不出寂寞来。只是听说宇文清一直在服药,始终不曾再来看望我,让我很不踏实。
我的话才说完,猛地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心格地一跳,几乎顿住,而宇文清温润的笑容立刻无限地放大:“你的眼睛,终于恢复了!”
“栖情!”宇文清唤着我的名字,忽然冲了过来,已从身后将我拥住,紧紧地拥住,声线颤抖着:“就不肯让我陪你一段时间么?你还是……厌烦我么?”
我惊忡了半天,忍不住也绽开大大的笑容,傻瓜般地伸出手去,把宇文清光洁柔和的面庞摸了又摸,傻笑道:“是啊,是啊,我看到了!”
“病了?”我神思一恍惚。
连心灵都在战栗时,我听到了宇文清苦涩痛楚的低喊:“情儿,清无能,许不起你一生的幸福,许不起!”
第二日,昊则不知怎的听说了传信之事,到我帐中坐了好久,忽然和我说道:“栖情,你若真的很喜欢这个宇文清,我把他扣在这里,再不许他回去,让他做和*图*书了你的夫婿,好不好?”
宇文清温和望着我,明珠般的瞳仁,有着劫后余生的庆幸。
添丁是其一,恢复视力是其二,钦利可汗赐了不少代表如意吉祥的玉器、骨器过来,因听说中原有产妇饮鲜鱼汤、鸡汤养身的习俗,特地叫人到边境买了鲜鱼和活鸡,专炖给我喝;
这一次,昊则没有躲,站在那里委屈地叹息:“栖情,我说的是真的。你才比我大了那么两三岁,年轻得很呢,难道就为和安亦辰决裂了,以后就不嫁人了?我瞧着那宇文清待你不错,你又有那个心,才为你这样思虑着,哪里又说错话了?”
安亦辰,宇文清,明明都喜欢着我,终究,都离开了我,也迫得我不得不离开他们,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到第二天傍晚我醒过来时,我才知道,宇文清指的,是另一层意思。
“在黑赫,以白衣的身份,陪我一生,好不好?”
酒斟时、须满十分。
那个以为不能实现的梦想,真的有可能实现么?
我不想耽误他的前程,但我还是软弱,软弱地一时就说出口了,然后缓缓靠到他的胸膛。
那一天,很冷,也许,是因为我在月子里,身体还很虚弱吧?回去的路上,连月光都如寒风般渗着凉意,冷得我直掉眼泪,好后悔走了这一遭。
我点点头,看着他额前松散垂下的一缕发丝,被烛火投照着,映了一片安静的阴影,静静拂动于美好秀逸的苍白面颊,试探道:“若是好得差不多,你也该回你的大越了吧?你的家国和梦想,都在那里。”
这一次,我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字迹甚是俊逸,行笔处也是连贯,可见写字人的确无甚大碍。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夕姑姑,宇文清……回中原去了么?”我终于忍不住问起夕姑姑。
他伤我至深,而宇文清早晚会离去,终究会只剩了我,带了这小小的婴儿,遥望着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为了所谓的国家社稷,生死相拼,血肉相搏。
我如同被人从火焰山一下子扔入冰冷的海水,所有的冲动和兴奋,霎那烟消云散。
“情儿!情儿!”
我摇了摇头,回头他看面容时,依然很是苍白,眉宇间隐有憔悴病容,遂问道:“你什么病呢?怎生拖了这许久也好不了?”
无恨似觉出了不适,张了张嘴,小手在襁褓中挣着,啊啊地哭了起来。
犹豫半晌,只拿张空白信笺折了,置于封套之中,封好,让侍女送去给宇文清。
看他稚气尚存的面孔上,居然一本正经的模样,倒叫我说不出话来了。
唇舌纠缠时,那愉悦和*图*书的战栗,是我久违了多少时候的幸福?
肯为我放弃业已到手的江山与权势,富贵与尊荣么?
他本为医我双眼而来,如今我既已复明,孩子也顺利降世,莫非他依旧回了南越,卷入到与北晋安氏如火如荼的大战之中?这本是我所期望的,但他若不声不响走了,也不和我告辞一声,却又让我不由黯然。
而宇文清,居然也就由着我走了,没有追出来,更没有安慰一句,解释一句。
“白衣……不,清,从此我们便在这里开心活着,一起到老,到死,好么?”我喃喃地说着,泪意迷蒙:“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若走到这种地步,我们的誓言还可以实现,我会用一生虔诚地感谢上苍,将你送回到我的身边。”
自从浏州再见面,我几乎没看到过他精神奕奕神采飞扬的模样,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么?
宇文清的身体明显僵了一僵,然后有些颤抖的手臂温柔地旋着,将我扳过身来,面对着他。
且陶陶、乐尽天真。
我怎会厌烦他?他的话语,他的笑容,他的拥抱,都是我多少年来的梦想,即便在与安亦辰最情浓之时,也曾如针尖一般无声扎于心底最深处。
思虑片刻,我叫侍女取来纸笔,欲要写几个字相询时,又不知从何说起。
夕姑姑忙拦道:“现在不能去。他正病着,这会子去了,过了病气,就是公主自己不在意,宇文公子只怕也要过意不去了。何况宇文公子自己也说了,公主才生产,身子正弱,一定要好好调养。我看公主还是隔几天在去瞧他吧!”
那么还不如不陪,趁着那从灰烬中重新燃起的感情尚未燎原,及时抽身退步,以免再度沦陷,直至万劫不复。
而端了鱼汤走过来的夕姑姑,笑容已和宇文清一样欣喜:“果然复明了么?宇文公子说你可能已经恢复了,我还不相信呢!”
而昊则见我不答,又道:“如果你不喜欢他,那最好。等你身体大好了,我迎你过门,你以后就住我帐里好了,我来照顾你一辈子。无恨长大些,直接让他学着叫我爹爹。”
初时我尚能泰然自若,只作并不在意,眼见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转眼孩子落地已有十天了,他居然还不见踪影,渐渐让我不安起来。
宇文清更久地沉默,然后盯住那不断跳跃的灯火,低沉说道:“不管过多少年,历多少事,栖情,总还是那个栖情,能将一根狗尾巴草的戏言,用岁月磨成了最真实的存在。栖情,让我多陪你一段时间好么?若不能见你们母子好好地生活着,我总不能放心。”
昊则最有趣儿,一心想我那和_图_书才几天大的儿子叫他叔叔,同时对宝宝的皮肤大是疑惑。因为他认定我的皮肤很好,小孩的皮肤一定也会雪白粉|嫩,不懂为什么会那样又红又黑,皱成一团。——却不知,婴儿初生时皮肤都是那样,要到满月时才能褪去胎里带出的红黄肤色,变得光滑白|嫩。
宇文清用手指轻轻弹了弹我的鼻尖,笑道:“你啊!还是几年前的脾气。”
我推开宇文清,愤怒漠然地瞪着他,然后掉头而去,再不看他一眼。
柔软而微凉的唇,缓缓贴到我额,鼻,然后是唇,缓缓厮磨着,属于他的清淡气息,迅速缭绕于鼻端,让我轻轻呻|吟,然后将他抱住,热烈地回应。
清朗月光,正寥落投于前方徐徐行来的那出尘男子,如雪白衣被冷风卷起,翩然翻飞处,如有莹光辉耀,让他整个人都镀了层淡银的晶芒。
果然,不一时,侍女就回来了,依旧原信交还给我,打开看时,还是原来的信笺,飘了淡淡的墨香,却只两字:“平安。”
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这日晚间,我正想着要不要和夕姑姑说下,明日一定去看看宇文清时,只听一缕箫音悠扬传来,缈缈袅袅,韵致清远高洁,拂然出尘。细细辨其音韵,乃是一曲《行香子》,一时立不住,已至天窗前搬过七弦琴来,随了那箫音,拂弦而歌:
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这么多日的针灸,居然在生育那样炼狱般的过程中起了作用,我的双眼,复明了!
夕姑姑点着头,慈和地望着他道:“公主没事了,你也该回去歇会儿了吧?从公主生产,你就一直守着……瞧你这孩子身体也不是很好,得多休息休息啊!”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我抓着桌上的一堆尿片,就向他扔了过去。
而我身畔人影一动,我才发现宇文清正坐在我的床头打瞌睡,一见我醒了,苍白的面庞立刻浮出微笑:“看到我了么?”
“夕姑姑,我不想提他了。”我打断了夕姑姑的话头。
我横着眼睛说道:“什么月子里月子外?我就瞧着这小子还是欠教训!看你连阿姨的主意也敢打!”
不想回答也不想拒绝他的话,我垂了头,默默站起,将裘衣领口紧了一紧,慢慢向门口走去。
多陪我一段时间,然后最终还是要走。
肯为我再度抛弃那个姓氏么?
“没有,见到你还和以前一般待我,我很开心。”我半倚到他身畔,轻叹道:“不过,你终究会回你的大越,而我,终究也不是原来那个年轻任性的皇甫栖情了。”
安亦辰……
一时昊则走了,夕姑姑一边hetushu.com.com捡起我扔的尿片,一边迟疑着说道:“其实……昊则王子说得也很道理。唉,秦王……现在正打仗打得顾不得吧?等他有一日发现那个传说中跟了越太子的女子并不是你,只怕要后悔莫及了。”
许不起?
宇文清见了,该知道我不放心吧?
我听他说得温存,不由心旌动荡,轻笑道:“有甚么如何是好?横竖你的医术好得很,还怕你不给我治么?”
我一时瞠目。
小小的眼角,居然也滚下一滴小小的泪珠。
我无声地叹息着,低了头在摇篮里温柔望着我的孩儿。小小的脸蛋,有着圆润清晰的轮廓,浓黑的眉,俊挺的鼻,尤其一双清澈的眼,极是明亮,像极了安亦辰宁静望我时的模样。
宇文清低了头,缓缓弄着炭火,半晌才道:“也不过着了凉,因为身体素来不是太好,又有些水土不服,才拖宕了这么些时候。如今已好得差不多了。”
而宇文清,纵然他还是那个不曾辜负我的医者白衣,我又怎能强留他下来,留他一颗我抓不住的心?
宇文清侧了脸不看我,只在唇边抿出丝笑纹,走到暖炉边加了炭,扶了我在暖炉旁的兽皮软榻上坐了,问道:“还冷么?”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
抬眼处,他也看到了我,眸光顿时柔润,迅速赶了几步,已紧走到我跟前,牵住我的手,边向他的帐篷跑去,边说道:“听了你的琴声,我就猜着你可能会过来,急急想先去看你,不想还是晚了一步。若这月子里着了凉,可如何是好?”
抚了抚烧红的面颊,我扭头抓了件裘衣披了,不顾夕姑姑惊讶的叫唤,弯腰钻出帐门,冲了出去。
“啊,他,他还在这里啊!”夕姑姑期期艾艾道:“那个孩子前儿可能累着了,正病着呢。不过,他的医术好得很,自己叫人煎药服着呢,应该不会有事。”
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他呆在黑赫,会困扰我,让我不开心?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以为,我还是固执地将他父兄所有的过错算在他的身上,或者,以为我依然信任着安亦辰,认定他害了萧采绎,追杀安亦辰么?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
宇文清靠住床棂,目光柔柔,叹息道:“你恢复了,我也放心了!”
曾经的伤害,和曾经的温暖,我都已不想再回忆。因为我不想再痛,为他心痛,亦为我心痛。
“好。姑姑请记着让她多吃一点,嗯,这次险得很,一定要好好养着才行。”
雪情早将幼儿的衣帽饰物送了一堆过来,又一天几次亲来瞧我;
我迷惘地点头:“看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