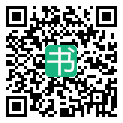第二部
第二十七章 揉碎轻花说缘尽
颤巍巍说完最后一句,嗓子口一阵阵的清甜,一时按捺不住,“嗤”的一口,竟吐出一大口鲜红的血来。
那鲜血阵阵簌动于一处砖石的合欢花纹中心,如同被冷风刮过的绝美花蕊,我眼前一阵阵的昏黑,几乎要瘫软下去。
果然,果然。
当日傍晚,我搬去了青衿馆居住,只要了夕姑姑一人陪同,其他人都被我赶得远远的。偌大的馆子,只我和夕姑姑两人居住,连打扫除草的下人都被我赶走了。
安亦辰攫住我的下颔,呻|吟般说道:“你随了他逃去的日日夜夜,我如受凌迟!我只想将宇文清碎尸万段,再打折你的腿,把你关在秦王府中,让你也尝尝,什么叫痛苦,什么叫……万劫不复!”
天知道,我多么盼望安亦辰终能容下这个孩子,哪怕我不得不向他低头,向他乞恕,哪怕他一时对我冷颜相向,相敬如“冰”。
那么,万劫不复的人,只剩下了宇文清,——如果他真还如以往那般爱着我,他也会,痛苦到万劫不复!
爱或者不爱,现在的意义似乎都已不大,重要的是,我要保住我的孩子,保住我的家,所以,我依旧竭力开解着安亦辰。
难道,那一日,我表现得很孟浪,很轻浮么?
被心上人说成不如自己的情敌,对谁都是相当致命的打击。
“给我时间,我会忘掉他,一定会忘掉他。”我匆促地打断他的话,吻一吻他柔软的唇,急急说道:“而且我发誓,我不会见他,永远不会再见他。”
相信只要他出世,他与安亦辰父子之间天生的血缘亲情,早晚会被唤起,而我的清白,则再也毋须分辩。我的幸福依然有着希望,纵然目前会很艰难。
夕姑姑忙拉我:“公主,别和他们计较,等王爷回来,我们和王爷说吧。”
但这一次,不管是不是他的骨血,他显然都不打算怜惜。我已觉出,他按在我小腹的手掌,力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五只手指,已经深深凹陷入我柔软的小腹,似欲这样子生生地扎进去,把他讨厌的孩儿连血带肉勾出。
习武者略有些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拭了我眼角的泪,如羽毛般尽量轻盈地滑过我的面庞,沿着我的颈,肩,胸,腹,温柔滑下,停于我的小腹处。
没有了安亦辰的支持和保护,在秦王府,甚至在整个的大晋,我都是孤立的,孤立而无援。
我的心跳隐隐加速。
安亦辰,你可知道,那份幸福,对我有多重要?
很痛的感觉,却不仅在面颊。
“一辈子!”我垂着袖子,轻轻笑道:“太远了。我顾着眼前就够了。”
安亦辰的面庞在一瞬间变得陌生。
安亦辰呼吸立刻浓重,灿如星子的眸中闪过冷厉和恨怒。或者,他有些方面真不如宇文清吧,但若从我口中说出,可能立刻变成对他的侮辱。
我安定地轻轻一笑,所有的思维渐渐被抽空了,陷入沉沉的昏睡之中。
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的悲哀和不安,我继续卧于榻上,阖着眼,只和图书作睡着,却终于还是忍不住,眼角慢慢溢出温热的水滴。
宇文清甚至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免我们夫妻失和;而安亦辰却在猜他用心卑鄙,如他那般一心想将我骗上床。
夕姑姑又是心疼,又是莫名其妙。她叹息道:“那些菜虽是大厨房的,不过并不是我们一处吃,别处也吃这些,公主为什么就不放心呢?”
宇文清性情虽是恬淡,但看人看物,远比常人看得清,看得透。在江畔分别时,他开始放任我的选择,后来发现安亦辰见到了那一幕,又改变主意想带我走。他说,安亦辰不会饶我。
第二日,有太医上门请脉,被我逐了出去。
我要去园中散步时,被院外的侍卫拦住:“王妃,王爷有令,王妃体弱,宜在房中静养,不得出院一步。”
夕姑姑半晌不语。
安亦辰紧盯着我,唇角的弧度宛如弯刀的形状,锐利吐字:“当日在沧北行馆,你明明尚未喜欢我,还是经不住我的纠缠,让我轻易便占有了你;以你这样心软而冲动的个性,又怎能拒绝得了你喜欢了那么多年的男子?宇文清若肯放过这个机会,除非他是傻子,或者圣人!”
但他目前接不接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得不到他的允许,只怕他不会容这个孩子平安降临人世。
我想哭,可居然已掉不出眼泪来。
因为我不要别的侍女跟来,夕姑姑年纪又大了,向来地位不低,也不曾这样劳碌过,未免辛苦了,我就亲到灶下帮着添加柴火。
七日后,我依旧咳血,遂将当日在沧江边的渔村里,宇文清留给我的药取出,挑那益元补气的,服了一粒。虽然不知道其中有没有损害胎儿的成份,但宇文清用药向来谨慎,估料着总不致有大毒。服后果然咳血之症好转不少,精神也恢复了些。
“公主!”夕姑姑失声叫喊,一把抱住我,满眼是泪问我:“你怎么了?怎么会吐血?”
安亦辰对我的感情里,已经有了太多的猜忌,我们再不可能回到过往,再不可能。
“对,我们过得很开心。即便是出征在外,我同样开心。那件你亲手做的斗篷,是我出世以来收到的最珍贵最美好的礼物。你心里有我,才会送我那样的礼物。每日我对着它,就似看到你的笑脸,满心的欢喜,一心想给予你更多的快乐,作为对你的回报。我以为去浏州可以让你更开心,不料宇文清居然也会冒险去了浏州……只见了一面,一面而已,你就为他惊慌失措,心神恍惚……所以我动了杀心,用你的玉轻易就诱擒了他。我很想杀他,可我又不敢。我不知道若有一天你猜出是我下的手,会用怎样的眼神看我……你心里有了我,却还是发了疯地喜欢着宇文清……”
“我已经万劫不复了!”安亦辰近乎绝望地盯着我:“与宇文清几度交锋,在战场上,我始终落于下风;而在情感上,我更是一败涂地!你当真……宁可与我决裂,也要为他生
https://m.hetushu.com.com下这个孩子!”“没有了孩子,这里,对你就没有了意义么?”安亦辰寡淡地笑着,自嘲地反问着,一步一步向后退着。直至走到门槛处,被门槛绊了一下,才回过身来,踉跄向外走去。
“亦辰……”我颤抖着声音唤着他的名字,咬了咬下唇,盈了满眶的热泪,低声哀求:“这孩子是你的,让它好好生下来,好吗?”
夕姑姑已闻声奔了进来,赶开侍女,安慰道:“不要怕,公主,真是治咳血的药,我看着大夫开的方子。”
第三日,我让夕姑姑设法从外面高价买了数本医书回来,为的是研究哪些药草会对胎儿有影响。
“你和王爷说什么了?你和王爷到底说什么了?”夕姑姑眼泪汪汪:“我劝了他好久,他答应好好和你谈谈,为什么……越谈越糟?他的脸色跟死人一样难看,你……你也这个样子。公主,我们不是说好了么,好好和他商议,只要他容许这孩子生下来,我们什么都依他。你……你又说什么激怒他的话了么?”
安亦辰似被我戒备的举动震惊到,眸光凝了一凝,浓黑的眉深深蹙起,看来萧索而落拓,不见寻常的雍容。
身处灶下,我早就脱了那一件件的华丽衣衫,只穿了花色最简洁的青布小衣,淡淡冷笑:“夕姑姑,有些菜,平常人吃了没事,但有身子的人却吃不得。比如薏仁,能收缩宫体,导致流产;比如鳖甲,可通血络、散瘀块,也可……连胎儿一起堕下;再比如螃蟹,其性寒凉,活血祛瘀,也是堕胎良药。”
安亦辰的部属,个个出身行伍,只知军令如山,和他们说了,也不过为难他们,让安亦辰知道了,反而更不自在。
我紧张地抱住他,失声哭道:“多信我一点,好么?多信我一点!我也喜欢你,我绝不要你离开我,绝不要你恨我。”
那一觉,睡了很长时间,模糊间有人唤我,又有人为我把脉,最后,有人将极苦的药往我口中灌去。
他们不会趁我睡着了,在喂我吃堕胎药吧!
我双肩一耸,猛地坐起来,挣扎着推开他的手,喘着气,惊慌地望着他,双手紧紧护住自己小腹。
而我要的,就是这个孩子的平安出世。
我竟让安亦辰有了这种感觉么?我甚至根本不曾离开过他,即便伴随宇文清逃亡的路上,我心里一直牵挂着他,他感觉不出么?
“可后来我们还是很好,不是么?虽然没有了孩子,我们也是过得和和美美,每一天都很开心,不是么?”
夕姑姑拍着我的肩,泪水簌簌滴落到我的面颊,哭得泣不成声:“是,公主。夕姑姑一定帮你保住这个孩子……我不会让王爷欺负你,不会……”
我记得自己的身份。即便在江畔,我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安亦辰的妻子。我的夫婿是安亦辰,我打定主意携手一生的人。
我伸出毫无血色的手,指住夕姑姑道:“你不帮我搬么?你怕跟着我受苦,不愿再跟着我么https://m.hetushu•com•com?那好,我自己……我自己搬。”
安亦辰回来了么?夕姑姑是去见他么?
安亦辰走后不久,夕姑姑就回来了。
“夕姑姑……”我脆弱地回答着:“明天帮我收拾东西吧,我搬去青衿馆。如果他不许,那么随便去哪里吧!我跟他的缘份……到头了……”
以前总觉得夕姑姑偏心,总是护着安亦辰。原来她并不是偏心,她只是护着她认为弱势的一方,努力保持着我和安亦辰之间的平衡,不让我欺负他,或他欺负我。
我惊急地高叫道:“亦辰,我和宇文清,绝对是清白的!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为什么?”
我从不知道,在我生死交关的八天八夜中,安亦辰居然也曾这等盼着我死,不因为恨,而因为爱,爱得太苦,太累,太灰暗。
脚步声顿在我的榻前,呼吸声沉重而熟稔,曾无数次轻旋在我的睡梦之中,让我安妥,让我宁和。
那个小小的牢笼,曾用情丝编织,让我不舍离去;当我想离去时,情丝中已缠入了金丝,成就了挣不脱也舍不得挣脱的金丝笼。
抬起头,我直直看向安亦辰,淡然道:“安亦辰,明天我会搬出正房,你爱让谁住就谁住,爱娶谁就娶谁。但这个孩子,我要定了。”
而我喜欢宇文清,就那么深,那么深么?
而屋外,渐有熟悉的脚步声轻缓地传来,又有侍女蹑手蹑脚离去的轻微动静。我便知道,安亦辰来了。
“不是我要选择,是你逼我选择。有了孩子,这里还能算个家;如果连孩子也没有了,那么……”我凄瑟地轻笑:“我已不知道,这里对我还有没有意义。”
万劫不复?
那他就不是安亦辰了!
夕姑姑急忙道:“公主,太医说了,公主的是旧疾,若不好好治理,可能会落下一辈子的病根!”
夕姑姑惊惧地望着我,一时骇得呆了,竟不曾接话。
安亦辰凄凉笑着,往日灿如星子的眸中,已迷蒙着滚下泪来:“栖情,知道吗?你一直让我感到很失败,我走来走去,似乎永远走不到你心底最深处。你小产时,在死亡边缘徘徊了八天八夜,我也在你身畔衣不解带守了你八天八夜。那八天八夜里,你迷迷糊糊唤过很多人的名字,从你的父亲,母后,颜叔叔,夕姑姑,绎哥哥,甚至也曾唤过我。可你叫得最多的,是白衣!把所有的人名字加起来,也不如唤他的多!”
拖着绵软的脚,我走到床前,无力滚入锦衾之中,默默抓了夕姑姑的手,靠到自己的面庞,虚弱地说道:“夕姑姑,帮我,帮我保住这个孩子。如果保不住……恐怕,我也活不了了……”
披了浅蓝披风的身形,孤凄而落魄。
可安亦辰坚持认定我和宇文清有染……
我摇晃着身体,自行去取房中偌大的箱笼。
忍了气,我默默回了房中,卧于长榻上,把头发散了开来,让夕姑姑一下一下为我梳着,感受着头皮渐渐放松,心神方才略略舒展,迷蒙欲睡。
门外依然有侍女在守着和-图-书,察探着我的动静。
但到傍晚时,我已发现我的处境着实不容乐观。
安亦辰蓦地扬掌,狠狠掴在我的面颊,涨红的面庞满是羞愤,无可掩抑。
安亦辰双手扣着我的肩,嘴唇黯无血色。他深深地望向我,忽然一把将我拥到怀里,将我的肌肤按揉得几乎每一寸都贴到他的身上。他的话语中,纠结了黑夜般漫无边际的疼痛和沉郁:“栖情,拿掉那个孩子,算我求你,行么?我不想见到你日渐挺起的肚子,更不想见到……见到属于那个人的孩子在我跟前活蹦乱跳……我真的承受不住……不要逼我恨你,不要逼我离开你……”
“别……公主你别乱动……”夕姑姑恍然大悟般冲过来将我抱住,颤声道:“你有身子,不能乱动。我……我这就叫人搬东西去。”
我也想骄傲,骄傲如以往一般伸展我的伶牙利爪。可我只是个被捆了羽翼的鸟儿,困囿于安亦辰给予我的小小牢笼中,根本无法飞开。
安亦辰胸部一动,已嘲讽般叹出一口长气,温热湿润的鼻息扑于脖颈,泪意般的咸涩;他破碎般哽咽道:“我信你?栖情,你告诉我,我怎么信你?从去年春天把你带入晋国公府,我竭尽所有给予你我所能给予的全部,不论是尊重,还是爱情,只要是你要的,哪怕……哪怕知道你怀的是萧采绎的孩子,我都愿意视同亲出……看着你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睡得一天比一天好,我也很开心,我以为你的心里,总算有了我,并将……将宇文清渐渐遗忘。”
我突然也灰了心,无力地推开他,软软坐到塌上,轻轻笑道:“安亦辰,知道你为什么总是不如宇文清么?”
他在我沉睡中显现出的神情,是不是才是最真实的内心流露?
我犹记得当日怀第一个孩子时,他也喜欢那样抚摸我,特别喜欢抚摸我的小腹,虽然他知道,那个并不是他的骨血。
朦胧之际,见有侍女走到夕姑姑身畔,附耳说了几句,夕姑姑点点头,又瞧我一眼,我将微睁的眼闭了,不一会儿,才听她细碎的脚步声迅速走开。
“公主!”夕姑姑心痛地握了我的手,嚷着:“你别想太多,别想太多啊!王爷他也未必……未必会伤它啊!”
我不顾下颔被他捏得快要碎裂般的疼痛,紧紧拥着他,感受他激烈的心跳,低低喊道。
“我不要你万劫不复!当你万劫不复时,我同样也万劫不复!我只想和你快快乐乐生活在一起……”
他勉强肯接受我,心里却带了这根刺;而现在,他不肯再带着这根带接受那个孩子,那个他认定不是他骨肉的“小畜生”。
而我只是惨淡地笑,伏在软软的榻上咳嗽,吐被安亦辰打出的鲜血。
我清冷笑着,软软立起身来,劈头将侍女手中那碗药打翻在地,道:“我不会吃这些药!”
安亦辰会不想着伤我的孩子?这个他认定的野种?
侍女惊叫着,连忙回答:“禀王妃,这是治王妃咳血的药!”
夕姑姑好久都没有回来。
安亦辰和-图-书的黑瞳,已冷寂得看不到一丝波澜,连声音也平得听不出节奏:“也就是说,在我和你的孩子之间,你选择孩子?”
我明明用了全身的力气在吼,可发出的声音却低弱之极,只是语调中的惊怖,已激昂得让人恐慌,而我的面容,必定也已变得狰狞可怕了。
我失望地向他叹息:“因为他猜得透你,你却看不懂他。他比你……高尚。”
懵了一下,才意识到,自己被安亦辰软禁了。
我定定神,记起去年在晋国公府也曾吐过血,当时有白衣相救,如今……算是旧疾复发了,必定更难治了。
沧北行馆,我与他的第一次!为何今日从他口中吐出,竟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游戏?而游戏的目的,仅仅是占有我!而且是轻易占有我!
环视四周,我嘿然而笑:“腾出地方来,让他早日找了新人,只怕就能忘了我,不会整日想着算计我的孩子了。”
夕姑姑呵,还是当年那个将我抱在怀中,用儿歌哄我睡觉的夕姑姑!
方才似已干涸的泪水再度倾落,为了我的孩子,注定在风雨飘摇中出世的孩子。
但我明白,除了夕姑姑,其他的人,只要安亦辰一句话,立刻会由侍女变成我的监视者,甚至变成我的谋害者。
“知道吗?”安亦辰伤感地吻着我眼角惊诧的泪水,低低诉说:“那时,我就想着,或者,你死了更好,对你是一种解脱,对我,也是一种解脱。……可我很不争气。我就是放不下,放不下你……不管你唤的是谁,我只一遍遍告诉你,我是亦辰,是我在守着你。只希望这一遍遍的倾诉,能让你的潜意识里记起,我才是你的夫婿,最爱惜你的那个男子。可你叫的还是白衣……等你脱险后,我便发誓,绝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见到宇文清。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不可能动摇他在你心里的地位。”
“啊啊!”我大叫着,硬生生迫自己清醒过来,用绵软无力的手撑起身体,向喂药的侍女吼道:“你们给我吃的什么药?你们给我吃的什么药?”
夕姑姑目瞪口呆,迷惘地摇头。
我抬起被烟火熏得黑漆漆的脸,微笑道:“夕姑姑,咱们王爷,可着实不曾将我忘了呢,难为能在这些食物上下工夫想办法!”
半个月后,我发现夕姑姑从外面大厨房领回来的饭菜中,常有薏仁汤、鳖甲汤或炒蟹爪,让夕姑姑全倒了,让她将院内的小厨房整理出来,从外界买最简单的米面蔬菜回来,自己动手煮菜。
我被打得从榻上滚落,跌在泥金砖石上,喉间阵阵的腥气上涌。
我讥嘲一笑,不顾乱战着的腿脚,指住我的箱笼道:“立刻帮我搬东西,搬青衿馆去!”
夕姑姑见我倦了,拿条软毯子为我盖了,只坐在塌畔守着我,抚着我软滑如缎的青丝。
但我实在已经忍不了了。他不但侮辱了我,侮辱了宇文清,也侮辱了他自己。
我抓了她的手,问道:“是你去抓的药么?是你去煎的药么?你确信,药没给人换过,或加上一星半点东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