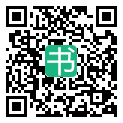第四十一章 皇后
两人又说了一会儿闲话,便上床安睡。
“你对着花说‘这里不是南国,虽然阳光冷了些、土地硬了些,可为了将你种下的人,也该好好开花’,”他笑了笑,胸膛微震,“当时你是想哭吧?”
宫中因皇后厌胜而获罪的宫人足有两百多人,其中能逐出宫去已是大幸,处死流放的不在少数。
两人正说话,宫女端着五色小饼和酒食灯进来,皇帝用了一些。子虞见状,忙问左右:“难道陛下一直没有用膳?”小宦官道:“太子殿下一直在宫外跪着。”
子虞见了他避之不及的样子,心里觉得好笑,推门进殿时便一直含着微笑。
太子到永延宫为母亲说情,被守宫卫士拦下,皇帝正在殿中听宫正司的审问结果,无暇宣召。到了夜间,议事的臣子已经全部离去,太子再次请见,又被宦官告之皇帝疲惫已经歇息。
赵珏的睫毛不自禁地颤了一下。
“你先看下这些吧。”他淡然说道。
皇帝的目光一凛,口气骤然冷淡,“她是皇后,理应为她的作为付出代价。”他容色微敛,将手一甩,把衣袖从太子的手中挣出,然后说,“回去吧。”
子虞点点头,又站在门外听了一会儿殿外的动静,这才从殿侧口踅出。
黑暗的并无一丝灯光的通道,子虞顺着一路走出殿外,抬头便看见了交泰宫。这处殿室原就在交泰宫的后方,绕过去,其实并不远。
子虞默默与她对视。
子虞仿佛穿透了时空,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
这里正对着一处宫殿,叫桐殿,往日人迹罕至,宫女们辟出偏殿给子虞休息。
“这样小小一件,居然这样繁复,”他双目幽深,唇角略含笑,温柔地看看她,“你的手很巧。”
穿透了几层帐幔的月光是那样稀淡,可她屏声静气,还是在暗色中看清了帝王的容颜。
他仅仅是皱了一下眉,朕知道了。
皇帝看着满桌的证物沉吟不语。
子虞神色淡然,不置一词。到了傍晚,只留秀蝉一个人在身边时,她突然开口说:“我要去交泰宫一趟。”秀蝉愣住了,不知这是她的突发奇想,还是早有算计。子虞侧过脸看她一眼,秀蝉就低头退了出去。
一种恐惧从他内心开始蔓延。相比桌案上的供词和证物,他的说辞是那样苍白无力。他不明白,为什么忽然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一个模样,他的舅母,那些曾拱卫交泰宫、忠心耿耿的宫女们在一夜之间背叛了他的母后。
殿中忽然一暗,原来是蜡烛熄灭了一支。
子虞从没有像今日这样仔细去打量过她,细眼一看,心里还是有些赞叹,这个占据后位二十年的女人,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来得年轻,她笑时眼角已有纹路,却带着一种风情,而这种独特的风情,有的女人即使一辈子也无法学会。
皇帝听着他的哀泣,目光软了下来。
子虞带着宫女到御花园散步。天色昏暗,点了灯才能看清,宫女们都觉得此行不妥,但却不敢拦阻子虞的雅兴。这是她大病后第一次出行,宫女们只能尽十二分心地服侍。
子虞顿时明白,太子整日跪在永延宫外,惹他心烦,到了这里,太子就无法跟随,只能回去休息。她心里暗哂,只怕那太子未必能理会这种苦心。
赵珏眸中不过迷惘了片刻,转眼又恢复了冷静,“我是什么样的人,难道你会清楚?”
他将手中的绳结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似乎很有兴趣。子虞换了一身衣服出来,看见他还在摆弄,心底不觉有些酸涩。
他伸手按住了她的肩膀,“怎么了?”
子虞习惯地笑了笑,又突然觉得黑暗中根本看不清,便把笑容省了,轻松地说:“这样睡不www•hetushu.com.com舒服,想靠里面。”
“是她,”赵珏喃喃道,神色复杂,似了悟又似嘲讽,“现在我才相信,这一次你能得手,并非侥幸。”
夜深了,寝殿内寂静无声,只有铜漏滴答。床脚的羊角宫灯已经熄灭,只有窗外的月色透进来,子虞骤然在梦中惊醒,举目四望,在看到睡梦正沉的他时,她才喘过一口气。
问题很快就突显出来。那些宫女大多魂不守舍,言辞闪避。在他严酷逼问下,几个胆小的宫女首先开了口,虽然没有直接揭露厌胜之术,却说出她们在交泰宫中遇到的各种诡异情景:宫殿险些无故失火,宫人白日看见鬼魂而发疯……说着说着,她们自己也怀疑交泰宫暗中进行着巫祝。
子虞叹道:“并不是相信老师,只是不能相信你。你的儿子曾对我说,他会追寻厌胜的真相。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感情深厚又执着的人。我能从东明寺回来,同样的结局我不想在你身上重复。”
子虞也不在意,随口反问道:“除了命,你还剩下什么?”
“以史为师,你真是一个不错的学生。”她冷冷笑道,“可难道没有人教你,这种逼人上绝路的事不该亲力亲为?”
她听后平静如水,殷荣也没有从她脸上看出端倪。
他呵呵一笑,“为什么不要?你能到我的面前,得助于宰相,又有一个能干的兄长,妃嫔该有的你一样也不缺,美丽,才情,生存的野心。你的身份那么特殊,在宫中所能依靠的只有我。那个时候,我需要的,也正是你。”
那一刹那,他的信念都开始动摇,难道,他的母后真的在宫闱中行了巫祝?
她垂下眼,放松身体,将思绪抛给沉沉的夜晚。她与皇后不同。皇后几代繁华,早已经忘记根源,妄图将富贵绵延。
御史大夫还想张口,姜明先一步道:“禀陛下,宫中行巫,前朝有例可循。”
“听说太子曾对你无礼?”不知是他无意,还是子虞脸上显出了思虑,让他提起这个话题。
御史大夫曾受倪相恩惠,勉力想挽救一把,“陛下明鉴,皇后娘娘一向宽厚仁慈,怎会突然行巫祝,此中必是受小人挑唆。”
子虞觉得周身一下子寒冷起来,她在被下悄悄握着拳,用眼睛在黑暗中勾勒他的神情。
子虞略怔,轻吁道:“我不会像你一样。”原本有很多选择,等赵珏到了承明宫,派人尾随,不知不觉地将她除去,就像她曾经对待文媛一样。
交泰宫的正殿外守着一个宦官,脚步踱来踱去,看到子虞走近了,几步迈到她的面前,低低地说:“秉仪可来了,快随我来吧。”领路走了几步,又发觉不对,回头仔细一看,分明是张陌生的脸,他心里一颤,装作不知,将殿门打开后便躲得远远的。
“是吗?”子虞微哂,“这句话,你说得可没有底气。他有三个儿子,以后说不定还会有,若真是对太子那么放心,你也不会对文媛那么不留情面。当初老师一定也对你说过:对待情敌,有时可以网开一面;对待政敌,才需要赶尽杀绝。”
“这样?”子虞想起当日,依然有些怅然,“我还以为,陛下会不要我。”
他心中顿时有了不祥预感,事情正向最坏的一面发展。
赵珏一凛,腰背绷直,端坐起身,直视了她半晌,才又道:“是她。”
“废后。”他纠正她的称呼,慢慢说道,“她掌握中宫二十年,大概已经感到厌倦,这是她自己选择的结局。”
赵珏看着她的眼睛,眉眼中透着嘲讽和不屑,仿佛在告诉她“这样的伪善不值一提”。
“你做了更大胆的事。”子虞瞥了她一眼,悠然道,“和-图-书夫君是帝王,总要担心他有所反复,若儿子是帝王,情况就大不相同。你曾经有这么想过吧。”
“唉!”她哀叹一声,忽然想起了当初那朵花,在含苞未放的时候,枝干已经枯萎。她心里一动,闭上眼,湿润的感觉忽然滑落在脸颊。
子虞知道话已经说完,转身准备离开。
子虞精神委顿,坐在榻上打起了盹,秀蝉见状就将宫女遣到殿外,独身留下伺候。等脚步声从殿内退得干干净净,子虞睁开眼,卸去头上珠环簪钗。秀蝉从床下拿出早就备好的一套宫女蓝衣,给她换上。又轻轻说道:“娘娘,可别超过一个时辰。”
并不是所有剖露的心迹都让人感动。子虞长长吸了几口气,才又找回了自己的声音,“陛下,如果,有这么一天,您不再需要我了,请告诉我……让我能安排自己的结局。”
尽管这一次的谈话仅限皇帝和太子两人,但子虞还是从殷荣那里知道了其中几句。
“我早就告诉过你,三思而行,做事决不能莽撞,而你却无所顾忌地将自己的思想暴露在他人面前。”皇帝道。
他的太阳穴突突地急跳,上前一把推开妻子,案几上那些画满奇异字符的经幔,还有余温的香炉暴露在人前。他面色惨白,直愣愣地看着,仿佛摆在眼前的是一道道催命符。
太子无言以对,仿佛有什么扼住了他的喉咙。
子虞原路返回桐殿,换回衣裙,又折返步寿宫,宫人只道她精神不好,借殿室休息了片刻。
子虞不知道他从何时开始知道了这个,微微垂下头,浅笑道:“一时兴起,摆着摆着就忘了。”
被召来永延宫议事的朝臣面面相觑。
皇后巫祝一事让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子虞道:“看似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要用点心就可以了。”
次日清晨,延平郡王府被一队禁军闯入,他们二话不说,直奔后院。郡王赵琛得讯后,带着家丁气势汹汹地来问责,却满脸惊讶地看着倪氏跪倒在案几前,双手死死地护着身后的物什,如惊弓之鸟。
子虞接口道:“是想不到。”到底是没想到来看她的人,还是没想到落到这个地步,她们俩谁都说不清这句话的含义,短短一句后就陷入了沉默。
子虞恍惚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脱口道:“什么?”立刻又反应过来,讪讪掩饰道,“以前……是什么样?”
殿中只点了两支蜡烛,泻着几缕昏黄的光,一个纤瘦的身影坐在榻前,透着一股子安详寂寥。
赵珏首先察觉,转脸看来,等看清后还露出一丝笑来,“原来是你,真是没有想到……”
皇帝皱了一下眉,对殿中大臣道:“退下吧。”几位臣子退下。他才转过脸来目视太子,目光中有浓浓的失望,放在御案上的手,轻轻叩了一下桌面。
尽管如此,还是在一条甬石漫道上出了错。子虞崴了一下脚,难以再行。
废后已成定局,倪相一系官员上书为皇后求情,太子也日日跪在永延宫外为母陈情。皇帝犹豫了两日,下诏“阴怀妒害,包藏祸心,宫中行巫,弗可以承祖宗,母仪天下,其废为庶人。”过了半日不到,又令庶人赵氏迁往承明宫。
他说:“太子以情动人,陛下难以下定决心,到底是处死,还是贬为庶人。”
太子拉住他的衣袖,“她是您的妻子。”
太子绝望地看着他,喃喃道:“母后她不是那样的人。”
他没有回答,手指温柔地穿过她的头发,轻轻拍在她的后背,过了片刻,他停下动作,安然入睡。
“那时陛下已经觉得不再需要皇后了?”她自己都惊异怎么将心中的疑问说出口。
子虞抿唇微笑,“你
和_图_书可不像是相信命数的人。”子虞站起身,“我让人来换烛。”
“怎么会……”他怀疑起自己的眼睛,这些交泰宫的女官、宫女都是母亲信赖的亲信,而另一份,出自他的舅母。他的手指关节握紧,手背上显出青筋。
他的醒了过来,提高了声音问:“什么事?”外面的周公公立刻回应,“陛下,是庶人赵氏,刚才自尽了。”他睁开眼,似乎一瞬间有些讶异,慨叹了一声后,他又重新闭眼,低沉的声音穿透了黑暗,“嗯,朕知道了。”
殷荣心道“妇人心慈,见识短浅”,不再赘言,拱手告辞。
子虞正观赏桌上的一幅书画,目光专注,似乎并没有为此分心,随口说道:“太子仁孝宽和,人人皆知。”
承明宫是距北郊皇陵不远的一处别宫,获罪的宫人囚在此处,从没有活着归来的,其中就有三皇子睿绎的生母,文媛。
皇帝长长叹息了一声,神色有些失望,也有些惋惜,命人起草诏书,“……阴谋下毒,用厌胜之术谋害妃嫔,有失国母母仪天下的体统……”说到这里,他语声渐停,目光悠远。
“你的母亲,也许不会行巫祝。她能做的、敢做的,远比巫祝更厉害。”他轻轻摇了摇头,“这一次的证据无懈可击,我不能再宽恕她,而在这之前,我已宽恕她太多次。”
赵珏冷哼一声,“我曾经怀疑是你兄长的苦肉计,可你居然也不知情,现在倒真是有些好奇了。”
这一下赵珏的表情凝重起来。
她入睡前,悄悄宽慰自己,等醒来,明日就会不同。
“儿臣刚才确实失仪,”太子垂下头,可声音依然那么颤抖,“可是儿臣心急,她们诬陷母后……”
子虞对这个囚而不杀的结局并不意外。女官不知怀了什么样的心思,每日打探了交泰宫的动静,事无巨细,一一回禀。比如,头一两日,皇后滴水未进,而今日听闻诏书后反而开始进食。
“第一次在步寿宫的花园里,你蹲在枯萎的花旁,自言自语。”
子虞微微一怔,随即又若无其事地笑了笑,“是哪个多嘴的宫人这样谣传,殿下不过是担忧母亲,言语着急,算不上无礼。”
太子迈入殿中,声音已经带了哭腔,“父皇,母后蒙冤受屈,定是受小人所害。”
如今的步寿宫已经不同往日,不到半个时辰,秀蝉就已做好了安排。
子虞脚步一滞,回过头去,“那是谁?”
赵珏目光骤然一冷,“他不会让你这么做。”
赵珏抬眼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眉宇中深藏的一丝疲惫渐渐变得沉重,“身在深宫的女人总有能让人大吃一惊的本领,第一次走进我的宫殿时你也是穿这样的衣服的,今日居然会变成这样的局面。”她怅然长叹了一声,“难道冥冥中真有命数?”
刚才的一切原来不是做梦,她有些哀伤地想。
赵珏吐了口气,垂眼笑了起来,“到底是小看了你。卑微出身的人,更善于揣测人心——老师当初所说,果然不假。”
不是印象中的交泰宫,也不是印象中的人,子虞慢步上前。
他根本无法推翻这些罪名。
太子心里焦急,只是在父亲严厉的目光下定神去看那些供词证物,随着一张张翻过,他越来越诧异,以致双手都有些颤抖。
“不用了,”赵珏一挥袖,半倚在榻上,“将死之人,不需要了。”
这一次是命令。
禁卫又送来另一份证物和供词,从延平郡王府搜出的经幔上同样绣着几个生辰八字,字迹都属于皇后,而用来制作偶人的布料,整个宫中只交泰宫有两匹,其中一匹被皇后赏赐郡王府。而倪氏被囚捕后,不愿独自揽罪,只一个劲儿地申辩,“并不是咒杀之和*图*书术,只是将身上的劫难转嫁,皇后娘娘也是知情……”旁人不愿再多听。
他挥手让宫人退下,宽慰地看着她,“不用担心,太子和他的母亲截然不同,那些话,等待时间一长,他自己也会忘记。”子虞应道:“是啊。”
子虞轻轻一笑,“宫中的事务,做得再完美,也总有蛛丝马迹可寻,他对你态度的转变,若是仔细寻察,也不难猜。所以你的父兄都难以幸免,他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了。”
皇帝打断他的臆测,“口说无凭,证据呢?”太子一愣,皇帝又道,“拿出一样能验证你的说辞,或者洗清你母亲罪名的证据来,证明你手上的那些纸都是谎言。”
子虞隐约想起了一些,身后有脚步声,她回头,本以为是兄长,谁知是皇帝……那时,他应该就猜测到了,这个相遇是一场设计的偶然,可惜被设计的人,都没有那样的心思,后来,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局面呢?
子虞淡淡说道:“你我都知道,侥幸只有一次,不会接二连三。今日的结局,追根溯源,是你太过自负,住在交泰宫久了,就以为它在的把握之中。”
殷荣笑容顿消,没好气地看了她一眼,“一个故事必须要有头有尾,若是半途而止,岂不让人伤心,宫正司正阖宫搜查巫祝布人,在明日,也许后日,从太子妃的寝宫搜出来,她是赵珏的侄女,旁人不会对此感到意外。”
“娘娘的仁慈宽厚,才让我佩服。”他讥诮地一笑,“在太子口出狂言后娘娘尚能如此安心。”
殷荣斜眼扫了他一眼,说道:“皇后是天下妇人典范,却做出如此失德之事,实在愧为国母。天下至尊的地方,传出龌龊之行,却不能明正典刑,天下人会如何想?”
“处死和贬庶有天壤之别,花草若是留根,春暖花开还能重遇生机,何况是野心勃勃的藤蔓?娘娘啊娘娘,莫非你把太子的有朝一日当成了戏言?真要有这么一日,太子不会忘记他的母亲,今日的铁证,只能变成我们的罪证。”
“这不可能!”他控制不住地对着父亲喊叫。
殿外忽然也有了动静,衣袖婆娑的声音不断响起。
他听了没有反应,反而伸手将她搂到身边,半晌后才又说道:“你的笑容,和以前不同了。”
皇帝起身走到他的面前,轻拍他的肩膀,“她是你的母亲,你所能记得的永远都是她美好的一面,这不怪你,回去吧。”
御史大夫道:“二十年来操持后宫事务,抚育皇子,皇后劳苦功高,请陛下三思。”
皇帝揉了一下额角,点点头,“让他进来。”
“我们”,子虞听到这个词蹙起了眉头,仅仅一瞬,又放松了神情。她将画卷收起,清晰地说道:“我听说,相爷为了今日,等待了十年,现在反倒沉不住气了。宫中形势一向多变,没有人能保证未来就能按照心意进行,顺其自然吧,反正,中宫已没有了皇后。”
子虞看着他,摇头喟叹,“想不到相爷也会被眼前的迷雾所惑。故事是否有始有终,从来都不是重点,听故事的人才至关重要。到此为止吧,把网拉得太大,会出现破绽。何况陛下已经失去了妻子,他一定不想马上失去儿子。”
当第一个人开口留下了供词,后面的人也就不成问题。
太子无法直视皇帝的目光。他伫立了半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为母亲请罪。他的眼中流下泪水,“父皇,母后与您相伴了二十年,您应该了解她,这一次就宽恕她吧。”
赵珏的身影藏在黑暗中,子虞无法判断这一句是真是假,诸多念头一瞬间从她的脑海中转过,却没有一个能真正抓住,在推门而出之前,她才轻轻叹息,“已经不重要了和_图_书。”殿中一片寂静,仿佛根本没有人,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将供词和交泰宫中搜出的证物都呈到御案前。
而她起于微末,所求的,不过就是一朝一代的荣华。
已经足够,皇后行厌胜之术铁证如山,何况,前一段时间宫中几位妃嫔毫无缘由地病倒,也是佐证。
“也许和你一样?”子虞冷笑,“不,不对,你在心里嘲笑我,我的下场会比你更惨,因为你心中始终还有希望,太子夫妇至今还平安无事。”
赵珏皱起眉,“有史以来,皇后的数量历来多过皇帝,没有皇后会以为中宫纳于鼓掌之间,我更不是那样的轻狂的人。”
两人相顾无言。片刻之后,赵珏才又重新开口,“你今日来的目的就是这样?对老师所授的坚定不移地执行?”
子虞今日经历的很多,身体有些疲惫,可躺在床上,精神又出奇的好。她侧过身,看着帐外,只有一盏灯火在黑漆漆的夜里,仿若发黄的明珠,身边还有他悠长的呼吸。她无端生出一丝心烦意乱,缩了缩身子,就想翻身向内。
“陛下。”周公公提醒他,“太子殿下已经在殿外等了两天。”
世人都已忘记,荣华富贵,从来都是短暂的烟云。
“恰巧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一些。”子虞道,“吴元菲,这个名字还记得吗?”
“怎么一直都没有打号?”他听到动静,抬头问。
皇后被废,后家也广受牵连。皇后的父亲宣王改封南宫侯,封邑减半。延平郡王夺爵免官,流放岭南。还有几个皇后的庶出兄弟也都不能幸免。
仅仅一日,司正就得到了十余张有用的供词。
皇帝听了便笑,“原来只用了一半的心。”子虞心中怦然一跳,上前从他手中夺了过来,嗔道:“只不过暂时忘了,日后打好再给陛下看。”
他的消息灵通,子虞从不意外,她抬起头,“皇后大势已去。”
笑到一半,或许是故意不想让子虞好受,她目光明亮,慢悠悠地说道:“你既然看的那么透,也该看到自己的处境:他让你变成了一把刀,除去了他不再需要的人,刀也就变得没有用处。难道你没有想过自己的下场?”
在宫苑北面有一座殿堂,常年都照不到阳光,宫人们也避讳提起它,那就是宫正司。司正姜明奉旨审理交泰宫一干宫人,他直觉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能将他的名字和皇后一起留在历史上。姜明拿出前所未有的认真,将每一个宫女仔细盘问。
皇帝漠然地看了他一眼,这一眼就让他冷静了下来。
他低沉的嗓音在她的耳边,让她的心有些发热,可想来想去,还是没有想起这一段,她有些沮丧地说道:“不记得了。”
“来看我做什么?难道我这里还有什么是你想要的?”赵珏说道,声音憔悴,口气却很轻慢。
“一个不适合宫廷的女孩,被引导了我的面前,”他轻描淡写地说道,“可后来,你还是让我大吃一惊。直到东明寺的那天,你让我觉得,即使在宫里,你也能生活得很好。”
“身为御史,居然说出以功盖过的话,”殷荣肃然道,“此例一开,后来者必然效仿,国法岂不形同虚设?”
步寿宫内外已点灯,子虞有些意外,步入寝宫时发现皇帝坐在床前,手里拿着一个绳结,垂下的杏色流苏让她眼熟,是一直藏在枕下的同心结。
一双大手抚在她的脸上,接住了泪珠,“为什么哭了?”
“你知道吗?”赵珏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刺伤你的兄长,让你主动向我动手的这件事,并不是我家的人做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几位大臣也看出风向所致。大多附和殷荣的说法,一两个与后家有牵连的,默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