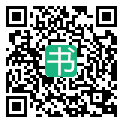第十一章 骑兽之势
宇文招急切地道:“三郎,我知道你为人仁厚,又是太祖驸马,忠君报国,绝非令兄那种貌似忠良、内实奸险的叛臣,如今只有你能救我,不知三郎能不能看在公主的份上,大义灭亲,铲除巨奸?”
淡淡的上弦月下,这些东西的影子浓浓淡淡地罩住了殿门外的白玉台阶和莲池。
顺阳公主恨不得当场掀席而起,但想着家庙后面已经伏好的甲兵,她强自忍下了心头的怒气。
“郑内史所言诚是,请皇后速召随国公入见!”出乎她的意料,刘昉竟然双膝跪倒,高声赞同着。
杨俊脸庞之畔,犹有尚未风干的泪水,道:“我不会打扰她,长孙将军,你让公主与我最后见一面,我有话要说。”
这封简短无比的信,立刻让杨坚看清楚了自己的处境,让他感觉了自己犹豫得如此可笑,苦心经营了二十年,他不就是为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时刻么?
难道自己就眼睁睁地看着尉迟家从这个夜晚开始飞黄腾达?
杨瓒也大为感动,紧紧抱住这个平时刁蛮任性也一往情深的女子,笑道:“公主说哪里话来,你我夫妻多年,恩深情重,公主为我生养了三个又英武又能干的孩儿,对杨家有功,对三郎有情,为了公主,为了大周,我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好,就按着两位大夫所说,召随国公入见。”杨丽华咬了咬牙,终于点头首肯。
一向对妻子言听计从的杨坚,这么热心地关注自己的婚事,多半就是出于独孤伽罗的指使吧?
杨丽华隔着温热的泪水凝视着她的丈夫,他们从十三岁时一起成长,而她终于没能遏制得了他的疯狂。
不要说别人,就连杨坚自己也不相信。
杨俊的泪水再次汹涌而出,这每日执念、相思不已的酸楚,是否永远都不能平息?眼前这张魂牵梦系的面庞,这个对自己一往情深的女人,自己却只能眼睁睁望着她远嫁,投入突厥人的怀抱……
从他厚实的肩背、纤细的腰身,还有那件她亲自裁剪缝绣的蓝袍上,千金公主一下子就看出那人是杨俊。
千金公主已哭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哽咽道:“阿祗,你万勿如此,你已尽力挽回,想尽了办法。我不怪你,我只恨自己身为宇文家的女儿,命中注定与你无缘,却偏偏痴心妄想,想要嫁入杨家,相夫教子一生……可惜天不从人愿……”
独孤伽罗在他身后冷笑一声道:“适才高颎和杨林带人入府密捕,这五王已经下了黄泉。三郎,原来你竟如此狠毒,为了听妻子的话,帮宇文家做最后一搏,竟然要向同父同母的亲大哥下手!”
千金公主掀开车帘,露出一张同样满是泪迹的美丽脸庞,哭着劝道:“阿祗,你不要出家当和尚,你好好在长安城活着,好好娶妻生子,建功立业。就算我在塞外,就算我住在突厥人的帐篷里,我心里也会安然,如果你非要执意自伤,我只会永远为你牵肠挂肚,永远生活在痛苦和追悔之中。阿祗,就算为了我,你也要忘了我,开心地活着。”
这次的迎亲副使长孙晟,本是杨坚的部属亲信,常年来往于漠北和长安,是两国间的使臣,说不定是他极力向突厥可汗游说,才让佗钵可汗指名道姓地要娶自己为王后。亲事定下不久,佗钵可汗老迈不堪,上个月一病不起,命归黄泉,又是杨坚上奏章,让自己嫁给佗钵可汗之子沙钵略可汗。
顺阳公主这才怒气平息,忧心忡忡地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对了,随国公府的厨子当年是从我们家借走的,要么我送药给他,让他下在酒水饮食里。”
宇文招悲愤地道:“姐姐责备的是,可杨坚和独孤伽罗千算万算,他们却忘了一招。我女儿千金公主如今是沙钵略可汗的可贺敦,沙钵略可汗对若眉十分宠爱,千依百顺,沙钵略帐下四十万兵马,虎视塞外,难道杨坚就不掂量掂量?”
而独孤伽罗却无情地拆散了千金公主和杨俊,前天夜里,杨俊最后一次与她相见时,痛哭流涕地说,随国公夫人绝不肯答应二人婚事,哪怕他以死相逼,独孤伽罗也没有松口。
总有一天她会发现,他是个充满机心和欺诈的父亲,他利用了女儿去换取权力、地位、富贵,他利用了女儿去控制这个日渐衰弱的宇文家。
北朝与南陈隔江对峙,周军早晚要渡江与南陈决战,杨坚不愿为了对付宇文家而损失重兵。
表面上一派从容的杨坚,心里却正在风起云涌。
你杀了赵王宇文招,还要把赵王灭族,把宇文家斩草除根,可你别忘了,赵王的女儿千金公主,身为突厥可贺敦,拥雄兵数十万,还可结盟达头可汗、阿波可汗等人的二十万军马,你远非她的对手。
她怎么连这点常识也没有?竟打算将她父母虎视眈眈已久的皇权轻巧地交给一个平庸无能的少年!
杨丽华有些木呆呆地注视着郑译,不出片刻,又将视线移到站在帷幔旁边的刘昉身上。
杨瓒更不答话,持剑直插前胸,杨林再次打飞他的长剑,道:“二哥何必如此,不过是一个女人,哪里值得你舍命搭救?”
北周宣帝宇文赟生前,对哪位叔叔都不放心,杀了齐王宇文宪后,他又将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滕王宇文逌等五位王叔全都打发到外州去任总管,在外就藩。
顺阳公主信赖地将脸埋入了他的肩头。
他来往关塞多年,意志如铁,是一条见泰山崩于眼前也不会变色的硬汉,杨坚这次派他当和亲副使,就是因为他孔武有力又深沉稳重,可以震慑突厥人,可此时,他望着面前这对璧人的心碎,也不禁感到酸楚。
杨瓒怒道:“二哥,你身为忠臣之后,也要附逆吗?”
遍布天德殿四周的雄鸡,此起彼伏地叫了起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早晨。在表面上一片沉静的天德殿里,以疯狂著称的帝王宇文赟咽下了最后一口m•hetushu•com•com气。
宇文赟抬起左手,向杨丽华摇了一摇,是永诀么?
杨瓒拭去腮边泪水,搂着顺阳公主在地下行礼道:“多谢大嫂成全!”
他刚刚奉夫人之命,赶在杨坚入宫前送来一封上着火漆的信,主公没有急着打开它,而是轻轻地揣入了自己的胸前。此刻,年近四旬的杨坚,站在天德殿阒静的廊下,似乎迟迟不想进去。
“天元皇后,”郑译的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尖,心里带了几分藐视,却努力用谦卑的声音回答道,“天元皇帝即将不豫,太子年少,非能干得力之人不能定社稷……若以汉王宇文赞辅阁,臣恐其非人。”
独孤伽罗,你别得意得太早。
或许是为了炫耀国力,前往突厥的迎亲车队长达百辆,饰满金络,车内全是装满金珠玉宝的箱笼。
但在这个热闹而华丽的夜晚,她忽然看见了宇文赟身上一闪即逝的清明和忧伤。
杨瓒的手一抖,将杯中的酒泼出了大半,他颤声道:“大哥,你说什么?难道你真的准备禅代了么?”
杨瓒吓了一跳,连忙拥住顺阳公主,温言劝慰道:“公主言重了。我适才沉吟不决,不是考虑除不除杨坚,而是在考虑如何除掉杨坚和独孤伽罗。那罗延身为当朝执政,位高权重,高颎、杨素、贺若弼等人又不离他左右,要想除掉他,绝非易事,何况独孤伽罗深沉多谋、心性狡诈,不是容易对付的人。”
长孙晟并不退让,道:“公主已受沙钵略可汗之聘,虽未成亲,如今也已身为突厥王后、沙钵略可汗的可贺敦,与你份属君臣、尊卑有别。杨将军,往事已杳,你放下旧情旧怨,早日释怀吧!”
杨素、贺若弼等人见情势紧急,大步赶来救主,却纷纷脚软乏力,倒在家庙前的地下。
纵然她并不热衷于权位,但她也不能让宇文家和杨家的命运操纵在别的家族手中,她自己更不能在一个刚满十五岁、来路暧昧的女孩子手下唯唯听命。
从小生长在军营的我只知道,唯有不断建立战功、攻克城池,才能得到封爵,才能显耀祖宗,这是我父亲教我的。
他的话音未落,高颎已带着院外的伏兵翻墙而入,杨坚的手下刹那间便布满了家庙内外。
酒中有顺阳公主事先放好的迷|药,过得片刻,便会奏效,令饮者手脚无力,杨瓒见四人都已饮下药酒,又与杨坚攀谈片刻,估摸着药性该发了,这才站起身道:“大哥,你身为执政,百务繁忙,不如先去母亲牌位前祭祀一番,便可回朝办事。”
顺阳公主呜咽着扑在杨瓒怀中,泣道:“三郎,今生有你,怡儿无憾!怡儿此生无以为报,愿以死明志,不拖累我的三郎!”
杨俊性格温文尔雅、仁恕忠厚、为人至情至性,相貌俊朗挺拔、英气过人,是有名的美男子,而且聪明能干,精通书史骑射,所以从千金公主懂事时起,她就把自己当成了杨俊的女人,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和亲公主,要出塞嫁给食膻卧毡的突厥可汗,在戈壁荒滩上度过一生。
既然,年轻的天元皇帝没有留下遗命,也没有指定辅命大臣,那么,此刻的天德殿,实际正在决定一个王朝的命运。
长孙晟拍马而出,举起手中长槊,横在车队之前,喝问道:“杨将军,公主出塞和亲,你何故要拦住去路?突厥使臣与大周使臣全都在此,望杨将军自重,勿扰公主。”
望着并坐一席的杨坚与杨瓒,人到中年的顺阳公主发现,当年杨坚的英雄气依旧威重,即使以杨瓒的风姿,在面貌古怪的杨坚身边,还是会被对比出一丝丝的平庸伧俗。
当年周太祖宇文泰共生有十三个儿子,可除了被宇文护所杀的明帝宇文毓、闵帝宇文觉,叛乱自杀的卫王宇文直,被侄儿杀死的齐王宇文宪,病故的武帝宇文邕、宋公宇文震、谯王宇文俭、冀王宇文通,眼下太祖十三子仅剩五人,赵王宇文招最年长,其他四王还不到三十岁,大周开国二十多年,她的兄弟们已死伤殆尽,而这全都要怪独孤伽罗那个野心勃勃的女人。
刘昉比郑译年龄大几岁,但外貌和举止却显得年轻得多,面容上带着一种无法掩藏的浮滑气息,此刻,这个平时十分能言善辩的御正下大夫,却保持着令人敬畏的沉默。
他虚弱地向身边不远处的杨丽华看去,却见她盘坐在紫檀漆几后面,一动不动,脸上连睫毛都没有掀动一下,只有两行清亮的眼泪顺着瘦削的脸颊徐徐流下。
车行十余里,来到龙首原下,千金公主不经意地抬眼望去,却见高高的坡顶上,有个人只身匹马,怔立风中,眺望着车驾的来处。
杨瓒扶起了赵王宇文招,道:“你们都别着急,杨坚与我同父同母,后日是先母吕夫人祭日,我在府上设家宴招待他与独孤伽罗,料他必不防备。你们五王伏兵家庙之外,待杨坚夫妇一入家庙,便合力拿下他们二人,首奸既除,其他人便不足为虑。”
可是伽罗,为什么你不能满足于这一切?
杨瓒持剑一步步走近独孤伽罗身前,近乎狞笑般说道:“独孤伽罗,你这奸险女人,也有今天!”
千金公主曾听姑母说过,独孤伽罗的父亲当年效力于自己的祖父宇文泰帐下,建下不世之功,最后却受冤惨死、家破人亡,可那是奸臣宇文护办的事,周武帝宇文邕不是为独孤公平反了吗?还把独孤家的几个儿子都任用为将军。为什么随国公夫人要把上代的仇记得这么久,甚至记到了自己身上?自己的血缘难道是与生俱来的罪愆吗?
不,明远大师早在他少年时就曾赞叹过:那罗延,你天生有着帝王的威严。
依杨丽华的意思,目下的第一件事情,应该将宇文赟的弟弟宇文赞召入内宫,指定他为摄政王。
杨瓒缓缓跪到地下,仰起脸庞,落泪道:“大嫂,既和*图*书是当年独孤家打来的天下,你已从宇文家手中夺走,太祖十三子,也已全都铲除干净,宇文泰已得报应,一切如你所愿,你为什么就不能饶了怡儿一命?她身为女流,从不明朝事政事,又有何辜?你与大哥真心相爱,我与怡儿也是真心相爱,夫妻情重、愿同生死,想必大嫂比别人更明白,今日你能放过怡儿,不拆散我们夫妻,三郎便愿屈膝为臣,追随大哥大嫂,倘若大嫂眼里真容不得怡儿,怡儿去哪里,三郎便去哪里,哪怕流落南朝乞食,我也决不后悔!”
同样人到中年的独孤伽罗,还是有同龄女子无法比拟的仪态和姿容,她夺走了顺阳公主当初的姻缘,又要夺走宇文家的天下。
叠成四叠的信纸上,是伽罗那颇具秀骨清相的字体,庄重而沉着:
她不能明白郑译、刘昉如此作为的背后原因,她只是在心底里涌起一种隐隐的喜悦,一方面是庆幸自己地位的稳固,一方面是为父亲能有这样的声威而高兴。
独孤伽罗下意识地一把抓住顺阳公主裙带时,顺阳公主的额角已撞出血洞,血流涔涔,纷披在那张苍白的俏脸上。
长孙晟见他痴情如此,又绝望如此,竟因婚事不谐出家为僧,心下不禁生几分同情,收回大槊,轻轻一挥手,转身拨马离去。
顺阳公主听他布策周全,大是感激欣赏,走近夫君身边,望着那张人近中年却俊美依旧的面庞,伸手抚摸着他眼角的皱纹,微笑道:“三郎,直到此刻,我才觉得今生所托是我前世修来的好夫君,三郎对我情深意重、恩泽家人、不惧凶险、不恋权位,让妾身满心感激、无以为报。大周宗室若得保全,我愿此生为三郎做牛做马,今后生生世世,与三郎永为夫妻,永续姻缘!”
顺阳公主眼前一花,脚步一软,颤声道:“你……你好狠毒,独孤伽罗,就算我爹算计了你爹,就算我爹的天下是独孤信一刀一枪打下来的,可独孤信不是我爹杀的,是宇文护这个奸臣杀的,这账你为什么要算在我爹头上?你夺了大周的皇权还不算,还要杀光太祖所有的儿子,你……你这个毫无信义的蛇蝎女人,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杨瓒知道自己论武艺不是杨林的对手,面前敌众我寡,此时已无退路,一咬牙,拾起长剑,对着自己的前胸道:“大哥、大嫂、二哥,你们做此无父无君之事,不但让我愧对武帝,愧对公主,更让我愧对杨家的忠臣名声。今日我杨瓒宁死不肯附逆,你们若愿留公主一条活命,我便与公主弃官归隐,隐姓瞒名,消磨残生,你们若不肯放过公主,我就死在你们的面前。”
杨坚携着独孤伽罗站起身来,杨瓒夫妇则陪在二人身后,杨素等四将在十步外跟随,一起往后院的家庙走去。
五位王叔领兵在外,他若想有所废立禅代,宇文泰这剩下的五个儿子肯定不会答应,立即会起兵勤王,围攻长安城。
除了丰厚的嫁奁,车队后面还跟着数百名浑身盔甲的大周骑兵,一个比一个显得剽悍神勇。车队不疾不徐地驶出长安城,前往朔州,再前往沙钵略可汗所住的都斤山。
只有尉迟炽繁的家里与众不同,论起家世,尉迟家与宇文家是亲上加亲,二世都尚公主;论起名望,尉迟迥收复过西蜀,当了多年辅政大臣,手下旧部不少;论起实力,尉迟迥现在是外任的相州总管,总揽北部军权,比自己即将上任扬州总管、总揽大周南部兵权的父亲杨坚兵力更强……
杨瓒从堂后走了出来,叹息道:“我大哥其实并无多少野心,都是那个独孤家的女人只手遮天,意欲篡夺皇位。如今她女儿身为当朝太后,她的夫君儿子领秦州旧部数十万,朝中七大虎将,全都被她收买,此刻你们宇文五王入京,只怕凶多吉少。”
“七弟,你明知叛党当权,杨坚那贼子要召你们入京夺兵权,为何还要前来?”顺阳公主怒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何况是杨坚、独孤伽罗这对篡国奸臣夫妇的矫诏?你们这一来长安城,还能活着回去吗?”
车队两旁吹奏着胡笳和羌笛,悠悠胡乐,越发让她心境变得悲凉。
究竟是毋令什么,他到底没有说出来,便昏迷了过去。
在这个非常时刻,她竟然是如此的优柔难决,旁边若换了别人,而不是郑译,早已将杨丽华玩弄于股掌之上。
“那……该召谁来?”杨丽华犹豫起来,除了宇文家的亲王外,朝中的重臣,就得算那几位皇后的娘家人了。
我只想携着你的手,坐在我们种满白杨树的府院里,看那些英气勃勃的儿子们长大成人。
杨瓒摇了摇头道:“如今大哥知道树敌太多,宗室欲行暗杀,家中门禁森严,厨子早已换去,还有大总管李圆通处处设防,想要暗中下毒行刺,只怕难以奏效。”
顺阳公主听得夫君情深如此,满眼落泪。
汉王宇文赞是个肥胖得有些愚蠢的少年,他甚至没有其兄长畸型勃发的生命力,整天显得无精打采,连脑子都懒得多动,只会抱着一袋水烟,和清客们聊聊天、喝喝酒,看起来暮气沉沉。
前来求婚的佗钵可汗年近七旬,居然能厚着脸皮向刚刚成年的大周公主求婚,千金公主甚至怀疑,这件事背后有杨坚夫人独孤伽罗的推手。
般若寺的明远大师虽然不断地向我说过:“你来处非俗,只怕是魏室子孙转世……”就算真是拓跋家的儿孙又如何?多少拓跋氏儿孙,被权臣们推上皇位当傀儡,又被随意毒杀,我在朝为官多年,看够了皇位上的血和变幻。
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独孤伽罗一言不语地坐在她身边,顺阳公主忍不住憎恨地望了她一眼。
见识不出宫掖的杨丽华,终于点了点头。
御正下大夫刘昉和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中https://m.hetushu.com.com大夫颜之仪,是最早被召入天德殿的三位大臣。
陈月仪的父亲陈山提和元乐尚的父亲元晟,均在不久前加封了上柱国,但他们并不带兵,徒有其名而已。
果然像郑译预言的那样,疯狂透支身体的宇文赟,没能活过大象二年(公元580年)的夏天。
你即将年满四十,成为一个半老的妇人,却仍然会在独孤信的忌日里手抚那柄弯月宝刀,泪流不止,二十多年的尘埃积累,再深的血迹也消失了踪影,而你却从不肯忘记。
伽罗说得没错,宇文赟是个过于任性的一直没有长大的孩子,他的悲剧在于,这个王国和这些大臣,总是恭顺地服从着他恣肆而狂野的念头。
原来她当年的承诺和疼爱全是假的,全是欺骗和伪装,她是长安城里有名的仁者,常常抚孤问贫,见到路边有人被行刑都会坠泪,她精通佛理、每年布施无数,可却独独对千金公主如此残忍狠心,莫非就因为她姓的是宇文吗?
坐在六马青盖安车里,被车队带往天边的千金公主宇文若眉,似乎仍然能感觉到长安城头上有杨俊烫人的目光。
“三郎,父母逝去多年,你我手足情深依旧,娘在地下有知,也当欣慰。”杨坚敬了杨瓒一杯酒,和蔼地道,“你也知道,大周天下得之不义,如今众叛亲离,我们杨家才是天命所归。大哥明天就加封你为邵国公、大宗伯,你我兄弟一体,今后共享荣华富贵,共守江山。”
杨瓒知道杨坚的心意不会再更改,心底也暗自下了决心,他望着杨坚与独孤伽罗夫妇身后站立的杨素、鱼俱罗、贺若弼、伍建章四员大将,心知这四人均是万人敌,若跟着杨坚夫妇同入家庙,自己所谋未必能成,便站起身来,命人端过酒壶,笑着为杨素等人一一斟满酒杯,亲手奉上,笑道:“今日杨府家祭,有累各位将军守护,这里是水酒一杯,杨瓒先干为敬了。”
杨俊抓着她的手,呜咽得说不出话来,千金公主一眼望见他衣服肩头绽开了个口子,笑道:“这还是两年前你过生日,我花了三个晚上给你做的衣裳,旧成这样,你还肯穿着,来,阿祗,姐姐最后一次给你缝补衣裳。”
从来没有一个和亲公主重返过长安城,今日之后,是为永诀。千金公主情难自禁的眼泪,一滴滴打湿了杨俊肩头的衣裳。
杨丽华不能甘心。
再过几天,八岁的小皇帝宇文阐就将临朝听政了,她就算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自己的五个弟弟着想。
不知道为什么,杨坚忽然有点手脚发抖,不,伽罗,我从不曾有这样的野心,我自幼心如止水,相貌虽然威严,其实并没有多么广阔的心胸和抱负,更没有高颎那么多令人赞叹惊讶的念头。
在这华丽的房间,凝视着这个终于在疯狂的顶峰凋谢的年轻皇帝,郑译在心里猜测,宇文赟想说的,大约是毋令外戚专权罢?而默默坐在床侧落泪的杨丽华却在想,是不是毋令宇文阐疯癫痴狂如乃父?
杨坚和杨林都没有说话,同时望着脸色沉静的独孤伽罗,独孤伽罗斩钉截铁地道:“除恶务尽,长安城里,一个姓宇文的都不能留下,既是三郎情重,要留顺阳公主一命,那就命顺阳公主剃度出家,落发为尼!”
我一直乐于享受清静无为的生活,沙场百战,我的心早已粗糙而倦怠,我甚至失去了对政事的热衷,也失去了对独孤信大人“一统九州”梦想的向往。
这就是他和伽罗窥伺了二十多年的机会么?
赵王宇文招走入上柱国杨瓒府中的那一刻,顺阳公主刹那间红了眼睛。
这狠毒的女子偏偏又如此能干,如此老谋深算,多年来对朝中重臣深相结纳,令他们甘心匍匐她裙下,成为大周的叛臣,大周皇室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今天的顺阳公主和杨瓒,不过是在做困兽之斗。
杨坚点了点头,望着画堂前艳若云霞的灼灼桃花,道:“宇文泰祖孙三代,多行不义,宇文护屡次弑帝、大杀功臣,篡夺魏室天下;宇文邕多疑好杀,灭佛毁庙;宣皇帝更是疯狂悖逆,惹来天怒人怨,灾荒不断。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唯有德有能者居之。三郎,你大嫂家与宇文家更有不共戴天之仇,愿你我兄弟同心,重振朝纲。”
杨勇在前两年就因为平齐之功被封为上柱国、大司马、总领旧齐之地的洛州总管,年纪轻轻便继承了外祖父和父亲都曾拥有的高位,而且,出身将族的他甚至比父祖更出色,不但会带兵打仗,而且雅通典籍、善解词赋,长安城里没几个少年能比得上。
杨坚见杨瓒早已设计要害自己,勃然大怒,拔出剑来,正要与杨瓒对决,却觉得眼前一花,同样手脚发软,瘫倒在地,原来杨瓒敬给他的酒中,也已下药。
“刘大夫,依你之见呢?”也许是为避亲嫌,杨丽华没有立刻答应郑译,而是不放心地询问起了刘昉。
独孤伽罗脸上神色微变,此时黑肤卷发的李圆通从画堂外走来,在独孤伽罗耳边轻轻说了两句话,独孤伽罗神情才重新变得平静。
虽说杨坚有老帅韦孝宽和高颎、杨林、杨素等七位虎将愿为他效力,就算决一死战,他也只会赢,不会输,但这场恶战打起来便会山河变色、死伤无数。
杨瓒心知有异,大喝一声道:“赵王何在?越王何在?”
待得宇文赟身故,身为执政大臣的杨坚便觉得有些棘手。
家庙外静悄悄的,几树盛开的桃花梨花,在春阳下粉白玫红开得正热闹,甬道两旁竹影森森,十分幽静,听不到半点动静。
那个人到中年仍然美貌端庄的女人,曾几何时,在自己的心里,她就是个温蔼可亲的亲人、内外兼修的贤母,在年少的梦中,千金公主甚至还想象过自己与杨俊能牵着一对同样可爱的儿女,站在当年的花树下,出现在独孤伽罗慈祥关切的目光中hetushu.com•com,亲亲热热地喊她一声“娘”。
据说仅宇文赟内室修饰所用的黄金珠宝,就动用了北朝整整一年的赋税。如今的北朝,比从前的哪一年都要徭赋沉重。
杨丽华细想一下,觉得果然如此。
杨坚疲倦地扶住身边的栏杆,他不知道自己该怎样面对天德殿里女儿信任的眼神。
长孙晟悄悄背过身去,擦掉自己眼角的一滴眼泪。
顺阳公主跺着脚道:“杨瓒,杨三郎!你们杨家世代将族,我父皇亲赐你们家‘普六茹’之姓,将你爹提拔至都督十五州军事、柱国大将军、随国公的高位,又把我嫁给你为妻,生儿育女,夫妻情深。你爹是个骨鲠忠臣,你也是丹心汉子,只有大哥被那蛇蝎女人蒙蔽,执迷不悟,你若能忠君为念,助七弟剿灭杨坚和独孤伽罗,太祖和武帝在地下,也会感激涕零,我宇文怡也将永生相随、生死不弃,你若仍念手足之情,暗中助逆,我就带着所有孩儿在你面前自尽,让你断子绝孙,妻离子散!”
因此他以小皇帝宇文阐病重为由,调赵王、陈王、代王、越王、滕王这五个王叔入京,欲行平抚之策,先夺兵权,再逼他们闲居在家。
“事到如今,你还假仁假义,救我干什么?”顺阳公主气息微弱,没好气地甩脱了独孤伽罗的手。
我曾向你说,此际宇文家都是孤儿寡妇,若忠心佐辅,可以成就杨家忠义保国的赫赫名声,传布四野,而你却鄙夷地答道:“那罗延,别相信那些忠君爱国的圣人曰,我爹就是死在这上头。宇文家的天下,来之不义,便应当受到不义的回报。”
紧随他进来的李圆通,在很远的地方注视着自己的主公。
独孤伽罗自己与杨坚夫妻恩爱,却为何不能让儿子也拥有那样的幸福?
杨坚点了点头道:“也好。”
杨瓒心下有些嘀咕,赵王宇文招与陈王、越王这五人,今天一早就预备了三百甲士,伏兵于家庙内外,这么多人的气息,竟会如此宁静?
千金公主实在是不能明白她,车驾又前行一里多路,驻马高坡的杨俊突然一提缰绳,驱马狂奔过来,拦在了迎亲车驾的前面。
独孤伽罗微微一笑道:“赵王、陈王、代王、越王、滕王,他们已经全数被高颎抓捕,就地斩首了!宇文怡,你所有的兄弟都死了,周太祖宇文泰所有的儿子都死光了!背叛兄弟、无信无义的奸雄,终于遭到了报应!”
顺阳公主拦住他道:“且慢,独孤伽罗,你刚才说赵王他们都怎么了?”
我答应过你,这辈子誓不生异母之子,因此从结发至今,我的视线从不曾旁移向第二个女人。
颜之仪赶紧出去,领命召集群臣,到长安城外各寺为皇上祈福消灾。
她站起身来,往地下巨大的铜香炉上一头撞去。
他怀中仍在哆嗦流血的顺阳公主,却向独孤伽罗投去仇恨的目光。
伽罗顿首
倘若因为自己此刻的犹豫,令杨勇、杨广、杨俊、杨秀、杨谅这些同母兄弟们永无立足庙堂大展身手的机会,那么,自己将成为家门的罪人。
五月天气,天德殿的莲池中竟然有大朵的红白莲花盛放,杨坚定睛细看时才发现,这些亭亭盛开的莲花,是宫女们用名贵细致的丝绢精心扎出来的,花姿、花形和花色各异,看起来生动极了。
这三个从不离宇文赟左右的心腹,此刻不禁沉入了巨大的惶恐中,怎么,这个从不愿过问政事的年轻皇帝就这样离开了,将大周的赫赫皇权留给宗室和大臣们抢夺?
这两个面目如画的小儿女,如此相配,又如此深情,为什么随国公夫人要活生生拆开他们,让他们从此走向茫然不可知的命运,从此在这世上与心爱的人永别?
她命人拿过针线来,就在杨俊肩头细心织补着绽口,针行细细,织痕浅浅,却是她最后的留念与诀别。
独孤伽罗长叹一声,望着地下搂成一团、泣不成声的杨瓒夫妻,淡淡地道:“世上尽有这些痴儿痴妇,令人感怀难安。三郎,宇文怡,我今天就成全了你们,不拆散你们夫妻,可是宇文怡平日常在背后设巫蛊,咒诅我们夫妻,罪不可恕,她的一应尊号,全都取缔,今后不得以命妇身份,出现在长安城中。”
就算他此刻停手,又有谁肯相信他的清白?
顺阳公主听得心中惨痛,对杨瓒大叫道:“还不快杀了她!”
不知过了多久,杨坚才信步走上了空无一人的游廊,他的长方脸被长须遮挡了一大半,看不出那神情是悲哀还是紧张。
杨瓒沉吟不语,赵王宇文招情急之下,跪倒在地,泣道:“三郎,如今大周的锦绣江山,宇文家的前程命运,全都系在你一人身上,三郎若不答应,我便跪死在这里,也不起来!”
装饰华丽无比的天德殿内室,即使在两枝素白蜡烛的照耀下,也发出了煊赫夺目的芒彩,这里的帐子帷幔上刺满了金绣,每一束流苏边都装饰着珍珠和宝石,地上用黄金砌地、白玉升阶。
杨俊缓缓摘下头顶的纱冠,露出新剃去长发的锃亮秃顶,黯然道:“我昨日已在左冯翊寺落发为僧,长孙将军,今日的杨俊,已是世外之人,绝无情思绮念,可前尘旧爱,贫僧也要一一了断。”
听母亲说,他们一个个都是英睿不凡的少年。
杨林与杨坚、杨瓒二人不同母,因此今天没有出现在杨瓒府上。
然而那已经不重要了,杨瓒才是对她一心一意、生死追随的夫君,杨坚,心里只有独孤伽罗,只有独孤家多年前的怨仇,已成宇文家的死敌,不除杨坚与独孤伽罗,太祖一手打下、百计谋得的江山,就会被独孤家收入囊中。
天元大皇帝宇文赟在夜宴上忽然一头栽倒,惊慌失措的妃嫔们将他扶起来时,只见宇文赟鼻歪口斜、嘴角流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一双酒色过度的眼和_图_书珠还能痛苦地转动。
宇文赟在忽而清醒、忽而昏沉的瞬间,吃力地向他们说道:“善……善辅我儿,毋……毋令……”
这一次,看样子他再不会醒来。
迎亲车队已停,杨俊翻身下马,走到饰满金玉的六马安车前,隔帘垂泪道:“若眉,不是阿祗有心要负公主深情,实是阿祗有心无力、身不由己,愿公主此去塞外,善自珍重,今后与可汗夫妻恩爱,安享尊荣。阿祗今生辜负公主,无面目再存活于世,又不能自决以伤父母怀抱,只能剃度出家,从此了尽尘缘、四海飘零。”
千金公主拿出手中绢帕,探出窗外,轻轻为杨俊擦干净眼泪,勉强笑道:“阿祗不哭,我也不哭,既是天意如此,我们便应该笑着分别。昔日情,往时意,种种美好,永藏我心。阿祗,哪怕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忘不了你给过我的温柔和深情。我不恨随国公夫人,她自幼待我如母,还生养了我深爱过的阿祗,可她放不下心底的父仇,这怪不了她……要怪,就怪我祖父宇文泰,他太恋权位、背信弃义、对不住独孤家!”
杨林面无表情地道:“爹临终之际,嘱咐我这辈子要好好听大嫂的话,爹也说过,宇文家所行不义,终遭报应,三弟,你别再为了顺阳公主执迷不悟了,好好追随大哥大嫂,另建新朝吧!”
当初她是大周公主,美貌如花、身份高贵,他真心爱着自己,如今她已是亡国余孽、半老徐娘,他仍对自己一往情深,此生得夫如此,夫复何求?
自宇文赟登基以来,天台天德殿的夜晚,还是第一次呈现出一派宁静的面貌,那密如急雨的丝管和彻照十数里的灯烛已经消失了,在门前往来不息的女装少年们也不知去了哪里,留下的是天德殿门外那些奇形怪状的设置:圈养巨兽的笼子、抛枪弄剑的钢丝套、舞伎攀爬的漆木蹬……
夜风越来越凉了,小宦官将杨坚引领至天德殿的二道院门外,便停住了脚步,恭敬地弯下腰来,道:“随国公,请自行入见。”
二十年来,李圆通来往边塞,冒着苦寒风霜与突厥大规模互市,而那些盈利所得,杨坚却全用来了交通大臣,还有他在秦州旧部里的市恩买惠,送女儿入宫为后,与宇文赟的宠臣郑译重叙同学情,收高颎、李德林两个以智谋闻名的大臣为自己左膀右臂……在做过了这一切后,他还想重拾忠君报国的臣纲么?
家庙之前,有两个汉子低头推开庙门,杨坚一把拉住杨瓒的手,走了进去。
这两个月来,她与他落下的眼泪,比长安城今年春天的雨水还要多。
那罗延:
借着天边微明的曙色,杨坚探手入怀,取出那封纸质精良的信函,伽罗很少舍得用这么好的纸,因此更让杨坚感觉了这封信件的沉重。
明明自幼相识相知,明明两人深情早种,明明可以厮守终生、白发偕老,明明二人宁死也不甘分离,却因了独孤伽罗心底对宇文家的敌意,狠心要斩断二人缘分,让二人从此坠入暗不见天日的深渊。
杨坚点了点头,迈步走进夜色深沉的天德殿前院,这座天德殿,他素日奏事时经常来,但此际的月色里,院中楼台幽静、池阁深沉,令他觉得异样陌生。
郑译口中不说什么,心里却觉得奇怪:这位性情贞静固执的杨皇后,看起来真不像是杨坚和独孤伽罗的女儿,她几乎完全不懂得权术——在这个非常时刻,谁第一个来到快要咽气的宇文赟身边,谁就掌握了北朝至高无上的权力!
“既临大事,当然该召请随国公入见。随国公亲则国丈,重则国之宰辅,而况明决果睿、名重北邦,监国之人,非随国公莫属。”郑译仍然是眼观鼻、鼻观口,但心里却起了阵叹息,这个杨丽华,为什么她没有她母亲一半的果断和明智?
杨瓒一把拔出剑来,怒道:“大哥还不是一样,一心只听妻子的话,要当大周皇室的叛臣贼子,做下这杀头灭族的勾当!独孤伽罗,你处心积虑多年,不就是为了篡权夺位么?告诉你,有我杨三郎在,你们休想!今日你俩一并在先母牌位前受死,我杨三郎大义灭亲,为大周除此叛贼!”
他们一个个看起来是那样优秀而且手足情长,出身将族的他们,像小老虎一样强壮,精于骑射,热爱谈论兵事,他们都是天生的大将。
杨瓒手起剑落,正要除去独孤伽罗,杨林从家庙外飞身而至,掌中一双水火囚龙棒交错,击飞了杨瓒手中的长剑。
独孤伽罗毫无惧色,望着杨瓒锃亮的剑尖,冷笑道:“太祖生前,宁可负尽天下人,也要为儿孙谋夺权位。我爹为了忠义二字,从不居功,明知太祖花言巧语,对他全是利用,却也看在兄弟情分上,心甘情愿为你爹卖命。当年独孤公追随孝武帝投奔到长安城时,你爹手中只有数千兵马、一座孤城,就算这数千兵马,也是我爹在贺拔岳帐下让给你爹的。此后你爹封我爹为荆州太守,我爹便以八百兵马对决田八能的万人大军,夺取荆州。太祖故技重施,又任我爹为秦州刺史,我爹便抛妻弃子十多年,困守荒无人烟的秦州,十年血战,辛苦经营,练成纵横天下的秦州铁军,前后为太祖攻取二十多城,占据千里关陇,得与北齐高家平分天下,却被你爹遗命,巧取兵权,以‘信义’二字诱迫,死于非命。我爹明知你爹奸险,却死心塌地,不肯防备,他临终之前,曾对我说,倘若他此生忠心侍君、信义待友,却最终不得好死,那就让他独孤信用死来告诉天下人,信义二字,从此不如粪土!宇文怡,你没资格跟我提信义二字,你爹用这两个字骗了我爹一辈子,骗得他含恨而死。所以我不但要杀光太祖所有的儿子,还要杀光他所有的孙子,杀光所有宇文家的人,让世人知道,背叛信义,会有什么样可怕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