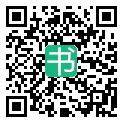第二十集
第七章
小镇来的猎人不慌不忙的藏在大树后,他的硬弓再一次张开,然后从大树左边闪身而出。“给好姑娘地!”一名敌人应声倒地!妥斯拉克闪回树后,再装新箭,接着便由大树右边闪出,“给海斯尔!”又一名敌人哀叫着中箭。
遍体鳞伤的艾尔巴被围在林地中心的开阔地,它很愤怒,但异常冷静。身体不但遭受的创伤并未消减它的斗志,它是丛林之王艾尔巴,即使是狡猾的妥斯拉克也不是它的对手,更别提眼前的这些三流货色。
“得了吧……”潘尼蒂哥隆嘲讽地打量着猎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父母妻儿会和那些被捆在木桩上待人宰割的士兵一个样。”
丛林之王在剧烈的喘息,它不认得猎人,只记得他的气味。艾尔巴也很疑惑,上一次他们抱在一起是为了争夺生存的权利,可是这一次呢?一切全乱套了!艾尔巴不喜欢猎人的气味,但却钦佩对方在战斗时的勇气。
马匹在山梁上跃动,骑士的面甲完全遮蔽了年轻的面孔,我们只能看到战士们的眼中映衬着壮烈的火光。
狗子们直到这时才清醒过来。他们怪叫着扑向同伴,但丛林中又透出一枚箭矢。强劲地铁箭将一只狗子射飞出去,不过余下的狗子已经看清箭矢来袭地方向,三四个人向敌手藏身的地方冲了过去。
“谢谢!谢谢……”女人向四周不断鞠躬。她知道自己和孩子们将是最后的乘客,而滞留在渡口的人则要面对毫无光彩的未知命运。
妥斯拉克是森林里的常客,就像睡在树洞草窝里的老豹!这名经验丰富的猎手常常都在想,若是让林子里的黑豹跟那些动不动就踢门的地方税吏打交道会怎样?估计老豹要是还想在森林呆下去地话就得为它那身黑丝绒一样华丽的皮毛支付三个银泰。
妥斯拉克就是这么简单,他觉得“好姑娘”的死完全是自己的错!
彭西勒上将从长旗官手里抢过自己的十二区军旗。他很自豪,因为军旗上有他最喜欢地犀牛角。要想获得犀牛角。猎人就得拼命。要不然……在犀角发动愤怒的冲撞时,猎人的胸膛也会像草纸一样单薄。
勋爵要被排除在外,男爵要给子爵让道,子爵要受伯爵奚落,而伯爵就用塞满钱袋的肚楠冲撞守护渡船的小兵。泰坦贵族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谦虚守礼,他们大声叫骂、疯狂诅咒、或威胁或恐吓地催逼附近的每一个人,直到一队战士将他们驱赶到远离栈桥的地方。
阿斯根上尉再次敬礼,他向自己的士兵挥了挥手,骑士学员就将那位面容枯槁的年轻母亲从人群里领了出来,不过他们在穿越近卫军组成的人墙时却遇到了麻烦,一名状似疯狂的贵族老爷用皮鞭抽打可怜的女人,并要挟她让出船上的位置。
“去他妈的!管他呢!”苏里加尔平静了一下,他抖了抖手。尖刀上地血珠立刻就被甩落了。敌人的炮火绝对不会等到自己的第一百刀,苏里加尔不想面对这个事实,虽然他见惯死亡,可并不代表他已厌倦尘世。不珍惜生命的亡命徒倒是很多,不怕死的刽子手却很少很少。
“去吧……”一名猎户打扮地壮汉突然对女人叫喊起来,“光明神祝福你!”
那位小姐叫什么来着?妥斯拉克仔细想。可他就是记不起镇长家的那位姑娘。不过猎人知道那是一个好姑娘。他对好姑娘的定义就是可以为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付一个银泰的姑娘。那个大眼睛细脖子的姑娘还对他说,以后若是遇到这种可爱的小动物千万不要用弓箭……多好的姑娘!
猎人的脑子很简单,但他已经知道眼前的这个少年人想要寻死。
刽子手听到身后的士兵发出密致的喘息。而敌人地阵营似乎也紧张起来,那几门铜炮附近人影晃动,似乎炮手已经得到命令。
今天。妥斯拉克又遇到海斯尔,他是被一阵阵凄叫吸引来的。看看那些古腾,再闻闻空气中浓郁的尿骚味,猎人强自打起精神,他知道丛林之王的巢穴就在眼前了。
“你会骑马吗?”预备役上尉兴奋地拉扯着年轻的猎人。
渡船离开栈桥的时候。人们都哭了,由贵族起头。这些佩带各种家徽地老爷就像指挥家一样,用歇斯底里的表现控制痛哭的节奏和音量;然后是商人,这些人心疼的不是命,而是腰里的金钱。他们害怕即将来临的抢劫,那比夺走他们的性命更加可怕,其实说白了,那还不如要他们的命;最后……贫苦的百姓哭得最有道理,他们身无长物,只有廉价的性命,可这个时候,生命已经是餐盘上地血肉,尽管他们已经习惯任人鱼肉,可绝望的心情仍要得到宣泄。
潘尼蒂哥隆,阿斯根上尉摆脱了纠缠他的一名贵族,他向面色阴沉的老巴克致以军礼。
妥斯拉克也不知是为什么,他竟然要该死的站出来了。“当兵的!我知道。我对附近地一草一木熟悉透了!”
“艾尔巴!”这是妥斯拉克为眼下这片领地的主人取的名,艾尔巴是少数与他打过交道地黑豹之一,它在妥斯拉克身上留下三道永不消磨的爪痕。而妥斯拉克也给艾尔巴的脊背划了一刀。就此,艾尔巴与妥斯拉克结了生死之仇,他们都在祈祷能够在广阔地原始森林里遇见对方。
于是这m.hetushu•com•com些外国人就变得很聪明,他们在遭遇抵抗之后便放弃试探,只是切断了国道,将渡口地区封锁起来,不过……据说这些家伙在沿途任意射杀逃难地当地居民。
潘尼蒂哥隆叹息了一声,难道真要带领余下不多的学员突破侵略军的封锁?这样根本赶不到卡封堡,他们在路上就会被歼灭。
“艾尔巴!”妥斯拉克惊异地抱着从前的生死之敌,他竟然从艾尔巴的目光中读到关切的意思,不过更多的仍是继续战斗的激|情。
至于那个俘虏,泰坦近卫军第十二军区总司令彭西勒·多涅尼斯上将爬上破损不堪的城头,他找了找。还好!那个荷茵兰军官还有一颗稍算完整的人头。
潘尼蒂哥隆的面孔冷了下来,他抓住那位老爷的鞭子,并用剑柄猛敲对方的脑袋。肥头大耳的贵族立刻摔倒在地,不过他仍在叫骂,说什么一个婊子和一群小杂种怎么可以取代一位帝国伯爵的位置。潘尼有点不耐烦,他用长剑削去了这个家伙的头发,结果这位伯爵便不敢出声了。
“是啊……去吧!快去吧!”人群突然响应起来,而那位母亲也已泪流满面。
年轻的猎手丢开长弓,他的杀猪刀挡开敌人的骑士剑,顺势一转便在狗子的大腿上带走一片血肉,余下的那个家伙反应不慢,他刺向猎人的左肋,可猎人急急转身,这一剑刺在坚硬的箭囊上。猎人刀交反手,在转身的时候借力一抹,狗子捂着脖颈跌出老远。妥斯拉克踏住腿部中刀的那个家伙,并从箭囊里取出一支铁箭刺入对方地眼睛。
这名战士自然很高兴,他用仅存的一只手臂抚摩小女孩儿的金发,并说:“谢谢……”
渡。他地祖先曾用最英勇的奋战守卫今日的军用口岸。于是泰坦皇帝就将渡口以布塞巴克这个姓氏命名。
“哈哈哈!”战士们这才笑了起来,“我们都是这样!”
城墙下面,很远的地方,侵略者的阵营里蹲伏着五门铜炮。苏里加尔回忆了一下。他记得就是这些铜炮打出的实心弹替换了导师的胸膛,他地导师直接从城墙上飞了出去,最后不知落在什么地方。
“你身手这么好。怎么不去参军?”
晴空下,窄刃短刀晃了晃,带起一片颤抖的阳光。刽子手的小徒弟大声报数,“第一刀!”
“第二刀!”
“谁想要一位寡母和四个孩子地位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但贫民地阵营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们眨着眼。用羡慕的目光盯着女人看。
阿斯根上尉笑了起来,“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都很小,您可以把他们安置在伤员的床板下面。”
妥斯拉克哑口无言,他不明白,他只能简单的认为,这是军人的使命感在作祟。
丛林中传来断断续续的豹鸣,年轻的猎人毅然决然地收起弓箭,他向奄奄一息的海斯尔拍了拍胸口,“我去救它!”
潘尼蒂哥隆带着自己的骑士学员和头脑简单的猎人上路了,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攀谈起来。妥斯拉克有点诧异,他看不出面前这个眼圈黑得像个无底洞的家伙会是一位圣骑士,而潘尼也在看到猎人怀里的那头幼豹时肃然起敬,他对艾尔巴与海斯尔的故事极为动容。
终于!侵略者的炮火如期而至!
巢穴里唯一幸存下来的幼崽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母亲身上以及兄弟姐妹的血腥气令它很兴奋,尽管它的母亲手刃了子女,可它还是围着母亲不断玩耍。对于它这种年纪的小豹来说,生命就是游戏的一部分。
猎人走出藏身地地方,他像往常那样搭弓上弦。箭矢直指正值壮年的母豹。不过现下的状况有些古怪,妥斯拉克在黑豹地爪下存活下来并不是一件幸事,他很了解这种异常凶残的掠食猛兽。海斯尔的状态很糟糕,它一定遭遇了什么!
精壮机警的海斯尔猛地抬起头,它发现了芭蕉树后的猎人,它很想扑上去警告一下冒失的入侵者,可它背上的伤痕已经完全开裂,它的血液在以洪水倾泄的速度流失着。
“海斯尔!”这是妥斯拉克为艾尔巴的妻子取地名字。它像丈夫一样凶猛,但比脾气暴躁的艾尔巴乖顺一些。妥斯拉克遇到过海斯尔好几次,但海斯尔只是对着空气闻了闻,然后便带这一身王后一般尊贵的亮丽皮毛默默走开了,它并不看好雄性之间的争斗,它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应付各种领地事务和仍在嗷嗷待哺地幼豹。
预备役上尉摇了摇头,“什么都不是!”
“还有谁想要一位母亲和这两个孩子的位置?”预备役上尉向人群高声呐喊。贵族跃跃欲试地凑了上来,但倒在地上的那个蠢货令他们不敢言语。腰缠万贯的商人被贵族落在后面,他们尽力睁大被金币的光芒灼疼的小眼,偷偷将沉甸甸的钱袋塞给那位已成众矢之的的母亲。
苏里加尔少尉突然想起自己的导师的话:一个优秀的刽子手,站在行刑台前,眼睛里就不应该再有活人;在他眼里,只有一块块肌肉、一条条血管、一件件脏器和一根根骨头。
“……第七刀……第八刀……第九刀……第十刀……”
不过……就目前看来,老布塞巴克是难以延续先祖的辉煌战绩了,他已经收到对岸和*图*书发来地最后撤退指令。
遇到现下这样的战事。肖伯河地作用就更加明显了,它是人们眼中的生命线,越过它就是生存;被它阻挡。就是死亡。一路逃难而来地泰坦人见惯了侵略者制造的苦难,肖伯河可能无法阻挡侵略者的步伐。但却可以为那些留恋尘世的人提供一线生机。
“第二十九刀!”在炮火奏鸣的一瞬间,驼背小徒弟尽量挺起胸。
格拉斯劳爵士知道自己会被误会,但他并不在乎。他喜欢画家这个公开身份,也热爱他在秘密领域的工作。作为帝国军事情报军前敌测控中心第一分队的行动长官,格拉斯劳的披风里藏着敌人的兵力展示图、靴子里藏着无数侦察员最终确认的敌情、就连他的画夹……小男孩儿专注地打量画家的作品,他并不知道画页的背面写满针对战况的第一手背景分析报告。
丛林中透出微光,这里连光线都是潮湿的,地衣眼着经年生长的高大灌木爬上树梢,露出惨绿的颜色。前日的大雨令森林中遍布泥潭,一些肉食动物就在泥潭边守侯。再聪明的动物也有失足的时候!这是猎人的谚语,也是狩猎的规范。
狗子们将丛林之王挑衅,并用长长的矛尖不断戳刺艾尔巴的四肢,艾尔巴躲闪得十分艰苦,好几次都险象环生,但它还是不愿放弃,它是丛林的主人,即使是死也不能让入侵者见到它卧倒在地,这是黑豹的名誉和为之奋斗的尊严问题。
年轻的猎人没有回家,他还是无法面对镇里人的目光和好姑娘的坟冢,他打量了一下森林里的尸体,也许……发现这些人的狗子们会找他麻烦,看来……他得避一避。所以他打算先去渡口那边碰碰运气,可能还有去往对岸的渡船也说不定。
歌声悠悠在唱……
布塞巴克渡口就在河流中游与下游地理分界点,两岸的河谷异常壮丽,但繁忙地人群不会在这种时候领略难得的夏日光景。渡口忙碌了几个月,近卫军、躲避战乱的人群、各种撤往后方的物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的话可以排成十几公里长的队列。足够渡口调度员数上一辈子。
西方来的狗子赶走了地方税吏,这确实值得感激,可这些家伙不该把镇子里的保安长吊死在树上!也不该把镇长的小女儿拖到马房!
他是泰坦帝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世袭漕运官,是第十一代布塞巴克渡口总调
丛林之王的生死之敌已经赶来了,杀猪刀利落地劈断敌人的长矛,并在一个起落之间带起一蓬血雨!法兰军人并没被眼前的景象吓坏胆魄,他们群起而攻,但猎人地身手好得出奇,妥斯拉克利用从猛兽身上学来的技巧不断闪躲,他的杀猪刀不是刺中狗子的心窝,就是劈开狗子的头盔。
这位正当壮年的贵族绅士穿着一身笔挺的衣装,靴子和手杖都很干净,他没有家小,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急待救治的伤痕。附近的士兵都有点怀疑,这样一个家伙到底花了多少钱才被送上船?
“臭小子!少来这套!”老巴克摆了摆手,经过一整天的相处,他已对这名年轻军人的伎俩了如指掌,不过老巴克还是说,“这次又是谁?”
在苏里加尔少尉后面,其实是城墙底下,泰坦近卫军第十二军区最后的五千余名士兵排成两列方阵,方阵前随意站着几名将校,里面有一个近卫军上将,还有几名已经看不出级别的校官。军官和战士们完全一个样,五千副铠甲破败不堪,五千具刀枪闪着浑浊的冷光。
那些西方来的狗子赶走了地方税吏!恩……这值得在星期天的祷告会上向地区教士说一说!妥斯拉克只念过乡学,他父亲掏不出中学地学费,结果这家伙也乐得清闲,从十几岁时就开始在森林里讨生活。对这样一位字母也不识几个的猎人来说,是非曲直很简单,谁能带给他快乐。谁就是朋友。
海斯尔大口的喘着气,它知道自己就要离开了,它的视线在唯一的小儿子与猎人之间徘徊着,它似乎是在考虑,先解决哪一个。
渡船摇摇摆摆。河水承载着它,渐渐驶往对岸。船上只有几名水手,余下的都是近卫军地伤员。年轻的母亲觉得该为自己的幸运付出一些。她便自愿充任护士。受了伤的军人很快就给年轻地寡妇起了绰号,他们习惯这样。军人叫她:“肖伯河上的巧克力糖块儿”巧克力糖块儿是那位预备役上尉塞给孩子们的,不过母亲从孩子手里夺了过来,她要用美味的糖果安抚那些快被痛楚折磨疯了的伤员。
妥斯拉克将发酸的面包吐到地上,他不敢面对镇子里的人,也不敢去看“好姑娘”的尸首。据说“好姑娘”被狗子们剥得精光,又拧断了脖子。她的脖子又长又细,但也不是那么容易折断的。年轻的猎人掩住面孔,他连夜就从镇子里跑了出来,有狗子和好姑娘的地方他是再也呆不下去了。
苏里加尔手腕一抖,小刀子翻起好看的光弧,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像弹丸一样嗖地飞了起来,飞到很高的地方,然后像鸟粪一样啪的一声粘在堡垒城墙的砖头上。
“要记得哦!一定要记得哦!”好姑娘边说边抛给猎人一个银泰,她的音容异常生动,像在眼前一样。妥斯拉克记得“好姑娘”的每一个眼神和动和图书作,但他不敢再想。
一支利箭突然出现在包围圈里,狗子们诧异地调转头,他们的男爵扶着脖子喷着血沫,下一刻这名打扮得色彩鲜艳的法兰军官就已摔倒在地。
突来的变故为艾尔巴带来一线生机,可这头畜生没有逃跑,而是利啸着扑向一名入侵者。呆愣着的入侵者被扑倒在地,艾尔巴疯狂地撕扯对方地喉咙,直到人体的碎骨卡住它的牙齿。
“喂!喂!”妥斯拉克抓紧这个小伙子的马缰,“年轻人!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不是跟狗子们决一死战的时候!你们这群军人难道没有父母妻儿吗?你们得为他们想想!难道他们注定要失去你们……”
格拉斯劳爵士抱起了那个小男孩,这个小家伙小到根本无法理解现实发生着的一切。作为一位著名的素描画家,格拉斯劳用极富情感的笔触快速描述了船舱中的一切。地板缝隙里的血浆、被疼痛扭曲面孔的士兵、天真无邪的女孩儿、“巧克力糖块儿”的奇效,画家不断地搜寻动人、热情、精彩、壮烈的画面,直到审美产生视觉疲劳,他才停下画笔,发出满足的叹息。
卡封堡南侧城墙的中心位置在火光和爆鸣声中剧烈颤抖,待硝烟散尽,木杆、死囚、刽子手、小徒弟,事件的主角都不见了,只有混合在一起的、堆积叠压着的血肉。
突然!妥斯拉克骇然回头,他的后颈被温热的血液打湿了,不知为何,一直匍匐在地的艾尔巴攀上了他的后背。猎人的目光越过黑豹,他用猩红的眼光打量着那个偷袭的杂种,小杂种惊慌失措,他的骑士剑卡在黑豹的身体里,不过他逃跑时的速度倒也不慢,但妥斯拉克的硬弓更快,熟铁箭矢带起一道血箭,绝强的劲力令箭矢穿胸而过,远远地落在一株大树上!一时间,沉寂的森林里只能听到箭尾颤动的声音。
不知从第几刀开始,那名荷茵兰军官开始喊叫,这种叫声就像人体被几亿只蚊子同时叮咬。苏里加尔像往常那样,他并没留意俘虏的表情,只是专注地打量刀口下落的方向。这是他最后一次表演刽子手的绝技,他知道,他必须做得尽善尽美。
妥斯拉克猫着腰,他把自己藏在一株大芭蕉后面,宽大蕉叶完全遮挡了猎人的身形,只在阳光触及的某个角落露出一双警惕凶悍的目光。
妥斯拉克看到了豹身上的凶器,那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在匕首手柄上镶嵌着一枚军徽,猎人小心地辨认,不是附近的近卫军,是西边来的狗子!
最后的最后……我们认识了格拉斯劳爵士、布塞巴克渡口的漕运官、简单凶猛的猎人妥斯拉克,以及……数不尽的倒霉嘴脸,这些人都在此时此刻按照命运的脚本进行着精彩的表演。比方说,近卫军预备役上尉潘尼蒂哥隆·阿斯根。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好小伙子,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军人已经为他地命运选择了一个句号。或者说……一个省略号。
妥斯拉克开始追,他在堡垒附近的一处台地上截住了这队年轻的骑士,骑士的队伍确实该停下来了,他们已经与燃烧着的堡垒非常接近,侵略者的欢声笑语就在台地下面。
猎人说完便抿紧嘴巴,他为自己的勇气感到诧异,更怀疑自己对从前的生死之敌抱持的是怎样一种情绪。
潘尼笑了!他看到浑身浴血的彭西勒·多涅尼斯上将不断的大声叫骂,还向每一个经过他身边的敌人吐口水。
垛口墙外就是侵略者的阵营,不需要仔细聆听就能感到密密麻麻的敌人发出的呼吸声,这令红头发的苏里加尔少尉感到有些紧张,甚至还有几分羞涩。不过他是一名久经刑场的侩子手,他知道该如何克制影响工作的不良情绪。比方说……不去看那些军官和士兵的脸色,一门心思地研究眼前的罪犯就行了。
“呵呵!没有那么多!”潘尼笑了起来,他看得出,猎人对算术不太在行。
最后……小女孩儿叫阿亚娜,她会是泰坦帝国音乐史上最著名的女高音,她的歌声会打动万万千千的泰坦战士。
老巴克无奈地叹息一声,“叫孩子们过来!”
、狐狸、山猪,不过也有狗熊和丛林之王黑豹!
白天的时候,大概是中午,通往渡口的国道陆续出现了几支侵略军的骚扰部队,不过这些不速之客都被一只不知从哪来的学生兵赶跑了。
潘尼蒂哥隆并没理会年轻猎人的唠叨,他仔细端详单孔望远镜中的呈像。首先入目的自然是城堡的火光,还有堡垒上面飘扬的军旗,那不是他所熟悉的十二军区的犀角旗,而是荷茵兰王国的白十字花军旗。
这句话令左近的骑士差点背过气!
时间已经是傍晚了,肖伯河仍像往常那样淡定,河水在夕阳下荡漾火色的波纹,静静向下游流转。这条大河寄托了两岸人民所有的希冀,它是许多穷苦百姓的衣食之源,也是传承数代地船工终身工作的地点。
艾尔巴怒吼终于化为哀嚎,一只小狗用铁矛刺中了它的腿窝,矛尖卡在骨头的接缝上。艾尔巴在挣扎脱身地时候被矛尖划开了骨髓。
说实在地!头脑简单的猎人妥斯拉克确实迟疑了好一阵子,他来渡口是要避难。不是去卡封堡送死。那里有十几万个狗杂种,他地杀猪刀要砍上半个月才能解决这十几万人。
hetushu.com•com“可……也是一切!”一位与潘尼同样年轻的小骑士接过话题,他率先放落面甲,然后他的战友便奏响同样的金属声。
又搭建了简陋的渡桥。当骑士牵着马匹度过悬崖地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转过一处山弯,燃成一个大火炉的卡封堡就在不远眼前。
母亲的两个小孩子就被安置在伤员的床板下面,女孩儿年纪大一些,胆子也不小!她伸出小手,接住那些从床板的缝隙中不断低落的鲜血,然后在接满的时候爬了出来,对上面的伤员说,“叔叔!还给你!”
相同的只有军人的面目,他们要观看苏里加尔少尉给敌人执行死刑。苏里加尔少尉是十二军区仅存的一名刽子手,当然,也是最棒的一个,他会给战友带来一次精彩的表演。
妥斯拉克就这样抱着生死之敌……哦不,妥斯拉克就这样抱着他的兄弟,直到它断气。猎人哽咽起来,就像刚刚得知“好姑娘”的死讯,不过两件事的道理是一样的,猎人的头脑很简单,他并不明白那些文人墨客不断渲染的大道理,他只知道,谁与他共同抵御来敌,谁就是他的兄弟。
“你们……你们疯了?那里都是西边来的狗子!他们是你们的……呃……几万倍!”
预备役上尉厌恶地调转望远镜。于是,他便看到成片的尸骸和城墙上竖满的木桩,木桩上捆着一息尚存的近卫军战士,其中最显眼的是一位被剥光了的军人,该死的狗杂种将第十二军区的军旗缝了起来,像女人的裙子那样套在一位近卫军上将的下身。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羞辱一位英雄吗?
苏里加尔在端详战争罪犯。而俘虏也在端详他。刽子手有点惭愧,因为他知道彭西勒·多涅尼斯上将没有权利判罚一名战俘,而且还判了一百刀。
妥斯拉克没再说别的,他目送这些年纪轻轻、连胡子都没长的小骑士行入山林。年轻的猎人并不清楚这算怎么一回事!他并不知道母语中有一个词汇叫做舍生忘死,也不知道军人的疯狂和执着到底为了什么,他只是觉得……若是这样走了,就和当初面对“好姑娘”的呼救无动于衷是一个样!他不忍看到艾尔巴夫妇的死难,难道就能看着几百名学生兵去打一场必死无疑的战争?
苏里加尔停了下来。他打破了十几年如一日的行刑惯例。这名军队刽子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又拿起总司令偷偷塞给他地军用水壶猛灌了一口。他的脸孔突然满布潮|红,看得出……水壶里装的是烈酒。
“我们就在这道别吧!谢谢您的指引!”近卫军上尉向年轻的猎人致以军礼。
“当然!”妥斯拉克懊恼地别开头,他越说越恨,当兵的都是些流氓地痞,他不想帮这些家伙,可就是这样站出来了,这真是见鬼。
在战场上我们是年轻的近卫军年轻的人儿吹响冲锋的号角在鲜花盛开儿女情长的时节我们向侵犯祖国的敌人投去刀枪祖国母亲,听听我们的呐喊近卫军,前进近卫军,前进……
妥斯拉克叹息了一声,他的良知令嘴里那块干面包更加难以下咽,在那位好姑娘被几个醉熏熏的法兰狗子拖出家门的时候他是应该做点什么的!他有两张硬弓、一张短弓。还有三把锋利的杀猪刀!他是远近闻名的猎手,他绝对可以为镇长家的好姑娘做点什么!可是……他那该死的婆娘跪在家门口,他那该死的婆娘还抱着两个孩子,他的怒火无处发泄,只得呆呆地倾听“好姑娘”的哭喊和呼救。
河对岸是这个国家的现实领土,猎人想到这里就啐了一口。他很简单,可也不喜欢这种说法,今天他和艾尔巴兄弟结果了十个入侵家园的狗杂种,什么时候才能把他们都杀光呢?不过……还是先去渡口那边避一避!
苏里加尔少尉手持一把窄刃尖刀,站在卡封堡南侧城墙最中心的位置上。他的旁边,站着一个有些驼背的小徒弟。他面前的那个垛口,竖着一根光滑的松木杆,木杆上捆着那名渗透堡垒未遂的荷茵兰军官。
经历十多年的磨练,苏里加尔少尉亲手做过的活儿几近千件,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健美地男性身体。这名荷茵兰军官光裸着上身。
这位母亲像被烫伤一样丢开钱袋,她的目光落在人群的最后面,那里是穷苦的贫民。侵略者毁掉了他们的家园,夺走了他们的一切,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没有装满金币的钱袋,有的只是满腹的饥饿和满眼的期盼。
城墙一侧,面目麻木地近卫军战士终于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他们将手中地刀枪指向天空。不过侵略者不甘示弱,庞大的集群在山脚下分裂,一座又一座方阵大力踩踏脚下的泰坦国土、缓缓接近已是强弩之末的目标。
小男孩儿叫米德尔斯,他会是那位最受安鲁大帝宠爱的宫廷画师,留存于世的大帝晚年画像有近三分之二都是他的作品。
“我父亲!”妥斯拉克回想起老猎人地教诲。“我父亲的屁股在军队里没少挨教官的大皮靴。”
“难道……军人的使命就对你们那么重要?你们知道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吗?”
潘尼就皱起眉头,“这话谁说的?”
潘尼蒂哥隆的手掌指向繁星炯炯的穹苍,然后他的手臂猛然下落,平胸而举。骑士的阵营终于开始全员运hetushu•com.com动,他们很快便把呆傻的猎人抛在身后。
苏里加尔的小刀开始上下翻飞,他找到从前的感觉了,十天来的战斗令他习惯了大力劈砍,疯狂喊叫,可一旦拿起这把小刀,他就是十二军区的行刑官,是军部最高法庭资格最老的刽子手。
胸肌发达,腹部平坦。苏里加尔喜欢罪犯那头耀眼的金发和被日头晒成古铜色的皮肤,尤其是这个家伙地脸上。始终带着讥讽的微笑,这令见惯哭天抢地等各种丑态地刽子手更加欣喜。
排除干扰渡口运做的一切,老布塞巴克仍算一名合格的漕运官员。
一名不甘忍受战前平寂的骑士突然唱起军歌,这声清唱甚至胜过军号的奏鸣。战马按着歌声的节奏踢踏地面,像舞者一样整齐。歌声由快至慢,由远及近!当冲锋掀起的蹄音惊醒静夜、在整个天地之间轰鸣的时候……
果然!就在妥斯拉克看到地上的那滩血迹之后,一切都清楚了,海斯尔已经无法移动。不过它地利齿还叼着一只死去的幼豹。猎人疑惑起来,残杀幼子?这表明丛林之王已经无法保卫它的领地,这表明它们遭遇了更加凶猛的野兽。
“换换吧!咱们换换吧!”商人露出一副真诚的嘴脸,他们在销售生命。“很少吗?再加一公斤?”
法兰王国军的狩猎小队由一名喜好此道的男爵带领,他们在入林不久便遇上巡视领地的海斯尔。
“你怎么了?”猎人向重伤的黑豹打招呼,海斯尔自然听不懂,它已经歪倒在地,不过它仍在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入侵者。
“真他妈的!这是什么世道?”猎人咬了一口干硬地面包,酸楚的味觉令他蹙紧眉头。
海斯尔的美丽令狗子们直吹口哨。虽然这头母豹不能满足杂种们的性|欲,但它的皮毛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狗子们几乎立刻就发动攻势,结果海斯尔遭遇重创,直到它的丈夫赶来助阵才仓皇退出战场。
整个渡口在老巴克发布撤退令后便陷入彻底的混乱。难民互相推挤,他们要搭最后一艘渡船撤到帝国的实际控制区。燃烧着的篝火将这些落魄无助的嘴脸刻画得异常清晰,他们的愤怒、他们绝望,他们为了渡船上的一个位置大打出手。他们为了走一步上船互相攀比。
这个办法很有效。甜美的味觉激醒战士们的神经,他们便停止嘶喊、停止挣扎,心平气和地品味这难得的陶醉。
现在,艾尔巴的处境也不乐观,狗子们拥有一个十人小队,都配备了军队制式的手弩。艾尔巴的肩骨和臀部分别吃了一箭,它的行动越来越迟缓,它的狂吼在入侵者的眼中只是绝望地示威。
后来,稍晚一些的时候,猎人将丛林之王夫妇合葬在它们的巢穴附近。这样一来,它们的魂魄就可以继续守护这方土地。在拼杀的现场附近,妥斯拉克发现了那只在母亲口下侥幸得存的小黑豹,猎人身上有艾尔巴留下的强烈气息,小黑豹误以为这个高大的猎人就是它的父亲,妥斯拉克也不介意,他在离开的时候就把小家伙带上了。
总之,潘尼蒂哥隆在渡船远离口岸的时候跳到栈桥上,他对人群高喊。“有没有当地人?有没有人知道避开国道通往卡封堡的小径?”
猎人将这队不满七百多人地骑士引入一处山谷,他选择了一条最为隐秘的路径。借着夕阳的微光,骑士们在一条深涧旁砍伐了几株大树。
近卫军上将把毁去一边脸孔的人头抛到侵略者地脚下,“有一个算一个!这就是你们的命运!”他向西方来的狗子愤怒地呼喊。
“我还在等什么?”苏里加尔想。
妥斯拉克就是一名猎人,他的家在布封堡附近。他习惯去几公里外的河谷森林打猎,因为那里人迹罕至,大自然制造了许多物种。有野兔、羚羊
他还记得他曾无数次向“好姑娘”承诺,他会猎得一条黑豹,再让家里的婆娘给“好姑娘”做件围脖。“好姑娘”的脖子又长又细,带上华丽的豹皮围脖再合适不过。
妥斯拉克耸了耸肩,“好男不当兵!”
至于孩子们的母亲,我们知道她只是一位再平凡不过的女性。人们不会记得她的名字,但总会有一位伤残或是受过重伤的老兵告诉你,“肖伯河上的巧克力糖块儿”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母亲的代名词,是祖国和神明的化身!
第二刀从左胸动手,还是那样干净利落,还是那样准确无误。尖刀一下子就削飞了俘虏左边的乳粒。结果荷茵兰军官的胸脯上就出现了两个金币大小的窟窿,流着血,但很少。原因是刽子手在动刀之前猛地向俘虏的胸口拍了一掌,这一掌把俘虏的心脏打得一缩,大大减缓了他的血液流量。这是军部最高法庭无数代刽子手在漫长的执刑过程中积累摸索出来的经验,可谓屡试不爽。
敌人的阵营终于开始移动,其实接近城堡的只是那几门铜炮。苏里加尔的小徒弟惊恐地打量着堡垒外发生着的一切。他报数时的声音瑟瑟发抖,可他就是不敢停下,因为他早已成为导师的一部分,甚至是行刑人的一部分,他的导师若是少了报数就会错过完美的节奏。
“绞刑没有创意、断头台也不新鲜,没有动手凌迟的刽子手不是合格的刽子手。”苏里加尔最后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