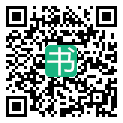第十三章 遗钿不见
第四节
皇帝脸上浮起了严霜,她又是这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即便那样亲密过了,她说放手就能放手。与其这样,他宁肯她刺猬一样的乍起满身的刺来,起码让他感觉自己曾经拥有过她,不要像现在淡得像烟似的,喘气大些就吹散了。
她缩成了一团,想到他说的孩子就觉得摧肝裂胆。不会这么巧的,好多妃嫔轮着翻牌子,也不是每一位都能怀上,自己只一次,绝不能够的!
他伸手去触那绳结,手指滑过她的手背,她猝然一惊。皇帝感到灭顶的绝望,喉咙哽得生疼,只硬忍住了不叫眼泪流下来。
浑身上下火烧似的疼,谁来救救她?她在这世上还剩下些什么?没有父母、没有家、如今连仅剩的一点骄傲也没有了!她原先那样爱他啊,甚至在那些妃嫔对她恶语相向的时候,她还能提起勇气来反唇相讥,依仗的不过是他的爱和敬重。
“爷,我的好爷,奴才求求您了,再这么下去非作下病不可!回车里去吧,后头的事儿咱们回头再计较,成不成?祖宗,您要急死奴才了!”冯禄在他头顶上支撑起大氅,雨那么大,淋得人睁不开眼睛。太子在雨里跪了半个时辰,怎么劝都不肯起身,如同失了提线的木偶,直把他急断了肠子。
他拧眉打量她,“锦书,朕对你,心如明月。才刚在泰陵……”
她醒了,双眼空洞地看着他。皇帝心虚而窘迫,不敢搂紧她,又舍不得撒手,只得别过脸去把视线调向别处。
她又哽咽着哭,心里说不出的失望无助。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口口声声的爱,最后不顾一切地把她毁了。要是她对他只有恨,她还能找到活下去的动力。可她的感情偏偏那么复杂,超出了她这个年纪所能承受的范围,她觉得自己要垮了,再也活不成了。
神道上停着的翠盖珠缨八宝车放下了呢帐帘,皇帝翻身上马,吓坏了阿克敦,他打千儿道:“奴才启奏万岁,天儿太坏了
https://m.hetushu•com•com,请主子保重圣躬,还是和锦姑娘一道坐车吧!奴才们在外伺候,也好放开了手脚往京畿赶。”
冯禄抱住他的腿就地跪下来,哭道:“主子,主子,小不忍则乱大谋!奴才知道您有多委屈,您心里过不去就打奴才两下出出气儿,奴才这都是为了您啊!万岁爷是怎么样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立起两个眼睛来就不认人的主儿!您杠着硬上能得着什么好?倒叫后头父子不好处,叫万岁爷更加的打压您,处处防着您,您还有出头的日子吗?”
锦书早就已经血肉模糊,他还往她伤口上洒盐,她失控了,捂着耳朵尖叫起来,“你胡说!你胡说!什么烙印……我和你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是仇人!是杀父仇人!”
他攥住了她的手就没办法松开了,外头电闪雷鸣,他觉得他头顶上的天也要塌下来了。他惶恐不安,他没了主张,他用全部生命把那双柔荑包裹起来,低头贴在唇上央求,“你要朕怎么样都行,你说句话吧,不要折磨自己!朕把后半辈子都交给你,朕带你住到畅春园去,就咱们俩,咱们朝夕相对,再也没有别的女人来打搅我们,好不好?”他的眼泪滴落在她的指尖,他抽泣,“……只要你陪着朕,不要离开朕。”
皇帝横了阿克敦一眼,“多嘴多舌!朕怎么,多早晚轮着你来置喙了?”
眼下说什么都不济了,冯禄磕头道:“爷,咱们从长计议,趁着绿营军都撤了,这会子就下山去吧!别等到万岁爷出来,万一遇上了,到时候又费功夫。”
皇帝从没有那样害怕过,她蜷在那里呼吸微弱,简直是一副油尽灯枯的模样。什么也顾不上了,慌忙靠过去替她搭脉,脉象又虚又浮,三焦六脉都已伤透了,干吊着一口气似的。
还是想走?他深深的无力,闭上眼睛咬牙道:“休想,除非朕死!”顿了顿睁开眼直视她,嘴和_图_书角浮起冷酷的笑,“你筹划已久了吧?难为你费了那么多的心思!朕一直以为你是受了皇后挑唆,临时起意,谁知你原来早有预谋。亵衣里的东西什么时候缝进去的?朕是个傻子,你只要冲朕笑一笑,朕就欢喜上三天。朕以为终于把你捂热了,谁知都是朕的妄想,你的心比石头还硬,你对朕没有半分的眷恋,说走就走了……”
积蓄了她所有力量的一掌,他头晕目眩,几乎懵了。
天又下起了雨,雷声隆隆,破空的闪在泰陵宝顶上方盘桓,瞬间照亮了半边天,照在檐角高昂的琉璃雕龙首上,眦目欲裂。
皇帝竟有些心虚,他也自责,怎么在泰陵里做出这种事来!时候不对,地点也不对,她该有多恨他,他不敢去想象。
原以为她还会哭闹,谁知她反倒沉寂下来,轻轻拿手推他,“奴才不敢,请万岁爷放开奴才。”
永昼往后退,眉目疏朗,淡淡笑道:“瞧瞧,还是原来的样儿!急不得啊,谋大事者要忍辱负重。你好好的,报仇不是女人的事,要活下去,等着我来接你。我要夺回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再还你个锦绣河山。”
太子泄了气,背靠着红墙喃喃,“是我不中用,保护不了她……”说着又像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捂着脸说,“我算个什么男人!原就不该让她留在御前,会有今天这局面是预料中的,是我坐看着一切发生,错都在我!”
太子摇摇晃晃站起来,红着眼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都怪你!要不是你这狗奴才作梗,我这会子早去救她了,也不至于让皇父对她做下这种造孽的事来!”
他慢慢坐正了,只觉脸上火辣辣的疼,却心平气和,“朕的确是做错了,可是朕不后悔。你打朕,朕可以不追究,全当朕欠你的。”
阿克敦颇有些忠心,他是宫旗下包衣出身,原来就是南苑家臣,比起皇帝御极后提携的那些汉臣体人意儿得多。他本着忠仆和图书的办事原则跪下磕头,“主子,姑娘一个人在车里,手脚缚住了不假,可难保没有别的差池。主子您瞧……”
锦书微喘着问:“你是谁?是永昼吗?”
神台上的巨烛已然燃尽,火苗子璨然一跳,一缕淡淡的轻烟在空气里弥散。满世界只剩下黑,像一口井,像人心。
一圈圈松开如意带,一点点解放她,她的手挣脱出来,他还没来得及查看她的伤势,“啪”的一声脆响,他右边的脸颊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
她没了意识,落进一片迷雾之中,他在她耳畔说话,好像隔了十万八千里。她放眼看,一片沉沉阴霾,没有边际,望不到头。盲目地往前走,突然一凛,发现自己脚下便是万丈深渊。
现在呢?在他眼里她成了三千粉黛之中的一个,和那些宫妃小主们没有区别。他对她还有爱吗,或许有吧!可是敬重呢?永远失去了。她就像绫子扔进了刷锅水里,管他原来是什么颜色,如今就是一块破抹布。
她霎时被巨大的喜悦笼罩,伸手要去触碰他,“永昼,好弟弟,我天天儿地想你。”
皇帝蹙眉看着她,有满腹心事无从谈起。得到了,为什么心却隔得越来越远?他坐过去,绳子绑得太紧,她的手腕子已经乌沉沉发紫,触目惊心。他心头一抽,低声道:“你听话些,不要闹,朕给你松绑,好不好?”
他的眼睛失去了光芒,铁青着脸道:“没有关系?或许你肚子里已经怀上朕的孩子了!没有关系吗?不要紧,朕回京便册封你,要逃?想都别想!朕是你丈夫,不管你认不认,改变不了了!”
他摇头,“朕不能像从前那样了,你能忘记,朕却做不到……朕一刻都离不开你,回了宫,晋位份是一定的。东围房往后就派给你,你是晋贵妃还是皇贵妃,由得你选。”
他点头,“是永昼,是老十六,我还活着。”
冯禄不禁叹息造化弄人,就差了那么一步!太子爷和锦书失之交和-图-书臂,事到如今,恐怕今生再也无缘了。
“主子爷,撒手吧!”冯禄带着哭腔的劝谏,“天涯何处无芳草,万岁爷已经……您再难过又怎么样呢!”
其实他们来得比万岁爷早,却发现山下遍布绿营军,好容易找着个豁口上山,正准备进泰陵寻人,御驾带着骁骑营禁卫军也到了。太子困兽一样地转圈子,离隆恩殿只一墙之隔,听得见锦书的哭喊,竟没法子进去救她。心爱的女人遭受凌|辱,自己偏偏无能为力,这对尊贵非凡的储君来说是怎样的屈辱!
她在宝座上福了福,“请主子别说了,奴才都忘了,主子也忘了吧,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主子要是不惩处奴才,奴才回养心殿,还像从前一样伺候您。倘或主子不想见奴才,就打发奴才回慈宁宫去吧!”
他扬起脸,似乎这样能叫眼泪流进心里去。他努力的平复心绪后方道:“朕劝你断了念想,你侍了寝,今生今世烙上了宇文家的烙印,就是走到天边又能改变什么?”
太子跪倒在雨里,浑身乏力,没法子站起来了。十指狠命的插|进泥泞的土里,春草尖利的锯齿割伤他的掌心,他浑然不觉得疼,只感到彻骨的冷。他颤得不能自已,脸上湿濡,分不清到底是雨还是泪。
大雨把他浇了个透,心思愈发清明起来。木已成舟,他恨不能立刻举兵,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不能操之过急。他缓缓直起身,怅然复看宝城一眼,带着满腔怨恨,由冯禄搀扶着从陵墓另一侧朝开阔地去,渐行渐远,成了莽莽一点,消逝不见了。
雾霭后面有悠长的叹息,她驻足回望,一个身影慢慢走出来,陌生的脸,感觉却又那样熟悉。他说:“皇姐,你要挺住。等我这里一切铺排好了就去找你,你要等着我,总有骨肉团聚的一天。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我们都一样……”他侧了一下头,无奈地笑,“我知道你在紫禁城里,可是我没有能力,我暂且救不了你。不过也快https://m.hetushu.com.com了,你再等我几日,少则三月,多则半年,我一定杀了宇文澜舟为家人报仇!到时候我带你走,到我生活的地方来。这里有牛羊草原,有绿树红花,我们姐弟再不分开。”
马车宽敞,宝座一角设了张花梨矮几,皇帝把她抱在怀里让她取暖,一面伸手去够几上的茶壶,斟了半杯热茶来喂她,看见她脸色稍好了些才松了口气。
欠她的,他穷其一生都还不清。她再没那些心力去计较那些了,“既这么,劳烦你放了我。我没脸见人了,往后就叫我半人半鬼的活着,与你再无干系。”
阿克敦一凛,皇帝说什么自然不敢违逆,他也是好心,这两位闹别扭是明摆着的,锦姑娘是绑着手脚扔进车里的,可……可万岁爷才震完卦,淋着了雨对龙体有碍。都是男人,他很知道其中厉害。
皇帝失望至极,这女人的心怎么这样狠?竟然比男人还要决绝!
皇帝讪讪下了马,站在车外犹豫了一阵,方示意侍卫打起了毡子。
她不答,一味看着他,眼神复杂莫名。
锦书缩在马车的一角,神色萎靡,发髻散乱,那模样极狼狈可怜。看见他进来恐惧地瞪大眼睛,嘴唇翕动几下,却发不出声音来。
“宇文澜舟,我恨你!到死都恨你!”她哑着嗓子嘶吼,“不要再碰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
她吃吃笑起来,“丈夫?你也配当这个字眼!”她像是听见了笑话,越笑越令人心惊,直笑得泪流满面,瘫软在彩金绣云龙坐褥上。
他挥了挥手,渐渐远去。锦书怔在那里,醍醐灌顶般的清醒起来。是啊,还有牵挂,还有永昼!姐弟尚未相聚,这会子撂开手,永昼回来了寻她不着怎么办?他们只有彼此,再没有别的亲人了,她要是死了,单剩永昼有多可怜!她还记得金亭子旁,为了一把弹弓哭得眼泪鼻涕混在一处的孩子,小小的,无依无靠的样儿。她不能再叫他伤心了,她要活下去,不为自己,不为旁的,只为了幼小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