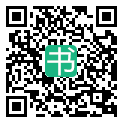第三十七章 思我
他的话里永远有种暧昧的味道,以前会让她脸红心跳,现在却只剩厌恶。她力气上敌不过他,也不想和他争辩,不过别开脸去不再看他。他是最警敏的人,应该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轻宵在偏殿的木架子上排日子,颠来倒去数了好几遍,喃喃道:“今天是丙午日,殿下信期迟了八天。”
“也不知怎么那么巧,偏偏箭匣子掉下来,压在了肋骨上头。医正说大约断骨戳伤了五脏,听这说法很凶险,能不能捡回一条命要看造化。”
令仪应个是,太后这才让人扶上步辇回昭阳殿去了。
她下了榻立在地心里,昏黄的烛火跳动,整个大殿都跟着颤抖起来。她眯起眼,脸上带着嘲讽的笑意,“你要孩子来同我说什么?采选的日子快到了,到时候有一车的女郎上赶着给你生孩子。”
弥生涨红了脸,“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侍寝?我是先皇的皇后。”
她惊恐地望着庞嚣,“大兄,陛下怎么了?”
令仪噤在那里,半晌才道:“阿嫂别说丧气话,九兄在我眼里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世上没有什么能难倒他,这次也一样。”
晴空里轰然响了声焦雷,弥生只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住了。惊到了极处,人抖成了风里的枯叶。不好了?健健朗朗的人,怎么就不好了?她转身就往外走,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的台阶,几次踉跄险些栽倒。眼前的景都看不清了,脑子里充塞满孔怀的话,只怕不大好……只怕不大好……
弥生歪在榻上叫宫婢剪指甲,听见她们唧唧哝哝地说话,转过头看了一眼,“聊什么呢?”
他真的很不要脸,因为屋里供暖,他脱起自己的衣服来毫不手软。那玄色的皇帝衮服被随意扔在了地上,他伸手抓她,她放声尖叫。他在她耳边吹了口气,“我喜欢听你叫,叫得越响越好。明天一早我就颁旨册封你,做了我的皇后,看你还能往哪里逃!”
“那你和九兄还这么闹下去吗?”令仪说,“我看他一直心不在焉,你不给他好脸子,他连这样的大日子也高兴不起来。”
他咳嗽起来,大概伤了肺,肺上像破了个大洞一样,飕飕地往里灌冷风。他吸口气,咳得更加剧烈。嘴里渐渐有腥甜的味道,然后大口的血涌出来,他自己也感到恐惧,他的命大概就交待在这里了。
“我潜出去,没人会发现的。”她卷起画帛挨到屏风边上,一闪身便遁走了。
她的那些小动作落在大家眼里,彼此都相视而笑。到底太年轻,十五六岁的年纪,能够承载多少仇恨呢?华山王再好,当时难过,时候久了渐渐也就淡忘了。看她眼下态度有了松动,总算是雨过天晴了吧!
她侧过身,眼泪从眼角流下来。也许是该好好想想,她只顾着自己,忘了他曾经受过的委屈。他一路走来,其实也甚可怜。
弥生心里突然升起不祥的预感,手里的玉水呈落在地上,霎时摔得四分五裂。元香忙上来扶,她一把推开了,对孔怀道:“你起来回话,到底怎么样,别光说半句!”
元香关心的不是这个,连麝香都禁用了,看来是要弥生作养身子好怀龙种。这是好事,皇后年轻,很多事考虑欠周全,有时候死脑筋不懂得变通。等为了人母,自然而然地就会以相夫教子为重了。
庞嚣垂着眼,脸色铁青,“陛下坠马,叫太医摸了骨,说断了肋,情况很不好。”
他痛得神识涣散,感觉自己像风筝,悬了空,飘飘然就要脱离躯壳飞出去。所幸有根线牵引着,是什么他分不清,隐约听见她喃喃说孩子。他倒是振奋了一下,当真有了孩子,他盼了好久的孩子。他动动手指都要耗尽全身的力气,但是要给她希望,舍不得她这样哭。
“谁耐烦在那里!早些回去省心。”她皱了皱眉,“我晚课还没做,心里惦记着,不念完一卷经睡不着。台子上太热闹了,吵吵嚷嚷的不知道在演些什么,我光听那胡乐就头疼得厉害,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她担心元香要念叨她不该这么早离席之类的话,也不看她,自顾自绕过她先走了。
看来昨晚没有太大进展,圣人文治武功,却并未换得美人芳心。元香把烛台放到桌上,斟酌了下扯谎:“早就没了,那药丸子不易保存,一个夏天过去全化了。上回收拾屋子,看见就给扔了。”她无奈叹息,“殿下……女郎,你多体谅体谅圣人吧,他不是别人,是你的夫主啊!你长在他手上,他教养你,爱你,你不能光想着他对不起和图书你的地方,要念着他对你的好。人谁无过?就说你自己,你能保证你一点错处都没有吗?你这么拧,我们下面伺候的人心里也不好过。”
元香听了凑过来看,一块块牌子数过来,讶然望着轻宵,“平常日子都很准,这回怎么晚了这些天?莫非是有了喜信儿?可是医官每天按时来请脉,并没有发现什么。”
弥生在太后面前没流一滴眼泪,等她一走就再也忍不住了,掖着帕子啼哭不止。令仪含泪来劝勉她:“阿嫂也仔细身子,肚子里有了孩子更不能哭。九兄以前行过军打过仗,身体底子好,这回也一定能扛过去的。”
他没有睁眼,却有泪水从眼角滑下来。她惊呆了,他听得见,但是说不出话来。她抑制不住地呜咽,“陛下,陛下你会好起来的。”她把额头抵在他手背上,那手冰凉,没有温度。她越发难以自持,“你是生我的气才不理我的吗?我错了,是我太固执,惹得你伤心。你不要丢下我,求求你,夫子……”
金虎台的大宴她去了,因为不好推托,也不想让人看笑话。他还没有正式册封她,不管别人怎么看,对于她来说可贺敦的封号是先帝给的。既然顶着这个帽子,她就该按照先皇后的份例来。
弥生捂住嘴才不至于痛哭出来,抽泣着,“怎么会呢……我不相信……”
“邺宫中的女人,我点了谁就是谁。你是先皇的皇后又怎么样?朕要你侍寝,你就得给朕侍寝。要你生儿子,你就得给朕生儿子。”他才说完,发现她居然想逃。他真的克制不住自己,积攒了那么久,总有爆发的一天。他奋力地把她扽回来,她还反抗,他气冲了脑子,反手便甩了她一耳光。
他一定疼得厉害,额头上冷汗淋漓。弥生一遍遍地替他擦,拿银勺一点点给他喂水。她没法替他分担痛苦,只好亲吻他的嘴唇,在他耳边说话。她喃喃同他说起第一次看见他是什么感觉,后来在太学被他责罚有多讨厌他。他在漫天飞雪里拥抱她,她暗中有多高兴。他为她拈酸吃醋时,她背着他的那些小小的得意……
孔怀手指扒着砖缝,颤声应个是,“陛下人歇在朝隮殿,回京将将要进城的路上叫兔惊了马,陛下伤了肋,这会儿……请皇后殿下随奴婢往朝隮殿去,殿下看看就知道了。”
“殿下不是说过宫里的太医只会治痢疾的嘛!”元香接过宫人手里的剪子,每个指甲上摩挲了一遍,边道:“轻宵说眼下太小,等满一个月就能号出来了。回头圣人回宫,殿下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吧,圣人不知怎么高兴呢!”
他没有一点反应,呼吸时断时续,甚至有些接不上似的。她心里又痛又怕,不敢碰他的身子,只有小心攥紧了他的手,压在她胸口上。前阵子和他反目,阿娘和佛生都劝她收敛性子,说老了要后悔的。果然是这样,她现在后悔至极,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同他怄气。可惜还没到老,现在已经悔青了肠子。
西边槛窗上挂着他以前做的风铃,长短不一的小竹筒上了桐油,在风口里互相碰撞,笃笃的声浪悠扬起伏。她调整姿势躺平了感受一下,并没有品出什么滋味来。交叠起两手盖在小腹上,弥生心里有小小的喜悦。
只是他没有再来看过她,他是勤政的好皇帝,他有太多新的法令要实行,他很忙……弥生不敢确定,也许他对她也有不满,因此有意冷淡她。
他永远都很自律,不管多累,到了该视朝的时候自然就醒了。他动了动,把手盖在额头上。弥生怕被他看出端倪来,忙翻身背对着他假寐。他撑起肘看她,在她裸|露的肩头印上一吻,下巴上有新生的胡髭,扎得人有些疼。
他似乎难以置信,“我选采女充六宫,你一点也不在乎吗?我和别人生孩子,你也不在乎吗?”
弥生踅身进了后殿,把跟前宫人都打发到幔子外面去,就自己守着他。面对面,觉得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她。
气氛果然大不同,还没进朝隮殿,远远就看见宫门前医正来往,个个表情肃穆,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弥生心都揪起来,提着裙裾迈进门槛,迎面看见庞嚣和几个近臣上来打躬作揖。
她迈不过自己那一关,她踅过身,长出了一口气,“陛下有了江山,势必不缺美人。他日开枝散叶,也在情理之中。”她回过头凄然看他一眼,“我已经不敢奢求从头再来了,要我若无其事地继续和你谈情说爱,对不起,我怕我做不到。”
弥生转和*图*书过脸看天街上的夜景,暮霭沉沉,把她的心也罩住了,“横竖我就看着他,他要是死了,我绝不苟活。”
她愣愣地看着她们,“有了孩子?医正怎么没说?”
弥生听她的话,想起以前太学里的时光。他端着架子高高坐在布道台上给三千太学生授课,那时她是芸芸学子中的一个,抬头仰望他。他就像九重天上的佛,光芒万丈,让她自惭形秽。后来……后来不知怎么到了这一步,弄得生死仇人一般。
弥生回过身来,启了启唇,却发现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勉强才挤出一点声音,也是暗挫挫的,“那个避子的药呢?”
眉寿和元香面面相觑,往宫门上看一眼,守门的内侍呆若木鸡。想来是没有凑手关宫门,闯大祸了。其实这也不怪内侍,谁能想到圣人会在大宴中途追出来呢?宫人们起了身,元香挥挥手叫她们回配殿里听旨。她和眉寿两个退出来,一左一右合上了正殿的大门。
蜡烛烧完了,到了五更,窗口隐约透出一丝微光。她在朦胧里看他,他依旧是她记忆里的模样,宽肩窄腰,朗朗的伟男子。彼时她天真无知,曾经那么敬重他。可惜了,可惜了她少女的梦。
她一再地吻他,“阿奴,你永远不知道我有多爱你。你一直以为自己低声下气,其实我才是最卑微的。因为我爱你,远比你爱我来得多。”
慕容琤也后悔,后悔之余看到她鄙夷的目光,心里越发躁起来。
弥生不甘心,急欲起身,他下狠劲往下按住了,切齿道:“你再犯倔!再犯倔我就把你绑起来!”
大道理谁都会讲,弥生这些天吃斋念佛下来,心气倒是平和了不少,谈起这个来也不会冲撞人了。她只道:“给我点时间,也许自己就想通了。”
她站在地心有一阵恍惚,突然回过神来,疾步绕过屏风。后面是他的龙床,高大,宽阔,四面不着边。他就躺在那里,面色惨白,无声无息。
案头的佛像前红烛泄了大半边,蜡油淌下来,积满了烛台下的碟子。偏殿也分里外间,地罩隔出个后身屋。顶上镂空雕花横木上挂着厚重的幔子,后面是弥生日常歇午觉的地方。他闯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地把她从蒲团上拎起来,一下子就扔到了胡榻上。
弥生怕太后过于伤情,忙道:“陛下吉人自有天相,母亲不必担心。这里有我看着,您还是回宫歇息。陛下一有起色,我即刻派人过去回禀母亲。”说完给令仪使个眼色,两人上去一左一右扶住了太后往前殿引。令仪也道:“母亲千万保重身子,别叫陛下病中还惦记着您。”
正阳宫里的每个人都在盼着圣人回銮,回来了有情人就能终成眷属了。可是等啊等啊,等来个不太好的消息。
弥生回到殿里往莲花台上一坐,不到一刻就老僧入定。
他放松了钳制,平心静气道:“我要个孩子继承大统,生完孩子你想成仙或是成佛,我双手供你去。”
令仪见她悄悄离席哎了声,“这就走吗?人都在呢!”
元香喜出望外,双手合十朝窗外拜了拜,“阿弥陀佛,这是佛祖保佑!”
弥生在他手上抚了又抚,“阿奴,你快好起来。等你痊愈了咱们到城外槐花林去,五月里正赶得上槐花开,你答应过我去看花海的。还有孩子,你说你占过卦,说咱们有两男两女的,你不能骗我。这回再骗我,我恨你一辈子。”
他听见她的尖叫,大批的太医进来查看,帮他翻身侧躺,怕血呛进气管里去。弥生在边上声嘶力竭地喊:“治不好圣人我杀你们的头。”她一直温雅恬静,只有真吓着了才会暴跳如雷,上回珩过世时就是这个样子。
元香清了清嗓子说:“应该不会吧!”她脸上发窘,拉着眉寿快步朝值房里去了。
她被他摁在月牙桌上,背后的皮肉贴着红木桌面,冷彻心扉。
黄幔子后面响起弥生的尖叫:“你怎么进来了!”
弥生愕然看着那把剑,“陛下这是存心要我难堪吗?我哪里有本事杀你!若是为这么点小事就要死要活的,当初陛下又何苦费尽心机谋取这天下?”
庞嚣晦涩地看她一眼,“殿下一定要冷静,眼下不是哀恸的时候,还有很多事要殿下拿主意。圣人的伤势不能传出去,对朝中外臣只说是碰了筋骨,要息朝将养几日。请太后来主事,政务切不可堆积,以免动摇了人心,引出不必要的麻烦来。再者本月正是外邦进贡朝贺的当口,四夷馆里还歇着高丽、契丹、靺鞨的使臣。这些人www.hetushu.com.com更要稳住,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令仪道:“说是兔惊了马,这马还是大宛名驹,绿豆大的胆子,当真可恨。”
患得患失,这是陷在爱情里的典型症候。弥生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他上赶着求她,自己不愿意理睬他。他若是没了消息,她又有点食不知味。
宫宴办得很隆重,台上张灯结彩,纵行排列的六只青铜大鼎里烈火熊熊,蒸腾出疯狂却又空虚的快乐。弥生坐在命妇中间,勉强打起精神和众人说笑。她左手边正坐着令仪,令仪觑她脸色,小声道:“自从我搬到西宫去后走动得少了,长远没见阿嫂,阿嫂近来好吗?”
弥生在兔笼前喂食水,闻言回过身来,“圣驾回宫了吗?”
元香听了,忙带着眉寿轻宵俯首领命。他振了振广袖出门去,脸上虽有倦容,并不妨碍他为君者的气度。三人在门前跪送,待他登上龙辇走远了才直起身来。
百年七七过后不久,他封她为后,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亲自宣读的圣旨。庙堂上反对的声音不少,都拿她侍奉过先帝做借口。但他做了皇帝,有不容置疑的威严。她受了金册金印,时隔半年终于又搬回了正阳宫。
她也承认自己脾气很固执,就是俗话说的认死理。自己想不通,别人怎么劝都没有用。百年过世差不多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想了太多,刚开始真是恨得牙根痒痒,到后来一些强烈的情绪冷却下来,有时虽然还会难过,但是不会再有那种锥心的感觉了。长信殿的封锁解除后,外头有消息传进来。原来百年的尸首当天就打捞出水了,送进皇陵里安葬,就葬在他父亲的地宫后面。弥生稍感安慰,总算留了全尸。这辈子吃了那么多苦,下辈子托生到个好人家,别再和权力有牵扯,做个普通的百姓吧。种种地,经经商,远离这些肮脏的政治交易。
一队人穿过花园往长信殿去,宫婢们挑着灯笼开道,特地绕过了凉风堂从北边走。弥生脑袋里空空的,没什么想头。念经礼佛真是好出路,木鱼笃笃地敲,敲着敲着就忘记烦恼了。
令仪啊了声,“这么严重……”
孔怀擦着眼泪说是,“陛下天天挂念着皇后殿下,如今殿下又有了小殿下,圣人可不是高兴坏了嘛!”
这巴掌打下去,两个人都傻了眼。弥生没想到他会动手,捂着脸奇异地望着他。
弥生笑了笑,“劳你记挂着,很好。”
“你如今放不下的不也正是这个嘛!若换个立场来想,圣人之所以这么决断,都是在为子孙们扫清障碍。”令仪转过脸看御座上落落寡欢的人,叹了口气道:“大邺开国才十八年,一个年轻的国家,面上光鲜繁荣,底下看不见的地方却满是荆棘和暗礁。守业太难了,尤其是二代君王,能在这个位置上坐下去,就得有长治久安的力量和决心。说真的,这么多阿兄里,我觉得九兄是最适合做皇帝的。他冷静、清醒、有铁腕,大邺到他手里才能传承下去。如果没有他,阿嫂设想在位的是百年,等他长大有能力把握朝政,也许可以很好地治理天下,但是这空白的六年甚至是十年,大邺的百姓怎么办?谁都等不起,即便九兄没有动作,别的王侯也会跃跃欲试,那样可就要大乱了。”
话虽这么说,令仪看来满不是这么回事。她和上次先帝大敛时比起来又有不同,两只眼睛像是不那么灵活了,有时候有点呆愣愣的。令仪心里着急,侧过身轻声道:“我知道百年的事对你打击很大,毕竟是自己看顾过的孩子,和别人不一样。太后也为这事和圣人大闹了一场,前些天病了,没叫告诉你,不让你去,省得大家见了面又要哭。其实这件事,依着我们女人来看,圣人办得是欠妥了。”她说着,一手牢牢抓着她的腕子,“阿嫂,我是在这邺宫里长大的,什么样的事都见过。尤其是上代里,几位从父和神宗皇帝之间的明争暗斗,那才是真正的腥风血雨。所以阿嫂看开些,哪朝哪代都有这样的事。做了皇帝的人,谁不想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本来就是条血路,就要用千千万万人的性命铺就。百年错在太不安分,他的那点小动作怎么瞒得过圣人的法眼?这回我倒觉得圣人没有做错。”
弥生奇怪地看着她,眼睛里渐渐暗淡下来,“你会这么说,是因为你没有见到百年惨死的模样。”
眉寿道:“可不是嘛!冷落了半个多月,别说是一国之君,就是寻常人家的郎君,还憋
hetushu•com.com不住往府里领人呢!再瞧瞧圣人,后宫就她一个,是要一心一意和她做正头夫妻的。这么慢待着,男人心里也有苦处。”殿里又是一声惊呼,把人吓了一大跳,“不会出事吧?”台下女官们一直在候着,见她下来元香忙上前迎接,“这么快就散宴了?”
他的症状缓和了些,弥生追问情况,医官们模棱两可,“臣下必定全力救治,只是究竟能不能脱险,还要看圣人自己的意志。”
她竟然嫌他粗手大脚?她把他干晾在那里半个月,现在嫌他不温柔?他气出了心头血,语气反倒难断起来,“要不是趁着今日大典,我还瞧不见你。来了怎么就走了?走也不同我打招呼,你藐视朕躬,该当何罪?”
弥生惊讶地发现他勾住了她的小指,她喜出望外,“元香,孔怀,你们快看,圣人听见我的话了!”
他撑着月牙桌苦笑,“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我杀了百年,你要用一辈子的冷漠来惩罚我?”他从玉带钩上解下佩剑扔在桌面上,“上回你来讨要虎符,我答应再让你难过就听凭你发落的。如今我又伤你一回,你动手吧。”
弥生被他剥得胸怀大开,也来不及顾脸了,抱着胸一下子缩到了墙角,“你敢乱来?”
慕容琤只觉满腔的相思苦都付诸东流了,她这么个态度,叫他痛心之余更加失望。她还是不能理解,百年刚死的头几天,他知道她心里难过,并不认真逼她。可她倒好,念起了佛,越发不待见他。他这样诚心对她,她恨他入骨?原来在她眼里自己比不上珩,比不上百年,甚至比不上任何人。
她瞧不起他吗?再清高又怎么样?她是他的女人,这辈子都改变不了。现在还能和他撇清,等有了孩子,看她怎么顽抗!他多可悲,这世上一向都是女人为巩固地位用孩子留住男人的心,为什么到他这里就变了?他们的角色掉换,他变成了怨妇,亏他还是个皇帝!
她勉强吊了下嘴角,“借你吉言,但愿如此吧。”
她只顾摇头,“你不知道,先头吐了那么多血,我看着心都要碎了。”
御前的孔怀抱着拂尘进正阳门,气喘吁吁爬上台基入正殿拜见皇后,跪在墁砖上磕头,“奴婢给皇后殿下问安。”
“圣人真好!”眉寿突然说,“他从来不叫人失望。”
她不说话,因为没法子表达心里的想法。他来缠她她感到厌烦,他若是真的宠幸别人……单是想想就足以让人生不如死。这样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以前以为他登基之后便不会再有阻碍了,可是他杀了百年。
“孩子小,才着了床的把脉把不出来,好歹要一个月才能有端倪。”轻宵算了算,“自打上回陛下临幸,到现在得有二十天了,我看这回八成是有了。”
他下了胡榻,窸窸窣窣穿起衣裳到外间。御前的宦者早已经恭候了,开始有条不紊地服侍他洗漱更衣。他垂下眼正了正腰上绶带,叫人传长信殿的女官进来吩咐:“从今天起殿里不许再用麝香,命医官每日来请脉。只要她无虞,你们的性命还能保住。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你们也不用活着了。”
弥生听庞嚣一样一样地请示,知道这回的确是出了大事,顿时方寸大乱。那些朝政她有心无力,勉强定了心神,一头指派人去请太后,一头对众人道:“陛下铸鼎象物,定能逢凶化吉的。请诸位代为督察朝臣,若有异动者即刻来回。我……心里乱得很,外面的事便仰仗大兄和诸位阁老了。”
一旁的元香忙道:“殿下怎么不把好消息告诉圣人?圣人知道殿下有了喜,便会有力气渡过难关的。”
眉寿添完灯油退出来,元香正在前面开槛窗,嘟囔着抱怨:“檀香味这么重,也不知道换换气,回头又该睡不好了……”她突然顿住了,慌慌张张回过身冲眉寿比画。眉寿还没闹明白就看见她跑到门前跪了下来。她一惊,忙跟着稽首,只见一片掐金满绣的袍角从眼前一闪而过,很快便进了偏殿里。
站在台基上往外看,清辉满地,森冷的一片月色。
偏殿里静悄悄的,她打起幔子往里看,没承想皇后已经醒了,正在屋里翻箱倒柜。天刚蒙蒙亮,看不太清。她点了宫灯进去,“殿下找什么?”
正说着,外头太后和令仪呜咽着进来,太后哽声道:“这是造了什么孽?到底是哪里邪行,打去年起一个接一个地出事。现在只剩这么一根独苗了,还要算计我!”
她字字尖刀插在他心口上,这比杀他好多少?他怒www•hetushu•com.com极反笑,“也罢,横竖恨我了,多恨一些又何妨?脱衣服,朕要你侍寝。”
元香和轻宵笑道:“说怎么给殿下道喜。殿下信期晚了好几日,想是送子观音来瞧过,种了个小娃娃在殿下肚子里了。”
“我不该打你,回头再给你个交代。”他说,两手抓住她的衣襟用力一扯,“在这之前先办了正经事要紧。”
他轻蔑一笑,“我不敢?这世上还有我不敢的事?总之今日你别想逃脱,我忍了这么久,够给你面子的了。”
轻宵是他一早派来的人,本就是为了行监督之职。眉寿吊起一边嘴角对她干笑,“看来要仰仗你了,求你多替咱们说好话,咱们好保住这颗脑袋吃饭。”
弥生上去搀她,太后不再年轻了,五六十岁的人老泪纵横,看得人心里更难过。她宽慰着:“母亲别着急,陛下刚才还拉我的手呢。不要紧,会好起来的。”
托付了众人她忙往后殿去,走到穿堂,脚下却踌躇起来。她害怕,害怕一切都是真的,害怕看见他垂危的样子……应该不会的,他一定又在骗她。她小腿里直抽抽,内侍替她掀起软帘,她打着战进了他的寝殿。殿里一室静谧,貔貅炉里安息香袅袅升腾,半边条窗开着,夕阳落在案上,昏黄得像个渺茫的梦。
如今不管是不是真怀上了,给他报喜,说不定他牵挂妻儿就舍不得走了。弥生点头不迭,“对,我险些忘了。”她接过宫婢手里的手巾给他擦洗,没有羞涩,切切道:“我原本想过些日子告诉你的,轻宵替我看日子,说月事晚了好几天……上回你来,到现在快一个月了,我想九成是有了。你高兴吗?瞧着孩子,你也要挺过来。你忍心叫咱们的孩子没有阿耶吗?”说着泪如雨下,“夫子……阿奴,你一定要活下去,还要教孩子如何为人处世。你不在,我会把他教成个傻子的。你愿意看着他和我一样傻,将来受人欺负吗?”
医官们忙碌起来,弥生瘫坐在地上,她不知道没有了他,以后的路要怎么走。如果他死了,她恐怕也不能独活下去了。
太后坐到床沿上抚儿子的脸,“叱奴,你万事一身,还没到卸肩的时候。咱们慕容家的男人都是有血性的汉子,这么点儿伤,咬咬牙就过去了。我才听轻宵说皇后有了孕,你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要是临阵脱逃,就愧对我,也愧对弥生,你听见了吗?朝上的事你不用记挂,我先替你料理两天。不过也不会太久,母亲上了岁数,精神头不济了,军国大事还是要你自己拿主意。所以快点好起来,那么多人眼巴巴地看着你呢!”
弥生还没从震惊里回过神来,思量了半晌摇头,“贸然告诉他怕空欢喜一场……”她羞涩地拿书挡住脸,“还是再等等。”
弥生的心都要被抻碎了,她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颓败的,嘴唇发乌,连眼睛都睁不开。她怕惊扰了他,跪在他床前的踏板上叫他:“陛下……你怎么了?细腰来了,你醒醒,和我说句话吧!”
她叫他夫子,他也大为震动。这个称呼勾出太多的回忆和情感,包含他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可是他没办法表达,他张不开嘴,发不出声音。肋上痛得撕心,他觉得自己可能要顾不上她了。这是报应,是他弑亲的报应。也许他注定做不成皇帝,即使机关算尽,最后还是这样无奈的结局。
是啊,他是天底下最严苛的人,也是天底下最不守规矩的人。他曾经有负于皇后,同时却又全身心地爱她。元香笑了笑,“咱们女郎苦作苦,认真论,是世上最有福气的。”
太后也怕在这里添乱,便嘱咐令仪:“你留下给你阿嫂搭把手,有什么一定要来回我。”
“你要干什么?”她真生气了,也讨厌他这样的做法,“你是强盗吗?一个皇帝粗手大脚的,你把我当什么?”
她还是难以置信,“你是在骗我对吗?只要你老实坦白,我就原谅你。我们和和睦睦的,再也不置气了,好不好?快醒过来,只有一次机会,错过就没有了。我数一二三,你睁开眼睛,好不好?”她颤着唇仔细盯紧他,“一……二……三……”
孔怀起身,迟疑着垂袖嗫嚅:“殿下听了别慌,只怕……不大好。”
弥生闻言一笑,“你太抬举我了,我哪里有那样的本事。”她左右看了一圈,召宫婢来问时辰,说是亥时三刻了。台上踏歌跳飞天,她显得意兴阑珊,抬起袖子遮掩着打了个哈欠,“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是坐不住了,你再看会儿,我先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