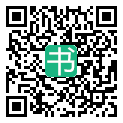第十二章 初吻
他颇意外,但是仍旧点头,“我是说过,而且我也没有违背。你说,我哪里对你不好?”
“我喜欢。”他很快说,其实当真没什么出众的,但是她买的,意义自然大不相同。他微微一笑,“你出去逛,心里还惦记着我,有这份心意,为师很高兴。”
慕容琤敷衍了句:“太学有事耽搁了,其他诸位王都到了吗?”
弥生还没从那一声“叱奴”里回过神来。她入太学三年多,从来不知道夫子的小名叫叱奴。叱奴、叱奴……夫子这等高山仰止的人,为什么会有个让人笑掉大牙的乳名?他上回还要刻印章呢,替她刻个无咎倒罢了,那她刻什么?就刻叱奴?奴这个字不是只有女人才会用吗?总算叫她逮住一个话柄,弥生兴奋异常,夫子也有让她取笑的地方了!
正阳宫里的宫婢和内侍一溜小跑过来迎接,内侍总管满脸堆笑地打躬作揖,“殿下来了?皇后殿下才刚在问,九殿下怎么这会儿还没进宫。原本要打发人到凤阳门上候着殿下去呢,不想殿下说到就到了。”
邺宫很大,大得超乎想象。以前经过宫墙下,抬头看看,视野不得伸展,看不见内城,就觉得那是个灰瓦组成的世界。连绵的,一片接着一片的檐角和斗拱,里面住着大邺最尊贵、最冷酷的一群人。
弥生道:“殿下邀我过府游玩,我一个女孩家,登堂入室的算怎么回事呢,就推说等有了机会,再跟夫子一道过去。”
弥生听她说了这些,才发觉之前错怪了她。她有她的难处,各自过日子,一家不知道一家的苦。她怯怯拉住佛生的手,“你恨阿耶阿娘吗?把你嫁给十一殿下,让你受了这些苦。”
他抿嘴一笑,“我知道,只要我在,便会保全你谢家满门。”
弥生认真考虑了下,好像不仅如此,还有他在摆弄麈尾时挑剔的口吻,也刺伤了她那颗热腾腾的心。
她唔了声,他的鼻息拂在她耳垂上。她心里嗵嗵急跳,想回避,他却不让。隔开她横亘的手臂,抬手在她背上轻轻一压。她身子往前送去,几乎和他贴胸合抱在一起。
慕容琤犹豫了下,“儿未曾听说什么,只是二兄精神头委实不佳。或者母亲得了空把他召进宫来单独问问,他旁人面前避忌,母亲跟前应当是会说实话的。”
慕容琤微笑在一旁看着,对那内侍道:“别客套了,你前头引路。”
慕容琤一哂,“这是内宫,岂是随意能笑的?”他垂眼看看她,她穿着丹碧纱纹双裙,挽洒金鸳鸯披帛。因为及了笄可以梳高髻了,云鬓堆叠出飞天的样式,把纤长光致的脖颈露出来,那么美,又那么脆弱。长眉之间贴着金箔制成的额黄,还有雪一样的皮肤,悍然的红唇……她和这邺宫很契合,她天生就是属于这里的。
她初踏进宫门有些怕,紧紧跟在夫子身后。夫子笑话她:“还是谢家后人,这点阵仗没见过吗?”
那琴砸在地上,发出铮的一声,细细的凤首摔成了两截。弥生愣住了,身上一阵寒冷。好几道目光齐齐射过来,她头皮发麻,为什么她觉得自己是罪魁祸首呢?真个儿冤枉,这事不与她相干哪!
宫里忌讳哭,弥生忍得胸口生疼,眼里裹着泪,闷头将她往外拉,直拉到廊子拐角上方停下来。闪身躲到一片背光的阴影里,姊妹两个抱头痛哭。佛生不住给她擦泪,没敢出声,彼此都憋着。
拓跋皇后对她也颇有好感,女孩家就应当不卑不亢,过于拘束显得小家子气。谢家女儿的长相自不用说,她曾派人打探过,七八岁上就已经初露锋芒,长到现在越发精进。果真命格是早定好的,有些人天生就应该站在塔尖上。骨子里的傲性旁人学不来,权贵当前,也自有从容不迫的气度。不过相惜归相惜,总这么盯着也不是办法,心里又实在喜欢,复招她近前来,拢在身侧笑道:“叫弥生吗?和佛生一样,都是与佛家结缘的好名字。”
慕容琤潋滟笑,果然和他想的一样。青涩的身体,充满诱惑性。他的手指缓缓游移,屋里地龙烘得很热,也或许心里有一捧火,他的鬓角洇湿了。稍分开些,低头看她,她两颊酡红,那抹羞怯的窘态自有种难以言说的妩媚之姿。他忍不住去抬她的下巴,她仍旧垂着眼,光洁的额头,精巧的鼻子,丰润的嘴唇……他越发觉得控制不住,指腹在她唇瓣抚摩,流连辗转。
他的心里安定m.hetushu.com.com下来,蛮好,和他预料的一样。想起她路遇了晋阳王,便又问:“大王同你说了什么?”
一行人上了丹陛,弥生每行一步都小心翼翼。不能四处扫看,只低头盯着自己的足尖。正殿里铺着厚厚的胡毯,踩上去脚底便陷进去半分。她敛裙而行,眼角掠过各色的杂裾垂髾。殿里渐渐静下来,座上有个和暖的声音招呼:“这是谢家女公子?”
慕容琤知道她在打什么算盘,并没有要生气的打算。只不过脸上装得严厉,冲她抛个眼色。但她好像并不怵他,巧笑倩兮,很是自得。
师徒两个喁喁低语,穿过一条笔直的甬路,两侧的紫薇发了新芽,在半抹残阳里簌簌轻颤。渐次近了正阳宫,老远就听见欢声笑语,间或夹杂着不成调的箜篌雅乐。这氛围和弥生想象中的不大一样,不似庄严肃穆的皇城,倒像寻常大户人家热闹的后院。她急切起来,不知佛生到了没有,暗暗牵挂着,脚下也加紧了些。
慕容琤安抚她,“别怕,皇后殿下向佛,尤其宽厚慈善。你进了殿门只管上前行礼,记住了目不斜视,就算你阿姊在边上站着,也不能够在殿下面前走神。他们都知道你在我门下,这点名门闺秀的风范都保持不了,可大大丢我的脸了。”
佛生往后挪了挪,靠在一片冰冷的石柱上。叹息着,换了个怅惘的语调,“我这样的,今生就凑合过吧!殿下遭了难,自暴自弃,脾气很不好。你先前没见着他,是皇后另给他安顿了地方,派宫里的医正过去给他瞧腿了。瞧来瞧去又怎么样,还不是没有起色,回回满怀希望,回回落空,然后越发暴躁,动辄扯着嗓子吼,还不如不治。我是不愿在他跟前,能躲则躲。躲不了,只有怪命不好。”
不过总归难为情,师徒两个做这种事太出格了。她退开了,幸好皓月她们都不在。她缩着脖子小声道:“夫子别这样,免得叫人笑话。”
弥生紧张得小腿肚转筋,死死攥紧他的袖子,指甲隔着布料压进掌心里。实在不明白他亲她和尊长关爱有什么关系,好在不算讨厌。他就那样贴着她,同小时候阿娘亲她是一样的。她温顺地闭上眼,夫子的呼吸很清爽。这个亲吻让她感到高兴,证明夫子是喜欢她的。
佛生诧异地望着她,“怎么推了?说的是王家哪个?”
正阳宫是皇后寝宫,放眼望去是一片开阔地,天阶上矗立着铜驼和巨大的仕女像。她脚下略踌躇,那里满堂皆是最高贵的人,实在令人感到惶恐。
皇后对她十分体念,问在太学课业好不好,吃住习不习惯,全然没有半点架子。弥生也会看眼色,平常糊涂,现在的情形下还是很清明的。回答每句话前都斟酌一番,她觉得自己表现还可以,没有太给夫子丢人。
“亲一下好不好?”他的嗓音低哑,把她搂得更紧。
这是他对她的评价?弥生觉得夫子真是高看她,她一直是个傻子,满肚子花花肠子的分明是他自己!她很不屈,反正恼他,不怎么想和他说话。纤髾一甩,也不等他吩咐,自顾自在圈椅里坐下来,拧着脖子别开脸。凉夜如冰,天是高而空的深蓝,只有铜钱大的月亮挂在树梢上。外面没什么好看的,但她即使脖子发酸也绝不把脸转回来。她要表明一种态度,让他知道她对他的不满。
这有点反常吧!
他先前回来的路上还在生闷气,但是踏进卬否,那些不称意的事通通都烟消云散了。他想她应该自觉把夫子气得不轻,心里一定很内疚。于是他抱着悲天悯人的态度进了大门,不负他所望,她的没心没肺再次给他迎头痛击。
外面渐次黑了,阖宫廊庑下都上了八角宫灯。天还没有回暖,和腊月里时没什么区别,一入夜就下霜。透过薄雾看远处的光亮,沌沌的,有些诡异的样子。
“好吗?”佛生在她胳膊上捏了把,“看着长大了,比小时候结实了。”
她顺着抄手游廊往回走,边走边琢磨佛生的话。这会儿爷娘在几百里外,邺城里亲近的两个人都是这意思。她很多时候没主见,一时也犹豫着吃不准方向。停下步子四周看看,这邺宫真是大,屋子多了人也多,夫人世妇的一大家子。统共一个夫主,怎么分派得过来?
“他家大郎。”弥生垂头丧气,“打小就胖,胖得不成话那个。你说要是不推,叫我往后怎和_图_书么处?”
弥生得了特赦,含笑起来欠身,慢慢退出正殿外,溜进耳房里去。
总管道是,“并不齐全。倒别说,康穆王殿下从封地来,却是诸皇子中来得最早的。”说着一瞥弥生,笑道:“女郎是十一王妃的娘家姊妹吧?奴婢早就听说过女郎大名,今日得见,好歹给女郎见个满礼。”
“为了表示尊长对你的关爱。”他好笑自己竟能编出这样的瞎话来,像是怕她拒绝,很快地把唇贴上去……
弥生纳闷着自己的名气什么时候那么大了?那内官再怎么说也是正阳宫总管,给她行大礼她可担当不起。他一弓腰她忙抬手,“不敢不敢,黄门抬举,这是要折煞我了。”
总算找到了症结,她变得振振有词,“樊博士家的女郎是不是要入夫子门下?夫子别忘了立过的誓,从此再不收弟子的。”
皇后和慕容琤相视而笑,“这孩子真个儿讨人喜欢,和那个摆在一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复拍了拍她的手背,“我晓得佛生几年未回阳夏了,总归是手头上撂不开十一殿下。今天好容易遇上,你们姊妹叙叙话,不用在我这里拘着,去吧。”
她从里间出来,一副蔫头耷脑的模样。烛火照亮了她,半边脸大约压着枕头睡的,留下了两道深深的印记。
慕容珩听了也不反驳,把头一低,冲皇后打躬道:“儿失仪,请母亲恕罪。”
他从来都可以轻易看透她,仿佛他们俩共用一颗心似的。他说:“王谢同是世家,相辅相成却又要彼此牵制。帝王业,没有一个人君会眼睁睁让几百年基业的望族壮大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所以要有谢家这样的大家来抗衡。你可曾听说过‘王与马共天下’?王家在前朝几乎和司马氏平起平坐,离宝座曾经那么近,难保没有谋逆野心。所以王家的女人不能为后,更不能生嫡长,你懂吗?”
弥生不防他会这么说,愕然瞪大了眼睛,“为什么?”
弥生猜不到夫子想些什么,只斜着眼睛觑他,“夫子是来找我算账的?”
慕容琤在席垫上趺坐着,淡淡地看她,“你还知道惶恐?我只当你眼里再没有我这个夫子了。下半晌在太学你跑什么?嘴上说得好听,我一直当你是个老实人,没想到满肚子花花肠子。”
“既这么,别的大族也是配不成的了。”佛生有些咬牙切齿地说,“何不索性往高处爬?大王御极不过是早晚的事,我才刚见他进门时瞧你的眼神,你若愿意示个好,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弥生顿在那里,是啊,好像说不出他的不是来。他教她念书识字,让她住到他府上,给她选料子做衣裳,好茶好饭的尽着她……哪里对她不好?哪一点亏待了她?以前她最懂得感恩,现在倒成了白眼狼。为什么?她仔细回忆了下,发现就是因为看见樊家女郎和他那么亲密,她才一肚子不满的。
弥生的榆木脑袋不见得真就笨成那样,可她没气力反抗。夫子就是一帖毒药,她说不清到底是畏惧还是别的什么,既近又远。他睥睨着三千太学生的时候,她对他满怀敬仰。他来到她面前,她习惯了俯首帖耳。现在他抱着她,她虽然惶惑,但还是有些欢喜。欢喜着,欢喜着……夫子的脸贴在她颊畔,她闻见他身上温暖的龙涎香,丝丝缕缕地沁进心肺里来。
弥生怔怔的,才想接话,听见青铜禁那里有宫人在寻康穆王妃。佛生冷声哼笑,“王妃叫得好听,不过是个名头。照应个瘫子,须臾也离不得,我还不如那些仆婢!”说着揽了揽她,“我先去了,这趟圣人看了他的病势下旨,叫在京机多留阵子。等我安置好他,拣个日子外头包个茶馆,咱们姊妹且好好团聚。”
他怔住了,这个问题让他笑不出来。怎么同她解释呢?说他不亲男弟子,只对她一个人感兴趣吗?他挠挠头,“你几位师兄悟性都比你高。”再纠缠下去也得不出好答案,他还惦记着那把麈尾,偏要套出她的真话来,遂抱胸道:“既然买了东西送人,就要抹得开面子。模棱两可要不得,容易叫人误解。我的话,你明白意思吗?”
“罢了,今天过节,旁的我就不多说了,横竖自省些。亏得陛下还未到,否则看你两个怎么交代!”她挥挥手把二王夫妇打发到一边去了,转过脸对慕容琤道:“我看你二兄气色怎么越发不济了,你在外头可曾听说什么?”
弥生摇摇和图书头,“不饿,殿下有吩咐就交代我,我伺候着。”
她扭过身子,脸红气短,“我没听说过学生要给夫子亲的,你诓我吗?”
她搓着手想了想,“夫子请坐吧!”转身对门外喊:“皎月,送茶水来!”话音才落,皎月端着托盘进来了,她立时有点讪讪的,装模作样地清了一下嗓子,“夫子这么晚还跑一趟,学生……惶恐。”
拓跋皇后赐了座,拉着她的手道:“年下听你夫子说你正月里及笄,如何,小字取了吗?”
弥生知道那就是拓跋皇后,是全大邺顶顶高贵的女人。她上前行稽首礼,跪在毡垫子上俯首拜下去,“谢弥生,请皇后殿下金安。”
佛生的眼睛里有凄怆的光,其实她还很年轻,却显得出奇世故。她在闺阁时就很懂事,如今嫁了人,又被远远打发到封地去了。自立门户后诸多历练,要比同龄的人更老到。弥生看着她,先前的热辣褪去了,唯剩下脉脉的温情,她颔首道:“我很好,就是常惦记阿姊。你在高阳过得好吗?殿下对你好不好?生活可顺遂?”
拓跋皇后很客气,示意左右人搀她起来,又道:“抬头叫我看看。”
佛生苦笑,“恨又如何?到了今天这步,万般皆是命,还有什么可怨怪的!只是你不知道他的腿……”她拿帕子掩着鼻子,极其厌恶的样子,“才开始的时候不能动,至少是活的,看着还有血有肉。后来渐渐不成了,血脉走不通,上年夏天得了坏疽,皮肉全都变成了黑色。那两条腿简直像干尸,别提多瘆人。”
她捏着衣角道:“不是顺带,我出门是专程为了替夫子挑礼物。我入夫子门下三年多,从来不知道尽孝道,每回都惹夫子生气,心里很过意不去。原本要买文房的,但是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中意的。后来无意间发现了这把白玉麈尾,觉得夫子清谈时用得上,就带回来了。”
他听了不言声,眉心却拧起来。明天宫里大宴,碰面是在所难免的。慕容琮上了心,不会就这么按兵不动。且探探底,回头再见机行事吧。
慕容珩是背惯了黑锅的,王氏自然样样归咎于他。她俯身一拜,觍着笑脸道:“阿姑息怒,这事怨不得我。我原说要早些出门的,偏偏我家大王来了门客,因此耽搁了。”
拓跋皇后是高明严断的人,究竟怎么回事,她不问也知道大概。她心里着恼,这儿子性善不假,轻重缓急还是懂得的。今天这样的日子宫闱里素来看重,平时再怎么不上心,今天断不能晚到。王氏本来应该辅佐夫主,如今竟换了次序,压他一头不算,还动不动拿他做幌子。可怎么办?他们夫妻间的事,愿打愿挨。别人要做主,总得有个人挑头才好。珩儿不吭气,谁能横插一杠子?
“你不相信我?”他低声呢喃,带了点霸道的口吻,“不许不信我。”
她转过去打量,阶下站着个高挑的丽人,缓鬓倾髻,衣着华美。五官还和记忆中的一样,可是神情里多了些说不清的东西,那就是佛生!弥生心里扑腾起来,那么多年没见,每天都在挂念着她。佛生的嘴角有浅浅的笑,她也是想着她的吧!弥生一头欢喜,一头又怨她凉薄。即使不见面,书信也应该相通才对,可是她却一去三年没有音信。
她在席垫上跽坐下来,往旁边一瞥,正瞧见一架凤首箜篌。看形制是汉代流传下来的,典型的木胎加金银错工艺。朱红底漆上施针刻嵌金彩锥画,凤头的冠子和凤眼用流云和涡纹施黑漆,琴身看上去华美并且精致。弥生读书不甚上进,对那些乐器却颇有研究。她暗里赞叹着真是一把好琴!一般箜篌是十六弦,看这把大致是二十二弦,那便是十足的上品了。
弥生听见有人应道:“殿下谬赞,家下大人是怕不好养,从小就把我们姊妹寄给佛祖做徒弟,才取了这样的名字。”
像集市上卖猪仔似的!看看脸,要不要再检查牙口?弥生只顾胡思乱想,脸上虽自矜着,眼里的笑意却憋也憋不住。单让人家看岂不吃亏?她还在琢磨着要不要赚回来,视线早就不受控制地往上溜了一圈——
诸王终于都到齐了,晋阳王携萧妃进门的时候弥生一扫而过,因为实在是提不起兴致来。吸引她的是后面姗姗来迟的广宁王和王妃,因为之前听说过那王氏的为人,再看看长相不过如此,心里也替广宁王抱憾。
他引她看远处的宫门,“那是止https://m.hetushu•com•com车门,不管亲王臣子,到了这里都要停辇下马。再往前是端门,过了端门就是文昌殿。你要试着接受这里的一切,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所有靠近权力的东西都那么美好。”
弥生吓得一哆嗦,“那就没法子可想了吗?”
她不大好意思,但还是抬起眼来看他。夫子脸上有动人的光,是从来没见过的,柔软温存,她瞬间溺进那片旖旎里。他渐渐靠近,她痴痴地看。夫子有世上最漂亮的眼睛,明亮、洁净、清澈见底。她又开始惊讶,男人怎么会有那么浓密纤长的睫毛哟!夫子果然是个齐全人,没有一处不是完美的。
佛生闻言笑起来,“傻丫头,你到底太年轻。爱情不能当饭吃,男人的心等闲看不透。你在太学读书,知道《氓》里说的吗?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把一生建立在爱情上是最傻的。再说为了权势依附某个男人,焉知那男人就不能给你爱情呢?”
慕容琤很高兴,她大约是习惯这种小动作了。只是姑娘家面嫩,触到他的指尖,微一掠就退却。颊上泛红,螓首低垂。他深深望一眼,要熟不熟的青梅,这时候是最有味道的。
拓跋皇后好相貌呀!果然是贵气天成的人,没有倾国之姿,但慈眉善目,宝相庄严。她很久以前就听说过这位皇后,传闻她是女中大丈夫,明悟又决断。群雄并起的年代里,拓跋氏戍守东南很有权威,强族多想通婚,然而皇后不允,竟看上了当时守城门的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家穷,她便暗使婢女送钱财让他来聘自己,婚后又出资协助丈夫结交英豪。神宗皇帝能够开创大邺基业,有一半的功劳都要归于拓跋皇后。弥生仰脸望着,满心满眼的崇敬。这么眼光独到的女人,全天下有几个呢!
弥生没想到佛生也是这见识,似乎他们都忽视爱情。可能愈是离皇位近了,愈是发了狠地想抓紧权力。她皱着眉头固执道:“我不贪图富贵,就想找个相爱的人。”
单这样倒罢了,偏偏地罩后面还有人。听见了响动打幔子出来,往地上一看,那张脸像给千年寒冰冻住了似的唬人。他阴恻恻地抬起眼,恨不得要把她生吞活剥了。
弥生揉着纤髾道:“我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得意,年下琅琊王家来提亲,叫我给推了。眼下没有了挑选的余地,将来不知怎么样呢。”
弥生咽了口口水,苦着脸小声告饶,“常山王殿下……不是我。”
弥生很感激他,垂下云袖悄悄拉了拉他的手,“谢谢夫子。”
女孩子闹脾气其实也别有味道,慕容琤才发现自己有这爱好。她固执的姿势没有触怒他,反倒是侧脸柔美的轮廓叫他心醉。他心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看久了低低地苦笑——果然还是逃不过这一劫。不管他承不承认,一些原定的计划已经因她改变。
“你说呢?”
佛生果然在那里,正和几个世妇打扮的人说话,见了她快步过来,捧住了手上下打量,哽咽道:“细幺都长得这么大了,若不是早就听说你今日会随九王进宫,我怕是认不出你来了。”
那王氏的脸架子不美,颧骨略高,吊梢眼,这种面相让人觉得莫名犷悍。她上前给皇后见礼,尖厉的一条喉咙,二王在边上完全被压住了,看上去有点可怜兮兮的。
“谁笑话?”他道,“谁又敢笑话?”
皇后望了眼慕容琤,“叱奴,作何解?”
“夫子说话不算话!”她突然指控,似乎按捺了很久,嗓音有些发噎,“你说过的,以后要对我好些。”
他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你同我闹别扭就是因为这个?”
他这半天在太学坐立不安,日头每西移一寸,心里就多一分焦灼。好不容易延挨到散学,他设想了她在灯下读书练字的样子;或者不长进些,和底下人聊天打茶围也行。只是没想到她会从日中睡到日落,整整三个时辰啊,还没有要起来的打算。眼下勉强站在他跟前,半梦半醒、糊里糊涂……他别过脸吸口气,她上辈子一定是块木头,一定是的!这样迟钝的人,谁才能走得进她心里去?
慕容琤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告诫她时时警惕,免于过失。”
皇后大概也不太满意,蹙着眉道:“今日出冬,十一郎远在高阳都到了。你们是京里的,来得倒比谁都晚!”
诓不诓的,横竖木已成舟了。嘴唇上还留有余温,他舔了舔,志得意满,
hetushu.com.com半带着促狭地低笑,“你叫我声夫子,除了课业,别的诸如为人处世我也有义务教导你。”佛生耷拉着嘴角仰起头,把眼泪都吞了回去,“枯木逢春倒还有可能,风干了的腿还能长新肉吗?从哪儿长?从他那两截棍子似的腿骨上?我如今不愿想那些了,横竖我们两人之中死了一个才得超生。细幺,你日后挑郎子定要把眼睛擦擦亮。你有本钱可以选择,千万别学阿姊,知道吗?”
弥生回身去开箱笼的铜搭扣,把锦盒取出来递给他,“夫子别嫌弃,学生感念夫子教导之恩,得个小玩意儿孝敬夫子。夫子喜欢就用,若是不喜欢……”
弥生拿手背碰碰脸,“那庞师兄他们呢?”
慢慢到了正殿门前,殿里人不知何时都散了,只剩几个侍立的宫婢,泥塑木雕般地伫在那里一动不动。没有人了倒也好,前头乱糟糟闹得头疼。后来露天说了半晌的话,身上的衣料像浸在水里过,拿手一抹,寒气逼人。要不是为了见佛生,今天万不会进宫来。她办事一向大意,宫里规矩又重。所幸皇后面前没有失态,否则少不得闹个不痛快。
她没有看到他眼里浮起的万丈雄心,一双手交握在腹前,她有她的考虑。其实坊间那句民谚,认真论,王谢并不是齐名。硬要分出伯仲来,还是王家的名头更大些。为什么谢家总能占据凤位呢?王家权势滔天,执掌凤印不是更加顺理成章吗?
她眨巴几下眼,自己拎得很清。初出茅庐的后生晚辈,哪里能同他这样老谋深算的人比肩呢!那柄麈尾分明是替他买的,只不过看见他和樊家女郎纠缠不清,这才临时改了主意。眼下算是和解了,那她留着也没用,还是送与他算了。
她怕的是那些俑人一样的禁军,穿着明光铠,一个个昂首伫立着,面无表情的样子很吓人。她挨得离他近一点,“那些人都不会笑的吗?”
贵重的东西不能上手碰,远观还是可以的。她没耐住,挪过去了些。后来回忆一下,其实还隔了两尺宽,连个边儿都没碰着,天晓得它怎么就倒下来了。
弥生应个是,“家君照着《易经》上取的,叫无咎。”
拓跋皇后手里的琥珀念珠握得咯咯响,“这么下去不成,我儿的性命都要交待了。”说罢又缓了缓声气,回眼看弥生,和暖道:“过会儿就开宴,可饿吗?”
弥生虽混混沌沌,到底也理解了大概。只是她没敢问,既然能够制约王氏,那么对谢家肯定也另有手段吧!她转过脸看他,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夫子,我们谢家人都很安分。”
慕容琤简直要笑起来,他不遗余力的种种终于起了作用,她开始懂得嫉妒,开始有了独占欲。他欢愉至极,起身过来安抚她,“我没有要收她做徒弟,真的,你要相信我。你入室三年多,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他把手覆在她肩头,那一点圆润单薄的触感,勾起内心深处最汹涌的欲望。他拉她起来,她扭捏的样子居然让他产生吞她入腹的冲动。
弥生忙应了,送她上台阶。佛生的腰裹得很细,走起路来摇曳生姿。她看着那背影施施然走远了,方才想起她和六兄的事来。佛生如今不相信爱情,大抵就是因为错过了六兄。如果她嫁的是谢允,远离了利益争斗,也许看法就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那柔艳的令人窒息的美好啊!他吻了她,才知道女人的嘴唇胜过世间所有。他不是未经人事的毛头小子,以往不带任何感情的接触里没有这个环节。只有爱了才可以,爱了会渴望亲密无间。可她似乎没有这个觉悟,她永远都慢半拍。显然是吓着了,浑身僵硬毫无风致。不过他不介意,把她抱在怀里,仍旧像对待最珍爱的宝贝。那些心计和算盘暂时抛开,脑子里盘亘着“以后再说”。这是个魔咒,支撑他暂时的放纵。
夫子躬身满揖,“回母亲的话,正是。”
“细腰……”他长长叹息。
“学生省得。”弥生点头不迭,油然生出磅礴的责任感。自己不打紧,但夫子最是要面子,若带累了他,那就是造大孽了!
夫子圈住她的腰,弥生没处躲,只好一味地低着头。怕和他贴得太近,曲起胳膊抵在他胸前,心里实在是忐忑,嗓子里也一阵阵发紧。梳妆台上的海兽葡萄镜角度那么凑巧,堪堪把他们的身影照进去。她侧过脸细看,同样洁白的衣衫,牵枝挂蔓地纠缠在一起,在镜面昏黄的光晕里暧昧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