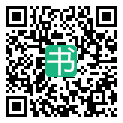第七章 尘起
那是晋阳王府的大管事吉甫,油水捞了不少,膀大腰圆,比王爷还像王爷。平素在手下人面前不可一世,见着皇亲国戚就成了孬种。当初七王和十王看他不顺眼,把他堵在巷堂里朝他身上撒尿。他哭哭啼啼地同慕容琮告状,弄得兄弟间险些反目。
他负着气过去,她很迟钝,等他将到跟前才突然看见他,咦了声,“夫子宴罢了,这样快?”
几句话夹枪带棍的,两个女人手绢掩着嘴,无比隐晦地嗤笑起来。这等小家子气,看样子大概是晋阳王的姬妾。弥生本就有些傲性,看不太上这些下等人。相安无事便罢,招惹到她头上来,还牵搭上了夫子,这叫她火气直往上蹿。她沉声道:“二位夫人以背后道人长短为乐吗?先前说广宁王,眼下说乐陵王?我竟不知道,你们晋阳王府是这样的待客之道!”
弥生很执拗,她觉得自己没有做错,夫子的火气来得没头脑。她梗了脖子,“我不去。”
慕容琮招呼兄弟坐下,饶有兴致地打量弥生,“女郎可愿同饮?本王可以命人备梅酿来。”
弥生独自转出了园子。
她没想到这等显赫的贵胄会关心那么多,也许只是怕急景凋年闹得国库空虚。但总算忧国忧民,很是值得夸赞。
弥生被他吓了一跳,忙赶上去跟随在他左右。她心里直犯嘀咕,夫子连庞嚣都没带,偏带她一个,莫非真的有意要把她塞给晋阳王吗?她开始有点怨恨夫子无情了,人家有嫡妻,就算以后御极也轮不到她做皇后呀!难道男人都比较疼爱小老婆,她还有晋封的希望?可是晋阳王对她来说年纪太大了,三十一二岁,九成是腆着肚子、胡子拉碴的模样。她自己想想就害怕,脚下迟疑着,迈不开步子。眼下开始后悔,真要是这样,还不如嫁给王潜呢!
她只是抽噎,把嘴唇咬得要出血。他再瞧不下去了,多瞧一眼就多一分煎熬。猛然回身上了车,帘子重重一落,把她挡在外面,眼不见为净。
弥生语窒,夫子这么个生气法,回头八成又要罚她了!她哭丧着脸拜下去,“学生委实不敢,有一句假话就烂舌头。夫子怎么不信我?我虽年轻,择婿还是有标准的。难道来一个就想要嫁给人家吗?”她怨怼地看他一眼,“学生在夫子眼里就是这样的人?夫子也太小瞧学生了。”
他蹙着眉,背着手慢慢地踱。踱了几步回头看她,“你喜欢那种没有刚性的男人?平常大气不敢喘,办事瞻前顾后,唯恐得罪了别人,满嘴只会说‘是’的?”他哂笑,“你果然独具慧眼,给为师长脸。”
她和广宁王在一起,叫他有些意外。两人似乎相谈甚欢,她脸上巧笑倩兮。他驻足看了一阵,心里恼她不听话。先前说好不乱跑的,结果他告辞出来,居然连人影都找不到了。
庞嚣愕然,“你反了吗?无论如何,夫子是尊长,你不去赔罪,难道叫他来向你低头?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夫子同府上大人有什么不同?若是谢尚书有了疏漏,你还要计较不成?”语毕换了个商量的语气,“就算是帮阿兄的忙吧!夫子生气,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兜兜转转过了一片梅林,积雪压在枝头,偶尔有簌簌坠落的声音。她往前看,青石路上并排走来两个华服女子,衣带飘飘,环佩叮当。边走边笑,“枉他是个王,一母所生的,同大王比起来差别竟这么大!”
她正被晋阳王看得发毛,夫子这话一出,她立时如蒙大赦。忙作揖道个是,“学生不走远,就到前头池子边上逛逛。夫子要叫我,我马上就回来。”
慕容琮审视一番,眯眼喃喃:“谢家的女儿果然不同凡响,今年多大?”
那是晋阳王妃萧氏,前朝后主的胞姐。虽说娘家没落了,但和慕容琮夫妻相处还算和敬,在王府里的地位也无人能够撼动。见慕容琤给她行礼,欠身让了让,“九郎来了?你阿兄盼着你呢,快些进去吧!”言罢不逗留,带着一干仆妇去了。
弥生趁这当口偷偷往上瞄了一眼,好家伙,原来那晋阳王和她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唇红齿白,乌发如墨,竟和夫子长得有七八分相像!据说三十出头了,可是光看长相,不过比夫子更显沉稳些,并没有显出老态来。
“什么都学。”她开始掰手指,“卜筮、医药、书画、弓矢、天文、棋博、胡书……太学生们学什么我就学什么,只可惜没有刺绣织布,和图书因而女红上欠缺一些。”她又吐吐舌头,“其实我学什么都是半瓶醋,常惹夫子生气的。逼得夫子要把我带在身边,方便随时调理管教。”
她道是,侧眼看他,他挺直了脊背。罩纱的袍襦从肩头飘坠下来,身形虽消瘦,但慕容家的气度传承得还是很好的。他是个轩昂的人,只是不知为什么懦弱得出了名。大约也有些误传的成分在里面吧!她以前听说过,他少时很聪明,也有学识。圣人曾出题考验他们众兄弟,各人发了一团乱麻,叫他们理出头绪来。别人都忙着梳理,只有他抽刀便断。圣人问他缘故,他说“乱者当斩”。分明那样决断的,怎么长成了,反而变得优柔寡断了。
陪同广宁王来的吉甫一味地递眼色,那两个女人脸上登时五彩斑斓。陈留谢家在大邺是鼎盛望族,“生女为后,公主满门”,说的就是谢家女眷的荣耀。对于她们这样的身份来说,调侃郎君们两句反倒无妨,但在出身高贵的女郎面前放肆,就有点丢人现眼了。也不知人家将来有什么样的成就,稀里糊涂得罪了,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因赔着笑脸告罪,“真是失礼了,我们原当是位少年郎呢,没想到是谢家女郎。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慕容珩缄默,天是冷的,她站在凛凛寒风中,冰清玉洁。这种性格的女子很少见,柔弱的外表下有颗果敢的心。他掉过头去,手指的触觉渐渐鲜明。这个冬天的收梢,出奇的温暖。
他朝门外看,天还是阴沉的。其实应该高兴些的,但是这天色,莫名令他心烦意乱。
这样的交谈实在是松散得很,弥生对笼着的手抽出来,对他扬了扬腕上的秋板貂鼠套,“我穿得多,还有这个呢!我是想,若是殿下冷,就用我的暖兜,里头还是暖和的。”
他看着那眼泪,脑子里乱成一团,“又哭什么?我说错了?”
慕容琤还是淡淡的,有点事不关己的模样,“她不是孩子了,若是有意中人,自己也可以做主。”
慕容琤嗯了声,“耽搁有一阵子了,太学最近要开女学,还有许多事要忙。二兄入园吧,我先告辞了。改天约个时候,咱们到桃花坞包个场子聚聚。”
她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还是有些的。慕容琤听了不反驳,只是抿嘴一笑,“你不必在跟前伺候,这园子里景致好,你自己到处逛逛。只别走远,回头迷了路,再叫我费力气找你。”
他顿了一下,想起来她可能对这话题不感兴趣,忙笑道:“以前常听说九王手底下有个女弟子,今天可巧遇上了。太学里的课业不是针对男子的吗?你在那里学些什么?”
他觉察了,调过视线来与她对望,随即一怔,眼里浮起探究之色。他咦了声道:“这是哪个?是你那女学生吗?谢道然家的女郎?”
“又惹夫子不快了?”庞嚣叹息,“过会儿等夫子气消了,去给他赔个不是。”
另一个道:“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只是懦弱得过了头,倒招人笑话。据说节下进宫拜年,一头走一头叫王妃数落。从延秋门骂到铜雀台,他只唯唯诺诺地答应,弄得大人训导孩子一般。”
慕容琤不屑与他耍嘴皮子功夫,别过脸去,朝金池那头望了眼,“王妃可在吗?”
西边门开着,打扫的婢女从里面提了水桶出来,从他们边上绕过去,渐渐走远了。庞嚣道:“你往后就在这里,我在另一边。若是有事不愿麻烦夫子,只管来找我。”
慕容琤从洵圩园出来,遍寻她不得。沿着金池边的石阶上去,才在梅林间的甬道上找到她。
他摇摇头,“不冷,你冷吗?”
她能看出他不高兴,真是很不容易!奇怪他竟这样生气,因为她没有按照他的设想走吗?但是她成功吸引了晋阳王的注意力,他觉得自己应该很满意,却不知为什么,还是不怎么快乐。
雕花门上的洒金帷幔都打了起来,两边拿穗子绑好,还没等他进去,慕容琮自己由两个婢女架着出了内堂。他耷拉着一条跛腿,襟怀大开着,累得气喘吁吁。两个女人力道小,搀扶又不得法,摇摇晃晃,几乎要翻倒。慕容琤见状忙上去接手,兄弟两个搭着肩背,才顺顺当当到胡榻上安置下来。
慕容珩笑容越发大了,“你家夫子是盼你成才吧!再说女孩子出来见识见识也是好事。”
慕容琤见她愣神,哗啦一下振了振袖子,转身就朝月洞门走。弥生忙缩着和-图-书脖子赶上去,心里对那二王感到好奇,没胆子在夫子这里打探,只有回去问问载清他们。
那两个女人交换一下眼色,“脾气真不小!我们又没说什么,倒叫你砖头瓦块来一车。问你是什么人,是男是女,这都问不得吗?”
“殿下仔细脚下。”内侍殷勤道,边说边哈下腰,仿佛九王一脚踏空,他就立刻横躺下来做垫脚石似的。
那内侍应个是,“宫里医官来瞧过,开了药,照方子吃了五六服,眼下好多了。只是还有些水肿,膝盖粗得穿不上裤子。医官说了,再看十来日。若是十天后还不能消肿……”左右觑了觑,低声道:“只怕那腿就废了。”
“我前两日去了趟琅琊郡,今早方回邺城。府里家奴回禀了这个消息,便先赶过来瞧瞧。”慕容珩把暖兜摘下来还给弥生,对她道谢,一面又问慕容琤:“如今怎么样?伤势可重吗?”
他暗里懊悔,便探身往后看。她坐在高辇上,毡子偶尔被风吹得掀起一角。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的袍襦和腰间璎珞编成的束带。穗子那么长,缠缠绵绵地垂到踏板上,辇车微有颠簸就轻轻地漾,像落叶激起的涟漪,一圈圈叫人头晕。
男人们喝酒是不看时辰的,想起来,兴之所至,就算大清早也可以摆宴设席。慕容琤难得来晋阳王府,碰上兄长诚意相邀,自然不好推辞。令人诧异的是厨子上菜的速度,像是事先就筹备好的一样,不过半盏茶工夫,杯碟碗盏铺排得满满当当。连着食案一同搬上来,再摆上厚羊皮的毡垫子,算是样样齐全了。
弥生讪讪笑了笑,夫子撩了袍角迈进一座庭院,她也没空和那管事搭话,忙不迭追上去。进门一看,金砖铺地,雕梁画栋,饶是见惯了大场面的也要惊叹。大到橱柜,小到摆设,没有一样不是别具匠心的。她暗里咋舌,这晋阳王肯定是个穷奢极欲的人。既贪财又好色……她咽了口唾沫,小腿肚有点转筋,越发感到惧怕。
王府着实大,远处有亭台楼阁,飞扬的檐角高低错落,掩映在长青木的枝叶后面,繁华之态不可比拟。她在湖畔站了一阵,像个探险的孩子,这里看看,那里瞧瞧,相当有兴致。走得渐渐有些远了,回头看看夫子所在的方向。洵圩园的走马楼很显眼,只要夫子还在那里,她走得再远也找得到来时的路。
家奴嘛,总忘不掉时刻表现他的忠心。慕容琤一哂,“你辛苦了,他日大王自然不会亏待你。”
他越说越苛刻,她涨红了脸没法反驳,视线里车辕都扭曲颤动起来。霎了霎眼,眼泪噗噗落在青石板上,喉咙里堵了口气,简直要把她憋得窒息。
吉甫仔细看了她两眼,“常听说太学里有位女公子,想来就是女郎吧!”
慕容琤接口道:“是她异母的庶姐。”明明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不知怎么,突然有些反感起来。她在他身后,他要费很大的力气克制着不去回头看她。琮的目光肆无忌惮,他不由蹙眉,话锋一转道:“这趟的事是谁下的黑手,阿兄可查出来了?”
慕容琤低头一笑,“阿兄说得是。”暗里忖度着,他到底不是个莽夫,要从他口中打探消息是不能够的。眼下以静制动未尝不是好事,就像宗圣寺和尚说的,“乐无为者,一切缚解”。置身事外,反倒更符合他平常的处世态度。
慕容珩道好,边上婢女来引道,他对弥生礼貌点下头,便掖着手施施然往甬道那头去了。
她装出一脸意外来,“同情殿下?殿下是什么人,要我来同情?”说着莞尔,“殿下是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大可不必!下回听见她们嚼舌头,就命人把她们捆起来,送到晋阳王殿下跟前请他发落去。晋阳殿下还是京机大都督呢,连内宅都管不好,拿什么代理朝政!”
慕容琤不耐烦地抿紧嘴角,迈出了晋阳王府门槛才道:“他做兄弟再好也没有,但对于你,做夫主还差了点。”
他缄默下来,穿过月洞门朝内苑去。才过门槛,金池边上远远有人快步迎上来,打躬道:“殿下来了?小人才得着消息,没能到门上迎接殿下,真是罪该万死!殿下快里面请,大王在洵圩园里呢!”
吉甫喏地领命,拱肩塌腰地说:“那殿下且逛逛,小的着人在边上候着,殿下若有事,只管吩咐他们。”言毕一拜,飞快地挥手,把那两个嚼舌头的女人一并支走了。
慕和-图-书容琤只觉好笑,这位大王平素再狠辣,对美人是相当怜惜的。但凡有点姿色的决计不能落进他眼里,何况现在这样一位出身高、样貌好的女郎!他笃悠悠道:“谢家没什么不放心的,她在邺城也不算无依无靠。横竖是我门下弟子,我自当照应她。原先住太学,如今大了,再和那些师兄弟住在一起不方便。我府里划个院子给她,日后下了学就回乐陵王府,总比住在外头强些。”忽而又一笑,“阿兄怎么问起这个来?”
吉甫躬身道是,眼风狠狠地对那两个女孩扫过去。嘴里低叱:“还杵着?等着吃鞭子不成!”
弥生倒也大方,垂眼上前长揖,“学生见过大王,大王安康。”
慕容珩更惊讶了,愣在那里不知怎么才好。想了想,大概是刚才那两个歌姬的闲言叫她听见了,不由苦笑,“你是同情我?”
一路说着过来,经过弥生面前停了停,其中一个女人偏头审视她,“这是谁?”看她一身青缘袍襦,因笑道:“究竟是男是女?样貌倒像个女郎,怎么穿着太学的衣裳?是跟着九王殿下来的?听闻九王殿下到如今还没娶亲,原来对弟子的挑选颇有见地嘛!”
他拱手作揖,“阿嫂这一向可好?”
他的眼睛很深邃,嘴唇却淡得发白。男人这样的面相,看上去像是身体上有不足似的。弥生作势往远处眺望,痛快呼出一口白雾,“风真大!殿下冷吗?”
慕容琤笑道:“正是。”冲弥生递个眼色,“来见过晋阳王殿下。”
弥生摆手不迭,“多谢大王好意,学生不会喝酒,一喝酒就上头。”
慕容琮和以往不大一样。从前兄弟聚会时,看上哪家的女子,不论大姑娘小媳妇,从来没有避讳。这趟却怪了,表现得很是从容稳重,这点叫他看不透。晋阳王一向不拘小节,想来不单是因为谢家女儿的名头……莫非是一见钟情?他险些为这个想法失笑。慕容琮是情场老手,可能像个毛头小子似的失魂落魄吗?若真能这样,倒是正中他下怀了……
慕容珩点点头,“你家夫子今日也来探望晋阳殿下?”
慕容琤是男人,男人最明白男人的心。这样举世无双的容貌,但凡是个人都不愿错过。他坐在官帽椅里,搁在膝头的两手无意识地握成了拳,脸上却是如常的,淡淡道:“刚满十五,前两日我去了趟陈留,就是参加她的及笄礼。回来的路上投宿在汲郡驿站,才得知了阿兄在太行遇袭的消息。原本昨日就要来的,碍于回城太晚,这才等到今日。”
慕容琤敛袖而行,问那内侍:“大王眼下可好些了?”
他和她的六兄谢允有些相似,都很谦和。一句话出口前要再三斟酌,唯恐刺伤了别人,却反而莫名落了个雌懦的名声。她欣赏这样的人,君子如玉,有思想,不一定要表现在言行上。
弥生望望夫子,陌生男子随意问年纪是不合规矩的。她不好回答,也不想回答。
吉甫道:“这会儿也在园子里,刚服侍大王用过药。”
吉甫唯唯诺诺,“殿下这是折煞小人呢!小人是做奴才的,能有什么福泽。只盼着大王好,小人在边上尽心服侍着,就是小人上辈子修来的好运道了。”
慕容珩哦了一声,踅身对吉甫道:“你不用跟着,我过会儿再进去。免得撞上他们喝酒,我清早上不爱这个,去了反倒扫兴。”
这个怎么说呢,说她和广宁王闲聊了几句,夫子误认为她瞧上了广宁王,所以大发雷霆?她搓搓手,有些难出口,踌躇了下才道:“都是我的不是,是我疏忽了,惹得夫子不快。”庞嚣除了叹息,也找不到别的表达方式了,往高楼方向抛了个眼风,“夫子在正衙里,我着人备茶水来,你送进去。”她张了张嘴,原本还想讨价还价,后来也硬了头皮。反正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还能躲到天上去吗?
她哑然,夫子和广宁王不是一母同胞吗?别人取笑他便罢了,怎么连自己兄弟都瞧不起他?她怔怔的,“夫子,二王殿下这样不堪?”
“大兄怎么自己出来了?”他看看琮的腿,“眼下怎么样?还疼吗?”
事情似乎是一步步朝着他设定好的目标发展,但是他却变得三心二意起来。奈何他不是个情感控制理智的人,也只一霎儿犹豫,随即便顺水推舟,一手把着斟壶添酒,嘴里应道:“她年纪还小,听她自己的意思,大约是想www.hetushu.com.com再过两年。怎么?阿兄这里有好人选吗?”
弥生不知道,自己和一个近乎陌生的人,也可以聊得很家常。
他没有理她,对慕容珩拱手一揖,“二兄也来了,真巧。”说着视线落到他手上,越发感到奇怪。再看弥生两手,手指冻得红红的,指尖有一小截露在广袖外,像颗半熟的樱桃。
他讶然,复一笑,“哪里有男人戴暖兜的,多谢你的好意。”
正盘算着,头顶上飘下来一声冷哼,“你倒是同谁都有话说,这个二王怎么样?你们说了些什么?”
慕容琮显然也不愿过多提及,拍手唤人,吩咐道:“去备桌酒席来,我与九王爷畅饮几杯。自从受了伤,好几日滴酒不沾,简直闷得要发疯了。今日便耽误一回你做学问的时间,咱们兄弟好好聚聚。”
慕容琤看他一眼,半带玩笑道:“几日不见管事,福泽越发深了。”
“殿下独个儿来的?”她仰脸笑了笑,“还不出太阳,连着四五天雨雪,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广宁王慕容珩。
慕容琮猜忌心重,如今受了重伤,在他看来那些虎狼兄弟个个都很可疑。个个为了争夺皇位,都存着心要害他。所以不待见众人是很正常的,横竖他是嫡长,就算再孤高,旁人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梅林的这条路上只剩她和广宁王,这位王性子淡,不是锋芒毕露的那种人,和他独处并不觉得压抑。弥生想起刚刚听来的消息,再看他委实是瘦,气色也不大好的样子,心里可怜起他来。
“谢家是什么打算?及了笄,怎么还叫出来呢?如今住在太学里?”
她走得实在是慢,他不得不停下步子,不耐道:“你可走得动?可要我叫人来抬你?”
这下她不大好意思了,想想为了她一个人,叫大家跟着提心吊胆,横竖是说不过去的。她垮着肩,只好应了声:“阿兄别说了,我回头就去。”
她眉开眼笑的样子尤为动人,慕容琮瞧得有些发愣。等她出去了方对慕容琤道:“以往只听说,并没有见过,我竟不知道你门下有这样的宝贝!我问你,她可曾许了人家?”
弥生道是,“这会儿正吃席呢,我闲着无聊,夫子就打发我出来了。”
他气不打一处来,指着她的暖兜道:“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跑到人家手上去了?我常教你要自省,你是女子,同那些师兄弟不一样,可你何尝听进耳朵里去了?你爷娘将你托付给我,我总要交代得过去才好。如今这么糊里糊涂的,哪天同人私订了终身,只怕我还蒙在鼓里!”
慕容琮倒不说话了,夹了口菜,半晌才道:“谢家的女儿不好乱配人吧!”言罢半带着笑意看他,“你这个做夫子的,将来少不得要多留心。”
庞嚣点了点头,“夫子叫在官署里拨个屋子给你,你下了学,读书写字都在那里。”
“前头在晋阳王府出了什么岔子?”庞嚣站在檐下,掖着两手,皱着眉头问她:“是你闹的,还是晋阳王那里怠慢了?”
到了太学门前,自有人来接应他们。他强迫自己不回头,快步进了牌楼里。庞嚣没来得及跟进去,有些莫名地往后面辇车上看。弥生蔫头耷脑地下来,拉长个脸,满是不痛快的神情。庞嚣知道,这师徒两个大概又为什么事起了争执。只是奇怪,夫子向来稳如泰山的人,心理也足够强大,近来不知哪里不对,情绪常常失控。他无奈打量弥生,人大了,也更会惹是生非了。
驾车的小子打起了门毡,慕容琤正要上车,听她这话停下来,转过身道:“是真的没有想法?别拿我当孩子哄,你们相谈甚欢,不是吗?”
女人对弱者天生就有一股保护欲,她生活在男人堆里,也不像别的女孩子那么多忌讳,没什么头回见面要矜持之类的自觉。他是温润的人,似乎不会对谁造成任何伤害。她自顾自把暖兜摘下来给他戴上,指尖触到他的手背,确实是冷的。她说:“殿下要仔细自己的身子,怎么连大氅都不|穿呢?会冻出病来的。”
弥生脸色有点发绿,自发地目测她和广宁王的距离,还好吧!三尺半肯定是有的。可是听夫子口气,还是不怎么满意似的。这样可就难办了,她一个大活人,周围又都是男子,到哪里都是和郎君们打交道。话要说吧?眼神要有交流吧?这不许那不许,她左右思量,真是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庞嚣领着她进大门,过了石碑往前和-图-书是牌楼,官署就在牌楼那头。高高的方砖台基,木柞结构的建筑。白墙灰瓦,大红抱柱,一派煌煌之气。边上另有左右耳房,略小些,直棂门窗,也是工整威严的。
慕容珩是个老好人,脸上永远是笑吟吟的,“我才进园子就听人说起我,能充当谈资倒也不错。”转过身看了弥生一眼,“我知道你,你是九王的女弟子,是谢道然家的女公子。”
慕容琮探手抚了抚右腿,“究竟是谁,我心里也有七八分把握。只是如今尚未证实,也不好信口开河。”
不管暗里怎样鄙薄,人家终究是王。那两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欠身福下去,“广宁王殿下长乐无极。”
慕容琤嗯了声,“其他王可都来过了?”
她木讷地仰头看他,夫子眼神里满蓄着风雷。她胸口突突直跳,“不怎么样啊!广宁王殿下很和气,同我说太学里的课业,还谈了两句老庄……夫子不高兴吗?”
正要吵起来,后面匆匆来了个人,身上也是亲王的绯衣金带。身量高高的,不知怎么却显得有些孱弱。白净的脸,五官极周正,看人的时候和别的慕容家男子不同,不那么锐利,也没有锋棱。目光像水,含蓄而柔软。
弥生看都没看她们一眼,只对慕容珩俯身作揖,“学生拜见大王。”
慕容琤道:“伤了右腿,想是没有大碍的。知觉还有,也能勉强下地了。不过熬些痛,过几日大约就好了。”他冷冷瞥了弥生一眼,“二兄怎么和劣徒遇上的?”
慕容琮点点头,“劳你记挂着。”又看弥生一眼,“我记得十一王妃好像也是谢家的。”
慕容珩嘴角仍旧挂着浅浅的笑,“我正想去园子里,恰巧就在这里遇上了。你这是要走了吗?”
慕容琮一哼,“怎么能不疼!那几个贼子冲着要我命来的,这一刀若是换成脖子,现下八成出完丧了。”他转过眼看那两个侍立的婢女,胡乱摆了几下手,“换伶俐些的来,没一点眼力见儿,差点害本王的腿又断一回!”
慕容珩谈吐很儒雅,说什么都留着点余地。比如谈起老庄,其实有些地方是不赞同的,但是不会直接表明。不过含糊地说“不怎么妥帖”“好像有些出入”,模棱两可。虽然消极,但不让人讨厌。大邺的郎君们太注重个人魅力,往往为了追求突出,故意表现得特立独行。也许文人圈子里吃得开,但奓了一身的毛,总有种薄情疏离的感觉。
她闷声道是,暗里只叹,如今好了,真正活在夫子眼皮子底下,须臾都离不开了。她打心底里怵他,这种怵很奇怪,就是害怕看见他。倘或以后朝夕相处,她大约会变成木钝钝的傻子。然而没办法,她哪里有挑拣的余地!夫子怎么安排,她照着办就是了。
“广宁王殿下还未曾。”内侍又压了压嗓子,“大王心里不痛快,来过的一个都没给好脸色。不过敷衍几句,便草草打发人去了。”
慕容琤打量她,她紧咬着牙关的模样像要上刑场。才想同她说话,里面幔子一掀,出来位云髻高盘的丽人,穿交颈裲裆,束鸳鸯抱腰,挑金绯缘的纤髾逶迤堆叠,更衬出灼灼的华美来。
弥生怏怏红了脸,“学生没有这个想法,夫子误会了。”
吉甫是个滚刀肉,大脸笑成了花,见缝插针地献媚,“都是小人分内的事,小人万万不敢邀功。横竖九殿下知道小人的孝心,就算将来大王叫小人去刷茅房,还有殿下记着小人的好呢!”
内侍道:“大王回府第二天来过,也没坐多会儿,借口营里操兵就走了。”
“自小爱哭出了名,长成了还是个老实头儿。不是我说,那广宁王妃也忒犷悍了些,哪里有这样对夫主的?说恨起来不叫他吃饭,怪道那么瘦,瘦得像个蚱蜢。”
“六王什么时候来的?”他边问边回头看,总担心她恍神走丢。时不时地关注下,见她跟在后头才放心。
她作了一揖,“多谢大兄。”
慕容珩背手和她在甬道上缓缓地踱,“总是这两天吧!但愿早些放晴,再这么下去秧苗冻死了,庄稼要影响收成的。”
车轮滚滚,心头的火气一拱一拱地冲得胸闷。他直着嗓子长叹,她含泪的模样总在他眼前晃,搅得他心神不宁。半晌逐渐平息下来,又开始反省,是不是把话说得太重了?她到底是个姑娘家,就算不懂事,也是因为年轻的缘故。他这样严厉地一通指责,又捎带上了私订终身之类的话,现在想起来,的确过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