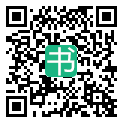第三卷 那一年,眉目依旧
第二十五章 岁月无声
这么多年看过了太多,我又何尝不懂?
他神情一时莫测,盯着我看了许久才说:“永安,你从未如此和我说过话,就好像你我从未有过关系,有过……”我打断他:“若非是婉儿亲口所说,我不会相信你真的就任由此事发生,甚至不惜推波助澜,将仙蕙推上绝路!”
直到听到脚步声消失,我才睁开眼,看着帷帐怔怔出神。
心大力一抽,我险些落了茶杯,可看她仍旧散不去的笑,才明白是被她骗了。她笑着摇头,又摇头,终是起身理了理衣衫:“罢了,你听好,突厥知虽挂帅为相王,亲自领兵的却是相王长子,寿春郡王李成器,故而王师未至而寇急退。听好,是王师未至而寇急退。”
若要取得皇位,的确不能如此干净。
远处李隆基只随意立着,似乎并不着急。
待到半月后,婉儿才说有幽燕的捷报。
不过四个字,我已明白此事远非他说的这么简单。一时有很多话想说,可看着他的眼睛,却都尽数打散了,唯有阵阵不安席卷而来,脑中早已乱成了一团。
“不是他,”婉儿忽然出了声,“此事表面上看,是那几个小辈口无遮拦,非议天子。实则是你皇姑祖母,或者更直接些,是张氏两兄弟为了打压太子一脉所做。”
他似乎在笑,却笑中带了几分苦:“我冷血冷情,无心无肺,却还能换你一个谢字,可算是此生无憾了?”我默看着他:“日后这份情,我会还上。”他又一笑,扶着桌角站起身:“走吧。”
她伸手抱住我:“还来得及,今夜只是下了密旨,永安,还不是绝路,”她的话轻柔暖心,一寸寸消融着我心中的恐慌,“你皇姑祖母以三日为期,这宫内外既然有人想要他们的命,那就肯定也有人要保住他们。你放心,我想办法救仙蕙,但是今夜你一定不能出去,这是风声最紧的一夜,你必须呆在这里。”
是了,若是皇姑祖母的本意,能劝服她的只有太平。
难道真是因为那些荒谬的话,就可以让皇姑祖母下旨要了三个孙儿的命?更何况仙蕙腹中还有孩子,那是武家李家的孩子,流着皇族的血,也同样留着皇姑祖母的血……我深吸着气,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不能乱,必须要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救仙蕙。
过了很久,我才紧紧攥住他的手:“今晚留下来陪我,好不好?”说完这句话,只紧张地看着他,再挪不开视线。他反握住我的手,凑过来搂住我:“永安,我今夜入宫不是想做这些,相信我,我们以后一定会很平安,也一定会在一起。”
她说的话,绝非是为李成器着想,而是知道,李成器是我最大的软肋。
他说完此话就拂袖而去,留了我独自呆立着。
我心跳得厉害,拼命挣开他的手臂,却被他越抱越紧:“曾经你也对我笑,对我说你留在我身边了,可你还是走了。永安,为何你要这么对我?为何要出尔反尔?为何总在我想要对你好好说话的时候,用最伤人的话赶我走?”
张氏兄弟……那就是太平公主的授意?或者是他们兄弟圣宠正浓,想要做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美梦?我无暇再深想,追问道:“李隆基在其中做过什么?或是……”脑中闪过李成器的影子,他和太平暗中有往来,难道……不可能!
过了很久,他才轻声道:“我带你去见她最后一面。”我不敢置信地回头,重复着这句话:“你带我去?”他点头:“我深夜入宫就是为了带你去见她。”
生死存亡,太重的四个字。
难道?我不等他回答又追问道:“你是不是要走了?”他微点了下头:“明日一早就走,所以才想来看看你。”我听在耳中,恍惚觉得不真实,可他就这样直接给了我答案:“为什么这么快?不是今日才的旨吗?”他笑:“今日圣旨上的离京日,本是半月前就定下的。可前半夜幽燕就再传来密报,突厥已大举寇边,皇祖母这才改了日子。”
我紧抓着桌角,强迫自己镇定,一定要想清楚,究竟还能做什么。
我忍着眼泪,用力点头。
大举寇边……
我不忍看四周花团锦簇,流水潺潺,只低头紧跟着李隆基的脚步,随着前面提灯笼带路的人,渐入了被锁着的院子。
李隆基正抱着永惠,笑眯眯看我。
直到坐下后,他才恭敬行了个礼:“刚才在府门口怕人多眼杂,还请县主务要怪罪。”我不自在地笑了笑:“无需如此大礼,先挑要紧的事说。”他忙起身回禀:“夏至已将书信给小人了,小人会尽快将此信送出和_图_书,但……”他犹豫了下,还是照实道,“恐怕郡王收到信,已是无力回天了。”
因为背着光,那眼中更显阴沉,我避开他的视线,没再说什么。
我看着他那双越发斜挑的眼,脑中尽是昨夜婉儿的话,胸口闷得喘不上气。只能捂住压制着疼痛,他脸色变了下,将永惠交给身侧李清,大跨步走下玉石台阶。我抬手示意他不要靠近,却被他一把握住了腕子:“永安,如何了?要不要传医师?”
我没想到他直接说出来,倒是有些不知如何说。
一句话乱了心神,我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去想想这其中的深浅利弊,可终是想见仙蕙的心思压过了一切,最后还是点头道:“多谢你。”
待到寿春王府,何福听说是我来,忙出府相迎,直接将我带入了李成器的书房。一路上竟是未看到任何闲杂人,我低声问他:“王妃……或是府中女眷可在?可有不方便?”他笑着回话:“县主无需忧心,大半个王府都是府中女眷的禁地,郡王若不想见,无人敢擅自违抗的。”
过了许久,我才握紧她的手,想问她可有什么心愿。可话到口边却发现如此可笑,一个女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夫君孩儿,都会随她一道被赐死,还有什么?她还能有什么牵挂?
我听着他同样的心跳,过了很久才轻声问:“累吗?”他抱着我,低声说:“永安,别说话,你不需要和我说话,让我抱抱你。”我嗯了声,任他把我抱上塌,缩在他怀里,开始止不住地流着泪,几乎把他的前襟都打湿了,才哽咽着说:“仙蕙说,她会等着你,等着你的盛世永安。”
他这才抬头看我:“小人要说的话,并非是郡王走前的意思,只是小人的私心。”我看他神情肃然,只颔首道:“但说无妨。”他仍旧是犹豫着,直到我又点了下头,才轻吐口气,重重地叩了个头:“小人明白县主对郡王而言,重过江山,但眼下这件事,关乎的不止是郡王的大业,更是郡王的身家性命,全府甚至是相王一脉的生死存亡。”
是李成器。
若说李成器的字是风骨卓然,那她的字就是风雅至极。
最后也没说一句话,扭头就走,我本就没有对他报什么希望,也就没去叫住他。岂料刚才转身走了两步,手腕就被人紧紧攥住,向后拉去,一把被他抱在了怀里:“永安,你伤到我了。”
“有何遗漏?”我挑起风帽看他。他摇头:“想起年少时,国子监内你也是如此装束。一晃竟是这么多年了。”我心头一酸,拉下风帽彻底遮上了眼。
可这背后他到底要做多少,要妥协多少,从来没有人提过。
然而,就是因为太清楚彼此的性情,我只能闭上眼,不再说话,让他能狠下心走。
“已经足够了,自降旨以来,总算是有人来看看我了,”她低头,“这么多年我太如意了。父王母妃重回太初宫,亲兄姐能常伴在一起,虽难忤逆皇祖母放下了张九龄,却也得了另一段好姻缘。那年我下嫁时哭得几乎没命,夫君手足无措哄了整夜,时至今日却也不明白我是为何哭得那么惨,想想真是傻,”她轻抚着隆起的小腹,小声笑,“姐姐从来都是先知,那一年在龙门山上的话终是应验了,只可惜了这孩子。”
冬阳见他走远,才立刻跑来:“县主可要去看恒平王了?”我茫然点头,又立刻摇头:“去寿春王府。”她惊看我:“不进去了?”我苦笑摇头,进了门不请安就走,的确有失孝道,可如今是人命关天耽误不得,只能下次再向父王告罪了。
门口守着的人见了李隆基都立刻躬身行礼,低声齐唤郡王,他只吩咐拆锁,侧头对我道:“快去快回,我在外等你。”我看他神色,知他不想入内,便颔首快步走了进去。
落在最后,都不过是自保而已。
“站住!”他阴晴不定地看着我,“你不是大哥的人吗?你可知他有亲信密令?你以为他对你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我愣了下,他又接着道:“他自做永平郡王起就有自己的势力,当年太子即位就曾谋划逼宫,这些你可知道?你来求我倒不如去想想,他有什么能给你的,而他真正给了你什么!”
皇祖母命相王为安北大都护兼天兵道元帅,统燕赵秦陇诸军痛击突厥大军。
“为什么,”我紧紧盯着她,“为什么皇姑祖母会下那样的旨意?为什么你会事先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了不阻止?为什么?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她攥得很紧,像是要透过手腕的痛感和-图-书,让我彻底冷静下来。可让我如何能冷静?
我哑然看她,那深笑竟是暖融融的,像是感同身受一般。
我沉默了下,才道:“不是任何物事,而是一个字,需是郡王亲笔所书的字,对不对?”他倒无意外,立刻道:“正是。”我反复掂量着,要不要再追问下去,他却已经看破我的心思,躬身道:“此密令事关重大,县主可是要动用郡王在圣上身侧的势力?”
他脸色一时泛白,却终是忍住,低声下气地说着:“有什么话进门再说,好不好?”此处是恒平王府,我不想在大门口和他僵持着,被人看了笑话,勉强说了句:“放手。”他傻看我,这才缓缓松开手,我没再看他,立刻让冬阳扶着我进了门。
他们兄弟间有一个皇位就足够刀兵相见,我不想再成为另一个仇恨。
我不敢再耽搁,转身就往门口跑,刚才想要叫夏至,又被婉儿一把拉住:“你想要去找太平时不时?太平是什么人?她是这宫中朝中最骄傲的人,除非你对她夺位有用,否则她绝不会多看你一眼。”
自大明宫到太初宫,自太液池到龙门山,她都曾拉着我的手,嬉笑怒骂。
这一生她总是笑着的,只恨着皇姑祖母一人,总好过被所有亲人背叛。
我任她抱着,怔怔地看着烛火。她不停喃喃着,我却再也听不进半个字,一念生死,我本以为自己已经看淡,可是今夜却又一次如此接近,近到无力承受。那日殿上众人不过是给了我稍许难堪,仙蕙便已冷声嘲讽,这么多年她一直没有变过,如果今天换做是我,她若是能先知道消息必然会不顾一切冲入宫,不顾一切去求情。
她说的断断续续,我却听得字字诛心。
“皇祖母已下了这样的圣旨,也只有姐姐敢来见我最后一面了,”她也握住我的手,冰得渗人。我喉头发涩,一瞬涌出泪来:“你喊了我十余年的姐姐,我却也只能做到如此……”话哽在喉,纵有再多的愧疚,也只能再咽回去。
“永安,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管,”婉儿告诫着看我,“这件事情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你管不到,也不能管。”我苦笑:“我明白,这宫中死任何人,都是有层层原因,都需要很多人在暗中促成。告诉我,是谁真想要他们的命?”
她沉默着看我,我身上忽冷忽热的,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
我盯着他:“若我相救永泰郡主……”他断然接口:“唯有宫变,只不过当年太子不似初入洛阳,根基尚未稳固,如今已是深不可测,”他顿了下,才道,“婉儿姑娘与太子的纠葛,县主想必已清楚。而眼下的太平公主也远非当年隐忍,还请县主三思。”
婉儿把我拉到塌上,寸步不离地守着我。
她护我敬我,信我爱我,可最后我却什么也做不到,什么也不敢做。
夏至忙起身,婉儿却忽然出声道:“让她回去,就说县主睡下了。”我听得心惊,看了婉儿一眼:“姐姐知道是什么事?”婉儿从不是喜管俗事的性情,又和仙蕙私交平平,为何才听见这么一句,就立刻能说出这种话?像是深知内情。
自她下嫁后,这还是我初入她的宅子。
自那日回,我始终未再出门,依旧是照常用膳写字,读得是往日的书,休息的时辰也分毫不差。直到她死后十余日,这消息才自宫中传出,无人敢议无人敢说。
“很晚了,你来做什么?”话说完,才觉得喉咙刺痛着,像是被火烤灼着。他缓缓蹲下身子,一双眼中尽是心疼:“永安,冬阳说你午膳晚膳都没用过。”我沉默不语,他又道:“这件事远比你想得复杂,你以为皇祖母猜不透想不明?若非她狠下心,没人能动得了她的亲孙儿。”
那夜我睡得很早,却总感觉着身边像是有人在看我。在半梦半醒中挣扎了很久,才勉强睁开眼,模糊的影子,近在咫尺的距离。
冬阳并不晓得此事,还以为我真的是回去探望父王姨母,很是欢喜地多问了几句,要不要将圣上赏赐的衣料也带些去,我无心再管这些俗事,是颔首让她快些准备。眼下婉儿在陪着皇姑祖母,也只有在这时,我才能有机会出宫。
夏至见我犹豫着,低唤了声县主,我这才狠心折好,递给她:“把这封信带给你哥哥。”夏至颔首,仔细收好后快步出了门。我坐下又想了很久,才又站起身吩咐冬阳去备下琼花膏,与我一道回恒平王府。
她怔了下,才轻摇头:“奴婢不知道。”我停下来,看了眼远处也停下来的李隆基:“冬阳,你www.hetushu.com.com这是在为难我,也是在为难你自己。”她眼中似乎浮上泪,默了片刻才低声道:“奴婢明白,奴婢是临淄郡王的人,可县主终有一日是要跟着寿春郡王的。即便是留在这里,也得不到县主的信任。”
她笑了声,放下手中笔,正要说话时,夏至就已经提裙跑了进来。我吓了一跳,正要问是何事,她已经噗通一声跪下叩头:“县主,永泰郡主遣人来,说是有人命关天的事要见县主。”我怔了下,心底阵阵发凉:“快让她进来。”
“姐姐?”她的声音从里间传出来,我应了声,这才有了些气力走进去。她似乎想站起来摸索什么,却忽然又停下来:“算了,不让你看我现在的模样了,地上很乱,你慢些走。”一字一句都很清晰,除却声音的喑哑无力。
直到回到宫中,我挥去所有人,坐在了书案后。
身上一时冷一时热的,却不想动上分毫。
一句话,如一道厉电,几乎让我喘不上气。
“我本想看看你就走,”李成器俯下身,很轻地用唇触碰我的脸,“没想到还是把你吵醒了。”我坐起来,手不自主抓紧锦被:“怎么这么晚还入宫?”虽然我与他已再无任何束缚,可他绝不是这么鲁莽的人,深夜入宫只为见我,那就一定是有什么要紧事。
这一夜,皇姑祖母在奉宸府内留住,婉儿也恰好不当值,就趁着这难得闲暇留在我这处吃晚膳,吃完不过一个时辰,又说要吃酒。我唤夏至冬阳去备菜添酒,她就在我案几边自行研磨写字,那一笔笔,一字字,都独有风韵。
他一动不动地半蹲在我身侧,我也只能这样坐着,不想再去责问他曾说过的‘严惩不贷’,此时此刻,我所做的与他并无差别。一个是殿前顺了皇姑祖母的心意,一个是放弃了救人的机会。
我摇头看她:“算了,放开我,我现在不需要知道到底是谁这么狠,能做到如此地步的,一定是他们的兄弟姐妹,一定是武家李家的人,”我看她眼神恍惚了下,使劲拉开她的手,“人命关天,先放我去救人。”
他眉头更深了分,斜挑的眼中尽是阴霾隐怒。
我耳根有些发烫,听着她一字一句的话,心中满满都是他的影子。
这是他的书房,我甚至能看到他就坐在书案后,抬头看我。
“李隆基,”我紧咬住唇,“不要弄得如此难堪,放开我。”他沉默不语,我也不再多说话,直到他松了手臂,立刻抽身退后道:“郡王息怒,永安告退了。”
院中极安静,几乎没有人走动的声响。
手中的茶有些烫,我强忍着心口再次的剧痛,颤抖着手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只觉唇舌微麻。
这一日用罢午膳,我刚才坐在塌上,随手拿起昨日读得书,就听见门口有人请安。下意识抬头,李成器正向我一步步走过来,那双眼中竟有了万分的心痛,我看着他怔怔出神,不敢动也不敢说话,直到被他抱在怀里才听见自己的心跳,每一下都重得发痛。
我立在一侧看,叹道:“说起来,当初姐姐在身侧,我竟然都不好好去学一学这笔法,真算是年少无知了。”
婉儿抿唇,似在犹豫。
半年前我还大言不惭地直视李隆基,告诉他,若真有一日,要在至亲和婉儿之间做抉择,我最后只能舍掉婉儿。到最后却未料到竟是仙蕙,毫无任何心机谋算的仙蕙。
他说的也是我所想到的,可却仍是让我心凉了下。
我不敢说话,只看着她的眼睛,直到她很轻地点了下头,才感觉到浑身脱了力,险些坐到地上。那两个虽是同父的兄姐,却并非和仙蕙自幼相伴,可李隆基……李隆基可是同仙蕙自幼一起,从大明宫到太初宫,都是情同亲兄妹的啊!
我闭了下眼睛,眼前一瞬闪过李成器的脸,还有仙蕙拉着我的手,笑着说话的神情。最终还是压着声音说:“我是你大哥的人,此生都是他的人。”他猛地收紧手臂:“你是我的女人,这是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事实!”
可若是他明白冬阳的心思,究竟会如何做?如何反应?我却猜不透。
不久,果真就降了旨。
当年初见他是在曲江畔,那时他便已是李成器的心腹,如今成器不在,我也只能来问他了。我不想再耽搁,直接道:“你可知道郡王的亲信密令?”他怔了下,忙颔首:“小人知道,但也仅是知道有这种东西,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
我心头一惊,竟是立刻清醒过来,却被吓得心跳得发疼。
眼前渐适应了黑暗,我才看见她斜靠在床边,似乎在对着我
和图书笑。这样的阴暗角落,竟像是她已经去了,恍惚在黄泉畔看着我,心越跳越慢,脚下却没有停,直到走到她身边坐下,握住她的手,才惊觉手心已都是冷汗。他安静地抱了我片刻,才松开手,扶着我躺好:“睡吧。”我不敢放开他的手:“明日什么时辰走?”他缓缓伸出手,抚着我的脸,压低声音说:“你醒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我明白他是不愿让我彻夜不眠,等着那个定下的时辰,可他也一定明白,即便是不知道,我也注定是整夜难闭眼了。
我紧咬着嘴唇,口中不觉已是一片腥甜。
我听这话,心里有些不是味道,没说话。
他伸出手想拉我,我抢先避开道:“郡王请自重。”
可婉儿说得句句透彻,主导此事的就是皇姑祖母、太平公主,这两个大周最尊贵的女人,想要哪个的命,那就等于彻底断了阳界生路,谁也无法阻挡。上次若非太平肯为我向陛下低头,我怕也早是这宫中一冤魂了……
我让夏至往李成器府上递了密信,虽然明知他不会在三日内收到,但总是个机会……待到放了笔,却又有了些犹豫,总觉有什么不妥处,却又摸不到头绪。
她仰面躺在塌上,笑着看我,眼睛里分明都是笑意,却偏就不告诉我她看到了什么。我无奈看她:“罢了,我也不等你了,既然是捷报我就安心了。”婉儿咦了声:“捷报归捷报,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他受了多重的伤?”
我摇头,示意他听我说:“今日我想求你,却并非是为我自己。”他倒是毫不意外,也摇头:“此事已成定局,如今谁都救不了她。”我静看他:“只要没有人头落地,就没有定局一说。这么多年,你们李姓皇族哪个是说死就死了?”
外边似乎有人在唤着我名,可她仍旧抱着我不肯松手,我也就这样任由她抱着,听着那一声声的永安,像是被人生生抽着筋,剜着肉。
他眉心紧蹙,重复着:“是婉儿说的?”我不置可否,继续道:“李隆基,你明白我的性情,日后若真有对立之时,我绝不会用你对我的情意要挟你。但这次,我不是为自己求你,我只要你想想那不过是你的妹妹,她不是皇姑祖母,也不是太平公主,她不过是个胸无大志,只想着如何做个好母亲的李家郡主,”我努力压住怒气,定定地看着他,“她还是和你自幼一起长大,一起嬉笑怒骂的人。”
“密旨是我写的,”婉儿直言不讳,“当时殿中还有几个李家小辈,其中就有李重俊、裹儿和李隆基,这几人在圣上大怒时,主动叩请你皇姑祖母降罪,严惩不贷。”
她闭上眼,缓缓地抱住我的腰。
她叹口气,挥手屏退夏至:“今日我留在你这处,就是怕你插手此事。”我不解看她,她伸出手,紧紧攥住我的双腕:“你皇姑祖母下了密旨,让李重润、武延基和仙蕙自尽谢罪。”她语气平淡,可却如巨雷轰鸣,震得我说不出话来。
自这句话,他再没和我多说一句。直到上了马车,才低声对外边人说了两句话,一路沉默着到了府宅后门处,他才示意我以风帽遮住大半张脸,我依着他的话戴上风帽,待到再抬头,才发现他仍旧是盯着我。
我反握住冬阳的手臂:“你说的一字不差,即便是日后留在我身边,我也绝不敢尽信你,不会待你如心腹姐妹。可若是放你回到他身边,”我又看了一眼远处的人,“我却不知他会如何待你,也不知是否真能如你所愿。”她犹豫着,低头半晌才道:“奴婢这辈子只想跟着县主。”
虽说有三日余地,可我却不能再如此等着候着,等到最后也不过是看她命丧黄泉。
我早知她的心思并非是只粗不细,若不然,李隆基也不会挑了她与夏至,放在我身侧。可却仍是未料到,她竟能如此坦然待我,说出了我和李成器的顾虑。
成器,你的盛世永安,究竟要等到何时……
没顶的绝望,几乎让我窒息。
我被他一句句问得哑口无言,可却又总像是知道什么,脑中乱作一团。过了好一会儿才猛地想起很多年前,他曾握着我的手,写下了一个字。我眼中浮现出那个字,还有他为了藏字而写下的一首诗,有些不敢相信:“你说的可是真的?”
再有不忍,也要断,也要伤。
大足元年,邵王重润、永泰郡主,郡主婿武延基因秘聚私议二张,遭张易之诉之御前。圣上大怒,九月三日,逼令三人自尽谢罪。
何福这些话都不过是点到即止,避过其中利害,到最后不过给了我三思二字。
她眸色一冷,肃和*图*书容道:“你要如何救?去求你皇姑祖母?她既然下了这样的密旨,就绝不容有任何人多说半个字。去求你父王?恒平王本就无权无势,自保容易保人难。去求李成器?他远在幽燕,怕是仙蕙已下了葬,他尚未收到密信。去求太平?还是……”她顿了顿,才莫测看我,“去求李隆基?”
可我却只想见到他,这么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很想他能在身边帮我。
我摇了摇头:“你走吧。”从昨晚到现在,已经听了太多的利益纠葛,他这一句句的重复,都不过是在刺着同一处伤口,痛入心肺。
李成器的确曾说过,以我的笔迹,以这个字我可以调遣他任何可用的人。如果真是这样……李隆基冷冷看着我:“我对你一向知无不言,可曾骗过你?”
永安永安,究竟这名字能保谁平安?
就这样默了很久,他也就头抵着地面,跪了许久。直到再入口的茶已冰冷,我才缓缓起身道:“你说的对。”言罢,才去看了眼空无一人的主座,快步出了书房。
可也无需杀尽李家武家的子孙,做的如此决绝。
他没有起身,反倒是噗通一声跪了下来,我被他吓了一跳,忙道:“你知我和郡王的关系,有话尽管直说,无需如此跪着回话。”
我下了马车,不知是因昨夜未睡好,体虚所致,抑或真的是天气所致,已出了一身薄汗。冬阳见我抬袖拭汗,刚想说什么却忽然僵住,我被她吓了一跳,抬头看大门口才终是明白了。
帷帐内只有一盏灯烛,将两个模糊的影子揉成一片,不分彼此。
我喘着气,几乎要哭出来:“无论如何,我也要去试一试。”她摇头:“不行,你不能去,你不为你自己想,也要为李成器打算。他当初放弃了很多东西,才能让太平入宫为你求情,如今他远在幽燕,你在这洛阳若是被无辜牵连,让他怎么办?万一太平以你为筹码,要他放弃更多的东西,怎么办?”
我颔首:“去替我唤郡王过来,就说我要私下和他说几句话。”冬阳应了是,忙快步跑过去传了话,李隆基这才独自走了过来,凝眸看我:“心口还疼吗?怎么忽然有这种病症了?”
不论是当年清润温和,或是经杀戮后渐已淡然的目光,都还是他,肯为我抛去生死,护我在乱马中的李成器。若是他在,绝不会说出今日的话,他只会说:永安,此事你只管安心,余下的交给我。
“我听到了,”他轻抚着我的背,柔声说:“睡一会儿,我会陪着你。”
一路沿着小路而行,经过的下人纷纷躬身行礼,连声唤着县主、郡王,我听这声音就明白李隆基一直跟在身后。约莫慢走了会儿,才舒服了些,便对冬阳轻声道:“今日碰上临淄郡王在此处,你可想好了,是随着我,还是跟他走?”
若是太平的本意,那也只有她能救他们。
“好,”我眼前早已模糊成一片,紧咬着唇不忍让自己哭出声,只紧搂着她,低声道,“我会帮他,帮他完成你的心愿。”
我没力气挥开他,只能冷冷看着他,痛得说不出话。
想让他告诉我该如何去做,如何做才能不连累任何人,如何做才能保住仙蕙……
很瘦的身子,就这样缩在我怀里,从轻微的呜咽声,到最后几乎是撕心裂肺的哭声,填满这屋子的每个角落,直到最后几乎喘不上气,才说:“替我告诉成器哥哥……我会阴间等,等着他登上皇位,只有他才能让李家真正太平。”
我只觉得眼睛酸得发胀,渐渐趴到了桌上。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久,才感觉肩上被人拍了下,抬起头去看时,李隆基就站在书案侧,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正是夏末秋至时,却还有着些虚浮的燥气。
我被她一句句问得哑口无言,可就是最后那一句李隆基,分明就带了些嘲弄的味道。我知道她不可能会以李隆基和我的旧事玩笑,难道真的是与李隆基有关?我不敢置信地看她:“真是李隆基?是李隆基做的?”
她不等我说话,又笑吟吟地添了句:“永安,你真是好眼光,好运道,连我都开始心生嫉恨了。如此男儿,别说是你皇姑祖母登基以来,就再往前说都未能有半个与他比肩的,突厥人生性暴虐,竟也能被吓得听见区区一个名字,就立刻退兵。这算不算是最大的捷报?”
我站在房门前,犹豫了很久,才轻推开。没有任何灯烛的火光,半室灰白的月色,半室却是漆黑一片。我只看了一眼四周被砸碎的物事,就有些脱力,生怕再走入见到的也不过是一具冷尸,过了很久,才出声轻唤了声仙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