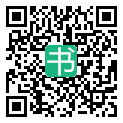第二卷 那一旨,终是错嫁
第十二章 完婚
水车的声响,夹杂着夏日蝉鸣,听在我耳中,尽是杂乱。
他放了茶杯,走到我身后,握住了我持笔的手,左手撑在桌子边沿,将我环在了胸前。
我攥着笔,强停了下来,侧头看他,道:“那为何暑气正盛时,手却一直是冰凉的?”他眼中笑意未减,看着我,道:“那年在天牢内住了几天,又受了刑,总会有些旧疾留下来。”我听他说起那年,心头抽痛着,低声道:“我一直没敢问你,来俊臣到底用了什么刑?”
我一动也不敢动,只觉得他右手微用力,就引着我在纸上写了个字:“若日后本王不在,怕只有你能假冒我的字,调遣兵士了。”
他握着杯,低头看我的字,静默了会儿,才忽而笑道:“笔法娴熟,点画圆润,结构梢整,的确好字。”我本是不好意思,听他话音中打趣更浓,不禁斜睨他道:“王爷这是在夸赞自己吗?”这一句词,不敢说有九成相似,却也七八分如他了。
众人自宫门处一直围到前厅,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我挤在众人身后,不时回应着身侧人热络的寒暄和异样的眼神,却露不出一个笑脸,看到他们眼中,却是另一种味道。
李隆基扫了眼桌上的字,随口道:“是陪了两日,她不时在耳边说永安的笔法好,让我请永安教她习字,我听着烦就寻了个借口,来你这里讨杯茶喝,”边说着,边拿起了那张纸,细看了两眼,叹道,“如此正好,就拿这张去给她看看。”
每每伴驾时,我总被问起是否去永平郡王处请教,寻了几次借口再无话可说,只能挑了一日午后,去了李成器的书房。既然是皇姑祖母开了口,总要有个交待才好。
身侧都是匆匆上酒菜的宫婢,见了我躬身行礼后,又匆匆入内或是出殿。我紧盯着他,想要走却挪不开步,只能在川流不息的内侍宫婢中站着,看着他自艳红毡褥侧而来,躬身行礼道:“恭喜王爷。”
眼中不停地涌出泪,止也止不住。
我又看了李成器一眼,他似乎也在想着此事,没有说话。李隆基看看我,又看看他,最后视线落在了手中纸上:“况且,你的笔法传承自李家,为义净大师抄经也算是皇室恩赏。”
最初他将我当做什么,我还是明白的,可到后来,我和他谁能说得清呢?
李成器见我如此瞅着他,不禁微微笑起来,温和道:“那个人,是我的人。”我心中一暖,问出了另一个疑问:“既有武家诸王和太平公主的密奏,为何只是贬至同州参军?”诸位叔父的性子,历来是无用者赶尽杀绝,如此心慈手软倒让人奇怪了。
我道了声谢,匆匆自门而出,一路沿着木阶而下,脑中不停想着此句。他将此情比作妄念,深知此情是妄求,是祸事,却仍留下了后半句。我走入三层房内,透过敞开的木窗看着太初宫中的亭台楼阁,一https://www•hetushu.com•com时感动,一时又是酸楚,呆站了许久。
我虽有些心不在焉,仍注意到此中蹊跷,想了想,道:“几年前雪地跪了一夜,王爷所受的寒气可都清了?”他没有停笔,边写边道:“那一夜虽寒气入脉,却并没有什么大碍。”
我没再说什么,躬身行礼后,转身离开了两仪殿。沿着张灯结彩的回廊,出了东宫,太初宫中的不夜天,遍地喜庆的红烛,照着我的前路。
他端起冷茶,轻抿了一口,道:“此念指的是妄念,说得易懂些,便是凡夫易起妄念,但若随妄念而行,始终不能觉察,只会永在轮回之间徘徊不得出路。常以告诫世人,不怕起念,但要极早察觉灭念,才是正途。”
我盯着他,犹豫要不要问下去。武家诸王的秘奏,必然不会轻易让李家的人知道,何况此次虽有太平公主在内,却是在洛阳,而他始终在三阳宫中,三日前的事怎会知道的如此清楚?更何况是其中的隐秘?除非这个局本就是他设下的。
“王爷,快放手。”我扫了一眼四周,匆匆回头,低声提醒。殿内就是朝中众臣,殿外到处是宫婢内侍,落入任何人眼中都是隐祸。
婉儿点头,扫了我一眼才继续道:“郡主的字,有欧阳询的神韵,却更多似一个人的风骨,可算是集两者所长。不过奴婢倒以为,若要更进一层,不如选其一而行,或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李成器看他,道:“今日怎么来了?成义说你这几日都在陪王氏。”
两仪殿中数十桌宾客,众人皆是盛装出席。我这桌本是武家郡主,婉儿却特坐了来陪我,身侧的人纷纷低声议论着,不时还瞟向我,我只能佯装不知,捧着茶杯与婉儿闲话。
完婚日,是我初次踏入东宫的日子。
太初宫的雁塔,本是皇上藏书诵经所用,如今都已搬空为义净大师所用。说是抄经,其实因为义净大师译经的速度较慢,又要带着众弟子翻查大量经典,传到我手中译好的经卷极少,大多时候是清闲的。
东宫的亭台楼阁,亦是金红长烛,喜红宫灯,亮如白昼。
原来我有那么多不甘,我也是自幼听着他的事长大,无数次在心中勾勒他的模样。我没有机缘与他自幼长大,却仍是早将他放在了心里,本以为只是儿时的梦,可这数年的相知相识,他一步步走近我,我也没能逃得开,也根本没有想逃开。
入门时,李成义正在里处议事,见我后神色隐晦,草草说了两句就离开了书房。
我点点头,胸口堵得厉害,压抑了片刻,轻声道:“若是妄念,害人害己,是不是该彻底放下才是正途?”他笑意渐缓,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被他看得心痛难忍,匆匆走下两级石阶,被他一把拉住左腕。
他静看了我会儿,神色平淡,道:“和_图_书不过是常例刑罚,他还不敢对我用重刑。”我还要再问,他又接着道:“三日前,武承嗣与姑姑联名奏来俊臣数十罪行,武家诸王皆附议,不出两个月,来俊臣就会被贬至同州参军。”
礼罢他们离去,我才觉有些脱力,低声对婉儿道:“我出去透透气。”婉儿没松手,也压低声音道:“看完李隆基的礼再说,不急在这一时。”我知道她指得是什么,只能心不在焉地看了又一遍,疾步出了殿门。
我心底发凉,没有说话,由他引着又写了几个字。
他喝下手中茶,才又道:“永安,既然拿了你的字,我也回赠你个礼物。”我看他,看他漆黑的眸子,不知他搞什么鬼。
我愣了下,忙走上前两步,对李成器躬身道:“还请郡王不要嫌弃永安愚笨。”李成器笑看我,道:“郡主言重了,本王定当倾囊相授。”他伸手将我扶起,我抬眼看他,忙又避了开。
木窗半敞着,临窗的木桌上,摊开了数本梵文经卷,还有早已凉透的茶,大师垂着眼眸正在休息,我晓得自己来的不是时,正要悄然离开时,他却睁了眼,道:“郡主请吧。”
他深看着我,点头道:“多谢郡主。”我直起身,勉强笑道:“王爷怎么这么急就回来吃酒了?”身侧人躬身行礼,他颔首后,才回道:“殿中均是众臣世家,容不得分毫怠慢,”他见我不再说话,也静了会儿,才道:“你要回去了?”
我盯着茶杯,说不上是喜是悲,竟有在这红喜中置身事外的感觉。
皇姑祖母微微笑着,看我道:“婉儿说得对,永安,你是何时起习成器的字的?”我忙回道:“幼时习太宗皇帝笔法时,先生就曾夸过永平郡王最得真传,前几年见了永平郡王便讨了几张临摹,”我恭敬看了一眼李成器,笑道,“不过是皮毛,哪里有上官姑娘所说的风骨。”
最后那一拜,他就面对着我这处,看着元氏向他盈盈拜下,广袖及地极尽礼数,他意外静立了片刻,才搭起手,回了一礼。
我耳中是她的话,眼却再也挪不开,只怔怔看着中庭身穿绯红礼衣的两人。从未穿过红衣的他们,一个是皎如明月夺人眼,一个是漂亮的雌雄莫辩晃人目,在众人的恭贺声中都带着浅笑,不停地颔首回应着。
他的呼吸声就在耳边,酥麻温热,将所有的伪装都化了去。我盯着纸上的字,想起昨日婉儿的那句话,低声道:“元氏的字颇得皇祖母赞誉,恭喜王爷。”他淡淡地嗯了一声,道:“她得北魏元氏真传,儿时又有章怀太子的点拨,的确在笔法上胜于寻常人。”
众人随着皇姑祖母又闲聊了片刻,沈南蓼请安入内,例行把脉。婉儿便带着我们退出了凉亭,一路说笑着将我送回了宫中。
我擦干净脸颊,走近雁塔,守门侍卫略有怔愣,待反应过来才躬身行礼,让出了和-图-书路。
义净大师浅笑看我,道:“郡主见过此句。”我点点头,静等着他。
我脸一热,想起和他共写的那几个字,更是心猿意马的,只随手拿起桌上的书翻起来,却不过是摆个样子,半个字也没看进去。
李成器淡淡看了我一眼,竟亲自挽袖研磨,道:“你若再不来,我只能遣人去请了。”我听他这话坦然,真像是拿了师傅的身份,一时不知如何答话,只能讪讪一笑,走到了桌边。他自架上挑了笔,沾了浓墨,又将笔括干些,递给我道:“写几个字我看看。”
他是想借此事拖延婚期。皇姑祖母素来信佛,不惜耗资在各地修建佛龛寺庙,若是我能以皇室身份译经,也算是代皇姑祖母敬佛了。如此事,本是李家皇室出面最好,只可惜这等露脸的事又怎会让李家人出面?
李隆基不知何时来了,正抱臂靠在门边,笑看我道:“这么算来算去的,本王倒和来俊臣攀上亲了,”他边说着,边走进来,道,“我也是前几日才知道,皇祖母赐婚王氏是有安抚的意思。”
我常在塔三层独自坐着,只有偶尔看不懂一些经文时,才上到七层与义净大师请教,连带着闲说上两句。大师经二十五年,游历了三十多国,自然见识甚广,每每听到兴起时才被几个弟子提醒,匆匆告辞。
他眼中的苦意,渐化在微笑中,再没有半分温度。
他叹了口气,半笑不笑道:“听下去就明白了。”我拿书敲了敲桌子,示意他继续。
我站定了身子,再不敢看他,笑着对李成义,道:“二王爷今夜可是两个新郎的傧相,快进去陪客吧,永安回宫了。”李成义若有所思看着我,点头笑道:“郡主说的是,殿内已吵闹着要与新郎吃酒,我这才寻了出来。”
忽然,身后有人轻叩门,低低地唤了声“永安”。
李隆基哼了一声,道:“最多一年,我要让来俊臣在洛阳城身首异处,任百姓踩踏尸身,”他顿了下,又补充道,“当初天牢内他对大哥用的那些,我要一个个在他身上加倍讨回来。”
这一日,我又拿着新翻好的经卷上了七楼。
他有意放缓了声音,一字一句道:“本王趁此机会对皇祖母说,永安郡主素来喜好读书,如今义净大师带回这四百多部经书,必是需要人手译经,倒不如让永安去试试。一能全了皇祖母对佛家的重视,二是能全了永安郡主的心思,三能在日后为本王增些颜面。毕竟是日后的临淄王妃,若能陪在义净大师身侧一年半载的,也是诚心,也是荣耀。”
坐上太子李旦频频颔首,面带平和的笑,李成器亦是微微笑着,眼眸深的望不到底。
我看着他,琢磨他这番话,渐明白了意思。
刚迈出殿门,就见他自远处走了回来,依旧是绯红礼衣,猩红刺目。
一道道俗礼,在通赞一声声的话中进行着。
身为武和*图*书家人,又是李家日后的媳妇,的确我是再合适不过的。
皇姑祖母,道:“永安既是李家的媳妇,就不要学欧阳家字了,”言罢,又着看向我,道,“永安,还不快拜师?”
婉儿轻捏了下我的手,道:“你先被赐的婚,却是侧室先进的门,宫中人的议论可不是那么好听的。”我无奈,道:“不用你说,我也猜的到,必是临淄郡王不满意与武家的婚事,借口先娶了王氏入门,独宠在先。”婉儿轻耸肩,亦是无奈一笑。
夏日将尽,秋暑却极盛,我被他握着的那只手隐隐冒汗,他的手心却始终冰凉着。
今夜的话,虽是脱口而出,却并非意气用事。如今宫中的局势比过去更复杂,叔父武三思虎视眈眈王位;朝中竟也有人奏请要立皇太女,太平公主素来自视甚高,又在此微妙的时候为皇姑祖母献上新宠张昌宗,是何意图不言而喻;因来俊臣被贬,李家旧臣又再次掀起风浪,将本是韬光隐晦的太子推上了争议之处。这一层层这一步步,不知要走到何时算是结束,而他要顾虑得太多,年少情意又能走多远?
我不停在心中想着,给自己讲着一切的道理,经书却越抄越乱。
我被他吓了一跳,却也被这话点醒,再看他佯作无奈的神色,不禁嘲笑道:“倒也是,你虽不能做和亲的公主,倒也可以做安抚人心的女婿。”
他没有答话,也没有放手。我伸出右手,使劲去摆脱他的手,正在挣扎不开时,李成义已揽住他的肩,笑道:“郡主走路小心些,好在大哥扶了一把,否则不是要在这大喜日子跌伤了?”他说话间,李成器才缓缓松开了手。
皇姑祖母果真应了李隆基的奏请。
封禅的日子临近,皇姑祖母的心神越发清朗。
皇姑祖母自婉儿手中抽出纸,对李成器道:“成器,朕为你寻了个好学生,不知你可愿倾囊而授?”她将手中纸递给李成器,李成器躬身接过,看了两眼,才微微一笑,道:“孙儿只怕教了徒弟,会饿死师傅。”
我忙走过去,草草将不懂的经文问了,正要告辞时,却扫见桌上他随手写下的经文,竟有熟悉的句子,不禁细看了眼,果真是那句‘不怕念起,唯恐觉迟’。我犹豫了下,低声道:“大师,可否为永安讲解下此句?”
“因为来俊臣的夫人是太原王氏。”答话的竟是门外人。
忽然,众人纷纷起身,向中庭望去。我心中一空,猜想到是谁,正不愿起身时,却被婉儿一把攥住腕子,将我硬拉了起来:“若不看,倒真会落人话柄了。”
在今日前,我从不敢在众人面前看他,唯恐落了把柄。而今日却也不敢看他,红色的毡褥自宫门一直铺到殿门,他亲自走到喜车前,向着下车的人伸出了手,那细白小巧的手就被他轻握在手心,一路踏着毡褥走到殿中,绯红礼衣和青绿礼衣,相得益彰。
待走到三
www.hetushu.com.com层房内,一侧内侍点了灯烛,见我的脸色,没敢说什么就退了出去。我坐在书案后,对着经卷,怔怔出了会儿神,才研磨提笔,继续抄经。
我沿着一路红烛,竟没有回宫,而是到了雁塔,因两个郡王的喜事,此处更显得安静。六层七层仍是燃着灯烛,这些早堪破尘世的出家人仍是在译经抄经,此时看来,却与这宫中的喜气格格不入。
我本是笑着,听他这话立刻看了李成器一眼,能让李隆基时隔多年仍记恨的,必是当日的刑罚触目,可他却仍轻描淡写,不肯说半句……李隆基似乎提起此事仍有恨意,走到桌边,倒了杯茶捏在手里。
我心猛烈地跳着,下意识深吸了一口气,移开了视线。
我细想了片刻,道:“叔父已常年在家,不问朝堂事,为何这次会忽然出了声音?”李成器自我手中抽出笔,放在一侧,道:“因为有人告诉他,来俊臣此番要诬陷谋反的,就是他。”
他盯着我看了会儿,才忽而一笑,道:“今日在皇祖母身旁听了个消息,义净大师已抵洛阳,自海外带回了四百多部经书。”他说的没头没脑的,听得我更是糊涂,只能道:“在你我未出生前,义净大师就已出海,如今能全身归来的确可喜可贺,可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日是碍于众人的面,不敢以惯用的来写,今日独有我和他两个,我却再不能以欧阳询的笔法掩饰,可若真落了笔……我看他闲适地笑着,在一侧自倒了杯茶握在手中,更有些不自在,只能随意在纸上写了句词。
我轻攥着拳,脑中不停闪现过去几年,那少得可怜的每一刻相处,身上又冷又热的,不停冒着虚汗。婉儿攥着我的手腕,看了我数次,却没有说一句话。
那日,纵隔着衣衫也能摸到深浅的伤痕,竟没有一处是完好的。可我却不敢深想,来俊臣牢里的刑具万千,种种酷刑,备极苦毒。他虽是皇孙,却以谋逆罪落了牢狱,能保得脸面上的干净已是庆幸,身上暗处受了多少刑罚,谁又会管?
婉儿有意隐去李成器的名字,可皇姑祖母又怎会看不出?
我接过笔,刚要写就停了下来,竟有些不好意思。
太子的几位郡王早年出阁,各有府邸,却因如今被禁足而长居东宫,只能自太初宫外走个过场,傧相迎亲,新娘接到宫中算是入了门。一切婚事皆按皇室例,那一夜,整个太初宫遍地红烛,彻夜不息,照得夜空如晚霞披挂,华美非凡。
我向前慢步走着,一时又哭又笑的,哭自己竟说出口是心非的话,却又笑我高估了自己。我以为我起码能做到笑着应对,这几个月我不停告诉自己要接受,我以为我日日对着经卷起码平复了一些,可在见到他还礼对拜时,一切的以为都瓦解了。
婉儿抿唇笑了片刻,才接着道:“永安郡主的字,奴婢也不晓得如何评了。”皇上不以为意,道:“但说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