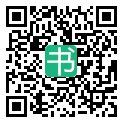第一卷 那一夜,命犯桃花
第七章 初生劫
视线扫过太子身侧,李成义正斜靠在案几后,亦是颇有深意地对我遥一举杯。
已经一天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敢说此话,亦不知会有什么后果。
一句话,恍如惊雷,震得我答不上话。我本以为我思虑的足到,连婉儿也不曾知那件事,如今才真算是明白,在这大明宫中,没有皇姑祖母看不到听不到的。
我只跪地听着,不敢抬头,亦不敢回话。皇姑祖母说的竟是婉儿。
皇上看着她二人,神色出乎意料的平静。
“你让朕想起了一个人,”皇姑祖母的声音在头顶响起,夹带着几分疲累,“七八年前,她也是如此跪在这里为朕的儿子求情,过了这么多年,依旧每逢腊月就告病,提醒着朕当年的丧子之痛。”
“抱歉,”我道,“此事也牵连到了你。”
李成器沉吟片刻,道:“孙儿并未见奏章,不敢妄言。”皇上拿起奏章,道:“细细看吧。”李成器躬身接过奏章,细细看着,殿内静如无人一般,无人敢动上半分。
“腊月一过,你就十三岁了,”婉儿捂着茶杯,道,“寻个机会出宫吧,虽然我舍不得你,却想让你远一些。”
我随她二人入了殿,却觉四下安静的有些怪异。论理我来得并不晚,却仅有太子妃和德妃在,并未有其它宫中的人来贺年。行礼问安后,皇姑祖母招手示意我到身前,我忙上前立在了婉儿一侧。
皇上淡淡,道:“东宫乃是太子居所,株连就免了,去查吧。”婉儿忙躬身道:“是。”她接了旨,只看了我一眼就要出殿。
他话音未落,身侧李成义与李隆基已砰然下跪,道:“请皇祖母名查,大哥绝无谋反之心!”
我紧咬着唇,眼前已一片模糊,却不敢发出声音。谁也不能知道,哪怕是宜平,知道只有死路一条。可东宫两位妃子自大明宫中消失无踪,又怎么瞒得住,难道就像太子妃和德妃甘愿受死,他们也要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就任由自己亲生母亲凭空消失?
我看着一心赴死的太子妃,竟像看见去年长生殿外跪着的永平郡王。一样的目光淡漠,如同看透了自己的命运,坦然平静。
我盯着她,脑中还记得方才殿前的温和笑语,岂料入了殿她就走入了死境。此时此刻,只有她认罪才能唤回东宫的生机,她没的选,只能认罪。不管是剐刑还是狄仁杰狱中那些让人彻骨惧怕的刑罚,她都只能去受。素来不出东宫的太子妃,与太子朝暮多年,自皇后位退让到太子妃,仍旧没有换来皇姑祖母分毫的怜悯,最后还是一死,死在最严酷的刑罚下。
太子偶尔来蓬莱殿,皆是陪皇姑祖母聊上几句便告退,倒是几个郡王呆得久些,皇姑祖母或有意,或是无意的总和他们说些政事,即便是李隆基小小年纪也答得极妥帖。
她走入殿内仍是神色倦倦,对李成器等人行礼道:“皇上此时正在见狄仁杰,几位郡王先回东宫吧。”她说完忙走向我,没说话,伸手把我扶了起来。
而如今,我看着她那张与永平郡王有五六分相似的脸,竟不觉有些慌乱,忙行礼道:“太子妃。”她轻点了点头,看了一眼韦团儿,韦团儿忙笑道:“这是永安郡主。”
没想到自重阳节后,大明宫中始终雨雪夹杂,四下里皆是湿漉漉的。
我忙拿起最后一个奏章,打开先扫了一眼,立刻如被人抽了周身之力,狄仁杰,是狄仁杰谋反的奏章!我手捏着奏章,深吸口气想念,却不敢出声。
那是他的母妃。是我亲眼见她的母妃被逼认罪,却连一句话也不能说。
玉盘上放了个制作极精巧的木头人偶,太子妃没敢拿起,只细看了一眼便脸色瞬间惨白,与德妃对视一眼,没敢说话。
武承嗣的声音又道:“人不风流枉少年,看来本王是扰了小王爷雅兴了。”李成义畅快一笑,回道:“无妨无妨,本王早有意向永安郡主讨人,只是郡主不嫁,总不好先嫁了贴身的宫婢。”武承嗣又随意说了两句,听声音是离开了。
在今夜之前,我从未如此看着人从生到死。我无法想象那如水墨晕染的太子妃,如何能经历剐刑的痛苦,被人绑在竹槎之上磨掉皮肉,只剩下淋淋白骨后再杖毙致死,只如此想着,我就已经喘不过气,手扶着地面屡次想起身,却没有半分作用。
皇上目视着二人的离去,才深叹了口气,道:“既为朕之儿媳,又何必想要致朕于死地。”她眼中冷意渐散,倒多了几分萧瑟,按揉着太阳穴,接过韦团儿手中的热茶,道:“永安,你既有心嫁李家人,朕不希望将来https://www•hetushu•com.com你也有如此怨恨。”
我忙低头,道:“皇姑祖母不是要听奏章吗?永安这就给您念。”
我听她一句句说着他,心中隐隐猜到了一个人。七八年前,我尚是几岁的孩童,而婉儿也不过十六七岁,护着的不论是李弘还是李贤,都最终是个惨淡的往事。
我攥紧她的手,汲取着她身上的温暖,过了很久才缓缓松开:“没什么,太冷了。”
皇上深深打量她二人片刻,才道:“团儿昨日给朕看了些物事,朕颇觉有趣,”她边说着,韦团儿已托着个玉盘上前几步,给她二人细看。
我恍惚着起身,本就是和衣而睡,只是发髻有些乱,宜平替我理了理,拉开了帏帐,我走出去,明知道他们就在外间,却不敢走出一步,直到宜平收整完出来,见我还愣着才压低声唤我,我茫然看她,恍惚一笑向外间走去。
李成器微蹙了眉,我也听出那说话的正是李成义。
我不信凭着当年的婉儿的记忆,或是如今我这一跪能让她改变心意,毕竟不是砸碎了碗碟,而是要篡谋帝位。狄仁杰谋逆一案定是到了我们都不知晓的地步,而这才是真正主导皇上没有追究的原因。
我又呆了良久,才猛地清醒过来。他们从不曾到我这里来过,今日今时,肯定是为了昨日的事,已经三十多个时辰了,他们一定知道我昨晚也在嘉豫殿,推测我见过太子妃和德妃,终是顾不得避嫌来问了。
我被这一句句话浸的冰凉,没有答话。
皇姑祖母,道:“朕不想太子知晓今日之事。”
因无常天气,婉儿染了伤寒,我便接了替皇上研磨的活。婉儿在时,大多诏书都亲出她的手,如今只能由皇姑祖母亲自起笔,只有疲累时才由我来念奏章。韦团儿始终待我和颜悦色,毕竟我与她从无交恶,我对于她就是个不得宠的王爷之女,平日受皇上宠爱多了几分。
我静看着她,她随手倒了杯茶,递给我,道:“你皇姑祖母本就多疑,若让她知道身边人也被拉拢,甚至不惜以命相保,岂不更让她忌惮?”
我听得有些无措,却不敢贸然告退,最后还是太子妃点了点头,让我走了。
婉儿自倒了杯茶,坐起来,认真道:“这样才好。这宫里谁不在算计?能让皇上看得到你的算计,她才会放心,那些看不到的才是她最忌惮的,”她喝了一口茶,叹道,“永平郡王若是有一两点错处就好了,也就不会做了众矢之的。”
我嗅到他身上清淡的菊花酒味,不禁笑道:“没想到王爷也即兴喝了酒。”他低头看我,平和道:“皇祖母都喝了两杯,我又如何逃得过,好在酒量不算太差。”我难得听他话中有玩笑口气,不禁笑出了声:“听王爷说话声音是没变。”他嘴角浮着一丝笑,道:“我很清醒。”他说完后,没再继续。
“来俊臣的奏章你都看完了?”
他愣了一下,咬着牙看我,竟怒火烧心的说不出话来。
皇姑祖母扫过三人一眼,对李成器道:“成器,此事你如何看?”
我又一磕头,道:“凤阳门一事永安假传谕旨,求皇姑祖母降罪。”
婉儿笑着看我,等着我将所有都想明白,才道:“不过你这一跪也好,将皇上对你凤阳门一事的疑心揭了开,否则你不知她的心思,我始终被蒙在鼓里,而仅有她一人带着那疑心始终观察你的举动,我光是想想就后怕。”
我听他们说着孔子,又说到周公的追封,不觉有些走神,想起方才皇姑祖母的话就心中大力跳着。若非韦团儿忽然打断,他会不会当即请皇姑祖母赐婚呢?自重阳节后已数月,叔父先被罢相,太子诸位子嗣又受召越发频繁,朝中宫中都因此而起了微妙的变化。
这一言后,我头抵地面不敢再有任何话。
太子妃和德妃砰然下跪,头抵地面颤声道:“母皇明鉴,东宫内绝无人有如此恶毒之心。”
待回了宴席,李成器正被众人围住,我诸位叔父亦在其中。皇姑祖母笑吟吟看着,和太平低声说着什么,太平盯着李成器亦是含笑点头。我如此看着,只觉得长寿年似乎是个吉祥的年头,自打入宫后还是头次见李姓皇族如此一派和乐。
殿中的宫婢见我如此,想上前扶却被我一把推开,终于撑起身子站了起来。待回到宫中时,宜平本是笑着迎上来,见我却瞬间变了脸色,道:“郡主怎么了?怎么脸色惨白惨白的?”
“臣,臣,”我脑中翻卷的都是上元节那句话,还有殿前李成器和狄仁杰所说的,竟觉得和_图_书眼前字皆模糊,不敢再念下去,忙跪地,道:“此奏章事关重大,永安,永安不敢念。”
殿内又陷入了沉寂,只剩下火盆中轻微的噗呲声响。我紧闭着双眼,等着皇姑祖母的暴怒,等着一切想到的和想不到的责罚。
我本在猜测此是何物,听这话才猛地明白过来,韦团儿,韦团儿还是下手了!即便是太子妃亲自示好,她还是布下了局!
不过短短时间,我已觉背脊尽湿,连呼吸都觉得吃力气来。
帐外人影走开,我才渐觉得困,迷迷糊糊趴在了床上。大片浓郁的黑暗中,只有太子妃温和的笑容和平静的目光,渐渐地,这目光添了几分暖意,远处永平郡王站在雪地里看着我,只静静地笑着,张口对我说了句话,我却半句也听不清,只急着往前迈了一步,问他在说什么,他却摇了摇头没再继续。他越不说我越急,就这样一步步想走近他,脚底冰凉凉的,像是被雪浸湿了鞋,如那夜长生殿前一样,仓皇地绊了一下,险些摔倒在地。
我没应声,和她都沉默下来。
我倚靠在她身边,手揉着膝盖出神。
到嘉豫殿前时,正遇上太子妃和德妃,我忙躬身行礼。太子妃笑着对德妃,道:“这是永安郡主,我正想哪日寻个机会和母皇讨来做儿媳。”德妃眯起漂亮的眸子,笑道:“姐姐好福气,隆基还小,若要赐婚还要等上一两年呢。”
熏香仍蔓延着,我亦是跪在龙椅一侧,不敢去看那几个人的神情。
难怪,他那日会嘱狄仁杰认罪,我竟没想到皇上有此赦令。
“成器过年也十七了,”皇上颔首看一侧的李成器,道,“太宗皇帝十六岁与文德皇后完婚,你一转眼也到了娶妻的年纪,可想过此事了?”
我强忍着心中悲痛,低头回道:“无论将来婚配何人,永安始终是武家人。”
宜平没敢多说,扶着我坐到床上。我仅剩了些镇定,挥手让她放下帏帐,自己哆嗦着手放了床帐上了床,抱着膝盖缩成了一团。这里再没有外人,只有我一个,可外边的宫婢还在来回走动,低声交谈着明日早膳。
恍如巨石砸下,轰然一声巨响,我脑中已尽是空白,只猛地抬头看他。他仍神色泰然地直身立着,眼中坦然平淡。
我隐隐听见二人说什么纳妾室的话,正便想自另一侧离开,岂料她听见声音回了头,竟是太子妃。我只在入宫那一年的正月见过她一次,之后她始终告病未露面,皇姑祖母显是对这儿媳并不上心,只偶尔与太子闲话时提上一两句而已。
我双腿早已跪的没了知觉,见李隆基目光灼灼地盯着我,忙侧头避开。皇姑祖母的话很明显,李隆基在几个儿孙中颇得她欢心,又非太子长子,与帝位相去甚远,自然是个安身保命的依靠。可难道在她眼中,我真就算计了一个十岁的少年?
“郡主,”宜平在身边叫我,“郡主,郡主。”
我每听到她说来年,就总记起婉儿的话,若要出宫并不难,只要父王来求皇姑祖母也不会强留,可是,我却不愿再深想下去。
身后人先轻关上木门,又关上了阁门,静守在阁外,两门之隔,仅剩了我两个。
皇上冷冷看着众人,沉默了良久,才道:“你既要自证清白——”她说了半句,略顿了一顿,似乎有些犹豫。我心头顿时如刀剜一般刺痛难忍,竟不知死活地磕了个头,抢言道:“永安郡王乃是皇孙,若是与谋逆之臣同刑审理有辱皇家威严,请皇姑祖母三思。”
她点点头,拿了热湿巾替我擦脸,低声道:“三位郡王在外头。”我心大力一抽,又喘了几口气,才镇定下来:“什么时候来的?”她轻声道:“刚来半个时辰,郡主睡了一天,已经过了晚膳时辰了。”
我尴尬起身,太子妃才温和道:“入殿吧,别让母皇等太久。”
“永安,抬起头看朕。”皇姑祖母命令道。
韦团儿见此状忙笑道:“年纪小面皮薄,皇上如此直问,让郡王如何说?”皇上温和一笑,点头道:“团儿说的是,”皇上笑了笑,忽而侧头看我道,“本还想问问永安,看来女儿家更不敢回话了。你们都该学学太平,若是有意就私下告诉朕。”
那日后,皇姑祖母恍如无事一般,只偶尔提起狄仁杰已被贬为彭泽令,竟和我谈论起一年多前那拜相的宴席。我谨慎回着话,偶尔能自皇姑祖母的眼中看到些遗憾,叔父武承嗣屡屡进言要诛杀,她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直言不再提及此案。
“丑时三刻,”宜平想了下,道,“好在我睡得不实。”我愣了一下hetushu•com•com,不解婉儿为何深夜来遣人传话:“还说什么了吗?”宜平摇头,道:“没了,就嘱咐郡主,今日是各宫人贺年的日子,千万别去晚了。”
皇上笑了两声,没再继续这话题。
我犹豫了一下,才道:“皇姑祖母为何今日不当场治罪?”
终于,皇姑祖母伸手拿过奏章,随意放在了桌上,道:“起来吧。”我忙起身垂头立着,就听见她又道:“今日拿这奏章,就是为了听听你们的想法。这是来俊臣奏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的奏章。”
我自桌上拿起奏章,一本本挑来读,皇姑祖母端着茶杯细听着,偶尔颔首却不说话,总到念完才持朱笔画敕,放到另一侧。只到追封孔子为隆道公的奏章时,才略停下与李成器和李成义说了两句。
“永安,继续念。”皇上忽地看我。
我终于抓住了什么,睁开眼,从一片模糊到清楚,才见她坐在我面前,被我紧攥着手腕,捏出了一片紫红。我深喘了几口气,松开手扶着床坐起来:“没什么,是噩梦。”
当年入宫前心中的悸动仍在,皇姑祖母像是儿时的一个传说,身为女子登上帝位,将武家带入了无上尊崇的大明宫,与李家比肩,这是何等厉害的人。今时今日在皇姑祖母身侧才知道,那是用一个个仇恨和鲜血换来的。谋逆帝位,这个罪名曾有多少人担过?都是最亲近的人。
我的手早就冻得冰凉,他也好不到哪处,却轻握着我,道:“既然怕冷,为何还要到此处吹风?”我抬眼见他微微的笑意,竟有些不好意思,想抽回手却被攥的更紧,不禁急道:“王爷,若有人看见终是不妥。”他道:“无妨,有何福在外守着。”
我正接过韦团儿递来的茶杯,心头一跳,手臂僵着将茶杯放在书案上。李成器竟意外沉默了片刻,没有即刻回话。
殿内诸人本是笑着,见我如此却都觉有异,不禁皆是色变。
我别过头去看曲江,方才满目簇黄,如今再添了淡淡的馨香酒气,重阳的味道也渐浓了起来。手渐被他握的热了些,竟觉有些潮汗,下意识低头去看,他的手干净修长,连关节处都极漂亮,只如此看着便能想出他执笔吹笛的模样。
婉儿侧头看我,道:“你是想问我,狄仁杰的谋逆一案到底如何了,对不对?”我点点头,等着她揭开这隐秘,婉儿撑着头看我,道:“此案我也不知情,是你叔父武承嗣亲自和来俊臣审理的,不过方才皇上既然已宣狄仁杰入宫,十有八九是要赦了。”
我不敢想象皇姑祖母会如何说,如何做,只紧闭着眼低下头,不敢再看。就凭着韦团儿的话,皇姑祖母难道真会相信?没有半点怀疑?东宫住着的不只是太子,还有诸位郡王和公主,不只是太子妃和德妃,还有诸多女眷。
“永安?”皇上催促地唤了我一声。
我点点头,总觉有什么,看了一眼白茫的窗外,却又想不分明。
皇上看了我片刻,道:“朕若想降罪,就不会留你到今日。”她说完,站起身向殿外走去,韦团儿忙跟了上去,留了一地跪着的人。
二人又同一叩头,起身随着婉儿而去,方才站在嘉豫殿前的温言软语还在,此时却已经是生命最后一程。太子妃眼中异常沉静,倒像前方等着她的不是剐刑,而是在东宫久候的太子殿下,和她那个被众人称颂的儿子。
皇上冷眼看着她,道:“你与德妃平日总在一处,此事可与她有关?”
忽然,听见阁外有声音问:“可见到永平郡王了?”守着的小太监何福回道:“回周国公,小的也在寻王爷。”那声音又道:“既要寻就快些,在此处耽搁什么呢?”
我抬头看李成义阴着脸坐着,李成器本是在宫门口背对着我,此时也回了头,他右手紧扣着宫门,像是要深深嵌进去一样,那双眼中密布着蚀骨的悲痛,浓郁的让人窒息。
太子妃抬头,白皙脸颊上划过凄绝的血痕,声音已涩如饮毒:“全部都是臣媳一人所做,与德妃没有关系!”她说完,又一重叩头,背脊挺直,跪立在殿中。德妃跪在一侧,从未抬过头,单薄的背脊深弯着,双手紧扣着地面,十指泛白。
太子妃笑看我,道:“没有那么多礼,”她侧头对韦团儿,道,“总听说母皇很喜欢这个侄孙儿,可曾有赐婚的意思了?”韦团儿摇头,回话,道:“今日还提起过,小郡主面皮薄,给搪塞过去了。”
“我随口抱怨的话,你不必当真,”婉儿吹着hetushu.com.com杯中茶叶,笑道,“方才皇上的确大发雷霆,说我每逢腊月他的祭日就告假,这么多年还放不下心中怨气。我是放不下,放下了有什么好,皇上肯定又会想,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就轻易放下了呢,肯定暗中还在恨着。”
待婉儿来时,已过了数个时辰。
我忙伸手想扶住什么,却什么也抓不到,猛地叫了一声就摔在了地上。
皇姑祖母冷冷道:“你既已认罪,就是不想牵连太子及朕的皇孙,”她看德妃,道,“德妃,抬起头。”德妃抬起头,看着皇姑祖母。
我此时才明白过来,李成义竟是和宜平在此楼的另一处,却不知他为何会突然出现,解了我们的困境。待门外再没了声响,李成器才示意我在此处留上片刻,他则开了门,穿过阁厅,带何福先一步离开了。
我不敢抬头,将奏章举过头顶,不敢再出声。皇姑祖母知道这奏章的内容,竟还让我当众念,究竟是何意?我来不及深想,已是周身冷汗,努力压制自己的情绪才能让手不再颤抖。
太子妃和德妃起身,却并未被赐座。
皇上看他,缓声道:“你可知牵涉谋反一事,朕从不姑息,到此时你还要为狄仁杰说话吗?”李成器缓缓跪下,直身回道:“无论是何人,牵涉到谋反一事均要详加审讯,皇祖母若认为孙儿需如此证明清白,孙儿自请入狱待查。只是此奏章上涉及诸人,皇祖母仅问狄仁杰一人,而孙儿也仅是对狄仁杰一人而发此言论。”
楼上的恭贺早已一浪高过一浪。
皇上见她二人神色,道:“此物是东宫内的宫婢发现,交给团儿的。上边的生辰倒真是朕的,只是不知东宫内是何人如此恨朕,要作蛊行法才能消去心头怨气?”她的声音淡漠平缓,却透着丝丝阴冷。
婉儿始终拿帕子掩着口,轻声咳嗽着,直到把我带到她住处才停了声。
我抬头看她,那双描绘的极冷冽的眼中,没有笑意亦没有怒意:“半年前凤阳门一事,你不惜冒死去阻拦隆基,今日你更跪地为他的兄弟求情,难道朕这几个儿孙里,你竟看上了一个小你三岁的?”
宜平在外轻唤时,我才出声道:“很累,让我再睡会儿。”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宜平显是已听出什么,犹豫了一下,道:“郡主可要唤太医,听声音怕是昨夜冻着了。”我也觉得喉咙生痛,可不想见任何人,只道:“是太累了,睡会儿就好。”
刚才迈出门,就有个人影冲上来,紧紧攥住了我的手臂,李隆基赤红着双眼盯着我,过了很久才说:“告诉我,太子妃和我母妃去哪儿了!”我被他捏得生疼,却恍惚笑着,说:“郡王怎么看着这么憔悴?出了什么事了?”
太子长子本就是众矢之的,有错便是死,无错也是藏着祸心。
我尴尬笑笑:“这一跪,算是落下了算计的名声了,被算计的还是十岁的临淄郡王。”
皇姑祖母静了会儿,才淡淡地道:“是,你和她们不同,你是武家的人。”她说完,便放了茶杯默然而去,我跪地目送她离开后,才发觉身子早已瘫软,没有了半分力气。
大明宫中曾有皇子谋反,亦是流放处死,何况他一个皇孙。我跪在地上,不敢想象此事竟能牵扯到他,更不敢去想之后的结果。只觉喉中鼻端酸涩上涌,眼前已是一片白雾。
但无论是哪个,都会牵连到整个东宫!
太子妃柔和看着我,眼中闪闪烁烁的添了几分暖意:“起来吧,还是入宫那年见得,这一晃就快三年了,模样倒有些不一样了。”我起身,道:“刚才天暗,一时没看出来,还请太子妃恕罪。”
皇上静默了片刻,对婉儿道:“婉儿,命人太子妃与德妃带走,今日之事不许有任何人再提起,否则一律以剐刑论处。”婉儿忙跪下领命。
我听她二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似是极相熟,却不像婉儿说得那么微妙。细细想方才出门隐隐听到的话,难道是太子改了主意,亦或是太子妃想要成人之美?那纳妾的话想必说得就是韦团儿了。
一时间江上都飘荡着万岁的声音,朝拜如斯,帝王天子。因这朝贺的声浪,紫云楼也渐沸腾起来,我和他静立着,享受着喧闹中的寂静。
曲江畔传来几声欢呼,随之蔓延开来,似是有人已去传了皇姑祖母的旨意。
她说的不假,亦是针针见血,方才我情急下也想着能让皇上哪怕多犹豫一下,记起那是自己的嫡亲的孙儿,说不定还有回旋的余地,却忘了我是姓武的人。
此时,早已软在地上的太子妃忽然抬起头,颤声道:“等等,”她紧咬着嘴唇,眼中已和*图*书是一片枯死,“母皇无需查了,臣媳认罪,此事与他人无关,是臣媳一人所做。”她说完,头重重叩地,一声声回荡在殿中,不消数下就已额间渗血,自眼上滑下。
“婉儿,此事当如何?”皇上忽然道。
殿内四周的火盆烧得正旺,将绵延大明宫中的湿气都蒸散,一室温暖如春。
“我十七岁时也如你一样,为了李家人跪在了同一个地方,”婉儿轻声道,“今日瞧见你,才真觉得当时真是傻,那是她嫡亲的儿子,她都能起了杀意,添我一个又何妨?本以为那一跪哪怕能让皇上多想上一刻也好,就有回旋的机会,可不料却是火上浇油。”
皇上颔首,道:“除了朕刚才说的人,来俊臣还提到了谁?”李成器默了片刻,平声道:“除以上诸人,来俊臣还怀疑孙儿参与此事。”
德妃手又扣紧了些,极其重地磕了个头:“请母皇赐臣媳一死。”她说完,并不像太子妃一般坦然,而是目光灼灼地盯着皇姑祖母,眼中有怨有恨,有不甘亦有讽刺。
宜平边仔细替我系好袍帔,戴好风帽,边道:“上官姑娘昨日深夜遣人来传话,说她今日会早些到嘉豫殿,让郡主自行去就好。”我嗯了一声,道:“什么时辰来的?”我昨晚睡得极晚,她竟更晚?
“你这一跪,算是把我也牵连了,”婉儿笑笑,拍了拍卧榻,道,“坐过来,我和你说几句话。”我走过去坐下,膝盖疼得不禁抽了口冷气。
婉儿住的地方挨着韦团儿,我本想避开那处,却没料一出门就撞见了个女人在和韦团儿说话,她穿着件月青色宽袖对襟衫,臂间斜斜搭着鹅黄披帛,衬得眉目祥和可亲,宛如水墨中走出的人。
竟是叔父,我抬头看李成器,见他虽面色淡然,眼中却已有些暗潮涌动。外头的何福似乎也不知如何答话的好,我紧揪着一颗心,在想着是不是要自己先出去解围时,就听见另一个熟悉声音道:“何福是我叫来的,周国公若要遣他寻人,尽管使唤便是。”
皇姑祖母心境好时,还会问些我前两个月收的琼花果实,笑颜我若是来年能种出新苗,便留在宫中御花园,专守着琼花也好。
他收起奏章,躬身放在台上,恭敬道:“依皇祖母先前的赦令,凡谋反者,一问即认罪者可免一死。如今狄仁杰既已认罪,孙儿以为可从宽免去一死。但谋反一罪事关重大,必要详加审问,不可姑息一人,亦不能冤枉一人。”
我将锦被拉起来,裹在身上,就这样脑中白茫一片,怔忡着坐到了天亮。
我猛地睁开眼,耳中已是阵阵蜂鸣。韦团儿布下的局,绝对不是针对一两个下人,只要此事查起,便是整个东宫,无人能脱开干系……我如被人拿刀一下下剜着心口,痛的难以自已,却不敢动上分毫。
我豁然开朗,皇姑祖母不过是要探一探那几个郡王,其实早有决断在心。她还是在试探,永平郡王在太初宫雪地所跪的一夜没有任何好转,自凤阳门起,抑或自我入宫前,还是根本就从李贤死,李显流放起,太子及诸位郡王就已成为她最不信任的人。
大明宫中雨雪始终未停,待到正月初二终是来了一场大雪。
他虽说得有礼有节,但却是在为狄仁杰保命,此种意思任谁都能听出。我紧攥着手,偷见皇姑祖母的脸色,不辨喜怒,连眼神亦是沉隐着。
婉儿忙回话,道:“遣人彻查东宫,寻出作蛊的真凶,严加考讯。”皇上点点头,道:“若是诅咒的是朕,当以何刑裁制?”婉儿顿了一下,道:“以前例来说,主谋当以剐刑论处,从犯以车裂、腰斩为佳,凡涉案者皆应株连。”
太子妃似乎并不知方才蓬莱殿中的惊魂一幕,只笑了两声道:“多乖顺的孩子,本宫倒是看着喜欢。”韦团儿看了我一眼,陪笑道:“几个郡王都可娶妻了,太子妃若是喜欢,不妨在皇上那处说上两句,皇上必会成全的。”太子妃笑着看我,没接话。
他二人这一跪,殿内众人皆仓皇下跪,头抵地不敢出声。
李成器恭敬回道:“孙儿都看完了。”
皇姑祖母有意看了我一眼,才转头去看太子妃和德妃,道:“都起来吧。”
李成器、李成义和李隆基一听,立刻起身静听,脸上均是震惊异常。
“不过,凡入来俊臣大牢之人,见了刑具已去了半条命,又何况是被审讯?”婉儿叹气,道,“若他还活着,也许我还会如你一般,心中人若是被钉住手脚,砸脑取髓,怕也仅有皇上那般的女人才能泰然自若。”
皇姑祖母仍旧笑着看我,道:“此案朕已知情,你但念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