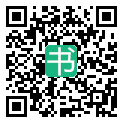玖 致最亲爱的彼岸
“巴黎她吃鱼,好像被鱼刺哽住了。”罗小雄想出一个死无对证的完美谎言。
“……最终他在麦田中央朝自己腹部开了枪,走回家后在床上躺了两天死去。”走过《乌鸦群飞的麦田》,讲完了梵高之死,邓夕昭清了清嗓子,用轻快的语气对雅乐说,“班上学生大都喜欢日本动漫,难得你对文森特·梵高的油画感兴趣,不然朋友送我的参观券就要浪费了。梵高这样的天才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被理解,直到现代也不可能变得通俗。杰出的作品有着生命力,有的回答问题,有的提出质疑。我不会画画,不敢说看懂或理解这些画作,但真心觉得它们很美。”
邓夕昭完全成了路人,罗小雄无视他,雅乐无暇理会他,他们俩并肩蹲在地上又是拍又是搂那个小女孩,仿佛亲密无间的一家三口。
“欧洲很多城市的建筑大都有上百年的历史,甚至几百年上千年。石头、花岗岩建造的房子,坚固美观,经历时间越久,越成为经典。特别是教堂,那是神的庇护所,是圣地,预备着要恒久地矗立下去的,因而总是精工细作,每一处廊柱的式样、藻井里的壁画都悉心打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已经造了几百年,至今都没有完工。十多年前贝聿铭负责卢浮宫的改造工程,特别设计了玻璃金字塔,法国人至今都在表示不满,痛陈说那是‘巴黎脸上的一道疤’。他们不喜欢改造城市,只喜欢经过时间洗礼、隽永的东西。”
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另一个美好、精致、温暖、儒雅、充满了格调的世界。
他们都知道雅乐绝对不想成为像丁野那样的人,死都不要,因为那极有可能是谋杀她亲生父亲的男人。
“巴黎她……她突然不舒服。”罗小雄慌忙之下打出儿童牌。巴黎趴在罗小雄肩头,很配合地咳嗽一声。
“要不要去医院?我有摩托车。”邓夕昭对雅乐说,“就停在美术馆门边,不过载不了四个人。”
邓夕昭驾驶着摩托车把雅乐和巴黎送回到德庆坊,看巴黎蹦蹦跳跳欢快地跑进巷子里去,邓夕昭忍不住问雅乐:“她真的是流浪儿?雅乐,你这样把她从街上捡回来留在自己身边,固然很好心,但真的不合法。政府有机构有体制,这是社会问题,不是你能解决的。你自己都是一个未满十八岁的少女,你的将来都要付出百分百力气去拼,哪里还有精力来操心一个孩子?你应该打电话给110,警察会查找流浪儿的原籍和父母在哪里,即便找不到,也会送去福利院,那里有的是和她同样经历的孩子,有老师、有医生,她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会健康成长。”
“小雄哥哥说谎骗人,难道就是好人了?”
安静的展览大厅里响起一连串的脚步声,一个少年抱着个小孩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直闯进来,喊道:“雅乐!”
“巴黎也有这么美的咖啡馆吗?”
搞定这一切的是罗小雄,但他不能让雅乐知道这一点。
带着孩子排队候诊,邓夕昭问雅乐:“在美术馆里,我没听错的话,你叫她巴黎?”
“对,她的名字就叫巴黎。”雅乐摸了摸巴黎的后脑勺,低头对她微笑,“云巴黎。”
“三条路。”雅乐轻轻指着印刷品说,“麦田里有三条路指向三个不同的方向。”
天气很冷,雅乐在厚实却会略显臃肿的白色羽绒服和轻薄却不怎么御寒的薄荷色大衣前犹豫了几秒钟,最后伸手选择了后者。这浅浅的薄荷色,看起来像夹着香草奶油的奶酪马卡龙,那是法国著名的一种甜点,被冠以“少女的酥|胸”这样甜美诱人的名号。绝大多数滨海人不要说吃,甚至连听都不曾听到过。
“……求求你不要给我添堵了,就先承认都是你通的路子就好了。”罗小雄头痛欲裂。
没想到还真有那么多人吃鱼被鱼刺卡喉,夜晚皇普中心医院的五官科急诊处门庭若市。
雅乐拽着巴黎试https://m.hetushu•com.com图送她进诊室时,巴黎泥鳅一样挣扎着,并且哇的一声痛哭出来:“……我晚上根本没有吃鱼,都是小雄哥哥骗你的啦……”
却意味着,我们又是那么忠实于自己。
“好!”于是陌小凯很爽气地华丽转身变成暗黑界深度隐藏的青年教父,压低嗓音郑重地说,“雅乐,你是罗小雄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你的敌人也就会是我的敌人。”
“梵高用金黄色的麦田来表现生命蓬勃鲜活的力量。中间那条道路是画面中唯一有尽头的道路,但尽头也隐没在麦田和暗夜之间,遥不可及。他明明有着那么强烈壮美的生命意愿,却又被疾病、困苦生活、不被世界承认理解的痛苦压迫撕扯,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往哪个方向去。向左?向右?还是向前?”
巴黎一直在观察对门房间里的医生是怎么给求诊者看病。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指着自己的喉咙“啊啊”地张嘴示意。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看不清面目的一个女医生拉过探灯照着男人的嘴,一手用一根竹签压住他舌面,另一只手从桌上的白瓷托盘里拿起一支长到匪夷所思的巨型镊子,眯起眼睛朝男人口腔里钻探进去……
没人敢告诉雅乐这一点,但他们都认为她越来越像她的继父了。
邓夕昭摘下眼镜,两根手指穿过镜框,灿烂地笑道:“没有镜片,假的。想着看画展嘛,增加点文艺范儿。”他戴上细黑框眼镜,暖暖地一笑,“走,我们进场吧。”浓密剑眉下星眸闪耀,真的太像青年学生时代的金城武。对了,雅乐想起来,金城武是中日混血儿,虽然哪哪儿都是亚裔血统,但骨子里却透露出别样的异国风情,就是这种感觉,在今晚的邓夕昭身上也格外明显。
黑手党小说《教父》中,维克多·柯里昂老头子问他的家族参谋汤姆·哈金:“那个男人真有种吗?”
“雅乐不是一般的女孩。”
“要不要一起去法国?”邓夕昭微笑着侧过脸来,“去留学,报名接收国际生的语言学校,搞资产担保,是有难度,但绝非不可能。我正在打听这些渠道和情况——”
“巴黎挺好的,没事了。隔壁王家伯伯刚才也来过啦,问他烧的鱼好吃不好吃,说以后他每次烧鱼都会记得给你端个十条八条过来,吃鱼聪明嘛。巴黎吃鱼要哽,你不会,你巧舌如簧。”
深夜躺在床上,明月的光透过玻璃窗一直映照到床头上来。
罗小雄抱着巴黎,这一路跑得又猛,脸颊通红,气息都很急促,他飞快地瞥了眼一边同样愕然的邓夕昭,视若无物般转过视线来,低头看着雅乐,再度低喊了一声她的名字:“……雅乐……”
很显然,王波军绝对不是西西里人,而云雅乐却很像西西里人。
“嗯,她……她不是发烧……她是……”
雅乐伸手去摸巴黎额头:“我出门时不还好好的吗……不烫啊,没有发烧?”
邓夕昭很愕然,隔了好一会儿才赞道:“你真的好有爱心。你自己都一个人……”他知道她父亲不在了,母亲也在几年前就离家和别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只有她孤身一人守在穷街陋巷深处的一个修车铺。
这一个刹那他真想再次问她“可以做我女朋友吗”,但那股热量和胆气尚未提升到咽喉处,雅乐就先开口了,话语声很温柔:“小雄,能帮我个忙吗?”
雅乐是在法文课堂上听邓夕昭老师说起的。Macaron,那是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法式杏仁饼,是法国西部维埃纳省最具地方特色的美食,制作工艺精良而复杂,很久以前只有贵族才可以品尝,到了现代普及了,但价格依然比较昂贵,是格调美食的象征。雅乐穿上马卡龙薄荷色的大衣,裹紧领子走进了寒冷的冬夜。
王波军虽然没种,但不是笨蛋,他观察得没错,桑塔纳轿
www•hetushu•com•com车、司机、把他绑上车的彪形大汉确实都不是雅乐的人,雅乐没有这样的资源和力量,她更无法找到那样一幢建造中的高楼作为整场行动的实施场所。
“画里的场景是一百多年前了。”雅乐话语间有轻微叹息。谁都知道,隔上几十年,城市的变化会有多厉害。
“好啦,你快回家吧,明天还上学呢。”
“是你堂妹?”
“真的、真的不痛,完全都好了。我现在就可以唱歌给你听!”
“对啊,一般的女孩知道你是富家公子少爷恨不能以身相许,情定三生,可你说雅乐如果知道你不是穷鬼就会叫你滚蛋。你这样下去只会越陷越深,伪装的时间越久,她将来发现真相时就越讨厌你。”
“法国到处都是这么美的咖啡馆,塞纳河两岸有太多令人流连忘返的咖啡馆和酒铺,每一家店铺里都可能留有举世著名的文豪画家的足迹。普罗旺斯乡间还有望不到边际的薰衣草田野,每年夏季到秋季,整片大地都是紫罗兰色的。”邓夕昭抱着臂膀,并肩站在雅乐身边,同样出神地望着那幅《夜晚的咖啡馆外景》。
雅乐这么一说,罗小雄就知道自己露馅了,只能尴尬地嘿嘿傻笑,扮可怜:“要不要这样讽刺我啊?”他本来很想说“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和一只禽兽在一起啊”,但觉得太过露骨,显得无耻。
雅乐没有说话,她的目光从陌小凯脸上转移到罗小雄脸上,轻缓优雅地慢慢褪下左手的手套,把一只掌心温热、指尖冰凉的手轻轻安抚在罗小雄的右脸颊,停留了三秒钟。对罗小雄来说,这三秒钟就是永恒。
那么美,却又充满了挣扎。即便是不懂画的人,也会被那种激烈对撞的视觉效果所影响。
“可他让你把我交给警察,送到福利院去。我躲在电线杆子后面都听到了。小雄哥哥就不会。”
——茨维塔耶娃
“还不是隔壁王伯伯,他们家晚上烧了红烧鲫鱼,儿子加班不回家吃饭,菜太多了,就端了一条过来,我才出去买瓶水的工夫,回来就看到鱼没了,巴黎她咳嗽不舒服了。”罗小雄边说边蹲在雅乐身后,冲仰着脸大张嘴的巴黎拼命使眼色:“对吧,巴黎?”
“赴汤蹈火!”
那个警告王波军的晚上,天空中的深蓝色夜幕也是这么浓重地垂挂下来。罗小雄、陌小凯、郑伊健、小飞龙、小甜甜、乌鸦、李跳、强仔……十几个少年少女在她冷静的布置调度下把王波军倒悬在高楼之巅。楼顶风很大,气温将近冰点,但她心里寂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掌心也是火热的。只要她不慌不忙、胸有成竹,他们也就都有了胆气,不再惧怕或因为惧怕而过激。绑架、威胁、恐吓……这些罪名她都可以承受,这是最坏的打算。对她来说,这次十足的冒险行动是否过激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不能让炮仗总是活在王波军的阴影之下,不能让炮仗和他奶奶流离失所。当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瞒着炮仗没有告诉他。
“雅乐,巴黎、巴黎她没事吧?”罗小雄双手支撑着膝盖,抬起头来问,一边眼珠子乱转,观察着雅乐脸上的表情,看来心里忐忑得很,不知道自己的牛皮是不是被戳穿了。
陌小凯皱着眉头对罗小雄摇头:“我帮你骗她我无所谓,但你总有一天会被识破身份,到那一天,她会怎么想你?你想过没有?女孩子都很难搞的,如果你解释说手段是为了目的,她就会让嚷嚷说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和手段,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欺骗的手段更令人心寒之类……”
“今天晚上我要去看梵高的画展,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巴黎吗?”
寒风里,罗小雄孤零零地站在南京西路边,望着邓夕昭开着摩托载着雅乐和巴黎绝尘而去,怒骂“禽兽”。妈蛋,这里是人流最密集的中心城区,打车比打劫都难,半天都看不到一辆空出租。
“你www.hetushu.com.com今天戴眼镜了?”雅乐发现了他的不同。
雅乐抬起头看了看邓夕昭飞扬的浓眉下星星般明亮的眼眸和阳光般和煦的笑容,觉得他是除了德庆坊那帮兄弟姊妹以外最可以信赖的人,为什么不告诉他真相呢:“不是堂妹,是我在街上遇到的小孩,我不能让她睡在马路上,就把她带回家了,跟我姓,巴黎是她原来的名字。”巴黎就在身畔,雅乐不愿说她妈妈死了,不知道亲生父亲是谁的事实,孩子虽然还小,但冰雪聪明,她都懂,她也有自尊心。
展馆进门玄关处悬挂着横跨整堵墙面的一幅画,巨大到令人瞠目的地步。不安的短线条,密密麻麻、层层叠叠排列的笔触。深蓝色夜幕浓重地沉积下来,金黄色广袤田野明亮耀眼,犹如暴风雨中的海洋一般汹涌翻滚,却仍被牢牢地扣压在黑夜之下,无处逃逸。夜空中没有星月,只有两个灰白色的漩涡,成群黑鸦在麦田上方盘旋。站在画前屏息的人们,仿佛都能听到漫天翅膀扇动的声音。
直到邓夕昭骑着摩托消失在街尾,直到雅乐慢慢踱步进巷子深处,走到自家修车铺门口,她的指尖都依然停留着刚才的温热触感。触感很真实,但一切又显得那么不真实,因为邓夕昭根本就是个梦境般美好的人。他刚才的话算是某种情愫的表达吗?算是告白吗?没有说出一个爱字,没有说喜欢,但每一个字都裹着薰衣草香,随风拂面,洋溢着浓浓情意。雅乐感觉自己成为站在法国南部小城阿尔的无边麦田里看艳阳高照、看群星闪耀的少女……而不是滨海万千众生中挣扎谋生的蚁族小民,也不是汽修技校里深藏不露的意见领袖,更不是镇守德庆坊、维护街区平安的混混女王。
罗小雄怎么能直言告诉她说,自她走后,巴黎乖乖在念拼音背汉字,罗小雄一个人望着阁楼窗外黑蓝色的寒冬天空寻思:梵高的画展?听说过他的作品要来滨海,就在离德庆坊不远处的美术馆里展出。问题是雅乐又不画油画,她怎么会突然想去看梵高的画展?和谁一起去?到底是谁邀约了她?他突然记起在法文课上曾听邓夕昭介绍过梵高,无比景仰地讲他笔下的浓墨重彩的法国咖啡馆和麦田,充满无边的浪漫情怀。梵高不就是个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送给妓|女的疯画家嘛,而他时好时坏的疯病也是因为梅毒入脑引起的,搞点艺术创作就一定要把自己搞得身心残疾吗?最后还自杀——只能说是放浪,实在看不出哪里有浪漫。一个念头突然闪入脑海——会不会是邓夕昭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约的雅乐?衣冠禽兽、图谋不轨!
这是印制品,并非原作,印制得如此巨大,大抵是为了增强冲击感,第一时间震撼到人心魂。
那个国度的人们相信流动消逝的仅仅只是时光和生命。而艺术和美,用绘画、建筑、雕塑、文字、音乐、舞蹈、戏剧……这些接近永恒的形式保存下来,不可抹除。真正成为一道盛宴,去到那里就可以尽情品尝,去到那里就能将曲折逼仄的巷道、阴暗暴戾的记忆都抛诸脑后,在一个古老城市展开全新的命运和旅途……但那又是多么遥不可及的彼岸啊。
雅乐看着上气不接下气的罗小雄,真对他是又气又好笑。这个笨蛋,这一连串的麻烦事,难道不都是他自己惹出来的吗?至于他为什么要假借巴黎鱼刺哽喉跑来美术馆见她,她心下一片雪亮,不问也罢。现在又说什么“配手机、配汽车”,简直是跑晕了头一个人在那里胡言乱语。
巴黎一骨碌翻了个身,趴在枕头上对雅乐悄悄耳语:“姐姐,那个眼镜哥哥是坏人。”
“那是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阿尔加萨咖啡馆。”邓夕昭显然对梵高的作品很熟悉。
雅乐皱眉笑了:“什么呀?小孩子家。他是我的法文老师,人可好了。”
雅乐,坚定不移的外壳看不出缝隙,从未对任何人流露出自己的软和-图-书弱。只除了那一天傍晚,冲出修车铺的她被罗小雄劝阻下,她对他喊道:“我不想留在这里!总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我要离开德庆坊,离开滨海,离开这些迷宫一样曲折逼仄的巷子,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个国家!如果有另一个地球,我恨不能离开这个世界!”那时罗小雄脸上的表情错愕极了。这个向她告白过的少年并没有因为她的拒绝而退离,才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已经成为德庆坊无比中坚的一分子。他和炮仗、小飞龙、郑伊健、乌鸦他们一样,以为她会永永远远地镇守在这些曲折逼仄的巷道里。她深爱这些兄弟姐妹,她愿意付出一切去守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但她又那么恨这个地方,恨那些抹不去的痛苦和记忆。
雅乐加快脚步走近前,喊了一声“邓老师”,邓夕昭转过头来,脸上漾出一个暖洋洋的微笑:“云雅乐。”
雅乐诧异地发现那是罗小雄和小巴黎。
对德庆坊的混混少年来说,王波军总是把他们踩在脚底下,他有很多体格健壮的小弟,甚至滨海汽修技校里很多学弟都崇拜他,想跟着他混出道,但绝大多数都被当作傻逼,狗一样替王波军和他的小弟们跑腿,打架时冲在最前面,分好处时全然没戏。这一次少年们在雅乐的领导下奋起抗暴,把王波军掀翻在地。王波军或许很厉害,但说到底也只是个地痞流氓。而雅乐的继父丁野却不同,丁野是真正的黑社会大哥。那天晚上她话很少,每一句话都像出鞘的匕首一样,冰冷、锐利、射出不容置疑的锋芒和力量。
困在这里,不知道究竟该往哪个方向去。向左?向右?还是向前?
楠京西路上的滨海美术馆门口,远远就看到人流中矗立着的邓夕昭挺拔的身影。
“雅乐!你回来啦!”一连串脚步声响起,罗小雄从巷外小跑进来,累得气喘吁吁,“我……我拦不到出租车,只有跑步赶到医院……却、却没找到你们……你、你又没手机……联系不上。我想只有回来等你们……完全拦不到车,又是一路狂奔回来……真该给你配个手机,再、再配辆车,这样,这样我就能找到你了……”
雅乐不放心:“还是让医生检查一下比较好。鱼刺一定要取出来才行。”
雅乐在一幅由大块面红蓝黄三色构成的画作前停下脚步,铺满鹅卵石的城市小广场,星辰如同宝石一样在蓝色夜空中闪烁,茂盛的树叶显示着这是夏季或温暖的春末秋初季。穿着西装的绅士和大摆长裙的女士优雅地走向咖啡馆。露天带顶棚的座位区,从屋内透出的灯光把墙壁和屋顶都映照得明亮金黄。红色的地毯上,白色小桌一溜儿摊开,人们喝着咖啡,三三两两地交谈着,享受着闲适的城市之夜,连端咖啡的白衣女招待也显得那么从容不迫。
陌小凯拍胸脯拍得几乎要把肋骨都拍断掉了。他遵守了诺言,这是小雄此前就已经和他约定好的,让他把一切道行都承认下来。其实桑塔纳轿车是罗智慧集团下某个分公司经理的座驾,司机和彪形大汉都是某家合作建筑工程队里的伙计,在建中的高楼是罗氏集团承包的某个项目,深夜停止施工后,凭着办公室秘书一通电话关照,工地保安就放他们上去“拍摄广告宣传片”了。
“我觉得这幅画美极了。”
邓夕昭垂下眼帘,他的睫毛比很多女孩子的都浓密,薄薄的嘴唇抿成一条细线,慢慢地,这条线向上弯曲起来,睫毛扬起来,漆黑眸子如同宝石一般灿烂,带着令人迷醉的闪光。邓夕昭注视着雅乐,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指尖:“……云雅乐,我是一个老师,我本不该说这样的话,但我真的对你有一种特别的关心,我自己也很难解释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做梦梦见我和你一起走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看到埃菲尔铁塔的光芒中你的发丝m.hetushu.com.com被微风吹动,轻抚到我脸上……我们在那里,我们在一起……”
邓夕昭认出罗小雄是法文班上新近加入的学生,只来过没几堂课,但不清楚他和云雅乐是什么关系,尤其是手里抱着的这个女童,要说是妹妹,年纪也未免差太多。
他穿着烟灰色粗呢竖领短大衣,宝石蓝的牛仔裤,围着一条浅蓝黑灰格子的厚实围巾,骨节分明、纤秀的双手自然而然地垂在裤缝两侧,抬眼静静眺望着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他不像雅乐见惯了的德庆坊少年那样,不是夹着烟,就是插在裤袋里耸起肩膀,整个人不安分地游移脚步,弓着背四处张望。
雅乐把巴黎翻过身来仰面躺好,给她掖上被子:“我可不喜欢被人骗。”
“是陌小凯干的。”罗小雄手指身边边抽烟边狼吞虎咽吃烤串的光头型男,“他是流氓,他在暗黑界很有力量。我就拜托他,他道上的朋友多如牛毛,都欠着他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
修车铺外的巷子里,罗小雄站在电线杆子下抬头久久仰望阁楼窗户,直到橘黄色的灯光熄灭。
任凭谁翻遍了信札,没有人能明白内中真情。我们是那么背信弃义,
“我们今天晚饭没吃鱼啊。”雅乐一边说一边让罗小雄放下巴黎,让她张开嘴检查她的咽喉。
“怎么了?”雅乐伸手拍抚歪着脑袋趴在罗小雄肩膀上的巴黎脊背,“你们怎么来了?”
汤姆·哈金懂得教父这句问话的含义,当时他们正要对付一个不听话的大导演伍尔兹。汤姆·哈金巧妙地回答说:“他不是西西里人。”真正的西西里人有着无比坚强的意志,为了原则上的问题,为了涉及荣辱的问题,或者单纯为了报复,敢冒一切风险,把一切都豁出去。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想和西西里人做敌手。柯里昂老头子知道伍尔兹不是西西里人,于是某一天早上,伍尔兹从睡梦中醒来时发现满床都是血,自己从伦敦花天价买来的最爱的纯种马的断头血淋淋地竖在床榻上。
陌小凯眨巴着怪眼瞪了罗小雄好一会儿,咽下烤羊肉替兄弟背负下又一口黑锅:“一点没错!我是流氓。我小时候是小流氓,老了是老流氓,现在是青年期流氓。别看我是个企业的正经员工,那只是伪装,我真正的身份其实是有逼格的暴徒之王,简称隔壁老王。罗小雄和我有过命硬交情,但凡有事,你让他来找我。”
巴黎眨巴着大眼睛,她虽然聪明,毕竟年幼,懵懵懂懂的,不清楚为什么小雄哥哥让她假扮被鱼刺哽喉:“……如果,如果说谎骗人不是为了做坏事,而是为了对人好呢?”她在街上流浪的那些日子,说谎骗人乃是家常便饭,但她从来不想做一个坏小孩。
“……他们居然没有放最著名的《星空》或《向日葵》,而是这幅《乌鸦群飞的麦田》……”邓夕昭沉思道,“雅乐,你知道吗?传说这是梵高生前最后一幅画作。那时他已经在圣雷米的圣保罗精神病院里断断续续地居住几个月了。评论家说黑暗的天空代表了梵高对未来的绝望,乌鸦代表了死亡的阴影。”
罗小雄很得意,衣冠禽兽,让你阴谋落空。论设局你够老谋深算,论搅局我可别有所长。
祖屋很快就归还到了炮仗奶奶名下,德庆坊再也见不到王波军的踪迹,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敢再挑什么事端来伤害被他称其为“野种”的弟弟。雅乐禁绝的三件事,很简单、很合理的三件事,是通过那么直接、虽不见血却凌厉异常的一场威胁最终实现的。
巴黎闭眼不敢再看,医生叫“下一个”,巴黎拽拽雅乐衣袖说:“我好了。喉咙一点不痛了。”
雅乐抬起脸凝视了邓夕昭英俊的脸好一会儿,此刻他微微锁着眉,满脸都是深切为她感到烦恼的神情。雅乐微微一笑:“邓老师,你对每个学生都这么担心吗?除了法文班的,还有市六高中里的学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