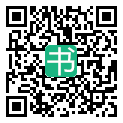第十四章 蛮火
“前面的路有古怪,像是有人泼了许多猪油在上面。这里是山崖,万一车子打滑,摔下去可不是玩的。公子和姑娘请稍候,我去看看情况。”
火火火,到处都是火,浓烟迷了她的眼睛,令她不能呼吸,她不顾一切地放开嗓子大吼:“舒隽!”
梦里殷三叔问得不错,他要的,究竟是什么?或许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只是前所未有地对前进的方向产生了怀疑。
晏于非微微一愣,殷三叔亲自照顾葛伊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约只有他自己知道。
舒隽在她额头上一点,似笑非笑:“你这丫头,独自在外面闯荡些日子,总算有点见识了。这么放心晏门,不怕他们在吃的里面下毒?”
伊春甚少见到这种旖旎景象,看得入迷,用力吸了好几口,赞道:“好香啊。”
晏于非拐个弯,迅速消失在庭院门外。
走了没一会儿,他忽然低声道:“殷三叔!”
“有你在。”她答得毫不犹豫。天下好像还没有能难倒舒隽的毒药,所以她一点都不担心。
马车里宽敞舒适,糕点热茶一应俱全,角落里甚至还放了一坛好酒。伊春拆了封口,抱着轻轻一嗅:“咦?是广陵琼花露!”
不知为了什么,他忽然举起袖子把她脏兮兮的脸擦了两下,原来她是长了这样一张脸,这样的鼻子这样的嘴这样的眉毛。记忆里那模糊的面容此刻全然被眼前的脸庞代替——她是个女子,她年纪不大,她有倾心相爱的人,除了一身武艺和那颗什么也束缚不了的心,她与世上所有女子都没有任何两样。
火,突然自地下烧起,后背一片烧灼剧痛之感,伊春倒抽一口凉气,猛然转身,却见火势早已窜了数丈高,浓烟滚滚而起,几乎遮住半边天空。
你骗人啊……伊春在心底低低说,这么容易就死掉,你还是舒隽吗?如果你没死,你为什么不见了?
晏于非猛然回头,神色十分古怪,脸色是煞白的,可是眼睛却亮得十分诡异,似是有无数巨浪在身体里拍打,不能安静。
他很圆滑谦卑,在两个小辈面前点头哈腰,连声说:“门主还未赶到江城,约莫着还有一天半天的工夫,公子和姑娘可有想去玩的地方?若有,不用客气只管告诉我。”
说罢用力将她一抛,伊春像飞起来似的,直直撞向对面一株高大的槐树上,她手脚灵活,当下勾住枝干,身子微微一晃,便翻身跳上了树顶。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
他看了看山崖边缘的几个脚印,转身便走:“去山谷看看!她……她不会如此轻易被杀!”
“……殷三叔。”过了很久,他低低唤了一声,“我们回去。”
舒隽摇摇头没说话,眼见老徐摇摇晃晃走在猪油上,四处张望,只怕是没见到什么异状,这才艰难地走回来抱拳道:“还请两位等候,待我将路上猪油弄干净。”
汪叔一直将他二人送上车,忽然想到什么,说:“那玉髓香,你要么?”
马车突然猛地停下,骏马长嘶一声,显是被人强行拉住了。伊春本能地按住腰上佩剑,舒隽丢给她一个安心的眼神,靠在车壁上懒洋洋地问:“什么事?”
后院那里果然停着一辆马车,驾车的人是一位姓徐的中年男子,伊春曾在扬州见过他一次。
他淡然转身,果然见晏于道笑吟吟地站在林中,前些日子他不知在何处受了重创,卧床半月有余才养好,那原本圆溜溜的脸也消瘦了下去,露出些尖嘴猴腮的味道来。
舒隽神色讥诮,淡道:“汪叔,当日东江湖的事令我好生惊讶,你这样的前辈人物,何时做了晏门的走狗?”
老徐笑呵呵地去赶马车了,好像一点儿也不生气。
晏于非先是一愣,紧跟着心里便是一惊,像是曾经竭力忘记忽略的一个回忆突然汹涌而来。他倏地转身,紧紧盯着晏于道,低声道:“什么意思?”
汪叔说:“马车在后院,老徐等了你一个上午。”
他低声道:“我说……回去。”
舒隽把试香盒往她手里一放,点头道:“我知道了,今年还不起,利滚利,明年我会找你的。”
“一千两!”
“你以为她是个好东西?”舒隽斜睨她,“坑蒙拐骗她样样都做,把你卖了你还得感激她一辈子。”
舒隽叹了一口气,回头看着他:“你将我卖了还这么理直气壮,这等本事我实在佩服。”
他曾是个侠客,如今是个商人,商人没有不爱银子的。千好万好,银子最好。
说罢他便转头望着波光粼粼的湖水,天气晴朗,湖面金光璀璨刺人眼。他微微眯起了眼睛,怀里有个东西硬邦邦,硌着胸口,他缓缓取出来拿在手上摩挲。
这边白石台选香品香人热闹非凡,那边大会主人却倚在别院小楼上眺窗远望。
伊春点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很香,但只有她这样的美人才配得上。”
伊春见白石台上许多人不试香,只管瞪圆了眼睛朝这里看,不由笑道:“他们都认识你吧?你一来大家都看着呢。”
“他们要见我,首先得有本事找到我,请到我。若连这点也做不到,凭什么
和图书叫我舒隽送上门?”晏于非猛然将拳头捏紧,断腕处的肌肉一阵剧烈收缩,牵扯出断裂般的疼痛,令他想起右手从身体脱离飞出的那个瞬间。
美人撅着嘴走了。
“没事么?!”是舒隽的声音,他第一次这么失态这么焦急。
殷三叔用手在地上抹了一把,放鼻前一嗅:“……少爷,像是有人在地上泼过猪油点火来烧。”
她张口要说话,他却忽然低头在她唇上吻了一下,低声道:“快!上树!不要下来!”
伊春故意低头在他身上闻了闻,撇嘴轻笑:“一个男人身上香喷喷的,好讨厌。”
“你到底是带着媳妇来看我了。”主人微微含笑,眼角皱纹密密麻麻,头发也已花白,神态中不知为何总带着一丝疲惫,令人不由自主替他操心身体。如果顺着胸膛往下看,能很清楚地看到他空荡荡的裤管和身下的铁轮椅,原来,他是个残疾。
伊春顿时对舒隽的砍价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
“舒隽!”她大叫,可是没有人回答她,冲天的火焰里隐约有几个人影一晃,奔至山崖边,有一人似是脚下一滑摔了下去。伊春又叫一声:“舒隽!”依然没人回答她,她只觉肝胆俱裂,没命地从树上跳了下来,又踩在猪油上,滚了好几尺,恨不得要冲进火里找人。
“舒隽!”她低声说,死死揪住他的袖子,“你这混蛋,活得好好的!”
断腕的地方没有受到任何刺|激,却在不受控制地一阵阵疼痛。提醒他小叔的耻辱,自己断腕的耻辱。
舒隽并不避讳他,飞快拆了信,里面包了一张信纸,两张千两银票,还有一块裂成两半的玉。他第一件事就是用两根手指捏着银票放在眼前仔细看,笑得眯了眼睛:“晏门主倒是会做事,大方的很。”
大庭广众之下,此人果然嚣张。
指尖在硬物上来回摩挲,猜测着信里的秘密。他有些后悔,不该答应晏门这桩事,也不该请舒隽来参加江城品香大会,但事情既然已经做出,那也没有反悔余地。
他长笑一声,剑尖回挑,桌上酒杯“噌”的跳起,酒液灌入他口中,一滴也没漏出来。
无论是断手,还是小叔。
江城九月有品香大会,无论是真正的风雅之士,还是附庸风雅的草包,这种可以体现身份与情趣的大会总是令他们趋之若鹜。各调香店老板亦是翘首期盼,因听说品香大会常有贵人秘密参加,一旦所制的香被金主看中买下,便有大笔进账。当年苏州香香斋老板便是因为制香出色,几个月工夫便进账数千两,令人艳羡。
话音未落,路边闪电般飞窜出十几个人,奇异的是每人手里端着一桶油,老徐大吃一惊,只来得及抽出防身兵器,但见他们呼啦啦将滚烫的猪油泼了满马车。
见到舒隽二人过来,他并不站起,只露出一丝笑容,颔首示意他们坐下。
伊春犹豫着给他行礼,却不知如何称呼,舒隽低声道:“叫汪叔,昔日助我钱财的也是他。”
前方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很轻,殷三叔动作奇快,瞬间便挡在了晏于非面前,手执双剑马上便要出鞘。
她毫不犹豫纵身跳了下去,风一下子就把她包围了,攀生在崖边的树木密密麻麻,柔软的树叶此刻擦在脸上疼得像要裂开似的。伊春护住头脸,把身体尽可能地蜷缩起来,下坠中感觉撞在一根树枝上,左边胳膊一阵剧痛,估计是断了骨头。
“一个女人臭烘烘的才可怕。”他在她脸上摸了摸,“但你不臭,我就爱你的味儿。”
殷三叔大吃一惊,本能地要拔剑相向,可他家少爷却一动不动,也可能是呆愣住了,任由她扑上去死死抱住他,脏兮兮的脑袋撞在他胸上,他微微一震,竟还是不动。
晏于非近几年常常会做一个梦,谈不上是噩梦或者什么别的。
伊春瞪圆了眼睛,骨碌碌转,用口型无声问他:“山贼?”
一个人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前,头戴斗笠缓缓跪下,正是许久不见的殷三叔。他垂头道:“属下已探访过,三少爷所说基本属实,门主如今人在江城,舒隽与葛伊春二人也在江城,三少爷的秋风班亦在江城集合。”
“没人来打招呼,你名声果然大大的坏。”伊春笑眯眯地走过去,拿起一个试香盒放在鼻子前嗅两下,结果却打了好几个大喷嚏,“好怪的味道!”她赶紧把盒子丢了。
殷三叔欲言又止,只得把斗笠往下压了压,随他一同攀下山崖找人。
那日晏于非为着扬州诸多帮派一夜之间解散不知所踪的事情去找门主商量。晏门有意拓展江南势力,奈何对方似乎并不怎么给面子,也并不像巴蜀湘地遇到的反抗那么激烈,江南大小诸多帮派玩的是龟缩战,一夜之间解散势力,将偌大一块江南宝地拱手让出。
更嚣张的是对方居然不羞也不恼,展眉朝他一笑,蜜色的皮肤,弯弯的眉毛,轮廓大抵还是娇柔的,是个年轻女子,既没有倾国倾城的容貌,看着也不像什么绝顶的有钱人,路边随便捞个人也就是这模样了。
“……我和你比试!”他不顾一切地说出www•hetushu•com.com来。
舒隽把正要说话的伊春挡在身后,摇头道:“少来,钱是钱,香是香,你糊弄我老婆可不行。”
浓密的草丛缓缓分开,“啪”一声轻响,一只脏兮兮染满鲜血的手抓在一棵槐树上,乱七八糟的头发耷拉在脸前,衣服也破破烂烂的,左手呈一个古怪的角度蜷缩在胸前。
汪叔哈哈笑了几声,终于从怀里取出那封信,随手抛给他:“晏门主给你的信。”
“舒隽,”他说,“你一直躲下去不是办法,我们都明白这事是你老爹做的,与你无关,但谁要你倒霉有这么个老爹。以前你一个人行走江湖,洒脱的很,自然什么也不在乎。但如今你有了媳妇,将来成家生娃娃,也要像你爹一样带着你们全家人到处躲避?”
她用手指刮他的脸,提醒他的肉麻举动应该收敛些。舒隽不甘不愿地坐直身体,眼见白石台近在眼前,便将她腰身一揽,纵身跳上了台子。
晏于道笑道:“二哥,我知道你素来冷静不轻易被人套住。也不能怪爹总偏心,你和大哥确实是有才干的,不过嘛,你们大才干是有,小聪明就没什么了。”
“门主说了是什么事吗?”晏于非有些奇怪,此时正值江南势力大变迁的要紧时刻,门主怎会不通知一声便擅自离开?
他将她的手捏了捏,没有说话。
汪叔笑了笑,眼神渐渐变得锐利。
敲了没两下,门主身边的贴身部下老林便来开门,朝他恭恭敬敬地行礼:“二公子,门主如今不在府内,临走时交代了,要事便由大公子二公子决定,他半月之后才能返回呢。”
信很短,上面写了两行字,都是时间地点,想是晏门主约好他在何处见面。信纸最下行还写了一行细细小字:【一别十余年,故人无恙?旧物奉还,沐香恭候少侠大驾。】
伊春恭恭敬敬叫了一声:“汪叔。”
品香大会的人对他已是相当熟悉了,纷纷点头微笑,心里暗暗纳闷那戴着斗笠的人是谁。舒隽虽有个小跟班,但品香大会他从来都只身前往不带下人的,因见舒隽对那人神态亲密,一手握住了对方的手,贴在那人耳边说话,这情形实在稀罕的紧。
他自己的右手也会忽然觉得空荡荡,低头一看,手腕不知何时断开了,肌肉收缩痉挛,剧痛无比。
汪叔扔给他一个香盒:“成交!”
身后忽然有人推门低声道:“那人还没来。”
汪叔抓住窗檐:“一千五百两。”
舒隽神色怪异地看着他:“您老还是那么会说话,但你搞错了一点,我从来也没必要躲着晏门。”
伊春笑了笑:“她是不是骗人,我知道的。你不用总担心我会出事。”
树树树,眼前永远是一株又一株沉默不语的树,谁也无法告诉她舒隽在什么地方。细长的草叶子刮在衣服上发出窸窣的响声,她想起那么多夜晚,舒隽与她细细密密的耳语。
心里有一种骄傲在抬头,葛伊春,要死也只能死在自己手上。最桀骜的鹰,岂能容别人染指!
晏于非朝前走两步,双眼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她,隔了许久,他低声道:“葛伊春,你没死。”
他捞起试香盒,并不搭腔,只放在鼻前微微一嗅,说:“这香不错,什么名儿?谁配的?”
“少爷,您带回的那个姑娘醒了,大夫说病得挺重,要好生照料。”仆人给他汇报昨晚的事,“殷先生照料了姑娘一晚,正吩咐厨房熬药。”
他吸了一口气,又道:“事情总要解决,你有本事,不应该到处躲,而是迎上去和他们把话说清楚!”
小叔轰然倒地,他心口被剜了个大洞,伤重无救。月光溶溶的庭院,忽然变成春光明媚的后|庭,凶手一身布衣,长发凌乱地披在肩头。
这座山并不高,身怀武功的人跳下去绝不至死,晏于非拨开拦在眼前的枝叶,心里不知为何有一种焦急,像有一面油锅在滋滋煎熬着,滋味相当不好受。
殷三叔终于忍不住开口:“少爷……要把这女子带回晏门有些不妥……”
美人把嘴一撅,哀怨的很:“每次见面你第一句话都是钱,好没情趣。”
“玉髓香。”美人嘻嘻笑了一下,“是我配的,你信么?”
是他?!是他?!老天!不要是他!
晏于道呵呵笑道:“我知道爹是做什么去了,他托人给舒隽带了一封信,打算见见他。那女的不是一直和舒隽在一起么?何况咱们晏门和舒隽他爹也有血海深仇,何必文绉绉的搞什么见面,直接杀了了事。我的秋风班,现在应当找到他们了吧?”
锦盒里是一双浓绿如春水的碧玉镯,纵然伊春并不懂玉器,却也能看出那是上好碧玉,价值不菲。伊春微一犹豫,本能地想拒绝这份重礼。
莫非有老婆大人坐镇,所以故意把别人当作路人甲?
湖水碧绿,石台玉似的白,上面有美人穿着薄纱在盈盈跳舞,琴筝琵琶的声音在水面缓缓涟漪开去,让这个略带闷热的初秋显得分外旖旎。
他甚至不能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偶尔脑海里会想到下一刻拨开浓密枝叶,看到的是她支离破碎被烧焦的尸体,自己会怎么办?
和*图*书晏于非这时才叫大吃一惊:“你派人跟踪监视门主一举一动?!”
这座山并不高,摔下去并不会死。
舒隽从后面抱住她,轻声说:“丫头,你别担心。”
美人长眉入鬓,眸光流转,不知倾倒在场多少男子。她却只看着舒隽,唇角微微一扬,露出个妩媚温柔的笑来。
他感到十分喜悦,先前的沮丧失落一瞬间全部消失了。
他随手将信撕了丢在脑后,默然无语地牵着伊春起身。
两人一顿大吃大喝,撑得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便撩起窗帘看外面飞逝而过的景致。
白石台上许多人都回头去看,眼见一艘小小渔船荡着碧波摇摇晃晃的近了,船头坐着一个身材瘦削头戴斗笠的人,因那斗笠压得低,看不出男女,只有几绺长长的头发随风在背后柔柔舞动。
他低头看看伊春,她也仰头看他,两个人的眼里都有同一种东西:傲气。
像是被无形又尖锐的东西击中身体,他实在禁不得,倒退了两步。小叔的尸体在身后飘荡,一遍一遍低声问他:于非,于非,为何不替我报仇?杀了她杀了她杀了她……
伊春从喉咙里发出一个古怪的呻|吟,像兔子一样跳了起来,一把扑上去。
她就地一滚,一直滚到山崖边上。
火光灼目,似是烧进了眼睛里,剧痛无比。刀光剑影在身边闪烁,她只是本能地反手挡下。
殷三叔跪在脚边,声音低沉:少爷,强极则辱。少爷最想要的是什么?
话未说完,人已经软了,真正晕死过去。
每夜每夜,他都感到那伤口传来的深深痛楚,只是觉得痛,却不明白为什么会痛。
她像个野生的小兽,劈荆斩麻出现在两人眼前,狼狈的紧,可那双眼却依然亮得惊人。
晏于非皱眉离开了门主的院落,刚过了竹林,却听林中一人笑道:“二哥,我知道爹去了什么地方,要我告诉你么?”
他长长吐出一口气,下意识地用手撑在椅子上想站起来,微微一动,才想起自己早已没有了双腿。许多年,居然就这么过来了。
晏于非眉头紧皱,低声道:“三弟如此胡闹!”
晏于非自失了右手,殷三叔为他走遍五湖四海,寻得一块千年香木料,请了最好的工匠替他做一只木头假手嵌在伤处。假手做得惟妙惟肖,连指甲上的纹路都好似真的,除了不能动,乍一看他与常人并无任何区别。
马车终于慢慢走远了,伊春把脑袋探出去半个,见汪叔坐在铁轮椅上,目光拳拳地看着这里,似是有些不舍。
这话说得非常突然,而且没头没脑,伊春一时倒愣住了。
没有人回答他,晏于非自嘲地笑了,顺手一拉床边的小铃,早有仆人端了热水进来供他梳洗。
马车离开繁华热闹的市集,开始往人烟稀少的山道行去,舒隽放下窗帘,只留一道小缝,细细的山风将伊春耳旁软发吹得飘来荡去,看得他心痒痒,抬手将她搂过来,有个冲动想吻一吻她沾染酒气的嘴唇。
舒隽懒得抬头,把脑袋放在她肩上,轻声说:“管他们做什么,咱们玩咱们的。回头我替你选几个香,提神醒脑相当有效。”
晏于非紧紧握住伤处,脸色惨白,想要从喉中嘶吼出伤痛,偏偏发不出一点声音。
他长歌而去,无人敢阻拦,晏于非胸中像是要爆裂开一般,双脚不受自己控制,飞快追上去,张开双手挡在那人面前。
伊春猛然回头死死抓住他,他浑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黑乎乎的,头发也被烧得少了一半,狼狈得要死。
她眼里有期待而且兴奋的光芒,遇到山贼对她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危险事,相反,山贼等于有银子进账,伊春相当的期待。
敲诈,绝对是敲诈。他舒隽走遍大江南北,从没遇过要卖两千两的香。
舒隽哼了一声:“她算什么美人……”
所以,舒隽,如果你摔下去了,如果你死了,我会鄙视你一生一世!
那人扶剑又是一笑,春光明媚的后|庭,不知何时再次变成月光溶溶的庭院,站在他对面的不是别人,正是葛伊春。
晏于非懒得听他废话,转身便走,只听他在后面叫道:“二哥!砍断你右手的那个女人,我遇上啦!你放心,我必替你报仇!”
小叔的声音在耳边徘徊,凄凉而且悲怆:于非,杀了她,为我报仇。
须知道肥肉再美味,也不可能一口全吞了,晏门得到势力的同时,还需要付出两到三倍的代价,光是在官府那里打通上下便是一笔巨款,沿河而居的民家们对新来的晏门亦是兴趣缺缺,倘若此时有人自外部集结反攻,晏门很可能在江南一块的计划功亏一篑。
晏门主的信,里面会写点什么呢?他已知道舒隽的身份,这次来,是祸是福?
舒隽本能地想拒绝,忽然想起伊春说那个很香,脸上有向往的神色,心中不由一柔,点头道:“也好,我要了。”
殷三叔默然点头,喉头颤了两下,转身先走了。
那人哈哈大笑,收剑回鞘,细小的血珠子落在地上,落在晏于非脸上,又烫又冷,令他不能呼吸。
此刻他正用那只假手轻轻敲门,平常这个时候,门主是在书房里批阅信件公文的。
舒隽回头看着他和_图_书,露齿一笑:“要我说,撑死十两,卖不卖?”
汪叔便笑着从怀里取出一个锦盒递给她:“匆匆出门来别院,没带什么好东西,这小东西便拿去玩吧。”
“……财迷心窍的老鬼!”
汪叔顿时无语。
他只能,眼睁睁、一次又一次地看着那呼啸的星光切断小叔的右手。鲜血像浓稠的液体,带着发紫的暗红色,如雨落下。
舒隽无奈地看着他,却听他笑了笑,带着些慧黠,又说:“你放心,给我再多银子,我也不至于把你家透露给他们。”
他简直不敢相信。
别院中树木森森,甚是阴凉,主人就坐在一栋小楼里,布衣铜簪,红木桌上放着一壶茶,三只青玉茶杯。
舒隽淡道:“你真能配出这种香,就不会在这里跳舞了。前年欠我的五百两银子,今年你到底怎么说?”
伊春眼前是一片刺目的白光,她在崖底躺了一天一夜,终于能收拾气力上路找舒隽。可是她在山林里徘徊了很久很久,舒隽究竟在什么地方?
开始他还会急切地在旁边呼喊,可很快就发现没有人能听见。
晏于非坐在床沿,静静看着那只盒子,看了很久很久。
他立即放下帘子:“不要了。老徐走吧。”
晏于非愣在那里,低头看着她肮脏看不出轮廓的脸,只有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能让他意识到这人是葛伊春。她的眼神充满了狂喜,跟着紧紧搂住他的脖子,轻轻说:“你活得好好的!”
说到这里,她笑了起来,眉眼灵黠,在伊春身上转了两圈,立即又露出亲近的笑容,一把挽住她的胳膊,柔声道:“这位妹妹好模样,和舒公子在一起真是天生一对。我这里还有别的香,妹妹看中了什么,只管和我说,就当我的见面礼。”
她生得瘦削娇小,身体却站得很直,脖子扬着,唇角似笑非笑,两眼却比星子还要亮。
舒隽却早已不客气地取出镯子替她戴在手腕上,左右打量一番,低笑:“漂亮得很,多谢汪叔了。”
两人打开车门探头去看,果然见前面很长一段山路都白花花的,显然是凝固起来的猪油,而且相当厚,不要说马车,只怕他们这种身手高强的武林人士在上面也要打滑。
晏于非对这个同父异母的三弟并没过多好感,只说:“这个时间,不去培训你的秋风班,来门主的庭院做什么?”
世上如果有人比他舒隽还爱钱,那人肯定是他。
“别说那么难听,什么叫跟踪监视?爹既为一门之主,做事当然要谨慎再谨慎,我不过是多替他分忧罢了……”
“他老人家并未交代,只说江南的事交给大公子二公子便足够。”
舒隽点了点头,握住伊春的手,笑着说:“走吧,这次的大会主人是我一个长辈,我带你去拜见他。”
晏于非醒来的时候浑身冷汗,喉咙像是被一双手扼住,无法呼吸。他揉了揉眉心,翻个身,微薄的晨曦透过窗纸撒在案上。
她几乎要筋疲力尽,只剩最后一口气便要再次晕死过去。
原来,他到现在还是没能放下。
她本能地上前一步,差点从树顶一头栽下。
没有人回答他,遥远的地方似乎有打斗声一阵一阵,还伴随着被烧伤之人的惨呼,令她心惊肉跳。
舒隽将盒子捧起,在鼻前轻轻晃了两下,闭目如数家珍:“麝香,龙脑……提神的很,是好香,只缺了点什么……”
殷三叔眉头一皱,正要拔剑,却听晏于非低声道:“殷三叔你退下。”
案上放着一个水晶盒子,里面是他的右手。
再靠得近些,那人忽然把斗笠摘了当扇子扇风,回头对舒隽说了一句什么,却被他在脸上相当无赖地亲了一口。
忽听汪叔话锋一转,低声道:“你向来聪明,比你爹娘强了何止千倍。既然聪明,便知道自己暴露了身份是什么后果,一直躲避下去自然不是办法。”
众美人舞罢,便款款迎上来,像一群小鸽子排成一队,每人手里都捧着一只试香盒,轻轻放在长桌上。桌上早已有人写好字条,谁家制香,材料为何,名称为何,众人只需挑选便可。
隔了一会儿,三弦声停了,跟着船舱的帘子被人一揭,舒隽从里面钻了出来。他今天穿了一身绛纱,长身玉立,站在船头映着江水,像个端丽的神仙。
“你们总喜欢强迫别人听从自己,可我偏偏不喜欢这样。”
舒隽不由低头凑在伊春耳边:“喜欢她身上的香?”
伊春痛得尖叫起来,后面有人一把抓住她的领子,硬是将她扯出来,然后噼噼啪啪一顿拍,把火苗拍灭。
最后才展开那封信。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替杨慎一起活下去。
伊春轻声说:“你对她好凶,为什么?”
他正要换另一只试香盒,忽听丝竹声又起,裹着轻纱的美人们款款舞来,正中一个美人一身皎白,长袖蜿蜒,腰身似蛇一般柔软,旋转间裙摆梅花似的绽开,淡淡的幽香顿时充斥了每个人的鼻间。
那是一封信,里面或许还装了什么重物,很硬。火漆印上是一只展翅的燕子,稍有江湖经验的人一眼便能看出这是什么印记,然后大多数人会选择沉默避让。
他不由犹豫了。
舒隽笑道:“听闻江城www.hetushu.com.com黄鹤楼赫赫有名,既然来了,不去观赏一番岂不可惜?”
伊春只觉眼前一红,炽烈的火焰便从四面八方一起朝自己扑来,她下意识地先去抓舒隽,谁知却抓了个空,她心中一沉,拔剑将燃烧的车壁砍得稀巴烂,没命地抱着脑袋冲出去。
他揽着伊春转身要走,美人赶紧追上去,委委屈屈地说:“好无情的男子,与我多说两句会死么?这香不是我配的,是大会主人秘制,今年的压轴香。你若买下它,里面有一半的钱便算我的债务……你别皱眉头,是大会主人说的,可不关我的事。”
葛伊春是强大的,不能轻易被打败的。在他心里对她一直是这个印象,她的鼻子眼睛长什么样,他脑海里是一片模糊,可是只要她一靠近,那种气味便令他振奋,像是发现了强大对手的那种兴奋。
话未说完,便见晏于非快步走出竹林,他在后面又大叫:“二哥!你安心等着我把那两人的脑袋提过来啦!”
那主人淡道:“不是今天也是明天,他向来逍遥自在的很,有享乐的机会又怎会放过。只管守在门前便是。”
难得的是她看上去甚是爽透利落,一颦一笑都令人觉得舒坦,毫不做作。她腰上还挂着剑,想来应当是行走江湖的侠女。如今这世道,侠女有这种气质的也不多了。
背后传来破空之声,是有人拿刀来砍,伊春本能地用剑一架,那人力气却极大,这一刀竟将她砸得朝前踉跄数步,一头栽进火海里,只觉浑身皮肤都要烧烂了。
汪叔缓缓摇头,声音很低:“世上有谁和钱过不去?”
有几个人想过来打招呼,但见舒隽搂着伊春,相当旁若无人,浑身上下更散发出一种“别惹我”的气息,众人只得看了一会儿,便各自去试香了。
变故只在一瞬间,不知是谁丢了个火把过去,“忽”的一下,火龙猛然窜上了天空,然后顺着地上的猪油飞快烧过去,眨眼工夫整条山道就烧得通红,老徐只来得及惨呼一声,很快就被烧成了个火人,在地上滚了几圈,再也不动了。
他回头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张开嘴想说点什么,最后还是吞了回去,默然退到一边。
晏于非默然垂首,看着伤口狰狞的右腕,他忽然感到,自己心里也存在着一个同样的伤口,还要大,还要深。
几乎是咬牙切齿的,他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道:“准备一下,即刻赶去江城。”
美人越舞越近,她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只试香盒,身体微微前倾,像刚刚收起翅膀的仙鹤,将那试香盒送到舒隽面前,跟着嫣然一笑,柔声道:“舒隽,别来无恙否?”
江面上隐约传来三弦声,放肆又悠闲,典型的舒隽风格,他总爱卖弄这些虚荣的。
横剑、斜刺、倒劈,有鲜血溅在脸上,伊春抬手想擦,可是脚底又是一滑,她狠狠摔了下去。那些刀光剑影一齐朝眼里扎来,要把她扎穿。
“小叔……”他发出一个低低的叹息,犹如耳语。晏门的二公子,许多人眼里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终于看上去有那么些脆弱无助,“小叔,如果你活着,告诉我要怎么办?”
大会主人特地选了一处新买的别院,东临湖水。自湖中心开始建了数个巨大白石台,中间以画舫接送。
最后身体狠狠落在一片厚实柔软的东西上,脑袋被什么硬邦邦的东西狠狠磕了一下,眼前顿时金星乱蹦,伊春哼也没哼一声便晕了过去。
拨开挡住视线的枝叶,在白光深处,忽然见到舒隽笔直地站在对面冲她笑,招手说:“小葛,怎么弄这样狼狈?”
“老徐快走!”
跟着看了两眼碎玉,他的嘴唇略带孩子气的抿了抿,若有所思地将两块玉捏了捏,飞快放进怀里。
说话间,却见一个蓝衣仆人匆匆走过来,垂头道:“舒公子,我家主人恭候多时,请随小人来。”
汪叔笑得狡黠:“既然如此,一千两拿来吧。那香我做了足足五年才做得如此精妙,安神舒缓是最好的。原本要卖二千两,但言丫头那笔债务算在我头上,便宜你一半,剩下的千两,只当她还了你的钱。”
舒隽忍不住在她脸上轻轻拧了一把:“你偶尔依靠一下我会死啊?真没情趣。”
梦里他只是个旁观者,模糊了很多年的小叔的脸在梦中是如此清晰。庭院深深,月光溶溶,小叔拿着匕首与人过招。那人身形犹如鬼魅,轻巧不能捉摸,短刀的光辉像呼啸而过的星光,短促急切,充满杀意。
葛伊春,你怎可以就这样死了?!死得这么狼狈又毫无声息!
小小山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只留下被焚烧过的痕迹,马车的废墟堆在山崖旁,隐约能看出是门主的车。
她慢慢点头,转身笑了笑:“我不担心,这次是我们两个人一起。”
三人喝了一会儿茶,聊了些家常,伊春憋住了好几个呵欠——这里凉快的很,香炉里也不知烧的什么香,让人浑身软绵绵,很想马上睡一觉。
老徐自己反倒先揭了帘子,神情疑惑,不太像是装出来的。
晏于非有些哭笑不得地抓住她的衣领,毫不费力地提起来,她出乎意料的轻而且瘦,真是这个看上去一折就碎的人挥剑斩断了自己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