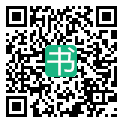第十五章 我之所爱水中沚
杞人不由得有些惴惴不安,心说怎么和彭莹玉临终前一样,一副交代后事的气氛。他只好低着头走上两步,来到床边。
韩邦道瞿然一惊:“你说甚么?”“我说甚么?”冷谦笑道,“我劝你好生吃药将养着,我每日子午二时助你行气活血,还可多活十余日,趁此先将他二人的婚事操办了,岂不是好?你便去了,也无憾也!”
这精彩的一幕,被躲在不远处廊柱后的冷谦和郭汉杰看得清清楚楚。“啊哈,”冷谦阴阳怪气地笑道,“汉杰,你便快有师母了,知道么?”“这个,”郭汉杰老实人不老实,“我早便猜着啦,不过恁么快,倒是意料之外。”
三人说说笑笑,暂时忘记了这几天来的烦恼。才走到韩家庄门口,一名仆人就急忙迎上来:“陈师傅,冷先生,二位可归来了也。小姐正劝老爷,老爷不肯吃药哩,二位速去看来。”
“哪,哪里……”杞人结结巴巴地回答。韩邦道追问:“那是嫌我女儿不漂亮,不贤慧么?”“不,不,”杞人的脸只有比绿萼涨得更红,仿佛关云长再世,“她,她,漂亮得很,贤慧得很……”
“我又何尝不想如此,可惜连年战乱,这城外哪里还有馆子?”杞人叹道,“便一两户卖村醪、白切肉……”“你怕英雄无用武之地么?”冷谦笑道,“且城里去呀。濠州虽不大,城西那几家馆子,你去了也不甚屈才。”
杞人瞟了冷谦一眼,打断了他的话:“老毛病又犯了也。”冷谦笑笑:“好,好,且不说书。当日两人一往一来的放对,堪堪四十余合,娄鹰一剑刺破了卢扬的衣袖,卢扬便即退后认输……”
“换了你,哪个傻婆娘肯要?”冷谦摆摆手,“走,且向韩邦道贺喜去。”
就在他迁往滁州的第三个月,也就是至正十四年的九月,元太师脱脱再度南下,总制诸王、诸省军马,镇压在高邮造反、僭称大周皇帝的张士诚,吓得张士诚去了帝号,俯首请降。十二月,脱脱突然接到皇帝的诏书,责备他“老师费财,坐视盗寇”,削去他的官职,暂时安置淮安。脱脱知道这是素来与自己不合的中书平章政事哈麻进献谗言的结果,他放声大哭,孤身驰马向北跑去,麾下百万大军,顷刻奔散。
韩邦道继续说道:“你年纪也不甚大,正当壮年……萼儿年轻守寡,这今后……今后可怎生孤单度日……我今将她付托于你,你可愿照顾她一生一世么?”
仆人答应一声,上前抱起小虎,一边哄着他一边出去了。冷谦再为韩邦道介绍了郭汉杰:“这是陈兄新收的徒弟。”郭汉杰行了一个大礼,韩邦道点点头,然后转向杞人,说道:“且走近些,我正有话要与你讲哩。”
小虎却先一眼看到了绿萼,挣脱了冷谦的手,扑上去叫:“韩姊姊!”绿萼急忙放下手中的药碗,迎上去一把把小虎抱了起来。“这便是小虎么?”韩邦道缓缓伸出手来。杞人走过去,叫小虎:“叩头,见过公公。”
“我便在这一两日要去了和-图-书,也无甚么遗憾,”韩邦道静静躺了一会儿,才眼望着帐顶,缓缓说道,“只是放心不下萼儿……”“爹爹……”绿萼扑到他的身上,低声抽泣起来。
“你怎的总将人心往功利上去想?”杞人把小虎扛上肩头,“咱们先回韩家庄上去罢,我不惯恁多人的场面——待静下来了,再到彭大师灵前烧香化纸钱……”
韩邦道这话说得狠,这哪里是谈婚,离逼婚也就不远了。杞人偷眼再瞧瞧绿萼,只见绿萼也正悄悄望向他。四目相交,绿萼的脸更是羞得通红,急忙转回头去,杞人却突然觉得膝盖一软,顺势就跪了下去。“叫啊,唤‘岳丈’啊。”韩邦道“哈哈”大笑。杞人感觉自己似乎是张了张嘴,但究竟有没有发出声音来,可就连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韩邦道叹一口气,只好就女儿手上把药喝了,又摆摆手,两人只得并肩告退出来。杞人只觉得自己行走在云堆里,脚下飘飘然的,不知怎么的就已经离开了卧室。绿萼掩上门,低声说道:“陈师叔,我爹他这般逼迫你……”
韩邦道轻轻抚摸着绿萼的长发,微笑道:“傻丫头,人莫不有死,哭些甚么?”他突然望向杞人:“她也甚是苦命,才死了丈夫,我这……”
杞人脑筋再木,也听得明白韩邦道究竟是在说些甚么了,当下更是慌得手足无措,嗫嚅了两声,没敢回答。“果然哩,”韩邦道的脸色重新又沉了下来,“我知你嫌弃她是个寡妇!”
“吃与不吃,有何分别,”只听韩邦道叹了一口气,说道,“我自知这伤势是无救的了,也便安从天命。只是放心不下你也……”
两人蹑手蹑脚地从廊柱后面蹩出来,经过杞人和绿萼身边,竟然没被发现。冷谦举起袖子,在杞人眼前挥了挥:“此番真的着了魔也。”笑一笑,推开卧房的门,就走了进去。
“是也,是也,”杞人拍拍骑在自己肩膀上的小虎的屁股,“若无兵燹,小虎也不会忒煞可怜,做了孤儿。”冷谦道:“他今有你做了义父,也算苦尽甘来了。往事已矣,多嗟多叹何益?”
杞人回头瞟了郭汉杰一眼:“讲得忒轻松呵,自开一家——你借本钱与我?”冷谦道:“且与韩邦道商借罢,他虽不是甚么大财主,这些许小钱总还有的。”杞人摇头:“我与他相知也只泛泛,怎好冒然开口……”“恁般说来,交情若是深些,便开得口,借得钱喽?”冷谦故意逗他,“罢罢,我且离你远些。”杞人终于也笑起来了:“正是,正是,你我至交好友,便请借个百八十贯来应急罢。”
杞人、绿萼守丧一年多,到了至正十四年的七月,朱元璋升任总管,攻克滁州,汤和在他麾下为将,就在滁州城外盖起了一家小小的酒馆,请杞人师徒前往打理。朱元璋很喜欢吃杞人炒的菜,虽然现在身份不同以往了,仍然经常带着汤和、邓愈、吴祯等人微服出城,到杞人的酒馆里来偷得浮生半日。杞人在滁州城外一住就是十和图书多年,直到至正二十五年,也即宋小明王韩林儿龙凤十一年,才搬去应天府。
“我却不想进城哩。”杞人低着头只顾走路。“与其投靠他人,”郭汉杰在后面大出傻主意,“不如师父自开一家,我便充作伙计。”冷谦“哈哈”大笑:“便你这般好相貌,面上恁长一道刀疤,你做了伙计,可有客人敢上门么?”
“今回彭和尚将那个甚么汤和托付你照顾,你怕是离不得濠州喽,”冷谦抱着双臂,和郭汉杰一起跟在杞人身后,边走边说,“何不便在此处寻家馆子,做你的厨子老本行?”
杞人深吸一口气:“你且放心,我,我会好生照顾她的,便如待亲生侄女一般。”韩邦道突然变了脸色:“本非亲生,哪里能当亲生的一般?!”
“不过藉此自抬身价罢了,”冷谦看了摇头,“为淮西白莲教主、天完国的国师主持了丧事,日后还有哪个敢小觑他郭子兴哪?这一来,孙德崖、彭大、赵均用他们,可便被压下去喽。”
杞人和冷谦急忙奔往后院卧房,还没敲门,先听到绿萼的声音:“爹爹,你吃药罢。不吃药如何得好?”
绿萼也不知道再说甚么好,羞得也低下了头。两人各自望着自己的脚尖,良久不言不动。空气在这一刹那,也似乎凝固了不再流动似的……
“我,我……”绿萼的面孔羞得通红,“我只当他是长辈哩……”“少掉花枪,”韩邦道说道,“你娘走得早,我一把屎一把尿将你拉扯大,你这点点小心思,爹怎看不明白?”说着话,又转向杞人:“大丈夫休婆婆妈妈的,是否答允,给我个回复——莫非,你怕低了辈分?”
冷谦摇摇头:“我也未见过此人,是自娄鹰处听闻的。”杞人问道:“汉北‘穿心剑’娄鹰么?”冷谦点头:“正是。七八年前,约摸至正五年前后罢,某一日,那卢扬来至沔州娄家庄上,欲与娄鹰较剑,是娄家庄客以他无名,拦挡在门外。卢扬也不多话,提起剑来便刺倒了两名庄客,说:‘请娄大侠明日午后,到城南汉水岸边来寻我。’待娄鹰出看时,那两个庄客伤得倒并不重,只是剑伤所在,极为诡异。娄鹰心动,第二日便前往寻他……”
杞人不说话,只是紧紧搂着小虎。冷谦和郭汉杰也不开口,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快要接近韩家庄了,杞人才象突然想起来甚么似的,问冷谦道:“那日听得宫秉藩言到,山西出了一个‘剑圣’卢扬,是你说与他知的,不知何如人也?”
到了日子,也没延请多少宾客,只有濠州城里的几家亲眷,及代表着郭子兴的汤和,十余人摆了两桌酒席。杞人骑毛驴出了前门,绕韩家庄大半圈,从后门进来。绿萼红巾盖头,由杞人扶着上了驴,接出后门,一般绕着圈子,再度进了韩家庄。鼓吹声响得热闹,一众宾客听了,纷纷起身迎候。新人进了正厅,只见韩邦道面色灰暗,被两名仆役搀扶着,挣扎着前来坐着受了三拜,又被掺回屋去歇息。东厢房早经https://www.hetushu.com.com打扫清洁,作为洞房,仆妇们拥着新人进去。礼仪诸多减省,只有好酒好菜,绝不吝惜,流水般给客人送上来。
韩邦道笑道:“你不见他唤萼儿‘姊姊’,怎么倒唤我公公?唤伯伯可也。”绿萼把小虎放在地上,小虎跪在床边,磕了个头,说:“伯伯安好。”韩邦道笑着眨眨眼睛:“好乖巧的娃儿——老六,且带他花园里耍子去,再寻些好吃的与他。”
杞人急忙帮小虎揉揉额头,还好没受甚么伤,连肿块也没起一个。再抬眼往屋里望去,只见韩邦道躺在床上,身上盖了厚厚的被子,才两天不见,人似乎瘦了许多,脸色也青黄色的十分怕人。绿萼端着药碗,坐在床边。
虽然绿萼的声音细得好象蚊子叫,杞人倒听得清清楚楚。此刻身外万物,对杞人来说,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如置身梦境。他偷偷掐了大腿一把,强自把自己从云端里扯下来,也轻声说道:“不,不,不,说甚么逼迫……我,我自知高攀不上,我,我……”
冷谦鉴貌辨色,知道韩邦道想单独和杞人谈话,于是一拉郭汉杰,唱个喏道:“小虎有些畏生,咱们且去领他玩耍。”说着话,两人一起走出屋子去,还顺手把门给掩上了。
“不,不,不……”杞人这时候只说得出一个“不”字来。“好罢,”韩邦道抓住杞人的手,“我是将死之人,你休教我死不瞑目。你若答允了,便跪下来磕个头,唤声‘岳丈’,若定不肯使我安心,要我阎罗殿里做个怨鬼,那便竹竿似立着休动。”
冷谦摇摇头:“你伤势本不重的,不肯善加调养,才耽搁到今日地步。我是救你不活了,这数日无常便来拘了你去。只令爱好可怜煞,自此守丧三年,不得谈论婚嫁,孤寂一人,独守空房以对青灯……”
听了这话,郭汉杰还没觉得怎样,杞人却长吸了一口凉气。冷谦继续说道:“初见此人时,态度恭敬得紧,第二回便有些意气飞扬,到第三回,嚣张跋扈,已大不似前也了。不过‘剑圣’之名,却不是他自取的,他战遍山西河东诸路剑客,已无敌手,此番又胜了陕西娄鹰,自有那溜须拍马的小人,给起这般一个绰号。”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韩邦道皱眉道,“却又为的何来?”杞人回答道:“是,是我……在下高攀不起,在下不过,不过一个厨子……”韩邦道撇撇嘴:“想那兴周吕望,不过渭水渔夫,辅汉诸葛,卧龙冈上农人,陶朱公做了行商,张子房漂泊江湖——你是市井隐逸,难道我不晓得么?门户登对,我说是便是了。你道我这老眼懵懂,挑错了女婿?若如此,你剜了我双目去!”
来到韩邦道床前,先唱了个喏,然后冷谦就伸出手去,给韩邦道把脉。韩邦道睁开眼睛望望他:“有甚么用?阴司的无常便在门外,这便要锁了我去也。”
杞人道:“能与娄鹰对战四十合,也算甚了得了。若想当‘剑圣’之名,可又甚不自量。”冷谦道:“且听hetushu.com.com我分说下去。那日娄鹰爱他的剑术好,要留他庄中一叙,那卢扬却婉言谢绝,飘然而去。一晃年许,卢扬再到沔州,此回娄家庄客们却不敢拦阻了,通报了放他进去。多的话也不用细讲,总之二人再次较量,这一回,翻翻覆覆斗了百余合,娄鹰才侥幸胜了半招……”
第二年的十二月,脱脱在流放地云南被毒死。元朝这株参天巨树,最后一支还能抽芽的枝条——即使是长歪了的枝条——也被折断了,他距离死亡,也就已经不远了……
“你都听得了,”韩邦道叹口气,“讲得也有理。只我这般模样,再无力操办了,都有劳贤弟了也。”冷谦一拍胸脯:“包在某身上便是!”
“百八十贯,忒煞小家子气,开鸡毛店么?”冷谦摇头叹道,“若我仍在大都做着协律郎,休说区区百八十贯,便千八百贯,都从内库里盗将出来了也。”
“定是韩邦道托孤哩,”冷谦笑道,“他们两个虽在心里你情我愿的,若非用棍子赶,哪里会走到一处去?”“师父面皮忒薄,”郭汉杰说道,“若换了是我……”
※※※
杞人还没回答,冷谦突然又“哈哈”大笑起来:“此人近日踪迹渐隐,莫不是真的白日飞升,做了天上神仙?哈哈哈哈哈哈~~”
韩邦道笑了一阵,突然咳嗽起来,绿萼赶紧去抚他的胸口。韩邦道挥挥手,勉强说道:“……不碍的……你去扶你好女婿起来,先出去罢,我一个人静一会。”“好女婿”这三个字,听得绿萼和杞人都是既羞且喜,杞人没等绿萼来扶,赶紧爬了起来。绿萼取过药来:“爹爹,你先吃了药罢。”
我怎么样?是要允诺么,总觉得不大对劲。要婉辞呢,又实在可惜,而且怕伤了绿萼的自尊。杞人嗫嚅半晌,只好把头低下去,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郭汉杰问:“两人可较量了么?胜负如何?”冷谦笑道:“你忒急性子,且待我慢慢地讲来。且说那卢扬态度却甚恭敬,见了娄鹰,先告了伤人之罪。娄鹰爱他剑术诡奇,相谈几句,就便动起手来。这一场好杀呵,正是……”
“乱世人不如犬,”杞人叹道,“做的甚么官?还是老老实实下乡种地为好。”“好?便能好到哪里去?”冷谦的脑袋摇得更勤了,“是故明晓得天下太平,百姓依然难免九饥一饱的,却总是盼他太平,多少免受些兵燹之灾也好。”
婚后才七天,韩邦道终于油尽灯枯,撒手西去了。就这样,婚礼刚完,又忙着办丧事,杞人缺乏处理这种事情的能力,也全靠冷谦一人操办,冷谦忙前跑后,时常私下对郭汉杰苦笑:“这都是我自招惹来的哩。”濠州帅郭子兴亲来吊唁,这次丧礼,可比先前的婚礼要隆重多了。汤和也跟着郭子兴来到韩家庄上,悄悄询问杞人今后的打算。杞人叹口气:“我却住不惯这偌大庄院,待除了服,便寻家馆子去做本行罢。”
“说的是,”杞人问他,“先时你助朋友,自内库里盗金,后话如何?”冷谦笑道:“我本意要助他度日,
m.hetushu.com.com难道反害他?自是早送他全家躲将起来了,朝廷休想捉拿得着——只是我那升斗小官,再休想做喽。”
杞人“咦”了一声,只听冷谦继续说道:“卢扬再去,约摸一年许,三访娄鹰,这一回哈,交手不过三十合,娄鹰已呈败相。那卢扬却不紧逼,喝一声‘住’,跳出圈子,向娄鹰拱手道:‘多谢娄大侠指点,卢某就此别过,再不来搅扰了也!’”
杞人想了一想,说道:“数年间,剑术精进如此迅速,待得今日,休说‘剑圣’二字,便武林泰斗,他也当得了。这般异人,可惜无缘得见。”冷谦笑道:“你莫想得歪了。武艺修炼,与诵经读史一般,或这两日豁然开悟,或三十年不得寸进,都是有的。况从来谦则益,满招损。那卢扬初时谦抑,怕不各处去寻人较量,艰苦磨砺,是以精进;其后狂妄自大,想其剑术,便未必能再有进展也。三年能败娄鹰,便如此增益能保持到今日,说甚么武林泰斗,大罗金仙都当得哩!天下焉有是理?”
※※※
仆人高声禀报道:“老爷,陈师傅与冷先生归来了。”杞人推开门,迈步就进,忽听“哎呦”一声,肩上骑的小虎,额头撞上了门框。“小心小心,”冷谦急忙把小虎从他肩上抱下来,责怪道,“这义父甚无头脑,可怜小虎……”
※※※
就这样,不顾杞人和绿萼的反对,冷谦就为他们操办了婚事。他既作媒人,也暂充男方子弟兼作使者,匆忙准备了头面首饰、一头小羊、两瓶村醪,到韩邦道床前来下聘。韩邦道起不了床,告不了庙,就写了祖宗牌位,放在床前,勉力支撑起身子,作了几揖,叫绿萼拿过皇历来看,三月廿一日是中吉之日,遂订为婚期。
杞人愣在当地。韩邦道怒色稍霁:“我唤你一声兄弟只是客气来,咱们既非亲眷,也非同一师承,你与文焕亡父也不过道义之交……”杞人一颗心“扑通通”地乱跳,连大气也不敢出。
“不,不是……”杞人一着急就结巴,这回结巴得最厉害。他偷眼瞧瞧绿萼,绿萼早已经停止了抽泣,恰在这个时候抬起头来:“爹,你在讲些甚么呀!”“讲甚么,讲你的终身哩!”韩邦道摆出了做父亲的威严,“你若愿意,休得开口,有爹爹与你做主。若不愿意,却又为何这两日尽在我耳边叨唠‘陈师叔’长,‘陈师叔’短的?”
郭汉杰伸伸舌头:“短短两三年间,竟能这般变弱为强,赢了‘穿心剑’娄大侠,此人果然了得!”杞人也说道:“若三十合能败娄鹰,这便勉强当得起‘剑圣’二字。”冷谦笑道:“此人诡异之处,并不仅如此。据娄鹰说来,与此人三番交手,他的剑术初则诡谲,继而流畅,到第三回时,只觉朴素寻常得紧,偏是娄鹰费尽功夫,寻不出丝毫破绽来!”
彭莹玉的丧事,濠州帅郭子兴一力承担了下来,按照白莲教的规矩,既请和尚念经,也请道士祭文,做了好一场不伦不类的法事。不过全濠州的红巾军全都白布抹额,为彭和尚戴孝,倒也隆重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