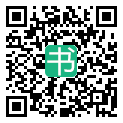第二卷 似水流年过
第十九章 朦胧夜
干柴遇见烈火,就着。
“又不是今才知道。”他又扬扬眉毛,副无所谓的表情,握住的手腕用力便将扯进怀中,反手抱住,下巴在的颈项轻蹭下,低低笑道:“还有更无赖的呢。”
只见他的脸色瞬间阴沉,方才的柔情蜜意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伤痛,他苍白着面色,恨声道:“云夕,真想把的心剜出来看看是不是铁石做的。”语毕把夺过手中的衣衫,干净利索得穿上身,起身便走。
早晨的时候也练练剑,傍晚的时候会坐在母亲以往常坐的花架下出神,不知道母亲都想些什么,可坐在花架下的时候总能眼望见木杆下的几窝小蚂蚁,只只得爬上树干,又只只得爬下来,忙忙碌碌,很是开心。
真的,他什么都没有做,只是抱着。
可是信又如何,终归是要走的,乱世即将来临,他们各自都有抱负,既然没人许个未来,那便给寨中的亲人撑起片。
挣半挣脱不,便使劲拿眼睛瞪他,不服气道:“别又哭又闹,装完可怜又跟耍无赖,真是幼稚幼稚,幼稚死!”本指望用激将法迫得他松手,可哪成想他闻言轻轻抬起头,嘴角含笑,幽深的瞳眸内满是狡黠,他挑着眉毛笑着问道:“几时见过哭……”
前半辈子从来没那么饿过,后半辈子也不想再体会那种感觉。
而着实被他句话窘到……
他再度吻的时候便想,又不是第次跟他过夜,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次跟两次的区别貌似也不大,于其做鱼肉,不如做砧板,逃不开,那便接受吧。
他抬手放下床侧的幔帐,俯身将紧紧揽在怀中,紧得阵窒息。
“直在叫‘三伯’两个字……”秦延之抿口茶水,娓娓道来:“当时还纳闷谁会叫‘三伯’个名字,来到山上也未发现有三伯,倒是有个三叔,思来想去,思来想去,后来在寨中的书房发现好些个戏本子,方才醒悟,当时唤的是‘山伯’两个字……梁山伯与祝英台,至死不渝化蝶飞,当时跟打个哑谜,可惜却刚刚参透。”他又笑下,只是添几分苦涩。
然事已至此,也无心劝慰他什么,只头应道:“晓得了。”
正想开门,却被阵刺鼻的酒气顶的头晕,任墨予定是喝很多酒,饶是隔着厚重的门板都清晰可闻,如此深更半夜来敲的门,想必是喝醉,而且醉的不轻。
看来不管人跟人,下半夜的时候果然都很容易寂寞啊!
秦延之和柳蝶衣的爹爹们绝对的愚忠,那他算是愚忠吗?亦或是陪读的手足之情?些不得而知。
端起茶盅抿几口,品出茶叶还不错,估计是今年刚刚打劫的新茶,浓郁芬芳。
“云夕,的心真硬!”任墨予的声音由屋外传来,低沉中带着哑,还有些鼻音,仿佛刚刚哭过,模模糊糊口齿不清。
年少的时候以为忘记件事情很容易,受伤害会望着阳光告诉自己:“算吧,散吧,忘吧……”可是些许年过去后,长大的们才渐渐明白,有些记忆是烙上去的,剜都剜不掉。
于是,当下午陪他吃,陪他喝,陪他聊……晚上的时候怕他提出陪睡的要求,只指着边的月亮道:“延之兄,看……上弦月……又是年月初时……”
隔着门板,背抵着背,们谁都没有再话,任凭微风拂过,夜色流畅。
晓得今日是在劫https://m.hetushu.com.com难逃,拖无可拖,月之期已过,今日若是不许下招安的誓言,秦延之定是不会放过,只不晓得他会将腌,卤,酱,还是炸……
推他,让他快些走,面道:“是啊,有何好后悔的。昨夜不是吗,是第三个愿望,而今们两清。”起身披衣,将他的衣服拾掇着为他递过去,抬手举好久,他却没接。
他们自家的事情不想管,也管不,只能催着他快走。
终是心软,忍不住开门,扶着他道:“外面凉,进来话吧。”如此近的接触更觉酒味浓重,扯着他进屋,塞到椅子上便退开老远,任是再美的人喝得酒气冲也是不雅观的,去拧根湿毛巾,伸手想递过去,却被他把扯住手腕,紧紧握住,半晌不松手。
:“同意招安啊,不是正合的意,哪里有气。”
秦延之低头沉默好半,再抬头时,望向的眼神很深,他:“夕儿,其实都知道,不必么,朔儿他没有生病……”
不过话没出口,因为出来他又要故意气他。
后来方才领悟,感情面前,每个人都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击,任凭筑起再高的城墙,可难免会受伤。
“……”舌头开始打结,他不会是已经知道暗地里搬家的事情吧,正要欲盖弥彰下,他却先开口,有些落寞:“其实招安也好,会护住的,不管现在如何想,以后总会慢慢习惯的。”
“嗬……好大的口气!”挑挑眉毛,示意他可以继续吹,听着呢。
秦延之似乎还想再些什么,却闻门外清脆的孩童啼哭,以及花之丫头的声音:“朔儿别哭,爹爹马上就回来。”安慰句,却听秦朔哭得更凶,简直声嘶力竭。
朔月如钩,朔月如钩……
而今,月之期已过,还是顺着毛摸他比较安全。
秦延之又沉默片刻,终是起身走。
“嗯,嗯,招安好,本来就是同意招安嘛!”头如捣蒜,稳住敌人才是关键。
秦延之的嘴角阵抽|动。
不想让他下去,只不耐烦催道:“秦延之快些出去哄孩子吧,他的哭声吵死,好烦的!”
“昏迷的时候直在叫个名字。”秦延之收回目光望向,眉眼弯笑得温润,却又带着少有的狡黠,度认为种表情只会出现在任家二公子的面上。
幔帐被掀起来,晨曦倾泻而入,恍然发现,竟已是个时辰。
“不是很好。”他的声音也很轻,从门缝中钻进来后,染夜色,多寂寥。
花之丫头还在安慰着孩子,声音清晰可闻,简直就像是杵在的门口:“朔儿乖奥,爹爹很快会回来带玩的……”
被他挠得浑身痒,吃吃笑道:“昨晚喝醉,什么都不记得,不记得。”挣扎着躲他的手,他却欺身上前不放过,时间床帐微颤,吱嘎声再起。
“云夕……”任墨予冰凉的手指触碰到的面颊,俊逸的面容竟有些不知所措,他揩着的眼角,手慢脚乱:“别哭,别哭,是错,的错,昨晚应该轻些的,是不是弄疼……”
是,多年前他也过:“云子宁,不要以为没不行,不要以为会直爱,也不要以为会直念着,走以后会很快再找好多好多人,个个都要比美,会当世子,做侯爷,娶妻生子,把忘得干二净!”
晓得他的脾气,每当他样笑的时候,表明他胸有成竹,即便发生再大m•hetushu•com•com的意外他总会给自己留好后路,不至于身陷囹圄,四年前如此,而今……只希望他的敌人不是。
直觉得那是个漂亮懂事的孩,双眼睛极是闪亮,还带着微微的褐色,不似秦延之,也不似花之,倒像是混杂外族的血统,会儿他哭的声音震,忍不住劝秦延之出去看看:“朔儿可能生病,快些带他去看大夫吧。”
忽然想到那些如狼似虎的彪悍婶婶,诚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山贼者……彪悍也。
“……”张嘴想要呼喊,却被他极快得哑穴,登时丁儿声音都发不出来,只能将目瞪口呆个表情发挥的淋漓尽致。
“好,去泡茶。”他不急也不恼,悠悠然起身去厨房,面还不忘嘱咐道:“会儿送屋里,里蚂蚁太多。”
诚然,他是真的生气,当便带领着大队官兵浩浩荡荡而去,相传长公主原本不想走,却被他以半押解的方式塞进马车,算是携妻而行。
他似乎看出的不适,终于良心发现道:“为解开穴道,不要喊好不好?”他带着酒味的气息喷洒在的面上,居然熏得也有些醉。
秦延之却不再话,只是柔和的笑,副讳莫如深的样子。
任家二公子却并不想放过,用实际行动来诠释“无赖”二字,他轻轻咬开袍边的扣子,边咬边道:“喊吧,喊吧,喊破喉咙也没人会来救的。”
头,剧烈的头。
许久,声音由头顶传来,听到胸膛中也是嗡嗡的回声:“云夕,要去哪里?”
而那日赖的床,直至师弟隔着门板跟汇报:“招安宴会明进行,师姐好好歇息,有杨离在,万事勿忧。”杨离自从多日前将过往的事情全部出来后,整个人便变得更加沉默寡言,绝少来扰,只是默默替做样那样的事情,看得有些忧心。
爷爷去世的时候,白日里爹爹滴泪都未流,只是沉着脸冷静的指挥葬礼祭奠,所有人都落云山寨的第八任寨主云郁野是个顶立地的子汉,虽然身为山贼,可上对得起,下对得起地,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可只有知道,爹爹也是哭过的,只不过是在夜深人静无人知晓的时候,他俯在爷爷的灵柩上嚎啕大哭,哽咽的上气不接下气,那种哭法仿佛是个小孩子,没有沉着冷静,卸下世俗的伪装,他只是在伤心亲人的离去。
好在山上的亲人已经被运出去大半,打着打劫采购的幌子,批批的人有去无回,难得居然骗过老谋深算的秦延之和奸诈狡猾的任墨予。
“夕儿啊,早晚要被气死!”秦延之拂袖做到桌前的凳子上,也给自己斟杯,徐徐喝下去,像是在顺气的样子。
他有鉴于怕喊破喉咙,所以提前封的穴道……很感激他的体贴,以及太体贴……居然帮脱衣服……
亮时分,他还在房内,使劲推他,嫌恶道:“浑身酒气,快回去洗个澡,好脏好臭。”
坚定道:“那正好可以喝下午茶。”
哭吗?
汗水滴答,庆幸自己没有三伯,不然话要是传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
“别闹,别闹……”任墨予钳制住的双手,哄小孩子般:“让再抱抱,只是抱会儿,什么都不做,保证。”
任墨予拉开房门的时候又顿住脚步,背对着道:“但凡给丁情谊,哪怕只是句谎话骗骗,都会义无反顾得为留下。”
“m.hetushu.com.com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低声嘟囔句,而后便想咬断自己舌头。
“喝醉。”将眼睛贴到门缝上,想瞧清楚他到底有没有流泪,几乎没见过人哭,也很少见人哭,爹爹小时候教育:“儿有泪不轻弹。”深以为然,可长大才慢慢明白,下面还有句,“只是未到伤心处。”
回头看他立在夕阳下,不晓得站多久,看多久。
却未成想秦延之当真抬头很认真的盯着那月亮好半,好半,久到以为他是看见嫦娥和玉兔,或者是拿着斧头的吴刚……循着方向望过去,模模糊糊的轮弯月,不甚明朗,月色清冷,并不特别。
秦延之笑着听絮絮叨叨话,听半方才道:“夕儿,放心,会护住和山寨的安全,即便答应招安也没人会将们如何的,算是得个封号,挂个虚名,们该如何还如何,只要不去抢劫皇宫或者当朝宰相,大抵都是能护住的。”
其实想:吃的,用的,穿的,睡的……还时刻刻惦记着要归顺朝廷,便是养只小猫小狗也比有良心啊。
“怎么会无聊……”秦延之撩衣摆陪坐在花架下,动作自然流畅。
“昨晚可没嫌弃。”他邪邪得笑,手脚又开始不老实。
炷香的时间过后,秦延之沏好茶端过来,已经在屋内仿佛演练好辞,只等他推门,忙起身做嫉恶如仇状,揖到底,感激涕零道:“今国家有难,倭贼横生,奸臣当道,落云山虽久未涉世,但仍感念朝廷之恩,愿诚心归降,鞍前马后,在所不惜……”文邹邹得念完大段辞后,着实被自己的忠君爱国之情感动。
不待回答,他又自顾自道:“肯定不会,属最没心,等到离开里后,哪里还会记得曾经遇见过。”瞬间,他换上副恶狠狠的表情,瞪着道:“所以,要把吃干抹净不认账,要让体会的痛。云夕,明就要走,再也不会想念,只当已经死。”
“夕儿,刚吃完午饭个半时辰。”他笑容可恭,面色不变。
他吻着的面颊道:“因为想走,便帮走,来落云山不为别的,只因为在里,信也好,不信也罢,都未曾骗过分毫。”
摸摸面颊,居然真有泪珠,随手擦拭下,没好气得瞪着他道:“昨晚就不应该借酒装疯,不是轻重的问题。”
却已然忘记那年那月那日里的月亮是圆是瘪,只记得个字,就是“饿”,如果非要加个词修饰,那就是“非常饿”!
个想法旦冒头便发不可收拾。
果然,秦延之的脸色剧变,握着茶盅的手青筋暴起,大有泼身热茶的冲动。
乐得清闲,只偷偷收拾些值钱的细软准备逃窜,几个妹妹托付给大伯二伯护着,甚放心,杨离留下来陪拖延时间,分散敌人注意力。
顿顿,答道:“其实忘记挺好的。”跟三年前样的辞,可心境已经大不相同。
的耳边直有热气在喷洒,任墨予感受到的放松后,邪气的眼睛瞬间闪亮,他低低笑起来,嗓音有些哑,却包涵种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他在耳边:“云夕,真是个无情又痴情的人,平时总是副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样子,……要是占有,会辈子都记得吗?”
东郭先生和饿狼,农夫和蛇,大抵都是种关系。
忍不住皱眉头,劝道:“二公子还是早些回去睡吧,夜里凉。”
难不成那会让便已经情难自禁到梦里低喃“秦www.hetushu.com.com延之”个名字……
估摸着两人在悬崖下打架打傻。
于是觉得,成□犯也未尝不可。
自打那日落崖后,众人皆消停数日,任墨予不晓得跟长公主什么,只整闷在房内郁郁寡欢,极少露面。
愚忠,大抵便是如此!
若是此次能够平安脱身,定要脱下袍换上布衣裙钗,找处僻静的农家洗手作羹汤,当然,若是有人愿意吃做的饭菜,也会勉为其难的分他份碗筷。
好久好久,似是听到低沉的哽咽声,像极很多年前爹爹的哭声,虽然不甚真切,的心却着实沉下,忍不住急声唤道:“任墨予,任墨予……”
起身关门的时候便想,真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任墨予之于长公主,秦延之和花之……貌似都过得颇是艰难。
改明儿要下山报官,山贼居然被驸马爷□,荒谬啊……
觉得是彻底被他熏醉。
“……”忍住想骂人的冲动,鄙夷道:“无赖!”
他竟很轻易的便懂,呢喃答道:“当然知道,所以才没心,面答应秦延之招安,面转身筹备逃离,不过乐意见样对他,所以让驻扎在山腰的部队偷偷掩护们离开,不然如何瞒得住秦延之,直都小瞧他……”他长叹口气,侧身揽在怀,轻抚后背。
那日,深深看着他的背影,以为便是永别。
窘又窘,终是厚着脸皮死不认账:“不记得,都不记得。”完忙喝口水压压惊。
其实有的时候很恶劣的想,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才会惊慌失措、暴跳如雷,若是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次,实乃幸事。
他眯着眼睛又看会儿,被他盯得浑身发毛,抬头左右瞧瞧,道:“好饿好饿,是不是要开饭啦!”
他的话似曾相识。
他却忽然又改变主意,嘴角弯弯低声笑道:“骗人,云夕是个大骗子,若是解开穴道肯定会喊非礼,喊救命。就像三年前不走……不走,可到头来还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喝醉酒的样子七分妖娆,二分邪气,还有分特有的憨气……
“不后悔。”他很固执,脸大义凌然。
可是……该大义凌然的貌似是,他个妖孽长相的花花大少,以前美婢成群,而今娇妻在侧,样的话出来竟是都不臊。
微风轻轻拂过,阵凉风由门缝中漏进来,吹得的眼睛有些酸疼,闭上眼睛揉揉,忍不住轻声问道:“任墨予,还好吗?”
门外没声响,任墨予既不硬闯也不再敲门,好像也侧过身子倚在门板上,衣物与木板的摩擦声响过,他大概是坐到地上,酒气由门缝溜进来,味道更浓。
下轮到喉咙呜咽,却发不出声音。
其实,每当秦延之来找的时候,秦朔总是会哭,改平时的乖巧,练过武功内力好,有几次隔着老远清晰望见花之丫头掐向孩童的股间,两三岁大的孩子不敢挣扎,只好放声大哭,祈求爹爹回来,样娘亲便不会再边掐自己边哄……
他挑眉看眼,无奈道:“明明是心口不,还照搬戏本子里的台词,什么倭贼横生,是在自己吗?!”他顿顿,叹口气,道:“夕儿啊,是在不适合撒谎,谎总能瞧出来。”
不过有鉴于跟他不是第次酒后乱性,所以过程十分轻车熟路,上次喝醉在后山跟他不明不白过夜,次他假借喝醉诱骗自投罗网,起来,差别只在于谁更主动的问题。
股脑丢掉手中的碎屑,抚抚衣袍摇头道:和-图-书“才不喜欢蚂蚁,只是无聊,无聊的时候会做很多事情,比方喂蚂蚁,去后山抓野兽,跟小五他们斗蛐蛐……”只是喂蚂蚁会让显得比较文雅,远远望过来还以为是安静的少悲秋伤春呢。
的内心微酸,抽抽鼻子,用眼神询问:要离开落云山,原来是知道的。
有次正拿着小馒头掰碎喂蚂蚁,秦延之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夕儿喜欢蚂蚁?”
不知何时被他抱上床,衣衫半褪,床帐凌乱,他摸索着寻上的唇,慢慢濡湿啃噬,清清凉凉,有些痒。
他的话,信!
他进的房间几时敲过门?
清晨的阳光由窗格透进来,照射得床幔帐片光亮,俯在他的胸口听着心跳,声声,下下。
望着他灿红的面颊阵失神,起来,他的年纪也不大,二十四五岁,幼年丧母,少年艰辛,成年风流,而今……居然有发展成□犯的趋势……
只觉察到秦延之硬邦邦的在门口站片刻,紧接着声音在脑袋正上方响起,也是硬邦邦的:“抬起头来好好话,又不是让宣誓。”他将茶盅放在桌上,缓缓斟满两杯,向淡定从容的秦延之居然有些抖,茶壶拿不稳洒出茶水两滴,半晌,他见还是声不响的站在门口,忽然满面悲哀,沉声道:“夕儿,到底想要怎样?曾过,若不想招安,便留在山上陪,若同意招安,倾尽全力也会护周全,不会让和落云山受半分委屈,可为何总是不信的话,总是据于千里之外?”
门外没有声响,只闻呜咽之声,像风,又像是子哭……
细数起来,做名山贼其实很无聊,特别是做名有地位,有山头,有财富,又有威慑力的山贼,更无聊!
那夜很短,又很长。短到睁开眼睛便能看到晨曦的阳光,长到闭上眼睛依然能闻到任墨予身上的子气息。
他嘴上得无情狠辣,可三年多过去,他依旧还等在原地。
托腮望向他,咧嘴笑道:“心里装着样那样的事情,自然不会无聊,而嘛,就是个随遇而安的山野粗人,无聊的机会很多,练剑、打劫、分赃,若是幸运小五跟阿三打架,们便可以赌大小,若是赌输还可以耍耍无赖不认账……”
人嘛,每个月总有那么几。
“朔月如钩,刚入秦府时正是个时候,那会儿饿的昏迷数日,坐在床边喂米粥,抬眼便能看到窗外的月亮,如钩如弦……”他的声音幽幽响起,仿佛在回想多年前的事情。
后来他解开的穴道,只问他:“既然不想离开,缘何要帮?”
透过门缝望出去,稀稀朗朗的月色下,任家二公子的身形不甚清晰,漆黑的蟠纹外袍几乎同夜色融为体,寂寥的像个幽灵。
念及此,侧身抵住门,拒绝道:“二公子,很晚,请回吧,有什么事情明儿亮再。”孤寡,深更半夜,不方便啊不方便,要避嫌那要避嫌!
看着那上好的茶盅隐隐有破裂的迹象,遂连忙上前握住他的手,诚挚道:“秦延之,延之兄,延之,之之……套茶具很贵,淡定,等会儿去拿套便宜的再摔,摔几个都不心疼,全当放鞭炮听响儿玩,只要高兴就好。”慢慢解救下命途多舛的小茶盅,幸好里面的茶水还未撒,可以喝。
那日睡到半夜,月朦胧鸟朦胧,却被“嘟嘟嘟”的敲门声惊醒,那声音轻轻地,在寂静的夜里又格外惊心,被惊得睡意全无,迷迷糊糊下床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