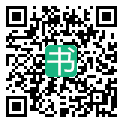烽火篇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长天留恨
归云捏着拳,暗自落泪。她扳住展风的肩:“你要做什么?你想做什么?”
卓阳无眠了。他知道蔡将军已经两天两夜未入眠,还有这等干云的豪气。
急救队的人们分不清生存的人或尸,处处大喊:“还有没有人活着?”不放过稍微的发出微弱求救的生还者。也有生命力坚强的生还者。“妈妈!哇哇哇!妈妈!”是突如其来的猛亮的儿啼!急救队的人飞跑过去,他们也跟着跑了过去。不远的地方,已成废墟的铁轨上,竟然坐着一个小小的孩子!他半身血满脸泪,幸存的悲号冲破硝烟仍未漫尽的废墟。那时那刻,人们震惊了。这里幸存了一个小生命,孤零零的,坐在萧条的铁轨中央,四周却没有其他尸。怎么竟然就会出现在这里?或许是濒死的大人们拼了命来保全的。蒙娜一把抢下卓阳手里的相机,卓阳再抢过来,泪逼住,手按下,“咔嚓”一下,定格地狱中最沉痛的一刻。而后,卓阳的手颓然地垂了下来。蒙娜用艰难的中文,表达意志:“这——是——证——据!”急救队的队员飞奔上前,抢救幸存的孩子。“那里有活口。”他们又不奔过去。卓阳看到了归云。归云蹲在地上,紧紧抱着自己的双臂,从脚到头,都在颤栗。他走近她,先舒了气,她是安好的。只是,受伤的人在他们的前方。归云霍然站起来,走过去。那片地上的伤者在哀号。“狗日的小日本鬼子——狗日的小日本鬼子——狗日的小日本鬼子——”嘶哑的声音是破的,拼了全力,从胸膛里发出来。他的半条手臂摔在头顶,和身体分离,半边身体浸在一片血水之中,眼睛紧紧闭着,半边的脸高高肿起来,灰红灰红的,身子在血水里痛楚地扭着。那嘴唇是干裂的,渗出血丝,一开一阖,还在叫:“狗日的小日本鬼子——”
司机一笑:“果然是很熟。”他们开始加速度,开到大道上。“你知道你的选择会怎样?”司机问卓阳。“一个不小心就被炸成人干。”“那么你还干?”“他们十几个人,我们两个人,我认路你开车,我们引开鬼子,天经地义。”
他对着轰炸机猛拍。司机把着方向盘开始咒骂:“狗日的,把咱们当猴孙耍。”果然呢,轰炸机是如影随形,像玩儿老鼠的猫,远处无天敌,就把这老鼠耍个够。
生离死别,痛苦这么一重重,箍得人透不过气。可儿子终于是回来了,还紧紧抱着她,任她责打。展风只盯着客堂间八仙桌上的父亲的牌位发呆。牌位是两只,一只上面刻着“先夫杜立行之位”几字。字迹他不认得,不知谁代庆姑和他刻了上去。他竟没为父亲做过任何事,连牌位都来不及安奉。这种诀别将他的心肝掰作了两半。他惭愧苦痛,“噗通”一声跪下来,磕头,猛磕。跟上来的归云归凤死活拉了他起身。“我没能好好照顾住你爹,没能好好照顾住你爹!”归云一边说着一边流泪,和身边的归凤又伏在一起痛哭。展风直挺挺站了半刻,又重重跪下,再磕头,这次谁都拉不起来,直到他的额头纹了起来也不停歇。“我没能找到班主的尸首!”归云哭道。庆姑醒了醒,红着眼发劲拉起儿子,嘶声:“展风,在你爹的牌位前答应我,等你爹七七之后立刻成家,和归云成亲!”她指着丈夫的牌位道,“你是杜家唯一的男丁了,这是你的责任!”
母亲还是万分不放心自己,常常备好点心送至报社。那日,他在拍摄涌入租界的难民们街头露宿的相片,忽就见弄堂里母亲和几个女童子军摆出了救济点,发米济困。“你爸爸把积蓄都拿出来。”卓太太说。卓阳哑口无言,万分情绪不知如何诉说!卓太太希冀地看着他:“别跟你爸爸闹脾气了,回去看看他吧!”他还是没回家,也负气也倔强,且还继续来了罗店。卓阳坐起身,回到庙里收拾了自己的行李,其实也就一件东西――相机。他准备最后再在这里拍一些相片,昨晚本要赶回市区,只因准备组织就近的陆家宅战斗的将军来布防了,他是景仰已久的,就留下来想做个访问。等到下半夜,这位蔡将军才姗姗来迟,身上有血迹,脸上有风霜,只是双目炯炯有神。
“国家形势如此吃紧,我爸他却一昧耽于个人安危!”卓阳对莫主编这样说。
它的速度忽快忽慢,低旋高飞,存心炫耀。最近落下的一颗炸弹,在他们身边的池塘爆炸,顷刻翻上满满一层鱼。卓阳咬咬牙,司机喝道:“是要把咱们炸成鱼干。”他倒郑重了,这司机这样谈笑风生,可不一般。手里的方向盘掌得娴熟,更懂怎么曲折迂回避开攻击。“听见上海空中的炮声,我自己只有欢喜。我觉得这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喜悦,我们民族有了决心要抗敌到底。”司机开口,吟哦两句,炮声真的在小汽车后面响起。卓阳收了相机,他也会。
“政商混沌,军阀乱战,这世间也只有自己一身一家可以保持清明!”卓汉书常常说,也这样做。可他养大的儿子偏偏老嚷着要去“兼济天下”。学生运动、政商联合、抗日活动一个不落,每每闹得他焦虑四和图书起,恨不能将他一条腿栓在家里不可。卓阳朝佛祖深深鞠一躬,法相森严,他觉得被注视了。他也希望被祝福,普渡众生的祝福。
“任云阁、阎海文,这次又是沈崇海!”他握紧自己的拳头。没有空防就没有国防!中国空军力量太弱了,也太小了。可是却壮烈。与敌人同归于尽是他们捍卫这片土地的最后的方法。他想起一上午的绝命狂奔,摊开手掌,将那张名帖收好。做过地上的人,知道那种恐惧蔓生,涕泗纵横的绝境。“谁同我去南站!”门被大力撞开,金发蒙娜冲了进来。她手里甩着报纸,海洋般的眼里是惊骇和恐惧。
“我们的武器或许不如敌人,但我们的民气和士气要超过敌人无数倍。我们并不怕绿气,不怕细菌,我们要以肉弹来把敌人摧毁。”司机笑:“小子,你竟然还是同道中人。”卓阳也笑:“这首诗从冯将军府上传出来,我专门听写下来给报纸发表。”
归凤的心跟着沉下去,终究还是抓不住展风。她掩了面,泪又在指缝里落下。
众人举头,空中渐渐起了“轰隆”的机声。卓阳极尽目力隐约望见远空里出现一架战斗机,从西北方飞来。是挂太阳旗的“灰蝙蝠”。他瞬间反应奇快,对展风说:“把蔡将军遗体搬出来。”展风还怔着,司机喝道:“快!”大伙都明白了,合力把将军的尸体搬了出来。卓阳对医护组的领队说:“这里往东边是农家,都搬空了,有几个谷仓底下挖了暗阁,可以避一避。”展风问:“你呢?”卓阳一下跳进车里,就坐在司机身边。“地形我熟,大家分头行事。”千钧一发,也不可再多思索了,展风背着将军的尸体,也有人骑着卓阳的自行车。大家同轰炸机抢时间。司机是个肃面的中年男子,他问卓阳:“你熟地形?”“我研究过地图。”“好,我们就搏上一搏。”“往西边也有一处农庄,庄子比较大,弄堂多,后面靠着小山丘,再过去就能过苏州河了。”
这话更骇人。归凤收了眼泪,欲发声,又憋着话,只把脸涨个通红,喃喃不出能半语。
她无暇顾及了,脱开他的手,与周围的搜救人员一起去扒挖那片废墟。虽然人们说着挖不出来了,但是挖掘的人还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那下面,是他们的亲人!但是一再努力的结果是只能看见被砖块和钢筋压住的衣服片迹。露出的一角衣袂,又眼熟,又陌生!也许正是那天她为杜班主缝补的那件褂子,也许不是。看得人恍惚了,分不清楚!
展风左手拉着归云,右手拉着归凤,就像小时候一起跳房子,跳在一间房子里的,同一个屋檐下的亲人,他把他的友爱均分给她们。对归云和归凤说:“我这个做哥哥的,老拖累你们。明日我不得不走,娘还是要托你们照顾着,等战事结束,我就回来。”他手里的温度也分给她们,归凤小心地贪恋。“你要小心。”望着他,万分不舍他,留不住他。展风的心里生了一团随战火越烧越勇的热气,腾腾而起,扑不灭,要冲天大烧一番。他走到客堂间,对着父亲的牌位又跪下来,重重磕头,还是一下一下又一下。这灭不了的怨仇,在身体里东窜西跑,狠狠啃噬他的心头,只有到了战火燎天的地方方可泄出来。“我们都留不住他。”归凤对归云说。归云默然,也黯然。奔腾的情绪,已是甩开缰绳的野马,在上海滩蔓延。
蒙娜说:“你看上去很累。”卓阳摆弄相机,零部件摔坏了,他在检修,确定还是能拍照的,心里一松。
归凤抹了把眼泪,说:“好,你做什么,我不拦着你,现在有你知心的来解难,你可以放心走了!”归云不解,望望展风。展风叹口气,他握住了归凤的手:“我何尝不知道你们的心,你们全指着我,为我尽孝,解我的后顾之忧。我老要你们担待我――”他放了手,向归云归凤深深作揖。归云归凤唬一跳,归凤更是哭也哭不了了,只凄凄道:“你这又何必?”
庆姑抓住儿子的手,不放过他:“好不好?你答应我呀!”还跺着脚,“我没什么指望了,我唯一的指望只有你——展风!”她的眼扫过在场的每个人,也压着每个人。她无处释放,唯此要求,歇斯底里的,挣扎出声。
一句话,莫主编便懂了。实习是个花差事,卓阳是卓家的命|根|子。卓阳听到莫主编对自己讲:“你年纪还小,凡事该多为父母想想。这次真是我给疏忽了,往后万万注意!”这一注意便是只给他跑一些家长里短的社会新闻。他自然知道是谁起了关键作用。那天在家里,他对父亲说:“我已有足够的行为能力为自己负责!”卓汉书却斜睨他一眼,好像还是在看一个七八岁的他:“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这才是正经!但凡我在一日,你给我万分保重,不可多生事端!安分守己些!”这位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沪上闻名的碑帖收藏家的思想正如他的职业和他的爱好一样,陈旧而停滞。卓阳是三代单传的独子,他父母的临终遗言便是万分保全这位珍贵的香火继承人。他就如此恪守。和-图-书卓阳气呼呼地冲出了父亲的书斋,回头望书斋的门头。门头上提着三个大大的颜体字——“独善斋”。卓汉书也写得一笔好字,尤善模仿。曾在兴致大发时将褚遂良的《圣教序》仿了一遍,竟有不少热衷收藏碑帖富绅愿出高价收购。但卓汉书毫不留恋地把帖子一把火烧了,他对卓阳说:“假的成不了真的,可叹我只能模仿前人而固步自封!”他是叹自己始终不能在书法上突破陈规,另出一脉,只囿于模仿古人而毫无创意。
展风骇着。庆姑耸着脖子,瞪着他。她非要他答应不可。他只好叫一声“妈”,不知怎生再说,或悲伤已压顶,无力再辩。庆姑却是精神涣散了,出口的话不成章法,突又道:“如果你不要归云,那么娶归凤!”
司机说:“这是一架侦察机,应当不会再往租界方向去,我把车开进农庄里,我们蓄机跳出去,再看各自祸福。”“好。”这是卓阳生平第一次冒险,且有性命之虞。时间那样短,他没有片刻思考的机会。那司机塞了一张纸片在他手中。“这样的朋友,我交得。”车在加速度,车门打开。司机瞅准了一处弄堂,卓阳也瞅准了,司机一把推了他下去。卓阳借了冲力,就地一滚,再看,车已飞驰向前,那轰炸机也跟着过去了。卓阳发力奔跑,四野旷寂,前方訇然一声,突燃了熊熊的火,浓雾起来了。他悚然一惊,想要看清楚,欲发步又止步。手掌被锐利的纸片划过。原来是一张名帖,上面有名字,叫“陈墨”。他再望向前方,那里浓雾更紧,腾腾而上,几乎遮蔽了那片天空。轰炸机高了,往北面去了。
“展风——”归云低低叫他。展风却仍继续:“罗店那里,到处是血。我只能抬着担架,把那些死的没死的战士们从火线上抬下来。我算是在做什么?我到最后连我爹都救不了?我算是个什么男人?什么儿子?我好想――我好想――”他嚎哭了。要顶天立地的展风,抱着头,蹲在地上,颤抖不能自制。从小到大他从不哭,这回,他哭了。
司机点点头,也算是遇到知音了。“如果今朝同你一起共赴黄泉,的确不亏本。”卓阳有片刻迷惘,却终是爽然一笑:“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
卓汉书也哈哈一笑:“我还供得起一个免费实习生!”并不是莫主编抠门,而是这份正经报纸确实经营困难,尤其是婉拒了几个有背景的团体公司入股要求之后。上海滩上的报纸,流行找靠山。靠上的,真是不缺金不缺银,只需要及时缺个德就成;不去靠的,除了不缺德,就真的什么都缺了!但莫主编还是支付卓阳的实习薪水,一个月两块大洋。他激赏卓阳的聪明,还有他的才。会美术又会摄影,这样年轻,又有思想,以及鸿图志。他乐意派他跟更好的新闻。然,就在卓阳跟了那回学生游行的任务后,卓汉书的德律风又来了:“老莫,我就一个儿子!”
蒙娜说:“听说现在已经开始救援了。”卓阳一把放下报纸:“走!我去。”秦编辑扯住卓阳:“你才刚回来,哪里有体力?”卓阳已发足随蒙娜跑了出去,她只得摇头,且听得二人急促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响起,“突突突”的,在上海的傍晚震出不安。这一天的卓阳,体力充沛得他都不自知。人被顶在关节上,不得不上,每个人都是被迫地。
前方隆隆的炮声传来,危险很近了。守备的战士肃然地跑进来。“卓记者,陆家宅那里在溃退,我们必须撤离。”卓阳心中一震,问:“我们败了?”战士面容沉痛而镇定:“蔡将军希望防区的记者和医护人员先退回安全区域里。”
归凤的一顿饭烧了很长时间,端着饭锅饭碗出时,双眼迷蒙而红肿,睁都睁不开。两人相视对望,各自无声。归云上前接过归凤手里的饭锅。“谢小姐讲展风他们现在被编进了急救组,她去打听他们的去向了。”归凤说。
这一仗,分外吃力。如果父母知道,势必会担心。父亲前一阵把话放到了报社:“如果卓阳十日内不回家,就在《朝报》上登脱离父子关系启事!”报社的记者编辑们听得面面相觑,都说这位父亲管着自己二十岁的儿子好像在管二岁的一样。
悲伤如何发泄?归云归凤带着一脸怎么都干不了的泪,连自己的悲伤都止不了,也劝不住两位已近崩溃的长辈。
她知道他想做什么,不能道破,更不能鼓励。一抬眼,是归凤责怨的眼,她便真的什么都不能说出口。归凤来了,说:“我们能做什么?好好守着这头家,不能再让长辈伤心,不能再让长辈有闪失了。你不是一向说要一家人好好生活在一起的吗?”说着也落泪了,她的眼泪没有止境地流,泪眼看住展风,“你不要再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了,打仗是当兵的事,你不要再掺合了。我们——我们再也受不住这些惊怕了!”展风起了决心,狠狠握拳,专注地看客堂间里,那正中摆的父亲的牌位,那么凛然地树立在那边。他站起来了。归凤一把推开了归云:“他已经昏头了,你看,你看!”www.hetushu.com•com归云一下没撑稳,跌坐到地上。“归凤——”展风一个字一个字对归凤说话,“我爹被日本人炸死了!这是血海深仇!家恨国仇!”他的脸上有异乎寻常的冷静和坚决,是一片哀恸之后已经无法动摇的决心。
归云在天井支了火盆,火舌东窜西窜,凶猛地吞噬下银色的脆弱的纸铂。最后化了灰,风吹云散。归云忽想,她竟还没为自己的亲爹烧过一张纸铂!她的爹,有张清朗风采的脸,总笑着,眉眼弯弯。她便是遗传了这张笑脸来,因此总能笑得动人。这张脸经过太多苦难,承受太多劳累,渐渐老了去。敛去笑意,凹陷了也严厉了,是杜班主,等于她的第二个爹。火盆里,烧的是双重的悲愁!她泪眼朦胧,看着这张脸隐入火焰中。泪又下来,流到嘴边,滚烫而咸涩,刺|激到被泪干住的脸。疼痛,由内而外。
归云见庆姑已经错乱胡涂得没边了,只得先一把挽住她的胳膊:“娘,您别再替他们操心了,好好睡一觉,一切都会好的!”“对对对,一切都会好的!”庆姑如小鸡啄米一般点头,喜笑颜开,“等明日一切都会好的。”一边说着一边被归云带去自己的房里。房里的展风却是急得抓耳挠腮,像热锅上的蚂蚁。时而看看不知所措地坐在椅子上的归凤,她低垂着头,把手上的他的衣服叠了拆,拆了叠,反反复复,没有停。“归凤——”展风很艰难地叫一声。归凤没抬头也没作声。“我妈这样做,实在不对,你一个姑娘家,你看――”归凤开口了:“这算什么对不住?我自小就是你家的人,如何安排自当听你家的话!”她那么温柔地抚他的衣服。展风皱皱眉毛。这叫什么话?归凤怎么能把自己的命交给他?他急了:“不是的,归凤,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你也有!”“展风!”归凤站起身,眼圈红了,“从小到了你们家,在这个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就是我最大的希望,这就是我的权利和自由。”她看穿了他要推却的心思,委屈死,也酸涩死。“娘这阵子受不住打击,她的话她做的事情,我们大家心里都有个度。你有你的想法,你想怎么做,我几时拦得住你?你何苦这样待我!”归凤憋牢一口气,却又泄了气,泪下来,在腮边,又苦又咸,还痛。真是什么念想都得不到。展风见她哭成霜打的芭蕉,更急了,不知道自己哪句话出了岔子。只一个劲说:“你、我、归云,我们打小什么样儿,现今还是什么样儿!我对你们的心,从没变过。”门“吱呀”一下开了,进来的是归云。“娘已经睡了。”归云晃了晃手中的钥匙,又见归凤哭红了眼,问,“怎么了?”
人人都觉得不妥,偏人人都不忍心说个“不”字。归凤望望展风,望一眼,又一眼。他站在那里,没有拒绝。她的心奇异地动了。这个家庭最悲伤的时刻,却是离她的朝思暮想最近的时刻。悲伤绝望里,又生出一点光,她望展风,就想要拢住这光。可光一斜,是杜班主的牌位。归凤难免生出锥刺的痛,醒了,走上前扶过庆姑:“娘,您别说了,去睡吧!”
有人破门而入,身上脏的,人也是脏的,汗血斑斑,目光呆滞,吓坏了归凤。
归云冷静地向救护人员交代:“他叫陆明,原住闸北。”她在忍着泪。救护人员点头记录,着手准备救护陆明。陆明突然有了力气睁开眼睛,无焦距、无希望、仰面望天。“啊——他们都被——候车室塌了,他们没有逃出来——啊——”归云跌跌撞撞往后退了一步,卓阳扶住了她。何老师同一名急救人员跑来,几乎是哭喊:“候车室下面埋的人,没有一个救的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搬开那些砖头!”地狱还有几层?归云狠狠掐住手臂,用力地让自己痛,因为痛了,她就不会就此倒下。这里有太多人倒下,她不能在这里倒下!卓阳握紧了她的手,她转头看他。是他呢!竟会是他?他又看到她这样悲痛的样子了。
黑夜里,火盆里的火焰更加耀眼。天上闪烁的星被乌云遮蔽,泛不出光,火盆是唯一的光,映出两条影子。卓阳看着归云的影子,肩膀一耸一耸,抽泣着。他很想伸手过去,搭住她的肩膀,让她不再孤单。但他只小指稍稍动下,又把手里的纸铂紧紧抓牢,几乎捏成团。就在夜里静默,只余火苗“咝咝”的声音。楼上悲戚到极点的女人们再一次嚎哭,用仅有的声音和气力干嚎。归云一直蒙脸流泪,她不知道卓阳是什么时候走的。他似乎就轻轻说了一句“好好保重”,然后就走了。她抬起头时连他的背影都没看见。
三个人,在一片悲伤里,各自流泪。归云最早醒来,勉力起身,要去继续支撑生活。她先做饭,将庆姑的那份送去了她房里。庆姑急促问:“展风去哪里了,不会上火线了吧?”归云不忍她伤心,摇了摇头:“他去医院看陆明了。”她喂庆姑吃饭,庆姑吃两口饭,心里的主意没丢下,又没头没脑,荒里荒唐道:“归云,你可别怪娘,展风不欢喜你,我不勉强他,他娶归凤也好,娘当你做女儿。” 归云听她m.hetushu.com.com竟还念叨这意思,不免担心的,就安慰:“娘,您只管放宽心,我谁都不会怪,只要您好好保重身子!”但庆姑还是惶惶的,头脑已混乱,最荒唐的事情也跟着做出来。晚上,她唤了归凤去展风房里送换洗的衣服,待归凤走进去,她便一下将展风的房门紧紧锁起来。“妈,你这是干吗?”展风没防备住,万分焦急地敲门。庆姑只说:“我不放心你们,你们今夜就给我圆房!”闻声赶过来归云傻了眼。庆姑瞪着她,恶狠狠威胁:“这样才栓得住展风那野猫子的心,他甭想往外溜!”
他睡了几个小时?一小时?还是两小时?睁开眼睛,看清楚自己身在一处古朴又简陋佛堂之中,佛像慈祥微笑,又俯瞰众生。除此以外,一切都很杂乱。破乱的席子随地都是,摇摇欲坠的窗楞大敞着。清风贯入,卓阳能看见窗外的密菁莽丛。他想起来了,这里是罗店的防区中转站,他是昨天清晨出发来这里,他临走时对《朝报》的主编莫华之说:“不去前线,不会有真实的作品。”他跑路跑的很快,莫华之在后面叫:“你今朝要给棉纺大亨王启德拍照片。”他装作听不到,他要去罗店。负气地,一力要去。卓阳想,父亲当初只是耍花腔一般历练他的意思,摇个德律风给昔日同窗莫主编:“老莫,犬子对摄像感兴趣,你那儿可有什么差使提供?”莫主编哈哈一笑:“我敞开大门欢迎,世侄爱做什么便做什么,只我未必给的出薪水!”
司机哈哈大笑:“好小子,这笔买卖做得。”卓阳掏出了相机,转头之前说:“而且绝不亏本。”他们全力以赴。卓阳调好焦距,对准越来越近的轰炸机。他想,就一架飞机,多半是侦查的,但是看到不明身份的交通工具,也会试探一番。只要进了农庄,有了障碍物,他们就容易脱身了。
卓阳却认为自己父亲墨守成规的不单单是在书法上。这“独善斋”只是“独善其身”的意思,所谓独善,不过善他卓汉书一身一家而已。
何老师何师母都上来帮着劝,最后也被勾出一脸泪。一屋子一堆女人只能让气氛更哀伤。
展风的脸,是疲惫而恍惚的,还有浓重的哀伤,已是木了。“蔡将军最后还叫着‘前进’。”又是平白的一阵风,卷得树叶呼啦啦一片响动,一阵一阵。是肃穆的,此起彼伏的,无法停歇的哀乐。小丁懵了,他一瘸一瘸,走到车前,把甘蔗重重扔在地上。他的双脚笔直蹬到地上,挺直胸膛。因为过于用力,那厚厚的白纱布上又渗出一星半点的红。但他不管,抬起右手,端端正正行出一个军礼!他声音嘹亮地答一声——“是!”卓阳颔首,致意。将军身上盖的是青天白日旗,可是,哪里是青天?哪里是白日?那白日中渗出的是中国将军的鲜血!“呜呜呜”的声音近了,刻不容缓,小汽车前排的司机探出头说:“快,你们找障碍物避避。”
“不累。”心中的念想只有南站。人行道两旁的树木,一棵一棵,飞快地消逝。终于近了,眼前荒凉的断壁残垣一座一座横亘过来。车被横七竖八倒下来的砖墙堵了去路,那两辆急救车也停在废墟中间,不能再近一步。有急救队的人正极力抢救伤员,也在安顿逝者。他们和时间赛跑,挽救生命,还要防备可能有的空袭。声声哀鸣和呻|吟!车里的人走出来,立刻就进了人间地狱,怔在当场。从断壁残垣的间隙里望去,入眼的是寸落的尸,伏在地上、零落的、衣衫不整、支离破碎。
他只留给卓阳一句话:“吾辈只有两条路,敌生,我死;我生,敌死!”
莫主编却摇头:“老卓为人虽然八股,但民族大义是有的!”他不知道,更不了解。或许真是如此。那十日,报社收到卓阳拍回来的前方后方积极抗战的各种相片;十日后,根本没收到卓汉书的断绝父子关系声明。卓阳想,也许是父亲默许了他的行为,心中带着的一点畏惧也稍稍松了。
归云惊呼:“展风。”展风已连爬带跑,一路上了楼。楼上的房间素白,坐在地上是瘫软的庆姑。展风一个踉跄,也倒在地上。庆姑抬眼,朦胧地看着眼前人,她爬过去,双手似鸡爪一般紧紧揪住展风的衣领,一头一脸都埋到儿子的怀里痛哭。“你不孝!没回来给你爹送终!”说完,一把泪擦在儿子的衫子上,又捶又打,又箍紧了他。
一条白色的手帕伸到她的面前,她接过来。递给她手帕的是卓阳,还是那身衣服,尘土满身,脚下黑色的皮鞋鞋尖被削了皮,破了,就要露趾。归云用手帕捂住脸,“呜呜”痛哭。卓阳拿过归云放在一边的纸铂,一张一张接着烧。隔着一盆火,蹲着的两个人,没有说话,一个埋头哭着,一个低头烧着纸。
走出寺门,仰望天空,一片开阔,云海连绵。这里地形未必好,后方有两个大农庄子和水田。田地已荒废,不适合做军用工事,好在前方有片未开垦的,高低不平的矮丛,都是密密长长的杂草。上海没有天险可守,日军也净捡平原无人烟处进攻。这里已经不太安全了,卓阳看到远处的流火和硝烟,是几天都没散
hetushu•com•com的。他时时闻到硝烟的味道。左邻右里张望着,同情着,摇头叹息,除了“节哀”再没更多能抚慰的话。
小战士扑过去,抱住展风问:“蔡将军怎么样了?”展风的面色凝重,低垂下头。他默默无言地将小汽车的后门打开。大家的目光转过去,那车后座躺了一个人,身上盖了旗,是一具挺直的身子,是一张闭着双目慷慨的脸,是一条已经牺牲了的生命!小战士愣了,看着那旗帜,和下面的人。旗帜上还有血迹,斑驳的,和霞光一样红。
卓阳无话,且动作有素,他准备好了。他知道他得遵守命令。战斗又开始了,撤离的人也是在搏命往回赶。卓阳有自行车,但是他断后。医护人员、输送队员和战地记者,不过才十来个人,男人护着女人,女人护着伤员。有个护士扶着一个包扎好腿脚的小战士走,男孩剃着青亮的头皮,不过十五六岁,手里拄着甘蔗做拐杖,一瘸一瘸。他问护士:“杜大哥一会儿就该回来了吧!不知道蔡将军怎么样了!”护士说:“蔡将军壮得很,一定打的鬼子哇哇叫。”小战士扭头望陆家宅的方向,很不甘:“我太不中用了,我得快点养好伤,再跟蔡将军杀到宝山来。”卓阳笑了,见护士弱质,他上来撑了一把手,要小战士上他的自行车。“上来,快走。”他有经验,远处“隆隆”的声音在逼近。他想,阵地可能崩溃了,心头乱了,步子却不乱。
庆姑由她扶着,还是转头看展风。展风始终低头,默不作声,她就变得可怜了,小心细声问:“那么,妈当你答应了,啊?”展风还是没作声,同归凤一起扶了庆姑进房。他们都默默地,安顿庆姑入睡。不发一句声响。他忍不了心,对母亲那般的乞求说个“不”字。只能望着归凤欲言又止。悲伤似乎是暂停了,杜家的东西厢房和客堂间都变得静悄悄。展风避开了归凤,同归云在晒台上烧纸铂。这些日子,除了战火便是这些纸铂,一直烧个不停。“娘已经歇息下来了?”归云问。展风只低头,将银色纸箔化入火焰中。“我们只能给班主做衣冠冢——”归云话未完,就见展风的手捏着纸箔愣在火焰之上,火苗窜上来,归云抓住他的手腕甩开那着火的纸铂。“你知道那些战场上的军人都是怎样打仗的吗?他们拿着自己的身体往敌人的枪眼子、刀尖子上堵,倒下来,后面的兵就地填上去。”展风犹自未觉得痛,就这样对着归云说话。
没有头的人,断了手足的人,内脏流满地的人。一个伏着另一个,是在死亡时的互相依靠,又有孤零零挨在一旁的,至死都没有找到依靠。蒙娜被空气里弥漫的血腥气冲入胸膛,弯腰一阵狂呕。卓阳微微开阖着嘴。他是彷徨的,是沉痛的,是无可奈何的,是痛彻心肺的。太多太多的情绪。
卓阳冲过去抢来看,是今日的《朝报》。“昨日日军轰炸我市南火车站,轰炸当时,约有三四百老弱妇孺候车。因战火封锁,死伤情况不明,我市医疗救护队将在今晨突破火线出发援救,但一直无法接近现场——”
何老师是这屋里唯一的男人,有一些主张,这时刻也就不顾其他,一管到底,提笔写了牌位,又作主唤归云出去烧纸铂,叫归凤去灶庇间做晚饭,方分解出凝聚成团的哀泣。
卓阳在一片阳光的照耀下醒来,他的半边脸,被刺痛。揉一揉眼睛,用手撑住额头。
卓阳转个身,捏紧名帖,往那方向奔去。但走不近,他捏紧相机。他不能!他拍这些照片干吗?除了留住那一刻的壮烈,他什么都抓不回来,也无法决定结局!连日来,他在战火纷飞里奔走,拍了很多照片。他总在想,我能挽救他们即将逝去的生命吗?能让这场战争胜利吗?卓阳狠狠闭上眼。一切都是徒然的。无法,只好先向南方奔逃。千难百险回到报社已是傍晚,留守的秦编辑正守着火盆烧纸。莫主编没有卓汉书那样八股和守旧,但在八月十三日之后,他在报社里支了火盆,买备大串大串的纸铂。每天都烧,每时都烧。他说要给在前线阵亡的将士们送行!火盆前还有有竹片刻好了牌位用来奠。“这次是空军第二大队的沈崇海,他在杭州湾上撞了‘出云号’(日军战舰)。”秦编辑告诉卓阳。卓阳根本已疲惫不堪,此时心里又一震。又是一位自撞敌机的空中战士!
小战士也是知道的,闭口了,跳上他的车,一行人疾速地往回赶。风飒飒,阳光高了,人人都是满脸的汗。有一小队人近了,他们开着小车。小战士兴奋地叫了声:“杜大哥。”车戛然停在他们面前,卓阳认得下来的一个年轻人,是归云身边的杜展风。
石库门里的悲伤也在加倍。两个新近丧夫的寡妇抱头痛哭,捶墙顿地,无所可依。
他们仍不放弃,再到生还者里面找。一直到不得不绝望!绝望到了深夜,夜晚又要无眠。石库门被逃难的人们挤得丝毫没有缝隙。厚的隔层墙板,薄的隔层木板,再薄的就只隔层帘子,人们一家紧挨着另一家。悲伤迅速传递和蔓延。日晖里的人们里都知道了那家唱戏的男主人死在南站,连尸首都没能找回来。